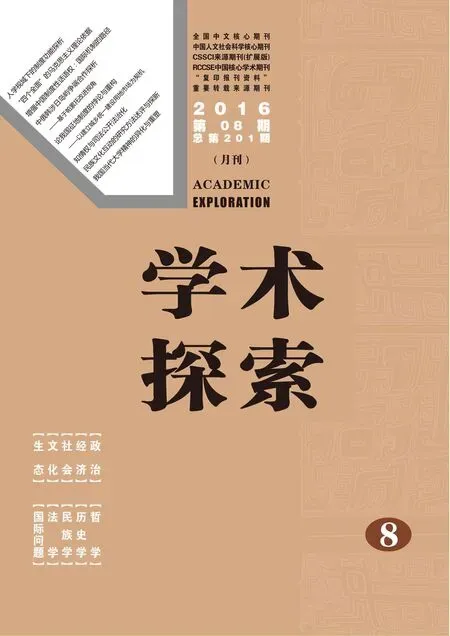滇西地区沿边产业带形成的企业集聚条件分析
陈 瑛
(云南大学 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滇西地区沿边产业带形成的企业集聚条件分析
陈瑛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沿边开放深化的新背景下,一度边缘化的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区位因素的重要变化意味着滇西沿边地区的企业集聚方式将发生变化。本文综合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与“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观点,认为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集聚是滇西沿边产业带形成的决定性条件,但这一地区还未能形成具有强“外部效应”的企业集聚,需要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改变区位优势推动企业集聚形成沿边产业带。
企业集聚;马歇尔;外部性;国际折中生产理论;滇西沿边产业带
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到地理中心的附近,集聚与区位会产生收益。分布我国西南的滇西沿边地区远离国内区域经济中心,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8个州中就有6个州市与云南省经济中心昆明的陆路距离超过了400公里,与国内经济中心的陆地距离如到上海的陆路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到出海口的距离超过了1000公里;而作为内陆边疆地区,毗邻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一体化水平仍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远离国内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与国际主流市场,处于边缘的空间结构,这制约着企业集聚并约束了产业发展。扩大沿边开放,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改变着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特征,实现这一地区的区位再造是建设沿边开发开放实验区的必由之路。重组与构建区位优势中的各要素,通过价值链与生产网络在空间上的重构,强化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促进沿边产业带的形成,是这一地区区域再造的客观选择。然而,区域自身的特殊性,尤其是远离国内经济中心的空间区位,意味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区域内部的企业集聚与沿边产业带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 企业集聚与沿边产业带形成的经济逻辑:企业套利空间的转换
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滇西地区既是我国经济上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具有较大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临近于东南亚国家的滇西地区资源富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地处边缘远离我国经济集聚中心使其发展长期滞后,随着扩大沿边开放战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的建立,滇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态势见长。工业化历史表明,区位和经济的区域模式尽管具有某种保持不变的倾向,但从长期来看会发生重大转变,区位因素的意义会发生重要变化。在扩大沿边开放战略的新背景下,沿边地区构建产业带,特别是在与周边接壤国家区域建立产业带是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发展的新契机。
(一)产业带形成的实质:企业集聚
企业集聚是指相互关联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和机构基于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大量聚集于一定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产业带实质上是众多企业因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递增而在某一确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结果。一个地区产业带的形成是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企业空间集聚实现的,特别是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倾向于集聚于特定区域,能引起企业集聚的原因,同样也是产业带形成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第三意大利”现象的出现引起国外学者关注于企业集聚的研究。所谓“第三意大利”是指意大利境内的东北地区与中北部地区,该地区在20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增长要远远高于意大利境内的其他地区。学者发现这一时期“第三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区域内部众多设计和生产轻工业品的创新性中小企业的空间集聚,资金、技术、市场、供应网络和地方政府等要素不是“第三意大利”兴起的前提,而是其成长后的产物。[1]此外,在印度也存在诸如此类的企业集聚,如旁遮普邦的路德海阿那的金属加工和纺织工业群、泰米尔纳德邦的提若普尔的棉织衣物制造业群、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的钻石加工业群、卡纳达卡邦的班加罗尔的电子软件业群、北方邦的阿格拉的鞋业群等。
那么企业为什么集聚呢?早期学者如韦伯(1997)、[2]勒什(1943)、[3]艾萨德(1990)[4]等认为通过拥有优势资源禀赋的区位进行选择而引起企业集聚。当资源性产品难于运输和减轻重量,难以集约使用劳动力和资本时,靠近自然资源产区,或者运输便利程度高,企业获得的利润率因此递增,资源禀赋可得性会使得经济活动异常集中。Ellison和Gleaser(1999)[5]把美国各州的就业量作为集聚变量,用来解释自然资源对集聚的作用,解释能力为20%左右,自然优势在集聚中的重要性得以证实。传统的区域发展和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的假设下基于资源禀赋学说讨论了企业聚集的原因。因此早期研究表明资源禀赋优势给企业带来的获利空间是企业聚集的主要动机。
但是,这些解释与分析无法应用于那些较少依赖于自然优势形成的企业集聚。马歇尔(1920)[6]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的角度阐释了企业集聚的来源,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一是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集聚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三是集聚使得企业能够从技术溢出中获益。后来的学者将其总结为投入共享、劳动力共享及知识溢出。“马歇尔外部性”理论表明企业集聚是源于生产过程,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区域内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专业化技能的集中,促进区域的外部性。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讨论了企业聚集的原因。强调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在促进贸易和专业化方面的作用。收益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者是产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Krugman,2001)。[7]规模经济及其外部性将资源禀赋劣势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改变为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区域和地方经济的集聚。
在现实经济中跨境或边境经济合作区是边境地区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途径,国内外学者对典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如美墨边境地区、欧盟一体化等展开详细的研究,并论证了边境地区能否具有形成企业集聚的条件。美墨边境地区的发展演变表明,尽管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减少企业集聚的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水平,成为边境地区企业集聚的必要条件,但早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没有带动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发展,只有随着北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才吸引了众多企业在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区集聚(Krugman and Hanson,1993)。[8]作为一个较小的经济体,墨西哥边境地区的企业集聚源自于NAFTA使得墨西哥能够自由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特征事实。事实上,墨西哥曾依托NAFTA实现大约10年左右的贸易增长,之后相互之间的贸易增长动力才开始明显减弱。欧盟则是依靠不断扩充新成员维系其内部的贸易增长。早期对欧洲边境的研究发现,企业集聚现象发生在国家内部层次上,属于国家地理的空间层次(Giersch,[9]1949);后期的研究发现企业集聚出现在了边境地区,其中对德国—波兰边界区域的研究认为边界障碍的清除有利于增加区域之间的企业贸易关系(Stiller,[10]2002);不但如此,边境地区企业间的经济关系还能决定这一地区企业集聚的前景,对进入边境地区的生产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还是融入区域大市场。对东亚增长三角的研究也表明,在边境地区吸引企业集聚并形成增长中心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与动力机制。其中,前者包括经济互补性、地理邻近性、空间可达性、(适宜的)制度安排等;后者包括区位指向、扩散机制、空间近邻效应、区际分工、国际组织的协调与推动等(李秀敏,2003)。[11]从这个逻辑出发,无论是基于理论推导还是基于现实经济的考虑,边境地区具备形成企业聚集的可能性。考虑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国家均为欠发达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这一方面意味着边界两侧地区发展是非均质的,呈梯度分布,*如中国与GMS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梯度性,黎鹏(2006)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进口总额、出口总额、旅游入境人数七项指标测算后表明,中国与GMS地区的经济梯度分布为:泰国为第一类,广西、云南、越南为第二类,缅甸、老挝为等三类,当中,越南实际利用外资得分远远大于泰国、广西、云南省得分。相互之间的资源、产业与技术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边界两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产生的交易成本制约商品、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跨界流动和延伸范围。这片地区的企业集聚将更为复杂。
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到企业集聚的微观基础重要性,集聚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表明,资源禀赋带来的利润增加是企业集聚的基础性条件,但是“马歇尔外部性”所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改变了资源禀赋的约束成为企业集聚的重要源泉。将这一理论用于分析滇西沿边地区的企业集聚时,建立经济合作区是改变这一地区因地理因素减少企业获利空间的重要举措,将资源禀赋优势与规模经济外部性相结合才能推动企业集聚。
(二)沿边产业带形成的约束条件:边界与空间
滇西少数民族所涉及的八个州市处于沿边地区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资源富足,气候宜人。特别是,靠西与缅甸接壤的德宏与保山地区,石材与林木资源较为富裕;临近东部与越南接壤的文山与红河地区,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间位置分别与缅甸、老挝接壤的普洱、临沧与版纳,茶树资源历史悠久、保护良好。这些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接壤,富足的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并未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据2013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云南25个边境县中,有17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边境地区人均GDP在全国7个沿边省区中最低。
研究经济开发区的印度学者Aggarwal(2011)[12]认为国与国之间边界的存在往往会改变边境区经济和政治活动,并引起制度在边境地区嵌入的脱节。这种因经济空间性与政治属地的差异,将边境地区的市场网络分割成另一个自然的经济空间,将边境变成地理上的边缘区。尽管边境地区往往不会在资源可用性方面具有相对弱势,但他们不会吸引生产活动。他们以非正规的、短期的及投机性的价格差,吸引着“套利”或“小商品市场(bazaar)”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从交易税和价格差异,到走私和非法移民等范围是以边界的存在为基础。因此,在经济方面,边境地区通常是低质量发展的典型地区。
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经济活动往往倾向于集中到地理中心的附近,区位和集聚会产生收益,主要表现为降低运输成本、素质良好的和高收入的劳动力、服务于不同产业的设施在理上的集中。Christaller(1935)[13]在其中心空间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中提出效率最低的地区是指相对交通要道、市场和社会政治因素而言的国家边界附近。A·Losch(1954)[14]强调政治边界的负面作用,即边界产生了市场空白并阻碍了产业在边境地区的区位选择。他认为,政治边界是比经济界限“更严格”而且是“通过关税、法律、语言、社会等更为明确的界定”。但运输成本对边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边境地区难以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区进行物资运输主要是因为到中心大城市的距离太远。根据早期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学家Dunning(2001)[15]的观点,企业国际经济活动的三种方式出口、技术转让与国际直接投资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影响,当企业具有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的时候,企业选择出口,只有当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企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更有利。从区位优势来看,尽管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滇西地区人口密度偏低,可用劳动力数量实际上是受限的,同时边界的存在及处于国内中心地区的边缘地带,且周边国家均属欠发达或最不发达国家,这一地区缺乏市场潜力,加之贸易壁垒较高,受相邻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较大,没有足够的区位优势可以利用;尽管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相比国内发达地区发展滞后,但在国内及省内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及影响下,与周边国家相比,这一地区具有一定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与交易性所有权优势;而从内部化优势来看,这一地区的规模较大企业多为国内内陆地区的分支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内部化优势。
因此,早期进入或历史上存在于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的企业往往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优势,通过可贸易品的交易获利,由于交易成本的畸高、边境地区的边缘性,以及跨境资源互补利用的高壁垒,选择这些区位的企业更愿意从事国际贸易或边境贸易,正是如此,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多数表现为“三、二、一”的特征。沿边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及丰富的水热光农业资源优势,为沿边地区粮、糖、茶、烟、果及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沿边地区农林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样利用资源优势,少部分地区的工业得以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但沿边地区二次产业是以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产品制造加工能力弱,产业链延伸有限,产业增值能力弱,制造业对沿边地区的贡献小,沿边地区整体上尚未实现工业化;而沿边州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这与沿边地区地理特征、资源开发、边境贸易比较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特色农业与商贸相关的贸易业作为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的重要产业之外,工业产业表现为国内市场原材料的供应商而存在。
边界的存在与空间上远离国内中心的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吸引了贸易企业进入。目前,尽管边境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已开展以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为主的边境贸易,然而以边境贸易为主体的口岸经济与通道经济尚不足以推动边境地区的企业集聚。显然,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推动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边境地区聚集。什么条件下能够在边境地区形成产业集聚?以Krugman为首的经济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三个主要因素通过市场传导相互作用而生成的,缺少任一方面,产业集聚就不会自我发生、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由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较低的产业聚集水平使得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缺乏,加之“边界”的存在产生了“屏蔽效应”并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要想加快地区内部的企业空间聚集,一方面需要加快国际大通道建设并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推动企业在边界两侧集聚。
沿边开放深化的新背景下,拥有面向“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一度边缘化的云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区位因素的重要变化意味着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的企业集聚方式将发生变化,通过边境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特别是通过边境地区市场的城市化突破边界的约束(胡超,2009),[16]改变边界这一空间因素的制约性,利用“马歇尔外部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而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这一地区。在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同时具备的条件下,区位因素的转变将促使企业不仅仅以贸易的方式在这一地区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将催生更多的企业直接投资于沿边地区,这有利于企业生产网络的建立,将通过贸易获得因区域间商品价格差异带来的利润,转变为通过生产规模扩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利润来源,这也正是企业集聚进而产业带形成的重要转变。
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马歇尔认为“外部性”是企业集聚形成的原因,前述分析集中于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及边界的空间因素等对企业集聚的影响与制约条件。然而,许多研究表明,“非经济性”因素尤其是企业家的偏好、当地的经济环境与政策激励,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而且除了制度创新以及企业组织演变以外,区别于其他区位的某些因素禀赋和人文特征,将是区位形成的重要条件。因此,要通过企业集聚来构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沿边产业带,并以此为基础重塑区域经济地理,就必须探讨沿边产业带构建中这些非经济因素给企业空间聚集带来的挑战。
从企业集聚的视角来看,尽管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是自由市场与政策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影响因素仍然包括空间区位条件、人文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因素、资源禀赋、政策因素、产业分工、技术条件与其他因素等。其中,空间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因素、资源禀赋状况为企业集聚的硬件因素,而人文历史因素、政策因素、产业分工、技术条件等则属于企业集聚的软件因素。在空间集聚的过程中,技术条件、政策因素、产业分工对企业集聚的发生起到了诱导作用,是企业集聚的前奏;当企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地方政策的政策、历史因素、地理因素、资源因素则能够促进企业聚集的快速形成,是企业集聚走向成熟的保障(图1)。
从上述逻辑出发,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企业集聚的因素不但体现在空间区位条件、人文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因素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产业分工水平、技术能力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第一,在空间区位条件方面。地理因素是影响企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纵观国内外的企业集聚,处于地理优势的区域往往都比处于地理劣势的区域更容易形成企业的空间聚集。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片区域不但位于我国经济最不发达地区,其经济密度要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密度;而且位于我国边境地区,拥有4060公里的国界线,其经济要素在区域外部的流动性也要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的流动性。需要强调的是,边界尽管减弱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但在沿边开放战略下,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由发展的后方转化为发展的前沿,并日益成为联系国内经济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经济的枢纽与桥梁。从这个逻辑出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集聚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优势。
第二,在人文历史因素方面。纵观国内外企业集聚的形成,工商业的观念、人文环境、市场氛围、创新意识、产业经验等因素都会对企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逻辑出发,历史因素在企业集聚过程中也十分重要。然而,就滇西沿边地区而言,多数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区,且云南省的国家贫困县大部分分布在这一地区,长期以来这片区域的商业意识、市场氛围、产业经验就严重缺乏,根本就无法与我国江浙一带的“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的历史传统相比。事实上,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末期或者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这种封闭的经济体系根本就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市场意识与竞争意识。虽然全国层面的改革开放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这片区域,但作为“直接过渡区”,这片区域的市场观念、商业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仍然十分薄弱。
第三,在基础设施方面。纵观国内外企业集聚的形成,包括交通建设、通信设施、电力、能源、水利等硬件设施以及大学、科研机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软件设施,都能对企业的空间聚集产生重要影响。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片区域本就位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的地区,对基础设施的供给要求甚高;尽管近年来这片区域内部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已得到了全面的改善,但水、电、路、气等硬件设施仍然十分薄弱,部分地区甚至还没有解决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与住房问题;加之部分地区的卫生条件落后、广播和电视覆盖率低、中等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等,这片区域的基础设施不但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而且还远远满足不了企业空间集聚的要求。以一般意义上的硬件设施为例,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体系仍然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等其他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
第四,资源禀赋方面。资源禀赋特别是自然资源对集聚的重要性受到学者与政府的关注由来已久。前述国外学者发现自然资源对决定集聚进程有重要影响。滇西地区七州市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电资源、生物资源,但是,滇西地区集中发展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低,资源禀赋并未能转化为集聚优势,反而成为“富裕的贫困”。
第五,在产业分工方面。由于产业分工不但能够促进产业内异质企业由竞争走向竞争与合作,而且能够提升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效率并促进专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产业的分工水平是促进企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产业分工主要体现为产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水平分工,以及产业内部的行业分工,即如第一产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的行业分工,第二产业内部的轻工业、重工业、建筑工业的水平分工等,第三产业内部的教育、商贸、物流等的水平分工;产业内的垂直分工,如制造业从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组装、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价值链条的垂直分工,种植业从种植研发、种植、收割、销售等的垂直分工仍然严重不足。
第六,在技术能力水平方面。企业的空间聚集既能够提升区位内企业的技术能力、促进技术创新并提升区域的技术能力,但区域内部的技术能力水平也能够影响企业的空间聚集,二者之间是互惠共生、彼此影响的关系。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无论是区域内部企业的技术能力,还是整个区域的技术能力,均要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能力;不但如此,区域内部的创新意识不足、创新动力不足、研发投入不够、技术产出效率不高等问题也较为突出,这不但会制约区域自身技术能力水平的提升,而且会深远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聚集。
第七,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金融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等,这些政策对企业空间集聚的宏观大环境有重要影响。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片区域享受企业集聚的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正如在前面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享受中央政府、云南省政府等各级政府的各层次、更类型的优惠政策叠加,其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要远远超过东部沿海地区目前能够享受的程度。
空间区位条件、人文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产业分工水平、技术能力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不可避免会强化或消解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集聚。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企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的影响。首先就企业集聚的激励因素而言,技术能力水平低下、水平分工为主的产业分工等异质性特征明显不利于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在云南省内的竞争。事实上,目前云南的经济集聚仍然集中于以昆明为主的滇中城市群内,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有部分企业集聚,但仍然无法做到与这些区域的企业全面竞争。其次是就企业集聚的分散力因素而言,空间区位的要素流动受限、人文历史因素中的商业与市场意识匮乏、基础设施的全面落后等异质性特征也不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稳定的企业集聚。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企业集聚仍然表现为特定区域内部企业的简单聚集,即不是按照产业的分工与协作、经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等方式建立,而是将所有产业的所有企业进行简单的空间堆积。以瑞丽开放开发试验区的姐告为例,作为享受“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姐告边境贸易区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管聚集大量的企业,但这些聚集企业涉及轻工业产品的加工组装、商贸物流、边际贸易、农副产品销售等行业,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与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也远远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本文认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异质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构建区域企业集聚的形成机制,而且使得区域内部已有的企业集聚呈现出脆弱性特征。
第二,各影响因素造成区域之间构建企业集聚的恶性竞争。由于企业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推动形成区域增长中心,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各个州(市)都十分重视区域内部的企业集聚。然而,由于这片区域的空间区位条件、人文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产业分工水平、技术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都不利于形成企业的空间集聚,各个地方政府则将企业空间集聚的着力点转向了政策干预,即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吸引企业投资并以此推动企业集聚。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片区域在整体上都能享受中央政府、云南省政府的各种叠加的优惠政策,但为了强化竞争优势并吸引外来投资和企业入驻,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各个州(市)仍然在土地、税收、环保等方面出台了特别性优惠政策,有些地州甚至不遵循土地的价值规律并以牺牲生态环境等为代价招商引资。因此,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异质性特征使得这片区域的企业集聚更多是强调政策的优惠幅度,而不是各个州(市)的资源禀赋与产业特征,这就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区域之间构建企业集聚的恶性竞争。
三、滇西少数民族地区企业集聚与沿边产业带的兴起
正如在前面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集聚效应与专业化是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主要驱动力。由于企业集聚不但有助于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而且能够推动沿边产业带的形成,因此企业的空间集聚能够重塑区域经济地理。具体而言,企业空间聚集与沿边产业带对经济地理重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区域经济密度,并有助于缩减任何类型的距离因素。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企业集聚所具有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能够扩张并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地方市场,而市场扩张又能够显著降低运输成本并缩短经济距离,企业集聚自然有助于缩短各种类型的空间距离。以企业集聚的知识共享为例,共享增加企业之间知识与技术相互溢出的可能性,其产业距离也就自然而缩短。不但如此,由于企业内部的空间聚集还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再加上沿边产业带的扩散与辐射效应,这些均能够强化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生产—投入—产出之间的联系,并促进生产效率与经济密度的提升。事实上,经济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各类型的经济集聚区,如城市的经济密度就要远远高于农村的经济密度,大城市的经济密度就要高于中小城市的经济密度。
对应于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的资源分布,与缅甸接壤的德宏与保山已成为全国玉石资源的集散地,与越南接壤的文山与红河自古以来就有矿产企业生产,现成为全省矿产企业的集中地之一,而与老挝、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普洱与临沧因其普洱茶资源的特殊性,现已成为全国普洱茶叶的重要产地及集散地。这一事实表明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中企业是沿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而呈现集聚的。自然资源禀赋是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企业集聚的首要因素,但是这些企业集聚存在以下特征:第一,集聚的企业主要从事初级产品加工,如珠宝玉石行业,早期主要以原料的贸易为主,即使现在原石加工业得以发展但深加工部分依然在外;如普洱茶产业。第二,集聚的企业多数以贸易套利为主,利润极为不稳定,但利润空间较大。第三,集聚的企业风险意识更强,具有开放意义,善于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优势。第四,集聚企业的产品以国内需求为主。
在扩大沿边开放的新背景下,仅仅利用资源优势的企业集聚不再满足现有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特征在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瑞丽开发开放实验区与红河综合保税区的成立开通了滇西地区陆路开放的通道,这意味着Dunning(1977)[17]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区位优势正在形成,为企业创造以投资而非贸易方式进入这一地区创造了条件。其次,利用资源优势的贸易性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市场波动使原来资源优势带来的高利润空间变得不稳定,单纯从事贸易可获得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如玉石产业,近年来缅甸公盘的原石价格攀升,瑞丽地区的玉石产业生产成本也因此大幅上升;再者,随着中国近年沿边开放政策的大幅推行,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需要更多的全产业集团替代原有的企业集聚类型,企业的产品性质发生较大变化,企业规模效应正逐渐显现。最后,区位因素的改变,产品的交通成本发生变化,更多生产性企业开始选择落户于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如银翔摩托、北汽集团、安琪酵母等。
沿边开放的新背景意味着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正在突破边界与空间的束缚,产生企业集聚的向心力;企业生产的“外部性”效应也正成为新的动力与资源禀赋的优势共同带动沿边地区的企业集聚;以前众多仅从事贸易的沿边地区的企业正向集生产、贸易于一体的企业转变。通过沿边开放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削减边界产生的高壁垒与高交易成本,改变企业集聚的类型,正是滇西少数民族沿边产业带兴起的表现,最终改变地整个地区的区位特征。
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集聚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产业带形成的决定性条件。但是,这一地区产业分工水平偏低,要素流动受限、人文历史因素中的商业与市场意识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使得区域内部已有的企业集聚呈现出脆弱性特征,制约着沿边产业带的形成,因此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企业集聚仍然表现为特定区域内部企业的简单聚集,不是按照产业的分工与协作、经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等方式建立,而是将所有产业的所有企业进行简单的空间堆积;注重本地内部企业集聚予以多重优惠政策的方式,使得这片区域的企业集聚更多是强调政策的优惠幅度,而不是各个州(市)的资源禀赋与产业特征,这就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区域之间构建企业集聚的恶性竞争。
尽管存在上述的问题,滇西沿边产业带已初具雏形,根据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集聚,滇西少数民族沿边产业带还未能形成具有较强“外部效应”的企业集聚,在规模经济效应、差异化产品的替代、较低贸易成本(含运输成本)以及技术知识溢出效应方面远远不够。滇西少数民族沿边地区发展的沿边产业带不会自动地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需要更为有力的外部条件予以支持,滇西少数民族地区沿边产业带的形成需要在边境的领土基础上推动生产网络的全面整合,而非仅仅增加跨境贸易。从必要条件来看,需要通过与国内大企业联合创造更强的所有权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内部化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的内部化。从充分条件来看,需要改善形成区位优势的条件,首先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支撑企业的发展;其次需要更好的贸易环境与良好的周边国家国际关系环境以有利于滇西沿边地区的企业挖掘这一地区的市场潜力;再者需要更为有效的投资与贸易激励政策以促进企业的集聚。
[1]秦岩,杨爱民,代志鹏.第三意大利的兴起及其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07,(6).
[2]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3]奥古斯特.勒什,经济空间秩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4]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5]Ellison,G. and Glaeser,E. L.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311-16.
[6]Marshall,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Mc Millan,1920.
[7]Krugman,P.Rethinking InternationalTrade[M].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2001.
[8]Krugman, P. and G. Hanson,“Mexico-U.S. Free Trade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M].In Peter Garber, ed.,The Mexic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MIT Press,1993.
[9]Giersch H. Economic union between nations and location of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49(17):87-97.
[10]Niebuhr, A. and Stiler, S.(2002), Integration effects in border regions. A surve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79, Hambu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ambourg.
[11]李秀敏,刘丽琴.“增长三角”的形成发展机制探讨[J].世界地理研究,2003,(1).
[12]AradhnaAggarwal(2010), Economic impacts of SEZ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analysis of newly notified SEZs in India, MPRA Paper No. 20902, http://mpra.ub.uni-muenchen.de/20902/.
[13]Christaller (1935). Walter Christaller.RuthHott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 73, No. 1 (Mar., 1983).Christaller, Walter (1933): Die zentralenOrte in Süddeutschland. Gustav Fischer, Jena
[14]A·Losch.区位经济学[M].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54.
[15]Dunning. J. H., (2001)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Vol 8, No.2.
[16]胡超.突破边界效应: 城市化与边境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以中越边境为例[J].国际经贸探索,2009,(8).[17]Dunning, J.H.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and Wis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London, 395-419.
〔责任编辑:黎玫〕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on the Industry Belt of Western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EN Y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opening up in the borders, Yunnan province becomes an important area in the strateg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important change of location means the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along the border areas of Yunnan will be changed too. Based on the OIL paradigm and Marshall’s externality theory, we argue that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with the scaly increasing returns is decisive to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 belt in these areas, but due to lack of strong “externalities”, the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fails to promot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se area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he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location advantage changed to promote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in the borders of Yunnan province.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Marshall’s externality theory; OIL paradigm; industry belt in the western areas of Yunnan
云南大学第四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XT412003)
陈瑛(1972— ),女,云南陆良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F127
A
1006-723X(2016)08-00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