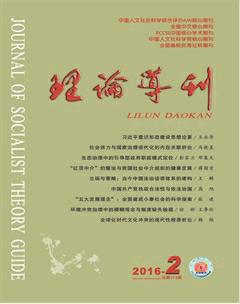协商民主: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应然选择
罗洪+刘纯明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包括农村居民经济上的宽裕,又包括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西部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社会分层进程逐渐加快,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关调研表明,当前农村的精英阶层在政治参与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和种地农民则成为弱势群体,在当地政治参与中处于边缘人的位置。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关注“平等公民的理性对话”,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结合实际引入这一范式,使之与选举民主相互衔接,有助于推动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良性发展。
关键词:西部农村;社会分层;政治参与;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67-04
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中央政府的这一系列“组合拳”推动了西部农村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快速发展,西部农村社会随之急剧变迁,日益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有关调研表明,[1]西部农村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在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富人治村”和“群体性事件”。我们希望引入协商民主,推动其与选举民主的衔接以缓解上述问题。
一、政治认知与存在问题
关于西部农村居民各阶层政治参与现状的研究,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四川省三台县S乡是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S乡具有远离县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商品经济不发达等外显特征,在西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2013至2015年寒假,课题组连续三年对S乡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S乡各阶层对政治参与途径、选择乡村干部的标准、选举程序和法规的认知等。
政治认知是产生政治行为的先导,它为S乡各阶层参与乡村政治生活提供了行动依据。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其一,S乡各阶层政治参与途径。乡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是选举民主所产生的两大渠道,即村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农民工和种地农民阶层选择利用“新闻媒体”来表达政治诉求的比例相对较高,他们认为这种参与途径相对有效。其二,选拔乡村干部的标准。S乡各阶层所认可的乡村干部标准排序如下:第一位是“经济能人”。在贫穷的S乡,脱贫致富是大多数阶层的共同愿景;第二位是“办事公道”。农村进入现代化转型以来私人利益凸显,各种民事纠纷上升。其三,对政治参与法规和程序的认知。除乡村管理者阶层之外,占S乡人口大多数的其它阶层,对支撑乡人大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支撑村民自治运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保障基层民主最为重要的法规的认知情况令人堪忧,大部分农村居民对民主政治仅限于形式上的认知,把乡村两级民主政治等同于在投票日参加投票的行为,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投票机器”。“投票机器”的自我定位,反映了弱势阶层在乡村政治参与上的被动和无奈,是乡村政治参与“非良性发展”的表征。
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富人治村”和“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富人治村”在西部乡村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在S乡,“富人治村”是外显的,“富人治乡”则是内隐的,前者指主要村干部及其亲属或为个体工商户或为专业养殖户,他们利用组织资源承包村里的鱼塘、河渠和山林等,优先租用集市的商铺或在交通要道修建住房和商铺;后者指S乡的主要干部利用组织资源,支持其家属或亲属在乡集市或县城购房与承租门面,甚至优先承揽乡村公路建设工程。有弱势阶层反映,村主要干部居住于乡集市,而乡主要干部购房于县城。“富人治村”对西部乡村治理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有些经济能人在担任乡村主要干部期间,致力于推动乡村发展致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有些经济能人则利用乡村公共资源谋取私利,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权力货币化”或“村官贪腐”。“富人治理乡村”的不良现象在西部农村较为普遍,这对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产生了不良影响,“富人治村”的运作机制有利于富人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一体化趋势,逐渐形成对乡村普通阶层的压制机制,从而将乡村中的大多数人排斥在基层民主决策之外。
“富人治村”和“权力货币化”是西部农村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是2014年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晋宁血案”。根据官方通报和媒体评论,这起群体性事件特点如下:第一,血色拆迁,数百富有村村民和施工方数百民工发生大械斗,死亡8人,规模和影响非常大;第二,施工方的数百民工持有催泪弹、“警用”字样盾牌等器械,冲突持续数小时,村民多次报警,始终未见警察到现场,媒体质疑当地公安民警不作为甚至警商勾结;第三,土地财政与拆迁暴利,村民种植大棚蔬菜的良田被当地政府征用,以300多万一亩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却一亩补偿村民不到2万,村民向媒体反映超2500万征地补偿款去向不明;第四,村民3年信访未见满意补偿,不满情绪积聚,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是导致村民武力抗拒征地拆迁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村民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应引起高度重视,这也是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非良性运行”的一个佐证。
二、西部农村政治参与“非良性发展”的原因剖析
对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 “认知和问题”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和种地农民等弱势阶层的自我定位是“投票机器”,强势阶层在乡村政治参与中具有垄断性优势地位,“群体性事件”是占人口多数的弱势阶层利用体制外的方式所发出的反抗强音。对上述问题进行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西部农村政治参与存在着“非良性运行”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即当下西部农村“多元共存,两极悬殊”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现有西部农村“选举民主”的缺陷。
第一,“多元共存,两极悬殊”的社会分层结构。学术界将西部农村社会分层格局分为“多元”和“二元”两种。多元社会分层格局论目前占据我国农村社会分层主流,其代表是陆学艺的农村社会分层研究,他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中,依据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对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把当今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民雇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村企业管理者阶层和乡村社会管理者阶层。陆学艺在研究中指出,“当代中国农村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中间阶层在变大……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大致是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2]陆学艺对农村中间阶层的过于乐观的预测引发了诸多争议,所以,最近几年他开始完善自己的理论,主张农村应调整社会结构,进行社会建设,以期推动农村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
西部农村二元社会分层格局论的持有者认为,我国西部农村社会分层在实质上不是多元共存而是两极悬殊,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对立和分化:第一,李强以全国“五普”数据为基础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指出“当下我国社会结构是一个‘倒丁字型结构,西部农村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3]这个群体的主体是普通的农民工阶层和以种地为主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却只占有西部农村少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第二,课题组对西部S乡的田野调查表明,该乡强富阶层占1%,主要是大私营企业主,家庭年收入超50万,在县城和乡村都有房产;富裕阶层占8%,包括小私营企业主、大个体工商户、大养殖专业户和乡村主要干部,家庭年收入在10~30万,有房有车;中产阶层占22%,包括小个体工商户、小养殖专业户、返乡农民工、乡村教师、医生和乡村非主要干部等,家庭年收入在5~10万;普通阶层占39%,包括回乡农民工中的失败者、以种地为主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在2~5万;贫弱阶层占30%,其家庭或劳动力不足或有长年生病的家庭成员或家庭负担重,家庭年收入在2万以下。由于中产阶层“积极向上”,严重依赖富裕阶层,缺乏独立性,所以该乡呈现富裕与贫困二元分化的社会分层格局。
课题组的田野调查结论相对支持李强等学者的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综合陆学艺和李强等社会学家对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论述,本文认为西部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多元并存、两极悬殊”的特征,这一社会结构也是西部农村政治参与呈现“非良性运行”的基本原因。
第二,西部农村“选举民主”的缺陷。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4]选举民主是统治合法性的民意基石,随着人类事务的日益复杂化,选举民主的缺陷与弊端也不断显现,选民—代表、委托—代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代表只能部分代表选民的意志,选民难以有效监督他们所选出来的代表;第二,选举民主是精英民主,普通的社会阶层参与程度不高。
代议制民主是以公民选举代表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一些学者称之为“选举民主”或“投票民主”,选举民主的基本特点为选民—代表、委托—代理模式。卢梭认为公民的意志不能被有效代表,只有公民本人才是其利益的最好代言人,所以他支持直接民主,反对代议民主。为什么公民的意志难以被有效代表,本文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选举民主的委托—代理链条相对较长,尤其在我国,乡村居民选举乡镇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县人大代表,经过县、市、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最后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如此漫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加上单一制的政体结构和富有集权传统的政治文化,基层的选民是很难有效监管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因而“由上产生、对上负责”成为部分地方政府公务员的一个潜规则;其二,选民通过选票选举产生的代表,遵循趋利避害原则,一直在选民集体意志和代表个体意志之间“游走”;其三,进入21世纪,公共决策日益复杂,一个代表所对应的选民数量在增加,每一个选民的个人偏好趋于多样化,选民之间的意志重叠与冲突共存,整合选民的集体意志对于民选代表来说,难度逐渐增大。
选举民主是精英民主,普通的社会阶层参与程度不高。选举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选择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却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这就导致普通选民参与程度低下。本文认为“选举民主”影响普通选民参与程度不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以选票聚合民意,选民参与讨论发言权利没有得到彰显。乡村普通阶层对于关涉其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诸如集资修建乡村公路,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与补偿,集体种植经济作物等,希望能够参与讨论与决策,而非简单投票;其二,乡村民选代表存在候选人“内定”,即“指选”这样一种非公开、不透明的政治现象。谁可以成为候选人,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这是民主选举的核心问题。西部农村普通阶层一致认为自己是“投票机器”,普遍认为乡村权力机关候选人的提名是“上级内定”,这是普通阶层对乡村选举丧失兴趣的基本原因;其三,乡村宗族或家族在乡村民选中利用“贿选”等违法手段操纵选举。在乡村居民的权利意识不够和相关部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选票的崇拜往往会造成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和金钱化,乡村权力机关的候选人以“金钱”与选民手中的“选票”进行交易,成功当选之后,大多又利用公权谋取私利。近年来,村民直选中的“贿选”和村官腐败成为乡村民主政治中的“痼疾”。
三、推动西部农村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路径思考
在西部农村,乡镇人大机制运作了近30年,村民自治机制运作了近20年,其贡献是突出的,缺陷也很明显,选举民主难以规避“精英民主”所带来的缺陷,占西部乡村绝大多数的弱势阶层,他们缺乏有效和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晋宁群体性事件值得我们反思,正是基层政府不作为、权力货币化,弱势阶层缺乏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才最终导致了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方式。完善西部农村民主政治,推动各阶层政治参与良性发展,保障弱势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通畅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这个问题导向,我们认为,应当在西部农村的基层治理创新中引入协商民主,使之与“选举民主”相互衔接,同时,逐渐提升弱势阶层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以推动西部农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相对于以选举和投票为主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在提升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对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能培养出健康民主所需要的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第二,广泛参与、公开决策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第三,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协商民主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在西部农村的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所产生的乡镇人大和村民代表大会,是宪政结构规定的乡村决策和立法机构,属于体制内的正式制度,属于精英民主,其固有缺陷是普通民众参与程度低,需要用另外一种体制外的非正式民主制度来拾漏补遗。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开始用协商民主来完善选举民主,并取得了不错的实效,其双轨民主模式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2009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并列,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创造,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5]胡锦涛同志的论述为我们在西部农村政治实践中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对接起来提供了顶层指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协商民主又做了进一步阐述,特别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提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6]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为农村各阶层有序参与乡村民主政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我们应该在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实践中,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体制内的民主决策和体制外的充分协商对接起来。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与选举民主衔接的民主模式在城市社区和东部乡村已经生根发芽,涌现出了若干典型:广州的“羊城论坛”、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南京秦淮区的“民生工作站”、天津宝坻区的村级重大事务“六步决策法”等。经过分析和比较,对西部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具有借鉴意义的是源起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温岭“民主恳谈会”的最大亮点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初步实现对接,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这种成熟形态的基层协商民主治理模式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其影响力逐渐从浙江扩大到全国,“恳谈式民主代表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7]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在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参与中,引进以“民主恳谈”为代表的协商民主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针对西部农村“多元并存、两极悬殊”的社会分层格局,在西部农村引入“恳谈式协商”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在西部农村着力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的中间阶层,该阶层主体是返乡的农民工阶层。城市改革启动后,每年西部农村有上亿青壮年进城务工,民工潮持续了20多年,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让欧美国家羡慕的“人口红利”。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央政府一系列发展西部乡村和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利好政策产生了吸引普通农民工返乡的内吸力,对融入城市失败者逐渐产生拉力,他们开始回归西部农村,在中小城镇定居与创业。当然“乡土情结和根文化”也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开阔了眼界、学习与获得了过硬的技能、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明晰了民主政治对于捍卫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把返乡农民工培育成支撑西部农村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主体阶层,是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的。
第二,“官”“学”“民”三方联合推动,基层政府承担组织和执行功能,相关专家承担指导和设计功能,乡村各阶层承担参与和监督功能。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对在基层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衔接,进行了顶层设计和任务布置,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尝试了主动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当然基层政府和专家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第三,建构一套相对完善的“恳谈式协商”机制,包括平等机制、对话机制、互动机制和接受机制。关于平等机制,主要是逐渐扩大农民工和种地农民参与协商的名额,给予两大阶层单独提出“议题”的权利。关于对话机制和互动机制,主要是每一次民主协商之前,相关的专家应该用一天时间对参会者进行基本参政技能培训,在协商进行的过程中,保障弱势阶层具有与强势阶层同样的参与发言和讨论的权利。关于接受机制,尝试把民主协商与乡人大和村民代表大会对接起来,同时构建发言记录、决策结果公开、人大表决、组织落实以及监督反馈等一系列有利于两个领域互动的机制,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西部农村实现有效衔接。
西部农村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其对西部农村民主政治的影响应用辩证的思维来分析,其积极作用是通过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社会整合,其消极作用是形成“多元并存和两极分化”的结构,这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各阶层以平等身份参与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在西部农村引入以“民主恳谈”为代表的协商民主,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对接,有助于西部农村各阶层以平等公民身份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政治。我们相信西部农村各阶层经过较长时期“民主协商”锻炼,有助于各阶层缓解“公”与“私”之间的张力,尽管参会者会从实现和维护“私利”出发,但在民主协商会上通过公开发言和讨论所提出来的观点,必然兼顾他人的利益,因为纯粹“自私”的方案,不仅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而且还会被大家公认为“自私自利者”,所以民主协商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必然是若干参会者解决方案的“最大公约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西部农村长期实践“民主协商”,不仅有助于提升西部农村民主政治的“质”,而且有助于培养具有公共精神和美德的公民。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7.
[2]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82-209.
[3]李强. 清华社会学讲义:社会分层十讲(第2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8.
[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2.
[5]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09.
[7]慕毅飞.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76.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