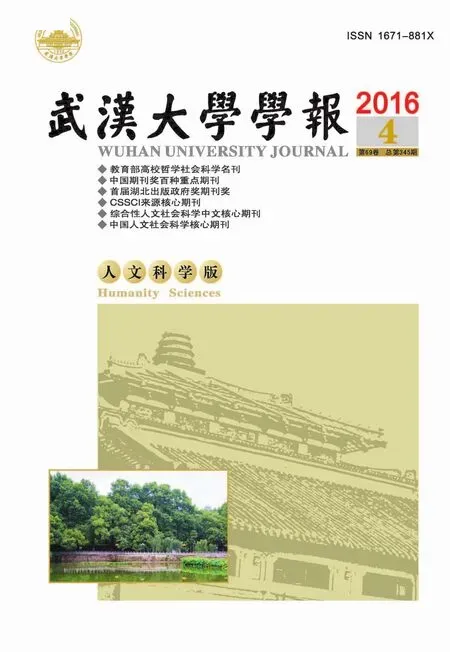文化翻译视角下诗歌意象的翻译
——以《鲁拜集》中“酒”的意象为例
王晓利
文化翻译视角下诗歌意象的翻译
——以《鲁拜集》中“酒”的意象为例
王晓利
摘要:诗歌意象不仅仅是诗人借以抒情言志的载体,它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一个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往往同一文学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和情感体验。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处于两种文学(文化)语境之间的译者,既要力求保留意象在源语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又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语境及读者大众的接受能力。因此,译者在翻译诗歌意象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本文化的诗学传统,借鉴并吸取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使他们获得跟源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最终达到两种文化互动和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翻译; 《鲁拜集》; 诗歌意象; “酒”
《鲁拜集》或译为《柔巴依集》,为古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3)所著,后经英国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译介而闻名于世。《鲁拜集》于“五四”期间由胡适译介传入中国,此后近一百年间,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译者,被不断地复译。迄今《鲁拜集》的汉译本已多达几十种,“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现象”*参见王一丹:《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页。。
海亚姆的诗歌短小精炼,但思想内容却极其丰富,包含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造物主的追问,对宇宙无法破解之谜的渴望以及对理性答案的寻求。诗人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些思想感情,其中“酒”作为贯穿《鲁拜集》始终的中心意象,直接出现在将近半数的诗歌中。本文拟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充分挖掘波斯传统文化中“酒”意象的文化意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英译者菲茨杰拉德如何运用这一核心意象构建结构连贯的诗歌语篇*《鲁拜集》的诸多汉译本中,除了少数从波斯语直接翻译的译本外,大多数都是从英语译本(菲茨杰拉德译本)转译而来的。因此,要研究《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汉译,首先要考察菲茨杰拉德是如何解读并处理波斯语文本中的“酒”意象的。。最后,通过比较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探讨不同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差异化及其成因。
一、诗歌意象与文化翻译观
意象是构成诗歌的最基本单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诗人借以抒情、释怀、喻志的工具,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在西方诗学语境中,与意象概念相近的术语是“Image”,最初在哲学和心理学领域中使用,随着20世纪初意象派的出现,逐渐被应用于文学理论领域中。尽管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意象”与西方诗学中的“Image”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可以对诗歌中的意象概念内涵作如下归纳:首先,意象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体,“意”指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等,“象”指自然、社会各种客体的具体物象、事象;其次,意象的本质是隐喻性的,诗人往往不直接言意而将意寄托隐含于象中,即从所表示的事物本身指向人的具体感受与经验;第三,意象是诗人独特审美创造的结果,同一种象,不同的诗人可以寄托不同的情感。诗歌意境的营造不仅仅着眼于单个的意象。一首诗一般是在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构思下由若干个意象组合而成。诗人不仅要善于选择、建构意象,而且应当巧妙地组合意象,使意象序列化、系统化,从而构成意境。
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开始由静态的、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转向动态的、开放的文化研究模式,既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处理,也考察翻译活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文化翻译”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任何一种语言都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本质上不但是一种跨语言的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行为。从语言层面来看,翻译中没有绝对完全的等值,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只能是功能意义上的对等,即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发挥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2.“文化翻译”更关注翻译带来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原作在进入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相互排斥和误解。一方面,译入语文化对原作中的异质因素进行选择,并加以改造和操纵;另一方面,翻译作品又以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译入语文化本身,促进其发展和革新。3.译者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者,既要避免对原文亦步亦趋的模仿,也要避免一味地发挥母语特长而忽视原文的特色。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移植和转换,“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以迎合译入语的读者,保证译文可以读懂”*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26.。
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诗歌意象时,首先应充分把握意象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包括诗人的个体思想情感及民族独特的群体文化意识,考察意象在源语文化语境中可能引起的语义联想和情感体验,并努力寻求适当的移植方法,以实现意象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的最佳转换。其次,要权衡单个意象与诗歌整体的关系,尽量在译文中建构类似于原诗的意象组合,以传达诗篇的整体意义,再现原诗的意境。最后,我们主张诗歌翻译应当“以诗译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应观照译语文化的诗学规范(文学手段、形式、审美思维等),借鉴并吸取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准确传达原作意义的同时也能保留原诗中浓郁的诗意和丰富的情感,“使译作在精神上与原作一致,但诗歌已脱胎换骨,没有留下翻译的‘挣扎’痕迹,即达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化境’”*参见罗选民:《衍译:诗歌翻译的涅槃》,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2期,第62页。。
二、 《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文化解读
(一) 海亚姆诗歌中“酒”意象所包含的多种意蕴
海亚姆对“酒”意象的使用是他诗歌中最显著同时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美国学者布里格姆·约翰逊(Brigham Johnson)曾评价海亚姆:“对某些人来讲,他不过是一个酒馆的醉汉;对另一些人来讲,他是一个为享乐主义而生的诗人;还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的异教徒试图透过迷雾看到上帝;还有的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迷茫的人在痛苦地询问:‘上帝,我相信你,可是你在哪里?’”*Brigham Johnson.TheManySidedOmar.Boston:Priv.printed,1925,p.15.这段话形象地总结了海亚姆诗歌中“酒”意象所包含的多种意蕴。
1.神秘意蕴。波斯古典诗歌与其传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并且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情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在宗教观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各自信仰的引导下,采用比喻、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将宗教情感与诗歌艺术完美融合。不少学者认为应该将海亚姆的诗歌放在其所在时代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去分析,《鲁拜集》中很多晦涩难懂的诗篇只有在这种语境下解读才更为可信。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欧玛尔·阿里-沙(Omar Ali-Shah)提出海亚姆可能沿用了苏非主义*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一个神秘主义思想派别,提倡通过苦修达到与真主的结合。苏非派诗人常使用传统诗歌中的一些意象,并把这些事物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体验,如用“酒”来象征真主的爱,把饮酒时的陶醉与对真主的迷恋做类比。的传统,他的诗歌中出现的很多意象,尤其是关于“酒”的意象,经常被苏非诗人所使用,如“将酒比作神的爱,陶醉比作神爱所唤起的狂喜,而酒杯则代表了神与人之间的联系。”*Robert Graves,Omar Ali-Shah.TheOriginalRubaiyatofOmarKhayyam:ANewTranslationwithCriticalCommentaries.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 Inc.,1968,p.4.由此,诗人得以将现实中“物质”的酒与宗教上“神智”之酒结合在一起。
2.享乐意蕴。尽管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为海亚姆及其诗歌带来了巨大声望,但不少伊朗学者对他的翻译予以否定并提出批评,认为他的翻译不但是对原作的不忠实,而且是一种浅薄和字面的理解,他的不忠实和误读将海亚姆以一个酒鬼和享乐主义的形象引入到西方。面对这些批评,尤其面对海亚姆是否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的争论,菲茨杰拉德仍然坚持认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就是现实中物质的葡萄酒(the veritable Juice of the Grape)。在第二版译本的序言中,他甚至将海亚姆与卢克莱修(Lucretius)相比。菲茨杰拉德带来的海亚姆的“葡萄酒”抚慰了当时苦闷、彷徨、迷茫的西方人,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他所宣扬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被这个深陷信仰危机的时代迅速接受。
3.智慧意蕴。美国学者马赫迪·阿敏拉扎维(Mehdi Aminrazavi)提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只能是一个哲学概念,因为他所发出的关于宇宙人生的疑问,不是借助酒精麻醉达到短暂的愉悦能够解决的。总的来说,海亚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重视理性和一切可以检验证实的事物。他诗歌中的酒是“智慧的酒”,智慧在此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海亚姆认为即使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怀疑和痛苦,也要带着欣赏生活的态度积极行动。
伊斯兰教视饮酒为一种罪孽,但不能简单归纳认为海亚姆是反宗教的,对于“生活在神权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贯穿一生的人,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反对宗教信仰本身的,”*参见穆宏燕:《波斯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其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宗教内的教派或观点之争,或是反对宗教中某些人为的、束缚人的、僵固的教条。海亚姆反对的是那些只注重外在形式和固守教条的正统教派,而“酒”就成了诗人在纷扰尘世获取思想自由、寻找精神归属的工具。因此,笔者认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可以指物质的酒,亦可以指神的爱,可以是任何能够把人从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心灵愉悦的方式。
(二) “酒”意象在《鲁拜集》结构构建中的作用
由于海亚姆不是职业诗人,他的诗歌或是通过口耳相接再由后人引述的方式流传下来,或是夹杂在他的手稿和文章中被后人辗转引用,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集结成册。因此,以菲兹杰拉德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常常面临着原文本的选择问题。菲茨杰拉德在参考了多个波斯手稿后,凭借自己的欣赏能力从600多首诗歌中提炼出他认为最接近海亚姆思想的诗歌,这些独立的诗歌经过译者的精心挑选和巧妙安排,呈现为一个有着连贯性和辩证性的整体,而作为中心意象的“酒”在诗集布局和结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鲁拜集》的整体结构来看,菲茨杰拉德描述了诗人海亚姆自旭日东升至皓月当空一天的生活,并借此传达出诗人在短暂的一天中对宇宙、人生的独到思索和深刻感受。当太阳升起时,诗人走进酒肆开始一天的生活。他在一开始就流露出对时间流逝的焦灼和人生短暂的感慨。酒馆内过往商队走马灯似的来去不停,昔日的奢华与今日的荒凉形成强烈对比,更使诗人感叹人世沧桑变幻。随着时间推移,诗人醉酒微醺,在苦苦探寻生死奥秘而不得解后,开始变得狂热和反叛,质疑造物主对我们命运主宰的不公。当夜幕降临,诗人走出酒肆,他最终变得淡然,发出最后的感叹“人最终还是如同酒杯中的泡沫一般,转瞬即逝,复归无形,死亡是唯一的归宿,”*参见李亚林:《波斯的李白—莪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载《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75页。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如此来看,《鲁拜集》诗集就变成了诗人藉“酒”或与“酒”相关的人、事、物来抒发个人情感的“饮酒诗”。
三、 《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汉译
本文以受关注程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比较两个汉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以及译者在处理“酒”意象时所采用的手段,并探讨不同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差异化及其成因。
(一) 两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
表1显示了菲茨杰拉德《鲁拜集》*菲茨杰拉德生前《鲁拜集》一共出版了四版,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改动。第五版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与第四版相比改动不大。郭沫若是根据第四版进行翻译的,而黄克孙依据的是第五版,并参考了其他版本。本文“酒”意象的统计则是根据《鲁拜集》英译本第四版。中的“酒”意象以及它们在郭沫若和黄克孙两个汉译本中所对应的翻译。在101首诗歌中,含有“酒”意象的诗有47首,共有70处涉及“酒”意象。诗中明言酒字、酒名、酒器物、饮酒,或虽无言酒而诗文醉意饱满者,都包括在内。
注:其他一栏主要包括描述饮酒后的感受、酒肆、侍酒之人等其他一些与“酒”有关的意象。
从表1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黄译本中出现的特称意象*特称意象相对于泛称意象,泛称意象指诗歌中出现的物象的总名,如“酒”;而特称意象则指相应物象的专名,如“杜康”。要比郭译本丰富得多。如前文所述,意象具有多义性,同一意象在不同的诗歌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情感。与泛称意象相比,特称意象更具体、清晰,译者为了让译语读者更快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往往会化泛称意象为特称意象,以求取得功能上的传情达意。
(二) 两位译者对“酒”意象的处理手段统计
表2统计了两位译者郭沫若和黄克孙处理与“酒”相关意象的手段(直译、增补、省略、互文)。
从表2可以看出:
1.“直译”是两位译者处理与“酒”相关意象的主要手段,但郭译本中的比例要比黄译本高出很多。诗人在诗歌中描写、叙述或者涉及某些客观物象时,有时只是为了构建一个场景,而对事物本身并没有给予任何特殊的象征意义,这时这一物象所表达的意义跟客观世界中这一物体本身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酒”意象常常与“及时行乐”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但“及时行乐”并非具象之物,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产生的缘由极多,可能是对个体生命存在时间短暂的认识,可能是对人生意义思索的痛苦,也可能是时间流逝带来的恐慌,“酒”可以使人产生兴奋、陶醉、麻痹等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从而缓解这种焦虑,使人忘却烦恼。这里“酒”是工具性、功用性的。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处理这类意象,无论任何文化的读者都不难体会原诗的意境。
2.黄克孙在处理“酒”意象时,“增补”和“省略”的手法运用比较突出,“增补”有33处,也就是说除了原有的70处与“酒”相关的意象外,黄译本中又额外增添了将近一半的“酒”意象。增补,也称增益,是在直译基础上采用的一种明晰化手段,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原诗的主题和意境,产生相应的审美体验。“省略”手段也在黄译本中出现了数次,而郭译本中却一例也没有出现。
3.两个译本也运用了较多的“互文”手段来处理“酒”意象,但黄译本中所占比例要稍高一些。从表1也可以粗略看出,相比于郭译,黄译译词的数量更加多样、词汇也更加丰富。互文体现了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渗透和转换。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沉淀而无处不在的互文指涉会给译者带来很大挑战;但同时,译者也可以借助互文手法在译本和译语文化文本之间建构起“互文”关系,迅速唤起读者心中的某种特定情感,从而拉近译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距离。
(三) 两译本呈现“酒”意象翻译差异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郭、黄两译本中“酒”意象翻译所呈现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位译者所采用的译诗形式及翻译策略不同。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受到了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个人文化趋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郭沫若使用新诗体译诗,语言以浅显的文言和白话为主,尽量避免添加自己的意象,同时也不删减原诗固有的意象,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的句法结构。这种译诗选择和取向与译者本人在文学和文化上的意图与主张有关。自新文化运动开始,许多诗人和翻译家为了打破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传统加于诗歌的重重束缚,开始倡导并实验使用白话-自由诗体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就是这一尝试下的产物。尽管闻一多评价郭译本中有不少忠实到笨拙的翻译,且“文言白话硬凑在一起,然而终竟油是油,水是水总混合不拢”,*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较大的影响,这多少要归功于白话-自由诗所展现出的返璞归真、鲜活自然的风格。
与郭沫若相反,黄克孙使用了旧体诗七言绝句来翻译《鲁拜集》,他在译者序言中提到:“《鲁拜集》的翻译,我的出发点是作诗第一。”*奥玛珈音:《鲁拜集》,黄克孙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页。译者深谙古诗传统,且造诣颇高,在译诗过程中,大胆借用本民族诗歌文化传统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在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跟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黄克孙译本语言优美、诗意浓厚,不但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誉,也让中国读者体验到了英译本带给西方读者的乐趣。
(四) 具体例子分析
下面以《鲁拜集》第12首诗歌为例,展示它从波斯文到英文,又从英文到中文的转换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变异的。波斯原文*英国学者爱德华·赫伦-艾伦(Edward Heron-Allen)曾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和他所使用的波斯原稿进行对比,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诗歌(49首)能够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的原文,而剩余的大多数是由多首诗歌拼凑而成的。这首是为数不多可以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原文的诗歌,由笔者从波斯原文直接逐字翻译而来。:
如果能有一个面包
一瓢酒,一个羊腿
然后我和你在荒原中坐着
那种快乐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有。
英译文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Wildernesswere Paradise enow!
郭译文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黄译文
一箪疏食一壶浆,
一卷诗书树下凉。
卿为阿侬歌瀚海,
茫茫瀚海即天堂。
这首是为数不多可以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原文的诗歌。原诗使用了一连串意象“面包”“瓢酒”“羊腿”“荒原”组成了一副贴近自然的和谐图景,表达了诗人向往自由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可以看到,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不但将“羊腿”替换成了“诗书(a Book of Verses)”,“君王”替换成“天堂(Paradise)”,还增加了“树(Bough)”和“唱歌(singing)”这两个意象,动静结合,由近及远,空旷苍茫的背景与眼前浪漫和谐的场景形成对比,诗人借助现实的景物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将天地人间巧妙结合在一起。郭沫若按照原文一行一字地直译,表现出客观写实的倾向,虽然直接传达了诗人的主观意向,但描写过于直白,少有顾及诗歌的艺术性,最后一行使用了两个感叹词“呀”“啊”,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原诗中诗人追求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变成了一种强烈而高昂的情绪。黄克孙在译文中引入了译语读者熟知的“箪食”“瓢饮”“瀚海”等极富象征意义的汉语意象,这时诗歌不再是单纯的写景和抒情,它已经将具体的物象与抽象的哲理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不以物质满足为人生目标,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乐。
四、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诗歌意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传递时,往往会产生变异。造成变异的原因,一方面是意象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关。译者处于两种文学(文化)语境之间,既要力求保留意象在源语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又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语境及读者大众的接受能力,这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译者在处理诗歌中的意象时,如果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就会使诗歌流于直白、浅薄、了无诗意。反之,如果充分利用自己文化的诗学传统,借鉴并吸取自己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跟源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最终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作者地址:王晓利,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Email:lili_books@126.com。
●责任编辑:桂莉◆
On Translation of the Wine Imagery inRubiy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angXiaol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magery is frequently used in poetry to express the poets’ feelings,thoughts,ideas,states of mind and any sensory experience.It is also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which always carries unique and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the translator,as a negotiator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should try at his best to reproduce the image and make it readable and acceptable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wine imagery i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Rubiy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lator could only preserve the original’s aesthetic rhetorical qualities by skillfully employing the poetics of his own culture.
Key words:cultural translation;Rubiyt; imagery of poetry; wine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