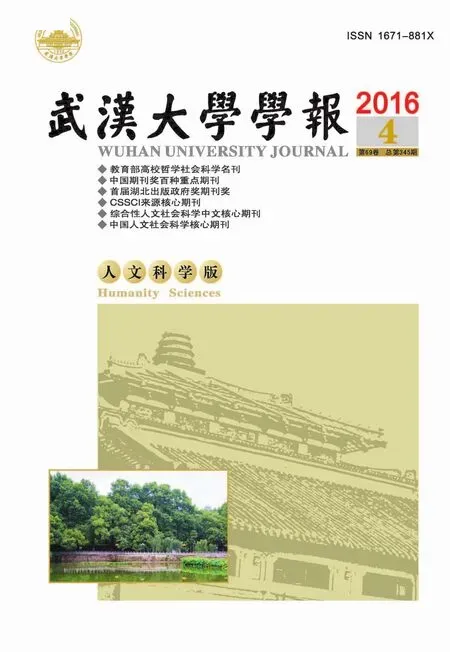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宋莉华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宋莉华
摘要:传教士汉文小说由晚明耶稣会士开启先声,西方传教士以中国古代小说之形叙写基督教文化之实,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体例和语言,又在其中融入西方宗教和文化内涵,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流传。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将宗教与文学结合的范本,传教士努力跨越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实现平衡,对于宗教文学的研究和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不无启示性。
关键词:传教士; 汉文小说; 基督教; 宗教文学
晚明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以汉文写作了大量小说,它们一度是学术研究的盲区,文学史上鲜有提及,学术史也将之排斥在外。无论是宗教学者,还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忽略了这样一批作品的存在。直到2000年12月,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发表论文《19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Patrick Hanan.“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2000,60(2).这篇论文后来由徐侠译成中文,收录在韩南的论文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200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它们才第一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与来华传教士本色化的传教策略密不可分。“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要……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3页。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以何种方式在中国传播?如何能被中国民众接受?这是西方传教士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他们试图理解并迎合中国读者的需要,努力在文学阅读与传播基督教信仰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由此产生了传教士汉文小说。对于这一类小说的文学价值到底作何评判?传教士小说是指向诗学的建构还是神学的建构?它们对于跨文化的宗教传播又有何种启示意义?本文拟通过梳理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历史,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 传教士写作汉文小说的历史演变
“传教士汉文小说”,简而言之就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为宣扬基督教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用汉语写作或译述的小说,总体上带有明显的护教特点和宣教倾向。由于传教士写作的小说中也包含了部分世俗题材的作品,因而本文根据写作主体称之为“传教士汉文小说”而非“基督教汉文小说”。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传播状况密不可分。晚明耶稣会士来华之际,中国古代小说尚未在欧洲流传,耶稣会士又以结交上层文人为策略,故而其汉文写作多师法史传文学和文言笔记传统。18世纪欧洲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中国古代小说开始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以后,遂以其为范本写作基督教汉文小说,一直持续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前后。19世纪后半叶,传教士虽转向译述西方小说,但仍采用章回小说、话本小说体例,直到1917年以后才逐渐抛弃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式。
(一) 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开启汉文小说写作先河
传教士写作汉文小说,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晚明。当时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可归入汉文小说的作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关于使徒和圣人的传记小说,它们并不是对圣徒真实活动的记录,而是着重表现圣人、使徒一生中某几个与宗教密切关联的事迹,特别是圣迹,以此感召读者。明万历三十年(1602)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编译的《圣若撒法始末》,被誉为第一部传教士汉文小说,讲述天主教圣人若撒法的苦修故事*李奭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106页。。这个故事源自佛教的佛陀传记,后因摩尼教传播,成为天主教圣人传记之一。龙华民不知渊源,为对抗广东佛教徒对天主教的贬抑而加以译述。意大利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的《圣人行实》(1629年)和《圣母行实》(1631),意在彰显圣人和圣母的“神迹”与“美德”。从1628到1630年,罗马帝国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天启进士王徵(1571-1644)合作译述了传记小说集《沙漠圣父传》,题为《崇一堂日记随笔》,崇祯十一年(1638)刊刻行世。书中于每位教中人物传记篇末都附一篇“评赞”,以旌表圣人的嘉言懿行。法国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的《德行谱》,雍正四年(1726)刊刻。该书是西方古圣贤达尼老各斯加的传记,“题为《德行谱》者,是欲以圣人之圣德,示人以修成之标式故”。
第二类是夹译夹叙地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译述欧洲寓言、轶事及中世纪的“证道故事”(exemplum)。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意大利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畸人十篇》在北京刊行,该书首次提到阨所伯(即伊索)轶事,译介了四则伊索寓言及其他西方传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西班牙会士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的《七克》在北京刊行,该书第一次将伊索故事以“寓言”名之。明天启五年(1625)法国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译、福建泉州中国传教士张赓笔述的《况义》在西安问世,可以视为《伊索寓言》的单行本,其中选译了22则伊索寓言,每篇的结构大致分为两部分:前面为“况”,即翻译故事,后面为“义”,即揭示由故事引申的寓意。清顺治二年(1645)意大利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五十余言》刻于福建,书中包括《伊索寓言》及西方历史故事等。顺治十八年(1661)意大利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的《逑友篇》刊刻出版,全书旨在论交友之道,但引用了十余则寓言、轶事及古史。高一志所著《则圣十篇》《童幼教育》《齐家西学》《达道纪言》《譬学》等书中,也可散见一些故事片段,不过描写较为简略。耶稣会士对伊索故事的原貌往往予以保留,或仅稍加变动,但在寓意上,“会士则摆脱西洋传统的羁绊,从天主教的角度试为再剖,从而在中国别创某种故事新诠的证道诗学。如此所形成的‘伊索寓言’,在某一意义上乃欧洲中古证道故事的流风遗绪,结果通常演为文学史上的正面贡献”*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第85页。。而历史故事、名人轶事一类的短章,则与“世说”体小说相类,机智隽永,每寓启示于讽谏之中。
尽管上述著述,比起宏大的文学史来显得微不足道,却成为晚明士子认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开端,丰富了晚明文学的内容,同时将中国与西方文学接触的历史上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非同一般*李奭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第2页。。总体上,耶稣会士对于汉文写作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以学者的严谨恪守宗教阐释与文字雅驯的界限,不肯逾越。其所推崇的是以理性的思辨说服读者,而并非以文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打动读者。也有极少数的特例,比如1729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曾以白话写作了六回的章回小说《儒交信》。这是由于马若瑟本人对通俗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其《汉语札记》的例句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当时流行的戏剧与小说,他还是第一个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的人。但是马若瑟对中国世俗文化的包容,使耶稣会感到了危险而被罗马天主教传道总会召回,而且由于天主教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儒交信》一直未获公开出版,直到1942年才在河北献县出版排印本,当然也就谈不上影响了。
(二) 1807-1860新教传教士模仿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白话小说
从1807年首位新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属于新教传教士们为了尽快打开局面,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模仿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章回小说写作基督教汉文小说被视为捷径,传教士试图借助通俗文学的影响力达到快速宣教的目的。马礼逊开风气之先,他1815年写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1819年的地理启蒙小说《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都显示了章回小说的某些特征*Patrick Hanan.“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418.。1819年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教传教士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问世*实际上《张远两友相论》最早1817年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第3卷开始连载,一直到1819年卷5结束,共12回,1819年初刻本在马六甲问世。。该书是用问答体写作的章回小说,作者为伦敦会米怜(William Milne),书中通过两位友人的对谈,试图实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该书可能是同一时期印行数量最多的中文小说,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后来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宋莉华:《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的流传与影响:米怜〈张远两友相论〉论略》,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这一时期的汉文小说在创作方式上,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度依赖性,不仅采用古代小说体例,而且直接套用原著的情节、人物,将小说中的语句、段落重新组织,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本土流传,以此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在题材和内容上,传教士则侧重对历史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世情小说进行借鉴和模仿。作者以英美传教士为主,在五口通商以前,来华的9个新教差会当中英美差会占了6个,德国礼贤会等其他欧洲差会的传教士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世情小说在描摹中国社会世情百态、众生世相方面的功能尤为突出,因而成为传教士重点摹写的范本。特别是由世情小说演化而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其情节、人物往往具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和特点,易于模仿,更加受到传教士青睐。郭实猎(Karl F.A.Gützlaff)所著《赎罪之道传》《诲谟训道》《小信小福》《是非略论》《常活之道传》《诚崇拜类函》《正邪比较》《生命无限无疆》,叶纳清(Ferdinand Genähr)《金屋型仪》、《庙祝问答》,理一视(Jonathan Lees)《伶俐小孩》《领出迷路》等都可以视为传教士模仿世情小说,甚至直接对才子佳人小说移花接木而产生的新篇。传教士的模仿性写作表现在情节、人物、写景状物、语言各个方面,甚至原文照搬。
此外,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下,传教士以中国时间为经,以西方史实为纬,采用“通鉴”式的叙事结构方式,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俗化、条理化、故事化和传奇化,创作了反映西方社会和圣经历史的奇特的历史演义小说,如《大英国统志》《古今万国纲鉴》《圣书注疏》《约瑟纪略》《亚伯拉罕纪略》《东西史记和合》《拿破戾翁》《马理王后略说》等。《圣书注疏》每介绍一部分《圣经》内容,就会根据中国历史年表谨慎地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将西方的历史时间纳于中国的编年坐标中。其第一回介绍《创世书志略》时,标注“自第十二章至二十四章,自夏帝扃起,终于帝孔甲二十六年”、“自第二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起夏帝孔甲,终商太甲二十四年”*《圣书注疏》,第一回《父谆谆告诫》,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5、6、9页。。小说第一回《父谆谆告诫》一面叙述:“汉朝年间,世界大变。灵帝无道,宦官弄权。”一面将目光迅速投射到西方:“至于列西国逐一归罗马民管辖,学文甚盛。”*《圣书注疏》,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1页a。
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写作,表现出对中国通俗小说的高度依赖,对中国古代小说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力求通过神形兼备地复制中国小说,使得作品被中国读者接受。
(三) 1860年到1917年半译半著中西合璧的汉文小说
1860年以后,除了少数原创小说外,传教士逐渐转为以译述为主。传教士的翻译至少包含了改写、重写、缩译、转述、调整文字风格等做法,自我发挥的成分颇多。正如杨格非释译《红侏儒传》时所说:“其间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是脱胎于原本,按字谨译也。阅是编者,谓之译可,谓之著可,谓之半译半著,亦无不可。”*《红侏儒传》“跋”,汉口:圣教书局1882年,第1页a。但在文学形式上,译述的小说则仍然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以章回小说、话本小说的面目出现。
小说的题材内容,较之19世纪前半叶有很大变化,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也跨越了宗教的藩篱,译述了大量世俗文学作品,引入西方的文学经典。如《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先驱,它在中国流传,英国长老会宾为霖(William Charlmers Burns)功不可没。宾译本并非最早,却是第一部完整的并被公认是最早的译本。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续作和其他译本:伦敦会绿慕德(Miss M.Lawrence)《小天路历程》、古爱德(Florence E.Gooch)《孩童天路历程》、谢颂羔译《圣游记》及《圣游记续集》、美国传教士麦体雅(Ada Haven Mateer)的仿作《天路日程》。1902年英国教士英为霖(William Inglis)用羊城土话翻译《辜苏历程》,相较于钱塘跛少年沈祖芬的译本《绝岛漂流记》(1902),是《鲁滨逊漂流记》最早最完整的中译本。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两部小说《织工马南》(SilasMarner)和《罗慕拉》(Romola),分别于1913年、1917年由美以美会亮乐月(Laura M.White)译成章回小说《马赛勒斯》和《乱世女豪》,她还把英国19世纪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长篇无韵体叙事诗《公主》也译成章回小说《公主之提倡女学》。19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以章回小说等中国古代小说体例译述了大量西方小说,最在将理想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引入中国,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题材,成为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的直接诱因和不可或缺的异质文化资源。
传教士译述的小说,最早将西方文学引入中国。这些作品呈现出中西调和的文学形态,对中国文学传统欲拒还迎,在文学观念、语言及小说技巧方面表现出了超前性和前瞻性。1917年新文化运动张开双臂拥抱西方文化,此时传教士再以中国文学传统进行自我约束和标榜,以寻求读者的接受,显然已经毫无必要,因而对西方小说的直译占据了主流。
二、 传教士汉文小说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性
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产物,传教士针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尝试以汉文写作,借助通俗小说这一文体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效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与中国民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争鸣。传教士汉文小说对于宗教文学的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第一,诗学建构与神学建构的融合。当我们用“宗教文学”一词来限定传教士小说时,实际上已经给它划定了界限,即将这一类小说作为特殊的宗教意识的产物。这就涉及宗教文学的写作主旨和评判标准问题,宗教文学的价值究竟是指向文学的建构还是神学的建构?
传教士汉文小说试图将基督教内涵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融为一体。1902年亮乐月把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晚期的中篇小说《行在光中》(Ходите в свете пока есть свет)译述为章回小说,二卷二十四回,并模仿明末清初薇园主人的小说《清夜钟》,将该书原名《五次召》(FiveCalls)改为《五更钟》*《五更钟》,亮乐月译,陈春生述,1904-1906年在《通问报》连载,190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单行本。。有广学会彩笔之称的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为此书作序,对《五更钟》称赏有加:
我很高兴《五更钟》的问世。原因有二:首先是它的主旨。“布丁好坏,不尝不知。”该书最早连载于吴板桥的《通问报》,后在一年里竟销售达两千部之多。第二,它为中国基督徒所写。相比西方作品而言,该书更符合中国风格,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并不能把它们(原著和改写内容)分离开来,反正结果就是,一个毫无异国背景,也无深奥的西方经典论述的中国《天路历程》诞生了*季理斐:《五更钟》“序言”,上海:广学会1907年,第1页。目前有关此书的研究成果有:林惠彬:《晚清基督教汉文小说〈五更钟〉初探》,载《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1年第4期;左维刚、吴淳邦:《托尔斯泰经典的重构改编》,载《中国小说论丛》第44辑。本文的译文参考了这两篇论文。。
两千册的销售数据显然让传教士感到了成功和兴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写作策略的有效性。作为该书读者同时也是序作者之一的王士瑛,回忆《五更钟》所带来的阅读快感以及此书风靡的情形:
仆回忆生平有三乐焉。……至第三乐,其惟读改良社会小说《五更钟》书一部乎。仆当一、二年前,阅《通问报》,每期见有小说《五更钟》一段,为之心醉,与二、三友朋叙谈,辄言念及之,以未得窥全豹为憾。及至去年,此书出版,仆劝古牧师,多购此书,以馈通人,牧师欣然应允。今年正月,购来一百部,已馈送罄尽。今又购来一百部,亦送去大半。迩来因看此书而望道者,有二、三十人,异哉!斯真生命粮之二膳,而新耶路撒冷之天梯乎*王士瑛:《读〈五更钟〉书后并题》,载《五更钟》,上海:广学会1907年,封3页。。
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武器,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具有“易感人”的伟大力量。他具体分析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今天看来,梁启超总结的这四种力量对于改良社会的效果似乎有限,但它们对宗教信仰的产生和确立却是必需的,可以有效唤起宗教感悟和对生命的体认。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初期,已经对此有了感性的认识,并将汉文小说写作作为重要的传教策略加以推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晚明耶稣会士,他们针对中国上层文士写作,追求逻辑的严密,理性的论证,风格的雅驯,对儒学有精深的研究,试图通过合儒、补儒被中国文人接受,但宗教影响力实际上却相当有限。当逻辑思维和冷漠的理性被奉若圭臬,便会感受不到宗教的力量。正如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说,宗教教义“不能像抽象科学的真理那样完全独立于意志”。以知性理解上帝的存在只会大大削弱宗教的力量,将会“牺牲信仰的活力以换取冷冰冰的机械的认同,因为这是强迫的认同,所以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带着强烈的感情体悟宗教,宗教才有无限的生机。在知性引领下进行宗教的探索是固定呆滞的*Samuel Taylor Coleridge.BiographiaLitera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p.135~136.。而文学恰恰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可以成为孕育宗教情感的土壤。19世纪传教士汉文小说正体现了在文学与宗教之间寻求一种自然结合的努力,其写作也日益摆脱早期粗制滥造的状态,向中国古典文学靠拢,以扩大读者面,不仅使社会下层民众喜闻乐见,而且吸引文人读者。这不但是传教策略和文字事工的转变,更事关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关系着基督教在华的文化品位和发展前景。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教士以中国古典小说为蓝本,写作汉文小说是顺应历史发展需求的。传教策略的选择与修正并非出于与生俱来的自觉意识,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传教士们会根据当地社会的需要,投其所好地选择传教工具和方式,因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汉文小说正体现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这里所说的“文化适应”政策着眼于广泛的文化层面,目的在于解释异质文化交流时种种现象与规律。总体上,传教士在汉文小说写作中越来越倾向于以文学为标准,更好地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的趋势。同时,作为宗教文学,传教士小说又并未因为文学的建构而与宗教割裂,而是将宗教的、神学的立场隐藏在其中,是将文学与宗教融合的范本。
第二,跨文化传教的宗教文学范本。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其在中国传播时必然遭遇冲突和阻碍。传教士汉文小说一方面借助文学的形式掩盖了过于强烈的宣教意图,在世俗的休闲读物与传播基督教信仰之间,寻求结合的可能;一方面努力弥合东西方文化的鸿沟,是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以及文化传播的范本,为异质文明在空间的碰撞提供了借鉴。
传教士小说在文学形态上保留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征,同时因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又夹杂了西方文化的视角,打上了时代烙印和传教士的身份烙印。这使得小说文本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隔阂甚至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最常见的表现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传教士常常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批评佛教的偶像崇拜、丑化中国的术士、僧、道等形象。郭实猎1834年写作了章回小说《赎罪之道传》,小说叙述明朝有一科甲翰林姓林名德表字道显,厦门人氏。其为人最重义,官又高,家又富,才学政望,与尊贵极相契厚,每每于公事之暇,不是他寻友,就是友访他。与林翰林往来的都是些饱学之士,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叙林翰林与朋友讨论基督教中的赎罪之道。其中第十一回,写一名星相术士拜访林翰林:
须臾见一人,从堦下走进来。怎生模样?但见一顶方巾,透脑油海清穿袖破肩头皮之上,加圈点假装出隐逸。三分髭鬚,短面不长,眼睛大而欠秀。见了人,前楚后拱,浑身都是谦恭。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势利。虽然以星客为名,到靠逢迎作主*爱汉者:《赎罪之道传》,载黎子鹏:《赎罪之道: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117页。。
郭实猎在此直接照搬了中国古典小说《玉娇梨》第二回中投机钻营、猥琐虚伪的星相术士廖德明的形象:
头戴方巾,身穿野服。头戴方巾,强赖做斯文一脉。身穿野服,假装出隐逸三分。髭须短而不长,有类蓬蓬乱草;眼睛大而欠秀,浑如落落弹丸。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恭。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势利。虽然以星相为名,倒全靠逢迎作主*《玉娇梨》,荑荻散人编,邓加荣、赵云龙辑校,线装书局2007年,第12页。。
《赎罪之道传》中又将儒、释、道的人生态度与基督徒相比较:
吴公道:“老先生说来最有理,进教解闷舒怀。但愚见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在海东’,惟有孔孟崇现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莫若今日饮酒食肉,明日诸事罢了。”且说林公听此言,甚怒道:“吉凶祸福由于天,非人所能主也。但放肆淫邪,招皇上帝之怒。轻圣教,纵邪欲,莫不惹万祸。上帝鉴万人,连心之私思可知也。相公若弃其实且随影,一定遭难无尽矣。”*《赎罪之道传》第十四回“论真道自证”,道光丙申年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19页。
小说人物在问答之间实际上显示了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广泛的对话,是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锋。“文化对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证实的东西是宽容的;而对它所排斥和贬低的就不那么仁慈了。”*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7页。与儒家学说相比,佛教和道教具有宗教突出的神圣性与排它性,与基督教存在更为明显的冲突。因此传教士小说在主张基督教一神论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佛教与道教的多神论、偶像崇拜等不断提出挑战,同时触及了深入人心的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死与基督教的复活思想之间的比较,民间流行的道教偶像崇拜则被视为低劣的迷信行为受到批驳。在宣扬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的同时,传教士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与攻击性。
关键是如何消解文化对抗和冲突?传教士在小说形式的掩盖下,通过故事中的人物间接批驳佛道,同时将小说中的基督徒塑造成应被效仿的正面人物,与异教徒的负面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读者自己判断孰是孰非,同时传教士努力寻求基督教与儒学的关联,适应中国文化,以此缓解正面论战可能造成的冲突,在差异和冲突中取得了平衡。这对跨文化交流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一直是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因素。在后殖民研究范式中,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西方权力及强势话语的批判,本土文化的能动作用则被简单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刘禾:《跨语际实践》“序”,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然而传教士汉文小说揭示了二者相互影响的多重可能。萨义德对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的复杂性有过精辟论述:“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独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22页。“西方/东方”二元对立话语之下的单纯主体并不存在,二者之间呈现的是既反抗又依赖的关系,其文化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而是冲突的双方都陷于一种混杂的、充满张力的文化政治胶着状态。郭实猎本身是一名持有强硬的欧洲文化优越论立场的传教士,但是他在实际写作中,表现出对中国文化高度的依赖和亲近。他一面懊恼地抨击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无知,一面又努力汲取中国文化的养分,对阅读和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乐此不疲,在书中连篇累牍地引用儒家经典,以儒证耶。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都属于传教型宗教(missionary religions),有赖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者劝人皈依。但是,唯有基督教得以展现在世界最广大的区域面前,其他三者在20世纪之前却仅限于东半球。不可否认,帝国权力为基督教扩张提供了机会,但基督教派出大批传教士并采取灵活的策略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要对传教士汉文小说包含的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力、它对个体宗教信仰改变的程度进行数据评估显得十分困难,但毫无疑问,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结合推进了中西社会的相互了解,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下,文化课题研究长盛不衰*杰里·H.本特利:《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载《全球史评论》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9~71页。。西方来华传教士试图运用东方世俗文学的影响力传播西方宗教,传教士汉文小说不只是东西方跨文化传教的个案,而是为考察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同时代文明的碰撞和文明间的理解提供了可能的模式和研究视野,具有示范意义和价值。
三、 结语
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产物,但是从晚明到清末民初的三百余年间,其写作却经历了逐渐去宗教化的过程,从撰写圣人传记、证道故事到把笛福、乔治·艾略特等人的小说译述成章回小说,世俗化的进程持续不断。这里的“世俗化”不仅表现为传教士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开始更多地触及世俗生活,而且许多小说对基督教信仰本身表现出了怀疑和不安,甚至以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进行论辩,讨论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语境中如何重新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这些小说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早期的传教士小说。传教士小说所传递的小说观念、对小说题材内容的拓展、对小说功能的延伸,为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提供了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从宗教文学的角度看,传教士汉文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宗教文学的本质和特点。宗教文学的内涵并不等同于宣教文学,宣教文学是“真诚地渴望促进宗教事业的人们所写的文学作品”*T.S.艾略特:《宗教与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其目的在于恢复宗教与文学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即便建立起来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早期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由于意在护教和宣教,艺术性差强人意,不同程度地存在仓促成文、情节雷同、人物类型化等不足,读者寥寥,与传教士的预期相去甚远。因此,宗教文学的价值在于用宗教精神来处理文学题材,而不是把宗教当作全部或最重要的文学题材。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莎士比亚比虔诚的清教徒约翰逊更深层地表现了宗教的精神,而但丁、高乃依和拉辛的诗剧,虽然没有接触到宗教主题,但他们依然可以被视为伟大的基督教诗人*林季杉:《T.S.艾略特论“文学与宗教”》,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194~195页。。宗教文学要实现其存在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宗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并非故意地、挑战性地为宗教辩护的文学*艾略特:《宗教与文学论文集》,第242页。。这是传教士汉文小说作为宗教文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地址: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34。Email: slh71@shnu.edu.cn。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Missionary Novels in Chineseas Religious Literature
SongLihua(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Jesuit missionaries break the new ground in writing novels in Chinese.Whe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ome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their Chinese literary writing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historical-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nd sketchbooks in classical Chinese targeted at a few upper-class scholars to popular novels for plain folks.By imitating the style and language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Wester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missionaries create new novel texts which are widely spread in China.As a model of the union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those novels are intended to publicize Christianity with a multiplier effect by turning to the great appeal of literature.In their writing process,missionaries try har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strike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conflicts,which is quite enlightening in the tran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religion.
Key words:missionaries; novels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terature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ZONGHE011)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