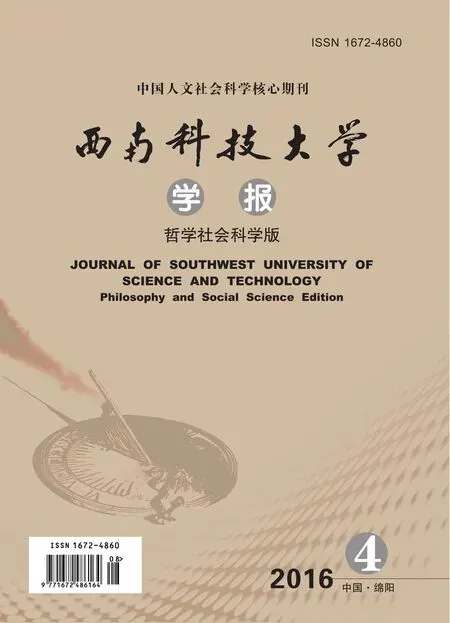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
——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袁 艳
(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四川绵阳 621010)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
——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袁艳
(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关键词】秘鲁;军政权;职团主义;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
作为一个政治学分析术语,职团主义(corporatism)被广泛用于观察不同时空的各种制度现象。从巴西到英国;苏联到美国;澳大利亚到罗马尼亚,近年来又见于该术语对发展中社会包括中国的分析。著名的拉美研究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认为,伊比利亚-拉美具有职团主义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影响至今。国内知名拉美史专家林被甸教授提出,职团主义同现代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共同构成推动20世纪中叶拉美社会大变革的主要内部非经济因素。1968-1975年间,在贝拉斯科将军领导下的秘鲁军政府实行了大刀阔斧的革命性改革。在改革中建立的“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具有强烈的职团主义色彩。
一、何谓职团主义?
职团主义(也译作法团主义、组合主义、多阶级合作主义等),是关于社团的古老思想,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受到欧洲学者的关注。职团主义概念众多,阿兰·考森在对其进行梳理时至少提到3种不同概念:[1]第一种由英国学者温克勒提出。他认为职团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统一、秩序、民族主义和成功的原则,指导私有经济的一种经济制度。第二种由杰索普提出。他认为职团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国家形式,伴生于议会制国家形式,然后才取得支配地位。职团主义和议会制度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利益代表和行政干预过程在制度上分离,而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利益代表和行政干预在制度上合二为一:利益集团既是利益代表成员,也是贯彻政策的载体。第三种概念由施密特提出。他认为,职团主义是利益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施密特提出的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制度的职团主义,日渐成为公认的定义。施密特关于职团主义定义的完整表述如下:职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并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相对控制。[2]我国学者夏立安认为,拉丁美洲研究学者提出了第四种定义,他们将法团主义视为特定地区和特定文化传统的产物。更具体地说,它产生于1500年以来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的独裁的、精英治国论的、天主教的、等级制的文化传统中。[3]
无论学者们对“职团主义”怎样定义,他们在使用该概念时均涉及4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作用,职团主义国家的功能是建立和保持一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国家直接介入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诸如政党、议会等民主体制,在职团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不起作用或作用甚微;三是职团主义国家仍是一个私人资本占主导的国家;四是利益代表组织的中介功能。[4]
由于“职团主义”定义有如上各种,故各国的具体实践也存在着差异。即使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职团主义国家,也存在未职团化的领域。施密特承认,他的定义只代表一种理想形式(ideal type),没有一个政权完全吻合他的描述。例如,大部分学者公认墨西哥是拉美职团主义的典型之一,但当我们考查墨西哥组织得最好的城市劳工领域时,还是发现该领域只有4项标准与施密特定义相吻合,而施密特关于职团主义的完整表述中有9项标准。[5]
二、贝拉斯科军政权改革及其对利益组织形式的选择
秘鲁于1824年取得独立,但长期处于分裂的社会状态。“秘鲁这个国家的地理和人口结构就像它的经济和政治一样很成问题。它的地理环境被安第斯山脉扭曲得支离破碎,它的人口又被分裂为这么多种族、阶级和民族。”[6]这种分裂性一直是秘鲁发展的绊脚石,因此秘鲁亟需实现国家一体化。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并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在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城市,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贫民窟大量涌现。将城市贫民、农民、印第安人等边缘人群整合进秘鲁国家和社会,成为秘鲁有识之士的共识。
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秘鲁历史上充斥着军人干政和考迪罗主义。同时,秘鲁也受到西方宪政主义影响。1933年宪法规定,秘鲁实行总统—议会制。①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议会有权质询和撤换内阁阁员。虽然也设有内阁总理一职,但总理主理国家典礼、外交礼仪和监督内阁事务,并不握有治理国家的实权。秘鲁政党的产生,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后期。文官主义党是秘鲁的第一个政党。20世纪20年代,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和民众部门的更加激进的政党兴起,取代了文官主义党的地位。在这些政党中,组织得最好的当属阿普拉党。1924年,阿亚·德拉托雷在墨西哥建立阿普拉党。该党逐渐成为秘鲁最主要的政党之一。
此后,政党在秘鲁政治生活中日渐重要,但很长时期内,其形象和作用并不正面。1963年7月28日,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就任秘鲁总统。贝朗德政府提出三大主要政策目标:一是颁布有效的土地改革法令,将大部分农村人口纳入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范畴;二是开展金融改革和税收改革;三是进行企业改革,增强工人的参与。[7]他在施政纲领中还提出石油国有化、经济计划化、推广“合作主义”等口号。但是,由于阿亚·德拉托雷和奥德里亚组成的反对派-阿普拉和奥德里亚国民同盟控制了议会多数席位,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和恶意妨碍议事的政策,使得贝朗德总统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严重受挫。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秘鲁有识之士认为,民主议会制是实现秘鲁结构变革的障碍,而要实现秘鲁的结构性变革,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或者建立一个不受议会诸多限制的“强大”政府才能实现。[8]这是贝拉斯科将军执政后弃政党议会制度不用,采取职团主义组织形式的重要背景。
在秘鲁日益严重的体制危机之下,国家精英-革新派军官集团逐渐形成。在军队职业化过程中,革新派军官们逐渐参与到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动中。在与人民的近距离接触中,军队精英们逐渐形成共识:(1)要想生存,必须对秘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基本变革;(2)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不能完成这些基本变革;(3)已经在其自身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内,发展出新的结构变革和社会发展计划;(4)自信必须由已经形成教育和知识体系的军队精英集团来执行其计划;(5)只有执掌政权才能实施计划。[9]
1968年10月,以何塞·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osé Velasco Alvarado)将军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贝朗德政府夺取了秘鲁政权。同年12月,贝拉斯科军政权正式接管秘鲁。军政权提出,政权的首要目标是打破寡头权力,减少秘鲁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以便实现国家经济自主,以工业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让民众分享发展的果实。此外,政权还提出,既然被寡头剥削的人存在共同利益,那么社会可以在没有传统组织方式和阶级冲突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并取得发展。实现一个被整合的统一的和谐社会,是军政权的另一个目标。[10]在此基础上,军政权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全民参与的民主社会的口号。[10]
在1968-1975年贝拉斯科将军执政期间,秘鲁军人精英按照其计划和目标开展了革命性的全方位改革。其主要改革措施包括:(1)国有化-对石油、外贸、渔业、私有银行、电信、铜矿等进行国有化;(2)汇率控制-国家对糖业、矿石和棉花出口寡头的外汇进行管制;(3)建立国家计划制度;(4)发展与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5)捍卫200海里海洋经济专属区;(6)土地改革-征收700万公顷给农民公司,在土地裁定组织里、在秘鲁历史上,农民首次得以申诉与获得裁定;(7)颁布《水法》,宣布水是国家财产;(8)工业改革:工人通过工业合作社,逐步参与工厂的管理和获得工厂股份直至占有公司50%股份;(9)创建支持发展的融资公司(Corporación para financiar el desarrollo);(10)承认秘鲁总工会,给予工人谈判的权利并开展工人与革命政府的对话;(11)进行教育改革和扫盲运动,组成教育点和社区教育委员会;(12)创建“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使全国的农民组织、土地合作社、社会利益土地协会、土地联盟、国家土地协会、工业合作社、全国工业合作社总会等成员有计划地参与和组织起来;(13)组成商业、矿业和电信合作社;(14)组成自我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公司;(15)承认克丘亚语为官方语言以使其能在学校、司法和其它活动中使用;(16)征收国有日报并使媒体社会化;(17)承认和促进国家与印第安文化表达的文化政策;(18)推动秘鲁电影生产;(19)颁布《秘鲁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las Bases Ideológicas de la Revolución Peruana),规定秘鲁经济的基础由国有部门、合作社部门、私有部门和社会所有制部门组成,其中最后一种占主导。[11]上述改革体现出如下主要特征:一是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实施国有化;二是试图建立多种所有制相结合的所有制形式;三是力图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将人民整合进秘鲁社会;四是在外交上重视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秘鲁革新派军人要实现其所追求的对秘鲁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全方位改造的目的,并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全民参与的民主社会,必须依托一定的组织或实体。在利益代表和沟通组织方面,当时的贝拉斯科军政权面临3种选择:1.创建一个官方政党;2.利用国内现有的一个或几个传统政党;3.摒弃所有先前关于政治活动和参与基础的构成,重新对政治活动进行界定。[12]像墨西哥那样创建一个官方政党来推进改革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当时以贝拉斯科为首的军人放弃了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严格意义上的军政府本质失去意义,会鼓励军人从事党派活动,这可能危及体制的完整性。此外,军方及其文职顾问是反对政党的,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剥夺了人民的权力”。[13]军政权也放弃利用国内现有的政党,其主要原因在于军队与当时秘鲁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阿普拉党存在诸多隔阂与宿怨。自1932年起,军队和阿普拉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当时,阿普拉党的好战分子突袭并攻占了特鲁希略的一个军营,大约60名作为俘虏的军官和士兵被残酷杀害。军队对此进行了报复,约1000名特鲁希略男性被行刑队处决。该事件给军队和阿普拉党造成了永久的、无法弥合的裂痕。20世纪30、40年代,阿普拉党多次试图夺取秘鲁政权,却均告以失败。军队的极力反对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样更加大了两者之间的鸿沟。[14]军队对秘鲁共产党亦存在严重的戒备之心。此外,基督教民主党实力较弱。至关重要的是,军队目睹了议会政治的低效率与腐败,极力杜绝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最终,贝拉斯科军政府选择了第三种形式,即关闭议会,排斥传统政党,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军人执掌最高权力。他们在后来的统治中逐步采取了职团主义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用以连接国家与社会,搭建起民众诉求与政府决策的桥梁。
三、职团主义实践-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
1971年,秘鲁全国范围内爆发教师罢工、矿工和糖厂工人游行事件,这使贝拉斯科军政府意识到建立组织,是作为国家和民众之间调解者的迫切需要。1971年7月22日,革命政府颁布了18896号社会动员法令。作为该法令的执行机构,“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正式建立。军政府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寄予厚望,在其初创时给予了约900万美元的公共财政支持,并配备4800名工作人员。[15]“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整合了8个与秘鲁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组织。这8个组织分别是:通过特别立法创建的经济发展国家基金会·国家发展公司·公共事务委员会、新城市发展国家办事处、社区发展全国办事处、合作社发展全国办事处、社区发展总代理处、农民组织机构、农民社区机构、土地改革促进和推广机构。[16]“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内部划分为6个基本领域:劳工、农民组织、城市强占定居者和其他落后城市地区的边缘城市人口、农村无产阶级、青年人以及文化和专家集团。[17]这6大领域基本囊括了秘鲁社会的大部分。
(一)“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目标
18896号法令规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全国人民自觉、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项任务为最终目标。其具体目标包括:(1)授权、领导、组织全国人民,以补充形式参与其他部门的活动;(2)促进社会利益团体的发展,比如合作社、社会利益土地协会(SAIS)、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及其他同类组织,不介入各部门各自的技术职责;(3)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交流尤其是对话。[18]
作为负责社会动员的主要机构,“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负责规范整个公共管理机器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其中心原则是“没有组织就没有动员的可能”。这个组织动员的过程将最终形成一个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之上的全民参与的民主社会:团结一致而非个人主义的道德秩序;以社会财产所有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基本上自我指导的经济;政治秩序不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寡头所垄断,在社会和政治机构中不设中间人或争取最少的中间人,决策权要直接扩散到建立组织的男女手中。[19]“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重要发言人德尔加多(Delgado)提出,社会动员过程必然包括参与,但不只简单地意味着组织民众举行公开的游行和示威,而是更直接地、更现实地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过程来改变秘鲁社会的权力结构。为此,德尔加多提供了两条互补的基本道路:一是通过结构改革以改变权力与经济财产的关系;二是民众参与以协助实现经济和结构改革。于是,“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 为达成这一目标促进和支持人民的组织,告知各社会集团政府有关社会改革的意义以及他们与革命理论、与当今社会、与革命建立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系,为民众提供向政府传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并执行为促进和支持民众自由而民主的参与的基本活动。总之,“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旨在协助秘鲁新社会革命建设的各项具体任务。此外,“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还负有两项主要政治任务:从长远看,促进新的国家形式的出现;从近期看,动员民众保卫支持革命。[19]
从创建一个全民参与的民主社会的远期任务,再到更实用主义的支持政府和促进发展,“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拟定了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中期目标是:(1)将民众部门纳入到结构改革进程之中;(2)扩大现有的和将来改革的社会基础;(3)促进民众部门参与到发展的规划中来。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全体秘鲁人民参与的全新社会。为达到这些目标,“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将从上到下组织秘鲁社会。
(二)“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层级结构
在结构上,“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基层被分为4个主要层级:国家办事处(Oficina Naci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 Social)、大区办事处(Oficina Regi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 Social)、区域办事处(Oficina Z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 Social)、民众参与推广小组(Equipos de promoción de la participación popular)[20]。每个层级有不同的分管领域和任务职责。处于最高层的国家办事处,负责全国政策的规划以及为10个大区办事处和70多个区域办事处提供支持。国家办事处的支持主要包括5个领域:培训、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金支持以及合法性和管理支持。当有基层组织需要得到上述所列的支持服务时,国家办事处就层层将其下达给大区和区域办事处。值得指出的是,要获得国家办事处的前述支持,首要前提条件是基层组织必须受到官方或“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支持。这一点,成为研究者给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冠以职团主义称号的重要依据。根据“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总体目标,其重要使命即是动员秘鲁人民。而要动员秘鲁人民,以将权力转移到人民的组织手中,首先需要培训人民,以使人民做好准备接受并行使权力。基于此,“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负有重要的培训任务,主要培训职责在于使培训制度化并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使培训的政治思想、技术和组织化方面系统化和标准化。除测试和评价培训方法外,国家办事处还发行并分配用于培训的材料。此外,国家办事处拥有支持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对各类组织予以合法性认定和支持的权力。
大区办事处是连接国家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的重要衔接点,是“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主要计划和管理机构。大区办事处接受国家办事处的政策指令,又搜集来自基层的区域办事处的诉求,并制定出规划和设想,以使两者相协调。然后它们形成特定的方案并制定出预算,并负责支持执行这些方案。因此大区办事处层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预算和管理控制来指导和协调地区事务。[21]70-71区域办事处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和民众直接连接起来。在区域办事处,制定计划不再是专家的工作,而成为普通民众的工作。普通民众提出影响自己所在社区的问题,并制订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同时争取其他民众支持这些计划。因此,区域办事处被认为是有组织民众直接公开参与成千上万计划和活动的重要连接点。区域办事处主要通过工作在社区的推广者(Promoters)来了解民众需求和开展工作。推广者们在沟通民众诉求和政府政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真正深入基层社区、最接近民众的。推广者们直接深入社区,了解民众生活存在的问题和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以及民众自己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向上汇报。在层层上报后,在国家办事处形成政策,再反馈回基层,由推广者们带领民众执行。[21]71通过这种方式,民众逐渐参与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三)“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活动领域
“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村和农民组织。在“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成立前,部分农民就已经加入到系列农业协会、合作社和各类组织中。1972年5月,根据19400号法令,与出口寡头密切相关的全国农业协会(National Agrarian Society) 被取消,与之相伴的是所有之前15年建立起来的农民组织的合法性都将受到重新认定。该法令特别指出,新成立的农民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是:支持公共机构为农村地区制定的政策,与政府处理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计划合作。法令明确限制各农民组织卷入政党政治,并要求它们到“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注册以便获得合法身份,而注册也是它们具备基本合法权利的前提条件。此外,当农民组织与国家的既定目标相悖之时,法令也赋予“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权力来解散它们。最终建立起来的国家农业总会(National Agrarian Confederation),成为全国农村和农民组织的最高组织。该组织成为国家制定农村和农业政策的主要数据和建议提供者,也是协助国家推行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主要依托。它基本垄断了农民和农村通向政府制定决策的传达渠道。[22]71-72
“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进行组织和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新城市(强占定居者们的聚居地)。贝拉斯科政府组建不久,就建立起新城市国家办事处,负责处理强占定居者们的问题。“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成立后,该机构并入其中成为新城市部门。“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工作人员进入城市贫民窟,帮助建立邻里组织和社区组织,负责邻里和社区组织领导人的选举。例如,“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制定了一系列当选组织领导人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包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正式合法的婚姻,此外不能有犯罪前科和政治背景。“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还鼓励在新城市社区建设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建立信用社以积累资金用于社区发展的各项开支。政府希望通过诸如此类方式,使强占定居者的具体要求得到革命政府的满足,以消除他们的政治情绪。[22]75-76“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成功进入贫民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有权赋予强占定居者合法的居住权。这使强占定居者非法侵占的土地获得了合法性。另外,“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工作人员通过进入贫民窟,带领社区居民主要依靠居民自助力量,加上少量政府资助,开展修筑道路、铺设管道、提供自来水等公共服务,使得贫民窟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因而得到贫民窟居民的支持。
政府也试图将青年人的活动组织起来。国家办事处的青年人指导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发展学生和青年组织。这些组织被细分为新城市青年组织、农村青年组织、城市青年组织。在城市中又划分为小学&中学青年人组织、学生工作和生产中心、志愿者组织和大学生组织。农村组织、核心城市组织被最先组织起来。1974年,“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组成一个大学生的全国组织。由于大学生是主要的社会批评者和激进主义分子,也是未来的专家和技术工作者,因此被认为是革命进程的基本力量之一。事实上从1964年起,通过国家办事处的青年人组织办公室,秘鲁学生就参与到了政府发起的发展计划中。1972年,一个全国范围的志愿者活动开展起来。1974年,成立了劳动人民大学(Trabajo Popular University)。劳动人民大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劳动人民大学在农村和农民社区的具体活动,加强大学生与国家现实的联系,支持学生志愿者活动的组织,支持革命进程;通过参与到当地的社区计划,促进工农团结。
除了上述3个领域,“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还渗入到社会其他部门,诸如工厂的工人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组织尤其有力。政府规定,凡是雇佣工人超过6人的企业必须建立工人委员会,让工人逐步参与工厂的决策和管理。到1976年中期,大约15%的秘鲁工人已经参与到一个或几个基层参与结构之中。[23]23但是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
(四)“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结局
“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在渗入强占定居者和建立被批准的社区组织方面最具成效。据报道,到1972年后期,2/3的利马新城市区域已经根据“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标准进行了改造。[23]184-185其次,通过分配土地所有权和其他批准管理权力,通过只许官方承认的组织接近政府,“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使得反政权的力量要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对领导选举、组织结构和资源途径的控制,使得“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处于一种极占优势的地位来控制公共政治活动。
但是,“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也遭到各方抵制,这成为其失败的直接原因。1973年,一篇题为“为什么‘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受到攻击?”的文章中总结到,在当代秘鲁历史上,很少有组织像“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那样遭到传统集团各种形式的攻击。该文承认,资本主义者、旧式寡头、极右分子、政党及其领导、管理者、官僚,所有人都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攻击“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文章还列出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受到攻击的9条理由:(1)“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是一个或即将成为一个官方党;(2)它的章鱼式的结构无处不在,渗透到整个秘鲁社会;(3)它是各种激进主义的温床;(4)它操纵控制基层群众组织;(5)它想取代劳工联合会;(6)它想变为新的劳工联合会;(7)它想控制农民组织;(8)它是一个职团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实体;(9)它妨碍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23]175-1761975年,对秘鲁市民的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除了登记、领取身份证、在社区选举中投票外,“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与自己无关。“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还受到各种暴力攻击。仅在1973年,“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至少6个地区的办事处被占领、洗劫甚至烧毁,而肇事者是各式各样的罢工集团,包括学校教师、建筑工人、矿工、渔民、钢铁工人和农民。由此可见,“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受到的抵制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部门。
伴随贝拉斯科军政府的倒台,及其实现秘鲁社会根本性变革愿望的落空,“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勉强维持至1978年最终解体。
四、职团主义实践失败原因分析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采用职团主义的组织形式,使墨西哥维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同样,巴西瓦加斯政权也被认为是职团主义的成功案例。但是,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却被公认为是失败的。
首先,军方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缺乏坚强的支持后盾。相关学者在分析“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失败的原因时,认为首要的、最基本的障碍是军政府在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支持上含混不定。[24]尽管在其初建时,“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极受军队重视。其领导人利奥尼达斯·罗德里格斯·费格罗阿将军,是总统贝拉斯科的挚友,也是10月3日革命领导指挥小组成员之一。最初,由于拥有数目可观的财政支持、庞大的人员队伍、领导人在内阁中的显赫地位,“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一时万众瞩目。但好景不长,“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使军队在各种反政权势力对政府的公开批评面前首当其冲。由于它在全国范围的动员活动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批评目标;由于它不能及时满足各方需求经常成为批判对象;由于其工作是官方性质的以及受官方支持而成为理所当然的众矢之的。在强烈的反对面前,军政权不是强化“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资源,而是撒手不管并拆台。当“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与其它政府机构争夺管辖权时,军队往往支持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将对劳工联合会以及工业联合会的培训剥离到“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管辖领域外。军队之所以这样,是不愿意因“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强大而削弱军队。
其次,“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结构上存在弊端和不足,这是不容忽视的。在“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组织之下,秘鲁成为了一个围绕系列符合职团主义概念的基层组织而构建的国家。[25]军政权承认了先前的一些组织,但大部分组织还是由“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这一官方组织发动并组织。秘鲁的大部分经济生活被分割为印第安社区、各种合作社、各种经济社团(工业、渔业、矿业等)。每一个这样的组织,都是在政府起草组织法令之下的、独立的、政府承认其合法性的个体以及最终依靠政府的功能实体。[25]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严密职团结构相比,秘鲁各式各样的合作社、印第安社区等显得尤其混乱。“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第二个严重障碍是由于因分权的管理结构和技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内部矛盾。在1974年国家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推广者抱怨区域办事处管理者以垂直的威权主义方式指导他们的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自己处于双重权力结构的底部,收到的是大区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自相矛盾的命令和指示。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推广者于是设法规避大区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直接依靠国家办事处获取资源和行动指导,但也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1)官员们在实施地区政策上相互孤立和缺乏沟通;(2)培训有的根本没有进行,要么时有时无,而有时候培训又是其他机构进行过的重复内容;(3)许多培训课程由利马的国家办事处官员制定,他们根本就不与大区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的官员进行交流。因此,从一开始,秘鲁的职团结构在组织的科学性和管理的力度上就存在着弊端和不足,这为其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再次,秘鲁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使得庇护主义难以实行,民众得不到实惠因而也不支持“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实质上,拉美的职团主义是与庇护主义如影随形的。庇护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恩主-恩客制度,恩主为恩客提供利惠和庇护,换取恩客的选票或政治支持。这就表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忠诚取决于物质刺激和回报。这种庇护主义在拉美一直根深蒂固。比如拉美职团主义的样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采取的职团主义组织形式的成败,全系于庇护主义提供的利惠多寡。在进口替代时期,革命制度党为工人和工会提供的利惠,主要包括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特权:保证工人最低工资水平,提供住房、社会保险、医疗、基本生活用品等社会福利和经济援助等。为农民提供的利惠主要有:领导土地改革,给无地农民以土地;国家给予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水源和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供应等。[26]94于是,在工人、农民都获得实惠的前提下,他们乐于支持革命制度党,使职团主义的形式能够健全存在。但是,随着墨西哥日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革命制度党支配的资源锐减,利惠来源枯竭,工人享受的福利待遇每况愈下,庇护体系难以为继;经济自由化废除了进口替代时期的国家保护政策,对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生产补贴,价格保护逐步废除。利惠的逐步减少,降低了工人对官方工会组织和农民对官方农会组织的忠诚程度,职团部门对工人和农民的控制能力也遭到削弱。庇护体系的松动导致职团结构功能障碍。庇护体系瓦解之后,职团主义也空具形式。[26]62
秘鲁的职团主义也一样建立在庇护主义基础之上。在贝拉斯科政权时期,精英和民众关于何谓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目的和为何个人需要参与政治的认识有本质上的不同。正如霍诺维兹(Horowitz)所指出的,民众渴望的是基于个人对社会-经济的满意,而不是政治动员。对穷人来说,把参与作为结果是毫无用处的,它只是获得物质利益结果的手段。如果政治体制或干预型官僚机构无法创造物质利益,不满就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27]由此可见,现实的普通民众并不在乎什么政治权力和参与,他们是想得到具体而实惠的利益,也即恩主的庇护。
从秘鲁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最初在农村村社和新城市社区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主要也是基于村社的无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小块土地,得到了实惠;新城市社区的强占定居者可以从“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那里获得土地授权。因此,“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而当农民和强占定居者们得到这些后,他们还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实惠,于是对军政府寄予了厚望,但军政府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将底层人民的愿望和诉求传达上去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兑现其承诺。因此,农民和强占定居者将不满发泄到“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上。这是“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四面受敌,处处遭到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职团主义政治参与形式的失败,最根本的是归结于秘鲁的经济问题。在贝拉斯科推行的经济改革中,他将石油公司和外资银行等收归国有,触怒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国内,他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征收大地主的土地,也触动了这部分人的利益;在城市的工厂里,贝拉斯科又建立工业委员会,对财产所有制度进行改革,逐步提高工人在工厂里的股份份额,工厂主只占50%,这种做法极大地打击了私人资本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贝拉斯科政府是想利用广大的中下底层工人和农民作为政权的支持基础,以这一部分人制衡上层有产者。但是,它迎合中下层的胃口,获取他们支持的愿望也由于秘鲁经济上的困难而落空。所以,贝拉斯科政府受到了左右夹击,同时腹背受敌。
归根结底,秘鲁当时面临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大量边缘人口排斥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之外,这部分人口需要整合进社会;另外,当时秘鲁刚刚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国家需要大量资本积累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要实现前一个目标,就需要用再分配的物质利益刺激手段,国家政策向左倾斜。而要加速工业化发展,就要求限制消费,积累资金用于再投资和再生产,国家政策又需要向右倾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化解这一对根本的矛盾,需要高超的政治手段和经济头脑。就当时的秘鲁政府来看,不管是采用职团主义的组织形式,抑或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只要这对矛盾解决不了,任何一届政府都会下台。
事实上,市民日益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来的主要动力,依靠的是对国家资源增量进行再分配,而不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分配。当经济增长快时,有足够的新资源产生来支持市民参与的动力;当经济增长减慢或停滞时(如1974年后的秘鲁),动力也减少,重点则会转向巩固和控制。[28]至于政治控制问题,政府不得不限制民众政治参与和经济重新分配的需求实现其经济目标,这也是必须的。首先,因为群众压力之大超过了重新分配的潜力,以及重新分配会与更加迫切的加速资本积累相矛盾。其次,政府不愿在国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中,允许其他组织同军队分享或竞争。出于这个理由,政府政治走向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尝试职团主义控制,不仅可对那些与寡头利益相关的组织加强控制,也可控制中低阶层的组织。[29]
塞缪尔·亨廷顿在对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解读中,精辟地分析道:“既想实行根本性变革但又不愿优先扩大政治参与的精英,在夺取政权后推行社会经济政策时,常常有些动摇不定。秘鲁军政府也为这种矛盾心理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秘鲁军政府颁布了一些旨在根本性改造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个典型的军政权对群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所具有的那种顾虑和猜忌。它企图通过设计一种新型的合作代表制和参与形式,将这些冲突的价值协调起来。然而,迄今为止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结果表明,这些新形式日益沦为管理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人们参政的途径。”[30]在亨廷顿看来,秘鲁的职团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多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结语
从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活动来看,“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具有职团主义政治组织的典型特征。[31]它由政府发起建立,其层级秩序以及试图垄断民众与国家之间利益诉求与政策制定渠道的努力,都与施密特关于职团主义的定义极为近似。作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建立的基层组织,成为了唯一合法的、通向政府决策的参与渠道。[32]秘鲁贝拉斯科政府希望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弥补摒除政党和议会之后留下的国家和社会间中介协调组织的缺失,并实现“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无疑,贝拉斯科政府建立“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结局虽然令人唏嘘,但其出发点却是值得肯定的。时至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然普遍面临贫富分化、边缘人群大量存在等问题。如何摸索并找到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组织方式,有效地实现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协调,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改革的有序推进,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依然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注释
①http://countrystudies.us/peru/71.htm
参考文献
[1]Alan Cawson.CorporatismandPoliticalTheory[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22.
[2]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J].TheReviewofPolitics, Vol.36, No.1, 1974:93-94.
[3]夏立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法治[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82-83.
[4]Peter J. Williamson.VarietiesofCorporatism:aConceptualDiscus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8-10.
[5]Alfred Stephan.TheStateandSociety:PeruinComparativePerspectiv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68.
[6](英)贝瑟尔,著.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595.
[7]Jane S. Jaquette. Revolution by Fiat: the Context of Policy-making in Peru[J].TheWesternPoliticalQuarterly, vol.25, no.4, 1972:651-652.
[8](英)贝瑟尔,著.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466-467.
[9]Alfred Stephan.TheStateandSociety:PeruinComparativePerspectiv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136.
[10] James M. Malloy.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A]. in Pike and Stritch eds.//TheNew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StructuresinIberianWorld:[C].60-61.
[11] Héctor Béjar.Velasco[EB/OL]. http://www.hectorbejar.com/docs/libros/velasco.pdf:15.
[12] Henry A. Dietz.PovertyandProblem-solvingunderMilitaryRule:TheUrbanPoorinLima,Peru[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173.
[13] (英)贝瑟尔,著.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471-472.
[14] David Scott Palmer.Peru:Theauthoritariantradition[M]. Praeger: praeger special studies& praeger scientific, 1980:99.
[15] James M. Malloy.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 1, 1974:66.
[16] Henry A. Dietz,PovertyandProblem-solvingunderMilitaryRule:TheUrbanPoorinLima,Peru[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173.
[17]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J].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 36, No.1, 1974:70.
[18] Ley Organica del Sistema Naci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 Social[EB/OL]. http://docs.peru.justia.com/federales/decretos-leyes/19352-apr-4-1972.pdf.
[19]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 in Pike and Stritch eds.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Iberian World[C]:61.
[20] Ley Organica del Sistema Naci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 Social[EB/OL]. http://docs.peru.justia.com/federales/decretos-leyes/19352-apr-4-1972.pdf.
[21]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 1, 1974:70-71.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 1, 1974:71.
[22] Julio Cotler. The New Mod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Peru[A]. in Abraham F. Lowenthal ed. //ThePeruvianExperiment:ContinuityandChangeunderMilitaryRule[C].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71-72.
[23] Henry A. Dietz,PovertyandProblem-solvingunderMilitaryRule:TheUrbanPoorinLima,Peru[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23.
[24] Sandra L. Woy. Infrastructure of Participation in Peru: SINAMOS[A]. in Booth and Seligsan eds. //PoliticalParticipationinLatinAmerica[C]:198.
[25]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A]. in Pike and Stritch eds., //TheNew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StructuresinIberianWorld[C]:73.
[26] 郑振成.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民众主义执政党[EB/OL]. http://202.113.20.226/kns50/detail.aspx?QueryID=38&CurRec=56:94.
[27] Henry A. Dietz,PovertyandProblem-solvingunderMilitaryRule:TheUrbanPoorinLima,Peru[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30.
[28] Henry A. Dietz and David Scott Palmer.Citizen Participation under Innovative Military Corporatism in Peru[A]. in John A. Booth and Mitchell A. Seligsan eds. //PoliticalParticipationinLatinAmerica[C].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Meier Publishers, Inc., 1978:174.
[29] Julio Cotler.The New Mod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Peru[A]. in Abraham F. Lowenthal ed., //ThePeruvianExperiment:ContinuityandChangeunderMilitaryRule[C].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45-46.
[30]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 著.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 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9.
[31] Henry A. Dietz,PovertyandProblem-solvingunderMilitaryRule:TheUrbanPoorinLima,Peru,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183.
[32] Sandra L. Woy. Infrastructure of Participation in Peru: SINAMOS[A]. //in John A. Booth and Mitchell A. Seligsan eds.PoliticalParticipationinLatinAmerica[C].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Meier Publishers, Inc., 1978:189.
The Corporatism Experiment of Belasco Military Regime in Peru——An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ystem to Support Social Mobilization
YUAN Ya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In 1960s and 1970s the Peruvian elites who were headed by General José Velasco Alvarado abandon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liamentary system. Instead by creating National System to Support Social Mobilization they adopted corporatist organization form to mobilize people and make channels between public demands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eru. However, since the vague support of military, the organizational defects of National System to Support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eruvian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corporatist organization form was short-lived and never institutionalized in Peru.
Key words:Peru; Military regime; Coporatism; National System to Support Social Mobilization
收稿日期:2016-02-03
作者简介:袁艳(1980-),女,汉族,四川安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拉丁美洲历史与社会。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专项(12sxlp1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77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6)04-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