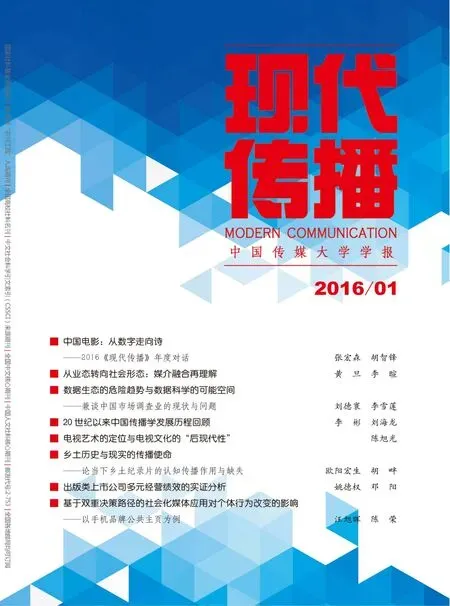简论媒介对于经验“自我”意识的影响
■ 王 瑞
简论媒介对于经验“自我”意识的影响
■ 王 瑞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于“自我”的探索可以具体到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就是“自我”意识的形成。以历史上各种媒介的发展为线索,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具体化认识。换言之,在“自我”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哲学与社会学对于“自我”意识的思考
西方哲学三次转向的核心都是作为个体的“自我”,并且范围层层缩小,对于“自我”研究的指向性愈发清晰。对于“自我”意识认识论的发展,笛卡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世思想奠定了基础。笛卡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证了哲学自我的实在性,这标志着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中的真正觉醒。(1)在笛卡尔之后,对于“自我”的具体认识问题成为西方哲学的争论焦点。在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康德从“自我”意识出发,提出物自体的概念,从而建构了整座康德哲学的大厦。黑格尔继康德之后,也对“自我”意识问题提出了见解:“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2)
西方社会学同样将作为“自我”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同样视作研究的核心。古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斯宾塞的全部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人性乃是社会影响的产物。”(3)斯宾塞的学说可以作为后世诸多关于“自我”是由社会环境所塑造而成这一观点的源头。到了19世纪,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人的“自我”意识问题成为更为重要的命题。随着库利“镜中我”理论以及米德“主/客我”理论的提出,“自我”意识的探寻似乎大功告成。但这个答案还是过于笼统。米德等把环境看成是“自我”得以形成的原因,那么如果再将“环境”中的各个要素加以细分,媒介便可以被视作“自我”意识形成的根本因素。
二、各类媒介对于经验“自我”意识产生的不同影响
所谓经验“自我”意识,简而言之,指的是人如何根据切实的所知所感看待自己。关于“自我”的意识存在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或者称为历史的坐标,另一个是空间的坐标,或者称为世界的坐标。通过这样两个坐标,便确定、认清一个具体的“自我”。以伊尼斯所提供的框架作为线索,以不同媒介的时空偏向性为根据,可以对于经验“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化做出分析。
1.口语媒介:区分“自我”与他人
使得人与动物有所区别的各种表现中,语言是较为明显的一个。发出声音使得人可以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来,这可以看作是个人“自我”意识最初的产生。可以认为,当一个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开口发声的时刻,正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开始。当代语言学提出假说,并不是思维产生了语言,而是语言使思维得以产生。人类的语言显然经历了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进程至今没有完结。最初的语言是单音节的一些叫声,这样的语言形式仅仅能够传达出简单的要求。一旦有意识地发出声音(如向同伴发出警报或是示威的声音信号),就意味着传播过程的出现,而这也就代表着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产生了分离,由此,“自我”产生。
2.文字媒介:“自我”意识的初步确立
社会学家舒茨对于社会世界进行了划分,包括直接经验的世界、周遭世界、前人世界以及后人世界。口语媒介使得“自我”意识在直接经验的世界里找到位置,而文字媒介,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出现则让人开始对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增强了了解。由于文字媒介的重要影响,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二元区分,即把人分为可以使用文字媒介的人以及没有能力使用文字媒介的人。于是,在文字媒介时代,可以使用它的人能够对前人世界以及周遭世界增加了解的可能性。于是,在文字媒介大行其道之后,人对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化,找到了“自我”在历史中、“世界”上的定位,当然这样的历史与世界是不全面的,人对于“自我”定位的解读也是非常狭隘的。但无论如何,人“自我”意识的理解范围得到了拓展。
3.电子媒介:“自我”意识的拓展
在各类电子媒介中,对于个人“自我”意识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电话和广播电视。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媒介也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内化。到了电子媒介时代,这种内化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相比于文字媒介,广播电视所展示的世界更加“真实”。人们通过广播电视可以参与到范围更大的周遭世界之中,当然这种参与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形式。
电话以及广播电视在空间的偏向上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偿。同时,人们借助电子媒介,对“自我”在世界上的定位更加清晰化。文字媒介让人们(可以阅读的人们)对远方世界产生了抽象的认识。这种抽象的认识建立在人们的想象之上,而想象的基础则是周遭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世界。于是,文字媒介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实际上就基于身边所见所感的合理想象。而广播电视媒介则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具象化。如果说文字时代是“见字如面”,那么广播电视就是让人们“真的见面”。在具象认识的基础上,人们的“自我”认知也愈发具体化、形象化。
4.网络媒介:“自我”意识的碎片化
在网络时代,时间与空间对于人们而言成为了需要重新加以定义的概念。网络节目的出现将对时间进行掌控的权力交到了人们的手中。因此,“我愿意、我方便、我选择的时间”就成为了“我了解世界信息的时间”。这个时间与其他人不再同步,所以人们的私人化“自我”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空间的角度而言,近些年来热门的社交媒介彻底改变了人们社交的范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跟自己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进行交流,选择时机以及对象的标准仍然只有一条,就是“我愿意”。可以说,“自我”意识在网络媒介时代真正做到了私人化。“自我”变成了每一个个体的分内之事。
一般而言,人们把信息的作用视作为“消除随机不确定性”,而网络时代,信息的爆炸似乎是在增加“随机不确定性”。人们难以辨别网络世界信息的真与假,甚至会觉得辨别信息的真假本身就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因为真与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呈现的样子。
三、结语
可以看出,从口语媒介时代直至网络媒介时代,人类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整体中的一部分,再到个体的发展过程。而必须加以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种循环的发展,不是一个闭合环形的过程,因为前一个“个体”与后一个“个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前一个“个体”是不知道整体存在、只知道“自我”的“自我”,而后一个则是明知道整体却更愿意只在意“自我”的“自我”。
信息的碎片化也使得“自我”意识成为了碎片。而近现代的思想家在反对由启蒙运动引起的科学实证主义过于强调理性而忽视人性的同时,也纷纷提出对于“自我”意识碎片化地反思。卡尔·马克思提出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率先引起人们的思考,反思人所创造的物对于人自身的控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对于使用者与受众的控制问题日趋明显。
媒介技术对于人类“自我”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加经反思、批判。在做出反思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现已形成的、由各类媒介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因为这样的做法绝不会是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反思,反而会陷入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循环之中。以先验的思考为共时性的纵轴,以经验的观察为历时性的横轴,在这样的坐标体系中进行关于“自我”意识所受影响的反思,或许会是一种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注释:
(1) 李美辉:《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
(2) 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溯源》,《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
(3)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