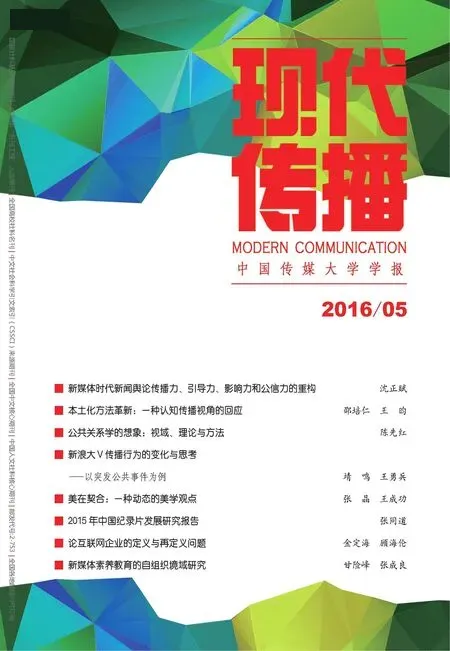社交媒体、“沉默螺旋”效应与青年人的政治参与
——基于25位香港大学生的访谈研究
■ 周 凯 刘 伟 凌 惠
社交媒体、“沉默螺旋”效应与青年人的政治参与
——基于25位香港大学生的访谈研究
■ 周凯刘伟凌惠
【内容摘要】近年来,社交媒体对青年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通过对25位香港大学生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四种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现象:观点一边倒、同辈压力大、“小众观点”被放大以及语言暴力。这四种现象对香港青年人在公共事务讨论中自我观点表达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催生了“沉默螺旋”效应。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的实名制和网络暴力妨害了个体观点的自由表达、社会观点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民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现。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理性地审视、辨识和引导。
【关键词】社交媒体;政治参与;沉默螺旋;香港大学生
社交媒体对青年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以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对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巨大: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英国伦敦学生的罢课行动,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年人获取资讯、表达政见、组织行动的重要媒介。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对政治不再冷漠,而是更加主动地介入政治决策的过程之中。
本文基于对25位香港大学生的深入访谈,发现在高度政治化(politicized society)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对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社交媒体抑制了个体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形成了“沉默螺旋”效应,妨害了社会观点多元化与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实现。因此,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理性地审视、辨识和引导。
一、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以BBS论坛、聊天室为代表的雏形期;以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发展期;以Twitter、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APP为代表的繁盛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聚拢了海量用户——截至2014年8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已超过20亿人。①一般而言,社交媒体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与即时性。在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每一个用户不再单纯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以“输入-反馈-输出”的方式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进行处理。在“刊发或播出”的时间节点上不受任何限制,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交互传播。此外,社交媒体呈现个性化与社群化的趋势:一方面,社交媒体提倡“与众不同”的空间文化,即制造、分享、传递个性化的信息;另一方面,利益诉求相同的群体在虚拟空间中互动和聚集,表现出社群化特征。如今,社交媒体不仅是人们通讯联络、情感沟通、人脉拓展的主要工具,并且在公民政治参与活动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学界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个体根据现有制度设置合法地介入政治运行的行为,如选举投票、竞选捐款、参加政党集会等。凯特·肯斯基(Kate Kenski)等学者发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内容鲜活、多样、即时且支持用户互动的特点激发了原本政治冷漠的青年人与女性选民的政治热情,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竞选活动之中。②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社交媒体对选举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社交媒体,政客们必须随时随地通过它回应民众或与选民互动。③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也认为,在美国竞选政治中,社交媒体能够有效拉近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距离,是政治沟通、政策协商、资金募集的重要工具。④因此,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促进了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即时互动,成为影响选举政治的关键要素之一。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国家日常政治运作之外的公民行动,例如聚众闹事、示威抗议、骚乱暴动等“街头政治”。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亚历山大·赛格博格(Alexandra Segerberg)认为,社交媒体赋予个体以信息传播、组织动员的力量,传统的集体行动已转变为个人化的联结行动(connective action)。⑤默林那·利姆(Merlyna Lim)指出,社交媒体有助于个体扩大抗争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争取社会关注或寻求第三方(如社会精英、媒体等)支持,从而有助于维系抗争行动的进行。⑥针对中国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杨国斌、邓燕华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降低成本、提升集体认同和创造新机会可以促进运动动员”⑦。吕德文则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指出,社交媒体作为“弱者的武器”有助于抗争者争取舆论关注、社会同情及法律援助等外部资源,以弥补弱势群体的劣势并迫使地方政府作出妥协。⑧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社交媒体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论断持怀疑态度。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指出社交媒体实际上助长了“点击式参与”(point-and-click activism),即个体仅仅通过“转发”或点“赞”的方式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却不愿意亲身参与线下活动,其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在点击鼠标的那一刻便消散了。⑨娜塔利·芬顿(Natalie Fenton)和维罗妮卡·巴莱西(Veronica Barassi)发现社交媒体虽然为个人的观点表达和行动组织提供了工具,但也导致了个人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模式(self-centered participation)。⑩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则认为网络传播技术存在数字鸿沟效应(digital divide),即社会成员对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存在差异——在网络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穷困人口、老年人及教育程度低的社会群体有可能无法有效掌握这些信息传播工具,因而在公共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⑪因此,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正引发愈来愈多的关注和思考。
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的逻辑关联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视角,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社交媒体的功能及政治参与的方式进行理论分析,而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为了进一步探析社交媒体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以香港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探析在高度政治化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对独立个体的实际影响。
二、实证分析:高度政治化社会中的社交媒体
选择香港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两点考量:首先,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香港的普及率高,对青年学生几乎全覆盖。⑫其次,近年来香港大学生频繁发起或参与一系列的集体行动及其他政治活动,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香港也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公民政治参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因此,对香港青年学生的访谈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在抗争性(contentious)政治行动高发地区社交媒体对个体参与行为的影响。
本文以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确定受访对象。受访者的筛选标准是:第一,在香港的学习生活经历至少一年以上;第二,本人经常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体(每天至少登陆一次)。在田野调查期间,共计完成访谈案例25例,其中,男生15名,女生10名;从学历来看,本科生9人、硕士生9人、博士7人。受访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多元,涉及法律、政治学、医学、计算机、物理学、文学、教育学、机械工程、经济学等专业。每个访谈均由2名访谈人员完成,采取半结构式的问答方式,一人负责访谈,另一人负责记录和补充提问。访谈开始前,我们向受访者说明了访谈目的,并事先征得所有受访者的同意,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全程录音。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逐字逐句转录成文本资料。本文作为研究结果呈现,为了使访谈者的叙述便于理解,我们在逐字转录的基础上,对访谈者的口头叙述进行了“标准化”的文本转化处理,即删除了访谈叙述中的口头语、无实质意义的重复语句。这一基于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不仅为理解香港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交媒体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实际作用。
Facebook是香港大学生最主要的资讯获取渠道、虚拟互动平台及策划活动工具。受访者均表示他们通过Facebook联系朋友、了解新闻资讯、追踪社会热点、讨论及分享消息、组织线下活动等。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香港青年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存在四种较为突出的现象:观点一边倒、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大、“小众观点”被放大以及语言暴力。
1.观点一边倒
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人们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与发布者。社交网络为个人提供了表达个性化意见的空间与平台。然而,在现实中,许多青年学生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中所形成的虚拟“意见气候”影响,不敢自由“发声”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导致社交媒体上的观点往往呈现“一边倒”态势。
“其实Facebook本身有筛选功能,它只会把你亲密的朋友的内容呈现在你的Wall上,其他80%的朋友的信息你未必能接触到,除非他(她)转发的内容特别有意思,特别多人赞。所以我每天接触的信息都是那几十人的。”(访谈代码20150804NJQZK02)
“那段时间(占中期间)Facebook上面信息一边倒。Facebook上信息看多了,会潜意识地被洗脑。”(访谈代码20150804ZKLW01)
“我感觉网络世界里的Facebook和现实社会的情况也差不多。支持泛民的那些就比较积极。但那些建制派的就显得中庸些,好像是沉默的大多数。”⑬(访谈代码20150804NJQWL03)
“大家很少进行深入思考,草草得出结论,并且常年累月的同种信息的进入造成严重的洗脑。《苹果日报》等新闻传播极快的原因可能也与此有关。”(访谈代码20150804ZKLW02)
“Facebook很高效,青年人们不思考,看到新闻就转发。”(访谈代码20150804ZKCBY02)
从理论上讲,青年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信息是海量的、多元的,但实际上对于个体而言,其在社交媒体上所获得的信息严重同质化——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不断向用户推送其阅览过的类似信息,从而影响青年人对社交媒体上“意见气候”的判断。例如,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苹果日报》《明报》等一些本地媒体极为擅长利用Facebook吸引青年读者,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融合图片、视频与文本的新闻报道,许多青年学生出于好奇而点击阅读。从这一刻起,Facebook便会不断地推送类似的新闻报道和资讯,并将个人Facebook好友对此新闻的转发或点“赞”等消息全部传输过来,形成一种“众口一辞”的假象。青年学生长期沉浸在这种“一边倒”的网络氛围之中,不利于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树立正确的政治认知。
2.同辈压力大
同辈压力是指个体因担心被同伴(即与自己年龄相仿或所处地位、环境相似的个体)疏离、排挤或否定而被迫顺从他人的心理状态。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香港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承受着较大的同辈压力,在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时往往不敢畅所欲言。
“理论上我们在观点表达上机会是平等,但有时为了顾及身边朋友的态度,避免冲突,我会倾向于不表达。”(访谈代码20150805NJQLW01)
“当你表达自己的言论时,大多数人都会看到,就算你和他(她)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也能看到你的言论,因此如果我是蓝丝带,大多数朋友是黄丝带,这时我宁愿不发表自己的言论。”⑭(访谈代码20150804WSHMYQ01)
“Facebook上的‘反对派'言论已经占据了主流,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同辈压力,而且严重的进攻性使支持(政府)派不敢发表言论。”(访谈代码20150804NJQWL02)
“因为我在Facebook里的朋友越来越多,站在不同政治立场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我还是觉得不要去伤害不同人的感情。”(访谈代码20150805LWWSH01)
“那段时间(占中运动),我看到言论都还好,比较温和,因为关注的都是朋友,说话都会留有余地。像我自己说话都比较克制。”(访谈代码20150804WSHMYQ02)
“以我个人而言,即使我认为正确的言论也不太会去转发,可能只是点‘赞'一下。Facebook现在逐渐变成只是展示图片的地方。我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些言论,被‘反对派'朋友注意到的话甚至连朋友都做不成。”(访谈代码20150804ZKLW02)
对于许多青年学生而言,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表达个人观点容易受到网络“朋友圈”的影响。一些个人迫于同辈压力而倾向于隐藏自己真实的主观意见,或回避与朋友进行观点交锋,甚至违心地转发一些个人内心不认同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因表达个人观点而承受的心理压力,然而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准实名化属性却限制了人们意见表达的积极性。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大多数成员是亲友、同学或同事,还有一些成员是至少有过一次接触的“朋友”。在这种“准熟人圈”环境之下,个人在表达意见时难免有所顾虑。一旦个体的“朋友圈”内出现某种“铺天盖地”的导向性言论之后,原本没有特定态度或持相反意见的青年人,也会因为周边人频繁“发声”而受到影响,甚至产生一种被裹挟的压力,抑制了个体自由表达的意愿。
3.“小众观点”被放大
作为互动性的虚拟空间,社交媒体不断将利益诉求、情感情绪、思想观念等相似的个体从纷繁复杂的大社会中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团体。小团体技巧性地利用社交媒体“制造舆论”或“大造声势”,可以将“小众”观点不断放大并营造成为一种强势声音或“打造”成社会主流观点。在香港社会,社交媒体已经演变成了“小众观点”自我放大的主要平台和工具。
2.在对晶体管进行调试和设计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排除一切影响晶体管调试和设计的影响途径,这样做的原因是在于晶体管的抗干扰能力不强,没有良好的保护性能,对于外部影响较为敏感。在对晶体管调试和设计进行保护的过程中,还要对整个装置进行实时监督和测试。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香港青年人在政治上都很亢奋,只是小部分,低于三分之一,只是这些人把声音说出来了而已,其实大部分不发声的人的观点被掩盖了。”(访谈代码20150805NJQWL05)
“以前我会说肯定代表民意,现在就会觉得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social media的意见更多代表一些青年人。我觉得,某一个意见的声音太大,就会掩盖了另一方力量。”(访谈代码20150805NJQWL01)
“由于Facebook是最主要的表达言论看法的平台,但是活跃在Facebook平台上的‘反对派'比较多,每逢大事发生,Facebook被同一则消息占据的情况很常见。”(访谈代码20150805ZKCBYMYQ01)
“社交网络上的观点,大部分我是不认同的。网上有新闻的浏览量是17万,但是我认为并不是主流的民意,主要是一些青年人的观点。”(访谈代码20150805ZKCBY02)
“我没有参与过讨论,自己当时在潜水。因为看到发出与‘主流'声音不同的同学都会被围攻,虽然是小部分人,但是声音太大。所以很多人选择潜水,不敢表态。”(访谈代码20150804ZKLW02)
“很多时候就是那些人在作秀,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表达诉求,但是大部分人只是从众,只是为了迎合主流。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跟随趋势。”(访谈代码20150805WSHLW01)
社会舆论本应尽可能体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见,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客观性。然而,社交媒体对社会舆论形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少数人通过策略性“经营”社交媒体和掌握网络话语权,便可将小众观点“制造”成社会主流意见,压制社会观点的多元化发展。对于大部分香港青年学生而言,用功读书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使用社交媒体只是课余闲暇的一种放松方式;而小部分激进的青年却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找寻存在感,动辄在Facebook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病毒式传播”“刷屏”等方式霸占社交媒体的话语空间。更有甚者不惜采取歪曲事实、选择性描述、散播谣言等手段吸引社会关注并且打压其他观点。这种由少数人利用社交媒体而营造出的所谓“民意”并非原生态民意,不仅妨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意见表达,更容易造成公共政策制定失焦的危险。
4.语言暴力
社交媒体虽然是一个高效快捷的交流平台,却存在着语言暴力的问题。社会谣言、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等现象充斥着社交网络。许多受访者表示个人在发表政见时,最担心遭受言语攻击或引发“骂战”。
“我觉得评论可能会引发骂战,担心被别人攻击,有些人就是为了攻击而攻击;我感觉自己承受不来,觉得在上面发言没有意义。”(访谈代码20150804ZKLW01)
“其实,香港所谓的言语自由是另一种方式的言语压制。香港人发出‘偏中'(偏袒中央)一点的言论,也会被他们群攻。”(访谈代码20150804WSHMYQ01)
“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害怕发表自己的言论,因为他们的部分言论不符合‘反对派'的言论,担心受到攻击。所以有些人抱怨这像是一种Facebook上的言论不自由。”(访谈代码20150805ZKCBY02)
“我认为言论自由在Facebook里是有这个问题……在Facebook上,在你的账户里、文章里、分享里,专门留言针对性很强,我想这就是让大家不愿意发表自己观点的原因。”(访谈代码20150805LWZKCBY01)
“我在参与讨论时,争吵讨论的事情也有发生,但极其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围攻。不仅‘反对派'人数多、言论比较有杀伤力,并且进行争论时反方缺少理性的思考常强词夺理,并且存在逻辑漏洞,所以难以获胜、难以坚持。”(访谈代码20150805NJQWL01)
“围攻者们是有组织的,系统的,并不松散。”(访谈代码20150805ZKCBYMYQ01)
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化表达和语言暴力行为减弱了个体政治参与的愿望。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充分保障了个人的言论自由;而另一方面各种谩骂他人的现象却在社交网络世界盛行。“人肉搜索”“骂战”“约架”等现象屡见不鲜,口水战多过讲事实、摆道理,情绪发泄多于理性讨论。这种网络暴力让更多理性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上保持沉默或彻底“逃离”。在香港社会,当Facebook所标榜的个人言论自由变成肆意辱骂他人、用户表达观点意味着随时被人围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演变成党同伐异的战役,这些语言暴力问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必然抑制众多青年学生发表个人言论、参与政治话题讨论以及理性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行为。
三、讨论与建议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于1974年提出了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⑮诺依曼认为,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属于“小众”或“弱势”时,为了防止孤立(甚至是群起而攻之的遭遇)而倾向于保持沉默。由此,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一方的声音越来愈大,另一方意见则沉默下去,沉默的一方又造成了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螺旋发展态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沉默螺旋”效应是否存在于虚拟空间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使得人们从真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不必过度担心因小众观点表达而受到孤立,人们敢于表达与主流声音不同的意见,因而“沉默的大多数”变得不再沉默。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互联网和现实世界并无二致,“沉默螺旋”的心理机制仍然适用于网络空间。基于对香港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本文认为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更容易产生“沉默螺旋”效应,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实名制和社交网络上的网络暴力。
首先,社交媒体的实名制不利于社会成员克服从众心理以达致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以Facebook、Twitter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推崇实名注册和实名社交,因而社交媒体实际上并未完全将个体从真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而只是把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移植到了网络虚拟世界。近年来香港社会正处于政治转型期(political transition),复杂的政治格局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使得青年学生在Facebook等实名制社交平台上发言变得格外谨慎。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每一个人实际上处在熟人圈的交往范围之内,人们的从众心理与“避免孤立”的心理倾向依然存在。个体时刻观察周围的“意见气候”变化,审视优势意见与“少数派”观点。当社交媒体中存在某种“一边倒”声音或主导意见后,许多青年人由于受到同辈压力或对遭受语言暴力的担忧而缄口不言,造成了优势意见的再增势,从而形成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沉默螺旋”效应。
其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的网络暴力削弱了个体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妨害了社会观点的多元化与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实现。客观而言,言语攻击、侮辱谩骂、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然而,偶发性的语言暴力与常态化的情绪化表达存在本质不同:前者具有显著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而后者则具有较强的预见性与重复性。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助长了常态化的情绪化表达等非理性行为,妨害了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意愿。以香港为例,不可否认,大多数香港青年学生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愈加了解和关心香港政治发展,但现实生活中频繁上演的政治争拗蔓延至网络空间,理性思维让位于情绪化表达,合理的意见表达在非理性的言语攻击之下难以实现。本应鼓励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虚拟公共领域充斥着情绪性、盲从性及非理性的个人行为,而大多数社会成员由于个人观点得不到应有尊重和理性回应而趋于沉默。网络暴力在社交媒体上一旦占据上风不仅扼杀社会成员理性政治参与的意愿、加剧“沉默螺旋”效应,而且将影响政治发展所需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活力。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而言,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的“沉默螺旋”效应无形中阻碍了社会成员形成健全的政治认知以及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现。伦纳德·毕福勒(Leonard Beeghley)将政治认知和政见表达视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提出了“认知参与”(cognitive participation)和“表达参与”(expressive participation)的概念。所谓“认知参与”,是指公民通过收看电视新闻、收听广播报道、阅读报纸杂志或经他人告知等形式了解政治资讯、增加政治知识并形成个人政治认知的过程。而“表达参与”指公民与他人就政治问题进行观点表达、意见交换或互相辩论的行为。毕福勒认为,认知参与和表达参与虽未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却是个体采取参与行动(如投票助选、接洽官员、示威游行等)的先决条件,属于政治参与的初级阶段。⑯迈克·戴利·卡必尼(Michael X.DelliCarpini)等也认为,个人关于政治的话题讨论或闲谈皆属于宽泛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着公共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及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⑰事实上,只有不同观点相互碰撞才能形成更加客观公正的政治认知。社交媒体上的“沉默螺旋”效应实际上不利于社会观点的多样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长远来看必将妨害公民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践与发展。
在社交媒体时代,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既可以满足个体目的性的需求,如获取资讯、联系亲友、组织聚会等;又是社会成员借以进行聚合与互动的重要虚拟空间。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和空间属性相辅相成,形成了对公民政治参与强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如微信、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已深刻融入中国青年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对香港青年学生的访谈研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交媒体对个人意见表达、社会观点多样性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主动加强对社交网络的有效监管和适度引导。
(本文系2015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课题“高校思政课网络教学互动的有效性研究”〔课题编号:2015-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2014年8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超过20亿》,http://yjy.people.com.cn/n/2014/0905/c245079-25613186.html,访问时间: 2015 年12月21日。
② Kate Kenski,Bruce W.Hardy,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The Obama Victory: How Media,Money and Message Shaped the 2008 Elec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s,2010.pp.251-302.
③ Thomas Friedman.The Rise of Popuralism.New York Times,2012-06-24.
④ Bruce Bimber.Digital Media in the Obama Campaigns of 2008 and 2012: Adaptation to the Personaliz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2014(2).pp.130-150.
⑤ W.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54.
⑥ Lim,Merlyna.Clicks,Cabs and Coffee Houses: Social Media and Oppositional Movements in Egypt 2004-2011.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2(2).pp.231-248.
⑦ 杨国斌、邓燕华:《多元互动条件下的网络公民行动》,《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
⑧ 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
⑨ EvgenyMorozov.The Brave New World of Slacktivism.Foreign Policy,2009年5月19日,http://neteffect.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5/19/the_ brave_ new_ world_ of_ slacktivism,访问时间: 2015年12月21日。
⑩ Natalie Fenton and Veronica Barassi.Alternative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Communication Review,2011(3): pp.179-196.
⑪ Pippa Norris.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8.
⑫ Facebook:《91%香港人愛用》,http://unwire.hk/2014/08/21/facebook-hkers/hottopic/,访问时间: 2015年12月21日。
⑬ 在香港社会,本地政党及社会团体大致可以划分为泛民派和建制派。泛民派又称反对派,泛指经常反对特区政府施政并主张实现西方式民主的政治团体;建制派泛指香港回归后支持特区政府的政治团体。
⑭ 在香港大学生中,一些个人将Facebook账户图片换成黄丝带图片以代表支持占中行动;而另一些用户使用蓝丝带图片作为账户图片以代表反对占中的非法行动。
⑮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4页。
⑯ Leonard Beeghley.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view and An Explanation.Sociological Forum,1986(3).pp.496-513.
⑰ Michael X.DelliCarpini,Fay Lomax Cook,and Lawrence R.Jacobs.Public Deliberation,Discursive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Engagement: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4(7).pp.315-344.
(作者周凯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伟、凌惠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