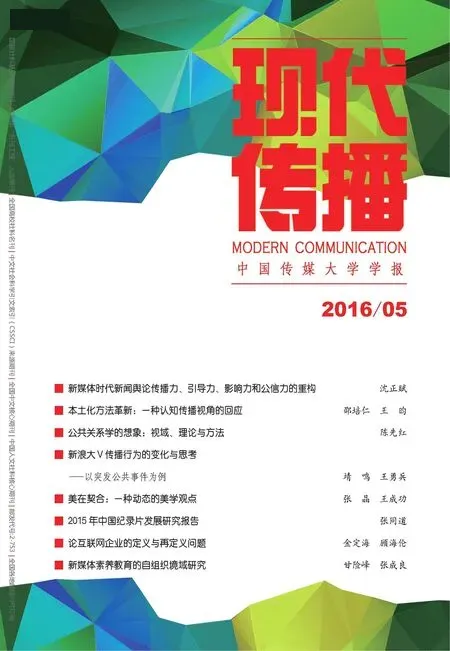电视媒体对彝族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影响*
■ 韩 亮 张 丹 张映兰
电视媒体对彝族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影响*
■ 韩亮张丹张映兰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浩大的现代化浪潮随之而来,影响、促进并改变着村落的发展,尤其是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远在云南省边陲的彝族聚居村落的公共空间,由于电视的到来而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电视媒体作为最普遍和重要的现代化代表,成为村落公共空间发生演变的主要因素和见证者,村落的变革历程就是村落电视媒体的发展历程。本文采用访谈法,走进彝族村落,考察电视进入后,给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电视媒体;彝族村落;公共空间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彝族村落的公共空间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而电视的介入,成为彝族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电视和村落发展的日常生活视阈下,从传统村落与现代村落的对比、家庭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交往空间内容的拓展等三方面,来阐释电视媒体对彝族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影响。
1960年,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自发组成的公共聚会场所和机构”①,他提出的公共空间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能形成公共舆论的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语境传入我国,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概念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最终用“公共空间”概念分析实际问题,促进了公共空间语境在我国的发展。
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属乡村范畴,其概念界定主要参考南京大学曹海林的论述,即(乡村)公共空间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交流、交往。②文中描述的公共空间囊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比如村庄里的跳脚场,从场地本身来说属于思想交流和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从跳脚的舞蹈来说属于乡村文艺活动。二者相辅相成,最终创造了这个生动活泼的村庄公共空间。
一、传统村落与现代村落公共空间的对峙
历史上村落的传统公共空间主要由跳脚场、姑娘房和火塘三者平分天下,它们都是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和现实需求,是村庄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孰轻孰重之分。
但改革开放以来,村落村民充分利用政策和地理优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也加快了村庄变革的速度。其中,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文明大量涌入村庄,打破了村庄的传统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村庄传统公共空间最终无法逃脱不断被挤压、变形,并最终走向没落的命运。
1.传统的跳脚场与现代的电视
“跳脚”是彝族村落居民最主要的集体娱乐活动,已经有上百余年的历史了。村落的跳脚场曾经是村庄里规模最大的村民集体休闲娱乐场所,这里不分男女老少,没有规矩限制,绝对自由奔放,任何一个村民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聊天、唱歌、跳脚,年复一年,在这个空间里打发着冗长枯燥的夜晚。
目前,村落村民的跳脚活动主要集中于红白喜事和传统民族节日,红白喜事的时候还是在村里跳,但跳的机会不多,村落虽说是个大村子,但就红白喜事而言,一年也没有几次;在传统节日时的跳脚一般去邻居姚安县太平镇跳,因为村里人少,加之孩子和学生都不喜欢跳,组织不起来,所以就只能扩大范围,和邻近村的人一块组织。
这种情况笔者也在走访中得到证实,在距离岔河村委会大约200米的山顶上,政府出资给当地村民修了一个跳脚场地,但是因为没有人去跳,从村庄到场地的小路都被两边疯长的杂草淹没了。村支书起贵才对笔者说,以前是小孩子的时候喜欢和大人们一块跳脚,可场地太小,里里外外围了好多个圈,还容纳不下,村民们只能轮流上场,可现在有这么好的场地,就是没有人跳,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看电视的看电视,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这块场地了。
“昨天放羊从那旁边路过,跳脚场都长草了,差不多有一人深了,就一天长一大截,长得太快了。”③
“现在的年轻人啊,太懒了,嫌跳脚把脚跳疼了,天天窝在家里看电视,等我们这一辈老了,跳不动了,就没有人再跳了。”④
村落里最早知道“电视”的村民主要是年轻人,当时大约20多岁(如今50多岁,是村落的主要电视受众群体),他们大多不想拘泥于父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走出村庄,试图在村外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电视”。
自从电视进村后,跳脚场几乎没有人再去跳脚了。这主要源于村落播放电视时间和“跳脚”时间的冲突。虽然也有其它原因导致这种结果,比如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和上学,在村里面的人少,热闹不起来,但是一年四季,他们总会回家几个月,而在回家期间,晚饭后他们也会串门,但串门不是去跳脚,而是看电视。
不知道是否因为电视的魅力太大,这个曾经承载着记忆和期待的传统公共空间已经慢慢淡出了村落人的生活,终将成为历史。
2.传统的姑娘房与现代外出打工
“姑娘房”是云南楚雄聚居山区的彝族所特有的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场所,和各种彝族风俗习惯的条条框框相比,这绝对是一个放松、自由、快乐的场所,是每个彝族姑娘必经的人生驿站、青春码头、抑或爱情的港湾,也是古朴独特的彝族风俗习惯中一道最为迷人的风景,充满诱惑,令人驻足。因为男女青年相会姑娘房的时间和跳脚一样,与电视播放时间冲突,这着实是一件让村落男女青年特别头疼的事。电视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最容易吸引的就是年轻人的目光,和中老年人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生活经验和压力以及更多的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所以,他们是一个最易于接受电视并容易受电视影响的群体。
“我们年轻那会吃完饭就去串姑娘房,喜欢上哪个妹子了就给她唱个调子,看她怎么对,喜欢不喜欢,听听她回的调子就知道了。现在的年轻人晚上电视好看的话,都不想去姑娘房了,就算去,也要等看完电视才去,那时夜都深了,白天干活又累,弦子都弹不动了。”⑤
村落青年男女在姑娘房谈情说爱的生活止于4年以前,现在的年轻人多数都是外出打工或者上学,很少有年轻人还在村落去姑娘房,在家的也不大愿意到姑娘房里住,一是伙伴少了,在姑娘房里也不热闹;二是等看完电视都瞌睡了,不想再走几公里的山路去姑娘房。
姑娘房在当年彝族村寨盛行除了要避开长辈谈恋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家庭住房问题。彝族居民长期居住在高寒山区,经济困难,搭建的房屋除了父母和爷爷奶奶居住的地方外,很少再单独给年轻人(尤其是姑娘)建一个屋子,因为孩子小时候一般和父母一块居住的,姑娘长大也是要出嫁,所以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姑娘住的房子,就用这种集体房屋替代。
现如今,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了,每家每户都有能力给自家姑娘建姑娘房了。所以,这个曾经令多少人神往的公共空间的彻底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出接受新事物、在家看电视都是其中的原因。
3.传统的火塘与现代的客厅
火塘是我国高寒山区少数民族最普遍的伙食炊具,类似于中原汉族地区使用的灶。其产生和发展与各族群所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火塘是在人类把火引进自己的居所后产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先民所使用的火堆是火塘的雏形,……是后来形成的丰富多彩的火塘文化的开端。”⑥火塘的结构因地域、民族而异。云南彝族的火塘主要是在正房堂屋左侧挖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坑(用来烧火),然后把铁钩和木钩用铁链或绳子悬挂在该坑上方的房梁上,再把水壶和铁锅挂在钩子上,这样就可以烧水做饭了。
还有一种是在该坑的周围立三块石头(当地人称之为锅庄),并把水壶和炊具放安在锅庄石上进行烧水做饭,根据彝族传统,火塘的锅庄不能轻易移动,除非迁移房屋,无可避免。现如今,彝族村庄的锅庄石已有铁制三角架代替,它和石头相比,更容易烧煮食物和摆放炊具。彝族人一年四季不离火,在火塘边吃,在火塘边睡,在火塘边交流、沟通、议事。火塘是彝族人家庭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房屋规划、构建的中心,是最能反映彝族人空间感的民居布置。“火塘己成为一个家庭的象征,其文化内涵是人们的空间秩序、伦理秩序、内聚模式和凝聚力的表征。”⑦
近几年来,村落的火塘却没落了。首先从外在形态上看,村落的火塘从堂屋里迁移出去,人们在院子旁边建一间单独的小屋子,火塘重新被安置在此。其次从功能和地位上看,火塘是大不如以前了,和以前火塘安置的空间相比,新空间比较狭窄,其主要功能是做饭,人们吃完饭后便移步到客厅,天冷的时候把事先准备好的火盆⑧端去客厅,边看电视边取暖,而传统的火塘已经被人们遗忘在黑暗中,已经没有人在意火种的保存和延续。
现在的村落,客厅这个在我国民居建筑中历史悠久的空间刚兴起十余年,其前身是彝族的传统火塘,是传统火塘空间在家庭里的延续和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从电视进村开始,或者可以说,村落的客厅是电视的衍生品,是电视在村落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空间。村落村民对自家客厅的改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般家庭条件好的人家都已建起了新房,并在新房屋的建筑过程中设计一间用来摆电视的房屋;有些人家则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没条件建新房,就把原来的安置火塘的那间屋子改造成客厅,方法是前一节所介绍的,把火塘迁移出去。
村落的客厅是随着电视而产出的全新空间,其和电视一样,是个新词汇,不能用彝语表达,但它和电视一样受村民欢迎,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使村落的电视和火塘完全脱离而融入其中。如果没有电视,客厅在村落的境遇还真是个未知数。但是它的产生却实实在在地压缩了村庄传统公共空间,并在这个新空间里面孕育着新的村落故事。
二、电视媒介导致家庭权力的转移
“家庭权力一般是在某种社会文化的引导下进行的,通常看来有其充分的合理性。”⑨家庭权力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如父子、夫妻、兄弟等成员对家庭财产的管理支配权,对生产生活中各项事务的决策权以及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支配权。
村落是一个环境闭塞、开发较晚、文化传统保存完好的一个彝族聚居区,村民大多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家庭主要以夫妻、父母和未婚子女共同组成,家庭结构以夫妻及1至2名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夫妻双方父母组成的直系扩大家庭为主。在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男性(尤其是长者)有权决定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且其它家庭成员必须强制执行;妇女则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在家从父、出嫁随夫,不仅要料理家务、饲养家畜、伺候丈夫、照料孩子和老人,还要下地劳作,且对家中事务没有发言权,必须事事顺从和尊重丈夫;作为孩子,必须遵守礼节、尊重父母,不得违父母之命;另外,老人也因为有比年轻人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经验而备受尊重,老人对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
1.老人的权威去哪儿了
村落位于高寒山区,以畜牧和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艰难,所以村民长期过着靠山吃山、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老人们因为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体验、生产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比如他们教会了子孙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收割,他们掌握着饲养牲畜和保存食物的技巧,他们熟悉通往村外山路上的每个坎每个弯,他们能口述精彩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是年轻人心中的英雄。这种文化传递模式在交通闭塞、没有电视、社会变化极其缓慢的山谷里,一度成为主导力量,影响深远。
公路和电视的到来,它们作为“城市的”和“现代的”代表,打破了村庄的传统封闭格局,使之与外界联系起来。电视里讲述的是一个老人未知的崭新世界、老人无法掌握的海量信息、老人望而却步的先进技术。电视里面声话结合的故事比老人口中的民间传说和冒险经历精彩。年轻人可以通过电视学习和体验,还可以从中学习到新技能和技术。
在这场“电视化”变迁中,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反而成为适应新生活的绊脚石,客厅空间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神龛、没有火塘、没有专为他们设计的“上席”,只有他们无法掌握和接受的电视播放技术和信息传播。这些技术和信息取代了他们的发言权,他们在这个以电视为核心的空间里被失语和遗忘,什么先祖印象、民族传统、老人权威以及他们花了半辈子的心血丈量出来的生活经验都被模糊在电视画面里,最终致使本就缺乏电视信息获取能力的老人在客厅空间里越来越远,而统治村庄几百年的老人传统权威也在这个新空间里消解了。
社会的急剧变革促进了村庄传统农林耕作方式的变化,使年轻人对老人的依赖逐渐减弱,而电视带来的新生活方式和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年轻人能够比老人更快地获取新信息和技术,老人在家庭中的支配权逐渐下降,最终消融在“电视化”的客厅空间里。
2.遥控器的“摇身一变”
电视遥控器是一种远程控制电视机的机械装置,其核心是控制。有它在手,人们便可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轻轻一摁,就可以掌控电视。前文提到过,彝族村落的女人在家中几乎没有地位可言,更没有发言权和控制力。但如今的村落,这种情况却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而出现逆转,村落的遥控器大多数时间都由女人掌控,如果女人要求换掉男人正在看的某个节目,男人们一般都不会反对。
遥控器的摇身一变,似乎成为了家庭权力的象征,“它由谁控制,却是这台电视机前的权力场明争暗斗的关键”⑩。
“家里的电视几乎都是她(妻子)在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一般不和她抢,如果好看就和她看一下,不好看的话不看就行了,找我兄弟聊天去,一样的。”⑪
目前村落的电视大多数时间为女人所有,而男人们则对这种行为持放任自流态度,在相同的空间中,他们把曾经代表着男人的权杖的遥控器交给了女人。在客厅空间里面,这些在传统火塘边和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村规民约限制的女人们获得了精神和身体的释放,实现了个人感情的共鸣和宣泄,客厅空间给长期生活在“男尊女卑”思想观念阴影下的女人们创造了一个巴赫金笔下的人类的“第二生活”,即狂欢节文化。
狂欢节文化是“狂欢理论”的来源,萌芽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后来,巴赫金把这种狂欢节文化现象理论化,“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反抗霸权,建立普天同庆、自由而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⑫。如果说对电视的控制还是一场明争暗斗的权力游戏,遥控器还是权杖的代表,那么女人手中的遥控器无疑是对男权至上的彝族传统家庭权威的反叛和颠覆。
这种具有权力象征的遥控器转让虽然颠覆了传统彝族家庭的权力模式,为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宣泄感情的渠道、表达意见的平台以及对抗权威的机会,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反叛男权斗争的胜利,也没有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是一个男人主动让渡出来的、虚拟的权力狂欢世界。
3.儿子“挑战”父亲的权威
虽然村落村民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性别差距,不过作为夫妻双方的当事人却很少会为这个事情发生争执。但是,爷爷或者父亲和孩子之间却会经常上演节目争端,因为吃完饭后,男人和孩子都不用做家务,一同回到客厅,想看新闻的男人们势必会把孩子正在看的动画片调掉,理由是他就看一会儿,而孩子已经看了一整天,现在该让出来了。
这时,正看得兴致勃勃的孩子就会充满委屈,如果这时遇到个性强硬的孩子,并会去和男人们抢遥控器,要是不允许,孩子们便哭闹得让家庭不得安宁,听到声音的奶奶或者母亲也会出来调节,一般就是抱怨爷爷或者父亲怎么一点都不像大人,和孩子争。最后,爷爷或者父亲一般都会无奈地让出遥控器,重新选择去兄弟姐妹家看,孩子则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其它场合,孩子们一般不敢这样公然违背男人们的意愿,尤其是父亲。在平常的生活中,孩子们都很害怕父亲,比如出去把谁家的庄稼弄坏了、把谁家的孩子弄哭了、对村里的某某人大不敬之类的事情发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父亲知道。当然,如果有天纸包不住火,事情败露被父亲斥责时,从肢体到语言上他们都不会反抗,他们会乖乖地站在父亲跟前,低着头,拨弄着沾满泥巴的手指头,一直到父亲教训完毕,都不敢抬起头。
村落的孩子们只敢在电视机前面和父亲叫板,这里他们会理直气壮的说出自己心中的愿望:“我想看动画片”。并且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而挑战父亲的权威,最后父亲会主动放弃,把客厅的主动权给孩子们。客厅和电视也成了孩子们反叛父权的文化实践场所和有力武器。因为和村庄的传统文化相比,电视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面向大众的电视文化,相对于长者来说,他们是成长在电视时代的先驱者,在这个以电视为核心的新客厅空间中,这里没有代代相传的规章制度,电视是村庄里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⑬。因此,新的客厅空间中,孩子对电视节目的认知并不像对其它事物一样,因为基于老人们的传授教导而必须遵循老人们的意愿,相反,它成为孩子们反叛传统权威的突破口。
三、叙事从日常生活转移到电视媒体之中
和女人们相比,村落的男人对观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具有比较一致的、明确的需求。一般35至55岁左右的年龄群体喜欢看新闻联播和社会与法;55岁以上的人群喜欢看战斗片;20至35岁的青年群体则常年在外打工,在家时间不固定。村落的女性群体也是如此,年轻的都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看电视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妇女。所以村落的电视受众群体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孩子。
1.男人喜欢政治、历史剧
村落男人们的收视行为主要有收看战斗片、新闻信息以及对其进行讨论,三大部分构成。
“我是爱看打仗片,只要遇到好看的,一看起来就挺不下来(挺:彝族方言躺下睡觉的意思),每天晚上都按时看,直到看完为止。”⑭
“现在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爱看电视了,就算看也就只看看新闻和法律,里面有些东西很有用,比如教育孩子呀、了解国家政策呀、知法守法呀,这些都很好的。”⑮
至于村落男人喜欢这类节目的原因,主要还是出于生活环境、经历和需求方面的考虑,爱看战斗片的村民就是想看看仗到底是怎么打的,而且打仗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为大多数村民所知的事件,从时间上、地理上、心理上都离他们不遥远,他们能够理解片子所表现的内容并引起共鸣。
而对于看新闻节目主要是因为村落的生活、社交需要、男性的理性思维模式和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更注重其真实性。在他们看来,新闻节目里的事件是真正发生的、真正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好多内容都关乎家国天下,了解国家的形势、政策有助于他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更稳当地挑起家庭的大梁。
村落男人们看电视讲求实用性,是以追忆和求真为代表的的战斗片和新闻节目为主,他们对这类节目的选择主要有赖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需求,并且把电视信息运用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成为聊天的话题来源和观点佐证。
所以在村落,男人们看新闻不是休闲娱乐,而是一个的正儿八经的学习过程,因为了解国家大事和农业政策是一种有文化、有见识的体现,会被人尊重。村落大部分话题的开头和结尾都源于那句话:“电视上说了……”。
2.女人喜欢“正片”
“正片”是村落女人对电视剧的统称,其主要意思是指重要的、经常观看的电视节目,是为了把它和那些偶尔观看的新闻、广告和综艺节目区分开来。所以和其它地方的女人们一样,电视剧在村落女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她们茶余饭后最主要的闲暇娱乐活动之一。
“我看电视都是看正片,但你说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就是随便看,电视里放什么看什么。这几天看的那个正片我也说不出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它在讲些什么内容,只知道里面的人好像分成两伙,有一伙和我们一样是好人,不做坏事;另外那一伙是坏人,老是把像我们的人打死了。”⑯
那些充斥在电视剧里的,具有家庭日常生活参照意义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冲突延续都和她们无关,她们眼中的电视剧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人,其接受过程大多是对“好人”的担心和对“坏人”恶有恶报的期待。
村落的彝族妇女并不能真正理解“正片”传播者本身的意图,我国题材众多的电视剧在她们面前,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好人”和“坏人”的阐释模式,而对于“正片”传播者的回应,无非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把电视里面的人和村庄里的人对比一番,和传播者的初衷风牛马不相及,是一场没有效果或者效果甚微的大众传播活动。
彝族的传统社会本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习俗,尤其是现在40岁以上的这一代中老年妇女,可以说基本没有受过教育,结婚成家后主要工作就是做好家里的劳动,一般不会出去抛头露面,所以她们的生活圈子仅限于村落及周围不远的村庄。所以她们只懂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而对于普通话,大部分的妇女都是通过电视媒体接触到的,是一个非正式的、随意的、被动的接触过程,所以即便她们在漫长的观看电视过程中学听学说,但要真正理解其字面抑或深层含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她们来说,能运用“好人”和“坏人”的阐释模式,要付出的和克服的远比常人多得多。
在“电视化”引导的少数民族村庄变迁中,普通话是最重要的桥梁,这致使“在现代传媒文化的浸淫中,当地人背弃了自己文化中大多数的东西,转入了对于他们并不熟悉的文化形态的艰难适应中,这一艰难适应首先就是从语言系统上的适应开始的。
四、结语
电视,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产物,作为村落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一方面是村庄生活变革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变革中融入村庄生活,成为村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的村落居民,已经无法面对没有电视的生活。
对于一个村庄漫长的发展历程来说,电视参与其中的30年实在太短,对成长在电视出现以前的村民而言,他们在接触到电视文化时,已经饱受地方知识文化系统的浸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电视在村庄传播效果的实现,而对于和电视一块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还相对年轻,电视传播和制造的大众文化在他们身上得以明显体现。
“电视化”引导下的村落变革是一场由外而内、从物到人的变革。电视首先压缩了传统公共空间的生存缝隙,使其走向消亡和没落,同时又创造出以其为核心的客厅新空间,这直接促使彝族传统民居建造布局的革命性变化;其次它就像一盒粘合剂,把村庄变革最活跃的因素——村民全部吸纳到客厅空间里,促进了他们从村庄向家庭的回归,并通过村民的收视行为对由年龄、性别、权力而划分的传统家庭成员关系和结构因素进行了重构;当然到最后,这种粘合和重构又将促使新的冲突和隔离。
注释:
① 陈晶环:《农村公共空间的转型研究——以华北山区宋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 曹海林:《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③ 访谈对象:张天华(男,58岁);访谈时间: 2014年7月25日,晚上20: 30—22: 00时。
④ 访谈对象:周开贵(男,52岁);访谈时间: 2014年7月20日,晚上20: 00—22: 00时。
⑤ 访谈对象:周强(男,45岁);访谈时间: 2014年7月22日,下午15: 00—16: 30时。
⑥ 杨福泉、郑晓云:《火塘文化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⑦ 张瑞才:《彝族火文化探秘》,《云南消防》,1997年第2期。
⑧ 火盆:选一个底部通洞漏水、不能再使用的铁制洗菜盆或洗脸盆,先把烧烬的火灰垫在盆底,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火灰上,吃完饭端去客厅,这样就可以边看电视边取暖了。烧红的木炭没有烟,不呛人,移动方便,不会把电视以及客厅熏黑。
⑨ 亢林贵:《从父权到平权——中国家庭中权力变迁问题探讨》,《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⑩ 李春霞:《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⑪ 访谈对象:张天华(男,58岁);访谈时间: 2014年8月23日,晚上20: 30—22: 00时。
⑫ 王超:《论网络传播中的草根狂欢——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⑬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代沟》,曾胡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4页。
⑭ 访谈对象:李宗能(男,56岁);访谈时间: 2014年7月15日,晚上19: 30—21: 00时。
⑮ 访谈对象:李宗良(男47岁);访谈时间: 2014年8月4日,晚上20: 30—22: 00时。
⑯ 访谈对象:张天华(男,58岁);访谈时间: 2014年7月23日,晚上20: 30—22: 00时。
(作者韩亮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丹、张映兰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西北省级卫视的困境与出路研究”(项目编号: 11YJA8600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