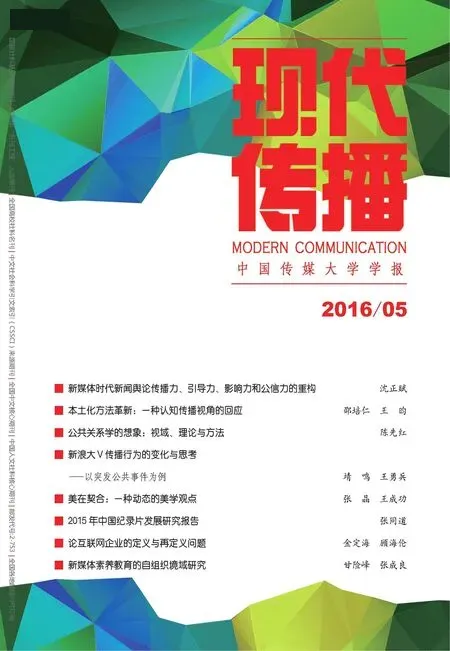视角·话语·内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传播研究*
——以广州为个案
■ 陈 娟 汪金刚
视角·话语·内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传播研究*
——以广州为个案
■ 陈娟汪金刚
【内容摘要】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已成为显学。以广州为个案,农民工城市融入历程表明,受中央各项关于外来工的政策及本地财政相对宽松的影响,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已开始扭转,但面向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资源配置存在以下问题:一、能分配给农民工的公共资源短缺;二、分配给农民工的资源大量浪费。本研究认为,现阶段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应当从组织化、媒介化的视角出发,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在“合作、同化”的话语框架下进行城市管理者、社会组织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对话,一方面逐渐提高农民工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将已有的公共资源盘活,使传播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公共资源;农民工传播
一、文献回顾暨问题的提出
整体而言,中国农民工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诉求。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①他们对于城市的渴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80后、90后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和老一辈相比,他们的诉求由‘进城挣钱、回乡发展'转变为‘进城就业、融入城市';由过去足额支付劳动工资,向参加社保转变;由过去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向要求分享企业经济效益和城市发展成果转变”。②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动机和对未来的预期明显不同于上一代打工者,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中谋生,更希望在这种经历中得到历练,甚至找到新的归宿。
这一背景足以让农民工的社会化研究成为显学。当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市场和该群体个人共同的诉求,其社会治理也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问题在于,如何融入、如何治理?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的研究:长期或者全家都在城市的农民工,有70%左右愿意接受市民化。然而,由于当前的城市发展无法解决这一群体的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一些城市及企业的管理者会在实际的农民工管理中对这一群体进行瓦解,或者说,避免其“组织化”,如“企业通过各种制度和举措,如临时性的宿舍居住安排、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分离工人原有的社会关系等,有意将工人的工作生活置于不稳定的境地,限制工人的社会交往和集体团结,造就了工人的原子化状态”③。肖云、邓睿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遭到了“内卷化”的限制④,但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内卷化”的限制,其本质是当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制度性社会排斥、“去组织化”后作出的一种反击。
2011年,民政部下发《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为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并真正融入城市提供了制度依据。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视角应该落在何处?这种视角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会有什么样的帮助?2.现阶段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容忍边界在哪?⑤在此前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这几乎是一个一直被避开的主题,但这已经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之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话语,其基调和基本框架/边界又在哪里?3.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媒介内容该做什么样的安排?在问卷调查中,他们都绝对地支持一份属于自己的媒体,但涉及具体内容时,他们的想法、观点多游移不定,甚至自相矛盾,因此,我们还在农民工田野调查的原音重现与各种现行农民工管理手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归纳。
在第一轮农民工媒介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被我们抽样的农民工并不适合做深度访谈,他们对城市融入、自身目标等多项指标的理解并不明确,表述也较为困难,随机抽样就很难获得最实际的一手资料,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寻找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在第一轮问卷调查中所获取的10位农民工介绍了第二轮的深度访谈对象10人,这10人又带来了第三轮的访谈对象14人,最终,本研究一共完成了34个农民工的深访。农民工管理部门的访谈则通过私人关系完成,共访问宣传部、公安局治安支队、民政局等部门的科级以上官员8名。本次研究所采用的访问方法是“无结构式访问法”,这种无控制或半控制的访问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打破固有的思维和研究框架,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从而奠定了本文的实证基础。当然,这一研究方法的弊端是导致我们所能获得的访谈对象比较集中,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的普遍性,因此,在研究设计中,第一轮的10位访谈对象互相不认识。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视角:组织化、媒介化
从现有文献来看,中国农民工“组织化”研究时间非常短,集中出现于2006年之后。最初的研究着眼于“组织化”的理论探讨,主要探讨点集中在以组织化这种形式来维护农民工群体权益的同时,通过组织化这种形式来加强社会调控、减少社会冲突、缓解社会矛盾;2008年之后,由于大量企业出现“用工荒”问题,“组织化”以解决农民工权利、政治参与等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但其目的依然是农民工为城市服务;2010年左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显现,随后,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大量出台,农民工“社区化”⑥被提出;2011年中,农民工的“组织化”抗争问题浮出水面,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此类报道;2012年,在农民工的组织化研究中突出了其利益表达功能,“囿于现行国家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制约,维权NGO无法实现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化,难以提升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的效率,不能引起农民工利益表达制度的普遍性变革”⑦。这一年开始,农民工研究的立场开始向农民工本位倾斜;2013年起,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认知模式开始出现,如高传智在增权(或译“赋权”)理论视角下,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怎样运用自媒体增(赋)权,涉及农民工利用新媒体的组织化⑧。也就是这一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的农民工NGO组织崭露头角,并通过QQ群、微信群传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2014年之后,一些农民工组织化的案例出现于该主题的各种研究中⑨,利用网络传播对其进行“赋权”已成为基本认知。
早在二十多年前,西方大量针对新移民社会化的传播研究已表明:新移民的社会化应通过有组织的新移民与土著之间正式或非正式(面对面)的互动展开,辅之以一些传统的纸质文件,如备忘录和培训材料。⑩新移民的城市化与组织化关系也密切相关: 1.与新移民城市化相关的话语必须在发展个人能力的同时强调现存的组织模式;2.当需要建构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时,非正式的面对面的沟通非常重要;3.在城市化的话语中,应当有一些与组织化相关的正面引导。⑪而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提升,城市融入研究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相应变化。目前,先进的传播与信息技术已成为组织内新移民寻求社会融入信息的第二大工具,仅次于面对面传播。⑫
虽然中西方新移民的所处的社会背景有所不同,但其城市化趋势一致。对那些努力寻求信息的人来说,使用先进的传播和信息技术、进行以同化为目的的传播可以有效提升其获得信息的机会,当然,这也有利于他们对环境的适应与同化。⑬结合中国农民工所处的社会背景,当下中国社会尚无可能大面积为农民工提供个性化、“面对面”的城市融入教程,这就为中国当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可参考的实用视角: 1.组织化;2.传播媒介化。
应该说,“组织化”是近年来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形式,“传播媒介化”则是借新技术发展所衍生出的平台,其传播话语的落脚又在哪里?
三、本土化传播话语:合作、同化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个体参与通常是基于很“自我”的动机,始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层次,其主要目标是改善生活境遇。⑭从调研结果来看,现阶段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集中尚处在“希望被接纳”,远未上升至“媒体可以为我做什么”的阶段,更未至“参与城市管理”⑮,这与农民工社会化的累进相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绝大部分的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留在城市的打算,因此,其城市化的时间很短,意识也非常不充分,对城市的理解也十分有限,这就限制了新生代在内的农民工群体所能获取的城市化传播话语。
作为新移民的一部分,农民工在中国也并非一个均质性的群体,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存在着农民工“半城市化”“半市民化”“半融入”“不融入”的特殊现象,这里既有身份无法成为城市市民,但享受城市福利,在城市工作的农村户口人员;也有已经获得城市户籍,但是在居住就业、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等层面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群体,等等。此外,对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对城市化的理解和意愿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非常多元。
“你说,我们图城市什么呢?养老?挣钱多?就是好玩啊!你说留在城市干嘛呢?”“我想我留在这里是因为机会比较多,什么机会啊?当然是挣钱的机会啦。另外啊,城里女仔就是比我们那(江西某县城)好看!(你去追那些好看的女仔了么?)不追也可以看看嘛(笑)!”“我跟着我男朋友来了这里。他说这里好,我就跟着来了。我觉得呢,见过广州这样的城市,肯定没人愿意回老家啦!(广州哪里好呢?)好的地方多着呢,你能想到的没想到的,这里都有。”⑯在如何留、如何融入、为什么要融入城市的问题上,90后缺乏思考,80后农民工的想法则明显成熟、实际很多。“房子肯定买不起,但在这(城中村)住着也行,你问我想不想留在这啊?当然想了。”“我在的企业不错,很早就给我们买社保了,等干够了30年(该受访者固执地认为满30年才能领到社保发放的退休金),我就可以领退休工资了。”“房子买不起也没什么,我们现在租房子也可以,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七岁,在老家读书呢。(寒暑假来玩么?)来啊,每次来我们都要花不少钱。等他们考上大学,上了大学就可以一起呆在广州了。(成绩很好吧?)还不错,我妈是小学老师,一直教着呢。”“我没参加过罢工,但我见过,如果可以加工资,我也愿意去。”与芝加哥学派当年所关注的城市新移民完全不一样,当前农民工这种身心不一、内部分化、城镇化主观意愿极其复杂的状态与该群体的城市管理部门一起,共同决定了目前其社会融入的话语基调。
虽然中央已出台多种文件,并努力推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学者也发出了“大城市人口合理调控应该以‘来者不拒,适者生存'为基本原则”⑰的呼声,但受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限制,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触摸到他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容忍边界:虽然个别官员姿态开明,现阶段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和手段仍以“稳定”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短缺的管理者数量无法匹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管理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并不清楚。当然,这还跟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对弱势的地位有关,对某区宣传部官员的访谈就呈现了这种思维:“你们调研农民工干嘛呀?我告诉你们,社会分为三个群体,精英、中层和底层。你们应该多关注下精英,他们才能为我们社会创造最多的财富!”但提及通过新媒体为农民工“赋权”的想法时,官员们的想法基本一致:“赋什么权?他们有权就造反了!”这也呼应了前文所提及的城市及企业的管理者对农民工的“去组织化”管理。
“在许多集体维权案例中,工人对争取眼前利益更感兴趣,对长远的组织建设却缺乏热情。”⑱当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分化及其对城市的理解、愿望捆绑上管理者对这一群体的主流认知,就决定了农民工组织化传播的话语基调只能以合作、同化为主。一旦走向对抗,基本只会引发“双败”⑲。因此,同样是外来者的社会融入,中西方、甚至中国不同地区的途径可能都不一样。
四、传播内容:从公共资源的让渡到对话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大体可分为三个过程:一是进城就业,二是定居在城市,三是角色转型和社会融合。前两个过程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第三步则需借力公共服务和相关的政策制度。对于不同的城市来说,规模越大,能为户籍居民提供的公共资源越多,也会更倾向于户籍居民,在帮助农民工进行角色转型和社会融合上就做得更为消极。广州针对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提供明显要低于户籍居民,但受中央各项关于外来工的政策及本地财政相对宽松的影响,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已经开始扭转。然而,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仍无法匹配。另外,因农民工群体的消息获知能力有限,部分针对或倾向于农民工群体的公共资源还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这与主办方事前的动员、告知有关。
针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广州市财政局局长袁锦霞表示,需要财政投入的肯定会投入。“我们现在对外来务工群体的教育、卫生、医疗已经投入了很多,教育、卫生等预算已经包括外来务工人口了,但还会再增加。”⑳但这些信息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被农民工接收或感知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一直在改进对周围事物的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又设法提高自身传播信息的能力、速度、清晰度和便利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的技术和方法论的思考,使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㉑为何在农民工身上,会发生对信息的麻木、质疑、乃至抗拒呢?
“姐,像你这样的人少啊,有几个广州本地人会和我们聊天?还告诉我们这个那个的信息?(我也不是广州人……)这些人啊,就是命好,出生在这里,所以就有房子(也有很多广州人住在很破很旧的房子里,甚至买不起房子啊?)孩子就能上大学(不会啊,好多广州人都没读过大学)赚的钱就比我们多。”“知道为啥我们住城中村么?便宜呗!那些人(屋主)自己不住,就建来租给我们,一个月好几万房租呢!(有那么多?你一个月租金一千多,这楼里哪有几十套房子呀?)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些人就是有钱!只有我们才会住那么脏那么臭的地方。(这里的条件好还是你们村的条件好?)这里好点。”“那些针对外来工的活动啊,我觉得都是在做秀。做给我们看呗,看了好好工作,安分守己。”
在城市管理者与农民工的基本沟通中,这种信息“熵”无处不在。之于城市管理者,他们为农民工所提供的公共资源,是一种基于对“他者”的理解,这些安排清晰地呈现出他们对这个群体缺乏认知。必须指出,这些服务大多依托街道展开,专业素养的缺乏决定了这些工作人员所能提供的社会融入服务有限,这不仅仅针对外来工,在组织非外来工群体的一些社会活动时也如此。而针对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受到质疑的原因在于:这个群体更需要他们的帮助,其他群体则不把这类活动视作参与、融入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于农民工,受自身信息搜索、整合能力的限制,他们对各类社会服务缺乏基本的辨识能力,对提供给自己的公共资源反应迟钝,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之于部分本该充当城市管理者与农民工桥梁的社会组织,或拥有激情但受限于专业训练,或把社会组织当做一门生意,或自身行政色彩太浓,或过于激进,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如意。因此,社会亟待提供以农民工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概念为中心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内容落脚点并非当前学术圈热议的农民工话语权,而是基本对话。只有在管理者、农民工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进行充分对话,才能将现有的各类针对农民工的公共资源盘活,减少目前普遍存在的资源的浪费,从而使得传播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
当然,本研究并非否定农民工的话语权,而是认为,在当前城市管理者的认知框架内,将更多的公共资源让渡给农民工群体,比单纯强调话语权更重要。对城市管理者而言,需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专业性,确保信息传播的通畅和有效,一方面让农民工看到他们为这个群体融入社区和城市所提供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减少针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所提供的各种社会资源浪费。以社区为平台、提供实用信息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发布各种实用信息,并搜集农民工群体关于城市融入的基本需求,与农民工群体进行面对面的互动,进行基本的城市角色训练。这样,才能在农民工、社会组织和城市管理者之间形成可流动的对话,完成城市融入的有效沟通。
五、结语:作为社会发展生产性要素的传播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与定居,可以解决当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治安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住得越久,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持续交往的预期就越高,就会增进双方的和平共处。如果农民工群体一直被城市排斥,游离于城市边缘,他们会把自己与本地居民的每一次遇见视作最后一次交往,背叛就会被视为最优选择——广州城里常见的抢劫、暴力,往往源于行动者认为自己可以“干一票就走”,“谁知道是我干的呢”。
这种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所接纳。因此,从“无视”到“有条件接纳”,虽步伐缓慢,但始终在前进。广州地区的田野调查显示,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依然是影响农民工角色转型和城市融合的重要体制性因素,但城市管理者已与农民工一起,在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上寻找各种机会。总体而言,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公共资源的配置,但目前面向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资源配置依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资源短缺;二是资源浪费,两者并行不悖。因此,本研究认为,现阶段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必须从组织化、媒介化出发,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在“合作、同化”的话语框架下完成城市管理者、社会组织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对话,一方面逐渐增加农民工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将已有的公共资源盘活,使传播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
注释:
①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 551585.html,2014年6月9日。
② 刘昊、昌道励:《深圳新生代外来工揾工日记:从进城挣钱到融入城市》,《南方日报》,2014年6月6日。
③⑱ 汪建华、郑广怀、孟泉等:《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二十一世纪》,2015年第8期。
④ 肖云、邓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 这个“容忍边界”看似残忍,却是我们在实地调研中触摸到的最尖锐的壁垒之一,打破这个边界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更多时间的培育。
⑥ 从文献来看,我们认为这种“社区化”的提出接近于“组织化”。具体参见刘建娥:《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社区融入的视角》,《社会》,2010年第1期。
⑦ 罗天莹、连静燕:《农民工利益表达中NGO的作用机制及局限性——基于赋权理论和“珠三角”的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⑧ 高传智:《增权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传播研究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院报》,2013年第12期。
⑨ 如胡宝华:《组织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王飞:《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行政与法》,2015年第1期;李文祥:《本土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整合与重塑——基于农民工城镇融入实践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1期;尹丁:《促进农民工组织化进程探析——从工会改革视角出发》,《新西部:中旬·理论》,2015年第1期。
⑩ 相关研究可参见: Allen,N.J.,& Meyer,J.P.(1990).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Tactic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Links to Newcomers' Commitment and Role Orient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3,pp.847-858;Fedor,D.B.,Buckley,M.R.,& Davis,W.D.(1997).A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Realistic Job Preview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14,pp.211-221;Jablin,F.M.(1987).Organizational Entry,Assimilation,and Exit.In F.M.Jablin,L.L.Putnam,K.H.Roberts,& L.W.Porter(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pp.679-740.Newbury Park,CA: Sage.
⑪ J.Kevin Barge & David W.Schlueter(2004),Memorable Messages and Newcomer Socialization,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8,no.3,pp.233-256.
⑫ Jennifer H.Waldeck,David R.Seibold & Andrew J.Flanagin(2004),Organizational Assimi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Communication Monographs,Vol.71,no.2,pp.161-183.
⑭ 贺美德·鲁纳编著:《“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许烨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⑮ 陈娟:《网络时代的社区媒体:城市整合的纽带》,《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
⑯ 这些访谈均来自于90后。
⑰ 宁越敏等:《“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社会融合”笔谈》,《中国城市研究》,总第6辑。
⑲ 如2011年广东增城的骚乱事件中,珠三角周边的川籍帮派被广泛动员起来,进行各种打砸活动,从推翻警车到捣毁店铺。但最后,工人的利益诉求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满足。
⑳ 《广州150万外来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约9.9万》,http://news2.ycwb.com/2015-02/11/content_ 8887540.html,2015年2月11日。
㉑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作者陈娟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汪金刚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项目编号: 11YJC860003)、2015年度广州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