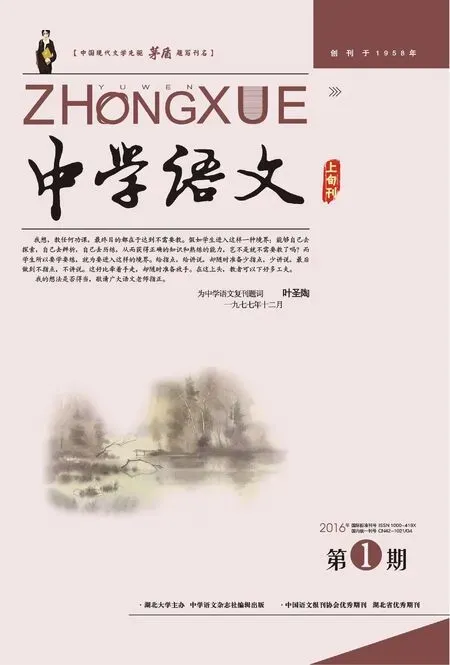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从“谁把侍萍赶出周家”谈起
李欣荣
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从“谁把侍萍赶出周家”谈起
李欣荣
长期以来,戏剧冲突是话剧文本教学的出发点,寻找冲突,关注戏剧情节,并通过理解潜台词把握戏剧冲突中的人物形象已成为话剧文本教学的不二圭臬。我们发现,这种形式的话剧文本的教学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窠臼:它过于强调情节的完整而选择能够印证情节合理性的人物语言,将有丰富意蕴的潜在语言简单化、表面化,将丰满的人物形象平面化、概念化;过分地重视话剧文本的戏剧性,而消泯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所带来的多元解释的可能。我们认为,话剧是对话的艺术,作者通过话剧的对话展现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中人性困境和挣扎的深入挖掘。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其实也是生活的真实逻辑,是不能单一理解的。话剧正是通过其对话的言语缝隙——除话剧语言的潜台性之外,由说话方式的选择带来的言语逻辑重点的变化、言语之间的龃龉或空白——来展现被提炼的生活逻辑以及其中的人物生存境遇。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能使我们关注被选择性遗忘的细节,去挖掘文本貌似没有显示的却可能真实存在的潜在情节,从而立体化、个性化地评价人物形象。
以《雷雨(节选)》为例,特级教师程翔老师曾在授课时基于传统社会中侍萍有做妾的可能,提出到底谁把侍萍赶出周家之问①。从传统的分析来看,这个问题解决的要点在于“你们”一词的内涵,且看文本:
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显然,它将冲突投向于周老太太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而程翔老师对“宁死不做妾,表现个性倔犟、敢于维护尊严的侍萍形象”的解读则将文本的分析放置在更为复杂的生活情境之中,从而丰富了情节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虽然激起了文本解释的分歧,但带来了话剧文本分析上的极富价值的思考。
一、透过话剧的言语缝隙,发现真实的生活逻辑
一般的文本细读只是通过语境理解文本词汇的深层意义,发掘文本的组织结构;而戏剧是行动和现实的摹仿与创造,“在摹仿中艺术家所表现的现实不但可能正如现实一样,也可能比现实更丑或更美。他们所再现的人也许恰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也许更坏或更好”②。由此,话剧文本的细读,必须在重视语境中文本词汇意义的同时,自觉进入到生活情境中去,探寻符合生活逻辑的各种可能性。“侍萍可以做妾”虽然不是文本所有的,但却符合那个时代的生活逻辑,是真实的可能。它在对文本传统的固化认识之外,提供了侍萍形象解读的新途径,不仅体现了教师作为读者所重视的文本逻辑,也向学生传达了读者要重视生活逻辑的意旨。细细想来,侍萍出周家可以是被迫的,毕竟文本中就是这样写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可以理解为三十年间侍萍心中压抑着的怨怼不断强化、将自己所有的苦楚全都推责于周家的表现,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所以,当有学生提出“侍萍不愿意做妾,自己离开周家的门”时,他其实已经进入到文本所呈现的生活情境中去了。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
鲁侍萍:……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
这段对话中,鲁侍萍的话不仅在语言逻辑上前后矛盾,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生活逻辑:一位封建大家族的主事老太太会坐视着一位没有获得“媳妇”名分、被赶出家族的丫头将自家的嫡孙(即使这个孩子因病快死了)带走不理?所以存在着鲁侍萍不顾一切硬将大海带走的可能。这种符合生活逻辑的真实的可能,使鲁侍萍的形象具有倔强乃至刚烈的一面。
二、透过话剧的言语缝隙,发掘真实的“潜在”情节
作为叙事作品,史诗和长篇小说的情节与话(戏)剧的情节之间的区别在于,前两者的情节都是“显在”的,情节在“事件的组合”中展开;话(戏)剧的情节则是“显在”和“潜在”紧密结合的。话(戏)剧实际表现时间和舞台演出时间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直接摆在舞台上表现的人和事只是情节中的冰山一角,而庞大的冰山之体——“幕后”“台外”那些舞台情节外的虚写的情节就要通过舞台上的戏剧展示呈现出来。《雷雨》也是如此。比如,“柜上的相片”勾连起三十年前的旧事和三十年后的现实。三十年后的现实是“显在”的情节,三十年前的“旧事”是“潜在”的情节。虽然在人物的对话中会不断地释放出关于“三十年前”之事的相关信息,但更多的信息并没有直接向读者展示。这些潜在的戏剧情节并不因为“潜在”而可忽略不计,相反,它们从生活逻辑上支撑着“显在”情节的真实可信。所以戏剧作者常常会在舞台语言中留下蛛丝马迹,来透露“潜在”的情节。
正如福楼拜跟莫泊桑谈论小说创作时所说的“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一般而言,话剧创作中真正能够表现人物在那时那地那场景中的反应的句子也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词语也只有一个。而对话中的这一句、这一词通过适当的言语形式留下理解的缝隙,产生理解的张力,引导读者去发觉可能的真实的“潜在”情节。就如周朴园负气、任性地脱口而出“你的第二个孩子”而不是“我们的”,是否能在“绝情”的表象下透露出在那风雪之夜可能发生的激烈的争吵?从而使周朴园在三十年的怀念中除了愧疚之外还带有某种责怪与怨念,否则周朴园怎么会主动提出“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这个“恩怨”不是单向的,是相互的啊。
所以,“谁把鲁侍萍赶出周家的门”一问的价值来自于引导学生透过“显在”去挖掘“潜在”情节,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作者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三、话剧言语缝隙中的“潜在”情节从生活逻辑上支撑着显在情节
谁把侍萍赶出周家之问不仅能够提供侍萍形象解读的新途径,而且能够使读者反溯情节,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三十年前的丫头梅侍萍凭什么会有做周家少奶奶的念头?当我们把一些零碎的“显在”情节重新组合后,就能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秘密:
鲁侍萍: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
鲁侍萍: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
鲁大海: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在叫江堤出险——
鲁大海:……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二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为什么梅侍萍会不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周家少爷周朴园产生了一段感情?为什么周家要“赶紧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为什么家大业大的周家要靠淹死小工来发昧心财?一切信息都指向一个可以推测的事实——三十年前周家败落了!只有如此,鲁侍萍才不会感到和周朴园之间的巨大差距,才会对“出周家门”抱以三十年之久的怨怼;只有如此,周家老太太容忍侍萍与周朴园交往生子才具备合理性;只有如此,周家才要“赶紧娶”有钱有门第家的小姐,背靠大树、重振家族,去撮合一段贾宝玉、薛宝钗式的婚姻。从这一“潜在”情节出发再来看侍萍的形象,不是更丰满了些么?
至于话剧中的“突转”情节——面对照片深情款款的周朴园在认出侍萍后迅速变脸——长久以来给读者带来的阐释困难与矛盾(那些从社会外部环境寻找原因的努力总让人觉得不怎么理直气壮),其实可以据此来作新的思考,因为存在矛盾的显在情节是否真实可信,必须探寻其背后是否有符合生活逻辑的潜在情节予以支撑。还是看文本:
鲁侍萍:……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日——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是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不禁要问:周朴园是在侍萍被赶出周家、投水自杀后马上设立了她的纪念仪式吗?恐怕不是的。周老太太不允许他这么做,有钱有门第家的小姐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可见,周朴园是一个心理受过伤的人。他纪念侍萍的仪式是他潜意识中反抗周老太太的一种方式,他越强化这种反抗就越能掩盖他所受到的心理伤害。当这种隐秘的反抗成为习惯时,他竟然也相信自己三十年来对侍萍的感情是一如既往、矢志不渝的。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周朴园在这一情节“突转”中会让人猝手不及地翻脸,因为他纪念的心理基础是反抗周老太太,而不是怀念鲁侍萍,现实的利益威胁自然容易战胜情感上的怀念。
透过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关注真实的生活逻辑和以之为支撑的显在情节外的潜在情节,能够丰富人物语言的内蕴,增加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的多元解释的可能。同时,也能引起对情节“选择”的探讨:作者怎样通过情节“选择”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作品主题,不仅体现着剧作家的艺术风格、创作个性,也是话剧文本教学所要关注的语文形式。
参考文献
①苏立康:《品课(高中语文卷001)》,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②(波)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