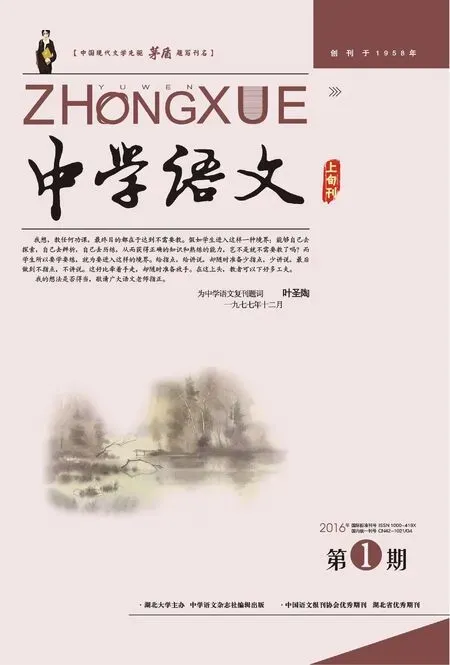《晚秋初冬》的中国尴尬——苏教版之《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审美(一)
张一山
《晚秋初冬》的中国尴尬——苏教版之《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审美(一)
张一山
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在日本中小学久负盛名,是散文经典中的经典。我接触过的日本教师朋友,他们能从头背诵到尾,令我油然而生景仰之情。
当下,中国教育界不断增进国际教育理解,广泛开展国际教学合作。在这种背景下教学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开放心态,从而使他们懂得尊重国际文化差异性,为参与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作好铺垫。
但许多老师对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的教学并不“上心”,即使开展了所谓的鉴赏教学,课堂上也每每是漏洞百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尊重日本文化审美趣味的层面,重新审视《晚秋初冬》。
一、《晚秋初冬》的审美尴尬
《晚秋初冬》这篇经典散文,表现了德富芦花的超一流的审美趣味,是反映日本民族审美取向的杰出代表!《晚秋初冬》从片断“一”写到片断“四”,其审美境界不断提升,不断攀高,最后达到了日本民族审美的最高境界——空寂境界,即像片断“三”“四”所写的“整个世界仿佛尽在雨中了”“夜里,人声顿绝,仿佛可以听到一种至高无上的音响”。——我们应该带领学生鉴赏这另一个民族的审美取向,亲近这另一种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但是,《晚秋初冬》进入了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之后,却遭遇了阅读尴尬,课堂上每每演绎着理解、鉴赏上的悲剧!有的把《晚秋初冬》之“空寂之美”理解得令人惨不忍“听”,不禁令人拍案而起!
悲剧之一:《晚秋初冬》“杂音”横生
一位老师教学《晚秋初冬》时,他先投影唐代杜甫的《登高》,让学生开展比较阅读。课堂上,师生经过互动讨论得出了“同”:两位大作者都在伤秋,都在借景抒情,都表达内在的凄凉与痛苦、孤独与寂寞。
之后老师开展“你喜欢哪一篇”比较阅读,结果学生纷纷表示喜欢杜甫的《登高》。他们如此生成的理由是,树叶落尽之后,德富芦花的内宅里很清静,树木都落叶了,焚烧枯叶的炊烟升起了,阵雨又敲打着栗树的落叶,暮雨潇潇时,作者“默默独坐,顾影自怜”。于是伤感产生,破坏了散文的美丽氛围。特别是“顾影自怜”充满的悲凉、伤感,使得情感表达上出现了“杂音”云云。
试问:《晚秋初冬》与杜甫的《登高》情感真的有那个“三同”么?“顾影自怜”真的是充满悲凉、伤感,使得情感表达上出现“杂音”了么?
典型的误读,用中国文化心理去揣测日本文化审美趣味!
悲剧之二:《晚秋初冬》“悲凉”浓烈
一位老师教学《晚秋初冬》时,他先让学生“读课文·拟题目”,结果两位同学根据四个写景片断拟出了两组题目——
残叶霜落·清秋静院·潇潇静夜·月色寒心
风霜残叶·冷清花鸟·孤单听雨·星月风雨
之后,这位老师便基于生成的两组题目开展阅读审美活动,一番审美比较以后,大家认为第二组题目更好,理由是,这四个题目表达了叶落过程中作者典型的心态、心境和心冷。因为《晚秋初冬》有着非常浓烈的悲凉,随着时间的逝去,作者的心越来越冷寂……之后,老师便介绍德富芦花的“不幸遭遇”——“芦花兄弟间裂痕”“革命家谋刺天皇,没有成功”……
试问:《晚秋初冬》写景过程中展示的景色图片,真的就是这种“凄凉”美么?他的内心真是的就这么冷寂?这篇散文真的就反映“不幸遭遇”?
我想,德富芦花平生是有些“不幸遭遇”,但与《晚秋初冬》写景有关联么?——完全是老师们的臆测!
悲剧之三:《晚秋初冬》“退出”有迹
与朱自清的《背影》一样经典的、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散文精品《晚秋初冬》,却在中国的课堂遭遇了尴尬。在南京市的一次校本《现代散文选读》阅读调查中,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是最不受中学生欢迎的篇目之一。学生学习后普遍认为,作者的情感表现前后不一,境界很浅,这样的写景散文“我们也能写得出”。学生们认为,这篇散文就是简简单单的描写景物,人物的情感也不怎么突出,结构上也没有什么智慧……
如果我们把学生的论调与教师的教学现场结合起来看,《晚秋初冬》的境界似乎还真的不够深,似乎还真的情感消极……所以,许多老师的处理方式便是“不用教”了。在苏教版篇目的不断调整的运作中,《晚秋初冬》早就被打上了星号——成为课外自读篇目了。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两位老师教学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让我很难过。因为他们没有读懂《晚秋初冬》中“物我一体”“物我合一”的趣味。这不仅是酝成了教学上的种种理解悲剧,还影响了学生的审美能力的提升与审美素养的丰富。
长此以往,这篇经典散文就很有可能真的被淘汰掉,那么,我们的学生在散文阅读的国际视野上就失去了一片“空寂之美”,我们的学生就失去了一次国际文化多样性的熏陶渐染。难道,中国学生的审美素养,只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圈子里练就?而中国学生未来所需要的国际审美素养,又能在哪篇散文哪篇诗歌中练就?
二、《晚秋初冬》的审美背景
中华传统文化是“感物吟志”的审美取向。刘勰云:“诗者,持也,持人之情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是以,我们阅读杜甫的《登高》便不自觉地将萧瑟秋江之景,与他飘零的身世、孤老愁病、苦恨艰难相勾联。而《登高》就是老诗人登高临眺的全部心情、心境。这种解读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由此,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也应该放在日本民族的审美背景上来审视。
日本民族从中国借去了“感物吟志”“天人之合”的理念,生成了“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观。在这种审美观照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审美的最高境界——“空寂”。什么是“空寂”的境界?简言之,就是“主客泯灭”“物我两忘”的境界。《晚秋初冬》美在逐步走向“空寂”。
彭修银、邹坚在《空寂:日本民族审美的最高境界》(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中认为:“日本人的原始的‘空寂’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作为环境的自然。”也就是说,“空寂”之美学受到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条件、自然观以及植物美学观的影响。而日本民族的这种独特的自然观,每每又向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交叉、聚结、融合,从而规定着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日本民族如果无法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太多的审美体验,每每容易产生孤独感。所以,他们更容易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中,从而从大自然中获得更多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享受。
在这样的审美背景下,散文创作中表达“空寂”之景仰,“空寂”之追寻、“空寂”之再现则成了日本民族审美的共同追求。大家熟悉的川端康成的《花未眠》,其审美趣味就是这样。川端康成凌晨醒来,忽然发现海棠花在夜晚还盛开着——“空寂之景”,从而引发了审美思考。在《花未眠》中,他这样写道:“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所以,川端康成是一个从人类社会逃向自然,并且深深感受到自然之美之趣的人。他的散文创作就秉承了日本文学“物哀”“风雅”“空寂”的审美传统,达到了禅趣、哲理与物哀之美的高度统一。在《花未眠》中,偶然开放的海棠花唤醒了他的自我意识。于是,他自然地溶进了柔和的海棠花的朦胧花影中——“天人合一”,从而展开了愉快的审美历程……而日本民族的这种“空寂”的审美取向,也左右着女性的审美。日本国民更欣赏“立如芍药、坐如牡丹、行如百合”的女子,——她们纯洁高雅而又美姿迷人。
那么,“空寂之美”意识产生的生活基础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日本人的植物美学观。日本民族核心的植物美学观表现为两点:“自然即美”和“物哀情怀”。彭修银、邹坚认为,“自然即美”的精神实质就是“寂”。作为一种美意识,“寂”最基本的精神之一就是“真实”与“自然”。他们认为,“自然即美”就有两层意思:一是大自然是美的本原、美的蓝本、美的极致。一切美的事物都源于大自然,最高的美只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二是自然的事物本身就是美的赤裸裸的表现——不需要任何修饰,不需要任何矫揉造作。
而“物哀情怀”又叫“樱花情结”,则是日本民族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思维。日本民族常常从自然界的花开花落中,联想到生命的生死荣枯。日本人认为,人类的存在与大自然就像树叶和树干一样。叶落了,树犹生。人生短暂即逝,自然天长地久。所以,日本人更愿意从短暂的人生之中去感悟“生”的喜悦,进而珍视“生”。比如,樱花花期很短,瞬间化为乌有;但是樱花花开时则热烈灿烂,令人陶醉。日本人认为,“与其因为飘落而称无常,不如说突然盛开是无常,因无常而称作美,故而美的确是永远的。”这样,开放的鲜花、飘落的叶子一样是财富、是美丽。
德富芦花在他的《我家的财富》中,就视满院的叶子为财富。他说:“屋后有一株银杏,每逢深秋,一树金黄,朔风乍起,落叶翩翩,恰如仙女玉扇坠地。夜半梦醒,疑为雨声;早起开门一看,一夜过后,满庭灿烂。屋顶房檐,无处不是落叶,片片红枫相间其中。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子里了。”德富从落叶中感受到的是美,是喜悦。因此,理解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也要放在日本民族最高的审美境界层面来审视。
三、《晚秋初冬》的审美境界
《晚秋初冬》是基于日本文化背景而写的,是表达日本传统审美趣味的。日本审美文化学习了中国“感物吟志”“天人之合”理念,但他们更加欣赏的是“景人同一”“天与人合”的愉悦审美境界。“无边落木萧萧下”“风急天高猿啸哀”在日本人的审美趣味中,是一种自然美丽、合乎自然的规律。他们认为,秋天到了,落叶飘下来,顺应了自然规律,值得审美鉴赏。而在“飞花落叶”之美的鉴赏中,最好能达到“物我一体”“物我合一”的状态,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我不知道蝴蝶是我,还是我是蝴蝶”。这样,“空寂”状态就成了日本民族最高的审美境界。显然,上述老师用比较方式开展的审美比较以及“你喜欢哪一篇”完全是出于中国文化和中式思维背景。
《晚秋初冬》审美的价值就在“空寂”的生成上。课文首先表现的是“自然即美”。这一点,《晚秋初冬》的开首表达得非常清晰。在“一”中,作者从“霜落,朔风乍起”写起,“庭中红叶”“门前银杏”不时飞舞着,作者用了三个优美的比喻:“白天看起来像掠过书窗的鸟影”;晨起一看,满庭落叶,“遍地如彩锦”;树梢上“那残叶好像晚春的黄蝶,这里那里点缀着”。这哪里能看出“残叶”“冷清”“孤单”“寒心”等字眼?——上述老师对拟题开展的审美鉴赏显然也带有中国文化的审美趣味。从作者的描写看,课文再现了“自然即美”的境界,院子里的落叶是“美的本原、美的蓝本、美的极致”;落叶之美,作者是“赤裸裸的表现”——刻画、描写、想像,没有添加任何动物的叫声,不像杜甫还有“风急天高猿啸哀”来衬托。
在“二”“三”中,重点转移到“物哀情怀”的逐步营造上。作者渐渐由落叶的“扑打着屋檐”过渡到描写“庭院之静”上。而“庭院之静”描写得曲折有致,生动活泼——
“白昼是静谧的”,他先写“高空之静”——“天空高爽,明净”“阳光清澄,美丽”,叶落没有带来伤感,而是喜悦、静谧、舒适;接着写“对窗读书,周围悄无人声”之“异常的幽静”;再接着写“院子之静”——李树“叶子落了,枝条交错,纵横于蓝天之上”,梧桐坠下的一片硕大枯叶之静美——“静静躺在地上,在太阳下闪光”,这是“中空之静”;然后,写“窗口之寂静”——看“经霜打过的菊花低着头,将影子布在地上”“残留的南天竹的果实,在八角金盘下泛着红光”——静物之“寂寥”,观“两三只麻雀飞到院里觅食”“廊椽下一只老猫躺着晒太阳”,听“一只苍蝇飞来,在格子门上爬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动物之静趣;最后是写“内宅之清静”,主要表现作者“静听静寂”,享受“静寂之美”——“月夜,满地树影,参差斑驳”“阵雨敲打着栗树的落叶”“暮雨潇潇,落在过路人的伞盖上,声音骤然加剧,整个世界仿佛尽在雨中了”。最后一句:“这一夜,我默默独坐,顾影自怜。”即表明作者基本融进大自然了,在初步享受“天人合一”的“空寂之美”了。这就是“物哀情怀”的境界,哪里有什么“悲凉”“伤感”?
《晚秋初冬》的“物哀情怀”在“四”中达到高潮。在“四”中,作者“踏着白花花的银杏树落叶”,听“树隙间哗啦哗啦落下两三点水滴”,看“月亮又出现了”,于是作者感叹:“此种情趣向谁叙说?”这就是典型的“空寂之美”。然而这种“空寂之美”的最高境界,还是这几句“月光没有了,寒星满天。这时候,我寂然伫立树下,夜气凝聚而不动了。良久,大气稍稍震颤着,头上的枯枝摩戛有声,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片刻,乃止。月光如霜,布满地面。秋风在如海的天空里咆哮。夜里,人声顿绝,仿佛可以听到一种至高无上的音响。”这里,作者与自然是“物我一体”“物我合一”,完全融入自然的“静”界之中了。这时,人与自然融通,物我同一——物即我、我即物。作者“不仅超越主体自然,而且超越客体自然,从具体实然的天人合一状态进入本体超然的物我两忘境界”。这就是日本民族审美的最高境界——“空寂”。
同样是写秋、同样是写静,中日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审美文化差异。我们不能以此观彼,也不能以彼观此。我在教学《晚秋初冬》时,一个学生针对“四”中“月光没有了,寒星满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琴声?如果此时作者弹奏一首古乐,岂不更好?”是的,“寒星满天”时一曲琴声不是更加衬托幽静么?王维不就是有这样的雅好么?他的《竹里馆》中就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秋初冬》里可不可以响起琴声?其实,“弹奏一首古乐”的设想,只是基于中国诗歌背景的审美扩张。中国与日本在欣赏景物时是两种审美取向。日本民族认为“自然即美”,不夹“杂音”,不作修饰。我们不能用读《登高》《竹里馆》的套路去读《晚秋初冬》!
综上所述,《晚秋初冬》是德富芦花借助对“晚秋初冬”景物、时令的直觉体悟而生成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代表着日本民族最高的审美境界。若问中国课堂如何避免解读《晚秋初冬》的尴尬,我想,只有从“自然即美”到“物哀情怀”去审视《晚秋初冬》,沿着“空寂之美”生成的路线——从酝酿、生成、壮阔、喷薄乃至淋漓尽致,才能最终进入作者营造的“空寂之美”的最高境界。这就需要我们有国际化的审美眼光,学会兼容中外文化差异。这样,才能少一些《晚秋初冬》似的教学尴尬,学生才能尽快的走出国际审美的荒滩、走出异域民族文化审美的沙漠。
[作者通联:江苏六合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