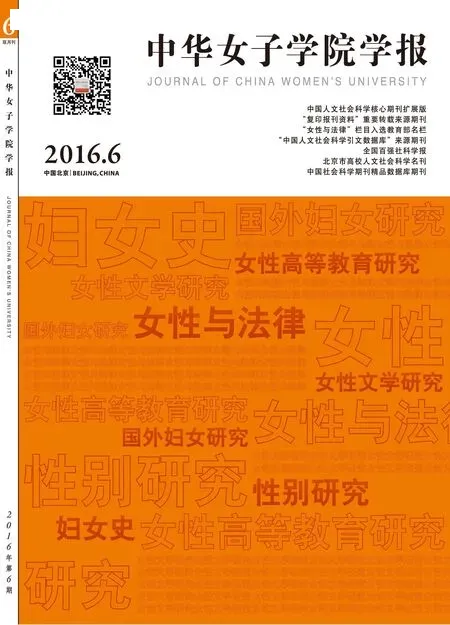他者言说与自我表达: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探析
——以山东淄博地区为例
赵天鹭
他者言说与自我表达: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探析
——以山东淄博地区为例
赵天鹭
近代以来,缠足被当作损害女性身心健康乃至国族衰微的祸首的观点,只是“他者言说”,缺少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与切身感受。通过对山东淄博地区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调查研究,并对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进行挖掘,来展现缠足对女性身体与日常生产劳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当地缠足女性早年主要从事各类家庭劳动,而非农业劳动,这既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遵循,也证实了缠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劳动时期,缠足女性被动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始承受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并存在鲜明的个体差异。
缠足女性;生产劳动;性别分工;自我言说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海内外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国内以高洪兴的《缠足史》、杨兴梅的《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等专著较有代表性,海外则以美国学者高彦颐的新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一书引人关注。在论文中,内地学者吕美颐、梁景时、杨念群等,台湾学者吴文星、林维红、苗延威等人的成果颇有新意。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大多未采用珍贵的口述资料,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价值难以呈现。为扭转这种局面,笔者自2009年起先后走访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和博山镇所辖部分村落,搜寻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口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系列研究论文。[1][2][3]
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军阀韩复榘已在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放足运动,然而对山村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开展放足运动,不少缠足女性在40年代中后期为支援人民战争事业而选择了放足。战争时期生存环境的艰难、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均加速了缠足风俗在该地区的消亡。
本文聚焦于缠足女性的日常生产劳动问题,探讨缠足对该群体的身体及其日常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根据调查,缠足的确对女性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强化了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模式。缠足女性无论在婚前还是在婚后,大多在家中从事家庭劳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时代的到来,缠足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各式各样的生产劳动。尽管大多数缠足女性此时已经放足,然而能否胜任各类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一、他者言说:近代反缠足主流话语之生成
缠足起源于何时?高洪兴辑录古代文献记载,列出多达10余种说法。[4]1-6不过,这些说法大多缺乏可靠的文献佐证,难以理清缠足的起源。宋代以来,缠足风俗日盛,至明清时已达极盛。明人胡应麟尝云:“宋初妇人尚多不缠足者。至胜国而诗词曲剧,无不以此为言,于今而极。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艳羡。”[5]122清初,满族统治者虽然曾一度颁行禁缠足的法令,但是这些禁令最终都难以奏效,往往无果而终。
缠足之俗长盛不衰,不仅在于它是两性共同确立的审美标准,而且与传统礼教相联结,承载了更多的文化与性别意涵。高彦颐指出,与其说缠足对女性是一种身体上的禁锢束缚,毋宁说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导引教化。儒家对女性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三从四德”。其中,“四德”在于训示妇女培养一种内敛型的人格及身体取向,而缠足有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经由缠足的行为过程,使得“内外有别”的理念被具体地呈现在女性的身体取向上,其所构建的内敛型人格与生活空间,形成一个“妇女=内人”的性别理想。[6]181此外,缠足是上层女性用以区别下层女性的身份标识。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或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皆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7]9-10缠足成为大家闺秀尊贵身份的象征,不仅显得比普通劳动女性更加秀美、端庄、有教养,还意味着可以养尊处优、不必整日奔波劳碌。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的传入,缠足风俗开始受到冲击,中国人对缠足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缠足的文化荣光不复存在,反而成为国耻的象征、妨害国族存续的祸端。随着新闻报道、摄影技术、医学、X光扫描以及博览会等新鲜事物纷至沓来,缠足成为一种可以被观看、测量、研究甚至公开展示的事物,其隐秘性被剥离殆尽。与此同时,新式视觉科技也被西方人拿来重新建构中国人对缠足的认知。“视觉化的缠足在帝制晚期里逐渐被建构为‘视觉知识域’上某种邪恶的存在:在病理学的建构上,缠足意味着有机体(个人)和社会有机体(国族)的肮脏和病症;在殖民人类学的建构上,缠足被视为一种野蛮民族的记号;以及在美学的建构上,缠足则被形容成一种不忍卒睹的丑恶品味。”[8]
西方人对缠足的批判,有着鲜明的宗教立场与科研关怀。早在1829年,英国外科医生库伯发表了一篇关于缠足的医学报告。1835年,该报告被转载于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上。裨治文对此评论道:“在中国的民族性的和家庭内的风习中,可以发现其道德体系之缺陷的充足证据。不仅其人民的心灵,而且他们的身体,亦因其违背自然的习惯而被扭曲和变形;造物主为了其创造物的利益而制定的身体和道德的律法,在这里被歪曲,如果可以的话,还会被湮灭。”[9]537这种颇具宗教与道德意味的说教,与科学研究互为表里,共同形塑了晚清时期来华西人对缠足的看法。无独有偶,1874年,服务于广州教会医院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诊治了一位缠足女性,她的双脚因组织坏死而脱落。此前,嘉约翰曾撰文抨击道:“残酷的缠足会带来长期的苦痛……它使得受害者终身不良于行,夺走她们的许多人生乐趣,使她们不适合工作,无法自立,身体羸弱,缺乏活力,缩短寿命,而且也不能孕育出体格强健的下一代。”[9]169晚清时期,类似嘉约翰的言论经由传教士的广泛传布,最终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晚清以来,男性知识分子一直将缠足视作野蛮与国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缠足不仅导致女性身体不适,而且阻碍她们接受新式教育和新鲜事物。这样的女子成为母亲后,孕育不出合格的国民。没有强健的国民,自然无法应对充满竞争的国际环境,民族的存续就会越来越困难。许多支持反缠足运动的改革家、官僚也发出了上述言论。如康有为曾言,缠足“且劳苦即不足道,而卫生实有所伤,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弃世体弱,是皆国民也,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11]509袁世凯也认为,“今缠足之妇,气血羸弱则生子不壮,跬步伶仃则教子者鲜。幼学荒废,嗣续式微,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12]233在进化论、卫生学等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晚清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将“弱国弱种”的标签贴于缠足之上,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形成了一套牢不可破的“科学话语”。科学话语的胜利,将缠足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缠足的认知。在“强国保种”的逻辑下,天足女性寄托了男性知识分子洗刷耻辱、重振国族的政治理想,而反缠足也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核心议题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权主义思想与妇女解放运动得到了长足发展。“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13]1-2于是,女性被泛化为饱受封建压迫的人,亟待被解救。一些撰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女权主义文章不乏对缠足的猛烈抨击:“缠足这件事,是一种肉体的精神的二重压迫,使妇女感到苦恼而不能言。美其名为‘装饰美观’,却暗教以屈从和忍耐,以博大众赞美,且以婚姻为要挟,所以缠足是封建社会男子麻醉妇女的鸦片,也是将妇女灭个干净的毒酒。”[14]缠足“封建压迫论”的提出,彰显了民国时期包括知识女性在内的知识分子对女性现实人生的关切,也体现了部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上述论断的影响延续至今,成为当代中国人评价缠足的主流话语。
二、男女有别:缠足女性的日常劳动与性别分工
尽管近代中国反缠足思想很少受到质疑,然而事实的真相有时又显得扑朔迷离。不少来华西人发现,缠足似乎并没有给所有的中国女性带来无尽的痛苦,这多少让他们感到意外。如英国传教士美魏茶所说:“如果紧裹的双脚真有痛苦与不便的话,活生生的现实会使你感到惊奇,女人每天可以步行几英里……无论是以三寸金莲摇晃行走的年轻妇女还是在街道上嬉戏玩耍的小女孩,脸上都没有我们期望的那种痛苦表情。……我看见一群卖艺人中一位妇女用两只小脚直蹬着一张四条腿的桌子平衡在空中,并用两只脚轮番转动桌子,但丝毫没有痛苦的样子。”[15]114除非亲眼所见,即使是严谨而理性的科学研究,有时也会与先入为主的经验相左。自19世纪末以来,还有不少医生致力于对缠足进行医学上的检视,医学手段日益先进,研究内容也从脚扩展至脊椎与骨盆等部位。[16]79-94但是,这些研究很难完全印证嘉约翰的论断。缠足对于女性身体的损害,似乎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
那么,是否如近代中国反缠足言论所强调的那样,缠足对女性身体普遍造成了严重的戕害,使得她们如同残废之人呢?对现今依然健在的缠足女性及其亲属进行调查研究,似乎是解答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海外学者对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情况的研究有所突破。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宝森对云南禄村的研究[17],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葛希芝等人对四川、福建、台湾、陕西等地的研究[18][19]等等。不过,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经济因素对缠足始末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近代商业与技术革命的压力下,中国乡村家庭纺织生产越发难以获得稳定丰厚的收益,缠足女性“快手慢脚”式的家庭劳动随之消亡,缠足也因之终结。
上述观点深化了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缠足风俗衰落原因的认识,尽管如何评估经济因素的作用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对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的调查研究,似乎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事实上,除了有助于培养女性形成内敛型人格,缠足还有效地强化了两性在日常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缠足虽不会完全禁绝女性外出,却也增添了一种行动上的不便,致使退居闺阁中的缠足女性更多地从事家庭劳动。依据刘晓丽等人对山西碛口镇女性的调查成果显示,当地的缠足女性无论在婚前还是在婚后,参加手工业劳动的人数都明显高于参加农业劳动的人数。缠足降低了女性参与农业劳动的可能性,使她们从田间劳动中退出,更多地从事生育、家务和家庭手工业等劳动。[17]于是,传统时代“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
在笔者调查的淄博地区,缠足对性别分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少缠足女性表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从事田间的农业劳动(当地人称之为“上坡”)。“早年的妇女没有上坡的。那时候的闺女没有上坡的,不缠脚的也不去,那时候不兴上坡。”由此可见,女性不事农业生产劳动,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其是否具备这个能力,而在于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女人(孩)该做的事,即不符合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以及“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规范。“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念的主要角色无疑属于家庭;对劳动的性别划分和对这种划分的合法表象的早期体验是在家庭中被规定的,这种划分由权利保障并被纳入言语之中。”[21]125
然而,该地区缠足女性并不是食利者和分利者。她们所从事的日常劳动主要是诸如推碾、推磨、喂牲口、摊煎饼、洗衣、挑水、掏菜、做饭、纳鞋底、绣花、制衣、看孩子等名目繁多的家庭劳动。上述技能大多需要在娘家从女性家长处习得,并要做到熟练掌握,以便在出嫁之后服务婆家。至于农业生产劳动,除非家中缺乏足够多的男性劳力,否则缠足女性的家长们不会轻易安排她们参加。在一些家境不甚宽裕、需要更多劳力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家庭中,一些缠足女性的家长因为需要女儿(媳妇)帮忙种地而不愿让她们缠足。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缠足的确有不利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一面。这些缠足女性的长辈大多没有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不太了解近代中国反缠足的思想主张。他们反对缠足原因,往往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如冯延贞幼年丧父,被送到北博山村,做了童养媳。由于战争年代生活艰苦,她不得不听从公公的要求,放足劳动。此后,她又举家逃难到东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返回村庄。
农业生产劳动需要持续消耗大量的体力,而对那些缠足时间较长、足部严重变形的缠足女性来说,无疑充满了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过农业劳动经历的缠足女性,其原因大多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劳力突然去世导致的。如黄长梅在追述自己婆婆的早年经历时,提到她因丧偶而不得不亲自“上坡”干活的窘境:“俺那婆婆就跪了刨地,那个时候痛苦。那脚就丁点点小,她站不住。她那儿子才10岁,领到那刨……手里没钱,雇不大起(人)。”又如姬秀清在30岁出头时,也因丧夫而被迫种地。由于她的脚太小,连过河都要靠别人背过去,自己刨地干不完,还要再花钱雇人帮忙。留在家里的孩子们还经常饿得到农田里去寻她。这一切都让她倍感艰辛。
需要指出的是,缠足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不一定比农业生产劳动更为轻松。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许多在战争时期参与过社会公共事务的缠足女性,在婚后往往因不堪家庭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双重压力而选择回归家庭。一些在战争年代积极投身革命、入党并担任基层妇女领袖的缠足女性,最终被养育孩子的重担所拖累,不得不选择退出公职。一些身体较好的老人则表示,她们对党的工作仍然难以忘怀,若不是现在年纪太大,村里的领导不允许,她们还想继续做下去。
三、新生活:集体化时期的缠足女性与农业生产
淄博地区的缠足女性在民国时期大多主要从事家庭劳动,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展了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在老解放区和收复区继续实行,直到1951年11月,淄博市的土改工作宣告结束。[22]330-337、363-368[23]38-43不过,对当地的缠足女性来说,尽管她们大多数人的阶级成分被划为中农或贫农,即使分得了土地,也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因此,土改带给她们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
淄博地区缠足女性大量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约始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似,淄博地区也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7年底,高级社在博山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此后,地方政府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农村地区建立人民公社,并对行政区划做出调整。1958年10月,省政府撤销博山县,将南博山、郭庄、源泉、池上4个人民公社划归博山区。至该年年底,博山区组成了11处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区公社化。[24]34
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进行社会生产的逻辑出发点,大体上遵循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观点。他们相信,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由她们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即不允许妇女参与社会生产,使她们陷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劳动之中。[25]287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6]87、185因此集体化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劳动光荣”的旗号下,女性被动员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然而社会和男性却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家庭劳动的责任。当时的妇女解放理论过于看重女性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对女性的家庭劳动缺乏足够的关照。广大女性不得不在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并忍受男女两性在劳动分工和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27]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淄博地区的缠足女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她们开始了入社、“上坡”、挣工分的新生活。然而,这一运动真的为她们带来了彻底的解放吗?尽管绝大多数的缠足女性此时已经解放了双足,但放足之后的身体能否适应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劳动,则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个体差异。对那些缠足年纪较大、缠足时间不长即放足的缠足女性来说,她们的脚在解放之后变得和天足差别不大,自然可以顺利地承担工作。如崔在英和刘玉英不仅可以较为轻松地从事生产,还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村里其他女性“上坡”干活。尝到甜头的崔在英感到如释重负:“大脚多好,不疼也得劲,干活得劲!”不过,与其他男性相比,她们也是半劳力,至多能挣七八个工分。
虽然无法挣得与男性等同的工分,但一些缠足女性在劳动中充分展现了个人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男性。如李玉田对妻子花成芬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说她纺麦秸可以顶十几个妇女,做其他的工作时也能顶七八个男人。在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花成芬还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对此,李玉田也是充满了感激:“这老太太都受了屈,吃了苦了,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晚上趴在煤油灯上做针线,做鞋、做袜、做衣裳。清晨早起来,男的在家,叫他听着孩子,省得摔下炕来,她去推碾推磨。白天还做饭……做八口人的饭,还能挣好几个工分呢……还得梳麦秸、扒棒槌子,都黑夜干啊……家里的活,她啥也不叫我干,我只要是办(完)了来家,她就不叫我管了,她说,‘我来弄就行。’那时候分粮食,她自己就拿200多斤。”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我们曾问他为什么年轻时不喜欢小脚,并力劝妻子尽快放足。他回答道:“缠脚不好,不能抗日。男女平等,从政治上、劳动上都得平等吧?你不劳动,光在家里,不能干,光做饭。”李玉田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本人早年接受过根据地的社会教育,这番话也在不经意间同共产党的主流革命话语相暗合。然而“缠足不能抗日”并不是一个事实,战争年代确有不少缠足女性在支援战争时并没有完成放足;而缠足女性进行家庭劳动,也不能说是不劳动或不能干的表现。
从传统到现代,女性家庭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国家与社会的普遍认可。传统时代基于“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女性的纺织工作不仅能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其生产的织物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女性的家庭劳动曾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28]139-214美国学者贺萧指出,近代以来,随着思想与社会的激变,原本被视为国家基础的家庭,转而成为国家贫弱、落后的象征。因此,将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以便充分发掘其潜能,成为历次现代化改革与革命事业的应有之义。集体化时期,家庭最终成为完全的私人领域,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价值被抹杀,家庭生活也在国家主流革命话语中隐而不见。[29]257-281
在主流话语的支配下,当地不少村民对缠足女性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她们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被禁锢在家庭之中,是无法从事劳动的“残废”人。而她们家庭劳动的价值不仅不被肯定,甚至不被定义为真正的劳动。心理学意义上的刻板印象,指的是对一群被赋予同样特征的人的分类;当个人因其是某一特殊群体或某一类人群的成员而被他人归类为具有某种共性时,刻板印象就产生了。刻板印象的目标群体是易于识别的,而且处于相对的弱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个群体具备的某些特征;刻板印象对这些群体的描绘通常是不正确的,而错误的观念又是难以更正的。[30]523[31]64-65
当缠足在淄博地区成为一种行将消逝的风俗时,缠足女性得以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群体中被剥离开来,成为一种可以被归类、歧视、误解的人群。李玉田没有在意自己略显矛盾的表述,或许在他心里,已经放足的妻子早已不属于他批判的小脚女人了。又或许,他在不经意间向我们流露了两种自成体系的叙事模式:一种是对官方主流话语的转述,而另一种则是基于生活经验而得来的真切感受,二者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他对缠足女性的认知。当聆听过他对妻子的赞美之后,我们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不帮妻子多分担一些家务,他辩解道:“她怕我累。我还在队里干,她不容易。”对他来说,公开承认自己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方面的工作能力都比妻子大为逊色,或许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总之,只有将来自他者的两种不同叙事模式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揭示更多的历史真相。
不过,像花成芬一样同时胜任繁重的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缠足女性,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对许多人来说,她们即便放足也无法像天足女性那样工作。“大脚的挣七八分,小脚的不能挑,吃亏。”“大活干不动,小脚白搭,(只能)挑挑担担,掰棒子,烧火呢。”缠足不利于农业生产劳动的一面,在此次运动中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随着“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开展,村里的男性劳力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外出从事博山的煤矿开采工作或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而留守村庄的女性,包括缠足女性在内,不得不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此外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落在她们身上的负担更沉重了。
相对而言,一些年龄较大的缠足女性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处理得反而轻松一些。这是因为她们的孩子年龄更大,只要假以时日,孩子们就可以帮忙去挣工分,自己便可以回归家庭。如任玉英就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坡”,自己留在家里为他们做饭。而对一些更年轻的缠足女性来说,繁重的工作简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磨。李英爱的丈夫在“大跃进”时期担任公社大队长,带领村民修水库、修桥,常年在外工作。李英爱不但要照顾公婆和两个孩子,而且要到公社食堂做饭,并带头在农田里参加劳动。由于丈夫的领导身份,即便痛苦,她也不能显现出丝毫的懈怠。“俺那孩子,领着的,抱着的,我也得挣啊!他当大队长,你不先领着行啊?走慢了,社里不依,咱领着孩子上头里去。俺挣的很少,那大男人一天才十分工,俺就五六分。”由此可见,集体化时代这种片面追求动员缠足女性参加社会生产的做法,非但没有让她们获得彻底的解放,反而在客观上对她们造成了困扰和伤害。
四、结语
缠足风俗绵延千年,历经兴衰荣辱。在传统时代,它不仅代表着一种审美趋向,还被赋予了深厚的道德意蕴。缠足不止是一种外在美,还意味着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的遵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传播,缠足作为一种奇异的风俗,被西方人置于一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加以重新审视。人们认为,缠足不仅损害女性身心健康,而且导致民族积弱不振。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将西方人对缠足的认识加以吸收,把妇女双足的解放视为抗敌御侮和复兴国族的重要一环。
以往关于缠足史的研究,由于材料所限,一些议题很难涉及。如缠足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放足后的人生经历等等。而由他者言说所形塑的近代中国反缠足思想,其有关缠足女性的描绘也呈现出某种自相矛盾的面貌,难以窥探出事实的真相。经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口述访谈,可以发现缠足确实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女的性别分工模式。淄博地区的缠足女性早年在原则上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既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遵守,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时期,政府将缠足女性动员起来参与公社的农业生产劳动。然而,广大缠足女性在从事社会生产的同时,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对那些无法放足或放足不成功的缠足女性而言,这种解放或许不啻一种新的苦难。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缠足对女性身体与日常生产劳动的影响,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
[1]侯杰,赵天鹭.近代中国缠足女性身体解放研究新探——以山东省淄博市部分村落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3,(5).
[2]侯杰,赵天鹭.文本·信仰·再现:辰巳山庙会研究——以鲁中三镇缠足女性信仰生活调查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5,(4).
[3]侯杰,赵天鹭.缠足女性的身体改造与婚姻家庭生活解析——以山东省淄博地区部分村落为中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4]高洪兴.缠足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5]姚灵犀.采菲识小录[A].姚灵犀.采菲录初编[C].天津:天津时代公司,1936.
[6]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A].邓小南.中国妇女史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吴震方.岭南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苗廷威.从视觉技术看清末缠足[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5).
[9]E.C.Bridgman.Small Feet of the Chinese Females[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5,(12).
[10]J.G.Kerr.“Small Feet”[J].The Chinese Recorder,1869,(6).
[11]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A].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Z].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2]袁世凯.直隶总督袁世凯劝不缠足文[A].姚灵犀编撰.采菲录初编[Z].天津:天津时代公司,1936.
[13](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4]孙文珊.放足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J].民众生活,1933,(51).
[15](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蒋重跃,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16]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M].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
[17](加)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8]Hill Gates.On a New Footing:Foot binding and the Coming of Modernity[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7,(5).
[19]Hill Gates.Footloose in Fujian:Economic Correlates of Foot binding[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1,(1).
[20]刘晓丽,秦艳.民国时期女性缠足与生产劳动——对山西省碛口镇女性的考察[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21](法)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2]中共博山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博山地方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23]中共博山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博山地方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4]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博山区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5](美)阿莉森·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6](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7]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J].社会学研究,2005,(4).
[28](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江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9]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The Fate of“The Private”in Revolutionary China[A].吕芳上.无声之声(I):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C].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30](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M].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31](美)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上)[M].许敏敏,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张艳玲
“Other Speech”and“Self-narration”:Daily Work of Foot Binding Women in Zibo,Shandong Province
ZHAOTianlu
In modern times,foot binding was not only regarded as an“undesirable custom”which harmed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but also the culprit for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However,most of these ideas were from other people,not from foot binding women’s“self-speech”and personal feelings.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 Zibo, Shandong Province,it showed the actual effects of foot binding brought to the female bodies and the daily production work.In early years,the local foot binding women were mainly engaged in various types of family work,not agricultural work.This was not the same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dered division oflabor,but alsoconfirmed the adverse effect of food binding on agriculture.During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the foot binding women were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began to burden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the family and society,which had distin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ot bindingwomen;productive work;gendered division oflabor;self-narration
10.13277/j.cnki.jcwu.2016.06.015
2016-10-09
D442.9
A
1007-3698(2016)06-0097-07
赵天鹭,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30035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BZS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