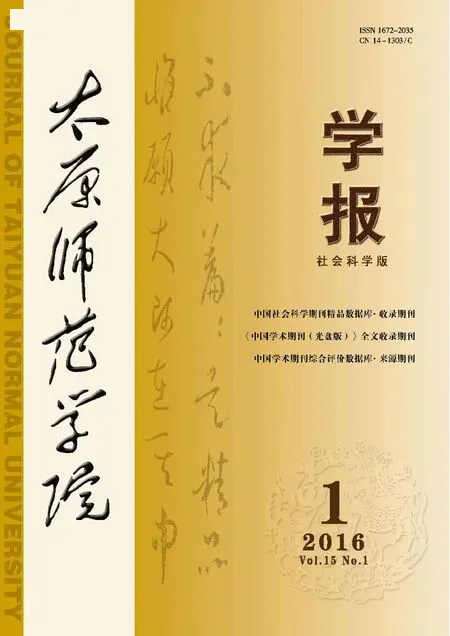债权意思主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模式
赵 磊,曹亚雅
(1.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重庆 401120; 2.湘潭大学 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法律学】
债权意思主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模式
赵磊1,曹亚雅2
(1.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2.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没有明确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第二十四条的解释几乎皆立足于交付生效的立场,这样的论证虽然坚持了债权形式主义的原则,却忽略了债权意思主义这一例外。基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可解释性、《物权法》对债权意思主义确立的统一性以及比较法中债权意思主义的实质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其确立了特殊动产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关键词]特殊动产;债权意思主义;登记对抗
一、问题的引出:基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上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主义模式,即以折中的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以登记对抗的意思主义为例外。我国物权法呈现出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交错的特征。[1]83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文不像《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第二十四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遵循何种变动模式,可谓是不完整条文。因此,围绕《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的关系以及第二十四条真实面目为何,学术界和实务界展开了持久的讨论。
《物权法》虽然没有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却规定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二十四条确立的登记对抗制度,取得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对特殊动产登记对抗的论证与说明几乎皆立足于交付生效的立场,这样的论证虽然坚持了债权形式主义的原则,却忽略了意思主义的例外。其不仅造成了逻辑上的悖论,也颠覆了登记对抗制度原有的理论基础。笔者同意特殊动产属于动产的语义解释,但并不认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的延伸,第二十四条应该是第二十三条的例外,也即是第二十三条“法律另有规定”所指内容。只有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作此解释,方可实现逻辑的自洽和理论的正本清源。
二、债权意思主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其确立了特殊动产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换言之,只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即可发生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作此解释并非臆测,有解释论和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为其佐证。
(一)《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可解释性
基于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这一通说和《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内容的自然延伸,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当然适用一般动产的物权变动规则,这才是体系解释的应有之义。其具体阐述如下:《物权法》第二章规定的是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一节规定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第二节规定了动产的物权变动。而第二十四条正处于第二节动产物权变动之下,其要解决的是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问题当无疑问。问题在于第二十三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为交付,但对“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具体内容没有进一步明确。其他的专门法律法规也没有针对此内容作出明确的说明。因而,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内容的自然延伸,抑或是第二十三条的“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具体规定,存在着可解释空间。在体系解释语境下,坚持认为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规定内容的自然延伸,其论证的理由核心便是第二十四条处于第二十三条之下,两法律条文应该存在统一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存在片面之嫌。基于动产的语义解释,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都是针对动产的物权变动所作的立法,此乃不争之事实。但论证者在论证过程中只看到了第二十三条前半部,也即“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与第二十四条的联系,但没有看到后半部与第二十四条的关系。论证者所谓的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规定内容的自然延伸,也仅仅是第二十三条前半部和第二十四条存在联系,并没有涵盖第二十三条内容的全部,这样的论证不失为一种片面。论者之所以作出上述的论证,是因为论者是在“动产”与“特殊动产”这种包含关系的统一逻辑下去考察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四条之间逻辑关系的,很容易得出上述片面的体系解释。基于论证者的逻辑,如果将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三条前半部对应起来,得出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内容的自然延伸的结论,同样可以将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三条的后半部对照起来,得出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的例外的结论。多种解释的可能,更能说明上述逻辑论证的片面。
在法律方法论上,也不能过分高估这种基于条文在法律中的体系地位而作的论证,只有留意到规范的目的,才能理解法律的意义脉络及其基础的概念体系。相较于其他法律解释标准,现代法律人甘愿将目的解释置于一定的优先地位,即根据法律规定的目的、理性、理由思想来研究,并从中考虑该规定的意义。[2]231-246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历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草案均未对该条文的立法目的作出明确的解释。这与我国法律草案对立法目的不作详细解释的现实相符。在《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对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目的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该弹性地理解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与理由,应该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探究法律的立法目的。[3]73-74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针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说明当然是探知立法目的必不可少的素材,但在立法过程中参与立法论证讨论的学者所发表的规范性意见也应该是立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对法律条文作出的立法目的说明不同于立法理由书,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其对法律条文的说明便是立法者真实意思的表达。无论是《物权法》的法律条文还是民法室的释义均未对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目的进行详尽说明,但可以从参与《物权法》立法论证讨论的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观点中窥见一斑。作为《物权法》起草小组核心成员的梁慧星先生也认为我国《物权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例外地采债权意思主义。而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物权的变动,系《物权法》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4]84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的法律文本中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特殊动产买卖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在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也罗列了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四种争论观点。其中一种观点便是认为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在合同生效时发生。就起草小组最终支持何种观点,及此选择的适当性等问题,暂且不论。起草小组列出“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在合同生效时发生”这一观点,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遵循债权意思主义,是具有合理性的。
(二)《物权法》对债权意思主义确立的统一性
如上文所言,我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上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主义模式,以折中的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以登记对抗的意思主义为例外。《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作为一个不完全法条,仅仅就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明确地规定了登记对抗,并没有明文规定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是遵循债权形式主义还是债权意思主义。如果说《物权法》第二十四条采取的是债权意思主义,那么以下《物权法》的规定内容可以为此提供论理根据。
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始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或者转让,当事人要求进行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以明确得知,《物权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采取的是债权意思主义,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互换、转让的生效要件是合同生效。相较于《物权法》确立的债权形式主义这一原则,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即设立,可谓是一种特例,但确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符。一是因为承包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互熟悉,承包的地块人所共知,能够起到相应的公示作用。二是因为承包证书的发放和登记造册,往往滞后于承包合同的签订,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户的承包经营权。[5]286虽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自合同生效时设立,但为了确定土地经营权变动的事实和明确权利人,《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确立了登记对抗制度,也即“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否登记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法律并不强制当事人进行登记。如此可知,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之上的。
《物权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也规定,地役权合同一经生效,地役权即为设立。地役权设立以地役权合同生效为要件,如果地役权人或者供役地权利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地役权的设立亦采取债权意思主义,只要地役权人与供役地权利人自愿达成的协议生效,地役权即宣告设立。根据当事人的选择,可以就地役权的设立进行登记,登记与否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立法者之所以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是源于这样的现实: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缺乏,为了解决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确认土地之上的各种物权实现土地的高效率的利用。为了方便群众,减少成本,物权法对地役权实行登记对抗主义。[5]348同样可知,地役权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是以债权意思主义为基础的。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工具,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条内容可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工具,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财产进行抵押也是例外地采取债权意思主义,当事人达成的抵押合同一旦生效,抵押权即告成立,并不以登记为其生效要件,因为采用不转移财产占有方式的抵押作为担保方式往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如果法律规定对这些动产抵押也需要进行登记,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不便,也会给当事人增加成本。[5]412虽说登记与否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但因第一百八十八条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是否登记将产生不一样的法律效果,即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样,《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对动产浮动抵押也规定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说,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内容再一次证明了登记对抗是以债权意思主义为基础的。
显然,《物权法》确立债权意思主义之处,也同时规定了登记对抗,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并非一种偶然。尽管动产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已是《物权法》之例外,但对某种模式的选择应当一贯地体现在法律制度构建中。基于债权意思主义和登记对抗这种契合性在《物权法》中的体现,以及《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内容,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既然第二十四条确立了登记对抗,那么其也应当是以债权意思主义为基础的。所以说,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亦遵循债权意思主义。同时,在比较法上,债权意思主义与登记对抗也保持着衔接的关系,对第二十四条作此解释,也是对被借鉴制度实质的尊重。
(三)比较法中债权意思主义的实质性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除了物权形式主义之外,尚有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等其他模式。就物权变动模式而言,不存在一个模式绝对优于其他模式,一国之所以选择某一物权变动模式,纯属是立法技术上的设计。债权意思主义作为一个典型的物权变动模式,其发展传承必定不可偏离其制度实质。
债权意思主义首创于法国。之所以确立这种物权变动模式是源于这样的理念:物权所有权转让不同于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其本身无法实现“自我表现”。所有权转让本身在客观上并无任何外观迹象,也无特别的形式可察,这种转让只能被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确认。[6]432基于此,《法国民法典》规定:自标的物应交付之日起,即使尚未现实交付,债权人即成为所有人。可以看出,法国民法规定所有权转让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意思,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和所有权人承诺出让所有权的时间保持一致性,也即只要所有权转让协议规定的转让时间届至,不管该标的物是否实际发生了转移,其所有权即完成了转移。
日本民法也采债权意思主义。日本民法规定,物权的设定及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日本民法典》第176条),同时规定了物权变动非经登记或交付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177条、第178条)。日本民法的规定,向世人展示了债权意思主义之本相。可以说,债权意思主义是与公示对抗相配合的一种物权变动规则。此制度设计基于这样的自然逻辑:在债权意思主义下,所有权变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一旦当事人就所有权达成协议,即使标的物尚未实际交付,所有权也真实地转移给另一方。但此种情形下,仅有当事人之间的内部意思表示,并没有物权变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受让人虽然享有所有权,但其没有让世人知晓的权利外观,不能向世人表明其所拥有的物权。为了实现物权的对世性,就需要完成一定的公示行为,方可使受让人享有对抗世人的绝对物权。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采何种模式,但清楚地规定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债权意思主义与公示对抗制度的衔接关系,完全可以将第二十四条解释为债权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即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在合同生效时发生。
三、结语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作为不完整法条,这种不确定性使其正确理解与适用陷入困境。基于债权形式主义在《物权法》中的一般性规定,也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解释为交付生效。这样的解读虽然做到了与学理通说和法律原则性规定保持一致,但并没有为正确理解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提供帮助。这是因为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放在交付生效原则下进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律体系性和原则性的要求,却漠视了例外。这样的解释既不符合一般性思维,也不符合法律体系设计要求。在原则性条款下规定例外,即《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的例外,是不违背一般性思维和法律体系设计要求的。以概念精准、体系科学而著称的《德国民法典》也是这样的立法设计,《德国民法典》第929条是对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的具体规定,即交付生效。但在第929条下规定了未登记船舶或船舶一部分的所有权转让,所有权可以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合意发生移转,不需要交付。也就是说,坚持严格物权形式主义的德国民法典,对未登记船舶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同时,债权意思主义与登记对抗在我国《物权法》中的高度契合,其实是债权意思主义实质性的体现。所以,笔者认为应该突破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改采债权意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特.物权变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3]崔建远.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J].比较法研究,2004(2).
[4]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高富平.物权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琴】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Real Right Transfer Pattern of Special Personal Property
ZHAO Lei1, CAO Ya-ya2
(1.InstituteofCivilandCommercialLaw,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2.LawSchool,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24 of “Real Right Law” does not explicitly stipulate the requirement of validity in transfer of special personal property. Both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base their stand on validity on delivery in their explanation of this article. The argument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ormalism of creditor’s right,but they neglect the exception of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article 24 of “Real Right Law”, the uniformity established for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 in “Real Right Law” and materiality of the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 in the comparative law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Article 24 of the “Real Right Law” is an exception of formalism of creditor’s right, and it has established the real right transfer pattern of special personal property by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
Key words:special personal property; intentionalism of creditor’s rights;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1-0045-04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赵磊(1987-),男,安徽阜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在读研究生。曹亚雅(1990-),女,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