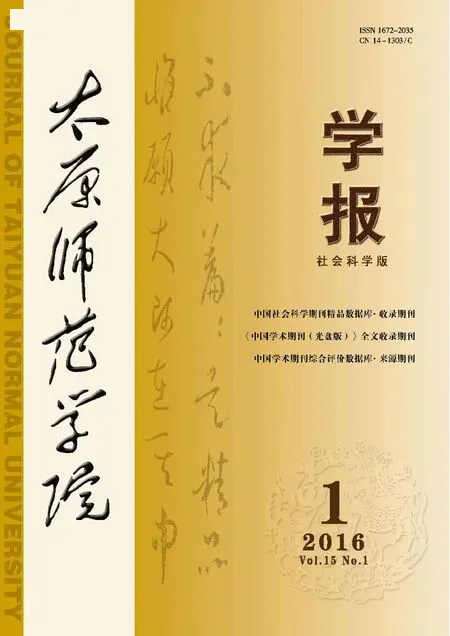同构与异构:比较视域下的“家”与“国”
刘亚明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政治学】
同构与异构:比较视域下的“家”与“国”
刘亚明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儒家的家国同构思想没有注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把国家理解为家的扩大化,把国家治理理解为家庭治理,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家国同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思想也导致了中国古代对法律作用的漠视,进而与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分野。即使这样,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颇有教益的公共议题,其中不乏浸透着沉甸甸的道德关切的议题,其中的智慧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关键词]儒家;同构;异构;“家”与“国”;私人空间;公共空间;法律
一、家庭:政治现象的开始
作为整个社会的细胞组织,家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诸多思想家也试图通过家庭来理解国家,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例,“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公孙丑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等自不待言。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事物本质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研究其最小组成单位和追溯其发生之端,城邦作为一种组织,是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组合在一起,从城邦自然发展的进程来看,起初是最简单的男女主奴的组合——家庭,“家庭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1]6。随着众多家庭的扩展联合,进而成为村坊,同样是村坊的联合导致了“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生活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1]7,至此,一切团体发展到了它的终点,组织的至善的目的因也达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是城邦的初始因,至善的城邦是家庭的目的因,从家庭到城邦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形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因果链。这样看来,从家庭出发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是中西方古代思想家的共同之处。
然而,中西方由于巨大的时空差异性,在这样的偶合之下隐藏的却是不同的思想路径、不同的政治观念和不同的政治实践。中国古代普遍流行的观点就是国就是“大家”,是扩大了的家庭,皇帝就是这个大家的“家长”,这样的理解更是被儒家学者所接受并着力论述,进而为之后数千年的中国君主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秦朝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侯国终于被整合成为一个国家,而武力就是这个国家形成之初的强力胶和粘合剂。在残酷的战争和杀戮之后,充当军事首脑的君主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君主专制体制由此而确立,至此以后,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脉传承,君主专制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底色。古代的中国从此摆脱了尧舜禹的“禅让”,也没有了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汉初时期就曾沿袭了分封的传统,但随后被逐个歼灭),更没有了逐鹿中原的诸侯,秦朝实行郡县制,全国大小事务统一归君主管理,对君主负责,君主成为了唯一的权力垄断者:“秦帝国的建立在实践上为强化君权提供了历史条件,同时,皇帝至上的理论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2]179
二、“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两种政治理解
秦朝的短命为法家的政治理论打上了问号,“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成为了汉初统治者对秦朝政治的反思而作出的选择,因为“秦朝的许多政策与实践走到了极端,是悖谬的,但它所建立的一整套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却是所有做皇帝的人都不会抛弃的。”[2]173客观条件上,随着民生凋敝的结束与国力的增强,黄老之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结束了自己的使命,选择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主观条件方面,在一个没有法治的人治社会,一种政治理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代表绝对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偏好。这就决定了黄老之术的政治理论注定是不能长久获得统治者青睐的,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绝对不甘心于简单的“无为而治”,没有限制的权力一定会像肆虐的洪水一样泛滥。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诸子之学成为君主桌案上待点的一份份菜肴,现在的问题是哪份菜比较适合君主的胃口。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标志着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主流,随后尽管有所变动,但儒学的官方地位越来越稳固,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可谓是一部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践史。儒家思想之所以获得君主的垂青是由其自身的学说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儒家思想秉承西周礼治,讲究上下名分,贵贱有别,有助于维持君主的权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既不像法家那样讲究严刑峻法,也不像道家那样缺乏对公共社会的道德伦理关注,而是主张“仁者爱人”和深度介入社会,是统治者最乐意接受的一种政治主张。
儒家向来有着深切的道德伦理关注,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国家、天下,从儒家《大学》对“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从个人的“修身”到私人领域的“齐家”再到属于公共空间的“治国”的过程就是一个“仁礼”伦理关注的外延不断扩大的经过,也是一个适用范围逐渐漶漫的进程。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家那里,个人、家庭乃至于国家的伦理追求都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伦理关注所应用的半径不同而已,很显然国家的应用半径远远大于个人和家庭,但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这点来看,儒家学者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例如“仁”在孔子那里可以理解为“仁者爱人”,可以是对各式各样的人的爱,爱自己的身体发肤是“孝之始”,爱长辈可以称之为“孝”,臣子爱君主则可以称为“忠”,君主爱民众可以称之为“爱民”,到了孟子那里则直接化作“仁政”说,很显然,一个“仁”字,可以运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在公共空间,“仁”都是普遍适用的准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思想家和西方古代思想家和近代学者之间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分野,因为在西方学者眼中,国家和家庭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岂能等而视之,所依据的规范准则也应该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他就对家务管理和城邦管理进行了区分:“可以看到主人的权威异于政治家的权威,各种权威(统治制度),并不像有些思想家所说,全部都相同。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的人;主人所管辖的则为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19进而亚里士多德把关于城邦的学说和关于家庭的学说区分开来:“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自行结合而构成的。……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的目的却是‘优良生活’……”[1]143亚里士多德把关于城邦的学说称之为政治学,关于家庭的生活称之为家政学,关于个体的生活则是伦理学,这种划分学科的做法对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韦伯说:“所有的亚洲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堪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的系统研究,而且还缺少一般的理性概念。”[3]2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区分使得西方世界早早就习惯于对国家和家庭进行两分法研究,西方的思想界始终恪守这样一个原则:个人、家庭和政治社会是不同的领域。
而中国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家国同构式的思维方式,把关于个人家庭伦理准则直接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君主成为了臣下必须“忠”于的父亲,进而形成了“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能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礼记·大学》)由家而国的演进。治国必须从齐家开始,在儒家的理解中治国和齐家是同一的,只不过是范围的大小有别而已,“故治国,在齐其家”(《礼记·大学》)、“宜其家,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礼记·大学》),这种家国同构式的治理方式一方面适应了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构成,另一方面也在强化着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结构,使得古希腊人的polis(城邦)、英语世界中的state与中国古代的家、国混合体“国家”有些微妙的区别,“国”和“家”的构词方式,至少说明了在中国古代,国和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公与私、法治与人治:两类政治发展逻辑
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结束后经过了短暂的马其顿帝国时期,之后是罗马时期。罗马时期是一个法律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罗马法始终是调节罗马公共社会的准则,即便在君主权力强化的罗马帝国时期,“事实上依然是:从长时段看来,那个植根于法律之中的理想乃是欧洲政治文明——亦即古老城邦自由生活的升华——中的一个永恒的因素,而正是这个因素能够在东方专制主义之奴性被明显移植到罗马来的那个时代中存续下来并超越那个时代”[4]219。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还是在古罗马,法律都是调节公共社会生活的准绳,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所缺乏的观念,在传统儒家那里,从来没有想到过用法律来约束公共社会,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人治传统和没有可以比较的参考系而导致的恶果。在中国古代,“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政治泡沫而已,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始终处于法律之上,据于金字塔的端点处,而且可以根据一己之偏任意改变法律,即便在历来以“法治”著称的法家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社会,法律只不过是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与西方的法治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西方社会,法律在进行政治构建的时候向来是被优先提及的对象,即便在固执如柏拉图者,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哲学家”理想国难以实现而不得不在《法律篇》中构建一个“次一等的理想国”,在这里,法律被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超越于“哲学王”之上,尽管柏拉图还是对自己的哲学王恋恋不舍,但在法律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律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对宪政统治的强调,实是他认真对待《法律篇》所提出的这样一项主张的结果,即不能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应当把法律视作是道德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4]133。
经过古罗马的发展之后,西方世界进入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传入又给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添加了新的因素。以世俗国家为一端的国王与以教会为另一端的教皇之间展开了对抗,虽然最终以国王的胜利和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为结局,但对抗的过程却激发了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意识。在这种对抗中,人们认识到国王的权力是可以受限的,当近现代的宗教不再充当对抗国王的角色而退出世俗社会专注于精神世界时,王权受限的观念却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直到近代思想家那里,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把王权受限的观念再次包含进去,产生了现代宪政国家。
中国历史的发展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自成体系,在东部是大海、西部是沙漠、北部是戈壁、南部是群山的自然条件下,不紧不慢,按照自己特有文化的节奏发展着,中国文化自成一派,鲜有外来因素的注入,即使有丝绸之路,但仅仅限于商品往来;即使有佛教的传入,但也有着儒道玄学的消解而终归“入乡随俗”;即使有郑和下西洋,但也仅仅是炫耀国威,而没有推进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中国相对安定的环境为取得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提供了条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儒家所具有的“仁礼”等观念没有意识到法制在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意义,中国整体文化环境的制约也决定了不能产生出法治社会,儒家文化传统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都不具有法治社会产生的条件。一方面,中国政治传统中没有君主权力受限的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自秦朝君主专制主义建立以来,纵贯两千多年,在这其中,君主一直是整个政治社会的绝对主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君主就是整个社会的主人,就像一个家庭不能缺少父母一样,整个社会也不能缺少君主,人们的全部政治期待都聚集在君主身上,君主权力受限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即使在君主专制发展的末期,中国本土思想家,诸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制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称专制君主为“窃天下者”,甚至提出了“置相权以分君权”的宝贵想法,但最后还是没有跳出旧有的政治蓝图: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圣贤明君的身上,借鉴古法,实行复古。所以他们的政治理想依然是旧式的,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治文化资源是既定的;另一方面,长期的君主专制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习惯,使得传统的古代中国人产生了“路径依赖”。这点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中,人们还是试图维持传统的统治而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器物层面的落后,实行洋务,兴办企业,力图用“中体西用”的方式来实现国强民富,直到后来学习西方政治文化,接受西方观念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现代的政治理念才被人们认识到,最后接受。
儒家家国同构式的思想方式和治国理念没有认识到公共社会和私人空间的区别,没有认识到公共空间是由处于不同位置上、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所组成的,软性的道德制约只能靠君主的绝对权力来贯彻。儒家学者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试图通过教化来唤醒人们的善性、激发人们的道德自觉,实现小至家庭的和睦、大至国家的和谐秩序。而西方学者对人性的普遍怀疑态度使得建立某些非人格性的法律成为必要,经过中世纪的宗教影响,“原罪”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人性恶的观念得到加强。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这一切都是人性中自然的、固有的原则和情感的结果;这些情感和原则既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人们会以为依靠于这些原则和情感的我们的行为也必然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不论道德家们或政治学家们如何为了公益干预我们,或是企图改变我们的行为的途径,那也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们的计划的成功依靠于他们在改正人类的自私和忘恩负义方面的成功,那么除非有全能的上帝加以协助,他们将不能前进一步,因为只有全能者能够重新改造人类的心灵,而在那些根本之点方面改变心灵的性质。”[5]557对人性的悲观态度使得古代西方乃至于近代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建立法律的绝对必要性,因为法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规则,这些强制规则是保证政治目标实现的可靠程序。该程序是非人格性的,能给予人确定不移的预见性,维持公共社会的正常运转。众所周知,尽管中国古代有性善论、性恶论、恶善混杂论以及性不善不恶论,但最后主流的理论普遍认为人性为善,并且人有巨大的善的潜能等待去挖掘,因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部分的笔墨都致力于论证如何发扬人的善性。对人性的高估使得人们全身心地关注于对个体自身的改造以及对圣贤明君等高尚人格的祈盼,而忘记了正是外在的强制规则和法律才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可靠保障:“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倾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致士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善的假设实际上为人治社会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与古代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相契合。
家庭和国家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规模很小,而且家庭成员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在儒家的家庭观念中,家庭中的权威是父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第四》)子女应该遵循父母的教导才合“孝道”,这种具有温情和血缘的特点在公共社会空间中是不存在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诸多个体组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缘于某种个人利益而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公共空间中,一方面,血缘的纽带被扯断,人们的关系不再紧密;另一方面,社会并不是一个个分离状态的人的机械组合,每个人的利益都要经过别人的合作方能实现,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人构成了其上的一个个扭结,一个稳定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良好的合作体系。[6]14缘于此,公共的政治和法律规则才有了用武之地。
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把家与国并列,并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理家政、管理国家,没有注意到公共空间与私人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公共空间显然不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是一个“生人社会”,每个人都不担负有像家庭中子女附从父母的义务,每个人也都没有权利享有像家庭中父母管教子女那样的权力,每个人都是单一而平等的个体。人们之间这种平等而又陌生,陌生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需要一种超越血缘家庭的规则来调节。这样的公共规则才能有效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链接,在这种公共准则下,人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善意的“赏赐恩泽”,也没有必要担心任何人的恶意侵犯,凭借着这些公共规则的庇护,我们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家长式的君主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和有效的公共规则,这些“规则”在人治的社会是不可靠的,因为家长式的君主的任意而为给每个人的前途都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这也是儒家家国同构式的治国方式无法导致现代公共社会产生的根源,也是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缘由。
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国家被理解为契约的产物而非血缘性质的产物,公共生活也是订立契约之后的结果,直接面对国家的是一个个参与订立契约的个体。通过契约,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的权力和义务都得到了明确的界分,这种界分又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保障,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互不干涉,在私人空间中,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因为不属于国家权力调配的范围,在公共空间中,每个人也都是安全的,因为国家这头“利维坦”的权力是受限的。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则没有这样的划分,也没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家国是一体的,君主的权力更是不受限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和家庭等私人空间都成为了政治权力场。
四、“国不以利为利”: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命题
尽管这样,在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儒家思想给人们提供了诸多很有教益的公共议题,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的命题了。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关于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的争辩,争辩的双方主要在儒家和法家之间展开。儒家坚决主张行王道,即以仁义德治治理国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与王道相对的是法家,主张“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纂文理也,非服人心。乡方略,审劳佚,谨积蓄,修战备,龄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荀子·王霸》),以刑名法术治国。这样的讨论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化为儒家内部的辩论。最为典型的是北宋时道学家与功利主义学派之间围绕着“利”和“义”展开热烈的讨论:治国应遵从“王道”还是“霸道”?“功利”优先还是“道义”优先?道家学派主张“道义”为先,功利主义学派则主张“功利”为先。[7]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很类似于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道义论”和“目的论”的区别。
北宋时期的道家学派如周敦颐、朱熹等,与事功学派如程亮、王安石等的对峙和辩论对我们公共空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代思想家讨论王霸义利,体现了思想家良善的政治愿望。从历代思想家论辩王霸义利的内容来看,尽管人们对于王霸义利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用善恶的标准对社会政治加以品分,意欲使社会政治最大限度地符合道义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颇近于希腊哲学家所追求的‘最大的Good’和‘永恒的正义’”。[7]这表明,“义利之辩”的公共议题涉及公平分配等正义问题,含有现代公共领域中的重要议题。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家对国家的规范性期待。作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应该秉持道义,而不是为了政府自己的私利。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约定的产物,充当的是“仲裁者”角色,这种仲裁身份的合法性源于各个缔约主体的一致同意,国家能够在各个利益主体发生矛盾冲突时进行公平的裁决。“国不以利为利”体现了对这种“公平裁决”的关注,这种关注能够引导人们思考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政策才是公平正义的。在儒家看来符合“道义”的治国策略才是值得向往的国家政策。作为一个仲裁者,政府本身不生产任何财富,只是对已有财富进行分配,政府是一个公共的权力机构,不应该有自己本身的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有其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彭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郑之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孙晓春.王霸义利之辩述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3).
【责任编辑张琴】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1-0027-05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刘亚明(1986-),男,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