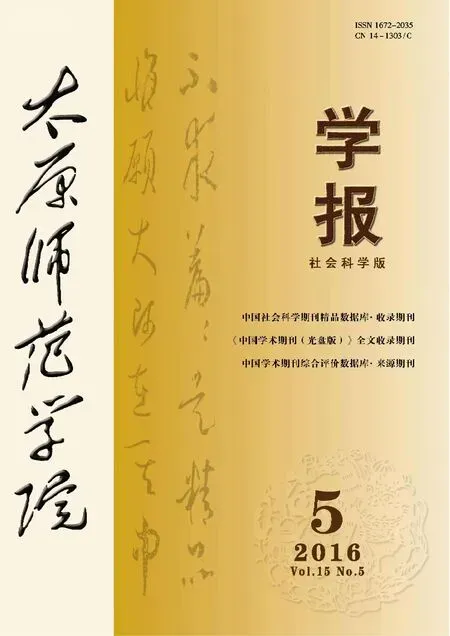春秋时期卿大夫明哲保身思想研究
李 睿
【历史学】
春秋时期卿大夫明哲保身思想研究
李睿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对个人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守身自保在他们的言论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种现象是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已被破坏、政治局势动荡所造成的结果。在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下,卿大夫将守礼视为保身之道,提高了“礼”的地位,为儒家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卿大夫;明哲保身;礼
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为了能够保证个人与宗族的安全,在政治上普遍主张慎言慎行,安分守己,并提出“礼以庇身”的主张,将守礼视为自保之术。认识这一现象对于研究春秋时代卿族政治的特点,探究“礼”的思想发展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通过对史料的归纳总结,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请学界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执著自保的表现
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在评价某人的时候,能否保全其个人与宗族是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弭兵之会后,郑国宴请晋国正卿赵文子,七位重臣依次赋诗言志。事后赵文子评价道:“伯有将为戮矣!……其余皆数世之主也。”[1]1135《左传·昭公元年》载:诸侯会于虢,郑国的子羽点评诸位大夫:“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鲋字而敬,子与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1]1204《国语·周语中》载:刘康公聘鲁,见“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于是预言:“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2]69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卿大夫应当具有识别时务、守身保家的智慧。《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齐国的庆克与声孟子私通,鲍牵举报而被刖,孔子评论道:“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1]899在孔子看来,不能够自保的人,即使遭遇不幸也不值得同情,哪怕这并非他的过错。类似的看法还有《国语·晋语八》赵文子语:“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称也。”[2]433他认为“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的人才是值得追随的。这一观点也得到时人认同:“晋人谓文子知人。”[3]304
守身自保的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活动,还渗透在了卿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并作为人生信条教育自己的后人。《国语·晋语五》载:范文子喜直言,范武子怒斥道:“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又“击之以杖。”[2]381在这样严厉的教导下,范文子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并终生恪守明哲保身的信条。成公二年鞍之战后班师回国,范文子认为:“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于是后入。范武子高兴地说:“吾知免矣。”[1]806晋楚鄢陵之战后,范文子预料到晋国将有大乱,于是祈神求死,说:“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1]897树大招风的范文子死后,他的家族果然在内乱中得以置身事外。可见,范文子一生谨小慎微,绝非因为个人贪生怕死,真正令他恐惧的是灭门之祸。童书业先生指出:“那时的宗族差不多有生死个人的力量……宗族的观念笼罩了个人的人格,同时也掩蔽了国家的观念。”[4]80在卿大夫们看来,保身的最终目的是“守其官职,保族宜家。”[1]1194为了这个最高目标,不仅无惧死亡,也可以承受比死亡还难以忍受的耻辱。鲁国的季武子在诸侯盟会期间起兵伐莒,致使叔孙豹被楚国扣押,险些丧命。叔孙虽然十分怨恨,却仍然与季孙和解,理由是“虽死于外,而庇宗于内,可也”[2]188-189。相比之下个人恩怨便微不足道了。
即便如此,能够在政治斗争中保全宗族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语:“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1]1236-1237岂止公族卑弱,即使是那些把持晋国大权的卿大夫们,最终大多也难逃一劫,沦落到“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2]453的境地。不仅是晋国,各国的强宗大族,到了春秋末年几乎全军覆没。《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总结得可谓精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1519-1520可见卿大夫保全宗族是何等困难,如此热衷于明哲保身,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卿大夫面对的威胁
卿大夫群体强烈的危机感,与春秋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首先,卿大夫与国君之间存在矛盾。朱凤瀚先生指出:“(卿大夫家族)随着自身实力的膨胀,公室的存在已成为其扩张政治、经济权益的障碍,于是控制与削弱公室渐成为卿大夫家族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时,“国君和公室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遏制卿大夫家族势力的发展,以保持自己的统治权。”[5]515-516因此双方的斗争无法避免。在卿族最强势的晋国,君臣矛盾表现得也最为激烈:宣公十三年,晋杀先縠,灭其族;成公八年,晋景公借赵氏内部不和灭之;晋国公卿之强,无过于“五大夫三卿”的郤氏,成公十七年,晋厉公杀三郤,灭其宗族。先氏、赵氏、郤氏的覆亡,成为后继者的前车之鉴。《国语·晋语八》叔向劝谏韩宣子时即以郤氏为例:“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2]438-439
到了春秋后期,卿大夫的实力已经开始超过国君,但仍然不能在每次斗争中都占据上风。《左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的范氏、中行氏自恃强盛,与国君为敌,高强劝道:“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1]1519二人不听,结果“国人助公,二子败”。何况,由于“春秋列国间的国际关系向弱肉强食方向发展,任何卿大夫家族依靠自身势力皆不足以在此种环境中独立生存,只有联合起来求得共同的生存,此种情况下,公室仍然是最适合的名义上的共主。”[5]514例如晋国正卿韩宣子,私人武装不过战车七百乘,还比不上“革车千乘”的鲁国,若没有国家的庇护,单靠一族之力显然是无法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自保的。这也是栾书弑晋厉公后,众人仍要拥立晋悼公的原因:“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无乃不堪君训而陷于大戮,以烦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业。”[2]403可见,国家仍然是卿大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卿大夫无法取代国君,自然也就无法消除来自国君的威胁了。
其次,卿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在春秋早期争霸战争的背景下,他们彼此还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团结,即使“兄弟阋于墙”,也要“外御其侮”[1]424。例如在城濮之战和鞍之战中,晋国群臣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加之“由于各集团内的诸卿族大致是由同一个基点起步的,彼此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个卿族欲压倒其他卿族独揽国政,都是不可能的。”[5]525但是,“经过春秋晚期近一个世纪力量积累,诸卿族坐大,彼此的矛盾走向激化”[5]527。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普遍拥有了采邑,并以此为基础组建起私人武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1]1192-1193,采邑及采邑武装既是卿大夫庇佑自身的根本,也是争权夺利的工具。卿族之间的矛盾一旦无法调解,便往往诉诸武力,这种争斗成为春秋后期卿族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昭公二十八年,晋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此后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齐国的栾氏、高氏等家族灭亡后,其封邑财产亦皆被胜利者所瓜分。越到春秋后期,卿族之间的自相残杀就越激烈。就是卿大夫自身对动荡的局面也感到恐惧,以至到了“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1]1359的程度。
另外,卿大夫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激化。春秋时代“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1]94,本意是为了通过分封侧室壮大自身的实力,以达到“使得世族血缘关系圈中所占领之土地扩大”[6]224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关系渐渐疏远:“小宗的经济力量增强后,旧有的血缘等级制即成为其进一步扩展实力的障碍,因而在家族内部,小宗强烈要求进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7]141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卿大夫视为安身立命基础的宗族,也有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隐忧。例如,文公九年,晋国的先都因未能得到提拔怀恨在心,结党作乱杀其宗主先克;成公八年赵氏的灭亡,就是由赵同、赵括与赵婴齐、庄姬之间的矛盾引发的;鲁国的臧会因窃取宝龟被臧昭伯囚禁,出逃后投奔了季平子,昭公二十五年在季氏的扶持下反而成了臧氏的宗主;定公十三年,赵氏内部再度爆发争端,最终以赵简子杀死赵午,吞并其采邑而告终。
卿族内部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是:家臣也有机会坐大。这是因为卿大夫的采邑扩大后,必须设置家臣管理。在家主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采邑的控制权往往落入家臣手中,成为卿族的心腹之患,在鲁国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柄”的局面:昭公十二年,季氏家臣南蒯据费邑为乱;定公五年,阳虎囚禁家主季桓子叛乱,后来竟挟持鲁君和三桓与他结盟,把持政权长达三年之久。此后又先后发生了侯犯、公山不狃、公孙宿的叛乱,几乎动摇了鲁国的根基,三桓虽未灭亡,但也元气大伤,昔日风光亦不复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集中体现在宗法制的延续和瓦解:一方面,血缘宗法制度的因素仍然在社会广泛存在,卿大夫作为家族之长,负有庇护宗族的责任,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君和同僚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随着宗法制度不断地被破坏,表现为“血缘亲族关系的进一步被削弱,宗法等级关系在实质上的瓦解,家主与臣民间的政治等级隶属关系的破坏”[5]491,卿族内部围绕着权力和财富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传统的血缘等级关系已经难以维持对宗族成员和家臣的控制,卿大夫阶层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明哲保身”思想的流行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三、卿大夫的保身之术与影响
在春秋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克服宗法贵族政治弊端的新的统治形式,以便“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7]164。但是卿大夫毕竟是宗法贵族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只能在既有的政治经验中寻找出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礼”。如《左传·成公十五年》申叔时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1]873可见,守礼在当时已经被视为自保的重要手段。《左传·文公四年》载,卫国的宁武子聘鲁,见宴席上奏天子之乐,便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1]536《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1]1295这两个例子都是“礼以庇身”思想的体现。卿大夫还时常将宽容、礼让、谦虚、节俭等品德视为守身之道,如《国语·周语中》:“以敬承命则不违,以恪守业则不懈,以恭给事则宽于死,以俭足用则远于忧。”[2]70这些观念同样体现出“礼”对其行为的规范。
“礼”作为卿大夫的保身之术,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隆礼尊君,谦恭待人,可以消弭国君和同僚的忌惮。《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楚国的薳子冯有八名宠臣“皆无禄而多马”,申叔时警告他这会招致国君的不满,于是“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1]1070《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坚决反对攻打子产的理由是:“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1]1177其次,示礼于下,又能上行下效,巩固对下属和民众的统治。《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曰:“礼,所以整民也。”[1]226《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1]1194
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普遍积极学习礼乐。晁福林先生指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指的是诸侯和卿大夫的僭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贵族已视礼仪如敝履而不屑一顾,恰恰相反,在迅速变动的形势下贵族为了稳固自己的根基和图谋发展,往往更加重视礼仪。”[8]227宣公十六年,晋国的士会聘周,不通享宴之礼而闹了笑话,于是“归而讲求典礼”[1]770;鲁国的孟僖子因不能相礼而愧疚终生,临终还念念不忘,要求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在时人言论中,“礼”出现的频率也呈现出递增趋势。以《左传》的记载为例,春秋早期隐公在位的十一年中,论述“礼”的言论(不包括后人评论)出现了3次,桓公在位的十八年里,出现了4次;到了春秋中期,文公在位的十八年增加到8次,而襄公在位的三十一年里,总计出现了31次之多。卿大夫“礼以庇身”的需求正是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贵族之所以循规蹈矩而不逾于礼,目的便在于‘庇身’”。[8]231
值得注意的是,卿大夫对“礼”也并非一味地肯定与吸收。通常来说,他们更强调礼的实际效果,而不看重其形式,《左传·昭公五年》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女叔齐却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1]1266《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亦认为揖让周旋之礼“是仪也,非礼也。”[2]437因此,卿大夫对“仪”往往因时、因地制宜,并不主张精确地恢复古礼。《国语·晋语八》子产曰:“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1]1457这是对晋国既得利益的一种认同。卿大夫推崇礼者也多属此类,是将礼乐制度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所以“春秋时期的卿大夫贵族,一方面恪守礼仪,把‘礼’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传统的‘礼’对自己的束缚,不少贵族千方百计要越出礼的樊篱。”[8]232典型例子如鲁国的“八佾舞于庭”[9]136、“季氏旅于泰山”。[9]151这些做法其实违背了周礼的规范,属于僭越行为,在维护周礼传统的儒家看来不但不是礼,简直是“礼崩乐坏”。但在讲求实效的卿大夫看来,儒学所倡导的繁文缛节才是不合时宜。这也是《史记·孔子世家》晏婴批评孔子的原因:“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10]1911
即便如此,卿大夫对礼的重视仍然为新生的儒学提供了发展空间,孔子的弟子们往往以为卿大夫相礼作为进身之阶。如《左传·哀公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齐,子赣(子贡)为介”[1]1693。《礼记·礼器》载子路为季氏相礼:“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3]669同时,卿大夫的明哲保身思想,也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体现出来。例如“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9]49;“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9]397;“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9]452;“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9]1097。可见,儒家学者与卿大夫虽然对于“礼”的观念大相径庭,但在守身自保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这种意见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扩大儒学的市场。
综上所述,卿大夫群体明哲保身思想的兴起,是春秋时代“旧的传统存留,新的因素出现,社会在新旧交迭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7]143的结果。战国时代,这种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劝谏孟尝君:“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11]622不过,由于郡县制的发展和官僚制度的兴起,卿族政治解体,以至于“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12]715,从而形成了稳定的集权制国家。官员不必像从前那样时刻小心翼翼,其言论中“明哲保身”所占比重也相对减少,与《左传》、《国语》中浓墨重彩的描述已经大不相同。这种差别,不仅是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在为人处世态度上区别于后世政治家的显著特征,也是官僚制度取代血缘宗法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表现。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童书业.春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6]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7]马卫东.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D].长春:吉林大学,2007.
[8]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琴】
LI Rui
(TheResearchInstituteofAncientBook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Research on Senior Officials’ Principles for Preserving Themselves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senior officials had strong sense of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prospect, so playing safe is a key principle in their public speech or a private talk, which attributes to the destroyed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turbulence at that time. With the principle in mind, the senior officials regard rituals as an effective way to preserve themselves, which helps improve the status of rituals and paves the way for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senior officials; play safe; rituals
2016-05-24
李睿(198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6)05-0014-04
K22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