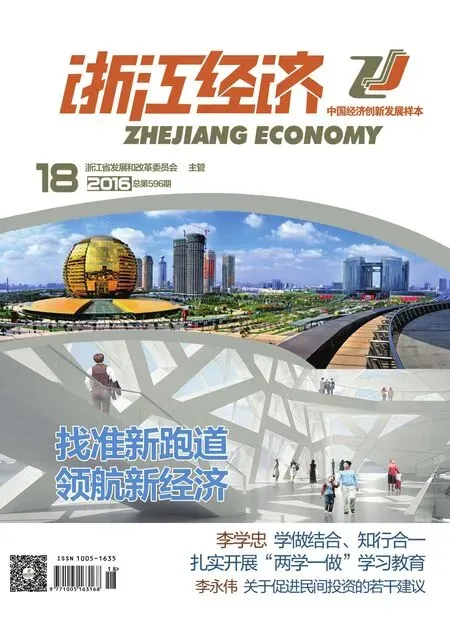优先推行信用记录报告
王宁江
·首席论衡·
优先推行信用记录报告
王宁江
在信用评级领域,资信一词后面,往往会跟着评级、评估等字样。所谓资信评级是指对被评价对象进行信用风险评价、评估,并且以专业的评级符号标明其信用等级。被评价对象可以是市场主体,也可以是一些涉及信用支付的金融产品,如债券、证券、票据等。通行的评级符号称为“四级十等”,如A级细分为AAA、AA、A,B级细分为BBB、BB、B,C级细分为CCC、CC、C,还有D级。评级公司还会对评级符号继续细分,如在分级字母上标示“+”或“-”,也有对字母作大小写区分的,慢慢地形成了某一机构评级报告特征。等级高预示着被评价对象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信用风险程度低,反之,则意味着风险增大。评级符号反映的是违约概率,在大样本中,这种概率符合正态分布。
信用是什么?概念太宽泛了,不在本文陈述之列。信用报告是个统称,产品种类五花八门,有征信报告、评级报告等,其中征信报告又分为标准报告、深度报告、专题报告等,这是专业的分类方法。个人理解,信用记录报告、征信报告属于记录类信用产品,此类产品强调尽职调查,内容上侧重于基本信息和事实记录;若编制主体是商业化第三方机构,那么称之为征信报告;若编制主体是公共性机构,那么称之为信用记录报告为妥。
由此引出本文的观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应优先推行信用记录报告。理由如下:
一是“用信”的认识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社会上对此认识高度一致。但涉及类似“用信”之类的具体问题,各方面认识上的差距便开始出现,会有种种托辞、会有畏难情绪。实践中,出实招、硬招不多,下决心、下狠心不多,还停留在“道德压力”传导层面,把信用作为“阳春白雪”放在手心捧着。当涉及利益时,更是有企业利益保护、地区壁垒等思想,推进“用信”裹足不前。运用信用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之后的大趋势,其中之一便是信用产品的应用。信用产品的应用可以帮助政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拍脑袋”决策到“精准识别”;可以帮助政府按照市场规则,优选交易对象,最大程度上发挥公共资源的开发价值,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化。
二是“用信”的习惯问题。国内市场交易活动中,在“用信”这个问题上,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小农观念,讲的是“义”和“情”,反映为“熟人经济”。市场主体普遍缺乏使用报告以了解交易风险的习惯,这说明文化的力量、传统的力量之强悍。一方面需要政府、媒体和信用服务行业等不厌其烦地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大家“用信”的习惯;另一方面,政府应带头示范“用信”,改善“用信”环境,激励带动其他主体效仿“用信”。2015年,中国人均GDP过了8000美元,按照国际上,3000-5000美元之间为信用重组阶段、5000美元之上为信用良性循环阶段的说法,我国应该进入良性循环阶段,但实际对比之后,社会各阶层的感知会有落差,这值得信用工作者的深思。当然,经济学上的不变价美元计算方法可能也是个问题。
三是“用信”的产品问题。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再次分配,带有公益性、垄断性、专有性等特征,有别于纯粹的市场交易、投融资等。一般市场活动中,需要的信用产品是基于交易对象履约能力,对未来风险定量的评判和预估的评级类产品。而公共资源领域,政府和公共资源管理部门更关注交易对象的信用行为以及以往公共资源交易履约情况,需要的产品是基于信用行为的写实性的记录类产品。评级报告对于公共资源领域“用信”来说,或许会有些复杂,概率、正态等专业名词太多,也不太容易接受,而且评级报告的编制成本更高些。
多角度评判,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用信”,尤其是在基层,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信用产品从无到有的问题,可以先从简单、管用、实用的信用记录报告应用开始。国家提出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应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我们在其中做个结合,把信用记录做成一份适用的、综合性、全面性的产品,这样更为务实。
作者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浙江省信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