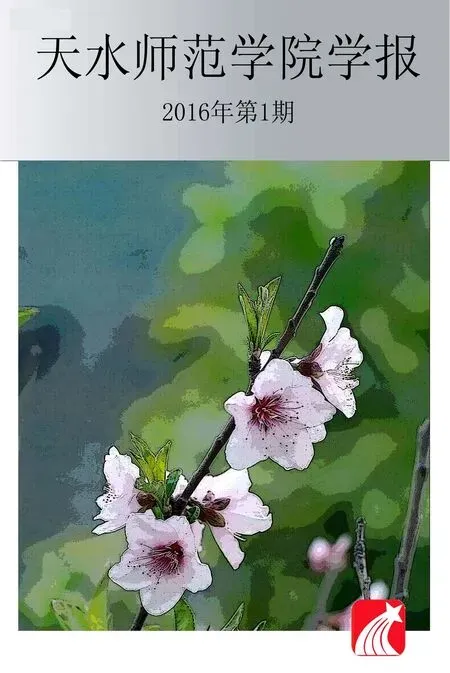敦煌本《大云经疏》研究综述
周倩倩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敦煌本《大云经疏》研究综述
周倩倩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僧俗界历来对《大云经》的真伪存在争议,上个世纪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研究涉及抄本、《大云经》与《大云经疏》的关系、《大云经疏》内容及相关研究等方面,但对其具体内容的研究力度还不够。对前辈学者关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研究情况做一详细梳理,以便后来者研究。
敦煌本《大云经疏》;《大云经》;研究综述
由于与武周革命的密切关系,《大云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关于《大云经》,史书记载或是薛怀义等人伪造,或是新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发现,重新引起了中外学者研究的热潮,先后有罗福苌、王国维、陈寅恪、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等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涉及的方面也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敦煌本《大云经疏》的研究进行梳理,突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一、关于抄本
关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抄本,有三种说法。狩野直喜是最早关注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学者,他游历欧洲,到英法两馆手录了敦煌残卷,其中就包括敦煌本《大云经疏》。罗福苌先生根据狩野直喜博士所录,复手录之,收入《沙州文录补》。[1]向达先生于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在不列颠博物院阅读敦煌卷子——《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的S.6502《大云经疏》(?三七五)中记录。[2]萧登福在《〈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中,认为薛怀义等人所上的《大云经疏》,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有数种残卷:藏于大英伦敦博物馆的编号为斯2658及斯6502两种;藏于巴黎的有伯2768号卷子。[3]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认为:“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卷P.2768,‘疏中并引证明因缘谶,亦造作佛语,彰天女授记之征,则谓永徽元年在阎罗王处所得。’”[4]对于S.2658与S.6502,学界已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大云经疏》残卷。由于藏于巴黎的伯2768号卷子本身的情况:前后均缺,可以看到“大云经六卷”,“中论五卷”字样,共存二十二行。很难将其判定为敦煌本《大云经疏》的抄本,《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将其定名为不知名佛典。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敦煌本《大云经疏》有藏于伦敦的斯6502和斯2658两个抄本。
二、敦煌本《大云经疏》与《大云经》的关系
对于《大云经》的真伪,是历来学者争论的热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长安志》均记载,《大云经》是武则天命人伪造的,但赞宁《僧史略》根据后凉的译本发现,有详说黑河女主之事以及《大云经》在晋代已经有译本等方面,认为《大云经》不是伪造,志磐《佛祖统记》延续赞宁的看法,认为《大云经》只是在武则天时重译了。直到上世纪初,敦煌石室被打开,发现了敦煌本《大云经疏》,中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前代史籍的记载,对《大云经》和《大云经疏》进行探究。现存的《大云经》有两个版本: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姚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仅存卷九)。学界现在基本上一致认为,两唐书等史籍记载的薛怀义等所上的《大云经》,其实是指敦煌本的《大云经疏》。但对其性质及其与《大云经》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
1.重译说
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有武周新字将S.6502、S.2658定名为《大云经疏》。罗福苌先生对狩野博士所抄录的西陲残经复手录之,王国维先生为其作跋《唐写本大云经跋》,对《大云经疏》的性质、名字等进行探究。王国维先生认为罗福苌复抄本是武则天载初元年所作的《大云经疏》,其内容与后凉昙无谶所译的《大方等无想经》、竺法念译本《大云无想经》有相同之处,且赞宁《僧史略》记载此经晋代已译,志磐《佛祖统记》也这样记载。因此,王氏认为,武后载初元年法明等九人是重译《大云经》,不是伪造。“今观此卷所引经文,皆与凉译无甚差池。岂符命之说皆在疏中,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诧歟!”[5]此疏写成时,与伪经同颁天下,故敦煌寺中会藏有《大云经疏》的残卷,并介绍罗氏所录敦煌本《大云经疏》的残卷内容。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与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相同,认为敦煌本《大云经疏》是对《大云经》的重译。“其年七月,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大云经》盖此前已译数种,怀义等因其内有女主之文,故特改造表上之。”[4]认为《大云经》此前已有很多种译本,怀义等因其内有女主之文,故将其改造并呈给武则天。而且,现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有武后登极谶疏者,中疏《大云经》,《东域录》中有《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就是敦煌本《大云经疏》。萧登福先生在《〈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中,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内容是依附《大云经》天女授记之事,时间上的吻合性,以及敦煌本《大云经疏》所用的都是武后所创的新字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薛怀义等所上的史籍中记载的《大云经》,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敦煌本《大云经疏》。并进一步说明,薛怀义、法明等人所造的《大云经疏》,是依据昙无谶的六卷三十七揵度本而来作疏解的。又从S.2658和S.6502两个卷号的内容来看,怀义等人所撰者,虽名为解经,其实仅仅是在阐述《大云经》第三十六、三十七揵度中,有关净光天女事迹的经文,来为武周革命寻求理论依据。[3]萧氏的另一著作《谶纬与道教》中,更直白的论及,《大云经》北凉时已有译本,唐世佛徒杜撰的是《大云经疏》,其延续汤用彤先生的观点,认为《大云经疏》的全称应是《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并以曲解附会的方式来解释《大云经》。法明在《义疏》中,将武氏比附为经中所言的弥勒及净光天女下生,当君临天下。[6]
2.注疏说
陈寅恪先生在《武曌和佛教》一文中,进一步探讨敦煌本《大云经疏》的性质和名字。陈氏对比昙无谶所译的《大方等大云经》原文,认为《旧唐书》等记载的伪造说与志磐等认为的重译说都不正确。陈氏将敦煌残本与今佛藏传本参校,发现几乎全部符合,即使有一两句不同之处,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陈氏认为《大云经疏》是薛怀义等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传会。全部袭用昙本原文,没有改易。所以,敦煌本《大云经疏》既不是伪造,也不是重译,而是对《大云经》的注疏。[7]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中认为武后为了使其篡政合法化,命人撰写和传播对《大云经》中带有倾向性的注疏。
《大云经》是一部真正产生于印度(南印度)的经典。武后曾令人撰写的疏注中有关于一位保护佛教的皇后登基的授记。注释文的发明者是武后的一位宠臣,叫作薛怀义,这是武后的一位心腹谋士,但不是宦官。为了组织这一编写工作,他又召来十几位才子和尚协助工作,薛怀义注释文的两部分恰恰在武后篡权之前就发表了,后来也是敦煌写本中发现的。除了《大云经》之外,这篇疏注文还引用了许多纯粹是汉文的神谕性短篇文献,如《证明因缘占》。在这一标题下所引用的段落与我们所拥有的那部标题相似的伪经文献仅部分相同。但毫无怀疑,这些段落与该经卷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8]意大利东方研究所的富安敦(Atonino Forte)教授1976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的《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意识》一书中,通过对《大宋僧史略》、《宋高僧传》等有关武周政权佛教性史料的反思,认为僧人们进献给武则天的是一份对《大云经》第四卷中有关女王登基的预言部分所作的“疏”,并于公元690年敕令全国寺院传抄。并论证《大云经疏》的作者们是根据公元4~5世纪昙无谶或竺佛念的译本作疏,以及证明了《宝雨经》中新加入的一节的预言部分与《大云经疏》的内容一致。
近来,林世田先生关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研究有四篇文章分别对《大云经疏》的基本性质、结构特点,及其与武则天称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大云经疏〉初步研究》从撰作人员、撰作年代等方面,对《大云经疏》进行探讨,认为《大云经》早已有之,两唐书等记载怀义等造《大云经》实为造《大云经疏》之误,撰作者是薛怀义、法明、处一、惠俨、惠稜、行感、德感、知静、公轨、宣政十人。《大云经疏》实际上是武则天授命薛怀义等所炮制,为她以女身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使她具有“受命于佛”的“合法身份”。《大云经疏》的创作时间,特别是图谶部分,在垂拱四年(688)已着手收集或撰写,后经多人(十个僧人),多次补充,最终在载初年间定稿。[9]另一作《敦煌所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及〈大云经疏〉考略——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校录》中,林氏非常认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薛怀义并非伪撰《大云经》,作伪不易,且难取信于人,不如取前代旧译曲加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功倍。更加详细的说明敦煌抄本乃是《大云经疏》而不是《大云经》本身,并且根据这篇疏文看来,所引经文乃是摘出六卷本《大云经》拼凑而成,文中穿插的大量图谶祥瑞之说,可能是武则天授意薛怀义纠合一群“浮屠”所为,是一篇集体创作。[10]孟宪实先生在《论武则天称帝的舆论营造》一文中,通过对《册府元龟》中李思顺案件的探讨,认为李思顺所引证的《唐兴辩占》是薛怀义等在为《大云经》作疏时抄写进去的,还得出:其一,现在所知敦煌本《大云经疏》是残本;其二,当时人很有可能直接把《大云经疏》称作《大云经》。[11]
无论是王国维、汤用彤、萧登福等所认为的重译论,还是陈寅恪、戴密微、富安敦、林世田、孟宪实等所拥护的注疏论,都一致的认为,新旧唐书等史籍记载的薛怀义等人上表的是伪造的《大云经》有误,其实《大云经》早已有之,并不存在伪造,薛怀义等人上表武后的乃是敦煌石室发现的《大云经疏》。不论是重译还是对其中武氏女身称帝有关部分的注疏,都是参照前代所译的《大云经》中对武氏称帝有用部分的利用,从而达到为武后称帝做政治舆论宣传的目的。
三、关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内容及其相关研究
陈寅恪先生《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武则天利用佛教符谶的原因。陈氏从武氏家世宗教信仰的薰习,及其女身称帝特殊的政治地位两方面,来说明武氏颁布《大云经疏》为其登上皇位所用的原因。陈氏认为武曌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大云经,属于大乘急进派的经典。并得出武曌与僧徒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武氏借佛教来证明其政治的特殊性,僧徒在被利用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考虑,那就是借武后来恢复自李唐开国以来丧失的权势。关于这一点,富安敦教授在其《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意识》一书中,也有同样看法。富氏对《大云经疏》产生的社会背景做了研究,系统阐述负责“疏”的九位僧人之间真实的社会联系,认为他们是当时僧侣中的精英代表,他们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意识——希望实现佛教同国家政权的结合。此外,富氏还重点研究了《大云经疏》,为我们呈现出一部完整的译本,对其结构也进行一定的分析。通过对S.6502残卷的深入分析,认为这就是法明等十位僧人于载初元年(690年)七月所上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这一点,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也有相同的看法:敦煌本《大云经疏》就是《东域录》里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富氏对《义疏》中征引的道教谶纬也进行了研究,翻译了其中的五处道教谶纬,分别是《卫元嵩谶》、《中岳马先生谶》、《紫薇夫人玉策成纬》、《嵩岳道士寇谦之铭》和《仙人石记》,并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对其产生的时间和背景进行初步考证或推测,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对富安敦教授的研究,雷闻先生在《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一文中,提出不同的意见。雷文对《大云经疏》中征引的《中岳马先生谶》的马先生进行考查,认为富安敦教授将其推测为法藏敦煌残卷P.2255《老子道德经》卷尾题记中出现的“三洞先生中岳先生马”,可能是“马遊定”这一结论是不准确的,谶中得中岳马先生应是长安金台观的观主马元贞。对此谶的形成时间也与富安敦教授的看法不同,雷氏认为此谶成于高宗去世、武后代唐之势已成之后。此外,雷氏经考证得出道教对武周政权是持支持态度的,这是前辈学者所未涉及的,对了解武则天时期道教的政治面目及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都有很大裨益,对研究我国宗教与政治关系也有很大帮助。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三阶教之研究》一书中,详述《大云经谶》,但有一些不当之处。[12]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矢吹氏提出“大授立邪三宝”指的是“大云经谶”这一观点,是对原文的误解,其应指三阶教。矢吹氏认为S.6502《大云经疏》末的“来年正月癸酉朔”是咸亨元年,岁在癸酉有误,应是天授二年,其正月朔日,恰为癸酉。
以往诸家都认为《大云经疏》是武则天利用佛教来为称帝营造舆论,是一部佛教经典注疏。但孟宪实先生在《论武则天称帝的舆论营造》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大云经疏》文本内容的分析,认为利用佛教确实是武则天营造舆论的重要部分,但总体而言,武则天利用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相关的佛教内容是在纳入中国特有的政治语言系统后被使用的。《大云经疏》表面上是一部佛教经典注疏,其实却是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或以传统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字。佛教部分,不过是汉儒以来祯祥观念的新因素而已。
对《大云经疏》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萧登福在《〈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中,批判《大云经疏》将武氏说成净光天女、弥勒下生两种不同的前世是相互矛盾的,文中广引当时许多的谶记、歌谣,来证明武则天当代唐而王,为天下女主。又说武氏大杀唐宗室及功臣,是在“诛灭凶徒,肃清天下”,这与佛教的戒杀戒律相矛盾。武则天五戒全无,杂引诸谶,牵引佛典,是愚弄人民、扭曲佛教。林世田先生的《〈大云经疏〉结构分析》一文,从《大云经疏》的结构特点入手,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大云经疏》初稿释文颇为简单,图谶之说不多,后来经过多人扩充增改,塞进大量图谶、祥瑞之说,利用佛经制造女身应当君临天下的舆论,并且利用图谶、祥瑞来说明武则天当为君主。林文对《大云经疏》的内容分析得很详细,对其中的图谶祥瑞也有较为周密的论述,为研究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符瑞的关系奠定基础。[13]林先生的《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对《大云经疏》所涉的图谶、祥瑞进行详细的研究,让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武则天是怎样利用图谶、符瑞来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的。[14]刘永海的硕士论文《略论武则天称帝与祥瑞》,对武则天称帝时期利用祥瑞的步骤、利用祥瑞的特殊性以及在称帝过程中《大云经疏》所起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大云经疏》是对《大云经》中有利于武后称帝的内容的发挥。[15]
四、总结
自上个世纪敦煌本《大云经疏》被发现以来,许多学者对其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研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目前对敦煌本《大云经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敦煌本《大云经疏》与《大云经》的关系,是重译抑或是注疏。第二,敦煌本《大云经疏》与武周政权的关系,武后利用《大云经疏》的原因以及利用的方法。对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具体内容也有研究,但除林世田先生的《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一文对《大云经疏》所涉的图谶、符瑞进行详细的介绍外,大多是就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做得研究。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对武则天时的佛教、道教、佛道关系研究得都有很大裨益,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和利用。
[1]罗福苌,辑.大云经疏·沙州文录补[M].铅印本.上虞罗氏编印,1924.
[2]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M]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232.
[3]萧登福.《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M] 萧登福.敦煌俗文学论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86-131.
[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北大出版社,2010:18.
[5]王国维.唐写本大云经跋[C] 王国维.观堂林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1016-1018.
[6]萧登福.谶纬与道教[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552-553.
[7]陈寅恪.武曌和佛教[C]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16-735.
[8]戴密微.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M]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编.敦煌译丛: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41-143.
[9]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J].文献,2002,(4):47-59.
[10]林世田.敦煌所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及《大云经疏》考略——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校录[J].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学志:第1辑,2003:165-190.
[11]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的舆论营造[C] 复旦大学历史系.“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知识、信仰与社会的交互视角”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2]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J].中国史研究,2004,(1):73-80.
[13]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C] 郑炳林,等.麦积山石窟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14]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02,(2):64-72.
[15]刘永海.略论武则天称帝与祥瑞[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王景〕
K879.21
A
1671-1351(2016)01-0027-04
2015-12-12
周倩倩(1989-),女,安徽凤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