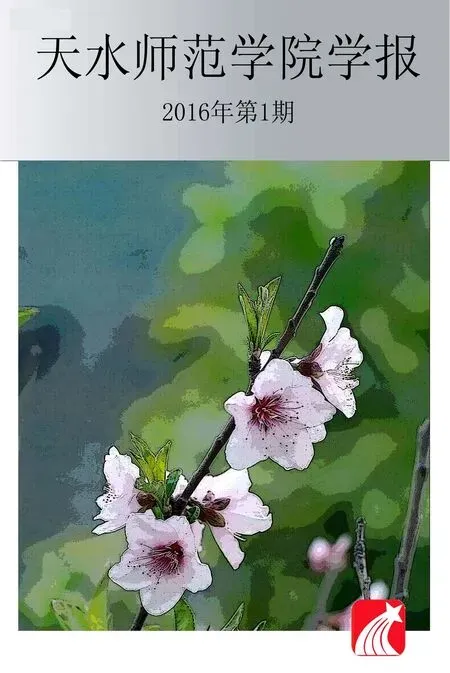综论清中期浙派诗群活动时期的政治生态
王小恒(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综论清中期浙派诗群活动时期的政治生态
王小恒
(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清中期浙派诗群作为一个诗史上独具面貌和认识价值的诗人群体,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清代中期特定的政治生态是重要因素之一。在清代中期,“文治”措施和钳制政策在众多浙派成员人格面貌形成、生活道路轨迹、创作风格走向等方面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面对此种威压交加的政治生态,虽然影响士心、诗心变化的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既然传统士人汲汲于功名社稷的抱负既无由施展,则浙派诗群成员的转而寄身山泉、啸傲江湖之间则为必然。
清中期;浙派诗群;政治生态
浙派诗群到清代中期,从其成员数量、诗坛影响、人格倾向、创作面貌都具有典型意义,进入到其发展的典型阶段,而典型意义、典型阶段的形成,都带有清中期特定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故而探讨清中期政治生态对于浙派诗群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阶段,政治上王朝政权进一步巩固,史家所羡称的“康乾盛世”初步形成,随着“武功”施展的逐步奏效,“文治”措施也愈见其力度。这一时期,文字之祸乃是政治上最为文字狱案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打击的重点区域乃是江、浙、皖地区,因此,江、浙、皖三地士人被祸也最剧。文字狱案表面看是因文字致祸,实则既是文化钳制,又是政治镇压。一轮又一轮的文字狱对此三地士人的严酷打击,足以使人人自危,士心危劫,在文化界更是造成噤若寒蝉、喑哑一片的阴暗生态。
一
浙派诗群的策源地在两浙。两浙地区素来人文繁盛,“浙东学派”又崇尚世用,与一般空谈性命之学迥异,加之两浙曾是古“越”之地,因其固有文化传统的熏炙,士风劲凛,特重义节,其立身态度倾向于在野之趣,后来浙派诗人浓厚的在野情调以及与王朝疏离的价值取向,亦受其影响。然而,当清朝入关、“夷夏大防”即将崩溃之际,浙东作为残明政权坚守的最后地区,浙地士人不论出身世家大族还是低微布衣,不惜破家死身,凛然以对,付出了极大代价。正如全祖望所说:“沧海之际,吾乡号称节义之区。”[1]两浙“如此”之地与“如此”之人,在随后的清朝取得政权、稳定统治和“反清复明”势力生死博弈过程中,成为清朝打击与防范的重点对象,似乎也成为浙地士人难以挣脱的“宿命”。
清廷对两浙士人的防范和压制,体现在诸多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皇帝,对两浙士人极其“厌恶”,一再称“浙省风俗浇漓”、[2]“风俗浇漓,人怀不逞”,[3]这足以让人感觉到其中的威压和杀机。此情此景,两浙士人士心将何以自处,最终的结果将必然导致“朝”、“野”之间更大的离心,表面的顺从包藏更大的危机,应景式的歌功颂德也时时令人啼笑皆非。带着这种“厌恶”之心,雍正还下令暂停浙江乡试、会试科考,此举在当时浙江引起极大的震动。雍正对浙人的这种“厌恶”之心,仿佛瘟疫一样,四处快速传播,浙人的处境一时十分困难。时人以接近浙人为讳,王公大臣也以幕下有浙人而惴惴不安,生怕牵连遭祸。仅以一事为证:浙江人郑亦亭时为庄亲王子教课授艺,“雍正四年冬,亦亭以浙江举人避嫌,力辞王门”。[4]浙人的生存境遇如此难堪,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浙派士人鄙薄仕进、以隐逸为归和与王朝相疏离的那种心态。
和这种以言论压制和打击浙人相比,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摧残士人、企图瓦解他们民族思想的是文字狱案,这也是浙派士人面对的主要政治生态。雍正、乾隆都是发动文字狱的“高手”。有清一代一百多次规模不等的文字狱,大多发生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而且随着清朝政治局面的愈趋稳定,文字狱案的发生亦愈加密集。一面是史家鼓吹的“康乾盛世”如日中天,一面是文字狱案的更加血腥。这些“脍炙人口的虐政”[5]尽管不都发生在两浙,但其威慑力却是普遍的,对士人心灵的戕害也是共同的。浙派活动时期及其后的文字狱案可谓愈演愈烈,这种赤裸裸的血腥屠杀使得诗坛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对其格局的发展走向和最终奠定产生了极大影响。浙派活动时期贯穿了有清康熙后期、雍正全部和乾隆前中期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政权已经稳固,开始腾出手来施展“文治”,加强思想文化钳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积极介入,主动控制。这一时期,表面上看,是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广大士人(包括浙地)最悲哀的时期,此期文字狱案就其密集程度、打击之广、对士人戕害之深,都可谓空前绝后。[6]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清人入关,盗憎主人,箝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7]
浙派领袖厉鹗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迈入诗坛,乾隆十七年(1752)病逝,若各上溯、后推五年,即我们把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这近五十年作为考察时段,对这一历史时段清廷发动的主要文字狱案略加排比如下。①这里主要参考了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见《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上海书店2011年版;郭成康、林铁钧著《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朱眉权《清前期的文字狱》(上、下),《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5期,等等。
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案,此案牵连数百人下狱,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方登峄等免死,其妻、子发配黑龙江。为《南山集》作序者汪灏、方苞遣归旗下。
雍正三年(1725)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斩立决,其妻发配黑龙江为奴,其兄弟亲侄具革职,发配宁古塔。且其五服之内族人任职及候补者,一律革职。借此案雍正将与年党有牵连者汪德荣、汪受祺一并查办。
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为年羹尧赋诗案,钱氏革职,发回原籍,雍正亲书“名教罪人”,令挂钱氏宅;翰林侍读吴孝等奉旨声讨钱氏,诗不称旨,发配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亦因是落职。
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试题案,时查嗣庭已死,遭戮尸;其子查沄应斩,秋后处决;其兄查嗣琛,侄查基、其幼子查克瓒、长椿、大梁,侄学、开长流三千里;江西巡抚汪漋降级,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副主考俞鸿图革职。
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文选》案,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戮尸枭首,另一子吕毅中、再传弟子沈在宽斩立决;吕、严孙辈远发宁古塔为奴;吕留良私淑弟子黄补庵已死免议,其妻妾子女罚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文选》刻工车鼎贲、车鼎丰以及与吕留良之友孙克用、收藏吕氏书籍的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秀才名分,杖责一百。
雍正八年(1730)屈大均诗文案,屈氏戮尸,后人流放。
乾隆十八年(1753)刘震宇献书案,刘震宇斩立决,销毁书版;范时绶不明大义,交部严议。
乾隆十八年(1753)丁文彬逆书案,丁文彬凌迟处死,文彬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斩监候,秋后处决,丁文耀之子丁士良、丁士信年不满十五,罚为奴;曾读过丁氏书、未揭发者王素行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曾看丁书的蔡颖达、徐旭初,各杖八十,徐旭初并革去衣顶;现任江苏巡抚庄有恭于乾隆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曾接受丁文彬献书,未上报查办,照庄有恭学政任内所得俸禄养廉数目十倍加罚。
乾隆十九年(1754)世臣诗稿案,将世臣革职,充发黑龙江。
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诗案,胡中藻凌迟处死;其弟胡中藩等从宽免其缘坐;其座师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尔泰之侄鄂昌解京治罪,后赐自尽。
以上所列案件就个案来讲,虽发生在一时一地,但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像吕留良案、查嗣庭案等发生在浙地、因浙人而起的文字狱案对于浙地士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对于文学发展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
二
清廷如此大动干戈,发动数量如此之多的文字狱案,从客观上看,足以说明中期浙派活动的雍乾时期,反清和民族思想及言论不但没有消弭,而且其传播有越加扩大的趋势。清朝雍、乾时期的越来越密集的文字狱案便是为了消灭此种思想及其传播的明证。
第一,清朝消灭和阻止民族思想、反清思想的最主要方式便是动用国家机器,大举杀戮,实施肉体消灭。其实,自从清初以来,浙地文士便屡遭文字狱案的荼毒和戕害,这种表面上看是文化事件但实质上是政治事件的一次次洗劫,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在清初顺、康之际的庄廷鑨《明史》案,可谓创造了此前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字狱案之“记录”,其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江浙文士,[8]其打击的严厉程度即使是文字狱案最为密集的雍、乾两朝也不多见。到了清中期,也即浙派士人活动时期,当浙地文士尚在《明史》案造成的阴影中颤慄的时候,一系列大小不等但震慑力均不可小觑的文字狱案纷至沓来,从上文可见,其密集程度可用“连年不断”甚至“连月不断”来形容。这些文字狱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足可使文人们防不胜防,如履薄冰,其中渗透的恐怖和血腥气氛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样的打击规模和牵连广度,使得文字狱表面上是文化事件,实质上也包含着社会、伦理等诸方面的认识意义。通过上文所列也可看出,文字狱案常常是无心著书(看书),旋即招祸;一人招祸,“殃及池鱼”,父子、夫妇、师生等常是牵连对象。因而可以说,读书人若一人招致文字狱祸,常常是该人所在家族圈、师生圈、朋友圈共同的毁灭性灾难。所以可以说,为了钳制反清思想、民族思想的存在和传播,文字狱只是载体,有时纯粹是借口。当然,某些文字狱与反清思想、民族思想关系不大,如上文所列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一案,株连甚广,打击面大,即是乾隆整治吏风、打击朋党的一个手段和借口。又如乾隆十九年(1754)世臣诗稿案,世臣为满族人,曾居盛京礼部侍郎之位,只是在诗稿中发了几句诸如“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9]之类的牢骚,便引起乾隆的不满,横遭祸事。
第二,清朝消灭和阻止民族思想、反清思想的又一大手段是长途流放、罚为奴仆。在清代前期,长途流放地一般为东北荒寒之地,以宁古塔为多。东北满洲为清朝“龙兴之地”,流放到这些地方可以实施有效监控管制,而且与流人原来生存之地造成空间上的巨大疏离,又不失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摧残。加之东北酷寒,对关内流人来说,足以使之心灰意懒,心理防线崩溃瓦解。所以清朝统治者的流放政策,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造成流人生不如死的巨大痛苦,是极其残酷的。另外,清廷罚“罪犯”给有军功者为奴也堪称向来此类处理案犯措施的“集大成者”。在清代相关文献中,动辄罚为“披甲人之奴”之类记载甚多。“披甲人”当然是坐享清朝俸禄的立有军功之人,将文字狱的案犯交由此类人管理,是破费思量的。主要考量是“披甲人”是武人和既得利益者,将“犯罪”士人罚为他们的奴仆,使得他们此身虽在,尊严和人格却已化为乌有,可以在精神上击垮瓦解之。
第三,清朝消灭和阻止民族思想、反清思想的第三个手段是销毁书版,从源头上加以肃清。清廷这方面的做法最能体现其发动文字狱的初衷和动机,他们戒惧的不单是这些动辄大言“夷夏”、“大夏”、“前明”、“恢复前明衣冠”的汉族士人,而且对反映此类思想的书籍更是坐卧不安,屡次严令各地方长官广加搜求,动辄大兴文字狱案。甚至对地方长官中搜求不力者,也动以刑罚处理,且有地方长官虽搜求甚力,但对罪犯处罚不合清帝心意者,也以“姑息”的罪名对相关官员进行严厉惩治。如上文所及乾隆十八年(1753)刘震宇献书案,湖南巡抚范时绶追查此案本已不遗余力,但乾隆认为范时绶有姑息该犯之嫌,除将案犯刘震宇斩立决、销毁书版之外,还将范时绶交部严议。在历次文字狱案中,涉及相关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成了禁书,不但毁版,而且严禁其流传,就是涉案著述的刻工也难以幸免,如吕留良《文选》案,因其中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夷夏之防”的思想,横遭狱祸,不但吕氏妻妾、子女、弟子、再传弟子、朋友、阅此书者等一干人全部遭祸外,就连此书的刻工车鼎丰、车鼎贲也被处决,可见在清廷看来,这些书连同见过这本书的所有人,如同洪水猛兽,必欲全部消灭而后安。另外,受文字狱的震慑,凡涉及相关敏感领域的著作,著作者、出版者、购买者也私下焚毁著作、书版者不少。朱彝尊曾记其遭遇说:“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比还,问向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10]可见文字狱所造成的文化损失。在今天看来,屡次文字狱案销毁的书版及书籍只是零星的,大规模的、集中性的禁绝和销毁“涉嫌”反清和民族意识文化典籍的事件当属《四库全书》的编纂,此次编纂虽整合了大量民间所藏文化典籍,然而其主导思想是“寓毁于征”,对于文化的正常发展消极影响仍然非常大。
正是在上述三重手段并举的情况之下,清廷在清中叶“开辟”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恰是这个时代被誉为“盛世”。这个时代的“开辟”虽使士人噤若寒蝉,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改变,并非像改朝换代一样,一时三刻就能奏效。事实是,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仍然没有被消灭,仍然以一定的方式存在着,传播着,只不过它变成了一种“潜流”和“暗流”,到了晚清政治统治行将崩溃之时,这种“潜流”和“暗流”又遇隙迸射而出,汇成巨流,直至清朝灭亡。
三
清代士人之大不幸由文字狱之酷烈即可见一斑,即由以文字狱为核心的清代文学生态影响之下,士心、诗心危劫,士人人生价值取向异化,一部分仍然汲汲于传统功名者人格上奴化倾向严重,即使有个别居于高位者,也鲜见其有什么突出的政治贡献,更大一部分士人则重视对生命、友朋、山水、学问等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人生目标的追索,且这部分士人越来越汇成巨大声势。伴随着士人人生价值取向异化,文士的文学创作取向、治学取向也同步异变,浙派可作如是解,即稍后之“乾嘉朴学”形成风气也可作如是解。文学、文化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而诗歌则是反映这个“风向标”诸样式中最为敏感者,其对于时代文化的发展风向几乎能够得到“即时”的反映。浙派正是以诗歌文体为核心,反映其内心在这个外表看来是“盛世”、内里却也不乏恐怖和血腥的颇为畸形时代的感受和体味。
大规模的文字狱对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它用强力政治手段重构了一代士心,又用超常规方式“规范”了一代诗心。浙派诗歌创作若作皮相诠解,可能只会读到一些游山玩水、搜奇访古的东西(也只有如此才能流传下来),但若参酌其他材料细加探查,其在所谓“盛世”的心灵挣扎和苦涩凄凉是不难体味的。若就具体案例而言,浙派中人也不乏直接罹受案狱之苦者,这里仅举数例进行说明。
厉鹗为浙派领袖,曾与同人共作《南宋杂事诗》701首,旨在以诗存史,故此集保存南宋史料十分丰富。此集成后分别由查慎行、查嗣庭、万经、章藻功撰序。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案发,此集及著者受牵连,厉鹗因此不能继续在浙江坐馆。今所见《南宋杂事诗》查嗣庭序已不存,然此书所散发的“弦外之音”,却也随处可见,如章藻功序末就不无深意地说:“以竹枝之逸韵,为黍离之变风。极南宋所不堪,与西湖兮何涉?独是一泓碧水,有情亦老之天,四壁青山,回首可怜之地。谁能遣此,尚忍言哉?”①厉鹗等《南宋杂事诗》,见日本富冈铁斋藏“嘉善刘子端手录、武林芹香斋摹镌”本卷首第三序。再如年羹尧一案,虽不是典型的文案,但其中包含着文字之祸。除了其中年氏因“夕阳朝乾”受谴案系自身造成,围绕年羹尧还发生过汪景祺《西行随笔》大案、钱名世向年氏献谄诗案等,俱震动一时。在整个年党案中,后来流落扬州、融入浙派诗群的胡期恒(1668~1745)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人物。据相关材料显示,汪景祺得识年羹尧,胡期恒实为中介。胡期恒后任甘肃巡抚,为年党案中“第一人”,晚景颓唐。流寓扬州时期,扬州二马等浙派诗人慷慨地接纳了他。其一生以显官始,以诗人终,生命的冷热转瞬和巨大落差在胡期恒身上体现得相当典型。可以想象,友朋之间在交往时谈及当日往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为此,胡氏好友张世进《著老书堂集》、张四科《宝闲堂集》中有“违碍语”而被列为禁书。②张四科《宝闲堂集》卷四有《客有谈故将军事者赋之》,“客”即指胡期恒,“故将军者”,年羹尧也。《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
浙派中人受文字狱祸最剧者当属王豫、姚世钰。王豫、姚世钰是生命旅程极其困苦多舛而又才华超人的诗人。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文选》大案起,姚世钰的姐夫王豫及好友朱霞山父子兄弟皆受牵连,于次年被押入刑部大狱。这件事对姚氏一生诗风有绝大影响,且其关于文字狱有大胆的言论,如“自昔称诗能穷人,岂更能死人耶?余生平亲故如王立父(按即王豫)、钱景泉、朱霞山,胥以坎壈失职死,其诗亦仅有存者”。[11]“昔称诗能穷人,岂更能死人耶?”一句诘问,充满了无限愤慨,这样正面声讨文字狱荼毒生灵的罪恶,在浙派诗人中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反映了其被祸之深。
王豫(?~1738),字敬所、立甫,号孔堂,吴兴人,有《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行世。姚世钰(1698~1752),③全祖望《姚薏田圹志铭》言薏田“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杨注”云:“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全氏言薏田“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杨注”云:“乾隆十七年壬申。”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为公历1698年,“乾隆十七年壬申。”为公历1752年,不知何据,然此说与全祖望《姚薏田圹志铭》所说“得年五十有五”符。另考之全祖望《王立甫圹志铭》后“严注”,其云“薏田卒于乾隆十四年”,则为公历1749年,所据者为鲍鉁《道腴堂集》载《寿姚玉裁诗》:“屈指今年四十强”,并说此诗作于雍正乙卯,“雍正乙卯”即雍正十三年(1735),以此推算,则姚世钰卒年五十五。然“严注”又说“姚先生卒年五十四”,殊不可解。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第二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第358页。字玉裁,号薏田,归安人,著有《孱守斋遗稿》。王豫为姚世钰姊夫。
在浙派诗人中,王豫是直接受其戕害的浙派诗人。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文选》案爆发,此案是清廷重点打击浙人的著名案狱。案发后,清廷借此严酷打击浙人,株连甚广,一时人人自危。王豫不幸也被株连入狱。关于此事,谢山稍述其线索,其云:“顾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于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于择交,而连染之祸,至逮入京师。”[12]王立甫“好名”者何事?“不慎于择交者”何事?谢山语焉不详。雍正素对浙江士风极有恶感,雍正六年(1728)八月,浙江巡抚李卫奏浙江士风好转,鉴于此奏,雍正特恩准浙江乡试、会试于下年恢复。就在此年九月底,《文选》大案发。王豫在浙江乡试禁令尚未解除的当口,决定参加顺天府乡试,“好名”之说大抵指此。又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13]安徽桐城人孙学颜,著《麻山文集》二卷,集中有《与严寒村书》、《送王敬所序》、《车南东四十序》等文,记载了其与严鸿逵、王豫和车鼎贲交往之事,严氏乃吕留良弟子,车鼎贲乃所谓“逆书”刊刻者,王豫及其好友朱蔚①姚世钰《孱守斋遗稿》有《书朱霞山小传后》,言“霞山噬书喜交游,而爱余尤厚”,朱氏乃与王立甫同受严氏案牵连入狱者。见《孱守斋遗稿》卷四,第555页。(其人亦为严寒村弟子)因遭横祸,被逮至刑部大狱。谢山所指王豫所“不慎交”者或为孙学颜。此事在东南士林影响极大,浙派士人自不例外。王豫文采出众,姚薏田云:“余两弟炳衡、丰万喜为乐府歌词,而余与立父兼治古文,年少气锐,自许要为数百岁杰出人,而立父尤明敏强记、落笔辄倾动诸老先生,诸老先生交加赏异,不啻口出。”[14]王豫之狱至雍正十年(1733)始解,严寒村在此案中被戮尸枭首,车鼎贲秋后问斩,王豫等十一人“革去教谕、举人、生员,杖一百”,朱霞山等“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俱著释放”,立甫系狱五年始获释,昔日圭角峥嵘的才人已奄奄不振也。谢山云:“立甫故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当大难,况家贫甚,锒铛就道,一无所资,长系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迨事解得出,而芒角已催困殆尽,不可复振矣。”②全祖望《王立甫圹志铭》,谢山言立甫系狱五年,似有差错。此处“杨注”云:“立甫以严寒村之狱牵染。其逮入京也,在雍正七年己酉,至十年壬子始论释。幽囚西曹者四载,此与薏田圹志,皆云五年,误也。”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第二十,第357页。杨氏之言是也,姚世钰有《次韵张喆士春夜听余闲话旧事之作》夹注云:“时及己庚间亲故逮系事。”雍正在位之年,始于癸卯,终于乙卯,无“己庚”之年,疑为“己酉”之误。见姚世钰《孱守斋遗集》卷二,第528页。又姚世钰《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序》云:“(立甫)己酉以同郡严氏牵连,逮诏狱。”见王豫《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193册,第3页。此言与杨凤苞夹注合,可见王豫逮于刑部狱时间当为雍正七年己酉(1729),系狱四年,可为定谳。立甫系狱未释,而其妻已死,人祸之惨,于此可见。关于薏田姊去世事,薏田有追悼亡女之诗,牵连及之,其云:
我怜有姊停丧久,念汝诸姑每涕零。
后死可辞为弟拙,一杯终瘗谢山铭。[15]
此诗后注云:“壬子六月遭王氏姊之丧,时立甫方系刑部狱。既归不数年,相继夭殁,草殡山间。女每与母语及,辄欷歔曰:‘安得吾父稍有余力,使诸丧备举,姑亦免于暴露乎?’其于亲爱伦理间,存心类如此。友人全吉士绍衣先为立甫圹志,谢山其别字。”“壬子”即雍正十年(1732),薏田姊亡去即在此年,而后薏田此女亦因难产早亡。关于谢山所作立甫圹志铭之事,谢山有云:“敬所死,余铭其墓,不讳其生平疵纇,薏田垂泪读之,已而相向噭然以哭,至失声。”[16]至言立甫“生平疵纇”,当指其“好名”、“不慎择于交”等事,由此也可见谢山作墓志,传主虽是生平挚友,也不“谀墓”的直书无隐的良史精神。
综上可见,文字狱案的主要危害是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高压,这种文化氛围使得人人自危,士心危迫。在这种高压下,从社会角度看,导致士人人格取向异化;从文学、文化角度看,导致诗风、文风的胚变和学术的转向,引起了从士人到士心、诗心、文心等一系列重构。当然,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其催生原因不可能是一元的,其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时期的浙派出现受文字案狱重大影响,此后登上诗坛的性灵派、格调派、肌理派似乎都可找到这时期特定政治氛围带给他们的影响,而学术上“乾嘉学派”的崛起受此种文化氛围影响,则已是学界共识。
[1]全祖望.贞愍李先生传[M]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第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02.
[2]萧奭.永宪录:卷四[C].朱南铣,点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310.
[3]雍正.大义觉迷录:卷四[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金埴.不下带编:卷五[M]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89.
[5]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M] 鲁迅全集:第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08.
[6]张兵,等.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5.
[7]钱穆.引论[M] 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27.
[8]张兵,等.庄廷鑨《明史案》与清初江浙文学生态[J].文学遗产,2012,(6).
[9]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131.
[10]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曝书亭著录序[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1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5.
[11]姚世钰.孱守斋遗集:卷三·石贞石遗诗序[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36.
[12]全祖望.王立甫圹志铭[M]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第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57.
[13]柯遇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麻山集》五卷”条[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466.
[14]姚世钰.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序[M] 丛书集成续编:第19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3.
[15]姚世钰.孱守斋遗集:卷二哭董氏女子二十二首之二十一[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21.
[16]全祖望.姚薏田圹志铭[M]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第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59.
〔责任编辑王小风〕
On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oet Group in Zhejiang in the M idd le of Qing Dynasty
Wang Xiao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s,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As a unique poet group in poem history,the poet group in Zhejiang during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lived in a special political period with particular ecology.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for the forming of this group.The governing and suppressing policies left indelible influence among these people in their character,life and writing style.Under this kind of severe political ecology,they turned to the natur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held the desire to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ambitio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poet group in Zhejiang;political ecology
I207.22
A
1671-1351(2016)01-0010-06
2015-12-19
王小恒(1973-),男,甘肃庆阳人,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中期浙派诗人集群研究”(13XZW007)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厉鹗与清中期江浙诗人集群研究”(12YJC75108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