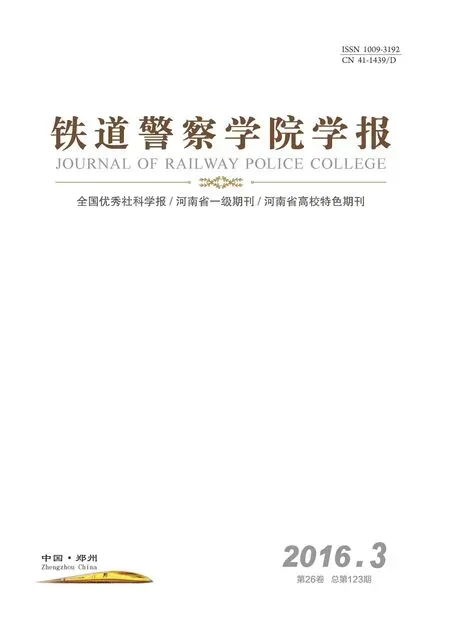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潘金贵,蔡岱燐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潘金贵,蔡岱燐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难”;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法典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化程序性制裁的重大举措,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实践层面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却不容乐观。近年来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成功案例,如2015年广东省陈某某故意杀人案非法证据被排除,但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仍然是公检法机关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拟在介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司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三难”现象的产生原因,并就如何破解“三难”困境提出浅见,以资探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大难题
(一)非法证据界定难
实务中,对于如何界定非法证据,司法人员普遍认为比较棘手。非法证据界定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引起的“剧烈疼痛或痛苦”的标准界定问题。虽然两高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剧烈疼痛或痛苦”这一主观性极强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不好把握。如何判断侦查行为是否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了肉体或精神上的“疼痛或痛苦”?何种程度的疼痛可以认定为“剧烈”?该规定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法官们对此问题的界定标准不一。
第二,疲劳审讯的界定问题。2013年《建立健全防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将疲劳审讯纳入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但是,对于如何界定疲劳审讯,实务中法官们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夜间审讯构成疲劳审讯,有人以是否更换侦查人员作为疲劳审讯的判断标准,有人以被告人是否疲劳作为疲劳审讯的判断标准,有人以24小时为疲劳审讯的判断标准”[1]等。
第三,“威胁、引诱、欺骗”所获得的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在取证行为上,《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但在排除非法证据上,刑事诉讼法却仅仅规定了应当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未将威胁、引诱、欺骗明确纳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范畴。这看似是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疏漏,实则是立法背后大有深意。立法旨在给司法机关以合法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之间界定的自由裁量权,但问题是,如何认定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合法侦查策略,还是非法取证。由于立法模糊,司法实务中对于如何界定威胁、引诱、欺骗以及是否排除由此所取得的证据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第四,重复供述是否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重复供述,是指被追诉人的首次有罪供述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其后又基于合法的讯问程序作出了一份或者多份内容基本相同的供述,后者便属于重复供述”[2]。首次有罪供述因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无疑是非法证据。关键问题是,后续所获取的重复供述究竟是不是非法证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此问题作出回应。学界对此问题虽然作出了积极回应,但也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重复供述是否为非法证据界定难,实务界为保险起见,对于重复供述干脆不予以排除。“据调研,西南地区某中院及辖区基层法院2013年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有9起,适用率为0.227%,其中,8起排除的是被告人供述,1起为物证。在8起排除被告人供述的案件中,排除范围仅限于涉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的初次供述,对后续的重复自白均未排除,最终,这8起案件均作了有罪判决”[3]。
(二)非法证据证明难
1.履行证明责任难
(1)辩方履行证明责任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方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须提供相关材料或线索,因此辩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但辩方往往举证困难,因为侦查人员采取肉刑取证方式多发生在侦查阶段,即使留下伤痕等证据,这些伤痕到了审判阶段也大多已痊愈,辩方无法举证;倘若侦查人员使用变相肉刑或者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进行取证,这些方式往往很难留下非法取证的证据,辩方同样无法举证。
(2)控方履行证明责任难
控方承担着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控方通常可通过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讯问时在场的其他人员的证词和情况说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来证明证据的合法性。但是,实践中控方举示的证据通常只有情况说明和看守所体检表。理由在于:案卷笔录全部在庭前已移送至法院,不需要举示;有些案件并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举示;侦查具有封闭性,一般没有其他人员在讯问现场,故没有“讯问时在场的其他人员的证词”可以举示;侦查人员一般以已有“情况说明”为由几乎不出庭说明情况。因此,控方举证方式有限,控方的举证难以达到证据充分的要求。
2.达到证明标准难
(1)辩方达到证明标准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条件是审判人员“有疑问”或者“认为有可能”。从证明标准角度而言,辩方所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优势证据标准”。
该证明标准看似所需完成的证明程度较低,但实际上辩方仍然难以达到该证明标准。理由有二:第一,审判人员“有疑问”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辩方举出的证据或线索具有可信性,二是辩方宣称遭受到的“刑讯逼供”达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的法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如前分析,对于非法证据辩方往往举证不能,口说无凭,举证不具有“可信性”。即使个别情况下,辩方能举出一定的证据,它们也可能不在排除规则所规制的法定范围或程度之内。第二,审判人员是否有疑问实质上属于自由心证范畴,因人而异。有时法官会因辩方举出的相关线索而产生些许怀疑,但有时法官也可能因控方对此问题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或证明”而打消心头疑问。比如K市中院遇到的一起冬季对嫌疑人泼凉水,然后用风扇吹干的变相刑讯案,即为此情形[4]。
(2)控方达到证明标准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控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实际上控方仍难以达到该证明标准,主要是因为控方证据证明力不足。
“无论是向法庭提供完全由侦讯人员制作、可能已经文过饰非之后的讯问笔录,还是提交难以摆脱先供后录、选择性录制之嫌的录音录像,亦(抑)或是缘木求鱼地提请利益攸关方出庭作证,似乎都很难满足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5]。而且,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中侦查人员都没有出庭说明情况”[6]。此外,控方通常举示的“情况说明”是自证清白,说服力不强,证明力也不强。实务中,控方往往是通过罗列出以上证据即完成其证明责任,实际上是降低了控方的证明标准。
(三)非法证据排除难
根据学者们的调研,非法证据排除难的问题在检法系统一直存在。在法院系统内,“2013年1—8月份,西部某省法院系统五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总共为14起,仅占全部案件的0.08%”[7]。“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至2014年8月,受访的东北部四个基层法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率为零”[8]。
不仅法院存在排除难的问题,检察机关也同样存在排除难的问题。“两个《证据规定》颁布至2013 年11月,J省S市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共19起,仅排除7起;T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17起案件中共排除4起;W市涉嫌非法证据案件共29起,仅排除了3起”[9]。“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真正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并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虽然存在,但数量不多;如J省N市G区检察院,2013 年1月—2015年8月共有4起案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排除了非法证据”[10]。
司法实务中,往往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明显的外伤或者同步录音录像明显不规范,法检部门才会排除非法证据。否则,法检部门会尽量采取其他变通方式处理,比如采取辩诉交易、说服检察机关撤诉、允许侦查人员反复补正而使非法证据合法化,采纳重复供述,进行虚假印证或片面印证,或者利用定罪量刑标准的弹性将其解释为不是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三难”的原因分析
(一)非法证据界定难的原因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剧烈疼痛或痛苦,威胁、引诱、欺骗、疲劳审讯”等词语看似明确,但在具体案件中,这些词语的含义却又不好把握。这是由规则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立法若要保持持续生命力和普遍适用性,法律规则的用语就必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模糊性就势必导致非法证据界定难。因此,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他们纵有严格司法的决心,也会由于无严格司法的依据而无法开展工作。实务中司法工作人员难以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形成统一认识,由此形成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宽严不一。非法证据界定难,在引起规则适用混乱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难。
(二)非法证据证明难的原因分析
非法证据证明难主要是由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对控方而言,侦查具有封闭性,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并不在场,驻所检察官对侦查的法律监督,其方式也以受理申诉的事后监督方式为主,一般案件也不介入侦查,因此侦查人员讯问时并无第三方在场。再加上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控方可以举示的证据极其有限。此外,如前分析,控方举示的每一种证据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证明力瑕疵。因此控方不仅履行证明责任难,达到证明标准也难。
对辩方而言,侦查环节以侦查人员为主导,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处于弱势地位,面对非法取证行为,辩方无法收集和固定证据。讯问时辩方律师不在场,不能作为讯问时在场的第三方就违法取证行为提供证词。对于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辩方往往举证不能,且无法达到证明标准。实务中,真正困扰辩方和法官的并非有无非法证据,而是如何证明犯罪嫌疑人遭受了非法取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到了非法取证,多数情况下控辩审三方心知肚明,却因举证不能,而导致无法认定。非法证据证明难,也直接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难。
(三)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原因分析
1.司法理念陈旧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
“法治秩序的建构不是制定了法律制度便高枕无忧,更重要的是形成与法律制度相一致的法意识形态”[11]。我国虽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与之相配套的程序正当性理念却未完全形成。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为了防止出现冤案的不利后果,而不是为了维护正当程序。对于司法人员而言,偏重发现客观真实的司法价值取向使其不愿受形式规则的束缚,尤其是当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导致客观真实难以发现时,大多数司法人员尚未调整好心态坦然接受形式规则。程序正当性观念的缺失和浓厚的口供情结,使得司法人员对于非法证据异常宽容。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希望司法人员秉公执法,但更不希望放纵罪犯。“以非法的手段实现法治、以犯罪的手段打击犯罪还大有市场,民众对有罪者被绳之以法的诉求盖过对正当程序的诉求”[12]。综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功利性导致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不彻底性。
2.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
(1)惩罚犯罪需求下印证证明模式导致排除基点混淆
为了追求实体真实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我国采取印证证明模式进行刑事证明,但是印证证明模式加大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难度。当非法证据的排除冲击到有罪的证据体系时,司法人员通常“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否定排除证据的正当性,以证明力的评价代替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只要该证据是真实的,即使非法也不予排除,而是将证明力减等予以使用,并转化为量刑问题”[13]。这实质上是混淆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基点,将证明能力替换成证明力。
印证证明模式之所以会导致排除基点的混淆,主要是因为该模式是在惩罚犯罪的背景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当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人们对稳定有着强烈的诉求。在惩罚犯罪的合理需求下,非法证据排除难以得到彻底的落实。“可以说,当前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求不足及该需求提升空间上的有限”[14]。
(2)法院不独立导致法院“不敢排”、检察机关“不愿排”
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果有限,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针对这一问题的改革措施无法发挥实效[15]。由于检察院对法院拥有制约性的权力,“一是拥有抗诉权,二是拥有反贪、反渎等侦查权,三是可以通过日常的诉讼行为配合或干扰法官,因此能对法官形成牵制”[16]。法官并无足够的司法权威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J省W市曾发生一个极端案例,某基层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由此导致起诉的罪名由重改轻)并将该案宣传报道后,惹恼了同级检察机关,最后,法院领导亲自登门道歉才将事件平息[17]。法院不独立使得法官担心排除非法证据会影响到检察机关的考核而引起反弹,故“不敢排”。
法院不敢排除非法证据,反过来使得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更加不愿排除非法证据。而且,排除非法证据倘若冲击到起诉的证据体系,“在检察机关内部,对于不起诉、减少起诉内容等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要在事前经过层层审批,在事后还要受到反复检查,如果在事后的检查中发现有该诉不诉的现象,还会对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是否有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行为进行审查”[18]。因此,在保底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检察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而“带病起诉”。这样,立法设计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层次性——“审前排”和“庭中排”就演变成“互不排除”的恶性循环。
(3)司法系统承担社会治理功能导致法检“不能排”
在我国,司法独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相反,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宪政概念”[19]。法院独立是“从属于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的第二层次的法治理念”[20]。司法系统除了承担司法功能外,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社会治理功能。“司法机关不能就案办案,刑事审判必须为中心工作服务”[21]。在非法证据排除后,法院若作出无罪判决,易引起民众的质疑和被害人的上访。此时,“维稳”便是中心工作。在被害人上访和政法委的压力下,法院必须服从于“维稳”这一工作中心,因此不能毅然决然地排除非法证据。可见,政策导向型司法在兼顾社会效果的同时,也以牺牲一定的法律效果为代价。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难”的破解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难的破解
法律规则的模糊性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在法律的框架内加强非法证据界定标准的操作性。具体如下:
第一,“刑讯等非法方法”引起的“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界定标准可以具体为:(1)侦查人员的行为强度是否明显超出正常人的忍受能力。(2)个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是否足以承受审讯人员的相关行为。(3)个案中犯罪嫌疑人遭受的疼痛或痛苦是否足以影响其供述的自愿性。
第二,“疲劳审讯”界定标准可以具体为:两次传唤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12小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将传唤、拘传的持续最长时间等同于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讯问的最长时间,如12小时或者24小时。由于立法采用的措辞是“持续最长”,所以在这12小时或者24小时内,给予犯罪嫌疑人多长的饮食和休息时间都不属于疲劳审讯。是否属于疲劳审讯,关键在于正确认定两次传唤或者拘传的“间隔时间”是否合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两次传唤、拘传的间隔时间。但是《规则(试行)》第195条规定“两次传唤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12小时。在刑事诉讼法暂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将此标准作为疲劳审讯的界定标准。应当注意的是,在讯问间隔时间内,除了必要的饮食外,剩下的时间均应是犯罪嫌疑人的“连续休息时间”。实务中“侦查人员每天只让犯罪嫌疑人休息2个小时并且每隔10分钟叫醒一次,且持续14天”[22]的情形应予以禁止。
第三,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在保障供述自愿性,从而保障供述真实性,所以界定“威胁、引诱、欺骗”所获得的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的根本标准是该侦查行为是否足以影响供述的自愿性。具体标准可细化为:(1)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基础。(2)是否严重违反了司法道德。(3)是否影响口供的真实性。(4)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公信力。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当加强案例指导,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1集中的“文某非法持有毒品案”就对重复供述排除与否作出了明确的指导,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该指导案例指出“判断后一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应当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否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为标准”[23]。“被告人是否消除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所造成的恐惧心理。司法实践中,可借助以下程序性的行为进行分析认定,(1)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权利的告知。(2)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启动的告知。(3)排除非法证据结果的告知”[24]。应当指出的是,非法证据被排除后,侦查人员重新取证时应注意采取以上程序性行为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由于前一阶段非法取证行为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免重新获取的供述因不法影响的持续效力而被排除。
(二)非法证据证明难的破解
对于非法证据证明难,解决出路重在打破侦查的封闭性,突破证明局限性,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
1.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在我国,实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并不具有可行性。且不说我国刑案律师参与辩护率不高,在有聘请辩护律师的案件中,讯问次数多和持续时间长,每次讯问均让律师全程陪同显然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却有极大的完善空间。
首先,应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时间提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讯问时”开始录音录像,但实践中多是“打后再录”。为此,可参照J省S市的做法,“在刑拘之前进入派出所办案区以后全程录像”、“进入看守所讯问室后全程录像”[25]。以保证同步录音录像的全程性。
其次,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案件范围扩大到“全部案件”。现行规范和实践均对此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规范层面上,2014年《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的通知》提出了要力争在2017年实现全国全部刑事案件全程录音录像的目标。实践层面上,“J省S市2013年已经实现对全部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26]。
应当指出的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应允许辩方律师查阅。虽然现行主流观点认为“同步录音录像不是证据,而是工作性资料,笔录才是举证质证的法定证据”[27],但是,“同步录音录像符合证据三性,理应是证据”[28]。既然是证据,就应当允许律师查阅。当然,“录音录像的复制权必须经过检察长的批准”[29]。
2.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必要时可“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此处侦查人员并不是证人,这是因为他是以“侦查人员”而不是“证人”的身份出庭,并且其出庭不是作证,而是“说明情况”。但从证据法原理上看,证人参与诉讼主要是为了协助司法机关更好地认定案件事实,而侦查人员出庭则是为了帮助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中的程序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侦查人员又是“特殊证人”。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后,能否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对此立法语焉不详。但是,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既可有效揭穿被告人恶意翻供的谎言,也可挖掘出违法取证的事实真相,既可丰富控方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手段、提高控方证据证明力,也可有效破解辩方证明难的困境。因此,侦查人员出庭的意义更在于接受质证,从而发现取证过程是否存在问题。此外,因为侦查人员不是证人,所以当他不出庭时,不可强制其出庭,但可推定其取证行为违法,排除该非法证据。
(三)非法证据排除难的破解
1.培育正当程序理念和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制度变革,观念先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证明力非比寻常的关注,折射出程序正当性理念和证据裁判理念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要打破惩罚犯罪需求下印证证明模式导致排除基点混淆的问题,除了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压缩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外,对于司法人员而言,关键在于要时常进行个体对刑事司法理念的自我教育,培育程序正当性观念。非法证据的排除基点在于缺乏证据能力,而非缺乏证明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突出体现了正当程序与客观真实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但是如果不彻底去除违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就无法遏制违法取证行为的泛滥和避免对人权的侵害,就难以实现正当程序与客观真实二者间的和谐。
此外,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的风险是可能放纵一个罪犯,但司法是对事实的“重构”,是否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无从衡量,可带来的收益却是避免酿成一个冤案。在风险与获益的权衡之间,不难看出,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是明确的选择。
司法人员应对证据规则存有敬畏之心,“裁判者作出裁判不仅要依据证据,还要求裁判者所依据的证据具有证据资格,且经过严格证明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30]。社会公众应当明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仅仅是给予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而且还是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保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罪犯,都需要该规则来保障自己的人身权益。因此,社会公众对法官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行为应予以理解和认可。即使真的放纵了罪犯,这也是我们为实现程序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2.破解非法证据排除难的体制保障
“排除非法证据本质上是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审查和制约,是司法权力对政府权力的程序性制衡”[31]。因此,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加强对审判权的保障,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样方能实现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和对公安机关取证行为规范化的倒逼效应。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可从五大方面着手:一是上级法院要尊重下级法院的裁判,充分发挥审级制度的功效。二是法院内部要完善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责任制,逐步消除司法行政化,把审判权回归、集中到法官手中。三是健全审判人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让法官独立裁判而无后顾之忧。四是推行两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法检独立司法的不当干涉。五是理顺党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党群机关要营造环境、创造机会,以保证审判机关职能的独立行使。政法委只作原则性、方向性把握,不再介入个案办理。司法机关依法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
此外,从体制上要适度提高法院在政治生态中过于弱势的地位,建议可以考虑:第一,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同级党委常委,以提高审判机关的政治地位。第二,在推行两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过程中,把地市级、县区级两级法检机关的“一把手”交由省委组织部门进行管理。第三,可以探索把对法检两院的普通干警的管理也上提一级,由上级公安机关进行组织人事管理。应当指出的是,欲让法官成为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证据防线的守护神,除了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外,还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完善公检法三机关的内部考核机制,二是重塑侦诉审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
综上,可以预见,破解非法证据排除难的体制困境之路将曲折漫长。从整体上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指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实现法院的独立和审判及其在证据层面制衡起诉、侦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背景。我们应抓住时机,大力推进司法体制的有序改革,让法院敢于对程序是否具有合法性和事实证据质量作出终局性的有力裁判。
[1][6][8]潘金贵.基层法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调研报告[R]//潘金贵.证据法学论丛(第3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255,260,251.
[2]杨波.由证明力到证据能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坛,2015(5):109-122.
[3]陈峰.排除重复自白的实务困境与应对思路[J].人民司法,2015(1):80-83.
[4]潘金贵.刑事证据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R]//潘金贵.证据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187.
[5][14]闫召华.“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181-192.
[7]王彪.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威慑效果实证分析[J].河北法学,2015(1):107-118.
[9]杨宇冠,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J].证据科学,2014(1):5-19.
[10][17][25][26]孙长永,闫召华.新刑诉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R].2015:26,32-33,16-17.
[11]蒋立山.中国法治论丛[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60.
[12]李昌林.刑事证据排除的范围、阶段和机制[M]//孙长永.刑事司法论丛(第1卷).北京:检察出版社,2013:118.
[13]李训虎.证明力规则检讨[J].法学研究,2010(1):161.
[15]李昌盛.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为中心[J].现代法学,2012(3):112-119.
[16]兰荣杰.把法官当“人”看——兼论程序失灵现象及其补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5):8.
[18]孙长永,王彪.刑事诉讼中的“审辩交易”现象研究[J].现代法学,2013(1):125-138.
[19]卞建林.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证实录——诉讼法卷[M]. 2009:2.
[20]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7 (1):76-88
[21]滕彪.话语与实践,当代中国司法“工作中心”的变迁[M]//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6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6.
[22]潘金贵.夯实防范冤假错案的证据防线——关于防范冤假错案系列规定的证据视角[M]//潘金贵.证据法学论丛(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8.
[23][2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总101集)[Z].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8.
[27]孙谦.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的若干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3):3-13.
[28][29]李昌盛,周玉萍.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分析[C]//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140-141,142.
[30]李静.证据裁判原则初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6.
[31]王彪.非法证据对法官心证的影响与消除[J].证据科学,2015(4):400-413.
责任编辑:赵新彬
Three Dilemm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 and the Solutions
Pan Jingui&Cai Dailin
(Law School,Southwestern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efinition,proof and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s have been three dilemmas faced by the police,procuratorate and court in the application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The internal defects of rules cause the dilemma of definition,to which the solution is to improve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strengthen case guidance.The closeness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proving ways cause the dilemma of proof,to which the solution is to improve the entirely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cross-examination of investigators appearing in court.Old judicial concepts,the confused exclusion of basic points under the mode of proof,the non-independent courts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ourts cause the dilemma of exclusion.The solu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dure and evidence judging and strengthen the guarantee of judicial mechanism.The dilemma of definition and proof also 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dilemma of the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s,concept innova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foundation,while mechanism optimization as the premise and system perfection as the cor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three dilemmas
D925
A
1009-3192(2016)03-0103-07
2016-03-15
潘金贵,男,贵州毕节人,法学博士、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证据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证据法学;蔡岱燐,女,广东汕头人,西南政法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