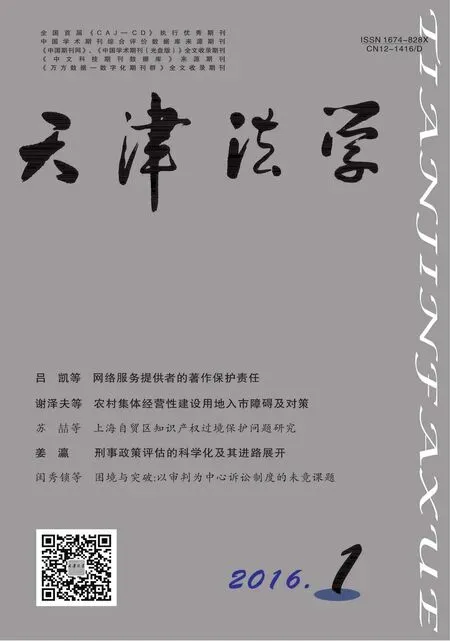论外国法查明中的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问题
丁小巍,王吉文
(1.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广东广州510230;2.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00013)
论外国法查明中的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问题
丁小巍1,王吉文2
(1.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广东广州510230;2.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00013)
摘要:外国法的查明是国际私法领域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了法院和当事人分担查明责任,但由于认定标准的缺失,司法实践中仍然频繁出现法院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时不当认定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从而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消极情形。这种现象或许是法院无法准确判断当事人所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性质所致,或许也存在滥用这个拒绝理由的嫌疑。为此,未来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民事证据标准。
关键词:外国法查明;未提供外国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
王吉文,男,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研究。
一、引言
在国际私法领域,外国法的查明是一个涉外(国际)案件始终无法绕过的环节,英国冲突法学者芬提曼教授(Fentiman)就曾经如此严肃地指出:“在冲突法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比外国法的查明问题更重要。站在更高层面上看,外国法的查明程序特别关系到冲突法本身的生死存亡”[1]。与此同时,受制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语言和法律概念、查明方法和能力的不足等诸多因素,外国法的查明一直又是涉外民事案件中一个异常困难的复杂问题。在晚近一个案件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伍德法官(Judge Wood)就如是评价了外国法查明的现实困难:“比较法的实践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人们很可能错过外国法中某些细微的差别,或者不能有效地形成这种观念,即外国法中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或者当外国法无从知晓时错误地认为外国法与美国法一样”①。各国司法实践也表明,无论是法律素养较高、司法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官,还是缺乏充分法律素养的涉案当事人,均把外国法的查明视为畏途。事实上,即使是法官,人们都会发现不应指望法官能够像知晓本国法那样熟悉外国法,并对该外国法的涵义和立法目的有着准确的理解,进而在外国法的查明上能得心应手、灵活自如;而且,即使是公正的法官也无法真正摆脱适用内国法的现实诱惑,从而可能在外国法的查明上虚以委蛇。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在案件审理中掌握着实际权力的裁判者,法官是经常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理由来拒绝实际承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并最终达到适用他们所熟悉的内国法的目的。而这种状况在强调“法官知法”观念的大陆法国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事实上,在我国以往外国法查明的实践中,就经常呈现出法院滥用外国法“无法查明”理由的情形。正如我国学者对司法实践长期研究和跟踪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在我国法院有关外国法查明的实践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两种消极的状况:其一,法院未做任何说明就直接适用了我国法律;其二,法院未做实际的查明努力就径直宣告外国法“无法查明”②。其他学者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至少有四种外国法“无法查明”的形式被我国法院经常性的滥用③。
当然,如果外国法的查明责任由当事人承担,法院则可以乐享其成,坐等当事人举证证明外国法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减少我国法院滥用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现象。毫无疑问,对于我国法院而言,如果可以合法地要求当事人承担外国法的查明责任,则将理直气壮地卸下一直背负着的外国法“无法查明”滥用的沉重包袱。所以,现行外国法查明制度④在外国法查明责任上根据法律适用的性质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所做的分配,显然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外国法查明负担。尽管如此,我国司法实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当事人负责提供外国法、承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时,法院应如何断定当事人提供了合适的外国法、并以当事人所提供的这个外国法内容为依据做出相应的裁决?法院是否会任意地把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作为其拒绝适用外国法的事由?虽然后者似乎有些反应过度,多少有些对先前法院滥用外国法“无法查明”的实践杯弓蛇影的意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实施后的相关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担心应该并不是多余的。某种程度上,现行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似乎正逐渐成为法院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新借口;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经常是作为外国法“无法查明”拒绝理由的基本依据,二者相互结合,从而共同为法院拒绝外国法的适用、以及为内国法的适用提供“正当性”理由。毋庸置疑,这种结果既有损于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有效性,也终将不利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公正解决,从而损害我国国际私法对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价值目标的追求。正是如此,加强对我国法院新实践的关注,了解其中的内在缘由,应当是提出改进方案的第一步。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基本类型
长期以来,当事人实际承担外国法查明责任的情形较为罕见,这当然与外国法的查明困境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与“法官知法”观念息息相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都绝对强调法院的查明责任。那么,这种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将对当事人查明外国法产生消极的影响。正是如此,在《法律适用法》实施后,我国法院应当对当事人查明外国法的努力加以鼓励和支持,否则极为可能挫败当事人查找外国法的积极性和信心,导致现行立法形成“徒具空文”的尴尬,进而也难以触及冲突法的正义价值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现行司法实践尚未呈现出这种积极态势;相反,在当事人负责提供外国法的内容从而承担外国法的查明责任时,我国法院却经常性地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为由,拒绝外国法的适用,并最终都代之于我国法。事实上,从既有司法实践⑤来看,在法院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的11个案件中,全部都提出了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显然,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已然成为了法院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核心依据。当然,如果就此不加分析地得出我国法院存在着“未提供外国法”理由的滥用情形,则可能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需要对现有案例中法院所提出的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理由加以详细分析。整体而言,我国法院所认定的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情形涉及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一)当事人可能⑥确实未能提供外国法而被我国法院认定为“未提供”
从整体案件情况看,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确实未能提供外国法,显然是导致法院认定“未提供外国法”的基本情形。从相关案例的具体内容来看,这种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情形大致包括三种状况:其一,当事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不提供外国法。在“上诉人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烟台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⑦中,提单约定适用美国法。对此,一审法院声称:被告虽主张适用美国法律,但未能提交美国法律;且未说明应适用美国的哪一部具体的法律。二审法院也认为,原审被告虽然主张适用美国法,但是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提供美国法的规定,因而认定美国法的规定不能查明。在“上诉人广东库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⑧中,一审法院声称,由于当事人选择适用香港地区的法律,应当提供该地区的法律;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香港地区的法律,因而应适用内地法。在许翎、张震与阿里巴巴公司与公司有关的两个案件⑨中,审理案件的同一个法院均声称,由于当事人约定适用开曼法律,因而被告要求适用开曼法律的主张应予准许;但由于被告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该外国法,应认定为不能查明。其二,当事人一方不出庭因而未提供外国法。在“原告龙钟永、永亚企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邦沪航运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⑩中,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合同约定适用新加坡法律,但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而原告请求适用中国法,所以应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实体争议。其三,当事人未选择法律,但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结果当事人未提供。在“原告永华油船公司诉被告江西星海航运有限公司等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⑪(以下简称“永华公司案”)中,一审法院声称,双方未事先约定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应以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地的香港法为准据法;但“因原告作为主张适用香港法律的一方未予提供,本院亦无法查明”,所以应适用内地法。在该案的上诉案⑫中,二审法院的理由和结论均与一审法院完全相同。在“上诉人邓剑华被上诉人陈滨松、原审被告林炳辉合同纠纷”案⑬(以下简称“邓剑华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当事人“均为香港居民,且诉争交易发生在香港,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虽然原审被告邓剑华主张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但其拒不提供香港法律,也未进一步提供可供法院查明的香港法律的线索,故能适用于本案的香港法律无法查明。”二审法院则更是提出:“本案应适用与该讼争民事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香港法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起诉要求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虽然上诉人对此提出了抗辩,主张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但诉讼中因其拒不提供香港法律,也未进一步提供可供法院查明的香港法律的线索,故可以适用于本案的香港法律无法查明。二审中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要求对方以及法院查询适用法律的相关法律依据。”
(二)当事人提供了未办理公证认证的法律意见书而被法院认定为“未提供”
与当事人对于提供外国法完全置之不理的情况不同,有时当事人提供了外国专家(包括律师)出具的有关外国法内容的法律意见书,但未办理公证和认证手续。那么,对于这种法律意见书的效力问题应如何确定?有的法院也以当事人“未提供”为由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在“原告国际金融公司诉被告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冯光成借款纠纷”案⑭(以下简称“国际金融公司案”)中,贷款协议约定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供了“安理国际事务所”(应该是一个国际律师事务所——笔者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证明原告选择的管辖法院、法律适用以及提出的相关主张符合美国纽约州的法律规定。对此,被告在其抗辩意见中则提出:这个法律意见书系境外形成,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因而不予认定。法院声称:“当事人约定适用美国纽约州的法律,应由当事人提供相关法律,现原告和被告均未向本院提供约定的外国法,本案应适用中国法。”
(三)当事人提供了经过公证认证的法律意见书而被法院认定为“未提供”
如果当事人提供了经过公证认证的法律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院是否会给予更大的效力支持?实际情形似乎也不容乐观。在“上诉人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鑫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城中支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⑮(以下简称“江河创建公司案”)中,一审法院似乎承认了当事人(原审原告)提供的法律意见书的效力:本案涉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应适用登记地的沙特王国法律。原告提供的登记文件译本显示,分支机构在沙特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但是,一审法院的结论却遭到了提供该法律意见书的原审原告(上诉人)的反对。并在其上诉意见中指出:“根据原告提供的经沙特王国公证和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沙特执业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并不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此外,本案双方并未约定适用沙特王国法律,原审法院在未依法查明沙特分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应适用沙特王国哪一部法律的情况下,对法律意见书置之不理。”对于上述情况,二审法院则在其判决书中声称:“沙特分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应适用沙特王国法律,但沙特分公司的登记文件译本中并未载明分公司在沙特王国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原审法院也未查明该国法律存在这一规定,却得出分公司在该国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进而认定该案须由沙特分公司起诉,于法无据。依据《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在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中国法律。”然后二审法院就直接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4条有关分公司法律地位的规定认定沙特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原告承担,而没有做任何其他相关的说明。从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法院应该是认定当事人未能提供外国法,因而“不能查明外国法”。
(四)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意见书和法律而被法院认定为“未提供”
在“上诉人卢胜苏与被上诉人万宁石梅湾大酒店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⑯(以下简称“卢胜苏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两被告约定夫妻财产关系适用英国法律,但因被告并未向法院提供英国法律,导致法院无法查明。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上诉人(原审被告之一)并不认可,在上诉意见中提出:“在本案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英国律师的答复函并附带了法律意见和理由,该答复函经过中国使领馆认证、英国联邦外交事务部秘书长认证。一审法院在没有查到相反意见的情况下适用中国法律,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在上诉过程中,上诉人另外提供了《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选集》(部分),以证明英国1935年法律规定妻子不承担丈夫的担保责任,除非是自愿。对此,二审法院则提出:上诉人卢胜苏系中国公民,其适用英国法律的前提是夫妻双方选择适用该国法律。原审两被告主张其在英国登记结婚时已选择适用英国法律,但其并未提交书面协议,其所主张的口头选择也无证据证明。因此,其所提供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二审法院进而提出:“根据《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上诉人选择适用英国法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其申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准许。”
三、我国司法实践不当适用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原因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适用法》第10条实行了外国法查明责任的“二分法”(即法院依职权适用法律则由法院承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则由当事人提供外国法),所以,在当事人承担外国法查明责任却不愿或者无法提供该外国法时,法院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而拒绝适用,显然是合适的实践。不过,一方面,法院应该对此严格区分,不应含糊其词,尤其不可有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本应由法院负责查明的责任转移给当事人,进而提出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提供了法律专家(或者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外国法资料或者司法判例时,法院是否仍可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来拒绝外国法的适用?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法院才会确认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案件的法院都没有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
从上述案例的判决结果来看,在14个明确提出了外国法适用问题的案件中,11个被法院认定为外国法“无法查明”而拒绝适用外国法,竟然占据了近八成的过大比例。由此看来,法院滥用外国法“无法查明”的不良习惯依然未能有效消除。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所有这些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案件中,法院都提出了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并以此为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外国法的适用,而选择了法院最为熟知、因而也最为乐见的内国法。不可否认,其中8个案件当事人确实未能提供外国法,从而在11个案件中又占据了近八成的超高比例。由此可见,外国法的查明确实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复杂问题,从而使得即使是对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也不愿意承担查明的责任;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与我国《法律适用法》刚实施不久有一定的关系,人们还没有真正形成对外国法进行查明的思维与习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8个案件中,其中3个(即“永华公司案”及其上诉案,“邓剑华案”)未涉及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的情形,结果还是被法院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为由拒绝外国法的适用。毫无疑问,这3个法院判决是有缺陷的,因为在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本应该是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但是上述案件中法院仍要求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并据此认定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显然是错误地理解了《法律适用法》。事实上,在“永华公司案”的上诉案⑰中,上诉人上诉意见就指出了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审理,法律适用明显不当……原审法院不愿履行自己应当积极作为的职责,一味把查明的义务强行推给上诉人有违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但是,对于这个重要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持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
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相关材料的其他3个案件中,法院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在这些案件中法院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进而以外国法“无法查明”加以了拒绝,其合理性就颇为可疑。在“国际金融公司案”中,法院显然是拒绝了未经公证认证的法律意见书在法律适用中的有效性,但是,法院对于这种法律意见书的认定问题未做任何说明,却直接宣称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毕竟,如果是因为这种法律意见书未经公证认证而缺乏有效性,则法院应做出效力不足的裁决,而不是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而在当事人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法律意见书、甚至外国法律的“江河创建公司案”以及“卢胜苏案”中,两个二审法院似乎都较为“明智”地规避对它们的认定问题。尽管如此,上述法院最后还是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拒绝了外国法的适用。在“卢胜苏案”中,二审法院为了避免认定当事人所提供法律意见书和英国法效力的问题,甚至提出了两被告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法律选择协议的理由。我们就此推测,法院此举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试图说明当事人选择适用英国法的所谓“协议”不存在,因而在本案中没有适用英国法的情况。但是,令人生疑的是,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是否应该或者能够主动质疑当事人(被告方)婚姻财产关系协议的存在与否?而且,二审判决理由中始终提到《法律适用法》第10条有关“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应提供该国法律”的规定,也很大程度上暗示着法院关注的重点应该并非婚姻协议的存在性问题,而是期望达到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英国法的目的。事实上,二审判决最后部分所提出的主张可略见端倪:二审法院在提出“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时是如此明确断言的:“卢胜苏主张选择英国法律但未提供选择适用的证据及该国法律,一审法院据此以不能查明英国法律为由……并无不当,卢胜苏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从逻辑上看,在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意见书、外国法资料或者司法判例的情况下,法院简单地声称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显然很难有信服度。不可否认,法律专家提供的法律意见书通常都有一定的倾向性,正如美国上诉法院的波斯纳法官(Judge Posner)对法律意见书的内在缺陷所提出的批评:“这些法律专家提供的证词都是收费的,他们根据顾客的诉讼立场来对他们的法律意见进行选择性的说明,或者在顾客的强烈要求下乐于提供对其有利的意见”⑱。尽管如此,法律意见书中通常都指明了相应外国法的内容,并对该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解释;由此看来,即使法院认为当事人所提交的这些法律意见书不全面、不完整甚至有误解或者曲解,声称当事人“未提供”都将与事实相悖。而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或者司法判例时,这种声称更与事实相去甚远。正是如此,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相关材料的情况下,法院仍提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就具有了明显的不当性,甚至可能存在为拒绝外国法的适用而滥用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嫌疑。
在《法律适用法》实施后,法院不当运用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理由来拒绝外国法的适用,或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法院在外国法查明上消极心态的延续。在当事人负责提供外国法时,法院虽然不再需要承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但仍然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外国法进行甄别、解释并将其适用于案件审理之中,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在这种情形中法院在外国法认定上的压力并没有相应减轻,不仅可能耗时费力,而且可能因为错误理解外国法而导致错误的判决。所以,法院期望适用熟悉的内国法的消极心态再一次被激活。第二,认定标准的缺失,是导致法院有关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理由不当运用的客观因素。《法律适用法》中没有规定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判断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⑲中第18条中也仅仅明确了当事各方一致认可的情况下外国法的适用问题;那么,像“国际金融公司案”、“江河创建公司案”当事人仅提供了法律意见书,以及“卢胜苏案”当事人也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时,应当如何处理,法院确实无法从现行法律中找到认定的标准。第三,更为主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法院在认定上的模糊观念。纠结于外国法的“法律”性还是“事实”性,进而说明应由法院依职权查明还是由当事人举证证明,一直是困扰国际社会在外国法查明上的一个复杂问题[2]。虽然我国总体上秉承了外国法为“法律”的观念,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不愿意明确回答有关外国法的性质问题。《法律适用法》确实没有纠结外国法的性质问题,而是规定了依法律适用的性质来分别确定法院的查明职责和当事人的提供责任;表面上看,现行立法似乎已经通过对法院与当事人的责任分配规定解决了外国法的查明问题,不过,在当事人负责提供外国法时,是否应把当事人所提供的外国法视为“事实”,进而以适用举证责任的方式来加以断定,法律是不明确的。毫无疑问,一直纠结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心底的有关外国法的性质问题仍是灰暗的。正是如此,多少有些“束手无策”的法院在面对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意见书甚至外国法资料时,除非有极大的把握,否则欠缺经验的法院以当事人未能提供外国法而拒绝适用,或许就是最为合适的逃避手段了。
四、有关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判断问题”的司法解释建议
法院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时所呈现出的各种乱象,久而久之可能将使法院沦陷到滥用另一个拒绝外国法适用理由的泥沼之中——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从而严重影响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有效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对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问题予以明确。现行《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8条已经规定了当事人一致同意的外国法的处理问题,但对于当事人未能取得一致同意的外国法没有明确处理途径。我们认为,未来的司法解释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加以考虑。
在内容层面上,一是在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时,明确要求法院应在庭审过程中告知当事人需要提供外国法;二是建立外国法的民事证据标准。要求法院的告知义务,很大程度是基于程序正义和诉讼便利的要求,以使缺乏外国法素养的大多数当事人注意法律权利义务的行使,同时也有利于法院避免当事人事后有关诉讼程序欠缺的纠缠。在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时,如法律专家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司法判例等,法院则要求另一方当事人作出确认与否的表示;如果当事人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法院就坚持民事证据标准来审查认定当事人所提供外国法的效力问题。用民事证据标准来加以认定,符合民事案件的基本实践,也利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不可否认,这种实践可以明确诉讼程序中的各方诉讼参与人(包括法院在内)各自的法律地位,并避免法院借此滥用当事人“未能提供外国法”这一拒绝理由。事实上,“国际金融公司案”、“江河创建公司案”以及“卢胜苏案”所体现出的法院束手无策而不当运用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这种拒绝理由,很大程度上就与法院无法准确把握应适用的标准直接相关。此外,这种民事证据标准与《法律适用法》根据法律适用的性质来确定外国法查明责任的规定也是在本质上是相符的:《法律适用法》未拘泥于外国法的“法律”或者“事实”性质来规定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而是要求根据法律适用的性质在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加以分担,从而摆脱了外国法的“法律”或“事实”性质,并因而需依职权查明或者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概念主义法学观念的影响。
在司法解释的形式层面上,建议采用“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从事《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工作,因而,理论上说,把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问题纳入到未来的司法解释之中颇为自然;不过,我们认为,采用“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形式或许更为合理:一是可以避免与现行司法解释协调上可能存在的痕迹清晰的不足,二是如何对当事人所提供的外国法进行认定的问题本质上属于法院内部掌握的事项,是指导法院具体实践的一个司法指南,所以,无需采用司法解释这种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形式。此外,“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这种形式已被先前实践证明是现实可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为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并逐渐提高了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能力。
五、结语
我国现行外国法查明制度所确认的外国法查明责任的“二分法”避免了外国法“法律”还是“事实”性质的概念主义法学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权衡了当事人和法院所可能拥有的资源和激励因素,从而更有利于外国法的查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想方设法地适用自己熟悉的内国法来审理案件仍是法官的一般期望;而作为在外国法查明中享有实际权力的法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权力来达到更符合自身需要的结果,显然并非意料之外的情形了。
正是如此,我们预计,在外国法查明责任“二分法”下,法院以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作为拒绝理由的现象将会更为常见,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法律适用法》通过后我国法院的上述司法实践已经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这种趋势了。为此,在当事人提供了相应的外国法资料时,坚持民事证据标准来判断这种“外国法”的可采性,既能极大地提升法院的审查自信,也更能使当事人信服,从而达到引导、激励当事人积极提供外国法,并最终实现合理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价值目标。
注释:
①Bodum USA, Inc., v. Lacafetiere, Inc., 621 F. 3d 624 (7th Cir. 2010), 638- 639.
②有关这些司法实践的相关统计和研究,可参阅黄进教授和其他合作者共同撰写的年度“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述评”,《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3年卷以次各卷。
③这几种形式主要包括:1.简单地强调“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的证明”,因而“无法查明”;2.未告知或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未予注意,因而“无法查明”;3.对当事人查明行为和提供材料采用严格标准,从而难以达到因而“无法查明”;4.法院根本不进行查明就认为“无法查明”。具体可参阅肖芳:我国法院对“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滥用及其控制[J].法学,2012,(2):104- 105.
④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⑤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 court.gov.cn/zgcpwsw/)中查找到了14个明确涉及到外国法查明的案例:(2010)浙绍商外初字第76号、(2012)津高民四终字第4号、(2012)杭滨商外初字第52号、(2012)杭滨商外初字第53号、(2013)鲁民四终字第7号、(2013)武海法商字第00845号、(2013)琼民三终字第75号、(2013)琼民三终字第79号、(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166号、(2013)高民终字第1270号、(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6号、(2014)闽民终字第146号、(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12- 2号、(2014)苏民终字第0205号。
⑥这里所说的“可能”,主要是因为相关情况均来自于法院的判决理由,所以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是否提供了外国法的相关材料,我们并不总是能直接从判决书中获得。正是如此,不能完全否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提供了相关材料,但未被法院接受。
⑦(2013)鲁民四终字第7号。
⑧(2013)琼民三终字第79号。
⑨(2012)杭滨商外初字第52号、(2012)杭滨商外初字第53号。
⑩(2013)武海法商字第00845号。
⑪(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166号。
⑫(2014)闽民终字第146号。
⑬(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6号。
⑭(2010)浙绍商外初字第76号。
⑮(2014)苏民终字第0205号。
⑯(2013)琼民三终字第75号。
⑰(2014)闽民终字第146号。
⑱Bodum USA Inc. v. LaCafetiere, Inc., 621 F. 3d 624, 633(7th Cir. 2010), Posner J., concurring.
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 24号。
参考文献:
[1] See R. Fentiman,“Englis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in Symeon C. Symeonides e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p. 187- 188.
[2]宋晓.外国法:“事实”与“法律”之辩[J].环球法律评论,2010,(1):14.
(责任编辑:郭鹏)
·司法理论与实践·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Not Providing Foreign Law by the Parties
DINGXiao- wei, WANGJi- wen
(1. Departmen of Law,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Guangzhou 510230,China;
2.Law School,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00013,China)
Abstract:The proof of foreign law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issu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for Foreign- related Civil Relations stipulates the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proof of foreign law between judges and parties; however, short of criterion of measuring the validity of foreign law, negative phenomena of refusal to apply foreign law occur frequently in judicial practice, which is used by the courts with the excuse of not providing foreign law by the parties. The reasons are that courts cannot decide its nature of the materials provided by the party/parties, or maybe the courts abuse it in order to refuse its application of the foreign law designated. Therefore, the futur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stipulate its civil evidence standard for the foreign law provided by the party/parties.
Key words:proof of foreign law; not providing foreign law;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 related civil relations; judicial explanation
作者简介:丁小巍,男,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法律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研究;
收稿日期:2015- 12- 18
中图分类号:DF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828X(2016)01- 0069- 07
——以“秦某某网络造谣案”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