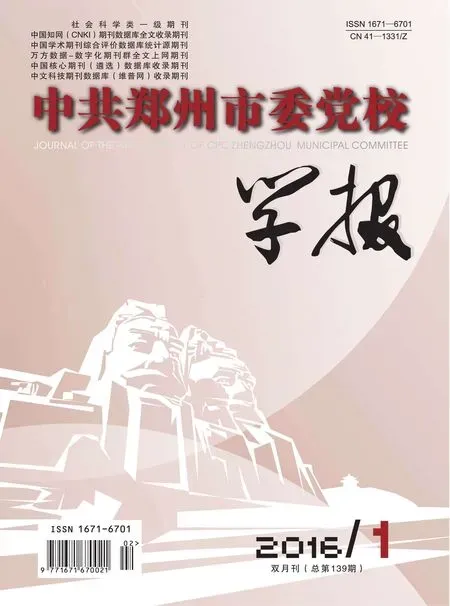近代文化思潮视域下儒学认知的嬗变
王 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近代文化思潮视域下儒学认知的嬗变
王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求新图变以救亡图存的大变动时期,社会的变动导致思想的变动。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尊孔与批孔之争异常激烈。尽管这些争论不尽完美,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长远而深刻。回顾、梳理20世纪初学术界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争论,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儒学大有裨益。
关键词:近代文化思潮;儒学;尊孔;反孔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之后,儒家思想就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在中国也就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其奉为“至圣先师”,用其“天命论”“纲常论”等封建伦理道德对国人实行思想专制。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听到的都是对孔子的颂扬之词,却鲜能听到对孔子的质疑之声,直至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丧权辱国的惨痛经历使人们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学产生了质疑,批孔反儒之声由此产生。然而,对于当时中国那些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儒学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圣教。由此尊孔与批孔之争随之兴起,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达到高潮。回顾、梳理20世纪初学术界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争论,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儒学大有裨益。
一、康有为的“尊孔保教”思想
1898年,侵入中国的德军闯入山东即墨文庙,孔圣像四体被破坏,先贤仲子的双目也被挖去。洋人对中国圣贤的亵渎,让康有为意识到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在进行文化的侵略。为了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康有为成立了“保国会”,其宗旨之一就是“保教”。为实现其保教主张,康有为做了大量理论准备。第一,“复原”传统孔教。康有为认为,变法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但“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改革,人必骇怪”[1],如若“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国人必不会反对。因而,康有为就说,后世所传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学说,而是后人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篡改和歪曲的“伪经”。既然后世所学儒学并非孔子的真传,那么孔子及其学说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对传统孔教进行“复原”。在康有为的“复原”下,孔子不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而是一位锐意革新创制立教的“改革家”,“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2]。第二,倡导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宗教强盛。为了中国的强盛,康有为倡导立孔教为国教,坚信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为了将孔教发扬光大,他倡导成立孔教会,在递呈给光绪皇帝的名为《请商定教案法律折》中,康有为详细地提出了设立孔教会的建议。第三,请求制定教案法。西方列强在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便开始用制造教案的方式侵略中国。为解决由教案引发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制定教案法。康有为以胶州案为例指出,“近者胶案割地累累,波及旅顺、大连湾、广州湾、威海卫、九龙,其他失权之事,尚不一而足也。偶有一教案,割削如此,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毁,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棼如,而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燎原”[3]。对于西方列强利用教案侵略中国的行径,康有为亦想出一套救济之策,即开教会、定教律。康有为认为,中国之所以因教案而丧权辱国,原因是既没有光大孔教又没有教案法。因此,他一方面呼吁在中国建立孔教会,尊孔子为教主,以衍圣公为总理,同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另一方面他又上书光绪帝制定教案法。康有为幼稚地认为,如若做到这两点,再发生教案时就可以由孔教会直接出面交涉,以避免西方列强的外交要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康有为想以此实现与西方列强平等解决宗教争端,无异于异想天开。
二、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批判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戊戌变法时期,其言论无不为其师摇旗呐喊。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革命志士和西方进步书籍的影响下,其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康有为的分歧也愈来愈大。《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既是梁启超冲破其师思想禁锢的号角,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尊孔与批孔论战的序幕。
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可保——保教禁锢了国民思想,违背了信教自由原则;教不必保——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哲学、道德、人文思想对于人格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无灭亡之理;如何尊孔——可则取之,否则去之,吸各家之长,兼容并包。梁启超从这三个方面对康有为的“保教”理论进行了反驳。但此时,梁启超对儒学的批判尚半遮半掩,从思想倾向上来说还是尊孔的,这从其对“如何尊孔”的论述可见一斑。
真正公开、激烈的批孔是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强调,独尊儒学本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实行的,但它禁锢了国民的思想,不利于思想的自由发展,“中国学术之所以不进化,曰唯宗师一统故”[4]。同时,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本身所倡导的“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5],也限制了思想的发展,使人们甘为古人之奴隶。梁启超还意识到了儒学与封建君王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也”,从“以犯上作乱为大戒”到“庶人议政,亦为无道也”[6],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利益。梁启超的这一论断道破了几千年来儒家学说备受推崇的根源,在儒学的批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梁启超还利用进化论的观点阐释其批孔的原因。他说,“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匤一时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年以后之人也”。也就是说,任何圣贤的学说、思想都是时代的精神和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也必将有所发展,所以,对儒学应该采取“可者取之,否者弃之”的态度。梁启超的这一论断是大胆的,也是深刻的,他关于孔子及儒学不可能为后人指明一切、规定一切的历史局限性地阐释,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儒学仍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也有偏激之处。对此,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推翻封建专制,因此对以封建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旧制度和以儒学为灵魂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批判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最首要的任务。
第一,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訄书》等文章,揭开了革命派反孔的序幕。一是章太炎引经据典对孔子的身份进行重新认定。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学家在进行学术争论时,为了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往往都打着恢复孔子本来面目的旗号。为了纠正人们对孔子“闻望过情”“虚誉夺实”的认识,章太炎在《孔订》一书中对过去被“篡改”的孔子形象逐一批判。章太炎说孔子既不是什么“至圣先师”,也不是康有为认定的“创制立教”的“教主”,而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孔氏,古良史也”[7],“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唯为客观之学”[8]。章太炎认为孔子创办私学,把“畴人世官之学”普及到了平民百姓,因而他还是一位教育家。章太炎对孔子本来面目的还原,打破了两千年来大众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章太炎重点批判了孔子及儒学在道德方面的缺陷。章太炎认为儒家学说热衷于富贵利禄,崇尚追名逐利。据《论语》记载,孔子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认为,只要学好仁义道德,就能得到帝王的赏识,获得高官厚禄,还谈什么农事呢?章太炎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在国家需要为民族而奋斗、勇于牺牲的时代精神之时,以富贵利禄为重的儒学思想势必会影响革命的热情和斗志。另外,儒学倡导的“趋时”“权变”“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等所谓“中庸”之道实则是“乡愿”“媚俗趋势”,必将导致道德生活的混乱和崩溃。章太炎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批判仅限于孔子及儒学的道德品行,并没有揭示儒学与封建制度之间的关系。第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章太炎作为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和革命理论家,其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很快在舆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孔浪潮随之兴起。《法古》《中国尊君之荒谬》《排孔征言》等文章就是当时革命派发出的反孔强音。君衍在《法古》中指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人类不断进步的今天把圣贤看成万世之师,“圣贤的言行不可不依”“真是放屁的话”。但为什么中国两千年来都对孔子极为推崇呢?君衍说,“孔子若是与他们无益,他们岂有这样尊敬他呀”,“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是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9]。对于这一观点,吴魂在《中国尊君之荒谬》中也指出,君主并非真正相信圣人的学说,只不过将其作为一种驾驭国民的手段罢了,“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岂一人之咎哉”[10]。在对儒学的批判上《名说》一文更为彻底,此文把君臣之伦、忠义之说、纲纪圣法等孔教观念,斥为杀人于无形的伪道德,认为中国要谋求进步,就必须彻底清除陈旧腐朽的思想,改变社会观念。这些论断揭示了儒学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孔子及儒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辛亥革命后的尊孔复古逆流
辛亥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废除了忠君、尊孔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儒学的垄断地位。遗憾的是,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了。作为封建军阀的袁世凯不甘心失去旧时皇帝的权威,妄图复辟帝制。思想界随之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宣传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之后又发布了《尊孔祀孔令》《祭孔告令》,极力吹捧孔子及其学说。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告令还要求全面恢复清朝的祀孔礼制。之后,袁世凯亲率各部总长及文武官员到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在教育领域,袁世凯宣布恢复尊孔读经的旧制,要求各学校崇奉古圣先贤。张勋在复辟前也有许多尊孔复古之举。1913年,张勋在向袁世凯提交的《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中痛骂革命党人批评孔教、废弃伦纪、破坏孔庙的行为,极力颂扬孔子及其学说,并指出“国体初更,民情浮动,欲谋统一,明教为先”。1916年,张勋又联合16省的督军和省长致电北京政府,请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并断言弃孔教即是弃国魂,他们还攻击那些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的议员,甚至以解散国会相威胁。
除了袁世凯、张勋等封建军阀外,许多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封建文人也乘机大肆进行尊孔复古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康有为。1912年在康有为的努力下,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并很快得到了袁世凯教育部的批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类似的孔教团体也纷纷宣告成立。这些孔教会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湖南各地,为复辟帝制造足了舆论。他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共和体制不适合中国。康有为在《中华救国论》中说,“夫共和之制,与国民共治之。须国民知识通,道德高”,但是中国国民愚弱,纲纪混乱,“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而且,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形势比以前更为混乱,改变这一混乱唯有恢复帝制,由孔子的后裔当虚君,实行“虚君共和”。第二,他们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将孔教定为国教是康有为领导的孔教会最重要的宗旨和目标。康有为认为“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为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11]。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其弟子陈焕章向国会提交《定孔教为国教书》,自此以后各地孔教会、尊孔会以及一些封建军阀纷纷上书通电、撰文,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第三,他们要求恢复辛亥革命时被废除的读经、祀孔活动。陈焕章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一文中说,“小学不读四书,大学不读五经,则废孔教之经典矣。春秋不释奠,朔望不释菜,文庙无奉祀之官,学校撤圣师之位,则废孔之祭祀矣。破坏文庙,烧毁神主,时有所闻,乃至内务教育两部,亦甘为北京教育会所愚弄,而夺圣庙之学田,则废孔教之庙堂矣”,因此陈焕章呼吁学校恢复读经课程,社会恢复祀孔仪式。康有为在给袁世凯的一篇电文中说,“顷岁俎豆停废,弦诵断绝,人无尊信,手足无措,四维不张,国灭可忧”[12]。只有祀孔读经,可厚风化、正人心。
五、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批孔思想
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合流,使新生的民主共和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同时也让人们看清了孔教与帝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历次改革成效甚微的原因。以批孔反儒、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为目标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是反孔勇士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在《驳康有为致总理书》中陈独秀驳斥康有为尊孔复教是“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他指出,独尊孔教,不仅妨碍思想、学术自由,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且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3],因此要捍卫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就必须批判孔教。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系统地阐述了“宪法与孔教”即共和与专制的关系,并从多个方面指出孔教与共和立宪政体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之不合。他大声疾呼:“妄欲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4]
李大钊也相继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战斗檄文,对孔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是近代中国反孔的另一面旗帜。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李大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孔子与宪法精神的不合,批判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为修身大本”的观点,坚决反对把孔子列入宪法。他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去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如若将孔子列入宪法,将是“专制复活的先声”[15]。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李大钊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孔学作了分析,他说,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孔子之道,已不再适应今日之时代,任诸自然之法则,其势力迟早归于消灭。
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子及其学说展开尖锐批判的还有鲁迅,他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抨击孔教以及由其带来的思想禁锢。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在小说《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分别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夫权”和“父权”的批判,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反响。
此外,胡适、吴虞、易白沙等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也纷纷加入了批判孔教的运动,形成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批孔洪流。在这次运动中,有一些新青年也发表了过激的言论。比如,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指出,“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对于这些激进、极端的错误言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反对的。陈独秀曾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同的”[16]。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虽然曾激烈地批判过儒学,但并不是全面否定儒学,而是对儒学及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客观的、分析的态度,他们为彻底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儒学负面价值的批判和正面价值的认可,对儒学所采取的辩证分析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做到了极致和完美。由于时代的局限及思想的不成熟,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偏颇,比如,过分强调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奴役性、时代性,忽视了其民族性;将孔教与儒学混为一谈等。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坚守,我们今天在研究儒学时还要继续克服其片面、主观的思想和做法。
参考文献
[1][3]马洪林.康有为大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67,461.
[2][11][1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198,733,925.
[4][5][6]夏晓虹.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5,43,62.
[7][8]姜义华.章太炎全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5,357.
[9][10]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532,545.
[13][14][16]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139,146-147,318.
[1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责任编辑张敬燕]
作者简介:王丹(1982—),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5-10-16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16)01-0104-05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