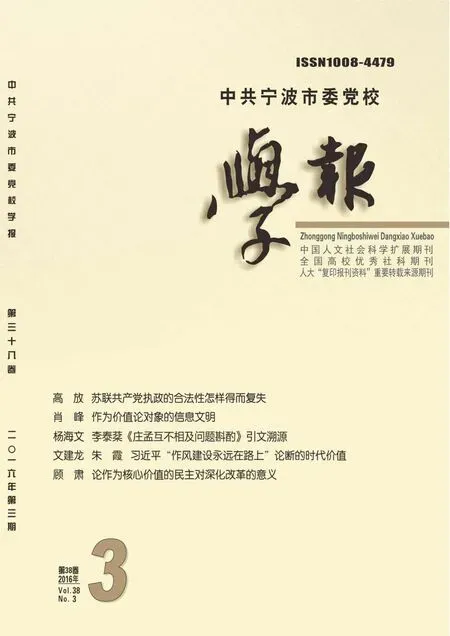抗日根据地司法权的统一: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张孝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29)
抗日根据地司法权的统一: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张孝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政权不同于传统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作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通过专门性司法机关的建立和完善来确立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尽管根据地采取了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组织原则,司法机关仍然基于其职能实现了专门化的发展。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各根据地政权大都明确了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统一行使的原则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加以贯彻实施,从而逐渐具备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司法机关;司法权;国家政权建设
与各种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相比,现代国家政权(modernstate)需要实现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作为依靠暴力后盾解决社会冲突的专门机构,司法机关的重要性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不断提高。乔尔·米格代尔就曾指出:“只有在法院统治区域得到扩张从而使得国家的社会控制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使得动员民众为一支标准化军队和其他任务提供人力和财政成为可能。”[1](P24)因此,司法机关的建立与司法权的统一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维度。
作为依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深知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列宁曾指出:“我们需要国家,需要强制。苏维埃法院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实行各种强制的机关。法院还应当负担起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2](P199)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专门性的司法机关,并且逐渐由这些司法机关来集中和统一行使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本文将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下着重探讨抗日根据地司法权的统一问题,从而深化对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认识。
一、司法机关在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各苏区建立了革命法庭、裁判部、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卫局等机关行使司法职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工农民主政权。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又与司法机关特别是政治保卫局在组织和制度上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3](P385~386)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抗日根据地政权中的司法制度建设都有重要的价值。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7月12日,中共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改组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苏维埃中央政府为了实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首先将中央司法部改组为边区高等法院,遵行南京政府颁行之一切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各种法令章程,工作人员仍本着十年来苏维埃艰苦奋斗的精神,紧张耐劳的工作作风,一扫官僚主义,成为一旧的形式新的内容的司法机关。”[4](P207)谢觉哉随即出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首任院长。根据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高等法院下设检察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总务科。其中,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院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民事和刑事法庭各设厅长以及推事独立行使其审判职权。[5](P355~356)在地方层次上,由于司法人员以及经费极其短缺,陕甘宁边区只在一些中心县设立地方法院,其他各县则设立司法处并由县长兼任司法处长。根据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1月15日发布的第二号通令:“除绥德、延安市已成立地方法院外,并在陇东庆阳及关中新正各设立地方法院,规定地方法院之编制为8人,院长兼厅长一人,综理全院司法行政兼理法庭之审判事宜。”[6](P277~278)
在晋察冀边区,根据1938年1月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边区设高等法院及高等检察处;县设司法处;地方法院于必要时配设。[7](P11)同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临时高等法院在阜平成立,冯振寰任院长。4月30日,边区高等法院奉命改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司法处。[8](P25)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恢复了高等法院的设置,内设司法行政科、民事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和劳动感化机构。高等法院分院则设于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所在地,为高等法院的派出机构。县设地方法院,不设地方法院又无地方法院管辖的县暂设县司法处。各级法院均设首席检察官一人和检察官若干人,由各地区的行政长官兼任。县司法处只设检察官一人,由县长担任。[9](P440~441)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1941年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于同年9月1日正式成立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高等法院内设司法行政处、检察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巡回法庭和劳动感化院。其中,检察处设检察长一人,独立行使检察权。在边区高等法院之下,边区所属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则各设司法科。[10](P445)
在山东根据地,1941年4月22日省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山东省改进司法工作纲要》,规定全省在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前暂设高级审判处为全省最高司法机关。1943年,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内设高级审判处,处长由战时行政委员会委员互推一人充任。[11](P446~447)
二、司法与行政合一的组织原则
在各个根据地司法机关建立和调整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司法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总体来看,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同级政府集中统一的领导,实行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原则。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则一律设于同级政府之内,成为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12](P427~428)
根据地这种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组织原则显然与清末民初以来司法机关独立化的倾向相当不同。1906年,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回国后,清政府对中央政府官制进行了整体改革,其中将原来的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行政事务,将原来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定性为司法终审机关。此外,成立民政部,负责地方行政、警察等事务。[13](P256)此后,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开始分离。辛亥革命后,虽然政体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司法机关的专业化还是晚清官制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发展。1909年的《法院编制法》在民初继续施行。审判采四级三审制度,新式法院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四级。[14](P179)那么,为什么根据地政权采用了不同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司法和行政合一原则呢?
这种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定位首先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5](P274)根据这一学说,所谓司法独立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遮羞布而已。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1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从这一角度阐述了边区司法机关与政府的关系:“法庭是政府的一部份,他的审判对人民(代表人民的各级参议会)负责,同时也对政府委员会负责。法律是应服务于政治的,所以规定高等法院受边区参议会之监督与边区政府之领导。人民对司法不满,可向参议会或政府控告,或依法改选法官,扫去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名独立实受统治阶级操纵的弊病。”[16](P220~221)
当然,这种定位不仅具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需要。在战争的严峻环境下,政府需要集中权力对各种紧急情况和重大问题作出及时的回应。在采取司法独立原则的西方政治体系中,“司法机构的职业专长就是保持稳定、因循守旧和维持现状。”[17](P310)显然,这种保守倾向与战争需要格格不入。事实上,为了实现战时动员,司法人员经常被政府统一安排从事更为紧迫的征兵征粮工作。不用说处在战争前线的华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就是在作为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也是如此。比如合水县裁判员史文秀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中称:“在这两年中间,由一半以上的时间,常在乡村做行政动员工作。”[18](P394)在这种环境下,司法机关只能服务于战争动员的大局。
此外,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根据地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在司法人员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各根据地难以组建众多的基层司法部门,只好在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司法工作。比如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三十一年五月战工会以各地区多迟迟没建立司法部门,对司法工作不能切实负责,遂训令各行政区、各专署、各县府尽可能建立司法机构。如因干部缺乏,也须在各级政府内设司法科;如设科也不可能,最低限度也要在第一科内派定专人负责司法工作。”[19](P317)由于缺乏合法的司法人员,根据地政权即使打算建立单独编制的地方法院也步履维艰。例如,陕甘宁边区在中心县设立的绥德、陇东庆阳、关中新正三所地方法院仍难以满足本区内各县人民的诉讼需求,最终不得不被撤销而回到各县设司法处的旧制。作为实际主持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谈到司法工作时就坦诚指出:“从前所谓‘青天’,即是会断案。现在老百姓的要求,也是:‘负担合理,断案公平’。对于这,我们还有很多缺点。没有足够的司法干部,也没有适宜的司法制度。”[20](P537)
基于上述原因,为了履行必要的司法职能,司法机关设立在政府之内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司法与行政在组织原则上的合一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不能专门化。司法机关的专门化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的)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21](P731)当然,暴力不可能只有国家来行使,但只有当国家允许时,所有其他的团体或个人才会获得使用暴力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被视为应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22](P731)由于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是国家政权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核心特征,任何现代国家政权都需要专门的司法机构来集中行使司法权力。这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的司法制度建设也不例外。
三、司法权的集中行使
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立和初步巩固后,集中行使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在战争的环境下敌我斗争尖锐,局势瞬息万变,同时由于苏区司法传统中“左”的残余,一般的干部和群众一开始难以接受。即使在作为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司法权的统一行使也经常遇到挑战。比如,“绥德县各机关都受理案件;延川保安科曾进行判决反革命分子;有的工厂私设公堂,审讯盗窃嫌疑分子;有的军队及其附属单位任意抓人罚人;特别是一些区乡政府对刑事犯进行拘捕、吊打、关押、审讯和处罚;有的县的区乡政府乱罚现象严重,订出了处罚人的十种办法:罚苦工、坐禁闭、罚钱、罚石炭、罚红布、罚红旗、罚做鞋、罚粉笔、罚粪、罚哨。致使群众不满的说,不怕八路军新四军,就怕基干自卫军;不怕官(法官),就怕管(区乡干部),造成了不良影响,破坏了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原则。”[23](P85)
基于维护根据地基本社会秩序的需要,中共中央不可能对这种混乱局面无动于衷。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24](P768)根据这一指示,各根据地大都明确了逮捕、审判权力由司法机关以及治安机关集中行使的原则,从而逐渐确立了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在司法权的集中行使上率先垂范。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任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25](P35)5月1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地阐述了司法权集中行使的意义:“我们在边区必要做到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边区就不会再有对群众打骂威胁、任意拘捕捆绑、滥用刑讯以及随便砍伐树木,侵占土地房屋、敲诈勒索的事件发生。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建起革命的秩序。至于破坏革命秩序、违犯法律行为的罪犯,必须要拘捕处罚的,这完全属于司法的职权范围。”[26](P360)在该项指示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权集中行使的具体要求:第一,人民非有政府命令无私擅逮捕任何罪犯之权。第二,团体、学校或机关(司法、治安机关除外)得自行处理本团体、学校或机关违犯纪律规则之事件,但不得有逾越违警法或刑法以上之处理;如有触犯法律的现行犯可送交当地司法机关。第三,乡长、区长在特殊的情形下得下命令逮捕一切刑事犯,但必须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将犯人连同有关的证据材料解送司法机关,不得自行判决处罚。第四,县裁判员或检察员得下命令逮捕一切刑事犯,负责审判,但判决死刑的案件,非经呈报高等法院批准,不得擅自执行。第五,县保安科逮捕犯人,必须得县长的同意批准。第六,军队逮捕非军人时,必须先行通知当地政府会同执行。[27](P360)此外,1942 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陕甘宁边区保证人权财权条例》对司法权集中行使原则的内容也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比如该条例第七条规定:“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个人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第九条规定:“非司法或公安职权之机关、军队、团队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查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第十七条规定:“区级以下政府对违警以外任何案件,仅可进行侦察及调解,绝无审问、拘留与处决权。”[28](P92~93)
当然,这些法令在贯彻过程中仍会遇到不少阻力,特别是当领导干部缺乏遵守法令的习惯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1942年3月~9月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以下违反司法权统一行使的案例:“富县杜茂林、扬石锁、刘秃子因捉奸击毙鲁党才,已经高等法院判决释放回家,该县又将杜茂林等逮捕羁押。本院曾以原告无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一再去令着行释放恢复原状,但该县坚持己意,延不遵办,以至狱窑塌陷,压死扬、刘两命。”[29](P167)因此,在法治观念尚不普及的情况下,集中行使司法权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继陕甘宁边区之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其相继颁布的施政纲领也都明确了司法权集中行使的原则。1941年9月1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民均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非依政府法定程序,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不能加以压制、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游街或任何侮辱他人人格之行为。”[30](P44)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1942年10月19日通过的《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中提出:“保障一切抗日的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权,除司法机关得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及个人均无权逮捕、审讯、处罚及侵犯他人之一切权益。”[31](P51)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在1943年1月20日通过的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中提出:“非依政府法令及法定程序,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不得加以逮捕、禁闭、游街及任何侮辱人格、名誉之行为。”[32](P38)1944年2月18日公布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则规定:“保障人权,非依民主政府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不能有威胁、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游街或任何侮辱他人人格之行为。”[33](P54)此外,这些根据地政权也在其颁布的有关人权保护的法令中对司法权集中行使的原则也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比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索侦查处理刑事、特种刑事犯之决定》等都有相关的规定。这些法令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维护了司法权力的统一性。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看,这些规定都大同小异。尽管各根据地处在分散经营的状态,中央关于政策的指示对各根据地施政纲领和相关法令的起草仍起到了汇聚焦点和凝聚共识的作用。
但是,与作为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相比,这些敌后根据地内部的建设与发展很不平衡。同一片根据地,基本区与边沿区、巩固区与游击区,以及抗日政府人员可以进入、人民又奉行中国政府法令的敌占区,情况又各不相同。[34](P245)此外,随着日军的扫荡,基本区也会变成边沿区,巩固区也会变为游击区甚至敌占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在原则上集中行使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灵活变通的方法以适应战时需要。比如在晋冀鲁豫边区,区公所依法规定本无司法职能,但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分割状态,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从司法的角度把它们划分成三种类型,即一般区公所、委托区公所和游击区区公所。其中,委托区公所是指地区特殊、干部配备较强,并有县政府命令委托的区公所,这类区公所除拥有一般区公所的民事诉讼调解权和少量罚金权外,对于违反法令的侵害事件有处1000以下罚金之权。受县政府特别委托的游击区区公所则有权处理最重本刑在刑徒两年以下、罚金1000以下的刑事案件。[35](P445)又如在晋察冀边区,“当敌军扫荡、清剿或武装汉奸滋扰时,对于证据确凿之汉奸,人民及民众组织具有逮捕之权。”[36](P93)在战争环境下,这些违反司法权集中行使原则的临时措施难以避免,但仍大都遵循了授权的程序或者依据了相关的例外条款。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堪称新中国政权的“雏形”。随着1949年国民党旧政权法统的全面废除,抗日根据地司法制度的遗产也变成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重要的历史基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其发布的文件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法制的典型代表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37](P138)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称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38]因此,抗日根据地司法权力的统一,不仅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也对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4.
[2]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
[3][9][10][11][12][35]张希坡、韩延龙.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85~386,440~441,445,446~447,427~428,445.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工作报告(1937年7月23日)[A].陕甘宁边区抗日民注根据地(文献卷·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07.
[5]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55~356.
[6]陕甘宁边区政府批答——为批答定边县司法处之编余情形(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A].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277~278.
[7]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三八年一月)[A].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11.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25.
[13]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6.
[14]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9.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16]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四一年四月)[A].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220~221.
[17]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0.
[18]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不应随便抽调司法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A].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94.
[19]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司法组总结报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A].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317.
[20]谢觉哉.边区参议会常驻报告(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A].谢觉哉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37.
[21][2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31.
[23]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85.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8.
[25]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5.
[26][27]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60.
[28]陕甘宁边区保证人权财权条例(一九四二年二月)[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2~93.
[29]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3月~9月工作报告[A].转引自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67.
[30]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4.
[31]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51.
[32]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8.
[33]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54.
[34]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245.
[36]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索侦查处理刑事、特种刑事犯之决定(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A].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3.
[37]张世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史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38.
[38]汪世荣、刘全娥、王吉德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责任编辑:刘华安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3-0070-06
[收稿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嬗变”(编号:11CDJ003)
[作者简介]张孝芳(1977-),女,湖北当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中共党史。
——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之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