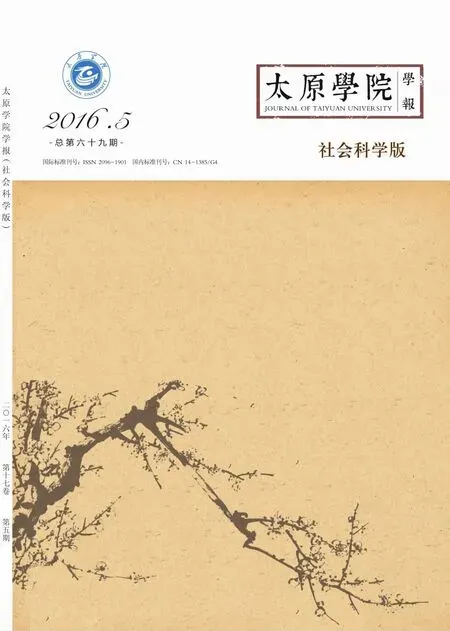合理性原则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适用
——以不确定性为视角
刘 富 城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合理性原则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适用
——以不确定性为视角
刘 富 城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垄断行为法律认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经济学流派对垄断这一经济状态具有不同的测定范式,另一方面是由法律语言和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决定的。因而在具体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就需要进行个案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合理的判决。通过对我国典型性司法案例的考察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就是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的“合理性原则”。
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合理性原则
哲学知识告诉我们,世界在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之间存在,变与不变,确定与不确定都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因而告诫我们在思考问题时要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不可偏废,涉及到法学和经济学的反垄断问题甚是。法学要求的是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知识观来处理问题,而市场经济行为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任何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某种模型之上,因而也不是准确的。当法学必须解决垄断带来的问题时,冲突就产生了:法学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要给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行为——垄断定性,法律规范提供的是明确的、可以具体提供裁判指引的法律条文,而垄断却是人们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综合评价。在另一方面,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反垄断法的许多法律条文本身具有模糊性和原则性,即使立法时规定得相对确定和具体,同时立法者又规定了豁免情形。法学意义上的垄断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一样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反垄断法适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指导裁判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有两个司法适用原则:一个是本身违法原则,另一个是合理性原则。这两种原则适用的具体情形是根据垄断行为对经济效果的作用来区分的,对于消极经济效果明显的限制行为采用本身违法原则,以快、准的方式认定该垄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自身违法性,如划分市场、固定价格、联合抵制等垄断行为;对于经济效果不好评估的行为则适用合理性原则。[1]31合理性原则是指某些垄断行为对竞争的损害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2]102-103在对之进行反垄断司法审查时,必须首先进行经济分析和法律对垄断行为的豁免考察,综合分析该垄断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以实质审查来决定该垄断行为是否违法,因而须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为了避免造成混乱,必须严格区分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和法律上的垄断。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本身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如两个企业之间进行合并;法律意义上的垄断更多地是指立法层面上把几种或者哪一类的垄断行为规定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简而言之,经济层面的垄断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垄断行为,但是法律上的垄断行为也不全是经济上的垄断,如行政权力造就的垄断就不是经济上的垄断。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和法律意义上的垄断是一种交集的关系。
言归正传,合理性原则的适用是因某些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危害性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那为什么某些垄断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模糊不定的特征呢?潘丹丹指出:反垄断法是开放多元的系统,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反垄断法具有不确定性。[3]149但上述解释恐怕还是太宽泛,关于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原因的探究必须寻根问底、追根溯源,须从反垄断法的产生,反垄断法的立法语言表述以及对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过程进行考察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一、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原因的考察
(一)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原因之经济学考察
前述提到过经济层面上的垄断和法律意义上的垄断。确实,在法律上,垄断这一术语是来自于经济学,反垄断法是属于经济法部门下的法律,其从经济活动中产生,因而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必然残留有经济学不确定性因素。经济理论是反垄断法制定与实践的基石,[3]3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前提假设的模型之上,因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未曾对“垄断”这一术语的概念取得过共识。[3]3可想而知,起源于经济理论的反垄断法无论是在立法上或是在司法实践中就更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了。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也不会自我产生,所以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首先要进行的是分析、论证和解释。然而对反垄断法所采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就是不确定的。以最早制定反垄断成文法的美国来看,站在经济分析上对反垄断法适用问题进行论战的当属哈佛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哈佛经济学派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的结构分析法,指出要保证市场绩效须控制市场结构,以防过度集中的市场,[3]8其首要就是政府强化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反映到反垄断法领域就是政府人为地审查市场集中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哈佛经济学派的经济分析模式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占主导。1950年,美国国会修正了《克莱顿法》,通过了《塞勒——克弗维尔法》,强化了对合并的规制。 1968年,美国司法部的《合并指南》更是委托哈佛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特纳(Turner)来制定,全盘采用了结构主义模式指导反垄断法适用。[3]9但是到了1982年和1984年,美国的《合并指南》却是由担任反垄断局局长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威廉·波斯特对之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对合并的干预。因而合并次数在次年就有了显著的增加,达3165次。[4]67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市场集中度问题的关键,市场集中度与市场范围和产业周期相关,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5]16从而得出结论:企业只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平均成本才能不断降低,进而生产出更加廉价的商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因此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不是采用非法手段,就必然具有合理性。从美国反垄断法经济学分析理论的这一变革中,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学理论主导的反垄断法实践是一个随着时间和具体市场情况演变的过程,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并不能给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确定的答案。因而也就不能不区分具体情况只按照一种经济学理论模型认定某种市场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进而给予制裁。正如克拉克所主张的:垄断分两类,效率垄断和非效率垄断。效率垄断是指企业由于创新等措施领先一定时期保持的市场垄断地位,其与动态竞争有关,是合理和可接受的。*徐伟敏,美国谢尔曼研究,山东大学2009博士论文,转引自潘丹丹,《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意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综上,市场经济中的垄断现象相当复杂,在进行反垄断法上的分析时必须采用二分法,而不是对所有经济中的垄断都采取干预的态度,欲除之而后快,而是要充分运用合理性原则,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二)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原因之法学考察
反垄断法是法律的一个部门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垄断的不确定性在法律上必然有不同于经济学的原因。法律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研究来说进行简单的界定是必要的。简言之,法律是用书面语言表达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法律必须由语言表达出来,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语言本身的缺陷——模糊性。这种语言的模糊性首先表现为每一个人可能基于不同的背景对同样一句话产生不同的理解。确实,法律需要作出解释才能适用,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死法”,不足以自行,只有经过解释之后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作用,成为“活法”。从科斯的一句话中可见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他说,“反托拉斯令人厌倦,因为价格上涨时法官说这是垄断,价格下降时,他们说这是掠夺性定价,价格保持不变时,他们又说这是默示共谋。”*Edmund W. Kitch, the fire of truth: a remembrance of law and economics at Chicago, 1932-1970, 26J.L. &Econ.13 (1983),转引自潘丹丹,《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意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换言之,从反垄断成文法的条文来看是无法预先给出垄断行为违法与否的答案,从而法官不能进行简单套用。另外,反垄断法本身的模糊性还在于立法语言中无论给一个名词加多少修饰性词汇,诸如“合理”“不合理”内涵的不确定性还是客观存在的。又如“滥用”“重大影响”“实质上”等词汇本身也需作进一步解释,但每一个人的解释又不相同,从而得出的结论相向也就难免了。
再者,反垄断法的法律规则也是模糊不定的。比如美国《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的“凡是限制贸易的合同都是非法的”。德沃金就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应该看做一条法律原则而不是规则。他指出,“美国最高院过去不得不做出裁定,裁定这一条款自身是否应该看做一条规则,或者把它看做一条原则”。[6]47德沃金认为这是一条原则而非规则,可是这明明就是《谢尔曼法》里正文的一个条款,有什么理由说这不是一个法律规则呢?笔者的理解是,无论对之作缩小解释也好,还是探寻立法者原意也罢,这一条款都太笼统以至于难以有效实施。因而在1896年到1904年,联邦最高院只能通过判例的形式来规定禁止哪些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合同。[7]117至于在反垄断法中为何会出现不确定的法律原因,潘丹丹认为,反垄断法律规则的有限性与反垄断事实的复杂性之间具有无法弥合的张力。[3]12确实如此,经济事实变幻难测,难以量化计算,因而更不容易使用一条或几条文字表述的法律规则进行界定。因而反垄断法本身就是带有不确定性因素的。
又再者,垄断法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垄断事实的认定。要进行反垄断司法实践,首先必须认定垄断事实,而后,才能作出司法推理。但是反垄断案件中的事实多为经济事实,但经济事实易变,从而经济事实到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也不会是容易的。[3]14确实如此,具体到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和企业行为的认定非常重要。相关市场不仅与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和时间要素有关,还与交易地区、阶段、对象、时间等具体交易因素有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同属于水果的苹果和香蕉在同一地区可能就属于两个不同的市场,其理由在于老人和小孩可能对香蕉这种特殊的水果(其实每一种水果都可能是特殊的)具有特别的需求。简而言之,相关市场的区分是一个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的,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系统。在反垄断法中,企业行为主要是垄断协议行为(包括无协议的共谋)。从企业定价这一微观的经济行为来看,定价首先涉及到成本,但是在经济学上有不同计算成本的方法,因而成本的本身也具有多样态性,诸如固定成本、不变成本、可变成本、总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平均总成本等等,面对这些不同的成本术语,不精通经济学,对企业定价行为的反垄断法定性也肯定无所适从。
(三)小结
以上两小节从经济学和法律的角度探讨了反垄断法不确定的原因。进行反垄断司法裁判,为垄断行为提供一个量化测定的方法,经济学内部派别无法达成共识。但是法律语言本身也好,法律规范本身也好,反垄断法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那我们是否可以遵从哲学上的指导,以此认为不确定性就是反垄断法的一个本质因素呢?因而呼唤着在反垄断案件中更多地考虑以合理性原则来指导反垄断法实践。
二、合理性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产生与发展
合理性原则,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反垄断案件中理性地对案件本身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武断和机械地适用法条。权威教授王晓华认为,合理性原则是指市场某些反竞争行为不必然视为违法,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某行为在形式上具有限制竞争的目的和后果,但同时又能促进竞争,或能显著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整体经济或社会公共利益,该行为就被判定为合法。[8]230-23此定义得到了众多反垄断法学者的认可,李钟斌先生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王晓华教授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他认为反垄断法上的合理性原则与竞争中的潜在效益及相关法价值之间的平衡有关,因而合理性原则是一种效益比较的衡平原则。[9]3-5合理性原则是一种追求实质正义的法律原则,合理性原则具有价值开放性、论证充分性和利益衡量多元性的特点。[3]88在合理性原则看来,企业的结合与共谋等垄断状态和行为本身不一定构成违法,而只有当该种状态或行为确实排除、限制了竞争,造成垄断弊害时才加以规制或禁止。[10]188但是也正是由于合理性原则体现出来的原则性和不确定性,合理性原则的客观性遭到了怀疑。美国学者卡斯滕森认为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的符号概念,没有实质内容。[9]18在此,笔者同意合理性原则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绝不认同合理性原则是一个空壳。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合理性原则指导判决绝不是法官为所欲为,而是把重点放在合理分析这一点上,法官作为正义的代言人,在做出判决时肯定要运用理性。
在美国反垄断实践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谢尔曼法》通过的前20年里,该法居然没有被真正适用过。究其原因,是因为《谢尔曼法》规定的太过于刚性和武断,其第一条就是“所有限制贸易的合同都是非法的”。采取概括禁止的表述而没有在法律上规定除外适用情况,《谢尔曼法》的适用就给法院带来了难题:假如一概禁止限制贸易的合同,那么有很多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将会受到影响。从而有的学者解释道,立法机关将合理确定禁止限制贸易合同界限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法院,[9]15从而需要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灵活把握。因而就呼唤着合理性原则的诞生。
合理性原则产生于《谢尔曼法》之后的1911年,“标准石油诉美国案”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在该案中,怀特法官认为协议限制了贸易不一定就是违法,而是要从协议的目的和行为效果来看限制贸易是否合理,如果限制贸易有损公共利益,才判断为非法。[3]87联邦最高法院为《谢尔曼法》指明了适用的方向,即原则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才属于该法第一条所禁止。因而反垄断法合理性原则产生了。美国最近一起较大的反垄断案件要数“微软公司案”。众所周知,微软占据的商用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高达95%,但是面对这么明显的经济事实,美国法院也没有直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来判定微软公司违法,而是进行了综合市场分析,比如其他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难易程度,其他企业因微软公司造成的损害等,才最终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具有垄断的性质。可见美国政府和法院的反垄断态度倾向于合理性原则。
(二)合理性原则与中国《反垄断法》
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的规定采取列举加定义的模式,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垄断协议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从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反垄断法》与美国《谢尔曼法》具有相似之处,如《反垄断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均表述为“禁止……达成下列垄断协议”,这一表述与《谢尔曼法》第1、2条所表述的“禁止一切限制贸易的合同”*Section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erman-Antitrust-Act,2016年7月3日访问。与“任何人垄断和企图垄断都是重罪”*Section 2: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erman-Antitrust-Act,2016年7月3日访问。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采用概括禁止、绝对禁止的立法语言来表述。不同的是,我国《反垄断法》在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对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所禁止的行为设置了“适用除外规定”,也即大家所说的豁免制度。在我国反垄断法领域,人们更多地是在学理上谈合理性原则。如王健认为,反垄断法禁止的是不合理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对绝大部分的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要进行合理性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反竞争目的和效果。[11]42在此,王健先生认为《反垄断法》禁止的是不合理的垄断协议,然而《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明确说的是“禁止下列垄断协议”,根本未作“合理”与“不合理”垄断协议之区分,那么这种解释是否有缩小法律文义之嫌呢?古红梅也认为对效果难评估的经济行为要进行个案分析,进行合理性判断。[1]31姜发根则指出,反垄断执法机构或法院要分析与垄断协议有关的市场具体情况,对比协议实施前后的市场情况变化,进而考虑协议的性质和后果。倒是国家工商总局在《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中有提及判定“其他协同行为”还应当考虑相关市场的结构、竞争状况、市场变化、行业情况等因素和经营者能否对协同一致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三条: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二)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三)经营者能否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认定其他协同行为,还应当考虑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竞争状况、市场变化情况、行业情况等。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法》及反垄断制度并未明确规定合理性原则的适用。但是从《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和工商总局《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法律要求对垄断行为进行合理性审视的意旨。此外《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设置的其他垄断协议之兜底规定也为合理性原则在具有成文法传统的我国无须通过另行规定就能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奠定了基础。
(三)小结
以上两小节主要讨论了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合理性原则与我国《反垄断法》的关系,通过对比美国《谢尔曼法》和我国《反垄断法》,可知合理性原则在中美两国都没有进行过明确的表述,稍有不同的是我国《反垄断法》的概括除禁止外还规定了豁免制度,这可能是我国《反垄断法》在世界上制定得比较晚,借鉴西方国家反垄断法律成果杂糅而成的缘故。在美国,合理性原则从判例中产生;而我国反垄断法中似乎预留合理性原则发挥的余地,那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合理性原则是否也能像美国一样得到适用呢?下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法院给出的两个反垄断司法案例。
三、合理性原则在我国反垄断司法案例中的实证考察
(一)锐邦公司诉强生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的考察
本案是一个纵向垄断协议纠纷典型案件*具体案情参见,“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等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判决书”。,即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垄断协议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经销合同中如何判断经营者向交易相对人限制商品最低转售价格的性质。本案由原告上诉,经过二审改判予以结案。一审法院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垄断协议须为排除、限制竞争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因此在认定《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的经营者向交易相对人限定商品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也应进一步考察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情形。但是从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向适用于第十四条垄断协议这一过渡,一审法院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其原理,因而这一缺陷在上诉人锐邦公司的上诉状中被抓了辫子。上诉人锐邦公司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垄断协议都因目的违法而被法律明确禁止,一经签订即为违法的垄断协议。但是两被上诉人辩驳,根据最高院《审理垄断纠纷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认定横向垄断协议尚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而认定最低转售价格限定来说更须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前提。被上诉人的这一观点,在二审法院的判决中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予以采纳。在二审抗辩时,两被上诉人也使用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进行辩解。本案的判决由二审法院以鸿篇巨制的笔墨完成,判决书说理分析部分占很大比例。《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之规定以适用于整部《反垄断法》为由纳入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纵向垄断规制的限定范围之内。最后二审法院对该案涉及的相关市场竞争度、被告市场地位强弱、最低转售价格限定目的以及最低转售价格限定所带来的市场效果四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被告强生公司限制最低商品转售价格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裁判。
本案作为我国法院审理的纵向垄断首案,因其典型性和二审法院的说理性被最高法院作为公报案例收入。可以说其对《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的把握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大多数认可。反垄断案件因其复杂性,在审理时必然要经过个案的具体分析才能实现法律价值——公平和正义。任何只根据《反垄断法》进行字面解释,再经过举证证明责任的简单认定做出判决的,都是一种司法实践上的偷懒和对法律价值尊严的亵渎,因而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也是具有负面作用的。
(二)巨星公司诉飞轮公司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的考察
在上一小节,对纵向垄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考察,发现法院在对个案进行具体合理性的分析之后才认定该垄断协议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横向垄断的典型案例,看法院是否也须作出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效果的认定。
在巨星公司诉飞轮公司一案中*具体案情参见,“苏州巨星轻质建材有限公司与南通巨轮轻质建材有限公司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判决书。”,一审法院的主要判决依据是巨星公司和飞轮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之禁止性规定,因而属于无效协议,根据《合同法》判决不支持原、被告的诉讼请求。因此可以认为一审法院将这起垄断性质的纠纷主要看作是一起合同纠纷,《反垄断法》的规定只是作为用《合同法》进行判决的法律参照,判决的重点并没有落在对垄断行为的分析上。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这起垄断协议纠纷时更多地是运用了一种法律适用的技巧进行判决,没有分清主次、抓住重点。这起案件与其说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倒不如说是一起垄断协议纠纷案件,但主要是一起《反垄断法》上的纠纷,因而法院应该更多地在当事人市场情况方面进行分析。一审法院判决的这一缺陷被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予以纠正。二审法院认定,《反垄断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垄断协议行为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而在审判时应重点考察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列举的垄断协议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因而为法律所明文禁止。进而,二审法院对固定价格和分割销售市场进行了个案的具体分析,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因违反《反垄断法》而无效。在判决最后,二审法院也对本案当事人双方协议的性质作了界分,认为当事人双方的协议虽是协商一致的产物,但是其通过了典型的垄断行为对竞争进行限制,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后通过适用《反垄断法》判决维持原判。
可以说本案二审对案件的定性是比较准确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起实施,而《合同法》从1999年10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了。因而《反垄断法》属于后法,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理,应该以《反垄断法》对本案进行定性。另外,在合同或协议层面,《反垄断法》对协议的规定相较于《合同法》对协议的规定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也是应该适用《反垄断法》对本案进行定性审理的。因而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方面存在错误。从本案的二审判决来看,二审法院也是对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了个案分析,对双方当事人垄断协议行为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驳之后才得出判决的。
(三)小结
上述第一个案例是典型的纵向限制竞争,而第二个案例是横向限制竞争。两个案例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一审判决比较简单,没有对个案进行详细的经济学上的具体分析就作出了判决,因此出现了一些纰漏或者错误的结论,经过二审判决的详细说理才得以改正。所以说无论是危害性严重的横向垄断协议也好,还是危害性稍弱的纵向垄断协议也罢,在立法采取概括禁止之后有原则性的规定垄断协议必须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须具有反竞争效果。法律原则具有指导具体规则适用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横向限制竞争还是纵向限制竞争,在司法实际中都必须坚持其指导性,贯彻适用。
四、结论
本文以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为视角,首先探析了反垄断法不确定性背后的原因,指出无论是从经济学上的分析,还是从反垄断法本身都不能完全清除反垄断法中所隐含的潜在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在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呼唤着合理性原则的产生。本文第二部分考察了合理性原则在美国司法判例中的产生及发展,同时对比了美国《谢尔曼法》和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表述,发现美国以普通法判例的传统,呼应司法实际的要求在判例中确立了合理性在反垄断司法判决原则;而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了西方立法成果,规定垄断协议必须要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和《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豁免规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就是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中要遵循的“合理性原则”呢?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就是我国《反垄断法》上的“合理性原则”。这一款之规定未置于《反垄断法》总则部分是立法技术上的一个失误,但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的发挥,司法的适用。
[1]古红梅.纵向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吕明瑜.竞争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潘丹丹.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意义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4]吴玉岭.市场之恶——美国反垄断政策解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胡甲庆.反垄断法的经济逻辑[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6]罗纳德·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M]. 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7.
[7]付池斌.现实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李钟斌.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2.
[10]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1]王健.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J]. 法学,2014(3).
[责任编辑:岳林海]
Rationality Principle in Practice of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 ——Taking Uncertainty as Perspective
LIU Fu-che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stitut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The uncertainty of monopoly conduct, in the one hand, is because different economic schools have different evaluation model to judge whether one market action or behavior is the monopoly conduction in Anti-monopoly Law; on the another hand, is becaus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Ambiguity of language. The aforesaid two factors construct an uncertainty of anti-monopoly law. Thus, in the anti-monopoly practice, we should make a specific analysis to each of the anti-monopoly case. Thereafter, reasonable and legal judgments can People’s Court reach. According to examining typical judicatory cases of monopoly, the author deems that article 13.2 of Anti-Monopoly Law of China seem as the basis of application of Rationality Principle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
Anti-Monopoly Law; uncertainty; rationality principle
2016-07-18
刘富城(1992-),男,江西赣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015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法律实务。
2096-1901(2016)05-0015-06
D912.2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