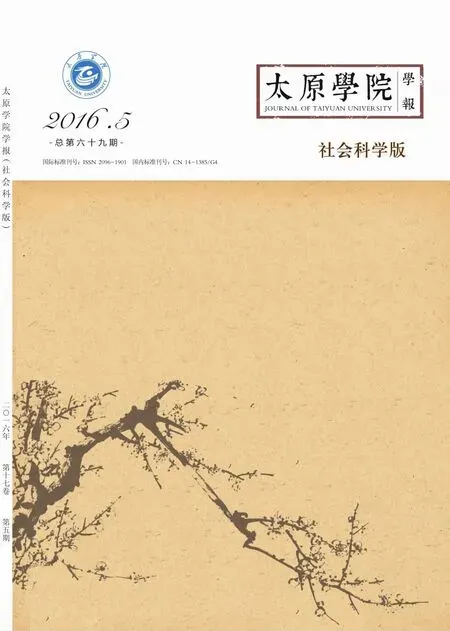任侠精神与自我悲鸣
——从《感遇》看陈子昂的理想与现实
王 施 懿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 人文社科系,四川 成都 610213)
任侠精神与自我悲鸣
——从《感遇》看陈子昂的理想与现实
王 施 懿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 人文社科系,四川 成都 610213)
陈子昂以其“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 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的文学理论主张以及复倡兴寄、刚健质朴的诗文风格在文学史上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感遇》三十八首是其当之无愧的代表作。该组诗反映出了支撑作者理想追求的任侠气质,以及在面对现实的挫败时表露出的情感独白,从理想性与现实性两方面解读贯穿陈子昂一生主要经历的《感遇》组诗,以期拓展研究视角。
陈子昂;感遇;任侠;初唐;忧患意识
在陈子昂现存的一百余首诗作中,《感遇》三十八首是其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更是齐梁浮艳之风向盛唐遒劲开阔诗风转变的关键之作。当前研究者解读《感遇》多集中于陈子昂的社会意识、政治思想或者哲学观念层面,却少有人重点解读该组诗中反映出的支撑作者理想追求的任侠气质,以及在面对现实的挫败时表露出的情感独白。鉴于此,本文将从理想性与现实性两方面来解读几乎贯穿陈子昂一生主要经历的《感遇》组诗。
一、理想中的任侠精神
“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隅,在悠久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侠文化。从广义上来看,侠文化中包涵了一种凝结在中国人人格中的侠义精神,即“侠性”[1],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在文人身上又通过文艺作品具体表现出来,因此侠与中国古代文学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魏是文学礼赞侠义精神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自司马迁《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后,所谓‘言必行,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以及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之类任侠精神,已经升华为一种社会品德,并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的愿望结合起来了”[2]。及至初唐,这种任侠风气在文人中重振旗鼓,并最终在盛唐达到一个高潮。据《唐书》载,初唐文人多豪侠,陈子昂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代表。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称其“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3],体现出一种杰才立身、仗侠使气的处世作风与豪姿英发的精神面貌。《感遇》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展现出了这种任侠使气的精神面貌。
《陈氏别传》言:“子昂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3]任侠之气从小熔铸于陈子昂的性格之中,并在之后的诗文中展现出来。在《感遇》诗中,这种“侠客之义”又多凝聚于其中的边塞诗与咏史诗里。具体分析,其任侠精神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尚气决”的经世之心、戎旅之志
在《谏理政书》中,陈子昂尝言:“以事亲馀暇得读书,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4]后又自言“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可见,其虽然精于治学作文,但却怀抱一颗立功立德、经邦济世之心。在《感遇·十一》[5]中,陈子昂刻画了一个胸有雄才大略,心处白云之间的隐士形象鬼谷子。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著名隐士,也是深谙经世之道的纵横家,他“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有抱负、有才能,鄙弃浮荣、韬光养晦。诗人对其形象的精心树立,实则是“以鬼谷子自负”,一表“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的豪情壮志。《感遇·三十五》中,诗人再一次慷慨发出“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5] 59,表露自己不甘于笔下生风、纸上谈兵,而愿投笔拔剑奔赴战场。除了树立自己建功立业的形象,陈子昂的“武毅”气质更表现于众多边塞诗中。陈子昂曾两次从戎边塞,在对边塞风光、生活、战场的描摹中,自己的豪迈激昂、英武神姿喷薄而出,展现了性格中积极进取、张扬自由的浪漫气质。《感遇·三十四》:“自言幽燕客, 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 白刃报私仇。避仇至海上, 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 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 常为汉国羞。”[5]57该诗盛赞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游侠年轻时候的豪侠生活,全诗以“幽燕客”自述的口吻,叙述了游侠生活,并抒发被压抑、打击的愤懑之情,引发了陈子昂的共鸣。《感遇·三十七》作于陈子昂在从容边塞时,诗人愤恨突厥的猖狂入侵,并由“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尖锐指出,正是“由于将领腐败,不能捍卫边塞,致使战祸绵延,百姓遭殃”[5]63。豪壮激荡的边塞诗可以说是陈子昂纵横使气,雄浑奔放气质的真实写照。
(二)“重恩义”的任侠原则
“义气”是自古以来侠士固有的行事原则。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对游侠的基本特征进行定义:“今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6]“不轨于正义”是侠义精神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因为侠士“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因此挑战着现行法律与统治者的权威。
“恩义”是侠士行事的主要原则,这种原则在社会中向上表现为“忠义”,知恩图报,他们追求较为平等的君臣关系,并时时体现出一种“君臣大义”。杜甫就曾在《感遇有遗篇》中称陈子昂“终古立忠义”。陈子昂早年深感武后对他的知遇之恩,并认为其为“非常之主”,因而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感遇·十八》感叹“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5]32,可见其为武后朝政直谏忠言、殚精竭虑,最后却不得不沦为“骨鲠之士”,展现出知恩图报的侠之忠义。陈子昂的“拥武”、“忠武”的态度后受到一些不公正评断,甚至被讥讽“人品不足论”“唐之小人无疑也”。但陈氏诗作反映出的“感激忠义”并非后人认为的“愚忠”,在《感遇》中诗人通过咏史诗展现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对武后一朝的忠愚难辨、世风日下的风气进行了揭露与鞭挞。如诗人在《感遇·十六》痛心疾呼:“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蚩蚩夸毗子,尧禹以为谩。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5]28陈子昂面对矛盾冲突激烈的社会,曾上书武后指出尚贤使能的重要意义,“批评武则天‘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强调‘圣人制天下,贤能至公’。”[5]28-29陈子昂的直陈谏言还表现在大胆揭露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作风上,《感遇·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朝。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通过抨击穆天子,对武则天和诸侯集团纵情享乐进行鞭挞[5]45。
以“恩义”行事的原则向下则体现出一种“急人之难而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7],一种对于下层百姓因遭受非正义的同情和保护。陈子昂一生主要生活时期处在武则天集团统治之下,在两次入仕、两次从军、两次被贬入狱后,陈子昂见识太多社会不公与苦难,寄希望于武后的愿望因而破裂。滥杀无辜、重用酷吏、好大喜功的武后让无辜民众人心惶惶,频繁的战争使边防战士和人民生灵涂炭,陈子昂愤然发声,控诉当朝政府。《感遇·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5]7《通鉴》记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必不可免无辜者的性命。“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其三》)[5]6,“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感遇·三十七》)[5]68诗人用沉郁苍凉的笔调描绘出一片满目疮痍的边塞战争场面,无情控诉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表现出陈子昂忧时忧民的情怀。
(三)慷慨扩大、气象雄浑的诗风
陈子昂重风骨、倡兴寄的古典诗风的形成与其纵横任侠的家庭出身息息相关,而其两度亲临边塞,驰骋疆场的经历也对其诗风的形成功不可没。刘大杰评价陈子昂:“只是用自然的音调,雄浑有力的语言,自由的格律去表现那种慷慨悲凉的情感,然而诗中却蕴藏着一种高远的意境与豪放的气概,充满着清新自由的生命力,正具备着他所说的那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特色”[8]。在陈子昂笔下的边塞气象是如“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的气势恢宏、笔调高远;亦是“信马胡关冲,亦距汉边塞”的恳切之词、不事雕琢。陈子昂面对国之边疆苍茫瑰丽的边塞风光,往往能用苍劲素朴的笔风来描摹最真实的边塞景象,如“从石何纷乣,小山复翕艳。远望多众容,逼之无异色。崔翠乍孤断,逶迤屡回直”,远望万千气象,近观却也逸趣横生。又如“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逦迤忽而尽,泱莽平不息”的山色与大漠交织的风景,宛如一幅辽阔雄浑的西北风景油画。“拳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诗人寄忧时伤世之情于赫赫料峭之景,语言却显得质朴苍劲,丝毫未有矫揉绮靡之病,胡应麟评价其诗“尽削浮靡,一振古雄,初唐自是杰出”可谓恰如其分。
二、现实中的自我悲鸣
陈子昂的豪侠精神与其生于蜀中多豪侠的社会风气及世为豪族的家族风格息息相关,这种精神凝铸于子昂的个性气质中,随其走出四川,走向仕途。“豪侠纵横的个性赋予他(陈子昂)君臣际会的浪漫幻想和屡次直谏的勇敢精神”[9],但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遭遇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子昂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他的从政热情和政治理念屡遭冷落,直谏良策,终不见用。“上数召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后的碰壁绝望,到投笔从戎、以身报国,却被降职最终归隐的悲惨落幕,使得陈子昂面对人生际遇与天人之道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入的思考;其中也不免抒发壮志难酬的自我悲鸣。
(一) 对个人命运的悲鸣
延载元年,即公元694年,陈子昂在任右拾遗不久便被人诬陷,身陷囹圄。这一政治事件对当时忠心于武后的陈子昂无异于是一次心理生理上的双重打击。这件事成为陈子昂创作心态以及诗歌风格的转折,由此萌发了对仕途的疏离感及失落感。《感遇·三十六》:“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婉妥将永矣,感悟不见之。”[5]61这首诗作于陈子昂官右拾遗之后,归隐田园之前,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忧谗畏讥、远祸全身的归隐心情。
公元696年,唐与契丹的对战节节败退,9月,陈子昂以幕府参谋的身份再次从军出征。又一次怀着“以身报国,我则当仁”的陈子昂为战事殚精竭虑、挺身急难,屡次上谏良策,却最终落得降职文官,报国无门。就在这段时期,悲愤填膺的陈子昂吟诵了那首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说,陈子昂的大半生都是在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中度过,因此他的诗中总是怀有一种命运悲歌般的忧患情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怀才不遇、理想破灭的孤愤之感。《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5]4这首五言古体诗,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借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表达了诗人壮志未酬、年华难再后理想幻灭的沉郁苦闷。作者赞美兰草和杜兰,是为了揭示它们遭受冷落的不幸命运。“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的“幽独”二字似点睛之笔,将草木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二者似乎彼此呼应。被冷落的兰若,便是诗人怀才不遇的写照,不禁让人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哀叹之感。其二是仕途艰辛、受制于人的哀鸣。陈子昂早年受武后接见,但其后的仕途并不顺畅,最后甚至因谗言被陷于囹圄。一腔政治热血也在仕途中被逐渐浇灭,《感遇》诗中便抒发了这种浓郁的挫败感。《感遇·二十三》:“翡翠巢南海,雄雌株树林。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固为累,嗟息此珍禽!”[5]40陈子昂才华横溢,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展露头角,为朝野瞩目,但在冤狱纷起,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他不能不提心吊胆。此诗托物言志,借对“灵兽”“珍禽”不幸遭遇的感慨,隐含着对自己命运的忧虑。《感遇·三十》:“朅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5]51此诗同样祖述《离骚》,托物言志,感叹势利之徒趋利得祸,多才之士却因才丧生。言外之意旨在悲叹自己仕途多舛,但却因为陈子昂怀着一种社会使命感,因此言辞饱含着一种浩然之气,具有悲怆之感。
(二) 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追求
陈子昂在《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并序》中自言:“讨论儒墨,探览真玄。觉周孔之犹述,知老庄之未悟。”可以看出他思想学问驳杂,融合了儒家、墨家、道家及佛教等思想。在陈子昂归隐后的晚年时期,其诗作中主要呈现的是对天道循环、社会交替、人的精神归宿等哲学命题的思考,这是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与遭遇息息相关的。而在其中,陈子昂受道家、阴阳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卢藏用《陈氏别传》云:“子昂晚年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3]
陈子昂的政治抱负在彻底破灭之后,于归隐前后集中作诗十余首,展现了有别于儒、墨政治理想之外的精神追求——对“道”的思考。在“天命”方面,陈子昂将人生放在天道循环的哲学视野进行思考,他认为“天道循环如日月交替、月亮盈缺,在此作用下,世间万物都处于无限循环之中。三统迭兴,五德更运,莫不如是。”[10]《感遇·其一》:“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5]3此诗前四句以日月交替代指万物都处于无穷的循环往复中,后四句言自古以来的朝代、人事兴替均乃天道使然。“幽居观大运,悠悠念群生。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等诗句也表达了同一种思想观念。在“人道”方面,面对现实挫折,陈子昂没有放弃精神追求,而是尝试着寻找自我解脱、超越的精神归宿。“黄老”之玄学契合陈子昂晚年的心境,因而其创作了许多玄晦之作。在《感遇·其八》中,诗人表现了自己对三玄的偏爱:“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窅冥”[5]13。《感遇·其五》:“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5]9此诗表现了一种洁身自好、全身远祸、绝圣弃智的老庄思想,这种思想为陈子昂处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提供了可倚靠的精神支柱,抑或称为其精神的最终归宿。
三、结语
陈子昂以其“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 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的文学理论主张以及复倡兴寄、刚健质朴的诗文风格在文学史上奠定举足轻重的地位。盛唐之前,陈子昂无论是在人格精神还是在诗歌创作上都有着别具一格的独特气质,使其在革新齐梁诗风的努力中能够取得超越初唐四杰的成就。但陈子昂的一生却是波澜起伏、“感士不遇”的,《感遇》三十八首似乎是一曲人生悲歌,书写、吟咏出了子昂生命中的那些豪侠激昂与慷慨悲怆。
[1]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
[2]陈伯海.唐诗学引论[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59.
[3]卢藏用.陈氏别传[C]//彭庆生.陈子昂诗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59-262.
[4]陈子昂.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彭庆生.陈子昂诗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6]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48.
[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6.
[9]赵男男.论陈子昂的边塞诗及其思想渊源[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41-45.
[10]张宗福.论陈子昂感遇诗的哲学思考[J].蜀学,2012(00): 34-42.
[责任编辑:岳林海]
Righteous Chivalrous Spirit and Self-lament ——Chen Zi-ang’s Idea and Practice in “Gan Yu”
WANG Shi-y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ina Police Academy, Chengdu 610213, China)
Chen Zi-ang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with his literary theory of “spinelessness, ups and downs, talent sophistication, and sonorousness and forcefulness” and his sturdy and simple poetic style. “Gan Yu” including 38 poems is of course his representative. This poem collection reflects some righteous chivalrous quality which is his idealistic persuading, and also reflects his practical emotional monologue.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interpret Chen Zi-ang’s “Gan Yu” which expresses his whole life experience in both aspects of idea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and research angles.
Chen Zi-ang; “Gan Yu”; righteous and chivalrous men; early Tang Dynasty; sense of worry
2016-07-19
王施懿(1989-),女,四川阆中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2096-1901(2016)05-0037-04
I207.22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