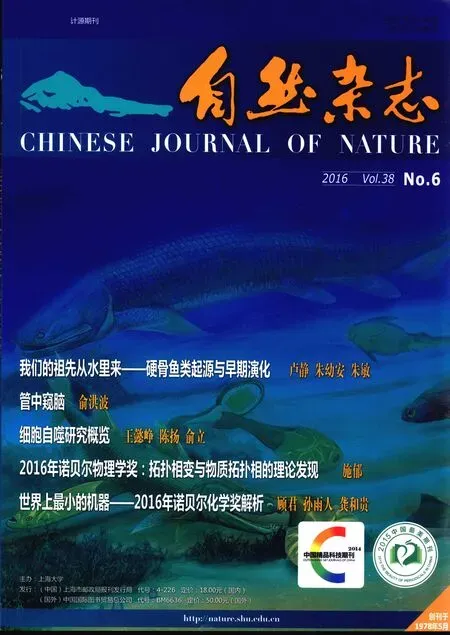近代解剖学之父
——维萨里
顾凡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近代解剖学之父
——维萨里
顾凡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解剖学;维萨里;盖伦;人体的结构
像哥白尼和伽利略这样的近代科学开创者已经为绝大多数公众所熟知,但是和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位可以与之比肩的科学巨匠维萨里,一般公众却很少听说。因此,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事迹还是很有意义的。
御医世家
1514年除夕,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图1)出生于布鲁塞尔的一个医生世家,从他的高祖父开始到他五代都是御医。说来也巧,正是在同一年,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放弃出版他根据解剖所得人体结构的画册,否则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丽的一本解剖图谱。这是因为教皇莱昂内十世(Leone X)禁止他再进行解剖,他不得不遵命放弃。他的那些素描也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世人所知[1]。
教皇的扼杀毕竟阻止不了科学的发展,维萨里完成了达·芬奇的未竟之业。时势造英雄,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欧洲人开始扬帆远航,探索未知的新世界,这催生了制绘学的兴起,一张地图比长篇描述更说明问题,印制高质量地图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亲眼目睹了一些集学者、艺术家和工匠于一身的巨匠,打破界限,对地理学和天文学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善于吸收新思想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思想。
他们家在布鲁塞尔远郊,俯瞰加洛(Gallows)山。那里是对死囚行刑之处,尸体就暴露在外,任凭飞鸟啄食。虽然这对小孩来说决算不上什么理想的环境,不过这倒也激起了他对解剖的兴趣。他把抓住的动物进行解剖,然后到他父亲的书房里找解剖学书对照。到他14岁时,他就已立志要当一名医生。15岁那年,他进入父亲的母校勒芬(Leuven)的城堡学院(Pedagogium Castrense)艺术系求学。这所学院是当时人文运动的中心,崇尚个性和独立思考,而不迷信教条。学校不仅教授当时任何有教养人士都要会的拉丁文,还教授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为他在后来可以阅读和比较解剖学书籍的原作奠定了基础。

图1 维萨里(1514—1564)(引自http://imgc.allpostersimages.com/images/P-473-488-90/72/7273/CCKT100Z/poster/sheila-terry-andreas-vesalius-belgian-anatomist.jpg)
完成学业
三年学业结束之后,18岁时维萨里到了巴黎去学习他的最爱——解剖学和医学。当时巴黎大学医学院所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是西方医圣盖伦(Claudius Galen)的著作。由于盖伦时代的罗马法律禁止人体解剖,所以盖伦只能对牛、猪和猴进行解剖观察。在他之后的1 000多年中,人们把他的著作奉为金科玉律。由于以往的译本有不少误译,因此当时又重新把盖伦的著作由希腊文译为拉丁文,这些译者中有两位成了维萨里的老师——西尔维于斯(Jacobus Sylvius)和京特(Johann Guenther)。他们很喜欢维萨里的热情,所以就让他在做解剖演示时进行实际操作。由此,他的得益比这些老师们教给他的更多,尽管他们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解剖学家。前者对制订解剖名词颇多贡献,而后者则把许多盖伦的著作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后来还在维萨里的协助之下自己写了本大学教科书。尽管维萨里很尊重他们的教导,但是由于人兽之差,盖伦的描述和维萨里亲身做解剖之所见不尽一致,这使他越来越感到苦恼。西尔维于斯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自盖伦以后人体解剖有了变化,而盖伦的话是不会错的。
1536年,在维萨里还未毕业时,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作为敌国的公民不得不逃离巴黎而回到勒芬,并在1537年完成学业。在勒芬,他认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获准进行公开的解剖演示。通过解剖死囚的尸体,他对人体的真实结构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因此也更向往当时的医学中心——意大利。
初出茅庐
帕多瓦(Padua)大学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医学院在解剖学和医学教学方面很有名声,而学校又有提倡学术自由和不受教会干涉的传统,这对于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来说自然很有吸引力。因此在他取得学位之后,他就启程前往意大利。途径巴塞尔(Basel),在当地稍事停留期间,维萨里结识了未来的印刷商温特(Robert Winter)和奥波林于斯(Johannes Oporinus)。
1537年他终于到达帕多瓦,并在同一年成了帕多瓦大学的外科教授,还负责进行尸体解剖的公开演示。此后他甚至还到远在博洛尼亚(Bologna)和比萨(Pisa)的其他单位去进行演示。他的演示大获成功,学生们蜂拥而至,复制他的解剖图。他打破了原来教授解剖的老方法:教授高坐堂上,照本宣科,朗读盖伦的“经文”;一位身兼理发匠和外科医生的操作者在堂下的解剖台上进行解剖;边上一位助手则当教授提到某处或是操作者解剖到某处时指点给学生看(图2)。维萨里对这种教学方法进行改革,集此三者于一身。正因为亲自进行了人体解剖,这才使他能看出盖伦教导的谬误之处。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盖伦的结论是根据对动物解剖所做的观察得来的,因此在一些地方和人体解剖不符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由此也培养起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如果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解剖实践或是亲眼观察,他宁肯干脆不提,也不愿轻信他人的结论。他的这一态度也遭致传统势力的激烈攻击。他们攻击他除了自己所见之外,什么也不信。
维萨里在教学上的成功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之所见所知写成一本书。他的这本书与前人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采用了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所绘制的大量图谱,这是他对解剖学的又一贡献。当时的许多医生反对插图,他们认为图画会降低学术性,并且使那些不用插图的经典著作中的深奥知识显得似乎很浅薄。他不为这些反对意见所动,1538年出版了由6幅可作挂图集成的解剖图谱《解剖图表》(Tabulae anatomicae sex),这样学生就不用为临摹他的图谱不准确所苦了。书中六幅图是有关生殖系统、血管、内脏和骨骼的大体图,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和图注。不过要完全和传统决裂并不那么容易,图谱里面依旧包含了不少盖伦的错误。同一年晚些时候,他又对他的老师冯·安德纳赫(Guenther von Andernach)(当年维萨里曾协助他进行解剖)编写的一本教科书重加编辑,改正了其中的不少错误。这本书基本上依旧是对盖伦著作的摘要。不过重编这本书也使他深入地回顾盖伦的论述,并与自己在人体解剖中之所见进行对照。这种对照使他越来越怀疑盖伦的教条,同时也越来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那就是解剖学必须基于直接的解剖观察,而不是“靠猜测和沉思默想”。这一点,他在1539年出版的《放血术通信》(Venesection Letter)中做了公开宣示。
传世之作
接下来,维萨里做了个勇敢的决定,他对维系了1 000多年的盖伦医学体系进行挑战,出版一本前无古人的解剖学图谱。他知道这需要他解剖许许多多尸体,还要组织一支卓越的画家和刻版匠师团队。为此他花了5年时间,终于在1543年完成了《人体的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该书分成7册(骨骼、肌肉、血管、神经、腹腔内脏、胸腔内脏、脑),约700页,包括200多幅插图。对此书他自始至终全力以赴,写作、研究、解剖、绘画,还要检查全部插图和木刻,还常常把一部分尸体带回家工作。书中他抛弃了盖伦根据动物解剖得到而在人体中不存在的组织;书中引用得最多的前人是盖伦,不过其中绝大多数是指出盖伦的错误。这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心。
维萨里自己也参与了部分画图,但是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所以他又找了些画家和他共同工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曾在大画家提香(Titian)处工作过的卡尔卡(Stephen Calcar)。要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共同工作并不容易,后来他回忆说:“美术家和雕刻师的坏脾气,比我要解剖的尸体更令我为难。”[2]不过得力于富有艺术修养的画家之力,其中的一些插图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还极具艺术价值。例如:其中的一幅图表示一具骨骼双腿交叉,一只手支头,另一只手摸着墓碑上的另一个骷髅,作沉思状(图3)。也许正是这张图启发了莎士比亚描写哈姆雷特和骷髅说话的情景。可能也得力于这些画家之助,他的图谱不仅显示了组织的细节,特别是一些大图还把各个部分连结成一个统一整体。也许正是这种对部分连结成整体的认识,使他在完成这一巨著之后,决定把自己的事业从解剖学转向医学。
要找出版商出版这样一本离经叛道的书也非易事,幸而当年他在巴塞尔结识的出版商帮助他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他们和维萨里一样不怕争议,就在不久之前奥波林于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可兰经》的拉丁文译本,而在一片反对声才刚平息,他又同意出版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当此书付印时,维萨里亲自到巴塞尔去照看,直到书最后出版。

图3 《人体的结构》中的一张插图(引自http://imgc.allpostersimages. com/images/P-473-488-90/22/2258/ LPWZD00Z/posters/andreasvesalius-leaning-skeleton.jpg)
不过传统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维萨里对盖伦的批评惹恼了许多盖伦的卫道士,令维萨里伤心的是在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中有他当年在巴黎的两位老师西尔维于斯和冯安德纳赫。西尔维于斯把维萨里描写成是“一个非常无知而又倨傲无礼的家伙,他无知、忘恩负义、无礼以及不知敬畏,妄自否定一切他那浅薄和疯狂的目光所看不到的东西。”[2]他还把维萨里称为瓦萨那(Vaesanus,拉丁文中的“疯子”一词和维萨里(Vesalius)拼法相近)。西尔维于斯甚至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告御状,为了他的这位前弟子毒害了欧洲的氛围而给维萨里严厉处罚。他竭力贬低《人体的结构》的价值,把这本书说成是“如果把图略去,(其内容)只要一张纸就够了,一文不值”。他的这种攻击或许并不出乎维萨里的意料,因为他在批评盖伦的解剖学时,也间接地批评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后来他在应对这些攻击时曾经说过“我的老师 (指冯·安德纳赫——引者注)除了在餐桌上之外,从来也不碰刀。”[2]事实上,说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教学思想上讲起来,和盖伦更接近的倒是维萨里,而不是以盖伦卫道士自居的西尔维于斯。盖伦也只相信解剖,甚至是活体解剖。他也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如果谁要观察大自然的作品,他不应信任解剖书而要相信自己的双眼,找我商量或者找我的同事商量都行,也可独自刻苦地进行解剖;但是如果他只是阅读书本,那么他可能相信所有早期的解剖学家,因为他们为数多得很。”[3]但是那些号称盖伦忠实信徒的卫道士们恰恰违背了祖师爷的最重要的教导。
尽管如此,《人体的结构》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意大利各地纷纷邀请他去表演解剖。有一次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去观看,甚至把演示的那天宣布为假日。为了看得清楚一点,许多人不顾危险把身子前探,有位外科医生甚至从高处的座位上掉落下来。佛罗伦萨的一位公爵甚至给他在比萨提供一个职位,不过维萨里婉言谢绝了,因为这时他已决定要返回老家。查尔斯五世在和法国的战争中急需外科医生,所以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这样他就回到了布鲁塞尔,还成家生女。到他31岁那年,无论在事业还是私人生活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
御医生涯
在此后20年中,他决心把他从尸体解剖上获取的知识用于对活人的治疗,这样他就从一名解剖学家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这样的转型并不轻松,但是他的辛勤工作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使他在医学界也迅速声名鹊起,并受到查尔斯五世的赏识。大量的外科手术和尸体解剖不断地丰富他的学识,他对解剖学的热情从未枯竭。这样在1555年他出版了《人体的结构》的第二版,其中补充了不少新发现,在叙述中也增添了更多细节。1556年他又被封为巴拉丁伯爵(Count Palatine),达到了他一生中职位的最高点。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也引起了他人的嫉妒和敌视,而赏识和提拔他的查尔斯五世又宣告退位,其子菲利普二世继位。虽然维萨里依然保持了皇家医生的职位,但是在西班牙长大的菲利普二世更愿意相信一些西班牙医生的话,而这些医生信奉的是传统的学说。因此,维萨里明白他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此后两年中由于两位经过他手的显贵不治身死,使他的敌人找到了攻击他的好借口:“他总是宣称病人已经病入膏肓,这样如果病人死了他就有了借口,而如果病人好了,那么他就创造了奇迹。”[2]
1559年菲利普二世把朝廷从布鲁塞尔搬到了马德里,维萨里也跟着去了,但是不再是作为御医,而只是给一些官员看病。更糟的是,菲利普二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制定了许多限制思想自由的法律。国王还禁止西班牙人到外国大学学习,环境迅速变得封闭起来,他还得不到尸体供其研究,因此他怀念起在帕多瓦的那些日子来了。
惺惺相惜
1561年,维萨里看到了继任他为帕多瓦解剖学教授的法洛皮阿(Gabriele Falloppia)的新著《解剖观察》(Observationes Anatomicae)。法洛皮阿在书中称赞了《人体的结构》,不过他也对书中的一些细节和自己的观察做了比较,他以维萨里之道还治维萨里其身,指出“神圣的维萨里(divine Vesalius)”所做出的某些不准确的观察,而“神圣的”这几个字正是当初维萨里用来称呼盖伦的。这年年底,维萨里写了一封长达260页的私人信件托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在回威尼斯时带给法洛皮阿。
他在信中说道:
“亲爱的法洛皮阿,三天前我从布鲁塞尔的医生埃尔托格(Gilles de Hertogh)那儿收到了大作《解剖观察》。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仅由于这本书是您写的,大家都认为您在尸体解剖以及医学的其他方面都技术高超,而且还因为这本书是由帕多瓦大学的人写的,该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我有幸作为您的前任在那里工作了差不多有6年之久……我衷心希望您能坚持研究……每当我想起我们共同的母校就感到非常珍贵,祝母校由于您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工作而进一步名声大噪。”[2]
维萨里从年轻的法洛皮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为什么他能那样大度地接受批评的缘故吧。在许多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错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些问题则遗憾地说由于在西班牙保守的气氛下他无法进行解剖学研究而不能回答。这封信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一事件更使他决心回帕多瓦重新从事学术工作。
力排众议
不过西班牙宫廷办事拖拉,一拖就是两年。到了国王终于批准他离开西班牙之后,真要走还是问题重重,尽管那些西班牙御医们竭力贬低他,但是一些达官贵人真有了大问题还得找他,这往往使他左右为难。1545年,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和皇位继承人堂卡洛斯(Don Carlos)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头部严重受伤。虽然立刻就把御医们找了来,但是几天后头部感染使情况还是不断恶化,希望渺茫。直到这时,菲利普二世才决定把维萨里召来。在怎样治疗的问题上,顿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立场:一方面是坚持盖伦传统的御医们,他们还在那里引经据典,争论不休,以致菲利普二世都忍耐不住要他们不要再引经据典而把话说明白了;另一方面,和他们对立的维萨里则根据自己的解剖学知识和行医的经验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在病人的头颅上打个小孔,减轻颅内压才是唯一的希望。开始时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但是病情继续恶化。病急乱投医,在伤口上涂上江湖庸医的油膏,结果反而使皮肤灼伤。在病人的床旁请来了去世已有100年之久的迭戈(Faiar Diego)的木乃伊化了的遗骸,据说在他生时曾创造了许多奇迹。在一片宗教狂热中,组织了成千人鞭打自己的苦行大游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采取维萨里的建议了,说来也神奇,在切开眼窝并从伤口处大量吸出脓液后,堂卡洛斯开始恢复了。这一切结果却并不归功于维萨里,反而认为这是迭戈身后显灵又一次做出奇迹!
巨星陨落
有关维萨里的最后三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很难搞清了,特别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帕多瓦,而要先去耶路撒冷。有的说是维萨里因进行活体解剖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了死刑,国王虽然赦免了他的死罪,但还是要他到圣地朝圣赎罪。还有一说是因为维萨里在这时对草药很感兴趣,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生长的药用植物。不管怎样,最后在1564年他终于离开了马德里。在西班牙和法国边界处他和妻女发生了争吵,结果是他的妻女北上布鲁塞尔,而他则继续东行。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倒真的实现了他在离开帕多瓦时所作的一则谶语:“一个献身科学的人决不要讨老婆,因为他不能同时忠于两者。”他取道威尼斯,可能是为了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求他们的帮助重获在帕多瓦大学的职位。他还在一个书店里会见了一些著名医生,他们谈到他托威尼斯大使带给法洛皮阿的信,由于法洛皮阿过早去世,这封信还在大使处,大家都想要份副本。店主答应在从大使处拿到此信后就把它印出来人手一份。
他在巴勒斯坦停留了4个月,他在那儿对搜集当地植物的兴趣要远高于做祷告。到1564年夏他终于准备回威尼斯和帕多瓦了,但是就在归途的船上他一病不起。也有说是因为翻船随后经逃生免于葬身鱼腹,但是还是因此得病,结果葬在了希腊的扎金索斯(赞特) [Zakynthos(Zante)]岛上。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543年一年里出版了两本为后世带来革命性影响的科学巨著——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前者推翻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宇宙;而后者则纠正了盖伦的许多谬误,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两者都是给教条主义传统的沉重打击,开创了通过观察和实践进行科学探索的新时代。在达·芬奇不得不舍弃了他的解剖图稿的同一年里诞生了维萨里,而在维萨里去世的那年里,伽利略诞生了,他后来也成了帕多瓦大学的教授。正是伽利略创造了实验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直接观察以及对现象的定量化。而现代医学正是建筑在维萨里的解剖学方法和伽利略的定量方法之上,观察和实验开启了现代科学发展之路[4]。
(2016年9月5日收稿)
参考文献
[1] 陈宜张. 探索脑科学的英才——从灵魂到分子之路[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2] CATANI M AND SANDRONE S. Brain renaissance: From Vesalius to modern neuro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FINGER S. Origins of neuroscience: A history of explorations into brain fun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WICKENS AP. A History of the brain: from stone age to modern neuroscience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5.
(编辑:段艳芳)
Founder of modern human anatomy—Andreas Vesalius
GU Fanj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natomy, Vesalius, Galen,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10.3969/j.issn.0253-9608.2016.06.010
†通信作者,E-mail: fjgu@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