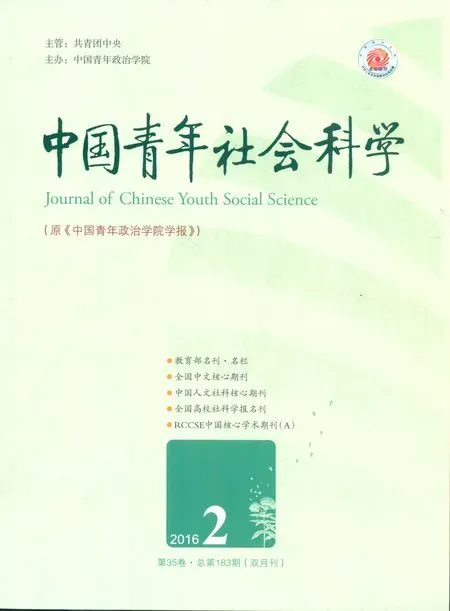郭象对魏晋文人时间意识的玄学思考——兼论当代青年超越迁逝之变的智慧
■ 刘国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100089)
郭象对魏晋文人时间意识的玄学思考
——兼论当代青年超越迁逝之变的智慧
■ 刘国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100089)
【摘要】郭象认为,在断裂的时间之流中,生死之变、事物之变、人生前后情境的变化不能相通和理解;主体要“忘先后之所接”,忘记前境、后境,而完全沉浸于当下情境中;“见独”,即在时间上割断当下情境与前后情境之间的联系,保持知觉对当下情境孤立化和集中化的反映;既不忆念前一情境,又不预想后一情境,不会有因情境的不同而产生的计较之心、得失之念、悲喜之情;主体与当下情境深相契合而安乐,才能真正顺应人生各种情境的变化;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则能齐生死、超越生死。
【关键词】魏晋文人郭象当代青年超越迁逝
一
青年正处于人生之途的展开之际,面临着人生各种情境的迁变与生死之变,如何超越之,不仅有哲学的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魏晋文人置身于断裂的时间之流中,追忆过去,展望将来,“向死而生”,不能顺应生死之变和人生情境的前后迁移,从而产生浓烈的迁逝之悲。
《庄子·德充符》之谓“死生亦大矣”。郭象注曰:“人虽日变,然死生之变,变之大者也。”[1]人生会遭受各种变化,生死之变是最大的变化。如何对待人生情境的各种迁变与生死之化呢?相对于童年少年人的懵懂不知与中年老年人的不惑、知天命,这是青年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生之途的展开之际。本文将着重讨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对人生迁逝意识的哲学思考,为当代青年提供超越生死和情境迁移的知识和智慧。青年在本质上是“革命”“革新”的,似与“古典”有一种天然的不和。但在当今“回归古典”的思潮下,也有很多青年人爱上古典,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现代和将来的语境下,扬弃已经失去活力的旧传统,发明新传统。因此,古典与青年的辩证关系是,青年的革命、革新动力驱使古典传统永远发生着回复的转变与更新,而古典传统的强大制约力与凝聚力保证青年人能“发而皆中节”(《中庸》),能有征而信。
建安诗人王粲《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诗人遭遇乱世而辗转迁徙他乡,至今超过十二年了,怀念故土和亲人而思归的感情,谁能承受得了呢?诗人表现出强烈的迁逝之悲。
西晋文人陆机《叹逝赋》:“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川之为川,因水的存在,水日日流逝;世之为世,因人的存在,人渐渐地衰老。每一世都是新的,因为每一世的人都是新的。每一世都是新的,但人生一世,何人能长久地留存呢?在人类代代绵延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时空永恒,生命短暂,构成人生的深沉悲伤,这是魏晋诗文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迁逝,即指空间的迁徙和时间的流逝。时空二维与人的生活和生命相结合,构成了人生的各种情境。在人生情境之变与生死之化中,时间具有优先性。时间意识的产生源于自然和人事的变迁。若自然和人事的变化缓慢,则我们可从过去、现在、将来中体悟时间流逝的连续性、变异性。在连续性中,现在的人事含有过去的因素,将来的人事是从现在基础上的合理发展。在变异性中,我们发现自然和人事的异质因素,且对将来的可能性寄予新的希望。
因此,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绵延的时间之流,人事流变使新旧事物相互渗透而打成一片。在绵延的时间之流中,我们的迁逝感不强。若自然和人事的变化急剧,过去很快消亡,现在转瞬即逝,将来不可预知,则过去、现在、将来之间发生了断裂。
在断裂的时间之流中,一方面,我们深感时间的匆匆流逝;另一方面,我们也证成人事变迁的非理性和荒诞性。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之一。这引发了魏晋文人强烈的时间迁逝意识。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2]王锺陵说:“在时人忧患百端的种种思想感情之中,迁逝感最为惊人心目。”[3]魏晋文人置身于政治人事的剧烈变化之中,过去、现在、将来是断裂的。在断裂的时间之流中,一方面,他们基于现在,而展开对过去的追忆;断裂中的今昔对比,亲人故友一一凋零,往日的繁华变成今日的憔悴,像梦一样的虚幻,令人感慨和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基于现在,展开对将来的筹划;断裂中的展望将来,将来的到来具有非理性、偶然性的特征,非自己所能预知和把握,像梦一样的神秘,令人恐惧和焦虑;再一方面,他们形成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死先行到生中,在生中,时时想到死亡的即将到来,从而产生一种畏惧和焦灼的情绪。对死亡主题的咏叹,本来是人之常情,但在魏晋的诗文中尤为突出。
一是动乱时代中的死亡哀鸿遍野,惊心动魄。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蔡琰《悲愤诗》“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二是动乱时代中的人事变化急剧,时间流逝迅速,本来就很短促的生命变得更加短促。时光飞逝与生命短促是相统一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在治世中,正命而死及死后的荣辱之名,本人是可大概预知和把握的,但念死尚不能安生。在乱世中,死亡的到来是无常而非理性的,死后之事及其荣辱之名并非自己所能作为,“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拟咏怀》)。
魏晋玄学的兴盛自有时代的意义。对魏晋文人普遍的时间迁逝意识的哲学思考,是其重要的意义之一。庄子的“物化”“齐生死”“坐忘”等观念,是玄学应对和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的《庄子注》,在对《庄子》文本的解释中,发挥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和生死观,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庄子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又着力消解魏晋文人因时间迁逝而产生的悲苦、畏惧和焦灼的情绪。
二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人事的变化异常迅猛,时间的流逝也异常急剧。庄子的迁逝之感非常强烈,《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一般而言,人处在变化之流中便不稳定,难以立足立身。老子以形上之道为本原,是为变化不居的万事万物,寻找一个不变的立足点,即“常”。庄子逐渐消解老子形上之道的观念,但也企图追寻事物和时间发生的始点,以始点的永恒不变来应对变化。《齐物论》:“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找不到事物的始点,宇宙和社会是无始无终,处于永恒的变化之流中。《山木》:“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既然不变的始点(基点)并不存在,那么只有委身于变化之流中,而不知其所终始。
郭象《庄子注》发挥庄子关于事物变化之无始无终的思想。他说:“与日俱新,故无始也”(《在宥》注),“世世无极”(《知北游》注),“于今为始者,于昨为卒,则所谓始者即是卒矣。言变化之无穷”(《山木》注)。宇宙和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开始,而是无始无终的永恒变化。所谓开始,不过是相对的,这个事物是开始,另一个事物是结束。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量变是事物在数量和程度上逐渐、不显著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事物变化的断裂。
庄子之“物化”包含量变和质变,但郭象明确认为,事物之变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质变。质变说明事物变化得显著和剧烈,割断了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展示了时间迁逝的急速和断裂。这正是对魏晋时代社会政治人事之断裂剧变的哲学反映。
郭象《养生主》注曰:“夫时不再来,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纳养而命续;前火非后火,故为薪而火传,火传而命续,由夫养得其极也,世岂知其尽而更生哉!”[4]事物之变与时间之流永不停息。昨日之我,于今已尽;今日之我,更生于后。向息与今息、前火与后火截然分别,其迁变是断裂的质变。
郭象《大宗师》注曰:“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觉,遂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岂不昧哉!”[5]郭象对“变化”的认知和感受非常突出。天地万物无时不变,其变是舍故趋新,向者已经消亡,今者转瞬即逝,皆不能留存;但世人怀旧念故,执守今之所遇,不能顺应变化。“向者之我非复今我”,割断了向我与今我之间的联系。
郭象《田子方》注曰:“唐肆,非停马处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复得也。人之生若马之过肆耳,恒无驻须臾,新故之相续,不舍昼夜也。著,见也。言汝殆见吾所以见者耳。吾所以见者,日新也,故已尽矣,汝安得有之!”[6]向者之有,已灭于前;求之于今,不可复得。
要之,郭象认为,事物之变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质变,其变化是断裂的;时间之流基于事物的迁变,过去、现在、将来也是断裂的;处于断裂的时间之流中,前后事物皆没有相通和理解的可能。
《齐物论》:“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庄子认为,生则不知死:当生时,你总以为死是痛苦和可怕的;到死后,你才真正知道死是快乐的。庄子以之破除世人悦生恶死的观念。
《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以梦觉譬喻生死的相异和不可相知。郭象予以推扩:“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于其间哉!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8]
郭象认为,事物的前后变化急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能通过过去的事物了解现在的事物,也不能通过现在的事物预知将来的事物。人生的前后情境,如同生死梦觉,是“今不知前”“今不知后”。庄周梦中变成蝴蝶,根本不知其前(未入梦)曾是庄周,也不知其后(觉醒)将是庄周。因此,梦前的情境、梦中的情境、梦醒的情境是断裂的,则基于事物变异的时间之流也是过去、现在、将来的断裂。
郭象的断裂迁变思想,与其自生和独化的观念相联系。事物的变化不是由某一事物变成另一事物,而是事物本身的自生和独化;事物的变化是自主的,是本性所决定的,不是凭借他物之“所待”而成,因而本事物与他物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彼此相互独立。自生和独化之思想皆强调事物本身的独立自主性,而不重视事物之间彼此的联系。例如,郭象对生死之变的理解:死不是生的变化,死是自己的变化;生不是死的变化,生是自己的变化;故生与死各自成体,彼此独立而不能相知。郭象《知北游》注曰:“夫死者独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也独化而生耳”,“死与生,各自成体。”[9]就人生的不同情境而言,前一情境是完整独立的,后一情境不是在前一情境基础上的发展,而是新的完整独立的情境,故前后情境截然分别。
要之,郭象认为,生死之变如同人之梦觉,如同人生的前后情境,皆彼此独立断裂而不能相知。
三
面对无始无终的事变之流,庄子主张委身其中而顺应之。《逍遥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乘天地之正即顺应任何事物的本性,御六气之辩即顺应任何事物的变化,故能游于无穷。《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顺应生死得失之变,不悲不喜。
人生之变,莫大于生死之变。我们最不能忘怀的,是生命的短促与死亡的恐惧。郭象《则阳》注曰:“今所以有岁而存日者,为有死生故也。若无死无生,则岁日之计除。”[10]岁日等计时名词的出现,是因为有生死之变。
如何要顺应生死之变呢?庄子首先认为,生与死虽是不同的事物,但皆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大宗师》谓“死生存亡之一体”。庄子再次认为,人的生死同昼夜一样是天,是命,不可抗拒,因而不得不顺应。庄子其次认为,世人之悦生恶死,主要是不了解死,以为死很痛苦可怕,实际上死有至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安慰说,天地善待吾生,也会善待吾死,因而不必恐惧死亡。《至乐》中有一个寓言。庄子到楚国去,路上遇到一个空骷髅,而怜悯其死亡,且追问死亡之因。半夜,骷髅现梦大谈生之痛苦,死之快乐,“虽南面为王,不能过也”。庄子以死的至乐来消解世人恶死的观念,从而顺应生死之变。
庄子主张“齐生死”,要顺应生死之变。但如何能顺应生死之变,即顺应生死之变的方法是什么?庄子并未说明,郭象则展开了自己的思考。“旧说云庄子乐生恶死,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至乐》注)”[11]郭象之谓“齐生死”有独特的内涵。生时安生,即生时忘死,因忘死而不会忧虑死,也不会计较生死的得失,因忘死而忘其对立面——生,则忘死忘生;因忘死忘生,而完全沉浸于当下之“生”(没有“生”的观念即指当下情境)中,与当下之“生”的情境相融相合而为一,故能真正地安生、乐生。死时安死,即死时忘生,因忘生而不会恋生,不会计较生死的得失,因忘生忘其对立面——死,则忘生忘死;因忘生忘死,而完全沉浸于当下之“死”(没有“死”的观念,即指当下情境)中,与当下之“死”的情境相融相合而为一,故能真正地安死、乐死。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则顺应生死之变,齐生死而超越生死。
恩格斯说过,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可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时代性和运动性,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前人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丰富、不断充实、不断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筑建了安定有序的社会文化环境。
郭象在《齐物论》注中充分阐释其齐生死的观念,即“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12]“故生时乐生,则死时乐死。死生虽异,其于各得所愿,一也,则何系哉!”[13]“由此观之,当死之时,亦不知其死而自适其志也。”[14]“当所遇,无不足也,何为方生而忧死哉!”[15]
“众庶冯生”(贾谊《鵩鸟赋》),众人贪恋生,尽管生活艰辛困苦;他们一般很少想到死,似乎死是遥不可及的事,而活得有滋有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君子自觉意识强烈,“向死而生”,生时忧虑死的到来,感慨生命的短促,追求死后的不朽荣名,因而颇不安生,活在忧惧之中。曹丕、曹植、阮籍等魏晋文人不能做到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而产生深重的迁逝之悲。不能生时安生,则生时痛苦忧惧,不能享受生的乐趣,且不能做好生时之事,生命的时间历程也会缩短,死亡将加速到来。魏晋文人多早衰、早死。例如曹丕(187-226)活了39岁,曹植(192-232)活了40岁,王粲(177-217)活了40岁,徐干(170-217)活了47岁。
概之,郭象认为,置于断裂的生死之变中,最好的处世方式是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进一步推扩到人生不同的情境中。置于某一情境,即忘记前后的情境,完全沉浸于此一情境中,与此一情境相融而安乐。因为人生的不同情境断裂而不能相知,对前后情境的追忆和展望,会阻碍主体对当下情境的实现。
《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女偊年长而色若孺子,是因闻道。闻道的功夫修养,是能忘。“外天下”,“外物”,“外生”,即忘天下,忘物,忘生。一切皆忘,内心虚静。内心虚静,无心应物,不悲不喜,故能活得久长。
郭象在庄文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深度解释:“当所遇而安之,忘先后之所接,斯见独者也。”[16]
所遇而安,遇到某一情境,则安于此一情境。“忘先后之所接”,置于某一情境,则忘记前后的情境,即斩断当下情境与前后情境在时间上的连接,主体既不忆念前一情境,又不预想后一情境,不会有因情境的不同而产生的计较之心、得失之念、悲喜之情,而完全沉浸于当下情境中,与当下情境深相契合而安乐。“见独”,即主体的知觉因完全孤立、集中于当下情境,而当下情境也被孤立化、集中化,故主体的全部精神和行为,都被吸入于当下情境之中,而感到当下情境即是存在的一切。郭象注曰“与独俱往”[17]。即忘前后情境,而完全沉浸于当下情境,割断时间前后的绵延,没有过去与现在的分别观念,也没有现在与将来的分别观念,只有现在,现在即成为永恒,这就不会产生时间流逝的观念,即庄子谓“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能入于不死不生”。
郭象认为,主体忘前后情境而冥合于当下情境,才能见独,与独俱往,真正地顺应各种情境的变化。《齐物论》注曰:“唯大圣无执,故芚然直往而与变化为一,一变化而常游于独者也。”[18]《在宥》注曰:“坐忘而任独。”[19]游于独者,才能直往而与变化为一;《人间世》注曰:“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间之变,应乎当世之节者,未之有也。”[20]
生死之变、人生情境的前后迁移,皆如同梦觉。《齐物论》中有“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寓言。庄子在梦中变成一只蝴蝶,栩栩然,自得其乐。其关键是他不知自己曾是庄周,也不知他还将变成庄周,即前后皆忘。他当前只知自己是蝴蝶,其他一无所知,知觉完全孤立化和集中化。从时间流逝上加以思考,庄子忘记入梦之前的情境(醒),也忘记梦醒之后的情境(觉),因没有醒觉的观念,也没有梦的观念,而忘梦醒觉,故完全沉浸于现在的情境而自得安乐。庄子慨叹:“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由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齐物论》)否则,庄周梦为蝴蝶,知道自己曾是庄周,必有计较之心,而不能安于当下的蝴蝶,不会“自喻适志”。这即是郭象谓“忘先后之所接”。
在郭象看来,事物之变是以故代新的质变,人生的迁变是前后情境的推移;不同事物和前后情境之间皆各自独立成体,不能相通和相互理解,即是断裂的;基于自然和人事变化得时间之流也是断裂的。置于断裂的时间之流中,主体不要追恋过去,也不要展望将来,而完全沉浸于当下现在,即只有现在而没有过去和未来。
《人间世》注曰:“当顺时直前,尽乎会通之宜耳!趣当尽临时之宜耳。不瞻前顾后,而尽当今之会,冥然与时世为一,而后妙当可全,刑名可免。”[21]《田子方》注曰:“不系于前,与变俱往,故曰徂。夫变化不可执而留也,故虽执臂相守而不能令停。”[22]顺应时变,与当下的情境完全相合而相宜,“尽乎会通之宜”。“不瞻前顾后”,“不系于前”,既不追忆过去,也不展望将来,而完全沉浸于现在,“而尽当今之会”。《德充符》注曰:“夫命行事变,不舍昼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随所遇而任之。夫始非知之所规,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变者,岂于终规始,在新恋故哉?虽有至知而弗能规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23]
顺应事变,随遇而安,即完全沉浸于现在的事变和情境中。事变的相对开始,已经逝去,非自己所能留存;事变的相对结束,尚未到来,也非自己所能预知和支配,“岂于终规始,在新恋故哉!”
《齐物论》注曰:“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夜之功,见弹而求鸮炙之实也夫。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辨非,皆逆计之徒也。”[24]不能安于当下情境,而探求将来的变化,如见卵则思鸡将来之报晓。这是“逆计之徒”,不能顺应变化而安乐的。
庄子重视“忘”的智慧。《大宗师》记述了颜回达到“坐忘”的人生境界。坐忘境界的实现是从外到内、从易到难,一步步地忘,“忘仁义”,“忘礼乐”,“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最后“同于大通”。忘是舒适和自由的表述,忘得愈多,束缚愈少,自由愈多;一切皆忘,内心虚静;内心虚静,则无心无意地应对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郭象注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25]
《德充符》注曰:“都忘宜,故无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26]郭象深入地阐发庄子之忘的智慧。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忘先后之所接”,而与当下情境融合为一。融合为一,则在空间和时间上斩断当下情境与周围、前后情境的一切联系,以达到知觉的集中化、孤立化,即“见独”。
综上而述,魏晋文人置身于断裂的时间之流中,追忆过去,展望将来,向死而生,不能顺应死生之变和人生情境之变,从而产生深重的迁逝之悲,加速他们的衰老和死亡,也使他们因不安现在而未能合理地处理当下的各种事情。郭象时间观的基本内容:
第一,自然和人事的变化是急剧的,基于其上的时间流逝是迅速的。郭象正是从自然和人事的迁变中理解时间的流逝,这揭示了时间存在的本质。
第二,自然和人事的变化是无始无终,以新代故;其变化是质变,因而前后并不存在联系,不能相通和理解。过去的人事一去不返,现在的人事很快会成为过去,将来的人事不可预知和把握。因此,时间不能构成绵延之流,时间之流的过去、现在、将来是断裂的。
第三,置于断裂的时间之流中,主体“忘先后之所接”,而“见独”、“与独俱往”;主体才能安于、乐于、足于当下情境,真正做到生时安生,死时安死,从而顺应人生情境的迁移与生死大变,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物不游,“同于大通”(《大宗师》)。
郭象之顺应人生情境的迁变与生死超越的哲思和智慧,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且对正在走向人生之途的当代青年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青年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能顺应各种人生情境的迁变。青年人正置身于变化之流中,要明白顺应变化并非是随波逐流。根据郭象的观点,青年人要立足于当下的情境,安于、乐于当下的情境,从而与当下的情境相融合,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处理好当下的各种事情。生死之变是人生最大的变化,郭象并不赞成青年人“向死而生”,从而对死亡产生强烈的畏惧之感,不能安于活着的人生,心不在焉,而不能很好地处理当下的各种事情。要之,青年人要立足于当下,割断当下与过去、将来的联系,从而一心一意地沉浸于当下之中。
[ 参 考 文 献 ]
[1][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南华真经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1、72、143-144、407、53、58-59、435、504、362、34、53、53、53、148、148、52、84、223、98、407、123、51、163、113页。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3]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责任编辑:任天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般项目“时间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意表现”(课题编号:189008033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国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
收稿日期: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