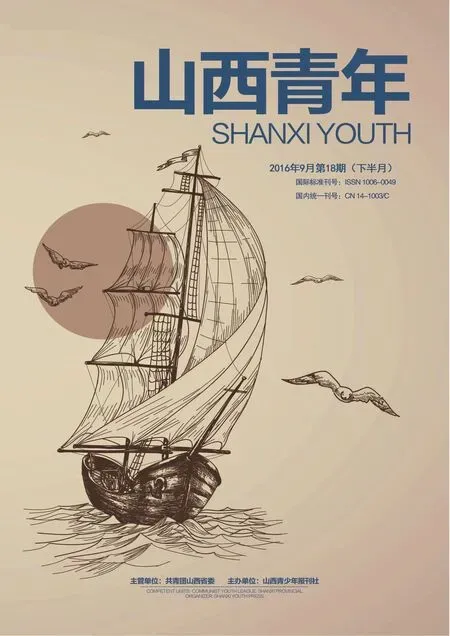我笔写我心*
——从身份立场看唐朝诗歌流派
王雪凝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我笔写我心*
——从身份立场看唐朝诗歌流派
王雪凝**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850000
唐朝诗人流派众多,而传统的流派划分并不能将诗人们尽数概括,若从诗人的身份立场角度来划分诗人群体则能将涵盖范围扩大很多。试设定宫廷诗派、士人诗派和布衣诗派三个大的群体,在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这三个群体都相应地有着不同的创作特点,本文试通过这一角度总结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梳理唐朝诗歌的脉络。
唐诗;流派;宫廷;士人;布衣
唐诗流派的划分存在不同角度,例如山水田园派与边塞派是后人针对诗歌内容风格提出的,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则是创作者因相同创作理念聚集形成的。这些流派的划分有其相当大的优势存在,但笔者认为不可因此忽略其缺点:即其针对的对象有限,譬如李白、杜甫此类的大家很难被归纳进去。唐朝诗人创作的一大特点是,他们往往是基于自己政治人的性质,而不是纯粹意义的诗人(不仅唐朝,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也鲜少有纯粹的诗人,而唐诗的政治伦理性表现得尤为强烈)。笔者尝试通过诗人的身份立场对诗人进行群体划分从而对相应诗人的作品流派做一归纳,希望能从这一角度对唐朝诗歌做一整体分析。
袁行霈先生在《唐诗风神及其他》一书中,将盛唐诗人分为三大类:宫廷中的诗人、在地方担任官职的诗人、在野诗人,每一大类中又可分出若干小类。[1]现试借鉴这一概念,将其扩展到整个唐朝,以传统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划分作为研究的时间段,考察各个时期的宫廷诗派、士人诗派和布衣诗派的创作情况。
一、初唐
初唐大致是指公元618年-713年,即高祖武德至玄宗开元初。初唐是唐诗的准备阶段,最初是南朝绮丽的形式文学的延续,后期逐渐显露唐音之象,近体诗的形制也得到了确立。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体主要集中在宫廷诗派。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身边文人促进了南北方诗风的融合,他们中有如虞世南、陈叔达、袁朗、褚亮、谢堰等直接接受过南北朝文风影响的“三朝元老”,也有由隋入唐的如杨师道、许敬宗、孔绍安、陈子良、李百药等“两朝元老”。这些老臣的诗歌中体现出浓厚的御用风气,多是应制诗、奉和诗,如“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孔绍安《落叶》),他们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贞观、龙朔年间,上官仪崭露头角,风格绮错婉媚,形成了“上官体”。这类诗无论是应制奉和的写作目的,还是歌功颂德、体物图貌的写作内容,都带有深刻的贵族文学的烙印。得益于上官仪提出的“六对”、“八对”等名目,诗歌的形式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高忠、武后时期,出现了以“文章四友”、沈宋为代表的台阁体,内容依旧是应制酬唱、咏物赠别。在诗艺方面,沈佺期、宋之问对永明体进行了改进,完成了五律的定型。在中宗景龙年间,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又完成了七言律诗的定型。初唐的宫廷诗派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诗派,诗歌内容思想上未有大的建树,主要成就在于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初唐也逐渐开始涌现出一批才高官微的士人诗派。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后世并称为“初唐四杰”,他们“行为脱俗而浪漫,遭遇悲惨,……其诗作的内容则楔入社会实际及世俗人情,诗风世俗化、人间化,给诗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2]四杰在作诗方面强调抒发一己之情怀,反对纤巧绮靡,把诗歌写作的范围从宫廷拓展到了民间,王、杨二人更是将创作题材移到了江山与塞漠。陈子昂的创作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复古意识,处处体现着“达则匡救于国”的忠义立场,被杜甫赞为:“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初盛唐之际,张若虚、刘希夷在创造意境方面独具特色。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这首咏物诗融入了诗人对生命的体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被闻一多盛赞为“宫体诗的自赎”。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意境与此相近。初唐时期的士人诗派创作在宫廷诗派奠定的诗歌体制中耀眼的亮出了个人意识的风采,将诗歌题材引导向社会现实生活,更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全新诗境。他们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做了突出贡献。
相比而言,初唐的布衣诗派则显得人丁单薄,则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王绩。他在隋唐之际三仕三隐,终在“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的喟叹中远离了官场。王绩诗作不多,但其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风格在初唐独树一帜,是唐朝隐逸诗风的发端。
二、盛唐
盛唐大致是指公元713年-766年,即玄宗开元年间至肃宗宝应。盛唐是唐诗的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诗人和诗歌涌现,艺术水平达到巅峰。士人诗派与布衣诗派的争奇斗艳是其主流。
盛唐宫廷诗派以唐太宗为领袖。太宗现存诗60余首,“其诗不再(或者说几乎没有)以后宫女性为重点,以享乐生活为重心,而是题材广泛,格力雄壮,从宫廷扩展到了外部世界,表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思想取向与胸怀气度,诗艺上也达到较高水平,为当时的文臣树立了榜样。”[3]聚集在太宗周围参与文学活动的朝廷重臣主要有张说、苏颋、张九龄、贺知章、裴淮、徐坚、许景先、席豫、徐安贞、孙逖等人。这些学者型的诗人更擅长于文章,其诗也有不少是御用诗或应酬诗,承续初唐的宫廷诗风,但多了一些刚健气。
盛唐的士人诗派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是主要的创作队伍。“唐诗的基本作者是通过考试途径进入上层建筑领域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4]这种情况到了盛唐之后表现的最为明显。盛唐士人诗派包括李邕、房琯、王维、张子容、常建、储光羲、李颀、祖咏、阎防、薛据、王湾、卢僎、綦毋潜、王之涣、王翰、崔颢、王昌龄、张谓、高适、岑参等。这时期的士人诗派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权力中心,在长安或较富庶地方为官,以王维为代表,相对于宫廷诗人来说,他们的诗作包含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生活层面,除了表现薄宦之悲,也有寄情山水、向往隐逸的作品;不过这类士人较少关注民生和社会矛盾。另一类则是游宦于各节度使幕中,有过边塞生活经验的诗人,以王之涣、高适、岑参为代表。盛唐开元四年至天宝末年有边塞诗传世的诗人共71位[5],他们几乎都是具有北方阳刚气质的豪侠才士。其诗歌多展现边塞风光,歌颂将士、反映战争、抒发抱负,格调雄浑豪放、壮阔大气。盛唐士人诗派的诗人虽多有屈原“发愤以抒情”之意,但对大唐帝国并未绝望,往往身处逆境而不气馁。
盛唐的布衣诗派人数不多,以孟浩然、李白、杜甫为代表。他们即便偶有为官,也流离在权力核心之外,总体来讲都是属于布衣身份;这不仅是后人的评断,也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孟浩然有着“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求仕欲望,但囿于种种因素一直隐逸。他的诗歌单纯明净,语淡味浓,其山水田园诗勾勒的平淡清远为后来的不仕之人推崇,成为继陶渊明之后又一描摹隐逸之乐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并称为大唐时代的“双子星座”,他们的诗作或尖锐或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混乱和人民的困苦,不同的是李白深受巴蜀文化影响,其诗作中自我意识明显,充满着狂放不羁、想象恢弘的浪漫主义气息;而杜甫奉儒为业,其诗作中忠君爱国与悯时伤民融为一体,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风格。在艺术形式上,李白的歌行与乐府具有蓬勃向上的阳刚之美,其绝句往往又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俊逸。杜甫的最高成就则在律诗上,形成了出神入化的浑融境界,被认为是集大成者。盛唐布衣诗派的诗人数量不多,但地位不容忽视。这些诗人虽然基本上未能进入仕途,但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们对各种社会矛盾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又遭遇坎坷,故而他们的诗作能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他们的创作,体现了盛唐诗坛的最高水平。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中呈现的时代风格。”[6]盛唐三大诗派的诗人们鼎力创作,形成了盛唐气象。
三、中唐
中唐大致是指公元766年-836年,即代宗广德初至穆宗长庆年间。中唐是唐诗的转变期,安史之乱使中唐诗人失去了盛唐的昂扬,转向细致省净。韩孟与元白的出现激起了新的浪潮,形成唐诗的又一高峰。
中唐的宫廷诗派几近衰落,可看作是初盛唐宫廷诗派的余绪。贞元、元和年间,历任要职的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形成了交往唱和之风,这批台阁诗人的酬唱应答之作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但却促进了“元和体”的形成。
中唐的士人诗派体现了转折的意味。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韦应物可算是一代表。早期的韦应物也曾写下“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这类带有明朗的盛唐余韵的诗句,而在后期,这种慷慨为国的意气全然被隐逸遁世的心理所取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种孤独与冷漠几乎是大历年间诗人的通性,例如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诗歌主要描写生活琐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清冷的孤独情怀,常是有佳句而无佳篇。在这冷落萧瑟的主流之外,还有两位独具特色的诗人:偏爱通俗明快的乐府的顾况以及善写壮烈慷慨的边塞诗的李益。元和年间,名家辈出,韩愈在诗歌方面提倡“不平则鸣”和“笔补造化”,看重创造性的诗思,他与孟郊领导的韩孟诗派走上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之路。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则重写实、尚通俗,其中张籍、王建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对新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元白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文学史上有两个名词:“元白体”和“元和体”。“元白体”是指在元稹、白居易领导下的通俗化、写实性的诗歌,多叙写时事来反映时代主题,例如《长恨歌》、《暮江吟》。“元和体”诗歌以叙写闲情雅趣、思念问候为主,创作者都是朝廷官吏,如刘禹锡、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等,但政治热情几乎消失不见。当韩孟元白等人活跃在诗坛中心时,刘禹锡、柳宗元在穷僻荒远的贬谪之地也在进行独特的创作。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他们的诗歌主要书写怀才不遇的苦闷和不肯辱志的执着。中唐士人诗派的创作带有明显的为官者的意识,无论是韩孟强调的“不平则鸣”还是元白倡导的“补察时政”,都是一种为国为民的思想的体现。同时,士人间也不乏闲适的唱和和苦闷的贬谪。
中唐布衣诗派的成分比较单纯,从风格上来讲基本属于韩孟诗派,比如一生未仕的卢仝、任侠重义的刘叉等,他们存诗不多,但都表现出明显的险怪倾向。此外还有因讳父名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的李贺,他的诗作追求凄艳诡激,注重内心世界的挖掘和主观化的幻想,是真正的“不平则鸣”。
四、晚唐
晚唐大致是指公元836-907约七十年的时间段,即敬宗宝历初至唐亡。晚唐是唐诗的衰落期,晚唐诗人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已然再不能达到盛中唐时期的高度。
晚唐的宫廷诗派几乎不复存在,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宫廷中人已无意进行自觉的诗歌创作。
晚唐的士人诗派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仍旧心怀天下,作诗抒发理想不得实现的苦闷和对国计民生的担忧的诗人,例如怀古咏史、吊古伤今的杜牧和许浑,关注乱离、感慨深沉的郑谷和韦庄,以及通俗快露、讽刺现实的罗隐;另一类是寄情闺阁,从男欢女爱上寻找慰藉的诗人,例如善写华美秾丽的情爱诗的温庭筠、善写绮艳轻靡的香奁诗的韩偓和吴融。深受朋党之争连累的诗人李商隐,算的上是唐朝诗人的最后一位大家。他有着不下百首的颇具锋芒的政治诗和咏史诗,同时也有凄艳浑融、朦胧缥缈的抒情诗,他诗歌的多义性已成为近来研究的热点。
晚唐的布衣诗派是感情基调最为沉重的一个流派。苦吟诗人贾岛、姚合及其追求者均是对社会关心不够,阅历范围狭窄的诗人,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隐逸诗人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则平安闲放,尽量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闲适恬静。
[1]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
[2]张碧波.论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三次美学论争——兼及唐诗流派兴衰演变规律问题的探索[J].文学遗产,1985(2):39-50.
[3]丁放,袁行霈.宫廷中的诗人与盛唐诗坛——盛唐诗人身份经历与创作关系研究之一[J].文学遗产,2009(1):29-41.
[4]汤贵仁.关于唐代诗歌阶级基础的几个问题[J].文史哲,1980(3):36-42.
[5]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J].文学遗产,2002(3).
[6]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J].高校理论战线,1998(12):32-39.
I207.22
A
1006-0049-(2016)18-0013-02
*2016年西藏大学文学院教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612)。
**作者简介:王雪凝(1993-),女,西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