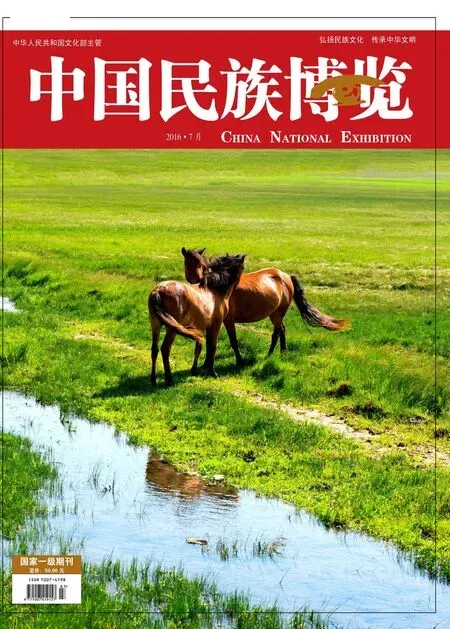凉山彝族婚姻聘礼问题初探
沈秀荣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凉山彝族婚姻聘礼问题初探
沈秀荣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自现代化的宏伟叙事拉开帷幕以来,凉山彝人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作为彝族传统婚姻制度重要组成的婚姻聘礼亦呈现异化之态,高价聘礼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在“高价聘礼”背后,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自处的问题引人深思。
聘礼;凉山;彝族
约在春秋时代中期,曲涅、古侯两支彝族先民从云南昭通渡金沙江迁入凉山,开启了彝族在凉山地区两千多年的繁衍生息。群峰横亘的自然环境使凉山处于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状态,为原生民族文化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历千年日月,凉山彝族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彝族习惯法,彝语称“简伟”,是凉山彝区最高权威的法律形式,调整着每一个彝人由生到死的全部过程。而婚姻,不论对于个体或群体,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自然成了习惯法重点规范的对象。凉山彝族的婚姻制度包括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聘礼立婚等内容。聘礼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与标志,从古至今都活跃在彝人的婚姻之中。笔者认为,它本身于婚姻立与破的重要性、它的变化与命数、人们对它的维护褒扬或口诛笔伐……都值得关注和深究。通过它,人们或许可以窥见一个少数族群的传统如何在现代性中求生,一个少数族群拥抱现代性时混沌、艰难的情感认同。
一、婚姻聘礼的渊源
聘礼,彝语称“乌惹者”,通常经议婚双方的“夫呷”(媒人)商定后,在婚礼前或婚礼时,由男方送至女方家中,至此,婚约正式成立。男方若是悔婚,女方不需返还聘礼;女方若是悔婚,需加倍返还聘礼。聘礼常以银子给付,也可用牲畜、布匹折算,近代还有以枪支、鸦片等实物折算的。
聘礼的形成与延续是凉山彝人在大山大河间选择与适应的结果。引用苏力在《藏区的一妻多夫制》中的观点:“人的任何制度选择,即便行动者在选择时努力理解和顺应相关的自然约束条件,其选择最终能否成为制度,即为足够多的人在足够长的时段并在足够广的空间中所广泛实践并自觉追求,则必须接受自然的选择,接受时间的检验。就此而言,每个制度都可以说是人的理性选择,但其选择是否真的理性,或是否足够理性,判断标准却不是人的自我感觉也不是自我推论,也不是是否符合某个理论,而是,在经过一个长时段后,它能否最终为自然所接纳。”[1]据此观点,聘礼习惯的持续使用,已经为聘礼存在的“理性”提供了客观上的证据支持。聘礼在旧的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合理性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
在过去,聘礼涉及的不仅仅是男女两人的婚姻关系,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加强亲缘和地缘社会关系。通过聘礼,男女之间、两姓之间的婚姻关系因符合习惯法规范形式而获得广泛承认。另外,在父系社会男娶女嫁的婚姻形式中,女性出嫁后在家庭隶属关系上的改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说,都意味着女方家庭的一种损失。就此,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具有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意义。此外,基于男方提出离婚,女方不退聘礼;女方提出离婚,加倍退还聘礼的习惯法规则,聘礼在有限的程度内利于稳定婚姻关系,还能为离婚生活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
二、今天的婚姻聘礼
(一)“劫”后余生
1956年民主改革后,1960、1976、1987年,凉山三次进行婚姻改革。第一次婚改将“结婚不给聘礼;离婚和解除婚约,原则上不退聘礼”作为重要的改革政策。但由于旧婚姻制度根深蒂固,社会条件尚不成熟,婚改几乎无功而返。第二次婚改的任务之一是彻底废除买卖婚姻制度。这次婚改对当地婚姻传统决绝的否定是尚在转型初期的彝族社会无力负荷的。所以,纵使有国家强制力保驾护航,婚改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终究难以巩固。1987年凉山州政府推行了第三次婚改,解除了9.9万人有包办或索要“身价”内容的婚约,占应解除总数的53.1%;退还725万“身价钱”,占应退总数的67.6%。[2]但婚改仍不彻底。
(二)异化的“样貌”
今天,聘礼依然为大多数凉山彝人婚嫁之必需。但越演越高的婚姻聘礼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城镇聘礼普遍高于农村。城镇聘礼普遍在10~40万元之间,农村聘礼普遍在5~25万元之间。二是彝族人口占多数的彝区十县聘礼高于其余县市。彝区10县聘礼不论平均水平还是最高聘礼数额,都高于州内其余县市。三是“再婚女”的聘礼远远高于初婚者。女方再婚时,女方家庭一般会将退婚的经济损失转嫁到再婚对象家庭。[3]
(三)已变迁的意义
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凉山之后,工具理性至上的现实过程中,聘礼的意义已变迁。如今,人们关注的是聘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价值。
改革开放将经济的概念输入凉山。经济建设过程中,彝人开始切换运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或在传统价值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放纵个人利益凌驾于传统价值之上。聘礼的经济价值无疑是诱人的。当人们服从内心对于经济利益的渴望,高价聘礼也就“应运而生”。
高额聘礼被赋予了对婚姻双方皆适用的象征价值,既象征男方社会地位与财富,也象征女子及其家支荣誉。这种象征价值带来的满足使人们竞相提高聘礼数额,不惜放弃经济理性。
三、势烈的社会问题
(一)高额聘礼已成为阻碍自主婚姻的桎梏
高额聘礼给部分适婚男女施加了较大的心理压力, “怕恋恐婚”的心理束缚着婚姻自由。不少情侣因家长在聘礼上的分歧而劳燕分飞,佳偶难成。
(二)高额聘礼引起社会纠纷
彝谚说:“亲开到哪里,冤家就打到哪里”。因聘礼协商不成、退婚离婚时聘礼退赔不成,两个家庭结亲不成反结仇的情况屡见不鲜,严重时引发家支纠纷,引起械斗等恶性事件。今年“峨边县3.8婚嫁彩礼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农村剩男”不断增加
贫困的农村地区,不少男青年因无力负担聘礼而“待婚”家中。“农村剩男”数量不断增长。如总户数仅380余户的甘洛县某村就有适婚“剩男”20余人。[4]日益增多的农村剩男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放之任之,极可能演变为社会祸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印度,这是已被验证的惨痛事实。
(四)加重贫困问题
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的高额聘礼吞噬了一个家庭辛苦积攒的财富。为支付聘礼,不少本已脱贫越温或致富的家庭再次返贫;一些农村贫困家庭只得四处举债,贫困程度不断加重加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严重限制了这些家庭的发展,极易导致贫穷的代际传递。
四、明天何去何从
聘礼的异化已是既定事实。对其异化形态的处理迫在眉睫。在凉山,政府和民间都已着手规范婚姻聘礼问题。例如,2012年布拖县政府发布了《关于在除陋习、尚新风活动中严肃纪律的有关规定(试行)》的通知,规定:“严禁高额身价。革除高额身价许嫁的陈旧婚姻习惯,聘礼金额从严控制,严禁收受超过10万元的高额聘礼。”2012年美姑县300名德古(彝族民间调解人)举行聚会,商议遏制婚姻聘礼过高的问题并达成协议:即日起,聘礼限制在9万元以内。[5]笔者相信,政府联合民间积极作为,是能有效控制高额聘礼现象的。
在这里,笔者更想关注这一异化的民族传统背后的问题,关于现代化对地方性、边缘性的尊重与兼容。“现代性堪称20世纪的宏伟叙事,以史无前例的姿态在人类史上掀起全球性的社会变迁。”[6]凉山彝族顺应时代大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浮沉。当传统不断遭遇现代化的冲击,旧事物如何在新世界生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刘绍华女士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写道:“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事实上是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他们进入主流之时,也是他们愈加边缘化之际。”[7]难道,现代化真的不能兼容边缘与地方的本色吗?笔者不敢做出回答,谨在文末引入梁治平先生的话语:
“在我们这样一个全球化与多样性并存的时代,一个具有不同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人必须面对共同生活的挑战的时代,一种审慎的、诊断的、理解的、对话的和宽容的姿态,应该比任何道德独断更有助于实现不同人、不同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要保有我们所熟悉和珍视的一切,我们就应该学会如何同他人一道生活。”[8]
[1]朱苏力.藏区的一夫多妻制[J].法律与社会科学,2014(13):26.
[2]蔡应律.凉山彝族婚改纪实[J].民族,1989(5).
[3][4]课题调研组.凉山州婚丧嫁娶高额彩礼和铺张浪费问题调研报告[N/OL].凉山日报,2006(3):30.2015(4):1.http://www. lsrb.cn/html/2015-03/30/content_112772.htm.
[5]凉山彝族婚姻聘礼现状调查课题组.凉山彝族婚姻聘礼现状调查[OL].2015(4):24.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504212618-1. htm.
[6][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M].新北:群学出版社,2013(1).
[8]梁治平.高研院的四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1).
C913.13
A
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