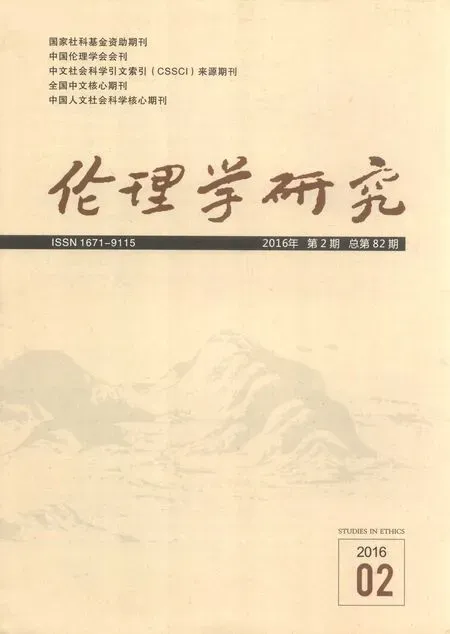佩莱格里诺医学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郭蓉
佩莱格里诺医学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郭蓉
佩莱格里诺在反思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和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基础上,立足医学哲学对医学本质、医学目的的确认和医学基本概念的澄清,建构其医学伦理学理论。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建构的医学伦理学是充满内容的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佩莱格里诺;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本质;医学目的
埃德蒙·D·佩莱格里诺(Edmund D.Pellegrino)是美国著名医学哲学家、医学伦理学家和医学人文学家,在推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H.Tristram Engelhardt)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离开佩莱格里诺,就无法理解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尤其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1](P1)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自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为我们认识医患关系、解决医患问题、建构和谐医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佩莱格里诺的医学伦理学理论极富特色,在医学伦理学中独树一帜。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对他的基于医学哲学的医学伦理学建构路径进行分析,以展示其医学伦理学的理论风格。
一、对医学伦理学两种建构路径的反思
医学道德是外在于医学的道德还是内在于医学的道德?医学伦理学是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还是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医学伦理学是充满内容的实质伦理还是不具内容的程序伦理?这些问题涉及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医学伦理学的建构路径。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建构路径有不同的回答。总的来说,医学伦理学的建构路径可从本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实质伦理—程序伦理两个维度进行阐述。本质主义认为,医学道德是内在道德,医学伦理学是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医学道德是外在道德,医学伦理学是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实质伦理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充满内容的伦理理论,程序伦理则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不具有内容的伦理理论。
佩莱格里诺的医学伦理学是在反思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和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基础上,基于医学哲学建构的。与社会建构的医学伦理学和基于后现代建构的程序伦理不同,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建构的医学伦理学是充满内容的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
1.对医学伦理学社会建构主义路径的反思
现代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以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建构的,其理论不是从医学本身发展出的医学伦理学理论,而是根据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将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应用于医学中的结果。佩莱格里诺认为,罗伯特·维奇(Robert Veatch)基于社会契约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是社会建构主义医学伦理学的典型代表。
维奇认为,社会契约作为一种普适性理论,是医学伦理学的基础。根据维奇的观点,社会契约理论包含基本社会契约、社会与职业之间的契约、职业人员与病人即医患之间的契约三个层次,医患之间的契约又是基于前两层契约的。由于前两层契约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预制和限定的,因此基于这两层契约的医患契约不可避免地被植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因素影响和塑造。在佩莱格里诺看来,根据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建构医学伦理学,将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取代病人最佳利益成为医学追寻的目标,使经济利益取代病人利益成为医学伦理学的内核,使社会责任消解医生对病人的责任,使医学伦理学沦为寻求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目的的附庸和工具。同时,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时代精神,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意味着不断修改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以迎合时代精神,同时,通过社会的、历史的建构或对话,不断地改变医学目的和目标,否认在医学这一人类活动中存在内在地决定医学目的和医学伦理学的因素。如此形成的伦理学是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1](P62-63)也就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消解医学伦理学的同一性和完整性。
在佩莱格里诺看来,汤姆·比彻姆(Tom L.Beauchamp)和詹姆士·邱卓思(James Childress)基于公共道德提出的原则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医学伦理学理论。该理论所提出的四个基本原则——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和公正原则,源自公共道德,其规范力量和道德权威由公共道德赋予。佩莱格里诺认为,基于公共道德提出的原则主义是将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应用于医学,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应用说。然而,“如果医学伦理学仅仅是已有的伦理学理论的应用,那么,它将迅速脱离医学的真实情境。这样的医学伦理学将不再有用,甚至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2](P173)。同时,由于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远离医学现实,并没有对特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作出规定,因而无法强有力地规范和约束医学共同体成员,为医学实践和医生行为提供有效的规约和向导。
基于对社会建构主义不足的认识,佩莱格里诺认为,要保持医学伦理学的同一性和完整性,医学伦理学必须相对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这就要求医学伦理学基于医学哲学,基于医学哲学的医学伦理学是直面医学现象的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
2.对医学伦理学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反思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现代道德困境。现代道德困境是指在道德多元化社会,对很多基本问题存在不同观点,而根据这些观点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又相去甚远。然而,通过诉诸各自的理论前提,这些结论都可以获得合理性论证,没有哪一结论能强有力地压倒另一结论,如此各方便陷入无休止的争辩漩涡中。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道德困境实际上表明了试图通过理性确立普遍性规范的启蒙运动道德工程失败了。恩格尔哈特吸收麦金太尔的这一观点,打破启蒙运动以来对普适伦理的诉求,立足于后现代,在承认道德多元化的基础上,主张现代社会主要是由不享有共同道德观点和主张的道德异乡人形成的社会。恩格尔哈特认为,宗教伦理在道德异乡人社会无法得到确立,俗世伦理才是适用于道德异乡人社会的伦理学理论。根据恩格尔哈特的观点,宗教伦理不仅指持有神论的伦理学体系,而且包括任何充满内容具有普遍规范性的伦理学体系;俗世伦理则是指超越具体宗教、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不具内容的程序伦理。程序伦理是以允许原则为先验条件,主张道德权威和道德内容源自他人的允许和同意而非理性的伦理学理论。
佩莱格里诺认为,恩格尔哈特的程序伦理过分强调不同共同体之间的道德多元性和差异性,忽视了人类存在超越文化与时空的共同性。同时,恩格尔哈特的程序伦理并不讨论实质内容,它只寻求解决问题而不追问道德真理,对实质内容的对错、好坏并未作出判断。在程序伦理中,行为的道德性质并不取决于实质内容,而是取决于行为是否获得了当事人的允许和同意。如若一个行为获得了当事人的同意和允许,那么该行为则是道德的;如若未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和允许,那么该行为则是不道德的,即使从实质内容上看,该行为是善的。也就因此,恩格尔哈特的程序伦理存在“X有权做A,但A是极其错误的”的问题。[3](P103-104)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自主原则和有利原则相冲突的问题。佩莱格里诺认为,在恩格尔哈特的分析中,自主被逐步绝对化,有利和社会中的其他重要价值被逐步排除在分析之外。然而,在佩莱格里诺看来,“权利的原初含义是自由地做有义务去做的事,而不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特殊待遇的资格”[4](P45),并且“自由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我们既不能将它视为道德的条件,也不能将它绝对化”[4](P45)。也就是说,自主并不是病人的绝对权利,而是一种相对权利,它受其他价值的限制和约束。
恩格尔哈特以承认道德多元化为前提,基于后现代建构的医学伦理学是不具内容的程序伦理。与之不同,佩莱格里诺试图在道德多元化社会建构普适的充满内容的医学伦理学。然而,在道德多元化社会,普适的充满内容的医学伦理学何以可能?在佩莱格里诺看来,这种可能存在于道德多元化社会中存在超越时空与文化的人类普遍经历,生病事实和治愈需求则是这样一种经历,“医学正是因生病和治愈是人类的普遍经历而存在”[1](P66)。生病事实和治愈需求的普遍性为普适的充满内容的医学伦理提供了基础。
医学伦理学社会建构主义路径使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渗入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同一性和完整性被销蚀。同时,医学伦理学面临着从实质伦理走向程序伦理、从追寻道德真理走向问题解决的后现代主义挑战。医学伦理学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而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佩莱格里诺认为,“医学伦理学必须基于医学哲学。由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异质性和医学科学的普遍性,任何合理的医学道德哲学无法仅从外在的哲学体系中获得,它必须‘内在于’医学本身”[1](P434)。那么,医学哲学何以成为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二、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佩莱格里诺对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和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反思回答了他缘何基于医学哲学建构医学伦理学,那么,医学哲学对医学本质、医学目的的确认和对医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则说明了医学哲学何以成为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1.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的确认
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是佩莱格里诺医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分别回答了医学“是什么”和医学“为了什么”。我们关于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观点取决于对这两个基本问题所持的观点和看法。对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的确认是有效解决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佩莱格里诺医学哲学通过医学现象分析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认为生病事实(the fact of illness)、职业行为(the act of profession)和医疗行为(the act of medicine)是医学的三种独特现象,“从医学现象可推出使医学成为独特的人类活动的根本性质。我们将这种独特性置于人类关系——治愈关系中。在治愈关系中,病人寻求治愈,医生承诺治愈,医疗行为将病人和医生连接起来”[2](P5)。
根据佩莱格里诺的观点,生病是超越时空和文化的人类经历,具有普遍性;同时,生病是主体对与健康相分离状态的体验和认知,是一种主观状态,具有特殊性。佩莱格里诺基于人的具身(human embodiment)的两种现象——生存自我(the lived self)和生存体(the lived body)对生病的影响进行分析。他认为,一方面,生病侵袭人的本体。在健康状态下,自我和身体是统一的,“我即是我的身体”,自我和身体以统一的方式面对外部世界、进行活动。然而,在生病状态下,自我与身体的对立取代了自我与身体的统一,身体阻碍着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实现,“我-世界”的关系转化为“自我-身体-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生病损害人的人性,它不仅限制了主体的自主选择和行为自由,同时也损害了人的自我形象。
生病事实产生治愈需求。治愈需求是人类的普遍经历和个体的主观需求,它要求获得实现和满足。在医学中,医生承诺有能力并且将致力于实现和满足病人的治愈需求,因而,转向了医学的另一现象——医生的职业行为。佩莱格里诺从词源上对职业进行了探讨,认为职业(profession)是“大声且公开的宣誓和承诺(promise)”,[2](P209)而“内在于职业行为的是医生将运用知识和技能实现病人利益”[1](P165)。也就是说,医生的承诺包括两个方面:医生拥有特定的知识和技能,有能力帮助病人、治愈病人;医生将为了病人利益而不是自我利益而行动。基于医生的职业行为,病人对医生的期望同样也包括两个方面:医生确实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医生将为了病人利益而行为。然而,病人的治愈需求和医生的治愈承诺只有通过医疗行为才能实现。医疗行为是连接医生和病人,将病人的治愈需求和医生的治愈承诺现实化,实现治愈目的的具体行为。
由于病人寻求的治愈是特定于自身的治愈,医生承诺实现的也是特定病人的治愈需求。因此,医疗行为必须是对特定病人的正确的且好的治愈行为,“正确的且好的治愈行为构成作为医学的医学”[2](P211)。佩莱格里诺认为,“正确的”意味着在科学上医疗决定与病人需求相一致,“好的”则意味着医疗决定尊重病人的价值需求。佩莱格里诺关于“正确的且好的治愈行为”的观点实际上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体现了在医学中将科学真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的诉求。
基于对医学现象的分析,佩莱格里诺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医学属于关系范畴;更具体地说,医学是由需求引起的通过作用于身体的治愈关系”[2](P173)。医学本质是寻求治愈的病人和承诺帮助的医生形成的旨在实现治愈目的的关系——医患关系。进一步说,医患关系是由病人治愈需求支配的治愈关系。在治愈关系中,医学治愈目的的实现要求医生将医学知识与个体病人联系起来,将医学知识个体化。医学知识的个体化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价值,充分发挥病人的主体性。基于对医学本质的确认,佩莱格里诺认为“医学是通过作用于身体,医患双方共同实现个体安康的相互关系”[2](P80)。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本质定义医学的方法是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对的本质主义方法,他关于医学是什么的观点实际上是本质主义的观点。
就医学目的而言,佩莱格里诺认为,“医学是最人道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最科学的人文学”[1](P310)。医学是连接科学和人文学的桥梁,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医学科学精神追寻客观真理,体现了医学的合规律性;医学人文精神追寻医学目的的完满实现,体现了医学的合目的性。然而,医学是作用于人的学科,医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必然而且应当以实现医学目的为导向,只有以医学目的为导向的医学才是真正为人的医学。因此,医学所寻求的不仅仅是对现象的科学解释和科学知识的获取,医学目的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目的,它要求在具体的医疗行为中实现对特定病人的正确的且好的治愈。然而,治愈不等于治疗,治愈是治疗疾病和关怀病人的统一,治疗可能无效,但关怀总是有效的。
佩莱格里诺认为,医学目的内在于医学,是医学存在的原因,健康是医学的目的,是医学存在的一个必定趋向,是医学必然追求和旨在实现的善,是医学的实现活动;而对特定病人的正确的且好的治愈是医学的直接目的。治愈是医学的内在价值,医患关系的道德主体——医生和病人行为的道德性质取决于医学治愈目的的实现程度。佩莱格里诺关于医学目的的观点实际上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目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实现内在目的;同时,事物的内在目的是解释事物存在的原因,是评价事物活动和发展的标准。
佩莱格里诺的医学哲学通过对医学现象的分析,明确了医学本质是治愈关系,医学目的是治愈,厘定了医患关系内含价值,医学是由病人治愈需求支配的负载价值的实践理论,从而为形成合适的医学伦理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同时,治愈关系的内在价值表明医学伦理学是与临床医学共生的学科,它不是外在于医学的伦理学理论的应用,而是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如同医学,医学伦理学也由病人的治愈需求支配,以实现病人的治愈需求为目的。
2.医学基本概念的界定
任何理论分析都基于明晰的概念和定义。对医学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医学哲学的重要部分,它贯穿于佩莱格里诺整个医学伦理学体系。佩莱格里诺对医学基本概念的分析部分源于他对生物医学模式以及医学去人性化现象的深刻体认。
生物医学模式是以疾病为导向的医学模式。该模式将病人视为疾病的客观载体,将病人和疾病分离开来,在具体的医疗行为中但见其病不见其人。同时,生物医学模式是单维度的,它只关注病人的生理维度,将病人利益限于生物医学利益,忽视了生病事实和治愈需求的复杂性,缺乏对病人价值需求的关注。生物医学模式孕育于技术理性张扬、技术价值中立论和工具论大行其道的文化土壤中,它不仅培植起了治疗至上和医学技术至上的观念,还形成了医学技术崇拜,以至于无视人的价值,隐性地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将医学的去人性化展露无遗。医学中人性的迷失是医学伦理学面临的巨大挑战。佩莱格里诺医学哲学通过对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的分析已经明确了医学具有内在价值,而医学哲学对医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则进一步深化了医学的内在价值和人文要素。
佩莱格里诺基于人的具身的三种现象——生命体(the living body)、生存体(the lived body)和生存自我(the lived self),对“健康”和“疾病”进行界定。佩莱格里诺认为,“生命体是作为身体有机体存在的先在领域”[2](P105),是人的生物性存在。在生命体层次,健康意味着有机体功能的稳定和协调,疾病则是指有机体功能的紊乱和失调。“生存体是无法被客观化的身体体验,该体验由个体和外部世界、他人的相互作用决定”[2](P105),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在生存体层次上,健康和疾病主要表现为主体对自我和身体、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主观体验和认知,具有主体性和相对性。在这一层次,价值因素融入“健康”和“疾病”概念,使这两个概念具有评价性。“生存自我是人类所形成的向世界呈现出的个性特征的客观范畴。”[2](P105)在生存自我层次,症状或疾病被对象化为客体,“健康”和“疾病”是纯粹抽象的科学概念,“疾病是对作为人的自我形象与姿态产生影响的病人整个世界瓦解的概念化”[2](P76)。佩莱格里诺从生命体—生存体—生存自我三个层次对“健康”和“疾病”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实际上表明了“健康”和“疾病”概念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评价性,同时蕴含科学因素和人文因素。
“治愈(healing)”是与“健康”和“疾病”相关的另一个医学基本概念。病人的个体性并不是客观概念所能完全描述和说明的,治愈目的也并非诉诸医学知识就能完全实现,从而使关怀病人成为一种应然要求。佩莱格里诺认为,治愈是治疗疾病和关怀病人的统一,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四个维度。佩莱格里诺关于治愈是治疗和关怀相统一的观点,摒弃了生物医学模式中见病不见人的弊端,将病人视为人而不是疾病载体。在这一意义上,治愈是指恢复人的完整性。佩莱格里诺认为,“人的完整性是一个道德主张,它属于任何一个人仅因为他是人”[5](P129)。具体来说,人的完整性包括身体的完整性和价值的完整性这两个方面。身体的完整性是指健康,身体的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协调;而价值的完整性是指个人价值的完整。人的完整性要求和生病的去完整性,使得帮助病人恢复身体完整性和保存价值完整性成为医生的应然责任。医学中,病人利益为医疗实践提供了一套相应的价值体系,以及衡量和评价治愈实现程度的标准。
佩莱格里诺认为,“医学是为了特定病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过程。医学的首要目的不是发现自然规律。归根结底,医学目的是道德目的——病人利益。病人利益是医学目的的辩护原则。医学中,关于应该做什么的选择取决于病人的价值、道德和人际关系”[2](P147)。佩莱格里诺认为,病人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包含终极利益、人之为人的利益、所认知的利益和生物医学利益四个利益成分。
终极利益是指精神利益或利益概念,是医生和病人在医疗决定中诉诸的最终或最高标准。佩莱格里诺认为,终极利益是病人其他利益成分的基础,我们关于利益概念的观点影响并塑造其他利益成分。同时,终极利益定义和论证道德选择的性质,是包括医疗决定在内的所有决定诉诸的标准。然而,不同哲学和宗教体系持不同的利益概念,个人对利益概念也存在相异的解释,利益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复杂概念,它表明病人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人之为人的利益是基于人是理性人而形成的利益,具体来说,是指人的理性推理和自主选择。佩莱格里诺认为,人之为人的利益是人之为人不可化约的条件,是不可协商的利益。医学中,病人作为人的利益是自主决定和自主行为。该利益要求医生在病人有行为能力时尊重病人自主,在病人无行为能力时帮助病人恢复和增强自主。病人所认知的利益是病人对自身最佳利益的一种主观认知,它是特定个体病人的利益,因而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生物医学利益是医学指征所表达的通过医疗技术和医疗干预可以实现的利益。佩莱格里诺认为,“生物医学利益是病人向医生寻求的工具性利益,是内在于医学的善,是特定的人类活动医学的一部分”[4](P78),但是,生物医学利益并不等同于病人利益,将两者混为一谈会产生两个道德错误。第一,将医学的道德性局限于技术干预的正确性,只承认医疗利益而忽视病人的其他利益,同时也忽视相互冲突的利益所形成的伦理困境;第二,将对治疗所产生的生命质量的容忍度的判断与治疗的医学指征混为一谈,将医疗判断延伸至合理限度之外。[4](P78)实际上,“生命是否值得一过”不只是一个医疗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病人只有根据自身的价值需求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
佩莱格里诺关于病人利益的分析表明,病人利益是一个复合概念,病人利益的某一个成分并不等同于病人利益。同时,病人利益成分不存在绝对的优先排序,不同个体对不同的利益成分赋予不同的权重。因此,医学治愈目的的实现不能只诉诸医学能做什么,更要追问医学应当做什么,也就是说,关心病人的价值诉求。应当做什么是对医学能做什么的规约和限制,没有对应当做什么的寻求,那么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将如脱缰之马肆意践踏人的人性。为此,佩莱格里诺一再强调能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之间的区分。总而言之,在医学中,医学科学固然重要,但只有在人文关照下的医学才不至于迷失人性。
基于医学哲学对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以及医学基本概念的分析,佩莱格里诺主张医学道德源自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而医学目的的实现要求医学道德主体具有相应的美德。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有利模式和医学美德伦理学,形成了一套以医学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医学目的为依归的融贯一致的医学伦理学体系。
在西方医学伦理学界,佩莱格里诺关于医学道德源自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的观点,乃至其基于医学哲学建构的医学伦理学理论也存在争议。围绕医学道德是内生于医学还是外在于医学,医学职业道德权威是源自医学本身还是源自外在于医学的其他因素等争论,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1年第5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批评者认为,佩莱格里诺的医学内在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本质主义内在主义,本质主义内在主义主张医学目的是永恒不变的,医学道德源自医学目的和医学本质。这种本质主义内在主义受到了质疑与批判。米勒(Franklin G.Miller)和布罗迪(Howard Brody)认为,佩莱格里诺关于医学目的永恒不变的主张,实际上是将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医学内在道德和医学外在道德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在米勒和布罗迪看来,医学目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佩莱格里诺关于医学道德的本质主义观点反对医学目的的任何改变,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是保守的。[6](P585)汤姆·比彻姆也认为佩莱格里诺关于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的理论是本质主义理论。他从有利和治愈两个方面对佩莱格里诺的内在道德进行分析,认为佩莱格里诺将医疗有利原则视为唯一导向医学治愈目的的内在标准,限制了对病人有利的行为类型。在比彻姆看来,医疗有利原则的局限性源自佩莱格里诺将治愈视为医学的唯一真实目的,这是佩莱格里诺医学伦理学体系的一大弱点,其基于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所定义的医学也因此存在问题。比彻姆将佩莱格里诺的医学理论称为“医学一元论”,认为“佩莱格里诺的医学观点忽视了许多医生能够并且应当提供的对社会和病人而言相当重要的利益,缺乏将医学替代性解释排除在外的原则性基础。”[7](P604)罗伯特·维奇对佩莱格里诺医学内在道德进行了最为犀利的批判,认为佩莱格里诺是从医学目的推出医学道德,而不是超出医学本身去理解医学道德。维奇认为,从医学目的和医学基本概念不能推出医学道德,医学内在道德是不可能的。维奇主张,医学道德必须源自更根本的道德,这种更根本的道德是社会建构的外在于医学且反映人类根本共同道德的道德[8](P621)。阿拉斯(John D.Arras)认为当代医学道德的某些必要元素无法从医学基本概念或医学目的的分析中推导出来,同时,本质主义内在道德缺乏确定规范限度或解决规范冲突的因素,因此无法解决复杂的道德问题。[9](P643)
尽管存在争议和批判,但毋庸置疑的是,佩莱格里诺的思想闪烁着人文精神,有力地回应了当今医学的去人性化现象,推动了医学人文学的发展。他从哲学层面上探析医学本质和医学目的这类内在的、永恒的因素,在寻求医学道德真理的基础上解决具体的医学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和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缺陷,为道德多元化社会提供了普适的充满内容的伦理学理论。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的医学伦理学建构路径为医学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对平衡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形而上的医学哲学和形而下的具体问题研究之间的偏颇,推动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H.Tristram Engelhardt,Fabrice Jotterand.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A Pellegrino Reader[M].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8.
[2]Edmund D.Pellegrino,David C.Thomasma.APhilosophical Basis of Medical Practice:Toward a Philosophy and Ethic of the Healing Professions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美]H.T.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第二版)[M].范瑞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Edmund D.Pellegrino,David C.Thomasma.For the Patient’s Good:the Restoration of Beneficence in Health Ca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5]Edmund D.Pellegrino,David C.Thomasma.The Virtues in Medical Practi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6]Franklin G.Miller,Howard Brody.The Internal Morality of Medicine: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1,26(6):581-599.
[7]TomL.Beauchamp.Internaland External Standards for Medical Morality [J].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1,26(6):601-619.
[8]Robert M.Veatch.The Impossibility of a Morality Internal to Medicine [J].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1,26(6):621-642.
[9]John D.Arras.A Method in Search of a Purpose:The Internal Morality of Medicine[J].Journal of Medicineand Philosophy,2001,26(6):643-662.
郭 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科技伦理问题研究”(12&ZD117);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移植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与法律问题”(12ZDB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