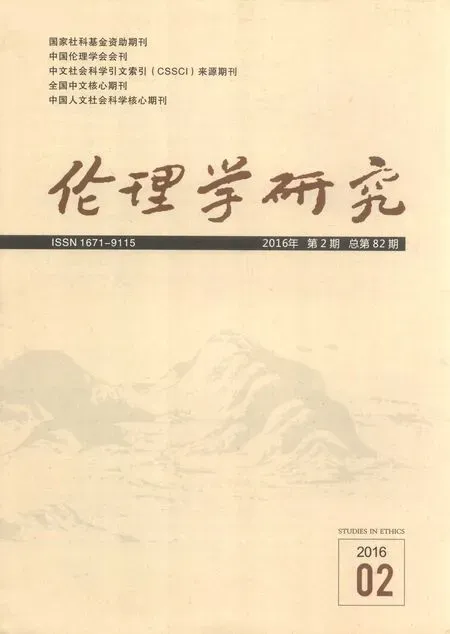“富而好礼”如何可能?
陈科华
“富而好礼”如何可能?
陈科华
“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是推进人类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但是富贵者与贫穷者的道德表现都具有坏的可能性,只有从制度合法性建设和道德主体性建设两方面来克治这种坏的可能性,“富而好礼”的文明社会才是可能的。
“富而好礼”;道德表现;文明社会;孔子
把“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观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因为富强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进人类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古代思想家管子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便是传统文化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但是,在富强或“仓禀实”“衣食足”的土壤上是否必然或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文明的或“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呢?如果不是,又怎样才能生长出文明的社会?关于这一问题,孔子提出的“富而好礼”思想具有十分重要启示价值。
一、富贵者“坏”道德表现之可能性
富裕虽然是主体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物质基础,但是,富裕的主体未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亦如贫困的主体未必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因为,在事实上,无论贫与富,其行为取向都具有多种或好或坏的道德可能性。其中富贵者的道德表现具有四种坏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富而骄”。在《论语·学而》中,子贡问孔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在子贡的这一问题意识中,很显然,“富而骄”便是富贵者主体容易或常常发生的道德问题之可能性,或者说“骄”是富贵者主体常见的道德病。对此,古人早有深刻洞察,如《道德经》第九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论语·皇疏》:“积蓄财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骄。富积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左传·定公十三年》:“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国语·晋语八》:“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论语·述而》:“奢则不孙”《礼记·坊记》:“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史记·管晏列传》:“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说。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将封晏,晏子辞不,曰:‘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王安石在《韩信》一诗有云:“贫贱侵凌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富而骄”现象高度关注一样,《圣经》也载,摩西这样叮嘱以色列人:“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申命记》)而在现代社会道德生活中,富裕起来的人常常有“财大气粗”之像,炫富夸富斗富甚至“有钱就任性”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权贵视公民道德和法律为无物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有的甚至还任性到国外,如泰国航空事件,个别游客任性嚣张到“老子给你飞机都炸掉”的地步,算是将国人之丑丢到了国外,等等,都反映出“富而易骄”的道德走向之可能性乃为古今中外之通病。
“骄”在道德心理上表现为态度上的傲慢、轻视与偏见,而道德行为取向上则表现为蛮横、失范与僭越。在古代社会道德生活中,“富而骄”最突出的莫过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当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经济势力的增强,周王室日渐衰微,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法礼乐体系即周礼受到了来自诸侯的严峻挑战,首先是代表周天子政治合法性的礼乐征伐权不断地出现权力下移的情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再“自大夫出”,到后来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论语·季氏》)。伴随着政治权力失范而来的是,诸侯、大夫阶层出现了普遍的僭越礼仪之风,如为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如被孔子所许为仁者的管仲,亦曾因为“邦君树塞门,管仲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仲亦有反坫。”而受到孔子的批评:“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再如,《左传·哀公七年》载“吴来徵百牢”一事,就是富强起来的吴国要求鲁国用猪、牛、羊各100头即“百牢”的级别来接待他们的君王夫差,而按周礼规定,仅子爵级的吴国只能享受“五牢”的待遇,这明显是“富而骄”产生的外交失礼事件。春秋以后历朝历代,这种情形更是屡禁不止,如据嘉靖《太康县志》载,明朝后期“(暴富之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簪拟无涯,逾国家之禁也。”至于历史上依仗财势欺凌弱者、作奸犯科甚至无法无天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第二种可能性——“富而奢”。“富而骄”之坏的道德可能性除了习惯于突破伦理规范的约束外,还表现为一种坏的生活方式取向即“富而奢”。富裕起来后,人都会有过上好一点生活的需求,且这一需求也可以获得一种伦理正当性的辩护,但是,一者财富的获取必须是正当的,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二者财富的消费必须是恰当的,而传统伦理的“恰当”标准乃是节俭,至于何种生活方式是节俭的,传统伦理的着眼点在主体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之间能维持适度的张力,如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朱子认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饮食是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是“天理”,而“美味”则是超出这一物质需求的“人欲”。但是,为孟子和理学所反对的“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孟子·尽心下》)的生活方式却是很多富裕起来的人的价值追求,如“管仲富拟于周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又如洪昇在《长生殿·献饭》中所说:“寻常,进御大官,饌玉炊金,食前方丈,珍羞百味,犹兀自嫌他调和无当。”这就是说,消费的奢侈倾向实际上是一种人之常情,以至于《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帝)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说。无疑,传统的消费伦理观将节俭的标准定格于人们最低的物质生活需求确有对人性残害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考虑到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限度,以及其严重的社会两级分化状况,奢侈性消费必然会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惨局,而且站在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即使在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人类也不能把奢侈的消费方式当作具有伦理正当性的生活方式来提倡。
第三种可能性——“富而吝”。“富而吝”是“富而骄”的另一种形式的坏的道德可能性。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骄且吝”可以说是富贵者的道德通病。何谓“吝”?《颜氏家训·治家》“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吝”与“俭”是相对待和联系的范畴,节俭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美德,但是,节俭作为一种美德也是有限度的,《菜根谭》曰:“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过于节俭者一方面容易出现孔子所讲的“俭则固”,即太过简陋以至于置礼仪的形式即“雅道”要求于不顾,特别是涉及到一些重大礼仪,如果一味从简,更是有伤国家制度的根本,如《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意思是时代变了,礼仪也应该从简,所以行告朔祭礼,没必要供奉饩羊。对此,孔子虽也主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可以从简,如《论语·子罕》:“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但举凡涉及宗法制度根本的礼仪如告朔祭礼,就不能从简。所以,“俭则固”虽在伦理上优胜于“奢则不孙”,但同样难以获得高额度的伦理正当性辩护。另一方面,“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即悭吝者未必是出于节俭的考量,毋宁说是贪婪财富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守财奴心态,他对于国家、个人的“穷急”之需缺乏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感,甚至还以不正当的手段敛取财富,如《世说新语》中的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但他在高价出售自家上好的李子时因担心别人用他的李子核做种子栽培出上等李子,竟事先把李子里面的核给去掉。又如五代大词人韦庄,八岁的儿子夭折了,下葬时,妻子为孩子穿上生前的衣服,却被韦庄剥下来,仅用旧草席裹着送去掩埋,且掩埋之后,竟还将草席带回来,全然不顾父子亲情和死者的尊严。悭吝刻薄如斯,恻隐之心何存?因为,儒家的孝道便是基于孔子所讲的“子生三年,然后方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贷》)的亲情,如果对自己的子女都如此刻薄,那么,需要主体或多或少短付出的道德行为即儒家所讲的“立人”“达人”之仁道如何可能呢?而在今天,我们的企业家和富裕起来的人对慈善事业的冷漠也正反映出“富而吝”的坏的道德可能性。
第四种可能性——“贵而贪”。上文所讲的富贵之坏的道德可能性只是笼统言之,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富与贵既相联系,又相区分,富是讲物质财富的多寡,贵则是讲社会地位的高低,富者未必为贵,贵则常常为富,特别是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重压之下,富而不贵的现象历代皆有。而在道德生活中,富与贵虽然存在共同的行为取向,但细究起来,二者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对此,清代纪晓岚的老师董邦达别有一番见解,他说:“盖富而过奢,耗己财而已;贵而过奢,其势必至贪婪。权力重,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守己财而已;富而过俭,其势必至于刻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士大夫时时深念,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有余地,则招福之道矣。”(见《阅微草堂》卷九)意即“富而过奢”或富而不俭的行为取向较之于“贵而过奢”的行为取而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后果,即前者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消费过度即浪费(“耗己财而已”)行为,它会引发一种不良的或坏的社会道德风气;而后者(“贵而过奢”)则会为了维持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而走向依靠权力来摄取财富即政治腐败,它会对社会公序和政治制度所要体现的首要价值——公正或“中正”带来严重的伤害,因而一种值得警惕与防范的最坏的道德可能性。至于“过俭”行为可能产生的道德后果,亦存在“贵而过俭”与“富而过俭”之别,即前者顶多是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守财奴式的消极的道德主体;而后者势必导致“刻薄”“计较”“机械”等对他人、社会存在积极伤害可能性的行为取向,因而也是一种值得警惕或“时时深念”的坏的道德可能性。而在今天,广受社会非议的“权贵”阶层的“有权就任性”、贪污腐化成风以及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冷漠等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冲击更是令人担忧。
二、贫贱者“坏”道德表现之可能性
在等级森严的宗法体制下,面对“富贵骄人”与“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或“轻仁义而羞贫贱”(《后汉书·班彪传》)的道德生活环境,贫贱者的道德行为取向也存在或坏或好的可能性。主要有三种坏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贫而谄”。何谓“谄”?《说文》:“谄,谀也。”《皇疏》引范宁曰:“不以正道求人为谄也。”可见,谀谄产生的前提是因为有求于人。通常,人们在两种情况下会有求于人:一种是因为在物质生活资料上的贫穷而无法维持生命体存在的情况下而不得有求于人;一种是因为在社会地位上的弱势而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得有求于人。在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家庭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生产方式,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自耕农基本上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从而基本可以实现“万事不求人”的人生理想。但是,一者自然经济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经济,天灾的发生是导致自耕农陷入贫困的原因之一,因而要想一生“万事不求人”是基本不可能的;二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得以长期存在的制度环境并不稳定,它经常受到来自地主豪强土地兼并的侵蚀,再加上战争等人祸的影响,自耕农“万事不求人”的梦想基本上也无实现的可能。既然如此,不得不“求人”可以说是传统社会弱势群体存在的常态。而当“求人”不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的时候,被求者便不可能把帮助或施舍他人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我们知道,权利意味着应当得到,义务则意味着应当付出,正是因为“求人”不是一种权利,所以“求人”的道德合法性无法得到强有力的辩护,而没有道德合法性辩护的“求人”必定是以丧失自身的人格尊严为代价,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便是“谄”或讨好他人。所以,我以为,在一个贫富两级严重分化的等级社会,作为弱者的一方根本不存在“以正道求人”的可能性。既然如此,“谄”作为一种非正当的或坏的行为取向便并不是贫贱者的天然道德弱点,或者反过来说,无条件地向弱者提出“贫而无谄”“安贫乐道”的道德要求乃是一种强者的道德逻辑,这一逻辑无法得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辩护。
诚然,“谄”毕竟是一种道德弱点或缺陷。但这道德弱点不仅存在于贫贱者身上,富贵者也有“谄”的可能性。因为,贫穷与富贵总是相对的,在中国传统宗法体制之下,富贵者之间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处于下等级的人在面对上等级的人时,献“谄”或卑躬屈节也是他们经常的道德行为取向,即使贵为天子,为求江山稳固,为求长生不老,也常常向上天或神灵或鬼神献媚,所以,只要人有所求,无论贫富,都有“谄”的可能性,只不过“谄”的道德弱点在贫贱身上表现更明显罢了,亦如“骄”的道德弱点在富贵者身上表现更为突出一样。而且,“骄”也不是强者的专利,事实上也有“贫贱骄人”的可能性。据《史记·魏世家第十四》载:魏文侯十七年,灭中山国,派子击据守。一次子击在朝歌遇见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他退车让路,下车拜见,田子方却不还礼。于是子击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回答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奈何其同之哉!”田子方的意思是:富贵者骄人会失去人心并进而失去其国与家,而贫贱者骄人虽不失去什么,但可以离开你不喜欢的国家,二者是不同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贫贱骄人之所以可能,诚如清代纪晓岚所言:“亦谓道德本重,不以贫贱而自屈。非毫无道德,但贫贱即可骄人也。信如君言,则乞丐较君为更贫,奴隶较君为更贱,群起而骄君,君亦谓之能立品乎?”(《阅微草堂》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换言之,富贵骄人是失德的表现,而贫贱骄人则必须以立德为本,必须有人穷而志不短的狷介之气,否则“寒士不贫贱骄人,则崖岸不立,益为人所贱矣”(同上)可见,在纪晓岚看来,贫贱骄人还是狷介之士处世立足且不为人所贱的一种存在方式。虽如此,骄人毕竟不是一种最优的道德选择,《增广贤文》有言:“贫贱骄人,虽涉虚矫,还有几分侠气;奸雄欺世,纵似挥霍,全没半点真心。”“几分侠气”毕竟还是掩盖不了“虚矫”的品德瑕疵。所以,儒家并不主张以贫贱骄人立德,按孔子理想人格的标准,贫贱骄人的“狂狷”之士是在“不得中行之士而与之”(《论语·子路》)的情形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道德择优,甚至在孔子眼中连“小人”也是在不得“狂狷”之士的情况下的再退而求其次的道德择优。
第二种可能性——“贫而怨”。《论语·宪问》:“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贫困意味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难以得到保障,人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抱怨是难免的。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及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困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中子路之“愠”便是一种抱怨。孔子认为:“君子固穷”,其实这是基于“君子”之“穷”是暂时的,或者说“君子”之“穷”乃是一种相对贫穷这样一种事实判断,如果长期如此,或者君子每天都过着“蔬食箪瓢”的生活,能否做到“不愠”或不抱怨,这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诚如《醒世姻缘传》中的尤畅所言:“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的日子……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蔬食箪瓢’?……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三日粮,……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有鉴于此,我以为,“贫而怨”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弱点,或者说,“贫而怨”只是在相对贫穷的情况下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弱点。
第三种可能性——“穷斯滥”。如上所引,孔子认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滥”是指一种胡作非为的坏的道德行为,它的发生经历一个由“贫斯约”-“约斯盗”的过程。《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礼记·坊记》又载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人陷于贫困,其实际的行为取向首先是对自我物质生活欲望的克制并形成节俭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约”即拘束的状态。朱子认为,“久约”之意是指长期陷于“穷困”,王夫之则认为是“窘迫拘束不得自在”,实际上二者可以互通。因为处穷困潦倒状态下,主体的人格尊严与人格独立丧失了其应具的物质基础保障,就会产生孟子所讲的“无恒产”因而“无恒心”的人格心理(《孟子·梁惠王上》),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行为表现自然会显得“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俗语所谓“贫穷说话牙无力”,指的就是这种“贫斯约”的人格心理状态及其外在行为表现。所以,我以为,“贫斯约”虽然是可以克服的道德弱点,但把它归结为“小人”或“不仁者”的独有的道德人格,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由“贫斯约”至“约斯盗”,是否存在必然的道德发展逻辑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如果贫困问题得不到解决,人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久约”之人确实具有走向“约斯盗”或“穷斯滥”的可能性,俗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贫困者具有为解决生存权而斗争的道德合法性。至于斗争方式的选择是否在道德上正当,这取决于社会制度本身的道德合法性。在宗法一体化的等级制度下,劳动者的生存权问题始终是决定王朝兴替的关键要素,历代的统治者虽都意识到“民为邦本”的道理,但却无法将这样一种理念转化一种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历史的事实证明,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使得“成王败寇”具有一种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客观上造就了一种“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的伪道德现象。如果道德的话语权取决于“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那么“约斯盗”或“穷斯滥”便可获得历史合法性辩护。当然,“盗”或“滥”毕竟是一种非正当的行为方式,因为,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既有制度安排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主体自身的主观原因。张载曰:“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划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张载集·经学理窟·气质》)“计穷”“力屈”“才短”及“好逸恶劳”等都是导致贫困的因素之一,因此,“约斯盗”或“穷斯滥”终究无法获得道德合法性的辩护,更何况还存在“安贫乐道”的道德可能性。
三、“富而好礼”如何可能
由上可知,“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物质文明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精神文明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构建只有克治了上述贫穷者与富贵者之坏的道德可能性其中尤其是后一可能性才是可能的。
如何克服富贵所可能产生的道德病?孔子提出了“难易”之说,即“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富而无骄”在孔子看来是一种比较容易克服的道德弱点,果真如此吗?尤其是当富与贵相结合形成权贵社会后,要克服这种“有钱就任性”与“有权更任性”的坏的道德行为取向,我看并非易事。因为,权力若不关进制度的笼子,就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所以,仅靠主体的道德修养来克治“富贵骄人”的道德通病,其成效是始终有限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中,探讨了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及清教徒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影响,其中“天职”观念是指“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路德语),即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把它当作上帝赋予你的义务与责任,譬如拼命挣钱就是上帝赋予资本家的义务,是资本家个人“荣耀上帝”的证明。既然发财致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圣经》告诫人们不能“富贵骄人”,相反必须持一种节俭的消费伦理观,这种清教徒精神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精神动源。而且,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西方文明逐步形成了“带着财富去见上帝乃是一种耻辱”的财富观,这为西方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的财富观虽亦有“光宗耀祖”的说法,但它并不是一种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相反,这种“光宗耀祖”的思想常常要借助奢侈的消费方式或排场来表现,常常会表现出将财富遗传给孙子而非捐给社会的吝惜,因而对富贵者提出节俭和慈善的伦理要求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其实是难于践行的。
那么,孔子提出的“富而好礼”如何可能呢?我们知道,孔子所谓之礼,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一种的制度安排。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作为一种体现宗法等级体制的制度安排,它对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换都有明确而细化的规定,凡事皆有“讲究”,这是传统礼仪的形式化特征。可以说,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礼就是一个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性笼子,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无论是富者还是贵者甚至贫者,都有突破(向上为“过”与向下“不及”)这一制度性笼子的天然倾向,而且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一方面说明礼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道德合法性有它历史的局限性,譬如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各种规定就带有明显的道德歧视,再如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说,在将普通百姓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限制在最低层次的同时,又赋予了帝王将相“食前方丈”的伦理合法性。所以,一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必须要充分体现历史的进步,尤其必须体现出对弱者的权利保障才是一种好的和人们愿意遵守的制度,这就是说“富而好礼”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所“好”之“礼”必须是一种“好的或善的礼”,否则,基于“恶法非法”的理念,“富而不好礼”便可得到一种合法性辩护。有鉴于此,我认为,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增强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认同,这是我们当下道德建设的重大任务。
另一方面,“富而好礼”之“好”也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文明社会构建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何种制度安排,它都有着其相对稳定性的特性,孔子之所以时常梦想恢复周礼,就在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适应于宗法一体社会结构治理需要并因而具有一种天然合法性的好的制度,庄子所谓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讲“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安排的天然合法性。但是,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变动出现了新的分化形势,富裕起来的诸侯、大夫们自然会对传统礼制安排产生“分庭抗礼”的非分之想,礼制的调整或改革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孔子认为,不涉及到宗法体制根本方面的礼仪改革是可以的,但涉及到根本制度的变革则是不能容忍的,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尽管如此,僭越礼仪之事在春秋战国常见于史载,这说明“富而好礼”的道德要求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但是,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宗法一体的社会结构仍然把礼制当作为主要的制度安排,这说明礼制的存在具有历史的稳定性。这一历史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动之际,社会分化或分层是难以避免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及其诉求会挑战现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因而与时俱进地改革现行的体制机制是必须的,但不切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改革则是轻率的。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富裕起来的人们即所谓既得利益阶层能否“好礼”,能否为制度的合法性建设做出或多或少的牺牲,能否承担起自身应负的社会责任,这既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在,也是文明社会构建的必要道德条件。试想,在一个贫富两级分化的社会,若权贵骄人或有钱有权就任性得不到矫治,贫而生怨或仇富仇官的情绪则难免会衍生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以,“富而好礼”意味着富裕起来的人们更需要自觉地担当文明社会建设的责任。
总之,文明社会的构建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过程,它既需要加强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建设,也需要道德主体克服因富贵或贫穷所产生的坏的道德可能性,只有这样,“富而好礼”的文明社会才是可能的。
陈科华,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伦理学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