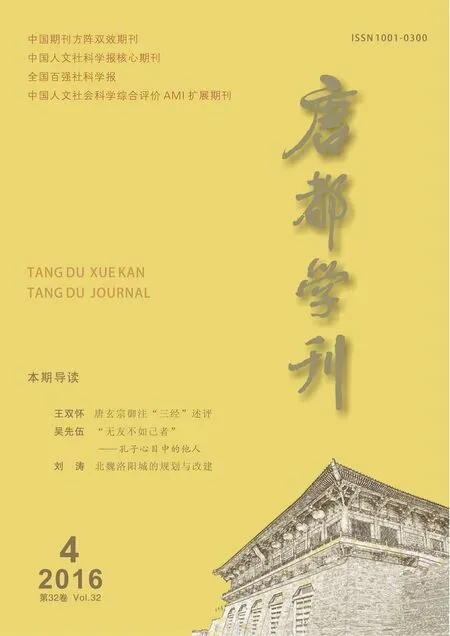西汉帝国和亲外交的国际战略透视
李源正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汉唐研究】
西汉帝国和亲外交的国际战略透视
李源正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从国际战略的视角来看,西汉帝国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和亲外交:一是作为一种“朝贡和平”的和亲外交,其代表是汉高祖时期采纳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开展的和亲外交;二是作为一种“联盟手段”的和亲外交,其代表是汉武帝时期细君、解忧公主与乌孙国的和亲;三是作为一种“抚远外夷”的和亲外交,其代表是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出塞外嫁匈奴。三种和亲外交都统一于西汉帝国的对匈战略。西汉帝国根据形势的变化,将和亲外交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有效解决了帝国战略资源有限性的问题,并在汉匈对峙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建立起帝国的霸权,重新塑造了地区秩序。
西汉帝国;和亲外交;国际战略
西汉帝国建立后,中原地区结束了战争状态,重新建立帝国的政治秩序。但北方的匈奴早已借助中国内乱的契机,整合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匈奴单于冒顿于公元前209年统一匈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1]2890与此同时,西汉的经济凋敝极其明显,“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1417。西汉帝国不得不面临着如何与强悍的匈奴相处的问题,国际战略的成败直接决定了帝国的生死存亡。在与匈奴的互动中,西汉帝国采用了和亲外交,并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一国际战略方式达170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当然,内外形势和帝国国际战略的变化也使不同类型和亲外交的目标和作用有显著的不同。通过运用和亲这种国际战略方式,西汉帝国最终在与匈奴的对峙中成功地制服了对方,建立起帝国主导下的霸权和地区秩序。
一、作为一种“朝贡和平”的和亲外交
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2]。它的内容是: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和平,即不遭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它是一种战略寓于外交之中的“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3]10。公元前200年,为了清除国内诸侯王韩王信的叛乱,同时打击韩王信的盟友匈奴,汉高祖刘邦组织了32万人的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在取得了先期几场战役的胜利后,轻率冒进的汉高祖“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1]2057。
刘邦反思了白登之围的教训,认为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匈奴问题,故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绥靖,即“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4]。刘敬的战略思想,是“势”与“谋”的统一。对“势”的强调体现在他先期对于帝国择都长安的建议上,“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1]2716。在对匈政策上,刘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1]2719。“谋”就是他提出的系统的和亲观,“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嫡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2719刘敬还系统分析了和亲外交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要遣具有皇室血统的公主并给与匈奴丰厚馈赠,同时对匈奴进行教化并拉近匈奴与汉帝国君主的血缘关系。“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1]2719高祖采纳了刘敬的意见,但是出于私人感情而用宫婢为长公主,远嫁匈奴,并命刘敬结和亲之约。最初的和亲并无明显成效,“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帝国仍苦于匈奴的侵伐和劫掠,直到“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1]2895。自此,主导汉匈初期关系的和亲外交正式形成。
但是,受制于匈奴单于更替(冒顿、老上、军臣)带来的政策摆动以及帝国叛徒(卢绾、中行说等)的叛汉助匈,西汉帝国的和亲外交成效几经打击。汉文帝三年(前177)、十四年(前166),匈奴两次大规模入侵,迫使汉文帝进行较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但“朝贡和平”终是断断续续地维持下来。西汉仍力图用“和亲”来维持双边关系,实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1]2903的战略目标。这实质上就是“基于互不侵犯和战略划界,并有违约制裁规定的朝贡和平条约体制。”[3]通过经济馈赠来部分解决游牧民族在物质上的匮乏,换取匈奴威胁下的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可能带来颜面上的屈辱。在面临威胁时,除迫不得已进行军事动员外,西汉更多地采用和平外交的手段来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尽管时常谴责匈奴无视道义的背约行为,“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1]2897。
白登之围与和亲外交决定性地塑造了西汉帝国初期的对匈战略,并形成了帝国君臣经久的历史记忆*吕后执政时,季布力驳群臣对匈开展的建议;汉文帝初期讨论对匈和战问题时,群臣主张和亲;汉武帝前期御史大夫韩安国反对王恢的建议,力主和亲;武帝时博士傅山主张和亲。参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张汤传》。。汉初“朝贡和平”式的和亲外交具有重大的价值。首先,它部分实现了维护和平的目的,这对于帝国医治多年战争带来的经济凋敝至关重要;其次,它使匈奴作为援助帝国内部分裂势力,干扰政治秩序,威胁帝国统一的重要变量的作用逐渐消失,西汉帝国得以赢得时间打击诸侯王的分裂和叛乱势力,巩固帝国内部政治秩序;再次,它将匈奴纳入到符合帝国利益的政治轨道上,使匈奴也认识到“和亲”应该是汉匈关系的主流状态,从而在几度背离和亲之后主动地寻求再次和亲。最后,它还具有改变匈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而“同化”匈奴的可能性[5]。
二、作为一种“联盟战略”的和亲外交
经过武帝时期三次大规模对匈奴的征伐后,汉匈关系中匈奴居于主导的态势彻底逆转,西汉逐渐掌握了双方博弈的主动权,作为“朝贡和平”的和亲外交已无存在必要,但汉匈双方的较量并没有结束,双方进入一种战略僵局,缺乏再次进行大战的能力。“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1]2911匈奴从进攻战略的立场后撤,几次重提和亲要求,武帝则采纳了丞相长史任敞的建议:“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1]2911不排除和亲作为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但要建立在匈奴称臣和匈奴太子入汉廷为质的基础上。新败的匈奴难以接受这一汉匈关系的新定位,而汉武帝也断然否定继续“朝贡和平”。拒不妥协使双方都进入到一种毁坏外交礼仪、拘留对方使臣的状态。“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1]2915外交的失效,使摩擦和冲突成为汉匈关系的主流。
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李陵进攻匈奴失利后,汉匈开始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双方对峙的僵局一时难以打破。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而西汉帝国也无法彻底根除匈奴的威胁。西汉帝国与匈奴的较量逐渐集中到战略意志和对外关系上。为打破战略僵局,双方都要争取盟友支持,都在争夺双方关系的主导权。汉帝国采取了扩张地盘与结交西域并举的策略。“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2913由此,汉匈争夺的主要场所转向了西域,争取西域重要国家乌孙的支持就成为汉匈较量的重要环节。西汉帝国开始推行一种“联盟战略”的和亲外交,力图组建共同应对匈奴的大联盟。这种联盟战略充满了曲折和个人牺牲,它同时还伴随着汉帝国的军事威慑和西域开发。这种战略约持续了50年,经历了武帝中期的进取试探,到武帝后期的狂躁冒进,再到昭宣时期的平稳审慎。长期经营和和亲公主个人的努力,使西汉帝国在这个进程中逐渐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无力影响乌孙到逐渐以大国的姿态掌控乌孙,并逐渐成为西域诸国合法的仲裁者。从面对匈奴的攻势和排挤,到逐渐将匈奴排挤出西域各国,消除匈奴的影响力。
汉帝国发现乌孙国,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1]3161武帝认为与乌孙国结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于是采纳了张骞的建议,“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6]2692。武帝不仅希望获得对付匈奴的盟友,而且还希望能够在西域建立汉朝的声望。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劝说乌孙王猎骄靡与汉合作后,武帝继而先后派遣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元封六年(前105),“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6]3903与此同时,匈奴也采取和亲政策,“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6]3903汉匈在乌孙展开了激烈争夺。细君公主“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6]3903她还遵从汉武帝的命令,按照乌孙昆莫的安排,嫁给昆莫之孙军须靡。但总体而言,在细君公主和亲时期,汉帝国在乌孙的影响力并不大。
细君公主死后,太初四年(前101)汉武帝又将解忧公主嫁给乌孙昆莫。解忧先后嫁给三位国君(军须靡、翁归靡、泥靡),甘露三年(前51)才返回长安。解忧与她的得力助手冯夫人通过高明的外交智谋以及机敏的时机判断,帮助汉帝国实现了重大战略突破。首先促成乌孙与西汉联手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和乌孙相约进攻匈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6]3786。当年冬季,匈奴对乌孙进行复仇,但酷寒的天气使侵略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6]3787。匈奴的衰落很快引起周边邻国的叛离,而匈奴主导的地区秩序也完全崩溃。“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6]3787由此,西汉帝国完全掌握了对匈关系的主动权,匈奴日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并最终丧失了与汉帝国较量的物质实力与精神勇气。“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6]3787其次,和亲的结果使汉帝国能将拥有帝国血统的公主子孙拥立为乌孙昆莫,并建立起帝国在西域广大地区的仲裁权。“冯夫人锦车持节,……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6]3907在此过程中,西汉帝国设置了西域都护,将这片区域纳入帝国的统治区域,“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6]3874。“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6]3874
自此,汉武帝制定并开始实施“联盟战略”,经过长达50年的运作,在宣帝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效。汉帝国不仅完全掌握了对匈关系的主动权,有效维护了自身安全,而且还逐渐介入到匈奴内部关系中,作为一个外部重要变量参与匈奴内部政局演变甚至是单于的确定过程。更重要的是,汉帝国将西域纳入到自己的统治区域,西域各国开始接受帝国的文明式的霸权和帝国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在竞争中,帝国逐渐将匈奴的影响力逐出这一区域。在这一阶段,和亲公主解忧和她的重要助手冯夫人发挥了重要角色,她们使帝国在乌孙的影响力从生根发芽到最后难以撼动。“随着匈奴在西域势力的收缩,乌孙最终走进了西汉王朝的羁縻体系之中。”[7]
三、作为一种“抚远外夷”的和亲外交
经过汉帝国与其西域盟友的联合打击,匈奴的国际权势被彻底摧毁,匈奴主导下的西域秩序也被颠覆。内外的变化使匈奴自身也在分化瓦解,不再成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在汉帝国的军事打击和自然灾害的相互作用下,匈奴逐渐克服了前期的和亲犹豫,到“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6]3787。但是,分裂的匈奴对汉帝国的边境安宁仍然存在着威胁。在此背景下,建立新的汉匈之间的关系互动模式,使匈奴成为帝国的可靠臣属就是帝国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帝国开始采取一种“抚远外夷”式的对匈战略,和亲作为汉匈关系中经久存在的历史记忆和实践经验,在这种战略的行使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抚远外夷”式的对匈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使匈奴彻底臣服于汉帝国,帝国保持对匈的优势地位;二是实现汉匈之间的经久和平,消除哪怕是小股力量对帝国边陲的威胁;三是用遣子入侍和单于来朝维系双方的关系,使之部分承担对匈奴进行教化的任务,使之“文明化”;四是对匈奴进行适当程度的支持,借助汉帝国的支持巩固匈奴单于脆弱且日益裂变的统治权。
宣帝五凤三年(前55),匈奴分裂,内战中居于弱势地位的呼韩邪单于率五万人归降西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驾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6]266。由此,匈奴的部分势力正式臣服汉帝国。次年,“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6]268北方安定使帝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边疆的安全环境明显改善。甘露三年(前51)和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朝见汉宣帝。而对与西汉帝国敌对的匈奴势力,帝国仍采取打击的策略。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帝国再次取得对匈的重大胜利,“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6]295。这种胜利兼具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它既是对匈奴敌对势力及士气的沉重打击,同时也是对匈奴亲汉势力的有力促动。“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6]3017同时,也有效促成了帝国声望和威慑力在西域的传播,汉使西域各国深刻理解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6]3015。在政治臣服之外,汉廷亦对匈奴进行援助,汉“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6]3798。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再来长安朝拜汉元帝,这次朝见的重要成果就是汉匈再行“和亲外交”。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汉帝国将宫女王昭君赐嫁匈奴单于呼韩邪,汉匈再次和亲。这次和亲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汉匈和平的基础有所扩展。和平不仅基于汉帝国的强势和匈奴的疲弱,而且还扩展到道义责任和情感维系上。双方都有和平意愿。匈奴表示,“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6]3803汉帝国希望“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6]297第二,和亲和双方交往缔造的和平存续了较长时间。“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6]3833第三,匈奴继续臣服于汉帝国。“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籓,宾于汉庭。”[6]3832西汉河平四年(前25)和元寿二年(前1),匈奴复株累和乌珠留两位单于先后来朝,匈奴单于同时不断遣子入侍。第四,匈奴承认汉帝国在西域的主导和仲裁权。哀帝建平二年(前5),匈奴与乌孙纠纷,汉帝国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制止匈奴要求乌孙派遣人质。匈奴还交出了叛汉降匈的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同时,借助于帝国帮助匈奴积累的道义优势和匈奴的感恩心理,匈奴接受了汉帝国提出的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6]3819。
在西汉帝国存续的最后阶段,总体上与匈奴维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与中国史上其他朝代末期边疆纷乱的现实相比,西汉帝国在最后阶段的对匈外交及其战略堪称成功。在此期间,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帝国在西域建立起一种文明式的霸权,从而塑造了区域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也将匈奴纳入其中。
四、和亲外交的战略效用之反思
西汉帝国在其存续的210年间,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北方匈奴关系的问题,其政策选择复杂而多样,按照班固的总结,就是“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6]3830。但班固仍低估了和亲的作用。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汉帝国不断对战略效果进行评估,但无论是以妥协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和亲政策都贯穿于对匈战略的始终,并有不同的成效。
和亲外交的战略效用发挥有其必须的条件。首先,和亲外交必须建立在帝国的实力基础上。西汉帝国最初选择和亲外交是国力羸弱时的必要选择,它是一种弱者进行适度的牺牲而谋求与强者和平共处的妥协之道。因而,它缺乏帝国实力的保障。和亲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它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平。虽然帝国君主屡次下达诏书,希望与匈奴,约为兄弟,各守边境,互不背约,但并没有得到匈奴的主动响应。而后来与乌孙和亲,以及昭君出塞,则是建立在帝国强盛权势的基础上,并使和亲对象在心理上接受汉帝国的影响力,所以较为可持续。
其次,和亲外交必须建立在与帝国其他战略手段相配合的基础上。帝国对匈战略毫无疑问包含着以和亲为代表的外交,也包含以征伐为代表的武力以及以羁縻为代表的联盟。这三者虽然不同时期在帝国国际战略中的主导作用不同,但却是同时存在的。在“朝贡和平”时期,汉帝国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并采取羁縻政策对匈奴内部进行分化。汉帝国既注意发挥和亲的重要作用,也适度进行征伐,保持军事的威慑力。可见,只有使和亲外交与其他对匈政策工具联结起来,形成动态的政策组合,才能将和亲外交力图实现的战略效果最大化。
再次,和亲外交需要持续的双方良性互动。在帝国初期的和亲外交中,帝国没有也无力实现双方关系的良性互动,除了送出和亲公主和馈赠匈奴钱帛,并用外交使节对匈奴进行适度的教化外,帝国毫无办法,最好的结果只能是在双方关系破裂后通过外交努力重回和亲的旧轨。它是一种力求不至于太坏的战略。更何况在双方叛徒(主要表现在帝国投降匈奴的叛徒)的挑拨下,双方始终存在匈奴背约的现实威胁。但在帝国中后期的和亲外交中,和亲伴随着持续的使臣往来、军事合作和战略配合,双方关系实现了较好的互动,从而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最后,和亲公主的个人因素也极其重要。“朝贡和平”时期,西汉帝国虽然多次对匈进行和亲,但现有的史料并没有记载和亲公主的作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记载。但在武帝之后,细君、解忧公主和王昭君的个人因素在和亲外交中体现出来,她们配合并实施了帝国的战略,有时甚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总之,和亲外交从属于更广泛的汉帝国对匈战略,这种战略应对的核心议题就是帝国如何处理与北方强邻匈奴的关系。从帝国初生到最后的王朝倾覆,对匈战略先后经历了力争和平、彻底击垮和谋求共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战略调整是在高祖、武帝和宣帝三位君主执政时期推行的,它符合帝国的国力变化要求,也深深地打上了帝王个人的性格特征。总体来看,和亲外交在实施中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帝国战略资源有限的问题,并在汉匈对峙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建立起帝国的霸权,并按照帝国的意志重新塑造了地区秩序,匈奴最终被纳入到帝国主导下的政治秩序之中。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时殷弘.从“朝贡和平”到决战决胜:汉初80年的帝国对外历程[J].文化纵横,2011(3):120-123.
[3]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6):4-33.
[4]时殷弘.《史记》早该这样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24.
[5]李大龙.“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3):50-5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石少颖.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40-344.
[责任编辑朱伟东]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Peace-makingMarriage Diplomac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 Yuan-zheng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is paper re-analyzes peace-making marriage diplomacy in the Western Han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eliev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in the Western Han Empire. The first type was thought to be “Tributary Peace”, represented by Liu Jing’s suggestion to Liu Bang, Emperor Gaozu of Han. The second was believed to be “Alliance Method”, represented by the marriages of Princesses Xi Jun and Jie You and the Kings of Wu Sun State. The third was considered to be “Governing of Minorities”, represented by the marriage of Wang Zhaojun and the chief of the Xiongnu. The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diplomacy served well in the strategy of Western Han to Xiongnu, an ancient nationality in China. The Western Han Empire resorted to the peace-making marriage diplomacy in polic-making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succeeded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the strategy resources. As a result, the Western Han Empire established its hegemony and gradually reshaped the regional political order during the standof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estern Han Empire and Xiongnu.
Western Han Empire; peace-making marriag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K234.1
A
1001-0300(2016)04-0030-05
2016-03-09
李源正,男,河南潢川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兴经济体对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