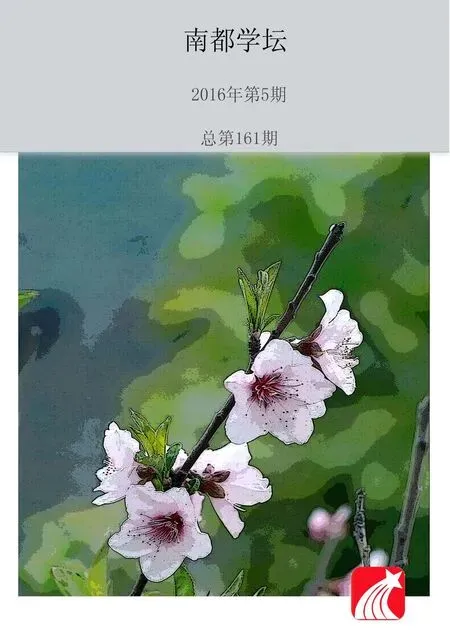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臧 知 非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臧 知 非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西汉前期的政治转型要求学术为现实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思想支持,要求士人的知识才干直接服务于军政实践,东方朔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落后于时代需求,距“大臣”标准甚远,仕而不遇是历史必然,所谓“朝隐”是腾达无望的自慰之语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
东方朔; “朝隐”; 政治转型; 价值取向; 仕而不遇
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为官数十年,位卑俸薄,以放诞滑稽著称,以“朝隐”自喻,在其死后不久即不断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下,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为后世文人所激赏,也为现代学者所重视,人们在深入发掘其文学、艺术、民间文化等方面贡献的同时,分别从文化、政治等方面解读其“朝隐”的由来和仕途沉滞的原因:或者以为东方朔虽然学问超众,但是华而不实,实际能力有限*持此观点的代表作有孟祥才:《东方朔简论》,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成、张景林《论东方朔的政治心理——中国传统恩宠政治文化性格的典型个案分析》,载《南开学报》2015年第6期。;或以为东方朔有着儒家和道家的双重性格,还保留着先秦士人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难以融入其时政治秩序中去*持此说者主要有王继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儒者:东方朔》,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陈兰村、张根明:《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与文学创作》,载《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谭慧存:《论东方朔朝隐思想》,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笔者以为,仅此是不够的,要从政治转型与士人价值取向的层面,分析东方朔仕而不遇的深层原因,从而深化对景武时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认识,理解其时政治变迁与士人命运的关系。故为此文,稍补时论之不足。
一
为便于展开,先要从思想史的层面对东方朔的知识结构和仕宦经历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汉书·东方朔传》谓东方朔风流倜傥,知识驳杂,志向远大,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少年即学习从政为吏的基本知识,即“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1]卷六五,2841。这里的“学书”并非学习写字,而是学习“史书”,即为吏需要掌握的法令、文书。所谓“文史足用”就是指经过“三冬”即三年学习掌握了为吏的法律和行政知识。这里的“三冬”是三年的意思,并非注家理解的三个冬天*如淳云:“贫子冬日乃得学书,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引同),第2841页。关于“史书”含义,参见拙作《〈史律〉新证》,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第二,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阵法。学兵在前,习儒在后,既掌握系统儒学知识,也掌握系统兵学知识,同时任侠使性。“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1]卷六五,2841这里的“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并非仅仅学一年以后就弃武从文,放弃学剑,在当时尚武风气之下,任侠是普遍风尚,以一个十五岁少年,绝不会学习一年以后而放弃,而是指先习剑后习《诗》《书》。所谓“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只是顺序概念,并不是绝对的时间含义。也就是说,在“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放弃练剑。同理,在十九学兵法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诗》《书》的研读。
第三,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所谓“十六学《诗》《书》”,《诗》《书》是儒家经典代称,这里的“十六学《诗》《书》”是指16岁开始系统学习儒家学说,此后在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的同时继续儒学的诵读,从东方朔劝谏汉武帝所透露的思想倾向来看,东方朔是在儒家君臣观念指导之下为官的。
第四,对法家学说有较多了解,兼习其他学说和民间术数。东方朔曾经上书汉武帝,“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1]卷六五,2863-2864。不仅在理论上了解商鞅韩非之说,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把握,充满着自信,才专以商、韩之言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并“欲求试用”。这“欲求试用”的“农战强国之计”具体提出时间不明,从历史背景分析,很可能与汉武帝的财政改革有关联。从其行为可知对民间术数杂学的知晓,射覆之术就是典型体现;其不拘礼法、狂放不羁、敏捷怪诞,被列入《史记·滑稽列传》,表现其道家任性而为的行为特征。而从东方朔与汉武帝的应对中,又不难看出其纵横家的风格。
第五,理想是做“天子大臣”。谓“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廉若鲍叔,捷若庆忌,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1]卷六五,2841。 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东方朔也因此被认为是“高自称誉”的典型。因为以一个22岁青年,既没上过战场,也没有像当时的刺客死士那样为他人出生入死,更没有从政经历,既不知道拼杀的残酷,也没有尝过权力所带来的快慰和好处,就说自己“勇若孟贲,廉若鲍叔,捷若庆忌,信若尾生”,显然是自我夸饰,其目的是通过“高自称誉”以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得到重用,希望成为“天子大臣”。贾谊曾论述过何为大臣:“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2]132东方朔之“大臣”的标准未必如贾谊所言,但是,按照东方朔的自诩以及后来和汉武帝的应对,他所说的“天子大臣”绝非一般的官吏,而是天子的辅佐之臣。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朔欲做“天子大臣”并非完全的高言求鬻,并非东方朔的政治品质有问题,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一般文职官吏和专业人员,经过学室培养,背诵指定的文书若干言即可授予相应官职。如当时有《史律》专篇,规定史、卜、祝的任职条件、考核和升迁办法,其中史是基层文吏,卜、祝是官府祭祀等神职人员,都以诵书若干为任职条件,如“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3]80。为史之后,根据考课情况依次升迁。参加考试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史、卜、祝之子,另一类是社会青年。卜、祝有专业的特殊性,世袭特点明显,应考者以现任卜、祝为主,而史的数量庞大,不具有世袭性,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出任,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可以看作这一制度的体现。若按照诵书多少任职高低,诵书五千言是出任公职的起点,可以为史,东方朔诵书四十四万言,外加各种“美德”,自然够得上“天子大臣”的资格了。而汉武帝少年即位,处于旧臣包围之下,急于打破旧格局,急于招揽人才,以便有大作为,较少顾及朝廷礼法,如私聚少年,出宫行猎游戏,既满足个人喜好,又了解社会民情,同时寻找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作为自己的班底,所谓羽林、期门之士就是这样产生的。东方朔了解武帝这个特点,夸饰自荐,君臣之间,颇有相得之处。所以,汉武帝欣赏东方朔的“文辞不逊,高自称誉”而“伟之”,只是没有轻信,要待事实检验,故“令待诏公车”[1]卷六五,2842。
众所周知,汉武帝虽然对东方朔以“伟”视之,无论东方朔语言行为如何乖张,始终是宽宏大量,对东方朔的“直言切谏”也“常用之”, 但所用均非军国大计,始终没有委任实权,东方朔的“大臣”梦最终没有成真。主观上“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客观上终其一生“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1]卷六五,2864。东方朔在晚年曾为此作《答客难》解释其原因,认为自己之所以学贯古今而仕途不达,并不是因为能力德行存在问题,而是因为时代不同,自己才华无从施展,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辏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1]卷六五,2845。尽管班固将东方朔的《答客难》定义为“用位卑以自慰谕”,但是,从中倒是透露出了东方朔的自我定位及其价值追求与时代的反差,为我们认识东方朔的价值追求与汉武帝时代政治实践的距离提供了真实的写照,为我们分析西汉前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笔者以为,我们不应该将目光局限于东方朔个人际遇,而应放宽视野,从思想史、学术史的层面考察西汉前期知识分子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从而说明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历史归宿。
二
东方朔年22岁上书,待诏公车,具体是汉武帝哪一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武帝即位初年的事,其学文史、学剑、学兵法、学诗书等等都是在景帝时代完成的。这时正是汉家政治的转折——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转折时期,体现在思想上的变化则是适应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在诸子复兴的历史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地占据主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东方朔之辈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这才是其仕而不遇的深层原因。
刘邦立国,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同姓王,“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4]卷一七,802。其目的是用骨肉血缘关系、以道德伦理实现刘家天下的千秋万代。此举在刘吕之争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恢复汉初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有着积极影响,也正是因为分封制度,汉文帝才得以入继大统。文帝明白,自己继承皇位是开国元勋平衡选择的结果,并非唯一合适的人选,之所以选择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能对元老重臣构成威胁,自己要想坐稳皇帝的宝座,必须保住元勋们的既得利益,满足其权势需求,而不能像吕后那样掌权以后一方面扩张吕氏实力,剪除刘氏宗室;一方面挤压元老们的利益空间,所以即位之后对元老们恭敬有加的同时,大力优待宗室,恢复被吕后剥夺的诸侯王的利益,加大对诸侯王的赏赐力度。在保证皇位稳固的前提下,全面实行无为政治,轻徭薄赋,把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
汉文帝的无为政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的,其“无为”并非政治、经济上的不作为,而是指减少对外用兵和公共工程,减轻农民徭役负担,而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则是大有作为的。文帝十五年九月,晁错在《贤良对策》中有过概括:“肉刑不用,罪人亡(无)孥;诽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蘖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1]卷四九,2296-2297。晁错所言,属于制度性变革者,都有明确年代。如“肉刑不用”即废除肉刑在十三年夏*《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十三年文帝诏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第427-428页,详见《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罪人亡(无)孥”即废除连坐制度在文帝元年十二月*《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第418-419页)。《汉书》卷四《文帝纪》云:“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第110页);“诽谤不治”在文帝二年二月*《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文帝诏云:“古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第423-424页,又见《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8页);“诸侯至国”在二年冬十月*《汉书·文帝纪》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诏曰:‘……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三年冬十一月,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第115、117页);“铸钱者除”即废除禁止私人铸造钱币的禁令在五年四月*《汉书》卷四《文帝纪》: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第121页)。;“通关去塞”即废除检查出入关塞者身份及其携带物品的制度在十二年三月*《汉书》卷四《文帝纪》:十二年三月 “除关无用传”(第123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面世后,我们可以了解此前出入关塞人员的证件、物品检查情况,详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下引同此),第83-88页。对《津关令》的研究参见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载《历史研究》2002年3期。;“尊赐孝悌”在十二年三月*《汉书》卷四《文帝纪》十二年三月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第124页)这“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是为常制。;“农民不租”在十三年六月*《汉书·文帝纪》十三年六月,诏云:“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第125页)按:关于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税是免除当年一年还是此后一律免除,学界有争议。直到景帝即位才恢复,但税率降低一半。详见拙文《汉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税新证——兼谈汉文帝经济政策》,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2期。。所以说,就制度变革而言,文帝一朝并非后人理解的那样“无为”而是很“有为”的。正是这一系列的“有为”为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谓文景之治,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制度上、政策上,都是以文帝时代为基础的。
文帝时代不仅是经济大发展时代,也是文化大活跃的时代。这一方面是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活跃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分封制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政治空间。其时之社会稳定与无为政治对思想活跃的影响及其体现,先贤已有论述,无须赘言*关于战国诸子余绪在西汉初年的活跃,首先是侯外庐先生指出,见氏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西汉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分封制与思想活跃的关系。刘邦时代,诸侯王国初建,大权掌握在汉廷派遣的丞相、太傅手中,这些丞相、太傅虽为功臣但大都出身下层,和汉廷大员的文化水平和行政特点相近,重厚少文,一切按照传统也就是秦朝传下来的制度法律行事,谈不上文化建设。吕后时代,大力剪除刘氏宗族力量,刘氏诸王能够自保已经幸运。文帝时,诸侯王才真正地扬眉吐气,势力迅猛发展。其中既有经济力量的发展,也有思想文化的复兴、学术自由的再现,各王国都聚集着数量众多的文人士子,其学派构成更是各种各样,其社会影响远远大于朝廷,构成西汉前期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众所周知,刘邦君臣出身下层,“马上”得天下,看不起士人,尤其看不起儒生,因为陆贾的一番批评,才使他们认识到打天下和坐天下的区别,知道了总结亡秦教训的重要,改变了刘邦的看法,揭开了朝野上下“过秦”的帷幕,也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历史之门。但是,限于认知水平,刘邦君臣仅仅是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并没有在制度和政策上给知识分子提供出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朝廷大权均掌握在功臣手中,也不允许知识分子有多大的政治空间,士人仅仅是通过报复式地批评秦政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诸子传人可以继续其所学罢了。而诸侯王国力量的发展,则为士人提供了政治空间。
本来,王国的百官设置和汉廷相同,但其选拔任命则是王国内部的事情。王国初置时期,诸王年幼,权力掌握在傅、相手中,傅、相由中央任命,多出身功臣,受到其学识和政治视野的限制及历史的惯性,任用的官僚,固然首选文吏和军功爵者,但是王国分布于关东,军功爵者有限*刘邦立国,新兴一批军功贵族和军功地主,但刘邦的核心集团是入关的丰沛子弟,取得天下的主力则是秦人,军功集团的主体是秦人和丰沛子弟,而丰沛子弟回乡者只有一部分。所以,尽管无法统计关东吏民在汉初军功集团中所占比的数量比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军功集团的空间分布来说,关东吏民远少于关中。,却是诸子传人分布的地区,而王国初建对官僚的需求又远大于朝廷,这在客观上为士人出仕提供了历史空间。因而,各王立国之后别无选择地要任用本国内的知识分子。历经惠帝、吕后时代,诸侯王长大成人,亲理国政,士人逐步地进入王国的官僚队伍之中,王国成为知识分子的乐土。所谓西汉初期子学复兴,和这个政治结构是分不开的。在任用知识分子方面,汉廷是远远落后于王国的。汉文帝注意到了任用士人的重要性,也曾经想打破功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下诏选拔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士,讨论时政得失,任用知识分子,但是很快淹没在功臣的抗议声中,仅仅一个贾谊也被赶出朝廷,汉廷为士人提供的舞台实在有限,士人自然地把目光投向王国。
从空间分布的层面,对西汉前期子学复兴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诸侯王国在其时文化繁荣过程中的作用。这由齐国首开端绪。刘邦封刘肥为齐王,命曹参为相。曹参治齐伊始,即“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经过反复探寻,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4]卷五四,2028-2029。战国时代,齐地是东方思想家的聚集地,学术传统深厚,在秦朝所受压制也最为严重,故齐国初立,即纷纷献上强国之道,最后曹参选择了黄老,这也是后来汉家以黄老治国的基础。无论是齐王刘肥,还是曹参,他们并没有复兴文化的自觉,他们招来士人无非是咨询治国理民的具体方法、壮大齐国国势而已,但是,在无为指导之下放手社会经济发展,也放手思想文化的活跃,这为齐地的学术复苏、自由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齐国成为汉初东方学术复兴的中心。后来吴王刘濞、淮南刘安、河间献王刘德门下都聚集了众多的士人,说明了西汉前期政治格局对于子学复兴所起的作用。
西汉前期子学余绪的活跃是全面的,除了墨家寂寂无闻未见史册之外,儒、道、法、纵横、阴阳、黄老各派以及兵家、文学之士都倚重诸侯王国,活跃空前,并形成几个有着学派色彩的学术中心。如齐国以黄老为特色,河间、楚国均以儒学为特色,淮南以道家为特色,吴王刘濞则以实用为原则,重文学,蓄养宾客谋士。在这一背景之下,只要有知识有文化,总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同理,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必拘泥于哪一个学派,只要有助于功名利禄,都兼收并蓄,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东方不亮西方亮,朝廷不用就到王国去,这个王国不用就到另一个王国。士人读书目的不是为了分析批判现实,而是为了谋生,增加谋生的本领,只要现实有需要,学习内容并不限于哪一家哪一派,统统为我所用,多多益善。也就是说,西汉前期学术虽然活跃,呈自由之势,但是和战国诸子之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一,汉初士人价值观以服务现实为核心,根据现实需要,论证现实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对策性的见解。众所周知,汉初子学活跃是以“过秦”为背景的,“过秦”的目的是希望汉家统治者吸取亡秦教训,按照自己说的意见办,尽管意见各不统一,但都是为了巩固汉家江山,从而使自己的主张变成现实,也为自己换来政治前途。其二,因为各家各派的传人主观上都有批判秦政、服务现实的自觉,因而都能或多或少地自觉地摒弃门户之见,彼此吸收、认同或者部分认同其他主张,丰富自己的学说和现实见解,以期得到当政者的青睐和采纳。这个过程在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只是那时的认同还缺少政治自觉,经过秦汉鼎革的历史变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服务现实的政治自觉之路*关于战国秦汉士人价值观转变,参阅拙文《秦汉历史转折的思想史分析》,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7期;《由“理想”到“现实”:秦汉之际儒生价值观的历史分析》,载《湖湘论坛》2011年第3期。。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东方朔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的由来了:就是学以致用,多多益善,“文史”是为吏的基本要求,是学习的首选;现实需要的多样性,则是学习兵学、儒学、术数的动力和基础,以为学富五车可以博得功名利禄。但是,东方朔误判了时代的脉搏,其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已经不符合现实政治发展的需求:其知识确实丰富,但学无所宗,不明大道,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而其价值观念的滞后决定其仕途不畅。
三
刘邦分封同姓王的目的是希望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实现政治上的尊卑有等,从而使刘氏一族抟心辑志、巩固汉家江山千秋万代,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王国实力强大,与中央王朝的实力对比改变,全国大部分人口、土地控制在王国之下,王国与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明显。贾谊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试图在不伤及皇族亲情的前提下采用“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办法削弱王国对中央的威胁,但是限于当时政治格局而收效甚微,而把这一问题留给景帝来解决。景帝以平定七国之乱为契机,在制度上杜绝王国势力坐大的可能性,继续文帝的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同时,降低王国政治规格,剥夺诸侯王治国的权力,由相、内史综览王国军民政务,只对中央负责,按照统一法令治理王国,不受诸侯王节制,所谓诸侯王名为王国之君,实际上“衣食租税”而已。因为王国独立性大大削弱,没有了独立的用人权,依附于王国的士人群体在思想意识上也逐步明白大一统的无上性,要想获得政治出路,就必须在思想上和朝廷政治需要保持一致,要直接或间接地论证现实政治大一统的合理性、正义性,这就要有新的理论建树。这是新形势提出的学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完成这一理论体系建构的是董仲舒。
战国诸子,除了庄子,尽管相互辩难以至于攻讦,但有三点相通:一是政治统一;二是尊卑有序;三是王权至上。无论儒家各派,还是法家、阴阳、黄老、墨家,在这三点上并无本质的分歧,只是理论基础和实现方式有别而已。至战国后期,诸子学说的政治立场已经逐步一致,经过秦汉更迭,过秦讨论,更获得了进一步的认同。董仲舒就是在这个历史基础上,以现实政治体制和制度合理为出发点,以儒家伦理政治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手段,论证了汉家大一统的神圣性,把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嵌入现实政治秩序之中,建立了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从而获得了汉武帝的赞同。所有这些,都是在景帝时代完成的,是以西汉前期的政治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建构是和汉景帝的政治变革同步的,起码在理论上说明景帝变革的正义性。所以,在汉武帝下诏求举贤良方正的时候,董仲舒之学才能为汉武帝所用而迅速意识形态化。尽管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1]卷五○,2317,没有按照董仲舒所主张的仁义德治施政,但是其“多欲”是在“仁义”的旗号之下进行的,是汉武帝“仁义”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学说为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提供了仁义的辩护,或者说汉武帝的多欲政治借用了董仲舒的仁义辩护,在仁义名下,推行的是功利政治:强化君权、强化大一统、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官僚选拔和使用上,看重的是能力和军政政绩,而不是理论学识。凭借知识、思想、学说赢得君王尊重、以君王师友身份自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明乎此,我们对东方朔的仕而不遇就多了一层理解:这就是东方朔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不符合汉武帝的要求。尽管汉武帝下诏求贤,但这个贤是有着时代标准的,东方朔自以为博学多才就能为“天子大臣”,认为自己的能力才干远远在当朝重臣之上,如果不是故意高言求鬻的话,就是对时代政治认识存在偏差。从其《答客难》以及与“非有先生”对话的内容来看,东方朔对自己境遇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认为是生不逢时,不是才华能力问题。
东方朔曾经多次上书言事,建言献策,有的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的多与礼法有关,是为了维护君臣尊卑,能够维护汉武帝的尊严,其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则石沉大海。其为现实贡献才智的愿望大多落空。这些众所周知,不予赘举。这还有着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东方朔的一系列言行表明,在其内心深处,多少保留着一些“士”的孤傲,对汉武帝还有些“道德”的要求,希望帮助汉武帝把个人好恶限制在礼法范围之内,没有无条件地迎合。但是,从汉武帝时代官僚队伍的知识结构和用人标准来看,主要原因还在于对当时政治需要没有清醒的把握,还在于其知识结构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虽然随侍汉武帝左右,既不能针对现实理论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些许思想资料,也不能对军民政务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修补国计民生;而行为的荒诞,更非“天子大臣”所应为。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把东方朔视为“朝隐”的代表——所谓“朝隐”不过是自嘲之词而已。遗憾的是,东方朔并没有意识到仕而不遇的真正原因,今人则不可不知。无论是把握东方朔个人,还是把握汉代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沉浮,离开其时学术、思想与政治结构互动的历史逻辑是难得确解的。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贾谊.贾谊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刘太祥]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Dong-fang Shuo’s Unsuccessful Political Experience
ZANG Zhi-fei
(Society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 requires the academy to provid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effective ideological support and requires the intellectuals to serv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with their intelligence. However, Dong-fang Shuo’s knowledge and value orientation cannot meet the times’ need and are far from the standard of officials, as a result of which his political experience is inevitably unsuccessful. Actually, the so-called “hiding in the court” is just his self-consolation but not his subjective choice.
Dong-fang Shuo; hiding in the court;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value orientation; unsuccessful political experience
2016-06-02
臧知非(1958—),江苏省宿迁市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教学与研究。
K234
A
1002-6320(2016)05-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