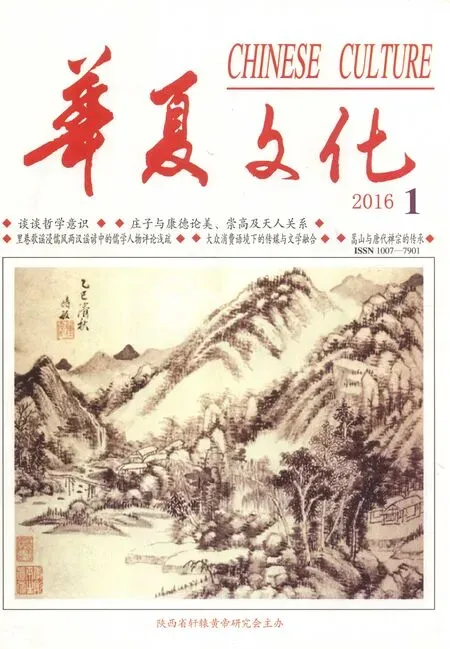大众消费语境下的传媒与文学融合
□柯弄璋
大众消费语境下的传媒与文学融合
□柯弄璋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已然进入肇始于西方的所谓“消费社会”,不但处于“物的包围”当中,而且沉浸于符号的“眩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里,认知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对于符号所指对象的淡漠抵触甚至消解了一切有涉深度的感知,以至于在大众阅读领域,“浅阅读”“轻阅读”蔚然成风,而针对传统文学(经典文学)的深度阅读与品评萎缩为专业者的看家本领或拿手游戏。于是,关于文学危机感以及出路的商讨与争论不绝如缕。面对如此艰难又混杂的探寻,唯有首先进入当下大众消费语境中,尝试厘清文学与传媒的融合模式。
1. 传统文学式微及传媒内容诉求
关于传统文学式微的典型案例是莫言的“诺贝尔效应”余波。在2012年莫言获奖后,带着明星的光环,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轰炸”,其作品一度一纸难求,然而它们最终却没能避免退货的命运。有出版界人士指出,“950万元码洋被退货,按照每本书定价40元来算,意味着在过去一年(2014)里,有23万册由某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到了书店却没有卖出去”(邵岭、黄启哲:《莫言作品遭遇年底结单退货引发关注》,《文汇报》2015年1月13日)。虽然传统文学如今的处境多少有些不堪,但很多人试图从本体和功能两方面阐述文学的独特性,进而维护其合法地位。前者如认为文学能够“表达复杂人类经验”,好比马克思评价巴尔扎克等小说家提供了比政治家、道德家和新闻记者更多的东西;后者如认为传统文学区别于网络文学能够满足已经分化了的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正像楚人有的好闻《阳春白雪》有的爱听《下里巴人》。当然,这不失为一种有说服力、容易理解的且老生常谈、非历史化的辩护手段,而美中最大不足在于自说自话,未能改变什么。文学的历史主义者则不但要苛责这种做法,而且愿意在立足当下的基础上放眼于未来。
当下,与传统文学式微同行并互相关联的重要现象是传媒文学的兴盛,即文学媒介化的涌现,包括影视剧的改编、网络小说的流行、文学的商业炒作(如“脑瘫女诗人”)等,尤其是一些被命名为“80”“90”的年轻作家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除去他们自身以文学方式顽强表现自我的主观因素之外,也借助了诸多外在条件与文化势能,这一点甚至是更为主要的。新的传媒的兴起,特别是网络传媒的强势登场”(白烨:《“80后”文学研究的新高度》《文艺报》2015年6月8日),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试想当年如果没有博客、没有榕树下,韩寒、郭敬明还能像今天这么有影响力吗?在传媒文学兴盛背后依托的是传媒产业的“整体繁荣”,“根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统计测算,2014年全年传媒产业总值达11361.8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万亿大关,较上年同比增长15.8%”(崔保国、何丹嵋:《2014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传媒》2015年第6期下,第11页)传媒产业产值逐年增长。传媒产业的“繁荣”一方面离不开技术、金钱、营销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内容生产也特别重要,“传媒的基础是内容,内容可以创造品牌,可以成就未来”(任慧、曹珊、李巍霞:《媒介内容产业生产趋势、困境与治理机制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12期,第57页),如2004-2006年的“超级女声”选秀活动以其海选-复选-晋级赛-pk赛-复活赛的全新赛程设置和专家评委-大众评委-短信投票的创新评选机制而“名”“利”双收。突显内容意味着媒介内容化,也预示着媒介文学化,即可以吸取传统文学尤其是小说中十分丰富、充满创新的内容,打造高品质的精品传媒模式。
2. 传媒+文学的协同生产模式:以电视包装、游戏开发为例
媒介文学化,或说传媒+文学的生产模式较早出现在软广告中。相比硬广告的简单粗暴,软广告的优势在于以温情含蓄又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输信息。这种加工方式大都用一定的场景和故事情节,重在服务于目标群体的情感需求,巧妙地将销售产品的品牌、功能等信息穿插其中。营销人员设计情节就好比小说家创作故事,场景的安排则像美文家对景物的精心配置。然而,软广告作为广告毕竟怀着宣传的根本目的,文学加工必须服从于功利性诉求,这导致它的文学性扭曲,以至于人们有时观看某个软广告时感到特别矫揉造作、如鲠在喉。传媒+文学的发展出现在近些年来的电视栏目包装和手机游戏开发中,因为这二者的首要目的是最大程度上满足目标群体的体验,即将产品精品化而非宣传,所以与文学加工达成融洽的合作,形成良好的观赏与娱乐效果。
2013年以来,以《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领衔的户外真人秀电视栏目在国内的电视、电影市场广受欢迎,这不仅与它们的节目理念如“亲子户外游”、“传递快乐与正能量”等有关,也与它们的栏目包装不可分离。栏目包装是指栏目内容的精心设计(包括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和栏目后期的精心制作(包括场景切换、旁白字幕、配乐等)。以《爸爸去哪儿》为例,“主持人/村长”这一人物就至少有三种功能,“第一,主持人首先作为规则的人化代表出现,是规则的代理人;第二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任务发布者’存在,他成为起因,导致了每一个故事的发生;第三,衔接故事事件,在节目中,每一次主持人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一任务的终结和下一任务的出现,成为连接每一个事件的节点”(张乃瑜:《〈爸爸去哪儿〉的叙事学分析》,西北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1页)。制定者、发布者、连接者三位一体是在白雪公主、牛郎织女等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原型结构。在这些故事中,“恶人”(继母、王母)既是禁忌的代理人,也是致使“主体”(男主角)追寻“客体”(女主角)的重要诱因,还是情节变化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该节目中的“嘉宾”由父亲与子女构成五个小组,组内亲子之间父亲是子女的“协助者”,有时也是子女的“反对者”(如为锻炼孩子让其独自完成某个较难任务);组与组之间既有互相协作,也有竞争。栏目包装中的故事扮演则是《爸爸去哪儿》这类节目中最为关键也最为出彩的地方。《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中就有在新叶村孩子们的古代童生扮演和父亲们的无节操舞台剧扮演,以及在呼伦贝尔草原中挤牛奶和抓羊的扮演。《奔跑吧兄弟》第二季中也出现了超体元素、锦衣卫、西域商队等故事扮演。这些扮演都是挪用人们已经知晓的故事或场景,像克里斯蒂娃所说,“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它们之间形成互文性关系,而后来者采用诸如“扩展”、“叙述视点转换”、“故事性转换(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及人物阶层的变化)”“主题倒转”(弗兰克·埃夫拉尔著,谈佳译《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等变换手法尤为重要。
在栏目后期制作方面,《爸爸去哪儿》的场景转换一般由四帧画面组成,待嘉宾们睡觉熄灯后,首先是暗夜天空中的月亮,其次是远长镜头中清晨薄雾笼罩的大地与村庄,接着聚焦盛着露珠的叶子或雨后郁郁葱葱的树木,最后回到嘉宾住处的外景。作为承前启后功能的承担者,这些看似简单的画面集中了动静、虚实、远近及颜色、音响、造型的变化,仿若一篇优美的诗歌,如杜甫《晨雨》“小雨晨光内,初来叶上闻。雾交才洒地,风逆旋随云”,又如沈从文笔下渐次铺展开来的清新边城、汪曾祺小说中灵动活泼的庵赵庄。而《爸爸去哪儿》的旁白字幕类似副标题、题词、插图等“副文本”,对节目内容起着补充、渲染的作用。如第二季第一站中Joe痛苦流泪时配以“崩溃”的红色文字,解说和强调人物内心的激烈情绪;第二站扮童生时字幕变为竖版手写体,以造成较逼真的现场效果;第七站杨阳洋说到六眼飞鱼时字幕真的出现了一只背上有六只眼的鱼,形成幽默滑稽的气氛。此外,配乐也是后期包装的重要元素,不仅包括主题曲、插曲,还有场景音响。《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都有耳熟能哼的主题曲《爸爸去哪儿》、《超级英雄》,还会配备一些相得益彰的插曲,如《奔跑吧兄弟》第一季的“新年运动会”中,王宝强跳着模仿孙悟空入场,就配合着1982年央视版《西游记》的片头曲。场景音响则十分常见,如《奔跑吧兄弟》中嘉宾踩在指压板上“嗞嗞”的电流声。这些配乐不仅是节目的“副文本”,而且它们自身会构成一个审美视听空间,让观众感动、激动、欢笑。
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和中新游戏研究(伽马数据)国际数据公司分析统计,近年来移动游戏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仅2014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就比2013年增长了144.6%,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移动游戏产品,如《刀塔传奇》《雷霆战机》等竞技类游戏,和《开心消消乐》《保卫萝卜》等休闲类游戏。竞技类游戏突出情节,注重斗智斗勇的对抗和五花八门的新奇技能,有些像武侠小说、演义小说,而更类似网络小说中仙侠一类作品,如网络小说《诛仙》就被改编开发成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休闲类游戏则偏重于界面设计,看重细节的制作。以《开心消消乐》为例,它以基于动物设定的颜色消除为核心玩法,目前设有5大类型、450个关卡,画风清新、Q版造型,其优势与特色在于关卡的创新和界面细节的包装。在关卡设计中,玩家每15关就会有一个全新的障碍,不断接受挑战,享受游戏的新鲜度,其中“(1)有不同的特效,如横纵四连特效、爆炸特效、五连特效,另外简单特效的结合可构成威力巨大的高级特效等;(2)有不同障碍物的设定,如冰块、毛毛球、鸡窝、雪怪、飞碟、绳子、毒液、礼盒等;(3)丰富道具的出现及试用,如:小木槌、强制交换、刷新、后退一步、加5步、以及魔法棒等;(4)游戏目标的不同,如:分数过关、指定消除、获得金豆荚、获得宝石等”(于金霞:《“开心消消乐”游戏体验分析》,《设计》2015年第5期第116页)。游戏中同样存在着普罗普发现的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只有“主体”是固定的(游戏者),不仅(1)和(3)作为“协助者”是变化的,(2)作为“反对者”也是不定的,而且(4)作为“客体”也是不断改变的,这样便大大增加了“故事”(游戏)的复杂性和可观(玩)性。《开心消消乐》的整体界面设计一目了然,每个关卡像果实缠绕在树藤上不断攀升,让游戏者很容易理解操作流程,几款动物形象的设计在颜色上和形状上区分度也较大(黄色三角形的小鸡、绿色菱形的青蛙、棕色圆形的熊、紫色椭圆形的猫头鹰、蓝色梯形的河马)。这些细节设计一方面能够降低玩游戏的困难,缓冲游戏者紧张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在美化游戏,提升了游戏的品质。
3. 文学幽灵的借体复生与技术世界的情感消费
传统文学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它却不会消亡,“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幽灵,飘荡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躯壳”(周南焱:《〈最小说〉胜〈收获〉,朱大可:纯文学病入膏肓》,《北京日报》2010年1月8日)。在尼尔波兹曼看来,每一种媒介都会塑造属于它的话语结构,如铅字赋予人相当强的分类、推理与判断能力,而电报使得公众话语散乱无序、转瞬即逝。今天,传媒不断进步与发达,产生了诸如软广告、电视栏目、手机游戏等新的媒介形式,它们在冲击着人们过去的话语结构,同时也在为古老的文学提供可能的新躯壳。文学幽灵的借体复生意味着文学的去中心化,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也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幽灵般四散、隐匿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无所不在、无处不居,却又难以辨别、不能把捉,它跟随着媒介而变动,时而停留在铜鼎、竹简,时而行走于白纸黑字,时而投影在数字媒体,未来或许又会附着在今天闻所未闻的更新的物体上。去中心化的后现代色彩也让文学幽灵的借体复生染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色调,也即文学幽灵能够寄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体上,大到家居装饰、城市景观,小到银行卡卡面图案、手机套。借体复生的关键是合适与否的问题,如上所述,软广告这副躯壳就可能产生别扭,而在电视栏目包装和手机游戏开发中也许就顺畅一些,因为文学缺乏直接的功利性,她学不来谄媚的本领。
传媒+文学的协同生产对于文学而言是借体复生,对于传媒产业则是技术世界的情感消费。“技术世界”是一些哲学家、文化批评者对于现代社会不满乃至愤慨的称谓,意在批判人类现代理性思维作茧自缚导致自身异化,如人的符号化与情感荒漠化,理性“思维把自身客体化为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推动过程,客观化成一种机器化身”(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人异化为如物般的存在,变得空洞、麻木,丧失了丰富的情感世界。此时,文学或许是人的救赎之一道,以至于教育人士站出来呐喊“文学缺失,警惕孩子情感荒漠化”,呼吁让孩子“静下心好好欣赏一下各类文学作品,只是一种情感体验,不要带任何功利目的”(李亚妮:《文学缺失,警惕孩子“情感荒漠化”》,《精神文明导刊》2010年第6期第13页)。确实,当人们从繁忙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中暂时抽身出来,观看诸如《爸爸去哪儿》等电视节目,打开手机玩诸如《开心消消乐》的游戏时,他们的情感体验瞬间会被激活,或捧腹于萌娃们的天真无邪,或沉湎于悠然恬美的别处空间,或新奇于意料之外的游戏关卡,或满足于费尽心思的游戏通关,似乎给坚硬的现实生活裹上了一层软垫,让冷漠的技术世界贴上几丝温情抚慰。然而,由于大众消费的语境制约,这种情感消费也不免成为被市场设定以及期待的后果,情感消费往往难逃情感致幻剂的下场。但这是传媒的先天基因,而不是文学的过错。
(作者: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邮编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