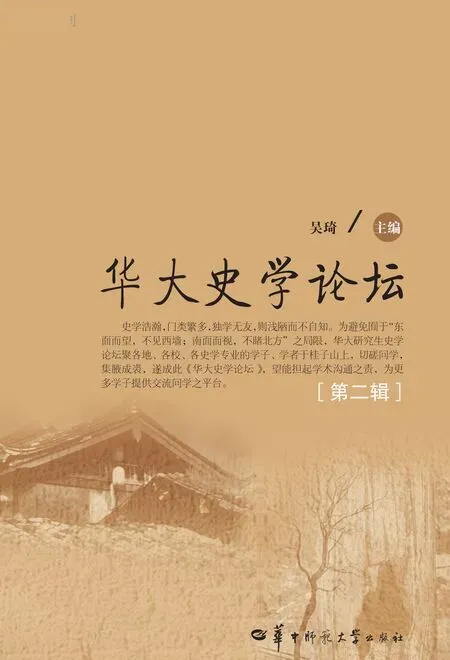近三十年来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林胜强
一、前言
20世纪20年代在国共合作旗帜下的国民革命波澜壮阔,影响深远,而其中的农民运动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随着宁汉双方相继“清党”和“分共”,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当时的农运大多由中共在基层打着国民党的旗号组织领导,随着国民党内反共政策的推进实施,中共主导的基层农运也遭到清洗。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国民革命开始时所形成的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也随之分崩离析,当时即有人喟叹“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注]转引自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见氏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北伐的胜利却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几乎同时,而以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为主的民众运动被压制无疑是时人认定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一环。当时的农运在北伐军经过和受北伐影响的区域都有开展,其程度以湖南、湖北为最烈,广东、江西、河南等次之,合计波及17个省区。中共革命被称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革命,对农运进行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
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述评,有台湾学者陈耀煌和大陆学者黄家猛的文章[注]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8期;黄家猛:《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但是他们的文章主要着眼于西方学界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并未论及国内学者的著述。在梁尚贤的著作和郑建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亦有对此问题综述的部分[注]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部分;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但并不完整,况且时日已久,也有重新梳理的必要。本文拟就这三十年来学界对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回顾(对象主要限于中文出版物),并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几点个人揣测。
二、对学界既有研究的回顾
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大陆因为属于革命史的研究领域,所以成果颇多。但因革命史观的束缚,即“一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二是中国近现代史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被高度简化为革命史”[注]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延续与递进》,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导言第22页。,因而早期相关的著作大多逃不出革命史观的羁绊。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包括一系列通史性的著作和资料汇编。典型的如1988年出版的高熙的《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注]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该书只是按日期排列重要事件,虽说详实,但并没有对事件本身的研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通史性著作有王全英、曾广兴、黄明鉴合著的《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和曾宪林、谭克绳主编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注]曾宪林、谭克绳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它们都只是进行了意识形态气息浓重的简略叙述,观点上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更重要的是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对史料必要的甄别辨析。出版的资料汇编主要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注]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台湾,则因为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分共”后,彻底否定此前的农民运动。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注]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将这段历史称为共产党把持、包办了农民运动,视农民运动为中共的专属品,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在台湾同样存在“国民革命史观”对学术研究的束缚问题,邹鲁的结论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台湾学界因袭。守着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五部档》、《汉口档》[注]五部指的是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及商民部,隶属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指导有关群众运动相关事宜。由于当时共产党员当时兼具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是跨党党员,因此大部分的报告、呈文皆保存在国民党中央的《五部档》,现存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有复制件。这些档案可以说是研究一九二○年代群众运动最直接、最基本的史料。《汉口档》是指武汉国民政府的相关史料,是研究当时政局的基本史料。等丰富档案,成果却寥寥,当然档案本身的不开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对这批档案的利用及其成果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了(1991年党史馆始全面开放提供学者研究[注]吕芳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新资料、新视野》,《近代中国》(台北)2005年3月第160期,第15页。),这就是本文后面将提及的郑建生及其研究成果。
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发轫于海外,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出的有Roy Hofheinz,Jr、Robert Marks、Fernando Galbiati、R.Keith Schoppa(萧邦奇)[注]Roy Hofheinz Jr.,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Robert Marks,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W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R.Keith Schoppa,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等。萧邦奇著作中文版[注]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于2010年引入大陆,该书以沈定一一生的传奇为叙述脉络,通过研究他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考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农民运动是他革命经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沈定一在家乡衙前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分为1921年—1922年的第一次和1928年的第二次。1921年9月衙前农民协会的第一次成立可以说成是首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注]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提要第1页。,但说成是中共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则略显牵强。衙前农民协会的创立者虽说是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但他此举更多的是个人性的举动,而非中共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发动。首先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直到1923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次他回家组织农民运动是在1921年4月,当时中共尚未成立;再次从当时中共的党纲和政策而言,并没有要求走向农村,进行以组建农会为核心的农民运动的指示。1928年因为他中共早期党员和西山会议派的双重身份,被排挤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领导层,在个人事业受挫之后回到家乡第二次组织农民协会,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农民运动的既有认识。在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在主流和极端对立的国共之外,还有类似于沈定一这样的第三方在组织农运。
梁尚贤的《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有近千页之厚,他不满于既有研究对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由中共包办的定论——对国民党在农民运动的角色含糊其辞或者完全否定,因而致力于对既有革命史观束缚下农运研究的突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退休之年,用十年的时间东奔西走搜集材料,尤其是个人自费到台湾查找材料,利用了珍贵的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五部档》、《汉口档》等一手档案。此书史料搜罗完备,对广东各地农运的描写巨细靡遗,还原了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关系的历史真相,将此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惜的是作者没有走得更远,虽抛弃了以中共立场为核心的农运叙述,仍然以国共合作领导的农会的立场为立足点,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农会和反农会的两极对立。对农会力量和反对农会力量只是笼统论之,而没有对它们各自内部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挖掘。农会内部不同的人员构成和利益诉求显然有深究的必要,反对农会的地主、士绅也非铁板一块。比如在广东农会和反农会力量的对立,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农会及其附属的农军和地主士绅及其领导的民团之间的矛盾对立,很有可能只是基于宗族或村庄既有矛盾的变体。因而分析的对象限于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却对广东农运的特有面相重视不够。更重要的是对站在农运对立方的地主、士绅、民团的描述近乎“妖魔化”,整体而论难言客观公允。
他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研究的文章[注]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有雷同的问题,从题目《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即可看出,还是以中共及其领导的农会为预设立场,卢毅的文章[注]卢毅:《国民革命后期工农运动的激进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8月号,总第138期。也同样如此。这些研究对过去的突破在于超越了以往中共党史研究的结论,即将国民革命的失败归因于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党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开始更多地从中共自身找问题,对以往的结论是个有益的平衡。但他们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地研究农民运动,没有顾及更多外在的因素,对农运本身也欠缺严谨的学理性分析。
上文提及的黄家猛在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述评中说:“这些从事农民运动的虽然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的,且农运政策、纲领皆由国民党制定,把农民运动简单归结为中共组织发动,似乎不妥。”[注]黄家猛:《近三十年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页。对农民运动以中共为核心的叙述方式提出了质疑,而且当时农运的领导者未必会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必然破裂,这多少带有一点后见之明的味道,呼应了上文所提梁尚贤一书中的观点。
李永芳的著作[注]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在时间上从清末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分为晚清农会的最初兴起、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和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五个阶段,时间跨度大,篇章清晰,资料详实。可惜的是言及国民革命时期的农会时,仍然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农会为立场选择和叙述核心,整体上偏于制度的研究。遗憾的是在国内已有人利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的《五部档》等档案的情况下,未能注意到这批档案的存在,也未加以利用。
王奇生关于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研究[注]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参见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第61页。,以国民革命时期广东和湖南的农运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是对革命者的底层动员和群众参与机制的分析。在不同的省份农民运动面对的具体处境不同,呈现的面貌也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有着不一样的侧重点、动员手段和表现形式。比如他对湖南农民运动中乡村小学教师扮演角色的注意,推衍出何以湖南农运将打倒土豪劣绅作为首要目标。还有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平粜阻禁”这个问题,何以在当时即广受各方注目。这些独到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发人深省。粮食上的“平粜阻禁”在湖南是有历史连续性的问题,辛亥革命前湖南的“抢米风潮”即是前例,学界以往已有周锡瑞、李细珠的成熟研究[注]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7-166页;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技能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这对此后其他学者的相关写作有不小的启发,罗辰茜的论文[注]罗辰茜:《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平粜阻禁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就是例证,她对湖南农民运动中“平粜阻禁”问题这一重要和特别的面相做了深入分析。
台湾学者郑建生的研究是当前目力所及最全面、深刻的成果,1992年他利用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的档案,撰写了题为《动员农民:广东农民运动之研究(1922—1927)》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继续此课题的研究,2001年发表的论文[注]郑建生:《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湖北阳新事件的考察(1927年2月27日)》,《政大史粹》(台北)2001年第3期。考察对象是湖北农民运动中的阳新惨案,除利用党史馆所藏档案之外,还利用了大陆出版的《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革命者后来的报告,以及当时的报纸《汉口民国日报》等,在史料的搜集上已经做得相当充分。该文以地方精英与革命者在地方控制权的争夺为考察对象,对事件本身有基本完整的复原。但他笔下的地方精英完全成为党部、农协等革命者的敌对方,忽视了返乡的党员和农运干部大多出身于当地精英家庭的事实,没有展示出农民运动与地方精英关系的全貌。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的截然对立,他们除了冲突的一面之外,也有利用与合作,后文将述及的陈耀煌和黄文治的文章就是例证。
2007年他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注]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将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文章对广东、两湖、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都有述及。在广东农运的主要诉求是以减租为核心的经济改良,在两湖已经达到土地革命的深度,掀起更大的声浪;在两湖农民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土豪劣绅,这在乡村无疑是一场革故鼎新的社会革命;在河南农民运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和原有的民间团体红枪会的合作与冲突问题,革命者与红枪会对农民控制权的争夺延续到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他还分析了农会系统的控制问题以及国民政府与农会的矛盾,两湖地区农运引起的财政税收问题和军队与农会的冲突使得武汉国民政府疲于应对,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对农运政策的改弦更张。国共关系的破裂,国民革命的失败,农运引起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因子。
既有研究对在农村组织农运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缺乏细化研究,对他们的活动多注重于和当地地主、士绅矛盾冲突这革命的一面。实际上他们大多出身本地的地方精英[注]关于地方精英的分析可参见郑建生的《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湖北阳新事件的考察(1927年2月27日)》,《政大史粹》(台北)2001年第3期,第53-55页。地主、富农并不完全是地方精英,但前者大多数无疑属于后者的范围之内,因而本文大而化之,未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家庭,他们返乡从事农民运动,对地方精英也有利用和合作这一面向。台湾学者陈耀煌较早注意及此[注]陈耀煌:《地方菁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政大史粹》(台北)2000年第2期,第100页。,他的文章探讨中共早期在湘鄂西苏区的发展过程中,出身于地主、富农这些地方精英家庭的知识分子党员在返乡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大多数选择了与地方精英的联系,放弃了基层农民的动员,因而当地农运也就先天地欠缺坚实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大多数的农民之所以被动员,并非是由于对中共的信仰,而是由于他们对于地方精英领袖的信仰。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成功与否就与这些地方精英党员态度密不可分,这也部分解释了国民革命时期在敌对势力残酷镇压之外农运何以大起大落。黄文治的文章[注]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第5页。关注的也是革命者在农村组织和发动农民的最初过程,出身于地主、富农这些地方精英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城市求学的过程中,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在主动或被派返乡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利用该地的地方精英和自身的关系网络来组织农民运动。革命者抱持的还是精英主义的动员路线,基层农民动员虽被提上日程,但并非主流。陈耀煌、黄文治的关注点都是革命者在农运中与地方精英的联系与合作,基层的农民动员其实并未充分展开。这为农运埋下了很大的隐忧,其负面影响在农运被镇压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侧重点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异曲同工。
罗志田的《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一文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也有涉及,他从南北地方意识、区域认同和南北象征新旧的角度对北伐何以成功给出了自己的诠释[注]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参见氏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3-196页。,角度新颖,让人耳目一新。在文中他认为湖南农民对北伐战争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南人驱逐北军驻防的地方意识在起作用,而非完全出自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民的组织、宣传、动员,对湖南农民运动与北伐成功的关系给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
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20世纪20年底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其说是‘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代际革命’。‘比农民积极分子的社会出身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代沟’。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往往是‘他们所在阶级的叛逆’。他们是‘地主’和‘富农’的儿子(有时候是女儿),是‘在城市里读书后回到家乡领导革命的知识分子’。至于运动的‘底层战士’,则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年轻村民,为革命提供了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成员’。”[注]转引自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这为研究革命者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他者视角。
孔飞力注意到农民运动中另外一个引起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即中国城乡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他在书中说:“革命者的在城市的经历和受到价值观教育的塑造,回到县城村镇之后面临着城乡差异的冲击,他们按照城市价值观改造乡村的渴望以及由此引起的与持有旧价值观的乡村社会整体上的冲突。革命者出身也许是本地人,但在价值观上是外来者。”[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革命者虽说是农民出身,但在城市学习的经历已改变了他们的认同,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由是观之,当时很多的冲突不难找到解释,他们虽然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为己任,但骨子里或难以与农民融为一体,与农民仍有隔膜与疏离。孔飞力注意到近代中国城乡在地理和心理上日益拉开的鸿沟,关于革命者和农民在价值观上差异的说法不无所见。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深远,今天海峡两岸的分治即可从中找到源头。1949年以后随着国共隔海对峙,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数十年,为了自身统治需要,两岸不约而同奉行对社会的全方位管制,而学术研究无疑深受其害。革命史观的约束,档案材料的封闭,对学术研究的损害不言而喻,大环境如此,农民运动研究难脱牢笼。其间在大陆出版的相关著作大多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痕迹,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唱赞歌;在台湾农民运动因反共的需要更成为政治上禁忌,遑论学术上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政治气氛的宽松,敌对态势的缓和,社会整体亦呈现出日趋自由开放的氛围,革命史观对学术研究的束缚开始松绑。以往秘藏的档案开始对外开放,以便公众查询和学者利用,严谨的高品质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前述梁尚贤、郑建生的著作即是显例。其间海外学者作品的引介,新的理论、观点、方法开始进入中文世界,对农民运动研究此项课题亦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然而,现在的这些成果只是阶段性的成绩,此项课题研究远远难以到达盖棺定论的地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批档案材料的编辑出版、数字化和对外开放,极大地便利了学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包括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级中共组织部门编辑的《组织史资料》,这些资料搜罗广泛,里面有不少和农民运动相关的文件、报告等。各地党史部门征集的党史方面的回忆材料,目前收藏在各地县市党史办或档案部门乏人问津,里面有不少当时农运人员的回忆录。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档案也开始了分批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以期方便学界利用。这些档案和资料为推进农民运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支撑,也可说现在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正逢其时。再辅以原有革命史观禁锢的解脱,以及国外诸多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农民运动研究前景可期。
三、对学界未来研究的展望
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现有成果基础之上,如何推陈出新,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谨就今后研究进一步发展可能的方向提出管窥之见。
1.对农民运动的整体研究细化到更多局部的区域性研究
现有的区域研究除湖南、广东外其他各地的农民运动尚欠缺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的研究就大有可为。北方冯玉祥国民军控制的区域也有农民运动的展开,因此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广东的农民运动虽有梁尚贤的厚重大作,其实也有另行深挖的余地。对国共合作前和国共合作后的农民运动在时段上似有分开的必要,前者更多是个人性的行动,后者是中共自上而下动员和组织的产物;而且前者的目标更多是经济性的,政治上至多是乡村自治的层次,后者除经济目的之外,还包括政治和思想属性。就像罗志田所认为的“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同时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于一身”[注]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页。,其时的农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这些都隐含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2.将农民运动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放入乡村社会变迁来研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在大陆近代史学界,革命史、中共党史与民国史、现代史呈现俨然打成两橛的学术研究生态,彼此之间畛域分明,交流不多。2015年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召开,主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注]相关讨论参见刘永华、张侃,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第11-80页。,与会学者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领域,是沟通两者的一次很好尝试。晚清随着中国“防御型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与转型,其中的乡村社会变迁是个莫大的课题。
中共之外的其他党派和团体也有自身的农村政策和农会方案[注]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运动来动员农民和成立具有基层政权性质的农会的中共模式只是众多方案之一。横向来说,民国成立后即有官员、学者、社会团体在农村推行乡村自治和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党对农村改造的效果虽说不彰,但也不能一概否定。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其直接统治区域的浙江和江苏省推行过减租运动[注]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57-265页。,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也有“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且在部分区域付诸实践[注]黄正林:《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问题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同党派和团体的农村改造方案的相互比较就成了一个有趣的课题,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可以相互参照来看。
纵向来看,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开展较为成熟的地方,很多在土地革命时期成为中共割据的苏区,两个时期是同一批领导者在主持其事,其农运政策有变与不变的部分。而且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推行农运的革命实践,深刻影响到后来革命的各个阶段,以至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农村改造都是如此。放宽历史的视野,拉长研究的时段,兴许会有更多引人深思的发现。
3.将农民运动的研究从革命史引入社会史,转换研究主体,拓宽研究视野
今后研究的立场和材料将不再限于革命者自身和革命者单方的材料,这将为研究带来新的气象。就像周锡瑞言及陕北早期革命史所言,“从党史方面转向陕北地方农村的社会史”[注]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前述罗辰茜的文章就是朝这个方向尝试的成功案例,作者不仅言及湖南农民运动自身,而且对民国初年湖南农村的粮食贸易和货币制度也有所探讨。
郑建生的研究虽说全面深刻,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政治事件史的研究。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方向。他认为事件史是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做出真实的描述。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注]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5页。。因而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成为一种史学范式的革新,也为进一步推进农民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武器。
周锡瑞说革命史研究应该“从关于革命阴谋的故事,转入革命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去”[注]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言说的对象虽说是辛亥革命,但对此后其他的革命运动研究不无借鉴意义。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注]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和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注]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成功范例,在裴宜理笔下的淮北和罗威廉笔下的麻城,地方的社会生态与革命和暴力有着深刻的关联,因而以社会史的方法对农民运动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就不再是无的放矢。
但是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革命史也有障碍,就是在具体做法上仍然主要利用党史资料,结果要真正了解革命进程中的社会,还是比较困难。那么这个革命的社会在哪里呢?在史料的方面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注]饶伟新:《赣南苏区革命中的宗族与阶级》,刘永华、张侃,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第18页。这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有待解决的难题。
以上各点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可以在研究中混流并进,协同运用。学界在此课题上取得的研究成果,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精华,自有其学术史上地位。目前随着中国档案开放状况的改善,学界对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必将步步深入,相信会有更多高品质著作出现,当然这要靠学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