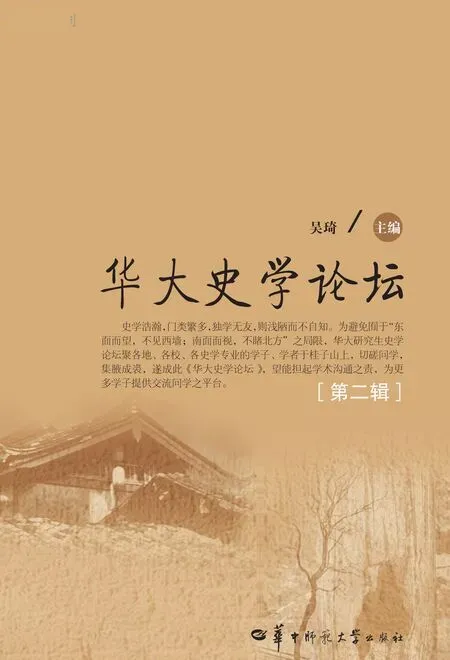从妖气到王气
——人参文化形象的转变与塑造
叶宇涛
清人袁栋曾言:“前明时,人参产上党者佳,辽东次之,高丽百济又次之。今人参产辽东东北者最贵重。”此时,辽参价格已经暴涨至“三十余换”,而“上党参一斤不过值银二两”。这种巨大的差异令袁栋困惑不解,只好归结到“王气”问题上:“岂古今地气之不同耶,抑物亦随王气而钟耶?”[注]袁栋:《书隐丛说》第14卷,清乾隆刻本,第171页。
对这一问题,年代稍后的梁章钜回答得更进一步:
人参随王气转移,而东方尤为生气所托,始故历代人参多产于东南东北,而西方无闻焉当时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兆,故钟山之参为上品。而上党为天下之脊,亦王气所钟,故前朝所用人参皆即今之党参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注]梁章钜:《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2页。
梁章钜在大肆吹捧“我朝”为“王气所钟”的同时,也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其一,人参主产区经历了从上党到辽东这一个大的转变;其二,人参与王气相结合,成为渲染人参功效与制造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那么,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人参作为一种药物,其文化色彩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说文解字》释“参”字:“人薓,音参,岀上党。”[注]李昉:《太平御览》药部8,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5829页。魏吴普《吴普本草》亦云:“人参或生邯郸。”[注]陆烜:《人参谱》,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年,第568页。表明汉魏之时,人参的主产地就在上党及其周边地区。《本草》云:“如人形者,有神范。”《春秋运斗枢》云:“揺光星散为人参,发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故人参又有“地精”之名。《礼斗威仪》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注]李时珍:《本草纲目》地12卷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约是沾了“如人形”的光,在当时弥漫于全社会浓厚的谶纬思潮影响下,人参或多或少披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
一、作为“妖草”的人参
《南史·阮孝绪传》云:
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反,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言其孝感所致。[注]《南史·隐逸下》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总1894页。
阮孝绪出身士族,又为隐士,更著有《高士传》。不仅收藏有谶纬之书,还能够“自筮卦”,效果颇为灵验,自然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因而种种“冥通”发生在他身上,还能够解释圆满,也就见怪不怪了。
《晋书·石勒载记》云:
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注]《晋书·载记第四》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总2707页。
又《隋书·五行志》云:
高祖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余。具体人状,呼声遂绝,盖草妖也。[注]《隋书·志第十八》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总645-646页。
可见,此时人参最多算一味比较珍贵的药材。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灾异谶纬学说,人参也就容易被人有意无意与政治问题相勾连,进而就变成“草妖”了。尽管如此,上党人参还是被列为贡品,上党地区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相当数量的人参。同时,出产于高丽、百济地区的辽东人参作为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贡品,开始出现在时人的视野里,受到时人珍重。辽东人参成为仅次于上党人参的珍品。
二、作为“神草”的人参
入唐,人参的形象开始有所好转,大概与这一时期上党人参在上层社会的广泛传播有关,其药用价值得到突出、神化。
《宣室志》云:
天宝中有赵生者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有翁衣褐来造之翁曰:“吾子志趣甚坚,老夫虽无所能,诚有补于君耶,幸一访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叚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椵树蕃茂。生曰:“豈非叚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闻参能为怪者,又可愈疾。”遂沦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览书自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注]张读撰:《宣室志 附补遗》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此故事颇为怪异,前几则故事涉及人参,多是泛泛而谈。此处对人参的描写却颇为精细,如生于“椵树”之下、甚肖人形,极有可能是有心人刻意编造,以渲染人参的神奇功效。其针对人群也很明确,正是那些“性鲁钝”却又想一夜之间“醒然明悟”的读书人,这在中古文学创作中是永不停歇的话题。或许是迎合了那些失意的读书人,人参开始屡屡出现于时人的诗中。
杜甫《绝句四首》其四: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
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注]萧滌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10卷,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227页。
又温庭筠《东峰歌》:
锦砾潺湲玉溪水,晓来微雨藤花紫。
冉冉山鸡红尾长,一声樵斧惊飞起。
松刺梳空石差齿,烟香风软人参蕊。
阳崖一梦伴云根,仙君灵芝梦魂里。[注]刘学锴撰:《温庭筠全集校注》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1页。
此处人参实际上泛指各类药材,仅仅作为一种意象,成为一种高雅生活情趣的象征。在诗人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模仿和践行,来表达诗人身体多病、隐居山林的志向,因而也容易成为隐士之间相互馈赠的佳品。如晚唐诗人陆龟蒙与皮日休,二人交好,常有往来。
如皮日休曾受到陆龟蒙所赠人参,谢诗云: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谁披露记三桠。
开时的定涵云液,劚后还应带石花。
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
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注]皮日休:《友人以人参见惠因以诗谢之》,《皮日休诗全集》,海口:海口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陆龟蒙和云:
五叶初成椴树阴,紫团峰外即鸡林。
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
品第已闻升碧简,携持应合重黄金。
殷勤润取相如肺,封禅书成动帝心。[注]陆龟蒙:《奉和袭美谢友人惠人参》,《陆龟蒙全集》,海口:海口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参具有“久服轻身延年”的特性。在皮日休笔下,人参不再是“草妖”,转而成为“神草”。出乎意料地被开发出“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的功能。而且其身价一路上涨,甚至达到“品第已闻升碧简,携持应合重黄金”的地步。
这种将人参与修道、隐居等名士风范相联系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宋代。虽然,宋人对于人参“草妖”之说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些关于人参的传奇故事“说益侈则益诞”[注]罗愿:《尔雅翼》第7卷,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74页。,却又忍不住被人参“久服轻身延年”传说所诱惑,加之道士别有用心地吹捧,宋人进一步强化了人参的“修道”功能。
《三洞群仙录》引《神仙传》云:
维扬十友者,家富足,拉为道友迟以酒食为娱。常有一老叟弊衣褴褛,每造其席,众亦不拒。一日酒酣谓众曰:“某虽贫乏,欲具一会奉酬可乎?”众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数辈相邀环坐,乃舁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视,即烂蒸小儿。众深恶之,皆不食。叟曰:“此千岁人参也,颇不易得。欲以此报,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升天而去。[注]陈葆光:《三洞群仙录》第5卷,明正统道藏本。
同肉眼凡胎的唐僧拒食人参果一样,人参的“妖异”特质此时反成为区别神仙与凡人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生长于太行山顶的紫团参,因为传说山顶常有紫气笼罩,因而成为当时流行的珍品。
大诗人苏轼对紫团参推崇备至,称其生长在“谽谺土门口,突兀太行顶。岂惟团紫云,实自俯倒景”。自己服用后,“蚕头试小嚼,龟息变方聘。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户,半夜珠落井。灰心宁复然,汗喘久已静”。苏轼贬谪广东南海时,曾亲手移植人参到居所,亦有《人参》诗。第一句“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如此刻意将“上党”与“辽东”进行对比,甚至将辽东贬为“井底”。恐怕不单单是诗人个人的好恶,而是当时同北方契丹、西夏对峙下高亢民族情绪的一种反映。出于同辽东人参的对抗的需要,上党人参开始具有了某种“王气”的特征。
另一位大名人王安石曾患气喘,需要用紫团参入药。薛师政正好从河东回来,带有紫团参,于是“赠公数两”。王安石拒绝了,并表示:“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王安石之所以拒绝,除了“拗”之外,恐怕还是认为这“数两”紫团参过于贵重,收受不当。相反,明末首辅周延儒,贪贿揽权,家中珍宝不计其数,其中最贵重的珍宝就是“清河参有一支重十两者”,结果“焚时火焰皆作五色云”[注]文秉:《烈皇小识》第8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214-215页。。可见,一直到明末,上党人参不仅是贵重的药品,也带有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三、作为赐物的人参
明中叶后,温补医学兴起,人参几乎成为百病包治的神药,市场需求量大增。偏偏此时上党人参资源已经枯竭,于是辽东人参趁势大举进入内地市场,一举成为人参中的王者。然而,清朝统治者对于人参的药用价值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康熙曾多次表示“北人于参不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85页。、“朕少年最不喜参”,但后来康熙自己服参感觉有效果后,开始信赖人参,并将其作为礼物赏赐臣下。这一风气延续到雍正、乾隆时达到极盛。人参成为皇帝展示荣宠、激励大臣的重要手段。
康熙十七年(1678年),陈廷敬正充任经筵讲官,备受康熙宠信。是岁除夕,康熙在“赐上尊食物甚众”之后,又“赐观人参桢本”。事后陈廷敬满怀感激地写道:“筋力已衰逢大药,生成难报是皇恩。”[注]陈廷敬:《午亭文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三朝元老黄钺致仕后,道光在其九十岁生日之际赐人参八两,并表示“知卿原不假参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语句诚挚、关怀备切。因而黄钺读后,“感泣至不能起立”[注]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第16卷,清光绪刻本。。
由于阮孝绪钟山寻参故事的模范作用,人参同样被赋予了孝的色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者家属对使用人参的态度。乾隆时期,安南国王阮平正因其母亲年老体弱,曾经写信向大学士福康安索要人参。乾隆得知之后,虽然对其贪得无厌略有不满,但对其孝顺之心仍然予以肯定,为展示天朝荣宠,仍然满足了他的要求[注]蒋竹山:《人参帝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
对出征将领赏赐人参,既是鼓励象征,也有实用价值。雍正三年(1725年),正在西北主持战事的靖逆将军富宁安奏:“今战场之官兵,由万里之遥,赏赐人参,实浩荡至恩,边外无有之奇宝,于战地大有裨益。除将所赐人参分送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地外,余参收藏。战地如有身体欠安、患病之人,倘有用人参处,恳请圣主施恩赏给。”[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075页。这对于鼓舞军队士气、拉拢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是相当有益的。
同时,出于推销产品的需要,商人不惜编造出各种关于人参的神话故事,鼓吹人参的神奇功效,通过饥饿营销的手段,来哄抬人参价格。这一手段极为有效,江南富豪之家,将人参尊称为“马佛”、“祖宗”或“爷爷”,买人参不敢说买,得说请:“尊老马佛爷爷来弊宅里歇一程脚。”唯恐有所怠慢,以至于人参幻化成型跑了[注]参见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这一时期的人参,既是神物,也是圣物。
四、作为“王气所钟”的人参
乾隆时期(1711—1799),人参贸易到达顶峰,每年给内务府带来了四五十万两白银的收入[注]参见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7页。。闲适之余,爱好作诗的乾隆对人参自然不会吝惜笔墨。在阿桂等人主编的《满洲源流考》中,乾隆以半追忆的形式写下了《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并序》,以“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注]《满洲源流考》,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在列举的十二种满洲特产中,人参排在五谷和东珠之后,位列第三。其诗云:
奥壤灵区产神草,三桠五叶迈常伦。
即今上党成凡卉,自惜天公保异珍。
气补那分邪与正,口含可别伪和真。
文殊曰能活能杀,冷笑迷而不悟人。[注]《满洲源流考》,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乾隆在诗题下自注:“深山邃谷中,参枝滋茁,岁产既饶,世人往往珍为上药。盖神皋钟毓,厥草效灵,亦王气悠长之一征耳。”又于“自昔天公葆异珍”后注:“昔陶弘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者神效。上党之参,直同凡卉矣。”[注]《满洲源流考》,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1-363页。
王气之说,始于秦汉。鸿门宴上,范增劝说项羽杀掉刘邦的理由就是“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注]《史记》卷9《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1页。。《东观汉记·光武纪》亦云:“望气者言,舂陵城中有喜气。曰:‘美哉王气,郁郁葱葱。’”[注]刘珍等撰:《东观汉记校注》,吴树平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页。除刘邦、刘秀这类开国君主外,某些地方也有王气。比如金陵,秦始皇因此南巡以应之,又埋金玉以镇之。孙权割据江东后,又借此大肆造作,以为政权合法性依据,更成为南方政权借以抗衡北方的重要意识形态资源。
而乾隆编撰《满洲源流考》,旨在重塑满洲集体文化认同感,强化满洲内部凝聚力。同时也需要借助神秘主义学说,来强化满洲统治的正统性,对于满洲历史自然会极尽美化之能事。由于人参早就具有“神草”之名,此时就被乾隆拉出来充当“盖神皋钟毓,厥草效灵,王气悠长之一征耳”。关键是乾隆还特地引用了陶弘景言,借以讽刺苏轼诗中“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之句,以表明满洲才是王气正宗。
乾隆之弟弘昼完全明白其兄歌颂人参的用意,也毫不客气地表示:
辽水乾坤见旋转,古称上党竟虚传。
松花粉落红葩绽,草露珠侵碧干妍。
五气精英含叶底,三才功用寄枝巅。
农经上品诚难得,妙益人间先后天。
又有:
瑶光星散灵根发,芝盖氤氲五叶敷。
沿路何须求鹿引,漫山岂必听人呼。
风披紫萼垂丹宝,露润青桠长白须。
上党虽佳谁复釆,三韩王气古来无。[注]弘昼:《人参》,《稽古斋全集》第8卷,清乾隆十一年内府刻本。
一句“上党虽佳谁复釆,三韩王气古来无”,淋漓尽致展现了满洲贵族对于自身族源骄傲自豪心态,也将人参与王气的关系,算是作了正式官方结论。以至于后人梁章钜生拉硬拽将钟山参也列为“上品”,目的只是为后面的“我朝”作铺垫罢了。这在当时并不鲜见,尤其是康乾之时,那些获得皇帝赐参的词林清贵、御用文人们,为感谢帝王恩典,也争先恐后表示人参确实是“王气所钟”的明证。
王鸿绪云:
天上瑶光宿,山川蕴地精。昔名推上党,今产重陪京。[注]王鸿绪:《戊子三月□日赐人参三觔恭纪》,《横云山人集》第23卷,清康熙刻增修本。
魏象枢云:
老迈何堪肺病攻,九重如日鉴臣衷。承将天语归元气,赐得神苗出大东。[注]魏象枢:《寒松堂全集》第7卷,清康熙刻本。
张英云:
紫团名重旧神京,琼金液枝色最莹。山泽常看运气护,海天朝映日华生。[注]张英:《四月二十八日蒙赐高丽人参一函恭赋》,《文端集》第2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廷枢云:
歘见摇光彩,俄看紫气新。欢声腾两陛,覆育仰洪钧。
联步趋西阙,封题燦北辰。三桠体全具,十稔味尤醇。[注]张廷枢:《戊子二月十三日经筵礼毕赐廷臣人参有差恭纪二十四韵》,《崇素堂诗稿》第4卷,清乾隆三十九年吉大泰等刻本。
相比之下,沦落已久的上党人参,此时却常常会引发汉族文人的悲吟。
吴清鹏云:
灵苗无根源,正似芝草醴。生气更休王,山阿随托体。
又云:
郁郁五原上,风云司闭启。百年发泄多,刨挖尽萌柢。
回首望佳气,忧来泪如洗。感忆桥山驾,尧颡瞻拜稽。[注]吴清鹏:《又和小圃五咏并序》,《笏庵诗》第12卷,清咸丰五年刻吴氏一家稿本。
吴清鹏所云,是感伤“五原”上“佳气”经过百年刨挖后发泄殆尽,不要说“王气”了,就连“生气”也无。生活于嘉道之际的吴清鹏,虽是在言上党人参。但话里话外,又何尝不是暗示着清帝国此时的没落呢?
值得注意的是,从隋代的“草妖”到宋代的“仙草”再到清朝成为“王气所钟”的象征,人参的每一次文化转型都可以看到商业资本或国家权力的介入。前者将人参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药,后者将人参塑造成“王气所钟”的“神草”。此时,无论是满洲权贵还是汉族文人,都将人参与王气的关联视为了基本“常识”,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梁章钜与袁栋那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