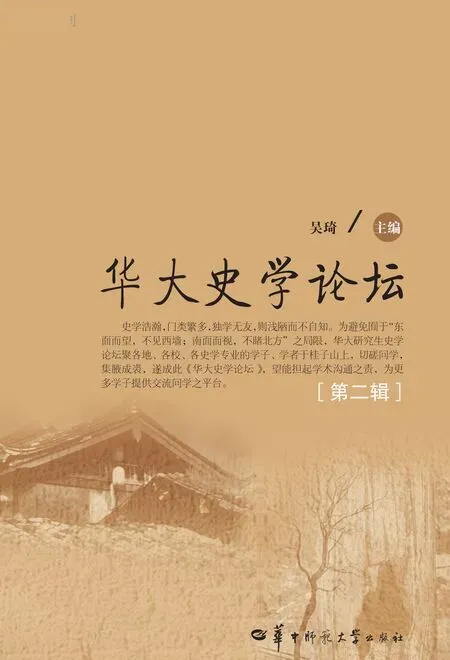《论轮台诏》、《制造汉武帝》读后
向 尚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原题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上。在此篇文章里,辛德勇主要以史源学方法讨论了《通鉴》汉纪部分的史料问题,并且通过知人论世,分析了前人作伪重构史事的原因。辛文发表后反响颇大,多有商榷讨论者。辛德勇文章主要攻讦的是田余庆先生,故而在田余庆先生逝世后,田门弟子及私淑田门者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对辛文也有所回应,但仅仅是断章残句,因此辛德勇才会在后来《制造汉武帝》一书的撰述缘起中说期待专文回应云云。
此后有专文回应或涉及辛德勇文章者为韩树峰、王子今、李浩、杨勇、成祖明诸位先生。韩树峰从讨论巫蛊之狱的性质入手,回应了辛德勇关于巫蛊之狱及卫太子的论说。王子今则透过他自己关注的东方朔劝武帝事,来讨论《通鉴》的史料问题,从而回应辛德勇对《通鉴》西汉部分史料的观点。李浩从司马光一隅入手,论说司马光没有重构史事,进而说明辛说无法成立。杨勇与成祖明则从汉武帝政治史事入手立说,勾画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政策,进而与辛德勇商榷。然而此五者,大抵皆为“六经注我”,虽然其论说深入,然而离辛德勇与田余庆二先生的争论攻讦已较远。此外,还有局外人商榷之文,多不庄重语,虽为田余庆先生辩驳,但已颇为局促。
而本文与以上诸文皆不同,本文主旨,意在回到田余庆、辛德勇二先生争论发生的最初,即两者所写的文章上,通过对两者文本的仔细梳理,将二位先生的争论如实呈现出来。至于更深层次的秦汉史事的讨论,则不在本文的论说范围之内。
一
辛德勇此书虽然征引市村、唐长孺等诸位前辈之观点,但这些实在算是虚晃一枪。就整篇文章而言,辛德勇想彻底驳倒的一直是田余庆,而且辛行文乃是除恶务尽、赶尽杀绝的,字里行间都甚恭敬,然而句句带有锋芒。辛在文章中不仅要驳倒田之史料,而且田文论说的边边角角,辛德勇也差不多都要驳斥,所以在彻底分析辛文之前,需要对田余庆文章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其实田余庆《论轮台诏》在发表之后曾有修订,不过辛对田的批驳,是连后来修订的内容也有批驳到的。另外,辛德勇对于田的另一名文《说张楚》其实也有商榷意见,虽然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其实此二者联系颇大,从中更能体味到辛与田在治学理路与方法上的差异。
辛德勇谈他自己立说,所言其最重要依据,乃是《汉书》和《盐铁论》等基本史籍之记载与武帝晚期政治路线转变。有趣的是,田余庆立说除用《通鉴》史料之外也是这些。而且田余庆对于《汉书》以及《盐铁论》中的史料,皆有较为可靠的解释。
田余庆文章在最初即引用《汉书·西域传》关于轮台诏的相关记载。关于“轮台诏”这一诏令本身,田余庆认为此诏“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昭宣中兴,使西汉政治再延续数百年”[注]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页。。接着田以年号年代年份来论说,证明武帝在元封年间准备开始改换制度。其实辛德勇对于改换年号这个问题也有更详细的讨论,语在《建元与改元》中,辛德勇认为所谓元封并非改元而来的年号,而是追认之年号,是追记往事[注]辛德勇:《建元与改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6页。。此处田余庆的论说其实在辛看来恐怕已有破绽。
田余庆紧接着从两方面论说,一是历史任务与武帝的意志意愿,田认为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完成了他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的政策的转折”[注]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改年号,告成功于天。二是社会形势,即元封年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险象。(在《中国史纲要》里,田直接认为社会现象是农民起义,此中转向其实颇有趣。另外《中国史纲要》里,田曾称引“法统”立说,此后《说张楚》里,此也为重要概念。)其实在这里,田余庆已经通过对年号和社会局势的考察认定了武帝晚年有转向。也就是说,在田文前半段,田就已经完成了对汉武晚年转向这一事实的认定,之后田文就以此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论说。不过田在这里的认定其实与辛德勇所提到的市村、唐长孺等人不大相同,田的思路比市村等人要复杂得多。
田余庆是由年代学相关讨论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来证明武帝改辙的必然——那么为什么武帝不早改辙,非要拖到征和末年才从轮台诏里确认这个转向呢?田认为这是因为:第一,开边问题,汉武帝对拓土开边的问题心中无数。第二,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政策的转变[注]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页。。
田余庆文章也主要从这两大脉络来论述。值得注意的是,田余庆全篇文章的重点,实际上并非是提出了汉武帝晚年有守文的转向,而是在认定这个史事的基础上(田余庆对这个转向的认定实际上依靠的史料是《通鉴》及《汉书》的记载),然后深描刻画史事。通过对卫太子与武帝的路线政争的问题与汉武帝开边政策问题这两方面立说,从而勾画出武帝晚年关于政策上的转向。辛德勇要彻底驳斥田余庆的《论轮台诏》的话,也就应该从这三个地方驳斥。一、田余庆的史料依据,即《通鉴》相关记载。二、卫太子路线事情。三、武帝开边事情。驳斥第一点,辛用的是史源学的手段,而第二点与第三点,辛德勇则不得不返回史实,从历史史实中反驳田余庆。
将视角回归到田余庆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田自己在文章的余论部分里,其实已经对他为何用《通鉴》史料立说做出了回应解释。田文首先说明《汉书》为何忽视武帝改弦易辙的问题:班固生活在所谓汉室中兴之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而颂扬武帝而对其的指责就含糊其辞[注]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页。。另外,田余庆通过对朱熹的言语,以及朱熹对《通鉴》的看法来佐证《通鉴》的可靠。这里其实正是破绽之处,在之后辛德勇对这一点攻讦颇有力。
另外,陈苏镇其实也有类似思路的提法。不过有趣的是,陈苏镇的提法主旨大意恰好与之相反。陈苏镇认为《汉书》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和轮台诏的意义。陈认为,这种夸大是因为班固不赞成公羊家的理论,原因是公羊家言太平世不外夷狄[注]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页。。不过陈苏镇其实也是肯定《通鉴》记载的,陈苏镇的论说实际上是对田余庆思路的补充。辛德勇在他的文章中其实也引用了陈文为自己张目,但与其说陈文支持辛说,倒不如说陈文实际上也是反对辛说的。
然后田余庆分析刘颁的政治取向,来说明刘颁对于反对开边事情的关注,田认为刘颁能够看出汉武元封之后开边事情以及当时政局的发展。田余庆在这里对刘颁的相关论述其实也可以作为刘颁伪造史料的原因,然而田余庆既然已相信《通鉴》为真,故而以此来证明刘颁的高明。此外田余庆在跋语里有引用敦煌汉简里武帝遗诏言,来旁证轮台诏的内容。这一点,辛德勇也有反驳。
上文已大致分析了田余庆的《论轮台诏》一文。不过所谓的“武帝晚年转向守文”之说,田余庆实际上已经调和这个提法和宣帝时期史事之中相矛盾之处。田并非认为武帝晚期转向“守文”,政治制度就变成了偏向儒家的守文之道了。在田余庆看来,武帝晚年转向守文,实际上促成产生的是一种杂王霸之道的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宽柔并济的,且一直从武帝末年延续到昭宣之时。田余庆是这样表述的“汉宣帝兼用儒法这种制度,正是武帝时形成的”,“汉武帝末年随着轮台之悔而出现意识形态的变化,反映在吏治上就是以霸次王,霸王相杂”[注]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页。。在这里,田余庆其实是在调和异说,排除反证。田余庆是一个很鼓吹排除反证的史家,他曾经说过:“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须在我们的考虑之中。”[注]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辛德勇以《汉书》、《盐铁论》中记载的“反证”来攻讦田余庆,实际上田余庆早已经调和了这些反证,虽然这些调和未必都那么坚实。田余庆实在算是一个有分寸感的史家,后人很难彻彻底底地驳倒他,而且田余庆在这里的关于“王霸制度”的论说,文章最初已有,而并非后来修订时加入。
二
前文已提到辛德勇这本书的攻讦乃是“除恶务尽、赶尽杀绝”的,辛不仅要驳倒田之史料,而且田文旁涉的其他内容,他也都要驳斥一遍。辛德勇甚至也兼驳斥古人前辈。颇有意思的是,古人处理这个问题时思路的错误,辛都要仔细说明一遍。本文梳理辛文乃是按其行文结构顺序进行的,故而辛文每个部分都会提及。
首先《制造汉武帝》此书名乃后出,辛言“希望这个书名,能够更加凸显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这一主题”。有人言此模仿制造路易十四云云,辛德勇已澄清。
先论辛之“目次”,实际上此处已见辛德勇老师家法深严。目录学之言,目者,目次也,为文章题目排列。录者,叙录也。此处所承袭的正是辛德勇老师黄永年的观点。黄言有的书不称“目录”而称之为目次,似比称“目录”确切些,但此法不甚通行[注]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3页。。另外,实际上辛书多称目次而不称目录。学者们讲什么,不讲什么,有时或可为苦心孤诣,有时则习以为常而不觉怪。此二者都要万分注意。
人性化护理要求医护人员应当为患者打造一个舒适、温馨的病房环境。比如,在醒目位置应当配有和妇产科防治有关的教育材料,以便患者及其家属学习。建立个人日常活动记录表,对病人治疗、饮食等进行记录,便于监测患者病情变化。患者出院后定期回访病人,继续强调妇产科相关知识[5]。
再论辛之“撰述缘起”,撰述缘起乃后出,其中辛德勇已经对各种先出意见有所回应。另外,此段为原论文所无,专为简介自己文章的写作缘起,包括最初文章的思路。辛德勇点出了黄永年先生对于《资治通鉴》的史料学上意义的教示。实际上关于《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前辈学者已经多有立说。这里辛德勇之后也会提到。此处辛德勇有言“由于拙文刊出后,得到的一些回应,似乎都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论述的思路。在这里,对本书的结构再稍加说明”。在此处辛德勇认为本书结构是:(1)前四章乃是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2)第五章分析王俭何以“制造汉武故事”。(3)分析历史的实在原型[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5页。。
要注意的是,这个撰述缘起乃后出,他的文章早已发出。这个撰述缘起实际上是对已经有的意见的批评与回应。而这些批评其实差不多都是纪念悼念田余庆文章里所提到的。
其实这些意见,多来自具有相同“家法”的学者,而他们与辛的争论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田余庆文章的评价问题,内里是治学方法思路上面的歧义,在这里不详细论说。
再论辛德勇文章之“引言”,引言正可谓学术综述。旁涉中外,有破有立。这里提到了辛写这篇文章的二重原因,第一重原因乃是进一步辨清《通鉴》之史料价值,第二重是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复因田氏将其基本看法写入先此两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秦汉史部分,而且后来还有一些大学教材,采纳了这一说法”[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0页。。
然后点出市村、唐长孺等人存在的破绽:①武帝用“丑诋”之言来抵消自己的罪过。此处辛用易佩绅语,颇有不坚实之感。②武帝批评自己的话,正在禅石闾之后。《资治通鉴》中正以此种变化。再言王应麟与黄中二人之前已有类似的观点。再点出这些人的错误乃是因为“单独阅读《通鉴》,很容易将泰山之诏与轮台罪己之诏联系起来”[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之后,辛德勇又举出明朝人王祎的《大事记续编》的论说,加以批驳。王认为武帝“亲耕巨定”恰好印证轮台悔过的合理性。辛以巨定远在东海,故而亲耕实际上是为向神仙示好。由此与禅石闾相合,论说这其实是“考神仙之属”的最后行为,而非是悔过的印证[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14页。。
要注意的是,此引言中,辛德勇所梳理的市村、唐长孺、王应麟等人的做法,乃是将泰山之诏与轮台罪己诏联系起来,进而认定武帝后期的转向。实际上,田余庆与他们稍有不同,田余庆直接以武帝一朝的政治局势与社会局势来看,并且配合轮台诏,进而说明这种转向。田并未提到泰山诏,或许是因为泰山诏本身即有破绽。而这两种思路,在辛德勇看来其错误根源即在《通鉴》的史料问题之上,所以辛德勇才会辨明通鉴史料。最后辛德勇表明了他引言最后的旨归,他先引用田余庆本人对于通鉴史料问题的辩白(前人历史文献解题类书籍,譬如柴德赓之书,柴书实际上渊源自陈垣之讲义。对于通鉴史料问题,论说“笼统”,黄永年是明确说明《通鉴》隋前部分宜引用纪传体而不用通鉴,黄永年实际上并没有论说通鉴史料来源上引后出小说的问题)。而在这之后,辛落脚到这篇文章的关键之处——对于《通鉴》的史料问题的考察。
然后,辛德勇解释了《汉书》中何以有“悔远征伐”等语,辛德勇觉得这是从刘向《新序》中所采录。辛然后引用刘知几的评价,来说明《新序》不可信据。辛德勇在这里的意图是要确定,《汉书》里关于悔过语不够可靠。这里辛实在得算赶尽杀绝。但此处其实有大破绽,辛德勇为驳倒汉书记载,征引刘向《新序》,并且认为《新序》不可信据,其实方寸大乱。因其核心乃推测语,不够坚实。
第二章,辛德勇在这一章里,开始论说攻讦的正是田余庆所用的《通鉴》中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相关史料的来源问题。这个乃是这篇文章十分精彩的部分,是特别坚实的地方。辛德勇关于《通鉴》此段的史料问题,所凭据的最关键的信息,来源于吕祖谦的《大事记》一书。实际上,前辈学者几乎很少引此书。辛德勇在其课堂上说明过,不是因为此书不好,乃是因为古之学者很难看到此书。吕祖谦家中富有藏书,其权威性不在朱熹之下。而他在《大事记》解题里言《通鉴》中言戾太子及巫蛊事,多本自《汉武故事》。有趣的是,辛德勇在这里,引用朱熹对吕祖谦《大事记》的赞扬,来说明吕氏说法之可靠[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7页。。此正与田余庆证明《通鉴》可靠的方法相同,辛也是以此来回应田说。之后,辛德勇用宋人王益之《西汉年纪》记载,说明王与吕同,乃弃除《汉武故事》的内容。辛德勇再说明征和四年罪己之语,不见于《西汉年纪》乃至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故只可能出自《汉武故事》。辛德勇以宋人晁载之《续谈助》中节录之《汉武故事》,乃推测《汉武故事》所言其实是服食求仙等事。这与司马光断章取义后所表现的有所抵触,所以才可能会出现悔己与汉书“禅石闾”相抵触的情况[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4页。。
第三章,此章进一步说明《汉武故事》的史料可靠性问题,而且兼及驳斥田说卫太子路线事情等事以及田文其他边边角角的问题。辛德勇先考察《隋志》与两《唐书》,在这些书里,《汉武故事》皆在史部里。但,吕祖谦、王益之、王祎等人却不信据。辛德勇解释到《汉武故事》一书的性质容易混淆,实小说而以为杂史。辛德勇继续从《续谈助》节录《汉武故事》来说明汉武故事充满怪诞传说,绝非信史。另外,田文跋语曾引述玉门花海出土之“汉武帝遗诏”。辛德勇以赵翼“汉诏多惧词”来说明不可轻易说此诏乃武帝遗诏。辛德勇再引用胡平生的看法,从受诏对象的年龄与无为而治思想来看,说明此诏有可能是刘邦遗诏,再从字句口吻说明此诏更类似刘邦的口吻。这里的论说其实也不够坚实。阎步克曾有文考证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说,阎步克文章实际上是承接讨论田余庆《论轮台诏》而来。辛德勇故对此也有驳斥。辛德勇承接阎步克文章,考察石德此人私德所为,以此证明他不是宽厚长者。但这里,实在得算是辛德勇的一个破绽。阎步克的主要立说其实皆凭借《史记》、《汉书》,而并非《通鉴》,阎说所立其实是很坚实的。而且“宽厚长者”一词在史书的编撰里,是有特定指称的。何人是宽厚长者,无论偏好儒术的或偏好黄老的,实在有其义例,并非仅仅评说私德如何就可以驳倒。此外辛德勇驳斥阎步克以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事。辛德勇认为太子十八岁小小年纪,能否了解谷梁系统的思想体系实在是很令人疑惑。之后辛德勇又梳理彼时史事,说明卫太子好谷梁的原因:辛德勇以为前辈学者多不能阐述西汉谷梁学真相,唯有柯邵忞最佳[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3页。。辛德勇借此说明谷梁大义在“长幼之序”,此正切合彼时戾太子的年龄与心理状况[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9页。。此处正是辛德勇又一大破绽,辛德勇引清时学者之孤说,来发明谷梁大义,并以此配合彼时卫太子之心绪,此种做法实在太过大胆。实际上阎步克立说以及史料来源均无较大问题,不易驳倒。辛德勇要赶尽杀绝,自然不甚容易。
第四章,此章乃返回到司马光时,说明司马光如何取舍史料。辛德勇考察《通鉴》汉纪所用的《赵飞燕外传》一书为情色读物,进一步说明《通鉴》史料选择上不可靠。辛德勇进一步指出《通鉴》用两《唐书》皆无的《天宝遗事》小说,说明我们要审慎对待《通鉴》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分析《通鉴》史料之是否可靠,此等论述其实乃辛书最不可磨灭之部分。
辛德勇再用日本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一书中关于《通鉴》用小说史料的看法来为自己佐证,接着引用赵翼言“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进一步为自己作证[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04页。。辛德勇接着揭示司马光篡改选择史事的原因其实是他的政治诉求与意图。辛德勇然后梳理史家叙事如实的准则,说明司马光的行为,实际上是史学著述流变过程中的新风尚。即以个人的私好、政治诉求、学说观念等来采选史事。辛德勇最后的立足点在于说明司马光的撰著意图与独特手法。而后来学者,也应该以更加审慎的态度看待《通鉴》的史料价值。有趣的是,在这里辛德勇虽然没提,但他已经悄悄修正了他老师的提法。黄永年实际上特别赞赏《通鉴》在唐五代记载中的史料价值[注]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48页。。
第五章,在这一章里辛德勇更返回到王俭时期,说明王俭制造《汉武故事》的原因。此章很精彩。首先依据余嘉锡《提要辩证》之思路,从《隋志》、两《唐书》以及《崇文总目》等书目中寻找《汉武故事》的撰者,然后从《续谈助》跋语以及《郡斋读书志》中的记载,将《汉武故事》作者确定为王俭。辛德勇接着考察王俭及刘劭的生平,说明为何王俭要完成《汉武故事》的“制造”。辛认为《汉武故事》中卫太子“守文”的理念,与刘邵王俭的主张恰相一致。这里需注意的是,辛德勇说:“从另一方面看,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的特定经历,在著述中,往往会或有意无意地掺入一些个人的感慨,或是寄寓某种情感或者主张。”[注]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9页。此处正点明辛的手法乃是颇为传统的知人论世,而非史料批判云云。
第六章,在此章辛德勇返回汉代,考察不类己事的原型。辛德勇引民国人李笠所言“史记通例”来说明太史公“假托”一法。也即后人在讲述史事时,因为情形相同而无意掺入前人的典型事例。辛德勇考察王俭所塑造的汉武帝与卫太子对立形象,还有西汉时代的原型。也即刘邦与汉宣帝时事情。辛德勇进一步说明宣帝史事,并且用宋人王应麟的提法,说明昭宣并非守文气象。辛认为直到元帝即位,才转向守文。前文已经提到,实际上田余庆也不认为昭宣时是所谓的“守文”,按田余庆所说,他是认为武帝末期到昭宣时是霸王道杂之的。有趣的是,在这里,在辛德勇和田余庆二者论说领域之中,所谓的“守文”其实含义并不相同,故而才有此矛盾存在。辛认为汉宣帝与元帝治国理念之不同,正是王俭《汉武故事》中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原型。有趣的是,王子今反驳辛德勇的攻讦意见也用的是同样的逻辑。王子今认为,似乎我们也不能排除《资治通鉴》和《汉武故事》分别采用了共同的可以看作“原型”的早期史料的可能[注]王子今:《“守住科学良心”——追念田余庆先生》,《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31日,第7版。,并以此来为田余庆辩护。
最后谈代后记,此文为出书时后加入,即辛德勇悼念田余庆文章。辛德勇以此文为后记,意在表示对田余庆先生的尊重。此篇代后记颇有意思,有些话意味深长,也内含锋芒。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末提到“实在没法跟先生谈这些不着调的想法。同时也不便汇报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先生不同的看法”[注]辛德勇:《田余庆先生印象(代后记)》,《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76页。。由此可知,此时辛似乎并不知道田已经读过他的文章。
陈爽先生在田余庆先生逝世后拍摄过田先生的书桌,由照片可知田余庆先生去世前一天仍在伏案工作,在他工作的书桌上方还摆放着他那本黄色书皮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上面则压着一摞厚厚的刚打印好的新论文。田先生视力不佳,许多书都需用放大镜来辅助阅读,那叠厚厚的论文恐怕是特意用大字打印出来的,或许那篇就是辛先生的文章。只是不知道田先生读着辛这篇专为批驳他得意之作的论文,心里又做何种感慨。
——薛天纬先生的盛唐边塞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