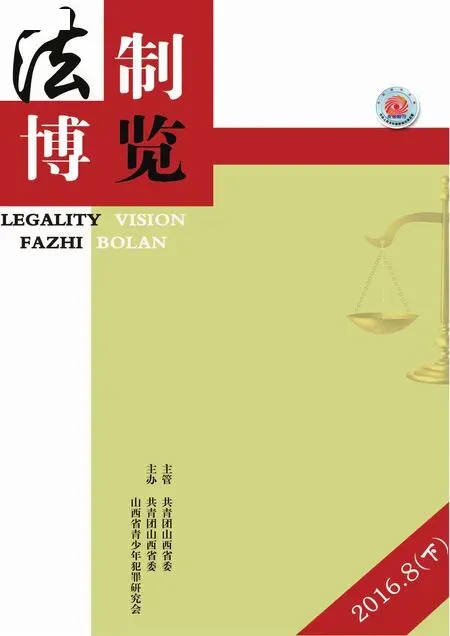唐宋时期商人法律地位浅析
严依涵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100876
唐宋时期商人法律地位浅析
严依涵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100876
摘要:商业之于经济亘古至今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态势下,各国商业无疑首当其冲成为竞争对象。与现代商法所不同,我国封建社会严重存在着“重农抑商”思想限制,统治者从立法、政策设计上都严格控制商业。本文拟通过从商业之源头探究唐宋之前历朝历代对商人法律地位的限制,对比突出唐宋时期打破惯例,提高商人法律地位。并且通过这种对比,探究缘何唐宋能够提高商人之法律地位,并借此进行评论。
关键词:重农抑商;市籍;商人入仕
一、唐宋时期之前传统封建社会商人法律地位
商人在古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但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离不开商人之存在以及其交往活动,正是基于此,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以法贱商,一方面维护其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权力,另一方面为维护社会稳态运行以及国库良性运作,不断打压商人,推崇重农抑商之原则并从古延续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中国国门。但商人这一阶层在古代存续期间,却并非一直遭受打压。
(一)中国史上之于商人第一个黄金时期
关于我国商人活动最早的记载,《易经·系辞》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后之西周因着其“工商食官”之政策,即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工、商强烈依附统治阶级。国家对商人之管控绰绰有余,并未出现重农抑商之思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之活跃必然离不开经济之发展。至此,我国进入了商人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亦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局面。
(二)重农抑商缘起及商人发展步履维艰
首先,在人身自由权方面上,与普通编户齐民不同,凡是长期固定在市里经营的商人都必须到官府登记,单列市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只要曾经有过市籍,不仅本人,而且子孙都是充军对象。此外,将商人单独列入市籍又为统治阶级无偿向商人征收赋税、要求其提供物资、劳役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在政治权利与自由方面上,受抑商政策影响颇深,士大夫一层、贵族阶层、统治阶层无不在社会生活之各方各面歧视着商人。最后,在社会日常生活方面上,唐宋时期之前对商人的服色、丧葬以及乘马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唐高祖武德初年沿袭旧制:“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二、唐宋社会变革之际商人法律地位之提升
唐宋社会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等战乱,但这也为商人之生存发展提供了第二个春天,值此之际,朝廷拉拢商人来支持自己的战争亦或维持自己之经济需求,就不然不能再继续贬低商人,势必要提高商人之积极性。
(一)唐宋时期国内商人地位之变革
我国封建社会进程中,自商鞅重农抑商政策及思想经由秦朝推广之后,为历朝历代效仿。然而到了唐宋时期,一方面唐宋社会变革之际商品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士大夫等统治阶层对商业、商人依赖性提高,与此相随,“农”这一阶层也伴随开始出现大量涌入市场中来。商人将农民剩余之农作物带入市场中有规模的出售,同样,部分农人也试图自己将自己所剩产品小规模的进行销售,至此,这种农业与商业互相影响之现象使得唐宋之际韩愈率先提出了“农商相补”理论。另一方面唐宋均田制瓦解、租佃制兴起、坊市制崩溃、两税法颁行等,都对唐宋商人地位之提高保驾护航。
三、唐宋时期商人法律地位变革之根源
唐宋时期统治者一改前朝重农抑商政策,这在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属巨大突破。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等方面上,提高商人之法律地位,无疑不使商人以及商业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那么,缘何封建制社会发展至唐宋之际才一改“贱商”态度,反而积极地倾向于保护商人呢?
(一)唐宋商人地位提升之政治根源
一方面,唐代中央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门阀士族势力不再一如往昔以及唐中后期均田制之废弛给商人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境况。另一方面,从唐宋的政治格局来看,唐宋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律中原先规定的部曲和奴婢等贱民都逐渐趋于消亡,唐宋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也由差役制向招募制发展,尤其是私有手工业中的工匠,雇佣制则成为主要形式,雇佣契约结构中最突出的变化。
(二)唐宋商人地位提升之经济根源
唐宋声名大噪的商品经济繁荣盛景,给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先来看唐代,“盛唐时期的商品市场,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扩大。此外,商人们的水路、陆路外贸活动也沟通了高丽(新罗)、高丽、日本、西域、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诸国以及西亚、欧洲一带各个国家,也促使统治者意识到其之世界地位。至此,势必当提高商人之法律地位。
四、唐宋之际商人法律地位转变之评析
唐宋社会变革时期,经济变革成为主导因素,基垫于唐朝盛世,为日后商人发展商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契机。但就我国古代封建史发展之大方向而言,这种片面的、口号式的“恤商”终难掩盖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之意志。
(一)唐宋改变商人法律地位之积极意义
唐宋时期不断完善其商事立法,革新旧制,提高商人法律地位,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范本。一方面,其使得商人摆脱了“贱民”之地位,使得其不再处于社会之最低端。另一方面,放宽对商人之诸方面的限制与歧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而不是被迫从事到商业发展活动中,经商致富,使得商人成为了令人羡慕的一种职业,据此,唐宋之际异军突起一大批保人、牙人、中人、引见人等商事第三人,为经济社会之发展提供活力。政府加之其对第三人诚信原则之渗透、对大商贾垄断损害普通商人之规制,维护了经济社会发展之稳定性。
(二)唐宋转变商人法律地位之局限性
唐宋提升商人地位无论从法律、政策亦或社会观念,面面俱到,具有一定的社会发展之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唐宋发展商业、提升商人法律地位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唐宋的这种转变仅仅是些微的量变过程,从未达到质变的程度。宋代禁榷制度的严苛性体现为禁榷种类的增多和处罚力度的加大,宋代禁榷物品除传统的盐、茶、酒外,又有矾、香药、铁、石炭、醋等。这种严格的对商人的管控可谓是另一种限制。
唐宋之际,我们不可否认其确实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统治者通过打着“体恤”之旗号,笼络商人这一财富聚集者联盟,无疑不体现着其压榨其财富、维护小农经济、达成其更好的统治之目的。这种放宽限制与实际管控的矛盾冲突也使得我国在封建时代不可能出现像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萌芽。
[参考文献]
[1]蔡泽琛,赵波.重农抑商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唐宋时期为中心的讨论[J].求索,2004(11).
[2]宋娟.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3]许华松.宋代商人法律地位之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0.
[4]许华松.宋代商人法律地位之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0.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4-0181-02
作者简介:严依涵(1992-),女,天津蓟县人,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学生,研究方向:网络法、知识产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