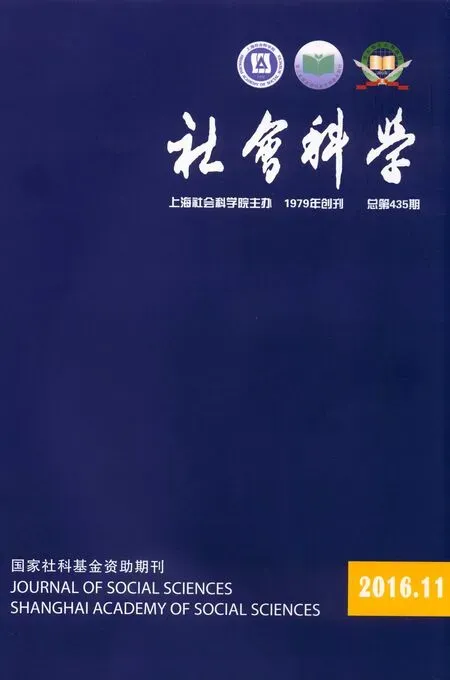通向身感心赏之学
——现代中国的美学需求
王一川
通向身感心赏之学
——现代中国的美学需求
王一川
美学在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层面受到高规格和高强度重视,有着比之单纯的学科专业缘由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深层缘由。尽管对美学学科的怀疑依然存在,但从美学在现代中国的需要及其演变看,美学已然成为中国人在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寻觅到的使身体感官需要与心灵需要之间臻于平衡和融合的通道。现代中国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于,依托现代性知识型的生成而产生的具象而精致的身体审美感性如何与逐渐被挖空和风干的中国古典心性传统重新接通。现代性身体感性文化必须和只能与现代性心性文化相匹配。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之说的疏忽在于,多满足于身体感性的现代性转化而少关注心性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在当前心体群己之间的分离加剧成为全社会难题的情形下,美学需继续处理中国人的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如何完美融合的问题。美学在当代可以成为一门身感心赏之学,即是关于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的融合的学科。由此可以获得美学存在的当代理由:通过探究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的协调而实现心灵的宁静。
现代中国的美学需求;身感;心赏;身感心赏之学;心体群己
在当前中国,美学自然不可能再度复制上世纪80年代有过的“美学热”盛况了,但其学科地位和作用却早已变得更加务实和稳固,同时在艺术界及相关社会各界仍然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这具体地表现在,美学在当前中国不仅已成为哲学门类下哲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而且,更被艺术学门类下几乎所有五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及其所辖的各类本科专业,都列为必修或选修课程以及需要持续研习的关联性学科领域了。这还远远不够,新变化已经初显:随着国家领导人发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号召(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落实为《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以及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美学显然已跃升到了国家文化强国体系、人才强国体系和科教兴国体系等多种国家战略规划的交叉地带。如此看,美学在当前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业已不局限于具体的学科专业层面,而是跃升到了更基本而又重要的国家战略高度。那么,应当怎样看待美学在当前中国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也就是说,美学在当前中国,为什么不仅在艺术学领域、而且更在国家战略层面受到如此高规格和高强度的重视?在这种超强度重视的背后,是否还有着比之单纯的学科专业缘由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深层缘由?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
一、 美学质疑
与美学在现代中国曾经受到热烈拥戴、并在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层面高端亮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曾经“发明”美学学科的德国,美学的地位并不稳固,几乎一直不停地遭遇种种质疑。被认为是当然的美学家的黑格尔,在其《美学》的开篇就列数诸多“反对美学的言论”,其中有如下归因:“纵使美的艺术可以供一般的哲学思考,却仍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适宜对象。因为艺术美是诉诸于感觉、感情、知觉和想象的,它就不属于思考的范围,对于艺术活动和艺术产品的了解就需要不同于科学思考的一种功能。”*[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这种质疑到上世纪30—40年代仍在持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就提出过如下判断:“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说关于艺术和美的无数美学考察和研究无所作为,无助于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尤其是无助于艺术创作和一种可靠的艺术教育。这种抱怨无疑是正确的,特别适合于今日还借‘美学’名义到处流行的东西。”*[德]海德格尔:《尼采》,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页。
其实,西方学界对美学的质疑或批判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8世纪末,早期浪漫派主将之一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August Schlegel,1772-1829)就表达过如下质疑:“审美的[ästhetisch]一词,在德国发明并在德国得以成立,在这个词这个意蕴中,泄露了这个词完全不了解它所描绘的事物及用来描绘事物的语言。这个词为什么还被沿用至今?”*[德]施莱格尔:《批评断片集》,载《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页。进入20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虽然没有怀疑美学,但也明确指出美学并非一门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源远流长的“古代科学”,而只不过是一门“近代科学”。因为,按照他自己提出的“美学是表现(表象、幻想)活动的科学”这一标准,“只有当幻想、表象、表现的实质……被确认时,美学才会出现”*⑤ [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那么,美学显然只能被置于稚嫩的“近代科学”行列了。所以,他公开宣布自己“不能不站在那些断定美学是近代科学的人的一边”。⑤
对一度不可一世的美学施加致命一击的,当推20世纪兴盛一时的分析哲学。英国的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干脆把美学同伦理学一道列入需要彻底否定的学科行列:“伦理判断只是情感的表达,不可能有任何方法去决定任何伦理系统的效准,并且,去问任何这样的系统是否真实,确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关于伦理学性质的结论也适用于美学。美学的词的确是与伦理学的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的。如像‘美的’和‘讨厌的’这样的美学的词的运用,是和伦理学的词的使用一样,不是用来构成事实命题,而只是表达某些情感和唤起某种反应。和伦理学一样,接着就必然会认为把客观效准归之于美学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并且,不可能讨论到美学中的价值问题,而只能讨论到事实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美学之中并不具有比伦理学中所具有的更多的东西足以证明那种观点,即认为美学是体现知识的一种独特类型。”*[英]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9、130页。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关于美学的讲演的开端处就说:“这个题目(美学)太大了,而且据我所知是完全被误解了。像‘美的’这种词,如果你看一下它出现的那些句子的语言形式,它的用法比其他词更容易引起误解。‘美的’是个形容词,所以你会说:‘这有某种特征,即美的特征’。”*[奥]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与谈话(1938—1946)》,江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他在《文化与价值》中指出:“审美力可能是令人兴奋的,但却不能把握。”*[奥]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就连中国当代美学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泽厚,也在其《美学四讲》的开头承认,“从很早起到目前止,一直有一种看法、意见或倾向,认为不存在什么美学。美或审美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学科,因为在这个领域,没有认识真理之类的只是问题或科学问题,也没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法则或客观规律。”*③ 李泽厚:《美学四讲》,载《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2007年版,第395、398—399页。他甚至接连引用黑格尔、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上述观点去阐述美学遭遇的质疑。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不必因噎废食,不必因语词概念的多义含混而取消美学的生存;正如并不因为审美的艺术领域内突出的个性差异和主观自由,便根本否认研究它的可能一样。事实上,尽管一直有各种怀疑和反对,迄今为止,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严格证实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不能成立或不存在。分析美学也未能真正取消任何一个传统美学问题。相反,从古到今,关于美、审美与艺术的哲学性的探索、讨论和研究始终不绝如缕,许多时候还相当兴盛。可见,人们还是需要和要求这种探讨,希望了解什么是美,希望了解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欣赏的概括性的问题或因素。”③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门连在西方本身也难免遭遇质疑的稚嫩的近代科学或学科,到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却都接连交上好运而成为中国艺术学子的必修法门?显然,通过一番简要的中国现代美学学科体制化进程回顾,去重新发现其中隐伏的问题,就是必要的了。
二、 美学在现代中国
我们知道,直到晚清或清末,中国传统文人依旧高度重视个体的安身立命,并且把它投寄到由儒家、道家和禅宗所代表的心学传统上。这具体表现在,儒家的仁爱之心、道家的“心斋”之说、禅宗的“明心见性”或“即心是佛”等把“在心上用功”作为个体的必修法门。但面对裂岸涌来的“西学”或“现代学”,这种传统格局无法不遭遇空前剧烈的危机。
晚清或20世纪初王国维的美学启蒙工作就具有其重要性。他通过日本的中转而从欧洲引进“美学”,是要为古典式文人在现代生活中遭遇的人生幻灭感找到一种思考通道。而他借助尼采的“梦境”(日神状况)与“醉境”(酒神状况)之说等的启迪而提出“境界”或“意境”说,则是试图找到可以在这条通道里歇脚的一个亭台楼阁,正是凭借这个亭台楼阁提供的特定视角,置身于新的世界条件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得以时时返身回瞥令自己流连忘返的往昔古典文化景致。但这条更多地仅仅通向过去的通道毕竟有些消极,无法让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脚下的现实和展望未来新景致。如何为在全球化世界里一时彷徨无依的中国文人找到一条新的解救之道,还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王国维提供的消极通道还无法圆满回答现代中国人在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如何安身立命的严峻问题。
与王国维的消极之道不同的是,一己而身兼清末翰林、德国博士和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这三重身份的蔡元培,则试图找到一条新的积极通道。他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以先后担任政府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的重要位置,在全国教育界大力倡导“美育”方针并推进其制度化,并在随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进一步推行美学、美育及艺术学科的体制化,还提出令人惊骇的“美育代宗教”主张。应当看到,蔡元培并非标举美育代宗教之类主张的第一人。王国维在1906年就指出:“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吾人对宗教之兴味,存于未来,而对美术之兴味,存于现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大。”*王国维:《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载《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他还只是在与宗教并举的意义上推崇“美术”(即艺术)的“慰藉”作用,蔡元培则进而要运用来自欧洲的“美育”及“美学”等现代性规划,给现代中国人输入一种新的宗教代替品——美育。蔡元培在“五四”时期撰文和演讲中多次倡导“美育代宗教”说。他认为,宗教诚然历来与美感或艺术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包含有“五育”的要素,但不仅时代在变,而且各种宗教彼此之间总是党同伐异,“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卷入现实政治、种族冲突之中,“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转以激刺感情。”*②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原载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33页。因此,蔡元培主张“纯粹之美育”,并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他在此高度倡导美育包含的“普遍性”或“公开”性内涵:“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②美育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有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的“公开性”或“公共性”意义。*关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参见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386页。尽管如此,蔡元培的美育遗产的疑难问题之一在于,假如光有现代美育中的艺术技能及形式感受方面,而不能在其中注入能令现代中国人足以安身立命的“心学”内涵,那么,无论是“美育”、“美学”还是“美育代宗教”等主张,都可能只是缺乏实质内容的空洞的外壳。这就是说,蔡元培难题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以美育手段把美感植入现代国民机体,以期起到宗教在西方起到的心灵皈依作用,安抚动荡不安的现代中国心。但另一方面,对缺少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人,美育又如何可以像在西方那样扮演宗教的拯救心灵角色?这难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中。蔡元培的美育方案的真正的教训及问题在于,虽已制定积极的美育制度措施,但光有美育外壳,终究无法解决中国人的深层次心灵安置问题。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心学”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问题的严峻性凸现出来了。
似乎正是要回应上述蔡元培难题,十多年后的朱光潜在其《谈美》(1932)中做了新的诊断:“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既然病根在于“人心太坏”,那首要的治疗方式就是疗救“心”:“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朱光潜:《谈美》,载《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有意思的是,朱光潜没去重复蔡元培的“美育”说或“美育代宗教”之说,而是转而倡导“人生的艺术化”。他的美学思想的逻辑线索在于,既然“人心变坏”了,那就迫切需要通过“人生的艺术化”途径而实现“人心净化”或“人生美化”的目标。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在于,人生本来就是艺术品,而提倡“人生的艺术化”不过是要让人回归于其原初本性罢了。朱光潜在该书中开列的“人生的艺术化”的具体途径有:“美感”、“心理距离”、“移情”、“情趣化”等。朱光潜那时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现代人的心灵困境问题的缘由在于中国古典“心学”传统的断裂,但毕竟准确地指向了蔡元培等所遗留下的“心”的缺失之症候本身,并开列出“人心净化”这一独特的药方。但是,他留下的疑难问题同样明显:“人生的艺术化”方案如何与其时“危急存亡”时代社会群体的民族危机拯救实践及“社会革命”行为相协调?当时的中国现实并未接受这一药方,而是相反选择了社会革命的改天换地之方——要用全“新”的社会革命去取代纯“心”的个人救赎。宗白华于1932至1949期间的系列探索,可谓与朱光潜异工同曲:他标举“中国艺术意境”或中国式生命之“节奏”,主张回归于“晋人之美”,力图以“中国艺术心灵”去建构现代中国人的完美精神世界,从而落脚点仍在于个体的“心”上而非社会的“新”上,无论两人之间对“心”的理解有何不同。他的问题与朱光潜的一样,这就是:个体心灵美化与社会群体行为的关系应如何协调?这些都可以视为现代中国美学体制化进程中迈出的有力的但又同时有缺陷的步伐。后来的越来越激烈的社会革命形势,使得这种“人心净化”的美学体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了。全社会的“新”表面看很诱人,但假如缺乏来自传统的“心”的充实,势必难掩这一庞大身躯内部核心或灵魂深处的中空。
与朱光潜和宗白华力图返回“人心”或从“中国艺术心灵”去安置美学视点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路线:不是少数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高贵心灵,而是绝大多数人民或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才是文艺及美学的唯一源泉。“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869页。人民或民众迫切需要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美提升到“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高度,于是才有了审美及艺术的需要。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审美及艺术领域的“自由竞争”:“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②这里吸收来自苏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美是生活”命题而又加以富于中国化特点的调整。但现在回头看,那时在返回社会生活源泉的时候在对个体心灵的安抚上是有明显的忽略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美学讨论,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核心学说的周围仍存在必要的美学维度,这种存在有利于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体找到自身的心灵安置之所在,但可惜没能深入下去。不过,朱光潜提出的美在“主客观统一”之说以及吕荧和高尔泰等提出的美在“主观”之说,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为今天重新接续中国自身的古典“心学”传统具有一种铺垫性意义。这里需要提及当时的年轻美学家李泽厚写下的《“意境”杂谈》(1957)一文:“艺术正是这样把美的深广的客观社会性和它的生动的具体形象性两方面集中提炼到了最高度的和谐和统一,而用‘意境’、‘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这样一些美学范畴把它呈现出来。诗、画(特殊是抒情诗、风景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概念并且还是互相渗透、可以交换的概念;正如小说、戏剧也有‘意境’)一样,诗、画里也可以出现‘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在这种深远的生活真实里,艺术家主观的爱憎、理想也就融在其中。”*李泽厚:《“意境”杂谈》,《光明日报》“文化遗产”1957年6月9日、16日,载李泽厚《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139页。该文独具只眼地首次把“意境”范畴提升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范畴“典型”相互平行的高度,突出“意境”范畴所具有的客观真实(身体)与主观情感(心灵)相互交融功能,无疑带有“补天”的勇气,有可能为王国维和蔡元培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悬而未决的“心”的问题找到一种合理的通道。
新时期美学热的导火线在于何其芳遗作中披露的毛泽东的“共同美”谈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从跨越各个阶级的“共同美”的争鸣中点燃的“美学热”,掀起了重新探究现代中国美学的学术热忱与生活关怀。似乎正是要接续50年代有关以“意境”去调和客观身体与主观心灵的对峙局面的积极思考,改革开放时代之初的李泽厚,敏感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性,也即不是像朱光潜和宗白华那样仅仅从知识分子个体心灵视角而是从族群或群体心理视角去凸显“心”的重要性。 “线的艺术(画)正如抒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212—213页。显然,李泽厚用群体式“文化—心理结构”一举取代朱光潜式个体“人心”。如此,艺术品符号系统的意义被认为直接指向整个族群甚至整个人类的群体心理结构:“人类的心理结构是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也许正是它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恒性的秘密?也许,应该倒过来,艺术作品的永恒性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生产创造消费,消费也创造生产。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传流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魂灵的心理学。”②这种注重群体心理的立场还表现在,他在为宗白华《美学散步》写的序言中提出中国美学的四大支柱之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并不否弃生命的中国佛学——禅宗,加上屈骚传统,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李泽厚:《美学散步·序》,载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而在其中,善于融合各家并高度重视群体心理的儒家美学,被他视为最主要的那根支柱。
有意思的是,80年代时的李泽厚并未遗忘蔡元培当年的“美育代宗教”留下的遗憾,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新提出的群体心理立场上、以及更基本的“美学的人化自然”途径中去加以实现:“如果说,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主体结构还具有某种外在的、片面的、抽象的理性性质,那么,只有在美学的人化自然中,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历史与现实,人类与个体,才得到真正内在的、具体的、全面的交融合一。……这种统一是最高的统一。也是中国古代哲学讲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是能够替代宗教的审美境界,它是超道德的本体境界。”*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这里相信他提出的“美学的人化自然”不仅是蔡元培意义上的“能够替代宗教的审美境界”,也即“超道德的本体境界”,而且还属于后来被钱穆临终前力倡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钱穆是在1990年96岁高龄、即将辞世前夕以临终遗言这一特殊方式全力标举“天人合一”观的:“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在钱穆看来,“天人合一”说有助于解决中国人的心灵乃至全球各民族心灵的安置问题。这一主张由于季羡林等的引用和倡导,曾一度在大陆哲学及美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包括争议。*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这种影响及争议本身表明,中国文化的归宿问题,也就是心的安置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又迫切了。
以上表明,美学在现代中国激发起强烈的需要并唤起持久的探究热忱,并非仅仅源于现代中国人以五官感觉去把握世界的需要,而是有更深且复杂的缘由:在急剧变化着的现代世界寻觅到一条能使身体感官需要与心灵需要之间臻于平衡和融合的通道。如此,把美学的热潮单单归因于身体感官需要或是心灵需要的做法,无疑都是简单化的。
三、 心体群己之间的当前分离及其后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方位社会变迁,包括艺术变化,当年的“美学热”在现实生活以及艺术生活进程中又出现了丰富而又复杂的分离式演变,很难加以清晰的概括。要而言之,其中有三条取向值得关注:取向之一,美学关怀下沉为日常生活中的美化过程,如美容、美发、美食、居室美化等;取向之二,美学关怀上升为抽象的学术思辨过程,例如美的哲学;取向之三,位居上述两者之间的美学关怀落实为审美心理的形式化、审美形式的艺术化以及艺术学科的美学化等过程。这表明,美学在今日中国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路径,交织着多重彼此难以归类的矛盾。
但有一点是可以指出的,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学及其相关的美育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地位有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当国家经济发展了,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但文化发展中的缺失、社会心理中的混乱无序及个体心理的皈依感的丧失也在加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对此所做的判断是:“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明确做出上述承认,体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当前问题的坦率和直面姿态。
从中国美学角度去看,上述问题或许可以集中体现为心体群己之间的分离。一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的悖逆越来越显著和突出,人们在身体需要与心灵需要之间的选择上陷入困境,往往为了身体需要而淡忘心灵需要,也就是为了身感而遗忘心赏。二是群众(群)与个人(自己)之间的对立愈益尖锐,体现为普通群众的娱乐需要与知识分子的心灵提升需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显著。这些表现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就是欲望、金融、资本或权势等成为艺术发展的强劲动因或严重桎梏。
也许,正是在上述严峻问题及其相关矛盾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才得以制订出来。国家领导人在前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同时,该讲话中还交织着以下一系列相关美学论述:“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等。随后有《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坚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颁布国办发〔2015〕7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基本原则在于“遵循美育特点和学生成长规律,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在整体推进各级各类学校美育发展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美育存在的突出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总体目标在于“2015年起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到2018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美育资源配置逐步优化,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开齐开足美育课程。到2020年,初步形成大中小幼美育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始终贯穿着美学学科领域经常运用并探讨的学科性或学术性命题,如“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格调、审美理想”、“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培养具有审美修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营造格调高雅、富有美感、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以美感人,以景育人”、“引导学生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等。这些表明,美学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战略的当然组成部分被设计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四、 美学研究的当前理由
从上面的简要回顾和讨论可见,美学在现代中国有自身的特定需要,并经历了盛衰演变,其间有过风光,经历暗淡,当前又正面临新的使命。那么,应当如何理解美学研究的当前理由?也即,在当前从事美学研究有什么作用?人们对此的回答想必人言言殊、见仁见智,不必硬求一律,基于此,我想在如上讨论基础上谈点初步考虑。
中国美学的基本的问题之一还在于,依托现代性知识型的生成而产生的具象而精致的身体审美感性如何与逐渐被挖空和风干的中国古典心性传统重新接通。当来自现代性传统的交响乐、芭蕾舞、话剧、油画等不断挤压古典式琵琶、戏曲、水墨画等的生存空间,并迫使其面向现代性而寻求转化时,由此产生的新的身体审美感性又该如何去与业已变得水土不服、气息奄奄的中国古典式心性传统相匹配呢?显然,中国古典式心性传统本身的现代性转化也同样变得重要而又急迫了。中国人的现代性身体感性文化必须和只能与中国人的现代性心性文化相匹配。由此看,蔡元培在“五四”时期倡导“美育代宗教”时的致命疏忽在于,多满足于身体感性的现代性转化而少关注心性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而后者更是具有致命的重要性。
今天,在追究这类问题时,不妨重温六朝宗炳《画山水序》的观点:“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还有,“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83—584页宗炳在此倡导的“应目”、“会心”和“畅神”三环节的整合相应之说,在清代叶燮的主张“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原诗》,载《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85页。中获得回应。在宗炳与叶燮两人之间略作比较,“应目”与“感于目”、“会心”与“会于心”之间但从字面上看是无甚差别的,只是宗炳的“畅神”显示了对一种积极的深层心灵至乐的发现和肯定。
这使我想到,美学在当代要继续处理现代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人的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如何完美融合?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在当代可以成为一门身感心赏之学,即是关于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的融合的学科。冯友兰指出:“哲学底活动,是对于事物之心观。……艺术底活动,是对于事物之心赏或赏玩。心观只是观,所以纯是理智底;心赏或赏玩则带有情感。”*冯友兰:《新理学》,载《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这里被叠用的“心赏”与“赏玩”,实际上正是指心灵的情感游戏,与康德有关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之说相通。艺术作为心赏,在这里应是指一种在身体感觉中满足心灵提升需要的自由游戏。这里的身体感觉是说,当前全媒体时代或互联网时代为满足人们的身体感觉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技术条件,致使人们无节制地冒险持续开发并放纵自己的身体感觉的满足。而这里的心灵鉴赏则是说,正由于此,人们诚然必须依靠身体感觉去证明自己,但更需从身体感觉层面升华到心灵鉴赏层面,直到回归于心灵的宁静。由此可以获得美学存在的当代理由:通过美学去探究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的协调问题,也即透过身体感觉而实现心灵归于宁静的途径。
这种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的协调,在当前具有必要性。张世英发现,现代西方艺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重感官美,声色之美;另一个是“为艺术而艺术”,其缺点是重视声色之美,好看、好听,感官娱乐,可是单纯感官娱乐没有深层内涵。这为西方后现代艺术所批判,强调艺术要深入生活里面。但后现代艺术明显有缺点,完全丢掉感性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针对这种偏颇,他提出一种主张: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就是艺术、文艺要深入到生活里面去,要和现实相结合。生活艺术化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到艺术水平,生活要超越现实。”现实的身体感性与精神超越之思应当结合起来。“我主张讲声色之美,但我们的声色之美也要看它背后有没有精神支撑,有没有背后的意义,有没有它深层含义。因此艺术生活化既不能离开感性美,又要讲精神境界的支持,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张世英:《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据《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发言摘要》,《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2日。这就是说,一方面艺术要从现实生活的沃土吸纳生气,另一方面生活要按艺术的精神境界去提升。这等于就美学中身体感觉与心灵鉴赏之间的协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当前全媒体时代或互联网时代条件下,中国美学更需要探索出从身感而上升到心赏之境的途径。
(责任编辑:李亦婷)
Toward the Study of Physical Sensation and Soul Appreciation — The Demand for Aesthetics in Modern China
Wang Yichuan
Great importance is currently attached to Aesthetics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China,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purpos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some deep reasons which hav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for Aesthetics and its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Aesthetics has been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ese to maintain balance between spiritual needs and physical needs in today’s fast-changing world,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some skepticism about Aesthetics. One of the basic issues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is that how to reconnect the physical aesthetic perception whose produc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modern episteme and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of mind-nature. The culture of modern physical perception must match with the modern mind-nature culture. The insufficiency of Cai Yuanpei’s theory of replacing religion b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a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perception was overemphasized whil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ind-nature tradition got less attention. Aesthetics must continue to deal with the issue that how to perfectly fuse Chinese physical sensation and soul appreci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aggravating separation between mind, body,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has been a social problem. Aesthetics could become the study of physical sensation and soul appreci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us achieving the peace of mind by harmonizing physical sensation and soul appreciation could be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Aesthetics at the present time.
Demand for Aesthetics in Modern China; Physical Sensation; Soul Appreciation; the Study of Physical Sensation and Soul Appreciation; Mind/body and Collective/individual
2016-07-11
I01
A
0257-5833(2016)11-0165-09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