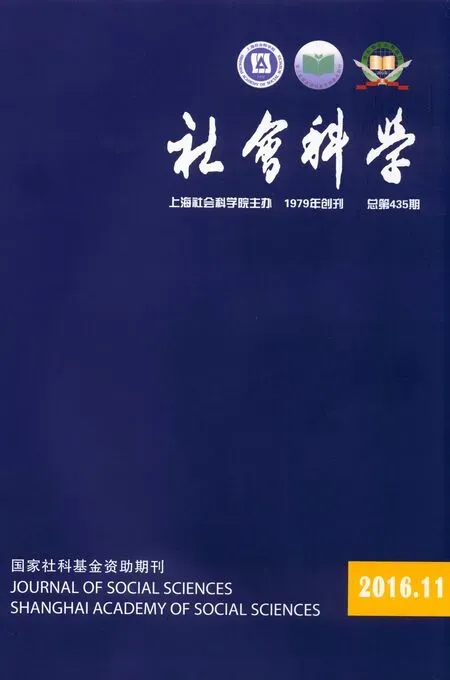义熙政局与“宋氏以文章闲业”之缘起*
李 磊
义熙政局与“宋氏以文章闲业”之缘起*
李 磊
晋宋之际,文学成为门阀文化新标志,以至南朝“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文学变化相关,更重要的是文学在士论中地位上升所致。义熙八年之前,门阀政治格局破坏、皇权政治尚未复归,谢混在文学上“大变太元之气”,获誉“风华为江左第一”,再凭借民望及世资在政治上荣登高位并“领选”,文华之风成为“流俗”。义熙八年后,刘裕独掌政权,但在其“造宋”活动中不得不妥协于门阀新文化,这是“宋武爱文”的政治涵义。经义熙年间的变化,重文华之风已从高门士族的人物品题扩展为包含士、庶的社会评价,并深入到九品中正制下乡论标准之中,对士人的仕宦生涯、社交声誉起着决定性影响。
东晋;刘宋;文学;士族
自五马渡江、江左政权重建以后,东晋南朝一般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其绍续魏晋,而与十六国北朝相对*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若从近三百年江左历史的内部进行观察,晋宋之际则被看作是一个核心枢纽。围绕着这一历史转折点,政治史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尤其以田余庆先生的晋宋之际门阀政治衰落论与皇权政治复兴论最为知名*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晋宋之际同样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百年后《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将这种变化概括为“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南齐书》卷39《刘瓛陆澄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86页。。那么,晋宋之际政治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两大变化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本文试图聚焦于晋末义熙年间,从刘裕造宋政局中高门士族的政治处境出发来阐述文学成为南朝门阀文化新标志的复杂过程。
一、 “宋武爱文”的政治内涵
《文心雕龙·时序》对刘宋一朝的文学盛况作了如下描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
刘勰以“霞蔚而飙起”盛言刘宋文才之茂,同时言及宋武帝、宋文帝、孝武帝三朝君主的文学爱好、秉文气质与文学才华。若将此段叙述理解为君主个人的文学态度对士林风气起了引导性作用,未免过于简单。对于正处于时风之中,并对文学潮流作出历史总结的刘勰来说,将君主的文学爱好与时代潮流并举的叙述模式绝非无中生有,也非流俗之言。或许提示着我们要探究南朝文学兴盛的政治社会空间,观察士风之变与政权建构之间的关系。
“宋武爱文”最突出的表现是宋武帝刘裕在彭城两次组织文学赏会。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九月至彭城,停至义熙十三年(417)正月继续北伐。《南史·谢晦传》、《宋书·王昙首传》所载“彭城大会”即发生在此期间的彭城戏马台*《南史》卷19《谢晦传》:“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于是群臣并作。”,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页。《宋书》卷63《王昙首传》:“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8页。。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为送别孔季恭,刘裕在彭城戏马台组织百僚赋诗送行*《宋书》卷54《孔季恭传》:“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第1532页。。谢灵运留下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两次“彭城大会”主题不同,一为出师北伐壮志,一为幕僚送别。所反映的是,无论是为国之大事,抑或为府主僚臣之私谊,刘裕似乎都喜欢以组织文学创作的方式介入其间。
其实,刘裕对于文学赏会是有文化隔膜的*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他出身于不以文化彰显的低级士族*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按《魏书·岛夷刘裕传》,刘裕“仅识文字”;《宋书·刘穆之传》亦言刘裕“书甚拙”。刘裕自己也曾说:“我本无术学,言义犹浅。”*《宋书》卷64《郑鲜之传》,第1696页。然而,并不能据此将刘裕的文化程度评价过低。如所周知,《魏书》撰写于北齐天保二年(551)至五年(554)之间,以北齐所绍续的北魏为正统,贬南朝君主为岛夷*[日]佐川英治:《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刘啸译,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448页。。其所言刘裕“仅识文字”恐须在此语境下理解为夸贬之笔。刘裕所自言“本无术学”的具体语境是,刘裕在与门阀士族的清谈活动中输给了郑鲜之,故“本无术学,言义犹浅”其实特指不预流东晋门阀文化。
据《宋书·武帝纪》记载,元兴三年(404)刘裕率军击败桓玄、控制建康朝政后专门整顿风俗,“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所谓“百司纵弛”的风俗,其实是门阀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的政治文化,即东晋初年熊远所言,“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晋书》卷71《熊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7页。。也即干宝《晋纪总论》所言,“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梁)萧统编:《文选》卷49《史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2页。。刘裕“本无术学”、“以身范物”施行“顿改风俗”,表明他对门阀士族政教传统并不认同的态度,这也将他推到了门阀的对立面。《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八年条记载:“(刘)裕素不学,而(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由此在晋末义熙政局中,刘裕无法获得门阀士族的多数支持。
义熙八年(412),刘裕击败最大竞争对手刘毅,独掌大权,成为门阀士族唯一可依附的权力核心。刘裕在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中,对门阀士族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做到了不咎既往。比如对刘毅的根据地荆州门阀,“除其宿釁,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宋书》卷93《隐逸·宗炳传》,第2278页。。同年,刘裕心腹刘穆之出任丹阳尹,“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四人中,谢混、郗僧施为刘毅谋主,因而于义熙八年当年被杀。“方明、廓后往造之,(刘穆之)大悦。”*《宋书》卷53《谢方明传》,第1523页。显见,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后刘裕在基本上已无来自于门阀士族的政敌*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此时,在刘裕太尉府中任职的高门士族有王弘、谢晦、袁湛、褚叔度、谢灵运、谢述、傅亮等。义熙九年(413),刘裕领镇西将军,任职军府的高门士族有王华等人。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受封宋公,担任宋国臣僚的高门士族有侨姓高门琅邪王氏(王敬弘、王惠、王球、王准之、王镇之、王智)、陈郡谢氏(谢晦、谢瞻、谢灵运、谢方明)、济阳蔡氏(蔡廓)、济阳江氏(江夷)、陈郡殷氏(殷景仁)、东海何氏(何承天)、琅邪颜氏(颜延之),南土士族会稽孔氏(孔季恭、孔琳之)*关于会稽孔氏与刘裕政权的关系,参见陈群《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这个名单几乎囊括晋宋之际的全部名士,尤其以东晋末年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主,参入济阳蔡氏、陈郡殷氏的代表人物。
刘裕阵营中的这些高门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文学名士。前引《文心雕龙·时序》所列“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便是指这些高门士族所具有的文学家族性质*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谢灵运、颜延之自不待言。王球“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宋书》卷58《王球传》,第1594页。。王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宋书》卷58《王球传》,第1624页。。谢瞻“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隋书·经籍志》记谢瞻有集三卷。谢晦“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宋书》卷44《谢晦传》,第1348页。。谢方明为著名文学家谢惠连之父。
此外,有关上述人物,按《隋书·经籍志》所记,王弘有集一卷、蔡廓有集九卷、殷景仁有集九卷、傅亮有集三十一卷、何承天有集二十卷。“宋武爱文”,其实标志着刘裕门阀政策的改变,即至少在文化上转而认同门阀文化。据《宋书·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在刘裕参与的“言论”活动中,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刘裕虽然“辞穷理屈”,但因为感受到是被当作对手,反而十分感动。刘裕尽管觉得与高门士族之间存在着不能“尽人之意”的隔膜,可依然“颇慕风流”,这是其独掌大权后的政治需要。所以,《宋书》特意强调刘裕“颇慕风流”的时间是“及为宰相”之后。
“宋武爱文”是“颇慕风流”的重要内容。据《南史·谢晦传》记载,“帝(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恐帝有失,起谏帝”。谢晦“恐帝有失”的心情正反映了刘裕“本无术学”却又必须勉强“纸笔赋诗”的不得已的处境。可以说,虽然刘裕在政治上战胜了高门士族,但在文化上却被其所征服。“宋武爱文”是被动地“爱文”。
刘裕之所以“爱文”,或许还隐含着对东晋孝武帝从政风格的模仿。据《晋书·王珣传》,“时帝(孝武帝)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东晋孝武帝在政治上以抑制门阀、伸张皇权著称,而在文化上,孝武帝又高度认同门阀士族文化。这种在政治与文化上相互矛盾、相互平衡的政策,使其统治时期成为门阀政治走向终结的转折时期*参见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载《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91页。,从而成为刘裕所属的北府兵势力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契机。这些都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初入仕途的刘裕所亲见*《宋书》卷1《武帝纪》载刘裕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为刘牢之前将军府参军。然孙无终隆安四年(400)为辅国将军、元兴二年(403)为桓玄所害时任冠军将军,见《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3页,卷10《安帝纪》第255页,卷99《桓玄传》第2592页。显然,《宋书·武帝纪》中所言孙无终“冠军”将军是指其生前最后的将军号,并非指刘裕起家时他的职衔。。或许东晋孝武帝对待门阀的两面政策为志在嬗代造宋的刘裕所继承*除政治与文化方面外,孝武帝时期也是制度变革的时代,太元旧制是南朝制度的直接源头。参见刘雅君《试论南朝的太子师傅》,《史林》2011年第6期。。
二、 “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及其政治缘起
“宋武爱文”除了反映新建立的王朝在文化政策上有因循门阀的一面以外,“爱文”之表述,还说明文学在晋宋之际成为门阀文化新的首要标志。按干宝《晋纪总论》对东晋门阀士风的描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梁)萧统编:《文选》卷49《史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2页。“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其实是两晋士风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包含在学、谈、行身、进仕、当官等诸多方面,但是干宝却没有强调文风方面。按《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指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学在文化形态上是玄学的附庸。晋宋之际文学成为门阀文化的新标识,所以才会有萧子显“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的对比性描述。“玄”与“文”的此降彼升,并不只是文风上的变化,而是门阀士族文化特质的变化,《文心雕龙·时序》将之表述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所谓“世情”、“时序”,乃指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
在晋宋之际“世情”、“时序”的转变中,谢混被看作是一个重要人物。《世说新语·文学》“简文称许掾云”条注引《续晋阳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隋书·经籍志》将《续晋阳秋》的作者署名为宋永嘉太守檀道鸾。大明六年(462),徐爰上表议刘宋国史起元时,时任尚书金部郎的檀道鸾曾建议以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起元*《宋书》卷94《恩倖·徐爰传》,第2309页。。显见,檀道鸾将义熙年间(405—418)视为宋史的一部分。“义熙中,谢混始改”,在刘宋的历史书写中除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之外,还具有王朝更替、时序兴废的意义。
随后在文学理论著作迭出的萧梁时代,谢混亦被看作是转折人物。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太元(376—396)为晋孝武帝年号,是东晋最后一个稳定时期,随后进入晋安帝的动荡时代,以至于檀道鸾建议刘宋以晋安帝元兴三年起元。《南齐书·文学传》论曰:“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萧子显“颇好辞藻”、“远思前比”、“自比古人”*(梁)萧子显:《自序》,载《梁书》卷35《萧子显传》,第512页。。其对文学史有着自己的理论视野,亦明确将谢混与“江左风味”区隔开来。
约略同时,钟嵘《诗品·序》亦言:“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梁书》卷49《文学上·钟嵘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5页。在钟嵘对东晋文学谱系的叙述中,谢混(谢益寿)属于“动俗”一系,即一反永嘉以降的江表之风。
按《隋书·经籍四》,谢混有集三卷,又撰《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可见,谢混“始改”、“大变太元之气”,是在熟悉文学史的基础上有意为之。《晋书·谢混传》云,谢混“少有美誉,善属文”,在晋孝武帝选晋陵公主婿之时,被王珣推荐,并评价为“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真长即刘惔,刘惔妹为谢安之妻,谢混为谢安之孙。刘惔“雅善言谈”,为东晋永和年间第一流清谈名士*胡秋银、刘浩:《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死后孙绰为之作诔文*《晋书》卷75《刘惔传》,第1990—1992页。。“不及真长”固然指谢混清谈水平不及刘惔,但这正是谢混与刘惔、孙绰等为代表的“江左风味”相区隔的特点。子敬是王献之,“谢安甚钦爱之”,“风流为一时之冠”*《晋书》卷80《王献之传》,第2104—2105页。。王珣所谓“不减子敬”当指“风流”而言。《南史·谢晦传》称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晋书·谢混传》:“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风华为江左第一”、“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等品题,均表明谢混在晋末士林中的领袖地位。
然而,谢混“江左第一”的“风流”领袖地位并非一开始便具有。上引《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文学传》皆将殷仲文与谢混对举。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钟嵘《诗品》卷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诗”条亦云:“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可见迟至萧梁,将殷仲文、谢混视作义熙文学的共同代表,已经成为共识。
《世说新语·文学》“殷仲文天才弘赡”条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仲文雅有藻才,著文数十篇。”《晋书·殷仲文传》称其“善属文,为世所重”,桓玄九锡之文,“仲文之辞也”。桓玄执政时期,殷仲文“总领诏命”。《晋书》本传又云,桓玄败后,北府诸将执政,“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可见,尽管梁人著述将谢混与殷仲文并举,但是在义熙之前的士誉中,谢混还无法与殷仲文比肩,并为殷仲文所轻。殷仲文为殷仲堪从弟,据上引《晋书·王珣传》,殷仲堪“以才学文章见昵于(晋孝武)帝”。殷仲文为“从兄仲堪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晋书》卷99《殷仲文传》,第2604页。。可见殷仲文是太元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其名声已为执政者所知晓。反观谢混,仅在太元末年晋陵公主选婿之时,因受王珣推荐才被孝武帝所知。义熙七年(411)谢混时任尚书仆射,但在《宋书》中仍被记述为“后进知名”*《宋书》卷60《范泰传》,第1616页。。可见义熙之前,谢混的确无法与殷仲文相比肩。殷仲文死于义熙三年(407),谢混获誉“风华为江左第一”,“第一”只有可能是在义熙三年之后。
又据《宋书·谢弘微传》,“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少所交纳”、“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都在强调谢混处于士林领袖之地位、高高在上。《宋书·刘敬宣传》亦言“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关于乌衣之游的时间,有元兴元年至义熙元年说*萧华荣:《华丽家族——西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8页。、义熙二年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义熙三年至五年说*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5页。。然而,如上文所述,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只可能开始于义熙三年之后。尤其需要分析的是,谢混在“乌衣之游”时的“少所交纳”,与“领选”时的“少所交纳”性质绝不相同。
如从史实上考证,《宋书·谢弘微传》所述谢混“少所交纳”、“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并非全然如此。谢混与琅邪王弘相善、品题泰山羊欣*《宋书》卷42《王弘传》,第1311页;卷62《羊欣传》,第1661页。,与羊孚及王恭二弟王齐、王睹清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6《雅量》“羊绥第二子孚”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谢混与时流“交纳”可明确发生在“乌衣之游”时代的记载也有不少。据《宋书·徐羡之传》,“义旗建,高祖版(徐羡之)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与谢混共事,混甚知之”。镇军将军、领军将军皆是元兴三年(404)刘裕击败桓玄后获得的首批官职*《宋书》卷1《武帝纪上》校勘记一一,第9页。,次年改元义熙。可见早在义熙初年,谢混便与“高流时誉”相“交纳”。即便是“乌衣之游”,也非“高流时誉,莫敢造门”。据《南史·谢瞻传》,“(谢瞻)尝作喜霁诗,(谢)灵运写之,(谢)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可见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弘与谢混及谢氏子弟有较密切的往来。
义熙三年(407),谢混参与政争已深,围绕着扬州刺史一职的空缺,“刘毅等不欲高祖(刘裕)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宋书》卷42《刘穆之传》,第1304页。。发生于义熙三年前后的乌衣之游,不可能脱离当日的政治。即便是“少所交纳”,其实是一种参政策略,而非真的“自负才地”。曹道衡先生认为乌衣之游是谢混“树立家族声誉、且寓抗衡王氏之意,事关两族势力消长”*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5页。。这固然为一重要发覆,然而与琅邪王氏相互竞争相比,谢混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可能是借助义熙年间政局大变之机摆脱谢氏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义熙八年,刘裕诛杀谢混,所发诏书言:“尚书左仆射谢混凭借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晋书》卷85《刘毅传》,第2210页。“超蒙殊遇”正指谢混在义熙政局中的快速崛起,《晋书》本传不载谢混在太元、隆安、元兴年间的官职,所历中书令、中领军皆在义熙初年。然而,诏书所言“凭借世资”却不完全确切。如所周知,谢氏在东晋孝武帝一朝受到压抑*王永平:《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因谢安曾牵制桓温,桓玄称帝,“尝欲以(谢)安宅为营”,后经谢混交涉才得保全谢安宅邸*《晋书》卷79《谢混传》,第2079页。。在义熙初年隐晦不明的政局中,谢混所凭借的其实是士林声誉,“世资”其实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发挥作用还有待谢混的运作。这就是为何诏书会言谢混“轻佻躁脱”,这一评价与《宋书》所述“少所交纳”截然相反。“轻佻躁脱”正表明谢混不可能仅“凭借世资”便可“职为乱阶”。
在谢混“轻佻躁脱”的举动中,乌衣之游绝非仅为“文义赏会”,其实际指向是人物品题。《宋书·谢弘微传》:“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儁,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摽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勌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宋书》所言之“韵语”实为五言诗,“韵语”的内容是品题谢氏子弟,这其实就是“状”。在九品中正制中,吏部选官以中正提供的家世、状、品为依据*唐长孺:《九品中正制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东晋后期,门阀士族一律为门地二品,中正的批评作用下降*[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书书局2008年版,第121页。。中正一般采信乡论清议*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释》,载《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陈郡为晋惠帝时置,属豫州*《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22页。。东晋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宋书》卷36《州郡志》,第1071页。。谢氏世居建康乌衣巷、又在会稽开创产业,早已脱离乡里社会。谢氏子弟获中正品所依据的乡论清议,其实就是谢氏族议。因而,谢混题目谢氏子弟,实有品状之意。
参照义熙十二年(416)袁湛以尚书左仆射领豫州大中正*《宋书》卷52《袁湛传》,第1498页。,元兴、义熙初年的豫州大中正也当由在中央任现职的高门出任。豫州属籍高门士族尤多,除陈郡谢氏外,还有陈郡殷氏、陈郡袁氏。如前文所述,陈郡殷氏在东晋孝武帝时代至桓玄执政风头正劲,乃有殷仲文轻视谢混之事。乌衣之游“文义赏会”中的人物品题实为谢氏于困境中的争鸣。谢混所品状之谢氏子弟的入仕时间均在晋安帝元兴、义熙年间,似乎也可证明这一点。谢瞻(远)元兴元年(402)起家桓伟安西参军*《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元兴元年,桓玄入辅后,以兄桓伟为安西将军。见《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1页。,谢晦(宣明)义熙初起家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宋书》卷44《谢晦传》,第1347页。,谢弘微(微子)义熙元年(405)起家员外散骑、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宋书》卷58《谢弘微传》,第1591页。琅邪王出任大司马的时间为义熙元年,见《晋书》卷10《安帝纪》,第258页。,谢灵运(康乐)亦起家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43页。。
由此可见,在义熙初年的政局中,谢混力图凭借文化优势、尤其是文学特长提升其在士论中的地位,进而为谢氏子弟出仕提供乡论声誉,这是“文义赏会”在九品中正制下的政治运作意涵。在这一政治脉络中,谢混“大变太元之气”,除了指文学本身的变化之外,同样隐含着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尤其象征着对压制谢氏之太元时代的反动。
三、 “士人并以文义为业”之形成
谢混“大变太元之气”,于文学而言,是变“盛道家之言”的“江左风味”。而在九品中正制下的人物品评竞争而言,却是提倡以文学水平作为人物品评标准。
义熙初年,除了以“文义赏会”品题谢氏子弟外,谢混还曾为东海徐羡之、泰山羊欣、庐江何尚之、顺阳范泰等人延誉。如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蒲,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宋书》卷66《何尚之传》,第1733页。。在乡论之中,“轻薄”是十分严重的评价,中正会予以黜品。如晋元帝时,“(华)恒为州大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任让失清途而参与苏峻之乱*《晋书》卷44《华恒传》,第1263页。。再如稍后,“(谢)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不为父知”,即指谢方明不认可谢惠连“轻薄”,不为之延誉,其结果便是《宋书·谢惠连传》所言的“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谢混与何尚之游处,实为改变其“轻薄”之乡论,故《宋书·何尚之传》随即叙述何尚之“起为临津令”,此即在书法上呈现谢混品题之于何尚之仕宦生涯的重要意义。按《宋书》本传,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谢混为何尚之延誉,或许正以其“雅好文义”。
事实上,在义熙初年高门士族的声誉竞争中,除了谢混品题提携人物之外,乌衣之游的谢氏子弟也以文学参与其间。《宋书·王惠传》:“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王)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此条记载,《宋书》记于王惠出仕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之前。刘裕担任太尉的时间是在义熙七年(411),谢瞻群从兄弟与琅邪王惠之间的这场酬应只会发生在此之前。谢瞻所谓“才辩有风气”,《宋书·谢弘微传》也有相似的表述:“(谢)瞻等才辞辩富”。谢混对谢瞻等兄弟群从的评价是“才义丰辩”。“才辞辩富”、“才义丰辩”的内容即《宋书·王惠传》所言之“文史间发”。从思维方式上看,谢瞻等人不追求抽象的“言清理远”,而追求具象的“极貌以写物”,这构成了“才辩”的一个面向。《晋书·列女传》言谢道韫“聪识有才辩”,即举其与谢安论“毛诗何句最佳”、“雪骤下何所似”之事,可见“才辩”与文学之关系。
按《宋书·谢瞻传》,谢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谢瞻在谈论中“文史间发”,其实是将其“辞采之美”用以清谈之中。关于晋宋之际文学的特点,《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以“极貌以写物”的文学思维入清谈,其实是通过舆论营造新的“风气”。
《晋书·殷仲文传》载:“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按《晋书·袁豹传》,袁豹“博学善文辞”。谢灵运对殷仲文的批评,固然有义熙初年谢混与殷仲文文坛领袖相争的背景,却也表现出义熙年间人物品题的一个新的标准,即“博”。谢灵运自己便曾为谢混曾评论为“博而无检”*《宋书》卷58《谢弘微传》,第1591页。。所谓“博”的知识追求,即与上引《文心雕龙》所言“近世之所竞”的“极貌以写物”、“穷力而追新”的美学追求相通*归青认为在山水文学中,赋比诗成熟更早,山水赋对山水诗的形成有影响,而赋的特点即以铺张刻摹、品物毕图为主。《从赋到诗:山水诗成因初探》,载《士族审美趣味和中古文坛风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50页。。
将这一与“文咏因革”互为表里的“博”的追求,置于清谈中,则与“言清理远”的东晋传统标准发生冲突,故而谢氏群从兄弟与王惠的这场谈论,以及谢灵运对殷仲文的评价,其实反映了谢氏在推动士论标准上的革命。谢混及谢氏子弟虽然提倡新的品题标准,但在义熙初年与其他高门士族的交往中,还是显得节制。如《宋书·谢瞻传》载:“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祕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从上文为何尚之等延誉可知谢混心中自有裁抑,谢灵运评论殷仲文也是为树立谢混士林领袖地位造势,并不忤逆谢混之意。对于谢灵运臧否人物,谢混所患者为引发对立。同样,按《宋书·王惠传》所述,谢瞻群从兄弟与王惠的谈论以“瞻等惭而退”。事实上,王惠之文名远不及谢瞻,《宋书·江夷传》传论对王惠的评价是“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谢瞻则是“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在当日士论中二者绝非等量齐观。也正因如此,《王惠传》才特意将王惠谈论胜谢瞻写入,以抬高王惠。《宋书·王惠传》中留下如此记载,其实是谢氏兄弟言论节制的结果。同样,在有限的几则史料中,谢混也都是以衬托者的角色出现。如:“(羊)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宋书》卷62《羊欣传》,第1661—1662页。羊欣在义熙年间的再次入仕,是在“义熙中”。而谢混任职中领军最晚不超过义熙二年(406),如《宋书·礼志》载义熙二年“中领军谢混”奏议云云。义熙六年谢混转任尚书左仆射。羊欣拜诣谢混之事,正在义熙初至义熙六年间。羊欣曾在桓玄辅政时“参预机要”,并出仕桓玄楚朝,在义熙年间属于政治上有历史问题者。故而其出仕需要新的士论。时任中领军的谢混其实以“拂席改服”礼敬的方式为羊欣延誉。按《宋书·羊欣传》的记载,义熙中刘裕重新启用羊欣时对郑鲜之言:“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恨不识之。”所谓“世论”,正是谢混所造。
虽然在义熙初年的人物品题中,谢混、谢瞻似乎都是以陪衬者的身份出现,但这正表明了谢混、谢瞻之“风气”已经成为当日人物品题的参照系。谢混及其子侄通过有节制的人物品题,获得了主导“世论”的领袖地位。尤其是在义熙六年(410)五月至八年(412)九月间,谢混以尚书左仆射“领选”*《晋书》卷10《安帝纪》,义熙六年五月尚书左仆射孟昶自杀,谢混接任当在此时之后。第261页。,即总领吏部选举*[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书书局2008年版,第129页。,他的品题成为官僚选任的制度性因素。《宋书·范泰传》:“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谢混)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范泰)为太常。”此事发生在义熙七年(411),正是谢混以尚书左仆射领选时期。
正因如此,谢混人物交往与品题成为舆论焦点。据《宋书·刘敬宣传》:“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着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涂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4页。刘敬宣为北府兵领袖刘牢之之子,绝非高门士族,“自负门地”的谢混与之“尽礼着欢”、为之延誉,不仅破坏他自己的“少所交纳”之例,更是破坏当日以“才地”相交之“涂限”。舆论关注谢混交纳刘敬宣,固然有体察谢混以北府兵将领抗衡刘裕的政治意图在内,但也表明身为尚书仆射的谢混已是士论中心。
《南史》所称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在“领选”时期所积累的士林声望。在义熙六年至八年谢混“领选”时期,其所看重的文学才能成为人物品题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样的时风中,倘若没有文学才华,是会遭到歧视的。《晋书·袁湛传》:“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俊,离群颇骞翥。’湛恨而不答。”据《宋书·范泰传》,“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袁湛年岁小于范泰,亦属“后生”,但因其无“文华”,故反遭范泰作诗作嘲弄。范泰诗作将袁湛“无文华”表述为“离群颇骞翥”,可知当日士风对“文华”之所趋,此即《晋书·袁湛传》所谓之“流俗”。如,与袁湛“无文华”相反,其弟袁豹“博学善文辞”,“为刘裕所知”。按《世说新语·文学》“殷仲文天才宏瞻”条注引丘渊之《文章叙》,袁豹死于义熙九年。刘裕“知”袁豹必在此前。刘裕“本无术学”,却去品题“博学善文辞”的袁豹,正是谢混以尚书仆射领选时“流俗”的表现。造就以文学论人之“流俗”的士林领袖正是谢混、范泰等人。
从袁湛之例可见,“文华”为义熙年间士人之所必须教养,而非可选项。此为义熙士风与此前两晋时代“理过其辞”(上引钟嵘语)之时流的根本区别。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4《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不长于手笔”并不影响乐广成为中朝名士,“其为识者所叹美”,夏侯玄、裴楷、王戎、卫瓘、王衍均为之延誉*《晋书》卷43《乐广传》,第1243页。。《世说新语·文学》篇“裴成公作《崇有论》”条注引《晋诸公赞》:“后乐广与(裴)頠清闲欲说理,而(裴)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虛无,笑而不复言。”乐广“自以体虛无”,对裴頠“辞喻丰博”“笑而不复言”,正是“理过其辞”之风的表现。
义熙年间,文华为“流俗所重”。不仅高门士族据以品题人物,而且次门士族也受时风熏染,扬州、荆州地区皆争相入流。《宋书·宗慤传》载:“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宗)慤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宋书》此条记于宗慤十四岁之后,又记于元嘉九年(432)随刘义恭征北将军府随镇广陵之前*《宋书》卷76《宗慤传》,第1971页;卷5《文帝纪》,第81—86页。。而据元嘉九年刘义恭应诏举才宗炳,可知元嘉六年至九年刘义恭出镇荆州时期已与南阳宗氏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宋书》卷61《刘义恭传》,第1640、1643页。。义熙八年(412)刘裕诛刘毅、自领荆州刺史,在“贯叙门次、显擢才能”的政策下,曾辟宗炳为主簿,此后又辟为太尉参军、太尉掾。晋宋易代时,宗炳被辟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被征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庶子等职。从世居荆州的南阳宗氏立场上来观察,“时天下无事”当指义熙八年后至元嘉初年晋宋境内相对安宁的政治局面,尤其是相对自晋安帝隆安元年(397)王恭、庾楷举兵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以来,至义熙八年(412)刘裕讨荆州刺史刘毅,东晋境内持续不断的举兵相抗之势而言。
“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正是义熙八年(412)后刘裕掌权、造宋时代的新士风。《宋书·谢灵运传》载,宋少帝景平年间(423—424),谢灵运移籍会稽郡,于始宁县修营别业,“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从谢灵运诗作在建康的传播速度(“宿昔之间”)、受众范围(“贵贱”、“士庶”)、舆论关注度(“名动京师”)、舆论褒贬(“莫不竞写”、“远近钦慕”)来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有着超越士庶阶层之别的社会土壤。正是有义熙年间形成重文华之“流俗”,才在宋初培育出“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社会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南阳宗氏为荆州士族。“士人并以文义为业”不仅存在于以建康为中心的士庶社会之中,还存在于荆州士族之中。南阳宗氏“诸子群从皆好学,而(宗)慤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所谓“乡曲所称”,即指九品中正赖以为据的乡论。义熙年间的“乡曲所称”,“文义”已为其中的重要指标。这使得义熙年间“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含义远远超出贵贱、士庶的“钦慕”层面,“为业”即以“文义”为“乡曲所称”,获得入仕的资格。
余嘉锡先生称:“益寿(谢混)之在南朝,率然高蹈,邈焉寡俦。革历朝之积弊,开数百年之先河,其犹唐初之陈子昂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其实除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率然高蹈,邈焉寡俦”外,谢混“开数百年之先河”还体现在引导出以文华论人的“流俗”。“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意味着谢混所造之重文华的“流俗”已从高门士族的人物品题扩展为包含士、庶在内的社会评价,并深入到九品中正制下乡论标准之中,对士人的仕宦生涯、社交声誉起着决定性影响。《梁书·任昉传》姚察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所谓“近世”正是从义熙年间开始。
正因谢混对晋宋之际士风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即便在他被刘裕诛杀后,其声望也未曾降低。宋末名士领袖袁粲品题王彧,“叹曰:‘景文非但风流可悦,乃哺歠亦复可观。’有一客少时及见谢混,答曰:‘景文方谢叔源,则为野父矣。’粲惆怅良久,曰:‘恨眼中不见此人’”。此事记于《南史·王彧传》,按照史传书法,人物品题一般以颂扬传主为主,这一记载却以传主承托谢混“风流”。可见谢混即使身死,但其对士林的影响一直到宋末都还存在。
(责任编辑:陈炜祺)
The Politics in Yixi Years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telligentsia’s Literature Worship in Liu Song Dynasty
Li Lei
Literature had become such a new symbol of the Powerful Family culture between the end of Eastern Jin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at the intelligentsia all lived on it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appearance of this phenomenon was certain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literature, but more importantly, due to its rising status in the scholars’ theory. With the destroyed politics of Powerful Family and unreturned imperial power politics before the eighth year of Yixi, Xie Hun greatly changed the Taiyuan Atmosphere on literature and won the first place in elegance and talent in the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gain,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the family capital, he rose to the top in politics and g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commending officials. The elegant and smooth literary became prevalent as well. After the eighth year of Yixi, Liu Yu held the power on his own hands. However, he had to compromise to the new Powerful Family culture in his movement of Creating Song which is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Generals keen on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changes in Yixi years, the atmosphere of focusing on the elegant and smooth literary had extended from the aristocratic characters appraisal to social evaluation containing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common people, even deep into the standard of folk comments under the ninth-class official system which played a decisive influence to the intelligentsia’s official career and social reputation.
Eastern Jin Dynasty;Liu Song Dynasty;Literature;Intelligentsia
2016-05-16
*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华认同与南北朝时代的国家建构”(项目编号:14JPC030)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K239.11
A
0257-5833(2016)11-0147-10
李 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