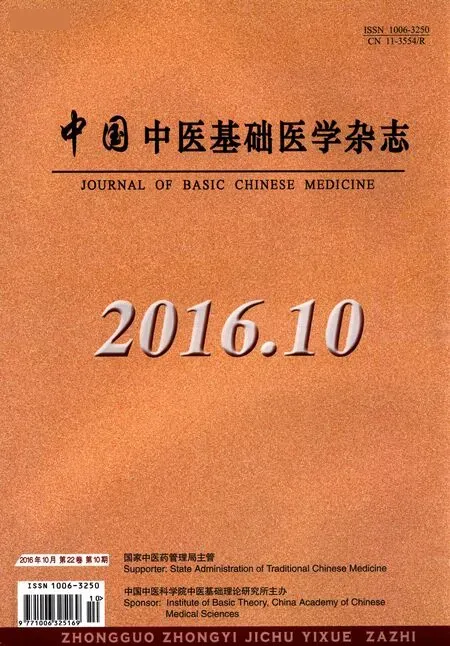国内外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研究进展*
曾 传,杨 惠,张何骄子,吴巧凤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成都 610075)
国内外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研究进展*
曾 传,杨 惠,张何骄子,吴巧凤△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成都 610075)
与穴位特异性比较,有关穴位的非特异性效应研究和报道相对较少。实际上,穴位非特异性效应可能是针灸特异性效应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故从国内外有关经穴效应特异性研究的争论热点出发,提出经穴效应非特异性研究值得思考。从临床疗效等对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总结,初步阐释了穴位非特异性的实质内涵,并分析提出经穴效应非特异性产生的基础可能包括皮肤结构系统、皮肤信号传导系统、针灸后穴位局部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以及中枢广泛效应机制等,为今后的穴位非特异性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经穴效应;经穴特异性;非特异性
现代针灸理论与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穴具有相对特异性,主要体现在经穴与非穴点比较的特异性、不同经脉经穴之间的特异性以及同一经脉不同经穴之间的特异性。但实际上经穴效应还包涵了一个重要内容,即经穴的非特异性效应,正确认识经穴效应的非特异性将是提高针灸疗效、促进针灸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1 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的存在与意义
经穴的非特异性效应是相对经穴效应的特异性而言。《素问·痹论》曰:“五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这些理论均是有关腧穴具有反映病候和治疗疾病作用的认识和总结,也是经穴效应特异性的反映。但近年来,随着国外针灸热的兴起,以及国外高水平研究团队和杂志对针灸临床疗效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对经穴效应的特异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2001年美国White A课题组首次在内关穴治疗妊娠呕吐的文章中提及了经穴效应特异性是否存在的问题[1],随后从2005年开始,德国 Witt C研究小组相继在 JAMA[2]、BMJ[3]、Lancet[4]等高水平杂志上报道了针灸治疗偏头痛、紧张性头痛、骨关节炎的RCTs研究结果,结果表明针刺刺激确实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症状,与非针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对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患者来说,针刺经穴与非经穴(或者浅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近年来,这一学术争论愈演愈烈,特别是对骨关节炎的针刺治疗,研究者更持不同意见。2004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对570位膝关节炎患者持续治疗26周的针灸治疗结果显示,针刺组在WOMAC功能和疼痛评分、患者整体评价方面优于假针刺组[5]。但随后1项1007人参与的针灸治疗骨关节炎的治疗结果却表明,针灸与假针灸没有差别[6]。2014年10月,Hinman RS在国际知名杂志JAMA发表了题为“针灸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临床随机试验”的文章,其结论是“对于50岁以上患有中度或重度膝关节慢性疼痛的患者,同假针灸治疗相比,激光针灸或针刺针灸治疗对改善疼痛或功能没有益处,因此不支持对这些病人使用针灸治疗。[7]”此外,近年来借助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脑功能成像等影像学方法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经穴效应特异性的问题,但与临床结果一样,研究结果目前尚无定论[8⁃9]。
可见,尽管有关经穴特异性的研究目前尚无定论,但绝大部分研究认为经穴非特异性效应是存在的。而我们对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研究的缺乏和不足,可能正是我们无法正确认识经穴特异性效应的特征和规律的重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根本上对经穴非特异性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2 经穴非特异性效应的表现
从临床疗效来看,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泛,提示经穴效应具有非特异性。国外文献的研究表明,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有110种[9],国内针灸疾病谱显示针灸可以治疗461种病症[10],这说明穴位具有较为广泛的临床疗效;不同选穴的研究在有效性报道上虽然有一定差异,但均提示有效,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临床疗效的非特异性。以偏头痛研究为例,在刘磊等关于针刺治疗偏头痛的文章中发现[11],针灸治疗偏头痛的临床疗法众多,除了常规针刺疗法还有多种其他针灸疗法,而且这些研究中的辨证分型标准不一:30.74%是辨证分型论治,5.33%是疼痛部位论治,分经论治占2.87%,其他占61.06%。可见,针刺治疗偏头痛的针灸疗法和辨证方法众多,相应地针刺治疗偏头痛选取穴位也更加多元化。在众多疗法和辨证方法均证实,其治疗偏头痛有效的基础上出现穴位选取多元化,这一方面说明某些单一的治疗或辨证方法的局限性,或是经穴特异性在临床应用时表现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体现了经穴非特异性效应在临床疗效上表现出的广泛性。
单穴的临床作用也具有广泛的非特异性,以关元穴和足三里穴的研究为例,在邢雪连等关于关元穴的临床数据挖掘研究中[13],从纳入的752篇临床研究文献中总结以关元穴为主穴治疗的疾病有104种。足三里适应症更多,甚至有“三里功多数不清”之说。独取足三里进行针刺或穴位封闭,艾灸等在治疗消化系统、心血管、泌尿、呼吸、运动系统及儿科、肿瘤科、妇科及多个系统作用,对改善化疗后副作用等均取得较好的疗效;有研究者在对足三里穴的古代文献研究发现,足三里单穴古代应用适应症记载达89种[14],这为足三里存在非特异性效应提供了证据。
3 经穴效应非特异性产生的可能基础
3.1 皮肤结构系统
皮肤为人体最大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器官,皮肤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为针灸作用的全身性调节途径的具体载体。皮肤含有多种细胞,这些细胞均能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完整有序的神经内分泌网络。如皮肤中的梅克尔细胞、朗格汉斯细胞、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真皮血管内皮细胞以及所有的免疫细胞(尤其是肥大细胞)均能合成神经肽,神经肽可被神经纤维及免疫细胞运输,从而发挥全身性效应。皮肤中还有很多免疫细胞如树突细胞等,这些免疫细胞可通过抗原识别、抗原呈递等过程将信息传递出去,从而募集更多的免疫细胞发挥效应。
皮肤中存在的肥大细胞是目前发现与针刺作用密切相关的细胞之一。目前对肥大细胞与经穴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肥大细胞在任何大鼠经穴区存在聚集现象,数量明显高于相应的非穴区,且多沿经线走行方向上的小血管、小神经束或神经末梢分布,针灸可以增加其数量,引起循经聚集效应,而且还能使其脱颗粒释放组胺、5⁃HT等物质。另一些研究表明,针灸能够稳定肥大细胞,抑制其聚集和脱颗粒,与针灸调节的非特异性相关,抑或是与针灸对生理或病理状态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解释[15]。与针刺作用密切相关的另一皮肤结构是广泛分布于全身皮肤的胶原纤维。研究显示,胶原纤维的破坏可明显减弱肥大细胞脱颗粒程度及针刺介导的镇痛效应,且胶原纤维很可能直接参与针刺信号的启动以及效应的放大。目前,有关肥大细胞、胶原纤维等参与针灸作用的机制被认为有力学信号传导学说、体液说和神经⁃体液学说等,这些也都是穴位产生非特异性效应的可能基础。
皮肤中还有其他一些结构,如皮肤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等,与中枢的HPA系统一样,皮肤局部的 HPA轴可以产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α促黑素细胞激素(α⁃MSH)、β⁃内啡肽以及表达主要的类固醇合成酶等,并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方式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3.2 皮肤信号传导系统
TRP(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离子通道是一个位于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大家族。TRPV1是表达于外周初级传入神经元上重要的伤害感受器,参与急性炎症痛敏的形成,并在体内分布广泛,皮肤角质形成细胞上也有广泛表达,能直接导致环氧酶⁃2(COX⁃2)的释放,表明TRPV1受体在炎症反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皮肤中另一重要的信号传导系统cAMP⁃PKA系统可能也参与了针灸非特异性的发挥。
3.3 针灸后穴位局部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
皮肤及其神经纤维中存在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蛋白、神经肽、生长抑素、P物质、血管活性肠肽、缓激肽、神经激肽、神经降压素、儿茶酚胺、内啡肽等20多种物质。当针灸刺激时,这些神经递质就会释放出来,它们具有局部的调节作用,可参与控制应激的反应,并调节许多身体活动,如消化、免疫系统、心情和情绪、性行为以及能量贮存和消耗。这些很可能也是针灸后非特异性产生的基础。此外,皮肤受刺激时会从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等产生颗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及IL⁃6、IL⁃1、TNF等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引起炎症反应,这也可能是产生穴位非特异性的机制。
3.4 中枢机制
机体接收针灸刺激时通过交感神经的反应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从垂体释放出ACTH和β⁃内啡肽,从肾上腺释放出糖皮质激素,从而引发广泛的生物学效应。除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外,蓝斑⁃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轴(sympathetic adrenal medulla axis)也会兴奋,两个轴系统中释放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躯体组织,完成全身的调节。因此,通过中枢机制发挥广泛的生物学效应是穴位产生非特异性效应的又一重要环节。近年来,脑功能成像技术为针刺的中枢整合机制提供了大量可视化证据。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针刺经穴后在特定的脑功能区有反应,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到,这些脑功能区往往非常广泛并相互重叠。如1项关于针刺太溪穴对老年轻微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表明,针刺可以引起20个脑功能区的激活[16],对1项15个健康受试者静息态针刺太冲穴后的fMRI研究表明,针刺太冲可以激活或负激活与视觉、运动、冥想、情绪以及镇痛相关的多个脑区[17]。尽管众多研究者认为针刺经穴后引起“特定”脑区的激活或参与,但实际上这些脑区与各经穴之间的联系是可变的,机体状态、疾病种类甚至个体差异均会引起这些脑功能区的变化,研究结果的广泛重叠性从某种程度上间接证明经穴在脑功能区有非特异性的存在。
4 展望
相比经穴效应的特异性研究,经穴的非特异性效应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正如2007年11月美国针灸研究协会(Society for Acupuncture Research,SAR)发表白皮书指出的那样[18],从临床研究来看,尽管已有一大批临床设计规范的研究报道认为针灸有一定疗效,但相比假针灸而言其差别并不显著,针灸特异性相关研究的结果很不一致;从基础研究来看,尽管很多研究发现有些研究指标受到针刺刺激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确证这些指标的变化与特定的疗效密切相关。因此,有关经穴特异性的研究还任重道远,而有鉴于经穴的非特异性效应是特异性效应产生的基础或前提,非常有必要明确到底哪些效应、哪些物质基础、哪些机制是经穴产生非特异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经穴的特异性效应及其生物学基础,通过这种策略有可能为经穴效应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1] Knight B,Mudge C,Openshaw S,et al.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nausea of pregnancy: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J].Obstet Gynecol,2001,97(2):184⁃188.
[2] Linde K,Streng A,Jurgens S,et al.Acupuncture for patients with migraine: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JAMA,2005,293(17):2118⁃2125.
[3] Melchart D,Streng A,Hoppe A,et al.Acupuncture in patients with tension⁃type headache: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BMJ,2005,331:376⁃382.
[4] Witt C,Brinkhaus B,Jena S,et al.Acupuncture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a randomized trial[J].Lancet,2005,366(9480):136⁃143.
[5] Berman B M,Lao L,Langenberg P,et al.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as adjunctive therapy in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J].Ann Intern Med,2004,141(12):901⁃910.
[6] Scharf H P,Mansmann U,Streitberger K,et al.Acupuncture and knee osteoarthritis:a three⁃armed randomized trial[J].Ann Intern Med,2006,145(1):12⁃20.
[7] Hinman RS,McCrory P,Pirotta M,et al.Acupuncture for Chronic Knee Pain: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JAMA,2014,312:1313⁃1322.
[8] Shan Y,Wang Z Q,Zhao Z L,et al.An FMRI study of neuronal specificity in acupuncture:the multiacupoint siguan and its sham point[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4:103491.
[9] Nierhaus T,Pach D,Huang W,Differential cerebral response to somatosensory stimulation of an acupuncture point vs[J].two non⁃acupuncture points measured with EEG and fMRI.Front Hum Neurosci,2015,9:74.
[10] 杜元灏,黄卫,熊俊,等.国外针灸病谱的初步研究[J].中国针灸,2009,29(1):53⁃55.
[11] 杜元灏,李晶,孙冬纬,等.中国现代针灸病谱研究[J].中国针灸,2007,27(5):373⁃378.
[12] 刘磊,张舒雁.针灸治疗偏头痛的文献数据分析[J].福建中医药,2012,43(3):4⁃6.
[13] 邢雪连,高晓珊,王洪彬.关元穴临床应用数据挖掘[J].河南中医,2014,34(12):2468⁃2469.
[14] 狄忠.足三里针灸适宜病症古代文献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09:62⁃63.
[15] 罗明富,何俊娜,郭莹,等.电针和悬灸对“大椎”穴区肥大细胞脱颗粒不同影响的研究[J].针刺研究,2007,32(5):327⁃329.
[16] Chen S,Xu M,Li H,et al.Acupuncture at the Taixi(KI3)acupoint activates cerebral neuron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Neural Regen Res,2014,9(11):1163⁃1168.
[17] Wu C,Qu S,Zhang J,et al.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Taichong(LR3)and Functional Brain Areas: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UsingTrue versus Sham Acupuncture[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4,doi:10.1155/2014/729091.
[18] Langevin HM,Wayne PM,Macpherson H,et al.Paradoxes in acupuncture research:strategies for moving forward[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1:180805.
Researching Status of the Non⁃specific Acupoint Effect at Home and Abroad
ZENG Chuan,YANG Hui,ZHANG He⁃jiaozi,WU Qiao⁃fe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n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engdu 610075,China)
Comparing with studies focus on specific acupoint effect,fewer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non⁃specific effect of acupoint which may play a crucial role or even the basis for the specific acupoint effect.In this review,we summarized the possible core meaning of the non⁃specific acupoint effect,includ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 function of acupoints,the features of the clinical indications which reflect non⁃specific effect of the aucpoints etc.Based on these analyzing we presented,we proposed that the non⁃specific effect of acupoint may produced by the skin structure,the skin signal transduction systems,extensive effects and other bioactive substances produced by acupuncture as well as the central prevalent mechanism in the human body after acupuncture treatment.This short review may give us new thinking about the acupoint effects.
acupoint effect;acupoint specific effect;non⁃specific effect
R224
:A
:1006⁃3250(2016)10⁃1432⁃03
2016⁃04⁃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373737,81330087);教育部霍英东基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141041);四川省科技厅课题(2015JQO058)
曾 传(1991⁃),男,四川达州人,医学本科,从事计量的临床与研究。
△
:吴巧凤,副研究员,从事针灸的作用机理研究,Tel:18215528936,E⁃mail:rwqfrwq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