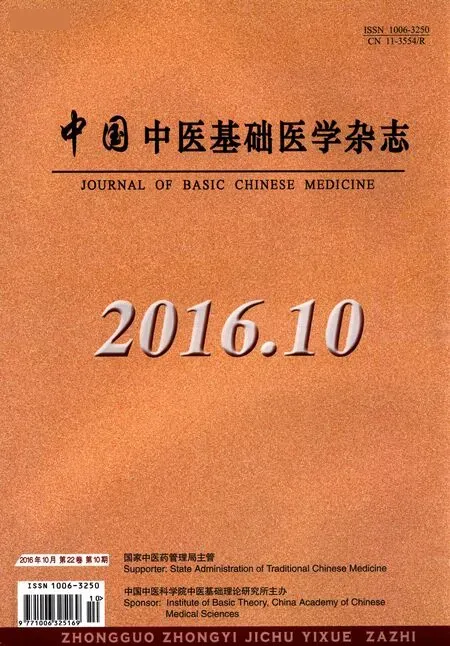壮医药理论对“痧”的认识和治疗探究
唐汉庆,黄岑汉,郑建宇,李克明,黄秀峰,窦锡彬,李晓华,赵玉峰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壮医药理论对“痧”的认识和治疗探究
唐汉庆,黄岑汉△,郑建宇,李克明,黄秀峰,窦锡彬,李晓华,赵玉峰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毒虚致病论”是壮医的病因病机理论,“三道两路”学说是壮医理论的生理病理观。“毒”“虚”致病因素是导致“痧”症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痧”症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用药经验。其中有关“痧”症的辨证分型和针刺放血疗法、刮痧疗法、药物疗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壮医药理论和应用的特色。通过总结和归纳壮医药理论对“痧”症的认识和治疗知识,有助于加深对壮医药理论和壮药应用的认识并促进交流,有利于指导临床工作并找到更多的治疗效验方法,从而丰富壮医治疗学内容。
壮医药;刮痧疗法;治疗
对“痧”的认识,历史上历经了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最初中医古籍中并无“痧”字,“痧”通“沙”也,为“沙”加病字头。清·蒋宝素《医略十三篇》表明,其本质属于一种病,致病之源为“沙”,故有成语“含沙射影”之说。在现在,一般将感受秽浊疫疠之气后出现头痛头重、咳嗽眩晕、心烦气紧、胸闷、手足肿痛、身体质量痛、脘腹痞满、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指甲瘀青等表现的一类病症归入“痧”或称之“痧”症。壮族聚居温热潮湿的山谷之地,雾霭瘴气甚多,一年四季感受秽浊之气几率大,正如清·林森在《痧症全书》中曾说:“岭南烟瘴,尤多痧病。”对于痧的防治,壮医结合地域环境和医疗实践形成了一些认识。通过总结这些认识,结合中医学对“痧”症的相关论述及相互借鉴和印证,可以为“痧”症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指导或参考。
1 壮医药理论对“痧”病因的认识
“毒虚致百病”是壮医药理论中的病因病机论,“毒”和“虚”两大因素在疾病的发生中起最主要的作用,差别只是“毒”和“虚”在不同的疾病发生中地位不同,“毒”在壮医药理论中的表述很丰富同时也是壮医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壮医认为“毒”可分为有形之毒和无形之毒,有形之毒如毒蛇虫豸、痧瘴蛊毒之类;无形之毒如暑气、伏热、秽气之类,一般将疫疠时病之毒归入痧瘴蛊毒等有形之毒[1]。“虚”指人体抗病力差,类似于中医学之正气虚弱,包括先天体质虚弱和后天失于调养两大因素。“毒”为外邪侵犯人体,如果人体体质本虚、不足以抵抗外邪之“毒”,则导致人体正气更虚,演变为“毒”“虚”并存情形更加重病情。壮医药理论认为,引起“痧”症的主要原因是人体正气虚弱,有形之痧毒侵袭人体而致。痧毒大部分可能指现代所说的致病微生物或病菌之类,具有细微、传染、侵犯人体途径广的特点,同时痧毒也容易停留在人体不同的部位,如皮肤、血肉或肠胃等形成不同的“痧”症表现。壮医根据不同“痧”症的表现进行分型,形成了壮医的“痧型”并据此进行治疗,类似于中医的辨证论治。
2 壮医对“痧”的分类和分型——“痧象”和“痧型”
“痧象”是痧毒停留在人体不同部位而出现不同的症状或体征。壮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观察到,痧毒如果停留在人体皮肤,则皮肤会出现鲜红、紫红、紫黑色斑或点状、小片状丘疹。根据颜色、斑块及丘疹的不同形状,分别冠以红痧、紫痧、铜斑痧、丘痧等,其中红痧为状如针尖大小的鲜红点,多分散发于背部皮肤,压之褪色;紫痧外观为紫红色小疹,呈斑点状,好发于胸部皮肤和四肢外侧皮肤,压之不褪色;铜斑痧状如铜钱大小的斑状斑块,颜色有鲜红、紫黑等,一般表示痧毒进入皮肤的深层;丘痧形如尖锐的小沙丘,比红痧大而小于铜斑痧,多为散发孤立的高于皮肤的丘疹,但以手抚之并无碍手之感。上述以痧毒稽留于人体皮肤,故统称之皮痧,根据留居皮肤深浅分为皮肤浅部型和皮肤深部型,如红痧、紫痧可归入浅部型,铜斑痧、丘痧则可归入皮肤深部型。
壮医药理论以“三道两路”学说为生理病理观,“三道两路”指“气道”“谷道”“水道”三道和“龙路”“火路”两路[2]。“气道”与自然界直接相通,实现人体与自然界环境气体交换的功能;“谷道”是人体消化、吸收食物并排出食物残渣的通道;“水道”是人体内汗液、尿液排泄的通道;“龙路”是人体血液循环的通路;“火路”则相当于现代医学神经系统,是负责接受刺激并对刺激作出反应的神经通路。“三道两路”学说认为,三道两路既是人体内部重要的通路,也是人体和外部环境维持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在人体内部是气血化生和运行的通路,也是人体和外部联系的通路。三道两路各司其职,使气血化生有源、运行有度,人体内外沟通有序,维持“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状态。壮医在针对“痧”症进行分型治疗时,结合痧毒侵犯“三道两路”的不同表现,分别分为气道痧型、谷道痧型、水道痧型、龙路痧型、火路痧型,各型均有其不同的“痧象”。
气道痧型:痧毒停滞于呼吸系统,表现咳嗽咽痛、恶寒发热、头痛头胀、全身重疼、胸闷气紧、倦怠乏力、周身骨节酸痛等,在胸部常可看到红痧或紫痧等痧点表现。气道痧型一般和重症流行性感冒的表现类似。
谷道痧型:痧毒停留于胃肠,表现全身酸痛、不思饮食、脘腹痞满、嗳腐吞酸或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有时在背部皮肤出现红痧表现。与慢性肠炎、胆囊炎、胆结石症等表现相似。
水道痧型:痧毒侵犯人体水道,表现为腰背部酸痛、身体质量痛,有时小腹肿坠难忍、小便短赤,以刮痧板试刮背部可见到紫黑色斑片状瘀血。相当于膀胱炎等表现。
龙路痧型:痧毒深入人体血分,以刮痧板试刮背部或胸部可出现紫红、紫黑色斑片,伴有唇甲瘀紫、胸闷气喘、形寒喜暖、浑身乏力、心悸等。相当于心血管疾病的部分表现。
火路痧型:痧毒侵犯人体火路,以发热、神志时醒时寐、时有谵语为主要表现,以刮痧板试刮背部或胸部出现铜斑痧痧象。类似于传染病如脑膜炎、乙型脑炎的部分表现。
中医学关于“痧”症的论述,以清·郭志遂《痧胀玉衡》比较全面和系统,壮医对“痧”的分类及分型和中医学相比较,显得比较简单、粗略,这与壮医注重外治、治病力求迅捷取效、避免过多理论论述的风格有关[3]。况且壮医也没有像中医学那样发展完备的辨证体系作为辨证分型的基础。
3 壮医对“痧”症的治疗
壮医学受到中医学影响,针对痧症的治疗发展了针刺放血疗法、刮痧疗法和药物疗法,但壮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色。
3.1 针刺放血疗法
《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说明针刺之法来源于南方,据有关文献报道[4],壮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针刺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正如在《素问·刺疟》所说:“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之间中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清·郭志遂在《痧胀玉衡》也记载:“迩来南方砭刺有人,略晓痧症一二……痧当砭刺,刺即救人。”此处砭刺为针刺放血疗法,认识到通过刺血疗法可以去除败血,使痧毒从败血而走,正所谓“邪有出路”。壮医采用刺血疗法治疗痧症,反映了壮医药治疗原则之一的“解毒”原则。探究刺血疗法治疗痧症的机理,由于痧毒稽留于脏腑或经络之间,通过针刺放血使痧毒随血排出体外,从而起到解毒作用。
3.2 刮痧疗法
清·林森指出治疗痧症三法,即“焠”法、“刮”法以及“刺”法,“焠”法和“刺”法相当于针刺放血疗法,而“刮”法与壮医刮痧疗法相似。刮痧疗法流行于壮族民间,刮痧工具多样,取材容易,牛角、牛骨、陶瓷片、竹板、汤勺、硬币等均可作为刮痧工具。刮痧部位以患处及患处周围为主,如头痛可刮颈部,发痧刮背部两侧或胸部,四肢酸痛可刮四肢外侧。刮痧操作先以润滑剂涂抹在皮肤上,所用的润滑剂除了植物油以外,也可以用酒或清水等。用刮痧工具从上向下刮,或沿着皮肤纹理和肌肉走向刮疗,直到皮肤出现暗红色或紫红色的斑点、斑块。在刮痧过程中,要注意用力均匀柔和,不要用力过猛,选择的刮痧工具边缘要光滑平整,以免刮伤皮肤。
刮痧疗法治疗痧症,可有效解除痧症的不适症状,缓解病情。与刮痧疗法具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相关。刮痧疗法通过机械刺激作用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提高人体抗病能力,起到类似于“补虚”作用,体现了壮医另外一条重要的治疗原则即“补虚”原则。药刮法因为有药物的直接作用,效果更好。
3.3 药物疗法
根据壮医药“三道两路”学说,针对气道痧型、谷道痧型、水道痧型、龙路痧型、火路痧型的治疗,壮医发展了药物(中药、壮药)治疗痧症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效验方。如陈晓丽等采用壮医健谷除痧验方(组成:鸡矢藤、炒麦芽、布渣叶、玉叶金花、地桃花、一点红、鱼腥草、火炭母、山芝麻、玄参、甘草)为基础治疗谷道痧症,对于改善食欲减退、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和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有较好的效果,这与壮医健谷除痧验方中鸡矢藤、炒麦芽、布渣叶调理谷道、解毒除湿、消食导滞;玉叶金花、地桃花畅通谷道、解毒止泻;火炭母、山芝麻、一点红、鱼腥草清热祛痧、通调谷道、祛毒止泻综合作用有关[5]。另外林辰等研究表明,采用壮医益气除痧验方(组成:岗梅根、龙利叶、一点红、南杏、鱼腥草、连翘、桔梗、玄参、蝉蜕、甘草)为基础治疗儿童气道痧症,能早期迅速控制气道症状,有效缩短病程且无任何不良反应[6]。对于其他如水道痧型的治疗,壮族民间采用具有清热利水、祛风止痛的壮药为主组方进行治疗,如马鞭草、白牛膝、木姜子、木满天星、鱼腥草等常用于水道痧型的治疗,能够缓解其身痛、小腹肿坠难忍、小便短赤的症状。总之,壮医在“三道两路”学说指导下,通过壮药的组合运用,对一些痧症的治疗获得较好的效果并形成了一些效验方,值得总结和应用。
壮医药理论对“痧”的认识和治疗蕴含丰富的内容,经验总结值得发掘和应用。目前,关于壮医刮痧疗法对痧症的研究,除临床报道之外已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7],为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唐汉庆,黄岑汉,黄秀峰,等.壮医药理论与中医学对“毒”论说的比较浅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4):902⁃904.
[2] 黄汉儒.壮医理论体系概述[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6):3⁃7.
[3] 班秀文.壮族医药学的防治特点[J].中国医药学报,1986,1(1):28⁃29.
[4] 钟以林,班秀文,黄瑾明.九针从南方来的实物例证—广西武鸣出土青铜针灸针初探[J].广西中医药,1987,10(3):33⁃36.
[5] 陈晓丽,蒋桂江,林辰.壮医健谷除痧验方治疗谷道痧症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疗前沿,2012,7(7):34⁃35.
[6] 林辰,杨建萍,方刚,等.壮医益气除痧验方治疗儿童流行性气道痧症临床观察[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0,16(9):1⁃3.
[7] 崔向清.刮痧疗法对大鼠和人体抗氧化及免疫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9.
Exploration of Zhuang Medicine on Treat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Sha Pattern
TANG Han⁃qing,HUANG Cen⁃han△,ZHENG Jian⁃yu,LI Ke⁃ming,HUANG Xiu⁃feng,DOU Xi⁃bin,LI Xiao⁃hua,ZHAO Yu⁃feng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Guangxi Baise 533000,China)
The theory of‘diseases due to toxin and feebleness′is one of the pathology of Zhuang medicine and the theory of‘three passages and two channels′is one of the physiology of Zhuang medicine.Toxin and feebleness are the key factors caus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a pattern.Zhuang nationality has accumulated much knowledge of treatment about Sha pattern e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medical practice.Differentiation of Sha pattern,Acupuncture⁃hemotherapy,scrapping therapy and pharmacotherapy have embodied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Zhuang medicine to some extent.It is helpful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pplication and theory of Zhuang medicine and to promote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medicines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sing such knowledge.And it is also expecte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better and find more effective therapies toward Sha pattern so that t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Zhuang medicine.
Zhuang medicine;Scrapping therapy;Treatment
R29
:A
:1006⁃3250(2016)10⁃1374⁃02
2016⁃05⁃17
唐汉庆(1976⁃),男,副教授,医学博士,从事民族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
:黄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