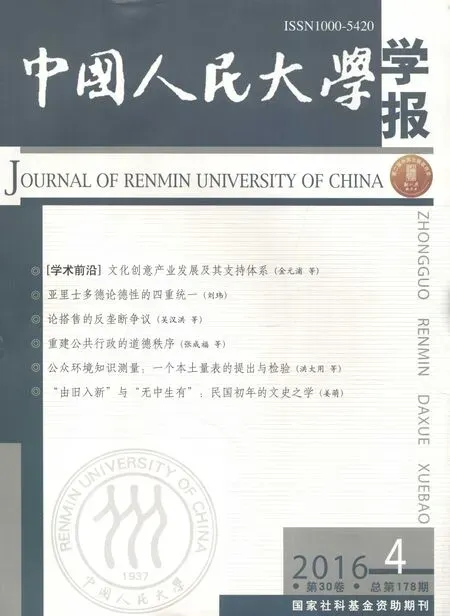“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
姜 萌
“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
姜 萌
处于激烈反帝制革命之后和艰苦反复辟斗争之中的“民国初年”,是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忽视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史之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民国初年”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萧条”和“颓废”,实际上也孕育着现代文史之学确立需要的积极因素:学术研究的观念与范式、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的蜕变;现代、独立、专业的文史学科或辅助学科,开始“无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关注的成绩;传统的各种观念逐渐趋于边缘化,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在学人群体中生成。这些“由旧入新”和“无中生有”的积极因素,为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史之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是中国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在继承这一优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尝试将目光向低潮、边缘和日常投射。只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民国初年;中国文史之学;世界维度;学术史研究;新汉学
一、被史学史忽视的“民国初年”
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可以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1](P170-171),那么20世纪的中国被称之为“历史学的世纪”也并不是毫无道理。从政治上看,自甲午惨败,历史学走向前台,成为政治运动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2](P 66-75),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有历史学的身影;从思想文化上看,不仅从清末开始的历史书写模式更替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影响深远,而且20世纪每次的思想论争或观念解放,历史学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从学术上看,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基本完成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3](P2)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十年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每一个重要的史学事件、史学机构、史家,甚至每一部重要的史著,都可以找到专门的研究论著。①王汎森教授曾说:“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家、历史著作、史学流派,或历史机构,几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于许多人感到好像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着手之处。”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但是热闹之中也有寂寥。检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已有研究可知,有一个时期的史学鲜有人问津,这就是民国初年——从民国政府成立到新文化运动这个阶段。*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第一个关注的重要时期是清末“新史学运动”时期,此处不需赘言。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汪荣祖曾说:“民国史学之成立,须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22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张越将1915—1927年视为“五四时期”,并认为此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参见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13-1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以此可知,民国成立后至新文化运动之间这段时间,常被忽略。
此一时期被研究者忽略,大概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此一时期激荡的政治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这段时间,国体之争、政党之争、派系之争、文化之争这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应接不暇。就时人而言,精力、心智皆大多消耗在政治上,譬如具有强烈经邦济世之心的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皆投身政治洪流之中;就后人而言,对此一时期的关注、研究也主要聚焦在政治事件、思想纷争上。第二,此一时期的确未有显著的学术成果,连民初的知识阶层自己都不满意。彼时既处清末激烈反满、反帝制革命激荡之后,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陷入艰苦的反复辟斗争之中,身心疲乏与精神煎熬是彼时学人的普遍状况,学术界的涣散与冷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可以找到一些当时的直观记载,如:任鸿隽在1914年悲痛地说,在美、英、德、法、日这些国家都可以找到“学界”,而“环顾吾国,则吾大索十日而未尝见也”[4](P44);1917年7月初,回到上海的胡适,面对中国学术界的毫无生气、成果寥寥,有“放声大哭”的哀痛。[5](P471)第三,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习惯有关。关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显著现象、著名学者与成果,或者追逐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包括因时事而引发的热点),或者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新颖、创新之处,是当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这一作业方式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之时,学术研究者常常会忽略学术的低潮、边缘和日常。第四,意识形态导致的眼光遮蔽。无论是国民政府时期,还是1949年之后,长期都将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并产生了反动黑暗的政治必然压迫禁锢学术文化发展的僵化认识,而未能很好地开展实证性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高峰、热点与新颖之处研究的普遍开展,以及学术史研究对意识形态因素的突破,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射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低潮、边缘和日常,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关于“民国初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史方面的成果。例如,通过对民初所谓“旧派”小说家理念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小说在近现代的演变,发掘了一些被遮蔽的现象;[6]在民国初年新知识阶层普遍“精神煎熬”的背景下探讨鲁迅的精神与生活状态,引起了我们对民国初年学人的日常到底是何种情形的关注;[7]此外还有对民国初年文学走向娱乐化的分析等。[8]这些研究对这个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开展,皆颇具推动和借鉴意义。
相比于文学史研究,民国初年的史学史研究寂寥得多。罗志田、桑兵等研究者虽然曾经将清季民初作为重要的研究时段,其中一些研究对了解民国初年的史学颇具启发,但基本上对民国初年多含混而过。*比如罗志田在《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等论著中,对“清季民初”史学裂变中“历史眼光”、学术认识论等方面的变化之探讨,对于了解民初的史学有一定价值;桑兵在《民国学界的老辈》等论著中对被遮蔽的民国学术现象之发掘,使人意识到民国学术还存在其他面向。据笔者所见,目前专门研究民国初年的史学史成果似乎只有陈其泰《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局》一文*其实,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一书是较早梳理、研究“民国初年”的重要成果,对此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梳理得颇为清晰,亦给予较高肯定,但其明确将时间界定为1915—1927年间,与本文的时段划分取向不同。。作者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对“民国初年”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未予以足够重视,并认为民国初年实际已有一个“史学领域的新格局”[9](P75)。遗憾的是,其分析路径主要是通过1917年前后的著名学术成果来倒推出民国初年史学存在着发展的情况,而未在清理民初文史之学发展具体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情况进行理论概括。此外,将民国初年的史学发展估量为“新格局”,似也存在拔高的嫌疑。
“民国初年”在史学史上究竟有没有地位?怎样相对准确地估量它的地位?一般而言,学术发展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由旧入新”,一个是“无中生有”。反过来说,这两个路径也是判断一个时期学术史地位的着眼点。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正是要通过实证性研究,尽可能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对民国初年学术发展的“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进行梳理,并以此研究为基础,对当前大陆学界的学术史、史学史研究有所反思,以促进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认知。
二、“由旧入新”:中国文史之学传统与现代的铆接
顾颉刚在1919年1月指出:
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第一,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无论如何见得突兀,既然你思想里能够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着。这伏着的东西,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10](P302)
在顾氏看来,由甲午惨败开启的中国学术现代化运动,从性质上而言是“由旧入新”,而不是“易旧为新”。这种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显现为一种共识性认识。*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多篇学术评论文章都流露出类似观点。参见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1922,19(3);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载《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10-10;甘蛰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载《东方杂志》,1924,21(纪念号)。
顾颉刚等亲历者的感受,主要是对“清末民初”学术发展整体情况发言,具体到“民国初年”,情况怎样呢?笔者以为,中国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蜕变在民国初年开始从多个层面显现:在学术研究层面,王国维、陈垣等人率先在继承乾嘉汉学遗产的基础上,更新了方法,扩大了视野,开拓了领域,为中国文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打开了新路;在学人层面,时势的变易和代际的转换使原本占据学界中心地位的传统学人,如沈曾植、缪荃孙等逐渐边缘化,而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和影响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垣、胡适等不仅在民国初年登上学坛,且迅速走向中心;在学术研究客观条件方面,蔡元培等有现代思想的学人执掌了北大等机构,对曾经充满腐败堕落气息的大学进行改造,为延揽现代学人、创设现代学术机构提供了可凭借的基础。
民国初年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第一个重要面向是学术研究范式的“由旧入新”。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时期就试图融汇西方现代学科知识对传统文史之学进行现代转化,但他们深受传统学术浸润而西学素养不足,多采取以中学附会西学的路径改造中国传统学术,不仅未能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现代化,反而加剧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存亡危机。[11](P95-99)*另可参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文,及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研究。就梁、章等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而言,他们所长在评判传统学术,至于带领中国文史研究实现“由旧入新”关键转换实非所能。具备此种能力之学人,不仅要熟知传统学术,亦要有相当的西方现代学术素养。直到民国初年,才出现了王国维等几位满足此条件的学者。*张广达先生对王国维为何能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及其贡献与不足有专门研究,如《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等论著,颇有价值。王国维早年接受了西方物理学、哲学、教育学的训练和熏陶[12](P3),1911年开始潜心经史研究,在学术观念上冲破“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束缚[13](P129),和日本、法国汉学界建立了联系,对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并尝试“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14](P344-345)。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的价值,尝试运用地下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互证来进行经史研究*乔治忠先生指出王国维在1913年已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参见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更准确地说,王国维1913年提出的是“二重证明法”,参见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载《历史研究》,2012(4)。,先后撰写了《明堂庙寝通考》、《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中国文史研究的“由旧入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汪荣祖说:“王氏之学已由旧入新,其治学之兴趣虽遍及经学、金石、小学与文学,但渐归宿于古史;治经与识字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22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从学术发展谱系来说,王国维将出土文献与传统典籍互证的“二重证明法”,是在乾嘉汉学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新观念与方法,使中国传统典籍、传统学术与现代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铆合,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汉学向新汉学的转变*1914年,王国维就特别表彰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这种“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的治学路径,参见王国维:《东山杂记》,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380-38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王国维自认其研究是在传统学术基础上的“新研究”,参见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1922,19(3)。关于《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的问题学界有争议,笔者采用系王国维的观点。参见侯书勇:《〈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载《齐鲁学刊》,2012(3)。,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研究路径的形成,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界后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广达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许多考证绵密、精心结撰的论文旨在遍检证据以达致综合判断,实际上起了转换范式的作用”,参见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3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傅斯年认为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并将王国维视为治学榜样,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311页,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王国维对傅斯年学术研究之影响,王汎森的《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一文有较细密的分析。顾颉刚直到1922年4月24日还因敬佩王国维“以新法驭古学”而希望拜王氏为师,参见顾颉刚:《致王国维·一》,载《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1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如果说作为新汉学开山的王国维*郭沫若认为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参见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历史人物》,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实际上,无论是从王国维继承程瑶田、钱大昕等人汉学路径的意愿而言,还是从郭沫若表彰王国维学术贡献的着眼点来看,称其为新汉学的开山可能更符合王氏的意愿,亦更符合事实。是在观念、方法、视野和辅助学科等方面为中国文史研究“由旧入新”做出重要贡献的话,那么陈垣的贡献主要是为新汉学在宗教史领域实现了大的突破。与王国维相似,陈垣早年对西方现代学术有所接触,并“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这为他能够促进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转化打下基础。[15](P61)从1915年开始,陈垣就倾注心力对《四库全书》进行认真研究[16](P65-66),并于1917年撰写出版了《元也里可温考》,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马相伯、英敛之于此文的“叙”与“跋”中都高度评价这一研究的贡献。陈垣同年在日本宣读此文,引起了日本学界注意。陈垣在日本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拙著《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参见陈垣:《致慕元甫》〔1917年12月8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另可参见牛润珍:《陈垣与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载《史学史研究》,2000(4)。此后又在数年间撰写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名论文,不仅使现代宗教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也使其成为一个可与欧美日本汉学界切磋、竞胜的领域。
“由旧入新”的第二个重要面向是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新一代学人在1920年前后陆续登上中国学术舞台,并迅速进入中心。民国初期十年间学人“由旧入新”的方式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清末在日本接受现代学术熏陶的学人逐渐抢占了传统学人的职位,最主要的表现是章门弟子在北大替代了桐城派学人[17];其次是民初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学人进入学术机构,如王桐龄(1912年)、陆懋德(1914年)、胡适(1917年)、何炳松(1917年)、陈衡哲(1920年)、凌达扬(1920年)等;最后是在国内大学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青年学子进入学林,如顾颉刚、毛子水、傅斯年等。学人“由旧入新”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1917年7月初,在回国途径横滨时,胡适读到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有“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18](P40)等观点。胡适认为此文“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19](P614)。带着蓬勃雄心和明确的启示,又受到糟糕现实的刺激,胡适乃以“平等的眼光”、“怀疑的精神”、“批判的态度”等犀利工具冲破了“中体西用”思想格局的束缚,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论著为媒介,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建立了让新旧学人都可以接受、借鉴、操作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新汉学,年纪轻轻就一跃成为学界的中心人物之一。[20](P157-232)如果说王国维、陈垣更多的依托中国传统学术资源来推动中国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话,那么胡适应被视为是依托西方现代学术的观念与方法,为中国经学与子学研究开创了新方向,并唤起了学界探寻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自觉。[21]
第三个层面的“由旧入新”主要是学术机构的改造。1920年前后,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在中国各大学逐渐成为重要力量后,开始着手整顿改造这些机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注入一股动力。在这个浪潮中,以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最早也最有影响。*除北京大学外,还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清华学堂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南高的情形可参见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清华学堂的情形可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北大虽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创建后并没有形成学术研究的风气,学生意在混文凭谋做官,老师教学也不用心认真。[22](P350)蔡元培在1917年1月正式就任校长后,决心革除这种腐败沉闷,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指导观念选聘教师,改良讲义,添购书籍,联络各界,鼓励学术研究[23](P2-5),并争取经费,每年派出几十名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以培养可“与欧美抗衡”的学术人才。[24]
学术机构的“由旧入新”可以说是学术观念与学人“由旧入新”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速了学术观念与学人的“由旧入新”,甚至“无中生有”:正是有了蔡元培对北大的现代化改造,胡适、李大钊等一批学者才可能逐渐聚集到北大,成立了史学门、国学门等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顾颉刚、傅斯年、毛子水等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生才会受到鼓舞,创立了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的“新潮社”。[25](P1-4)
三、“无中生有”:在“世界维度”中探索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
所谓“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一词受到了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一文的影响。参见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相较于史语所,地质调查所、北大史学门、国学门等机构创建更早,创建时期环境也更恶劣,既缺资金又少经验,似乎更宜谓之“无中生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现:第一层面主要体现在客观层面,即在新学术观念影响下,新学术志向推动下,学术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现代、专业、独立的文史研究机构或辅助学科的研究机构;第二层面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即学术界、思想界完全摆脱了“天下中心观”的束缚,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意识明确地推动现代文史研究或相关辅助学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互为表里,促进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与专业化的艰难起步。
现代而专业的文史研究机构或辅助学科的研究机构之创立,是民国初年学术史最应该关注的现象之一。要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之生成说起。*参见左玉河:《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载《史学月刊》,2001(4);《现代学科体系关照下之经学定位》,载《江海学刊》,2007(3);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载《学术月刊》,2007(7)。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四部之学”,其实都属于现代观念中的“人文学科”,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之生产,要晚于自然学科的学科意识。中国知识阶层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意识,是在清末民初。从“四部之学”走向现代的文史哲学科有两个关键的转换:一是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等官方文件初步承认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但是将“经学”独立成一科,仍然可以看到传统观念意识的强烈影响,而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批评意见则显示了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亦不小。;二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将经学科合并到文学科,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确立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之学”,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大学规程》又明确规定“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并有“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的“大学院”之设想。[26](P708、722)
毋庸置疑,民国初年基本确立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为现代、专业、独立的文史研究机构“无中生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学术研究机构最先并不是出现在哲学、文学、史学三门,而是出现在地理学门。*1913年的《大学规程》规定地理学门包括“地理研究法”、“中国地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地理学”、“海洋学”、“博物学”、“殖民学及殖民史”、“人类及人种学”、“统计学”、“测地绘图学”、“地文学概论”、“地质学”、“史学概论”等科目。1912年章鸿钊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提议于实业部设立地质调查所。这一提议虽未实现,但是实业部却于“矿务下设地质科”,并由章鸿钊任科长。民国政府迁北京后,地质科得以保留,并于1913年“改设地质研究所,先由丁文江先生主持”,但此一时期机构隶属变更频繁,人才匮乏,运转不畅,成果稀少。[27]直到1916年11月,在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有了专任所员、独立预算、特别所址及正式工作者。虽然地质调查所聘请了步达生等外国专家,但它的确一直是一个由中国人领导、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独立科研机构,并且推动了现代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28](P438-439)。
在文史领域,虽然1908年至1910年讨论举办分科大学时就有中国文学门、中国史学门等考虑*参见《分科大学牌示》,载《教育杂志》,1909,1(2);《分科大学先办经文两科》,载《大同报》,1909,11(16)等。,但最终只先开设了中国文学门一科。[29]文学门成立后开办效果不佳,“主课教授大半依文顺释,既非提纲挈领,亦非大义微言”,严复在民国初年主掌北大后,乃决定将经科与文科合并,并“拟分哲学、文学、历史、舆地各门”,希望能“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30](P30)但是,三尺之冰,岂能一日融化?直到1914年6月之后,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章太炎弟子陆续到北大任教,文史研究的现代化才逐渐走向正轨[31](P48-49),并在三年后“无中生有”方面取得了突破——成立北大史学门。1917年6月北京大学史学门成立后,尽管存在“不受重视”、学生不愿就学等问题,毕竟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走出了第一步。[32](P372)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史学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独立科系,对此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史学的独立意识愈发主动,促使其更快地从传统经史之学或宽泛的文科脱离出来,二是为专业史学研究者的积聚与后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体制的依托与保障。*关于北大史学门的情况,可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随着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速度加快,学界对现代学术研究的渴望不断加强,建立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呼声越来越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自觉”。[33](P69-79)在这种情势下,原本就有意“与欧美抗衡”的蔡元培在1921年11月28日提出建立“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北京大学研究所的设想。[34](P134)这一提议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和支持,国学门在1922年初率先成立,使中国文史研究具备了一个集开展学术研究、专门人才培养、材料信息收集、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为一体的现代机构,令中国学者联合起来开展高深的专业研究成为可能,为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界竞胜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平台。
“无中生有”的另一个表现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那就是中国学人已经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甲午惨败之后,中国人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试图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但彼时的中国学人充其量是将西方、日本学术当做一个学习、模仿的对象,而不是要与之竞胜的“他者”。换言之,清末的学人虽然已经放眼世界,但还未构建一个置身其中的“世界维度”。民国肇建之后,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从世界范畴观察中国学术的眼光,并且在这种“世界维度”的审视下,开始酝酿学者独有的国族情怀——用学术研究融入世界、用学术研究为国争光。1913年,再度到欧洲游学的蔡元培注意到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差距,指出中国学术界要“急取而直追”[35](P338)。在此观念引导下,“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学人已经清晰地表达出要从“世界维度”寻找与重塑“自我”的意愿。新潮社的青年们向全体国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36](P1-2)
不独新潮社的青年们从此“世界维度”出发,慨然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为重大责任,就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中青年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马叙伦1920年就因顾虑“吾国固有之学术”的“混沌絮乱”会引起欧美学者的误解与轻视,提倡“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补助”[37]的研究。*《 北京大学日刊》未标作者,但《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1年)所载《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标“马叙伦拟”。对勘可知二者系同一文。胡适在1920年因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备感惭愧而要为章实斋重新编写年谱[38](P1),两年后和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话时指出,“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中国学人要“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39](P772)。沈兼士也指出发展国学门是要“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国学季刊》未标作者,对勘《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一书收录的《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可知,两文实系一文。[40](P561),而陈垣更是产生了“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41]这样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想法。简而言之,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史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力的意识——与西方汉学竞胜,正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世界维度”之具体表现。
四、余论
从宏观角度来比较中国传统学术与中国现代文史学术发展的轨迹,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前者犹如黄河,主色调基本不变,上半段激流奔腾,但中后段渐趋平稳;而起源于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史学术,则如一段波浪线,随着时势这个轴上下波动,曲折前行。甲午惨败之后,朝野内外对现代学术文化的肯定与支持使其迅速走向中心,高速发展,但当清末政治活动趋于活跃之后,学人或为利禄饵诱远离学术[42](P98),或直接投身政治运动以改造中国*梁启超最有代表性,他在1906年和革命派论战后,便很少撰写学术作品(这一时期仅有1908年的《王荆公》和1909年的《管子传》可算学术性论著),进入民国后由于希望借助袁世凯实践开明专制,更是直接投身政治,直到1917年后才逐渐回归学术。章太炎1909年因《民报》被禁等事导致政治活动受阻而讲学,在1910年撰成《新方言》、《国故论衡》后,旋因辛亥革命爆发再次投身政治活动,后又醉心联省自治。读《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感知章太炎此一阶段政治兴趣之浓烈。除梁、章外,严复等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萌生阶段的重要学人大多皆被现实政治消耗了很多精力。,中国文史学术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便走向低落。这次低潮持续了七八年,直到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后,才明显地呈现出元气恢复的新气象:学术研究的人才与取向等方面“由旧入新”的速度加快,现代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也“无中生有”的出现,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中观察自己、定位自己、塑造自己、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进入20世纪20年代,文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文儒老病消愁送日之具”[43](P270),而是肩负着国家富强与荣光使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通过对民国成立后数年间中国文史学术发展情况的以上分析,我们才可以在学术发展脉络上理解“新汉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异军突起,才能让我们明白,学术发展的低潮在学术史上也有价值。以往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惯常路径是关注高峰、追逐热点、推崇新颖,而对于低潮、边缘与日常关注的不多,甚至是漠视。但是这种惯常的作业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对高峰与热点的研究成筐累箧,使很多人有题无剩意之叹,而学术发展的低潮、边缘与日常却少人问津;另一方面是对低潮、边缘与日常的忽视,使人不能对高峰与热点给出深刻透彻之解释,对学术史的认识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人与事。实际上,就以本文研究的时段而言,仍有颇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民国初年学术文化界人士在革命之后的心灵疲乏,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到底怎样*周明之曾指出,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退缩和对所谓文化运动的迷恋”。参见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2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对这一论断,目前还缺少检验性的实证性研究。?比如此一时期政治文化体制/机制革命与知识变革是怎样互动的*王汎森认为,只有支撑传统价值体系的君主制、儒家礼仪、经典教育、科举制和法律制度全部崩溃之后,“知识界的革命才真正开始”,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这个论断颇具有展开研究之价值。?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功力与识见要求更高:更多学科的知识、更多的资料、更广阔的视野、更细密的思考。一言以蔽之,眼光投向低潮、边缘和日常,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方法或理论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或许是此后学术史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也唯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1]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 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 任鸿隽:《建立学界论》,载《留美学生季报》,1914,1(2)。
[5] 胡适:《归国杂感》,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黄霖:《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载《文学评论》,2010(5)。
[7] 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3)。
[8] 郝庆军:《从文学期刊的繁荣看民国初年文学的娱乐化倾向》,载《东岳论丛》,2012(10)。
[9] 陈其泰:《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局》,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8)。
[10] 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1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3]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4]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5] 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载《晋阳学刊》,1980(2)。
[16] 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17] 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载《近代史研究》,2009(2)。
[18] 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载《新青年》,1917,3(3)。
[19] 胡适:《归国记》,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0]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1] 姜萌:《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载《文史哲》,2012(4)。
[22]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4] 蔡元培:《本校派生留学近闻》,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05-01。
[25][36]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1919,1(1)。
[26]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7] 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地质调查所创办三十年史要第一章》,载《地质评论》,1947,12(1/2)。
[28]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9] 《学部奏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载《预备立宪公会报》,1910,2(24)。
[30] 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贴》,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1]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32] 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载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34] 蔡元培:《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35] 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37] 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10-20。
[38]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
[3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0] 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计划书》,载《国学季刊》,1923,1(3)。
[41] 姜萌:《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载《东岳论丛》,2014(3)。
[43]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 张 静)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udy in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China
JIANG Meng
(School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China has been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This is a difficult period for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udy,which was not only a desolate scene on all sides,but has also undergone some changes.There were,actually,a few positive factors regar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udy.Some change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took place during this period,such as the concept and paradigm of academic,the academic environment,scholars,independent and modern institutions.By making comparison with the sinology of western and Japanese,Chinese scholars form their dimension of the World.The positive factors of their studies lay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udy.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China;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udy;dimension of the World;academic history studies;neo-sinology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项目(13XNJ021)
姜萌: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