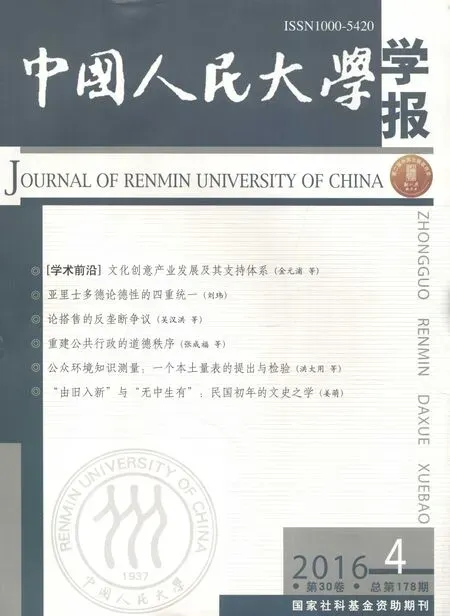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
李凤亮 宗祖盼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
李凤亮 宗祖盼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厘清二者融合的演进机理有助于把握科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文化与科技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原始蒙昧时代,原始文化与简单技术呈现出混沌般的交融共生形态,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而在漫长的古代文明时期,文化与科技则相对分离,并沿着自身的系统独立发展;进入近代社会后,文化与科技相互隔离的状态被打破,并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积极融合与消极冲突并存的局面;在信息时代,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发展正在引领文化与科技融合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文化与科技开始以主动姿态向对方渗透,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历史语境
文化与科技作为评价人类社会进步的经纬坐标,其发生和发展遵循着一定的演进逻辑,并在历史长河的激烈碰撞中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注脚。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迎来了新一轮更迭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深刻变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了文化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崭新动力。钱中文先生在谈及“评价新事物”时曾强调:“评判者要有充分的历史感,深入地研究新的对象和它们出现的历史语境,对于这种语境,不能因为自己未曾亲身参与而对它视而不见,不能因为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你不在场而否定这些历史现象。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出问题的线索,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1]就当下而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已呈现出常态化发展趋势,厘清二者融合的演进机理,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从而为当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出现的新现象、新业态、新模式寻求科学与理论的依据。
一、原始文化与简单技术交融共生阶段
要追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原点,当从文化与科技的起源中去寻找。但为了论证的合理性,文化与科技的概念需先在此予以澄清,才能做进一步探讨,这是由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比如,“文化”有广狭之分,有古今之分,有中西之分,历来都是丰富、复杂、多元的集合体。无论是英文世界“culture”一词的演化,还是汉语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追溯,“文化”都是最难解的词之一。因此,当我们将“文化”置于“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一当代言说语境时,其内涵与外延都应相对缩小。据此观照“科技”的概念亦是如此,因为即便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科技也可视为“文化”范畴的“交集”。[2]“科技”既有“功利—实证性”的一面,又有“精神—文化性”的一面;既是手段与工具,又具有思想和价值。综此,这里的“文化”应作狭义上精神层面的理解,意指与“科技”相对应的超越工具理性的人文价值与意义创造。“科技”则主要是指与精神文化相对应的“自然科学技术”概念,是相对狭义上物质层面的解释,既包括人类认识自然过程中不断揭示自然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科学知识,也包括改造自然过程中满足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手段。
“从世界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并非一次崭新的历史性出场,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脉络和发展轨迹。”[3]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言,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进化相似,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文化与科技作为人类社会最核心的要素,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其中,原始艺术作为原始人类精神层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作为探寻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开端。由于原始蒙昧时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科技的起源也只能从简单初级的技术中去考察。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第一,文化、科技与人类相伴而生,是在简单劳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积累、演化、发展而来的,具有“人”的属性,即文化与科技起源的地方,就在人类起源的地方。第二,文化与科技经历着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历程,二者相互交织,互为影响,互为促进。因此,当人类从猿分化出来之后建立第一个共同体时,文化与科技的交融就已经出现了。
原始民族具有原始的生产方式,其中渔猎和采集植物等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较高等的民族,都曾有过一个时期采用这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好些大大小小的社会集群,至今还未超脱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4](P31-32)这不仅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其适应生存的本能,如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头工具,亦可看做一种萌芽状态的“前技术”。随着人类能够从事更多的非生存性活动,思想或情感的积累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创造了前提,逐渐出现了原始绘画、原始装饰、原始舞蹈、原始诗歌、原始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并通过原始劳动技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格罗塞认为,原始艺术的产生与当时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是狩猎生活存在内在联系。比如,对于西班牙阿尔泰米拉山洞的岩画,最近情理的解释仍然是,“那些原始狩猎者认为,只要他们画个猎物图,大概再用他们的长矛或石斧痛打一番,真正的野兽就俯首就擒了”[5](P18)。用鲁迅的话解释,画这只牛“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6](P91),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简单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经验的积累和总结,逐步形成了最原始的技术。这种基于工具的有意识的“再创造”,如新石器时代学会磨制石斧、石镰、石犁、石铲等工具以及烧制陶器等,为人类向文明时代迈进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原始狩猎者过着一种漂流不定的生活,他们的生产技术也只是无足轻重的片面发展。唯独武器一项,因为须应付他们生活的最大需要已达到当时最高级的完美阶段。例如爱斯基摩人的铁叉、澳洲人的木棍、布须曼人的毒箭,等等。[7](P35)
原始劳动的产生,或为谋求生存,或为模仿自然,或为情感交流,抑或为游戏宣泄。但无论如何,原始民族从劳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简单技术的过程,本身可以看做是一种精神活动。由于原始精神活动与简单技术在主体、结构、起源、性质等方面具有同源同体、同质同构的关系,它们几乎同时发生,并依附于同一载体。比如在磨制石器或制作弓箭时,原始民族意识到对称既能保持很好的握持感,也有利于发挥工具的最佳效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对称”的审美意识,而装饰也不过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8](P3),变成一种“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9](P11)。也就是说,美感源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审美或艺术在当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种种原始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之中。再如制作陶器时,人们偶然发现用不同的泥土或使用不同的程序烧制,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使他们萌生了将“图腾”和“符号”绘入彩陶的想法。显然,这也并不是为了欣赏或审美而专门制作的。由此可见,“手的解放及以手为主要器官的实践活动是技术和文化产生的共同基础。在石器时代的漫长时期里,人类简单的实践与精神活动直接联系,即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活动”[10]。它们既是技术的,同时又属于文化的范畴。
“浑沌性”是原始文化与技术融合的显著特征,犹如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前的“天地浑沌”状态一样,由于原始文化与技术同根同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独立的发展形态。尽管原始精神活动出现的时间甚至早于较为成熟的技术,但很难解释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比如文身、黥面、涂彩等是为了刺激异性或者吓唬敌人,舞蹈则是为了祭祀或娱乐鬼神。一方面,它们当中大部分仍然包含着技术的成分,画家或雕刻家不过是一些高明的“狩猎者”或手艺人;另一方面,就算是一些基于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和感性理解,有时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劳动中表现出来。如《周官·司巫》中记载“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等等,讲的就是原始歌舞与劳动生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之,原始文化与简单技术是完全糅合在未分化的渔猎生活和巫术礼仪的混沌统一体中的,具体表现为“工具”这一实用载体的使用以及围绕“工具”的精神活动,既具有功用性,又凝结着原始民族的审美、情感、思想和信仰。
二、古代文化与科技相对独立发展阶段
普列汉诺夫在论及原始民族的艺术时坚信,“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看待它的”[11](P93)。其中的分水岭亦可看做文化与科技逐渐分离的坐标原点。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化和“前技术”的积累之后,首先是文化开始从劳动实践中脱离,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比如原始时期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艺术景观呈现逐渐裂变为单独艺术生命体的过程,即可看做精神文化独立发展的例证之一。古希腊时期的“七艺”(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与先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划分,也恰当地说明了音乐、书法与骑射、礼节、天文、几何、数学的区别。换言之,“无功利”的情绪表达为原始思维的解放创造了前提,只有当精神脱离了生产活动,文化艺术才有可能逐渐形成众多艺术门类。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标志着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的进一步加工,出现了区别于原始社会的科学技术萌芽。尤其是原始部落在各大流域的聚集生活,使得原始技术不再仅用于渔猎,而是逐渐发展成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耕技艺。同时,手工技艺也开始脱离了农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建筑等多个技术门类,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并且,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逐渐加深,还出现了早期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药、地理等科学萌芽。
如果用“源”与“流”的关系作为比照,这一时期的文化与科技正是从同一“源泉”出发,走向了不同“川流”的过程。它们既不脱离生活内容和实践过程而自行存在,又世代相继、绵延不息。相比原始时期的“混沌”状态,古代文化与科技的分离为彼此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科技对文化的影响远不如原始时代。一方面,文化脱离了劳动实践之后,开始沿着自身的系统有序地发展。比如诗歌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之后,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新诗等多种形式的演变,其与科技又有多少联系呢?另一方面,虽然青铜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简单的科学萌芽,但与现代科学与技术互为促进的状态相比,这一时期的科学与技术没有产生紧密的联系,几乎是分离式发展,技术的应用难以对文化内核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古代时期的文化与科技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以使双方紧密融合,而是沿着自身的系统和逻辑有序地发展,相互影响并不明显。相反,政治、宗教、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往往间接影响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例如,在古希腊时期,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但进入中世纪之后却“背道而驰”。在中国古代盛世与乱世的更迭中,也不乏这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古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繁盛之间并非是毫无关联的。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促使知识媒介的改变,保证了绘画、书法和诗词的普及和繁荣。在《考工记》、《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中,也记载了许多专门用于工艺美术的技术,如金银错、鎏金、失蜡法、錾刻、累丝、镂雕等古代工艺就广泛应用于青铜铸造、细工装饰、玉器加工、绘画美术等。显然,古代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是丰富的,整体水平亦高于原始蒙昧时代。只是相对于当下而言,这种交融仍然呈现出“零星状”、“偶然性”与“间接性”,其影响的人群也不广泛。
文化与科技相对独立发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起点,但我们大致可以从古代文明的开端去探寻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首先,手的进一步解放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独立的精神生产创造了前提,也是造成文化与科技分离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次,区别于原始时期的蛮荒状态,人类步入文明社会*摩尔根认为:“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10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之后,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仅垄断了精神文化领域,有时还利用政治外力强行扭曲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如用阴阳之道发展中医技术、用神权意识解释天体运行、用道家思想来解读地理现象,等等。[12]在中世纪,科学的发明和发现被当做“异端邪说”,基督教排斥人类的肉体而重视灵魂,将科学视为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之一。这些都导致文化与科技之间呈现出强烈的对立状态。再次,文化与科技的相对独立发展往往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有关。如中国古代社会尊崇“伦理至上”,认为文是“载道”之物,而技是“通道”之物,因此视“载道”为大任,而视“通道”为小技。[13]由于古代科技过于注重实用,且多为生产经验的积累,技术化倾向严重,科技发展往往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如“天文”之于河水涨落、“数学”之于丈量土地、“水利”之于农业灌溉,等等。由于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生产力,其片面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导致科技与文化之间未能产生太多的交集。
如果说原始时期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主要是以一种“工具”形态呈现,那么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当中,二者则多以“器物”*“器物”原指古代青铜“尊彝”,是古酒器名,也泛指祭祀的礼器,后为各种用具的统称。参见 《周礼·秋官·大行人》:“三岁壹见,其贡器物。”郑玄注:“器物,尊彝之属。”形态呈现,其区别于原始时期“工具”形态的最主要特征是其审美特质明显且象征意义丰富。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仪式中的“器物”从属于“文”,功能性处于次要位置。由于阶级属性明显,这些“器物”往往体现出“强烈的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14],大多只为精英阶层服务,不像原始“工具”那样属于所有成员,不存在对哪些成员亲疏利害的区别。它们或是帝王祭祀时用的青铜礼器,或是诸侯、大夫家中的奇珍异宝,或是工匠手中的精美雕刻,抑或是艺术家笔下的教堂壁画。总之,文化与科技之间的融合往往局限于少数传统手工技艺领域,无法进入广泛的商品层面,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生产,更不可能形成文化与科技广泛融合的浪潮。
三、近代文化与科技融合冲突并存阶段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与科技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几乎横跨了漫长的古代文明,而这种关系的打破则最早始于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之风吹遍整个欧洲,人文主义浪潮盛行,帮助近代自然科学从封建统治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与人文在经历了中世纪长期的对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借着这股“东风”,欧洲再次迎来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曙光,突出表现为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的联姻,出现了如达·芬奇、哥白尼、布拉赫、伽利略、米开朗基罗、丢勒等一大批显赫巨匠。恩格斯曾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5](P261-262)。如果说,近代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触发点包含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变革等多重因素,那么真正将之推向高潮的则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蔓延至法国、美国等国家,率先完成了从“手工”时代向“机器”时代的过渡,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变革。但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旨在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没有与文化产生广泛的融合。直到进入“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应用于各类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领域,摄影、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介的问世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高水平,也是物质逐渐丰富后转向文化消费的主要领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萌芽与兴盛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在近代文化与科技走向融合的过程中,科技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正如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一书中所感叹的,“自从人们最初观望星星而又不知其何以存在,已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在短短的三十年当中(1810至1840年),科学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比整个那一段时期要多得多”[16](P456)。由于现代科技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随之兴起,将都市人置于“机械复制时代”的精神生产与声、光、电的狂欢之中。诚如马尔库塞描述的那样,“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风景胜地,打字员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连黑人也有了高级轿车,阅读同样的报纸”[17](P206)。由此可见,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不仅人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而且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也被克服,他们共同分享制度的好处。这充分表明,区别于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的阶级划分,文化与科技融合从少数精英的“器物”层面转向了多数大众的“产品”层面。在这里,普遍性与特殊性已经统一起来,“大传统”与“小传统”*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peasant)或俗民(folk)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参见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界限模糊了。以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极力主张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他们更关注文化产品的用途,拒绝审美标准的绝对性。这种新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与艺术生产的繁盛。
然而,当现代科技强制助推文化符号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时,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失衡也随之浮现。近代“启蒙精神”动摇了封建文明的根基,却一度让科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狂奔。由于技术的工具理性、实用性与应用性被强调到极致,“科技万能论”与“技术崇拜”盛行,特别是科学研究的经验原则、数量原则、机械性原则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行之有效,人文精神则被虚置,使主流文化的发展处于极度被动的地位。而由于过度追求技术和物质导致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等,反过来造成了广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危机。如此一来,文化与科技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断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欺骗本质的揭示,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本雅明感叹“灵韵”(Aura)的消逝,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理论的思考,弗洛姆对技术人道化的研究,海德格尔对技术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的批判,等等,都无不表达了相当程度的批判和反省。而这一时期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裂痕。英国学者C.P.斯诺将其归纳为“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对立和“两个极端的智力集团(groups)”(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互不理解、歪曲甚至憎恨和厌恶。[18](P3)这种分裂和矛盾对抗,“使西方文化丧失了整体文化观,致使思想界无法对过去做出正确的解释,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的判断,也难以对未来有所憧憬和展望”[19](P17)。五四运动后期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思考和博弈,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70、80年代却一边倒地倒向科学主义,出现了一种极为畸形的分裂。现代化进程中的“功利主义”与中国人文土壤的“排异性”导致科技与文化“两张皮”现象越来越严重。
近代以来,文化与科技积极的融合与消极的冲突两种状态并存局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乐观派”与“科技悲观派”、人文阵营和科学阵营的博弈。如同“双刃剑”,任何一种新兴科学技术或科技产品问世总是会遭遇到人们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种“两面性”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工具属性而忽视其人文属性,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态度往往是中立而不是积极迎合。在大航海时代,各大帝国在争夺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方先进科技文明与东方落后民族文化之间独特的交融现象,但这种单向的强制渗透与融合又何尝不是一场激烈的“冲突”呢?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因斯坦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科技造成的直接灾难:“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年代,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爱因斯坦于1931年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初稿发表在1931年2月17日《纽约时报》上。正如《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所倡导的,对于新技术的迅疾发展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理性本质有更清醒的理解并保持基本的“批判”意识,就有助于人类合理把控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四、当代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阶段
尽管文化与科技在工业化时期的交融出现了诸多“不适”,但是两者互为影响、不断创新的趋势却无法阻挡。尽管站在严格的批判立场,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早在文化工业出现以前,娱乐和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就已经存在了,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结合形成的工业体系是自上而下被承袭下来的。[20](P121)究其根本,还在于文化与科技融合迸发出的巨大能量。犹如万涓细流汇聚成河,奔向大海;而那蜿蜒聚散、平缓湍急则是必经的“变奏”。它让人们深刻意识到,文化与科技之间在经历了长期的对立和矛盾后,有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高度的统一。虽然文化与科技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远不及原始时期的“交融共生”状态,但在这样一个“汇流”运动中,已然是最接近的了。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十几年,是现代科技发展人文化倾向较为明显的时期,即“在经历了过度膨胀的科技理性之后,人们的反思给予了科学深切的人文理解和人文关怀。它内含着科学人文精神在当代的重新唤起,也内含着科技理性在当代的人文重建,由此将当代科技导入人性化的轨道发展”[21]。这很好地旁证了C.P.斯诺所谓“第三种文化”的存在——“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关系将会很融洽,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会缩小”*C.P.斯诺在《两种文化》1963年第二版中,加入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瞬》(TheTwoCultures:ASecondLook)的短文,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将浮现并弥合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参见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在人文领域,科学的思想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立体主义、印象主义、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众多流派的起承转合受到了立体几何学、现代光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一些作家如乔伊斯、普鲁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科学的启发。在科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分形理论、协同学、混沌学等复杂性科学带来了思维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创新,打破了过去科学拜物教的状态,并且日益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些都反映出,文化与科技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分裂状态逐渐被打破,误解和偏见进一步消解,人类社会开始迈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22]时代。由此观之,未来科技融合文化发展、融入人文精神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大规模社会文化运动,人们重视差异,张扬个性,文化变得多元,形成了有利于发挥个人创造力的氛围。这不仅对传统的工业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的兴起蔚为壮观,为当下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提供了充足养分。一方面,由于科技是文化得以产业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包含着科技的成分;另一方面,许多文化科技产品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产业环境的成熟程度,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为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丰富的“试验场”。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人类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和消费日渐增强,经济重心已逐渐由物质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和服务领域。而现代科技频繁催生的新事物,也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消费的多样化、个性化和人性化。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设备等新一代科技的应用,不仅动摇了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组织的根基,在文化领域更是掀起了新的“文化革命”,对文化艺术的生长环境、传播途径、业态模式和消费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些都导致了文化与科技走向深度融合,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
应当说,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工业时期以来融合、冲突的延续与发展。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鸿沟大大缩小了。而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同样处于科技引领文化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如今文化的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向科技领域靠拢,科技本身的发展也更加人文化和人性化,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倚靠的新局面。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电视、舞蹈等传统文艺领域积极运用新的技术工具理性地进行全面改造,促进了流行文艺资源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过程中催生了许多新的文艺形态;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海量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刺激了网络应用和移动技术升级,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地需要文化内容的驱动,科技资源的人文化、创意化、艺术化和审美化趋势明显。
总之,在新的移动互联时代,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日益广泛和深入,彼此构成了对方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如此,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竞争开始转向以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为代表的“软实力”(soft power)竞争,文化科技产品以其极为有效的“吸引”(attraction)和“说服”(persuasion)能力[23](P6)获得了全球市场和各国政府的青睐。在一个多元文化竞争的新“战国时代”,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相较于工业时代“自产内销”为主的文化发展模式,当今各国无不“摩拳擦掌”,希望借助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力量抢占21世纪的文化制高点和话语权。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任何一次跨时代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文化与科技的相遇与对话。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是社会文化形态演进发展的催化剂,先进文化与知识积累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文化与科技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对待“文化”与“科技”的态度就常常因为政治、经济、宗教、战争等因素而处于不断嬗变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与科技之间本该交融的关系。然而,经历了漫长的古代文明和短暂的工业时期之后,原始艺术与简单技术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共生”状态有望在未来得到“回归”。我们假定以人类制造第一件“用工具制造出的工具”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实践的起始,其一旦产生,文化与科技就存在各自走向独立甚至对立的可能。但是,由于文化与科技同根同源的性质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与科技之间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触底反弹”的融合运动。所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早在西周时期,古人便将“天文”与“人文”相提并论,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庸智慧。无独有偶,如今人类社会也更加崇尚科技与人文并重,更加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追求的统一,这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运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脉络,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历史演进机理大致呈现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浅层”到“深层”、从“手工”到“机器”、从“零星”到“规模”、从“偶然”到“必然”、从“线性”到“网络”的运动轨迹,具体表现为“工具”、“器物”、“产品”、“产业”四种形态的过渡。简言之,过去科技对文化的影响表现较为单一,往往只在特定的阶级和历史时空中发挥作用,现如今却发展为“相得益彰”的格局。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渐成熟的今天,文化与科技融合为天马行空的文化创意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内容找到了更多元化的载体及表现形式,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的同时,激活了创新要素,增强了文化品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文化业态。“文化+科技”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发展最典型的模式之一,对繁荣文化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我们发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当代命题,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是人类基本意义要素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始终。而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问题,包括融合范围的广泛性、融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融合价值的丰富性等,则是一个不得不给予关注的当代课题。
对中国而言,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正处于一种“离异”*汤一介教授认为,文化的发展大体上通过“认同”与“离异”两种作用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方向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相反,“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兼容被排斥的、释放被压抑的能量,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参见汤一介:《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载《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1(7)。力量为主导的文化转型时期,面临的是“文化开放”与“文化坚守”的双重语境。其积极的一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孕育出了许多新生事物,也使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的行动中获得了飞速发展。而消极的一面是,西方价值观的长期渗透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阐释中逐渐“失语”,以至于面临着“后殖民时代”新的文化安全危机。目前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其一,要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去拥抱全球化,加强与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其二,需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坚守,以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置身此种环境下,通过文化与科技融合繁荣文化市场以及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具有了当代文化意义上的前瞻性,也对未来我国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实践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钱中文:《国别史与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贡献》,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10)。
[2][13] 于平:《城镇化进程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载《艺术百家》,2014(6)。
[3] 向勇:《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关键问题和人才要求》,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1)。
[4][7]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6]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9]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0][12] 黄韫宏:《文化与科技互动的历史形式和未来趋势》,载《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11]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14] 闫月珍:《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6)。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人类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8] C.P.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9] 陈俊明:《科技与人文互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0]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1] 廖清胜:《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趋势——兼论“两种文化”统一之路及其意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
[22] 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途径》,载《光明日报》,2004-06-01。
[23] Joseph S.Nye.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
(责任编辑 林 间)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Culture & Technology:Evolution Mechanism and Historical Context
LI Feng-liang1,ZONG Zu-pan2
(1.Institution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culture & technology is the most typical mod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hich follows certai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presents different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main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rules and path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culture & technology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At the stage of savagery, primitive culture and simple technique present symbiotic appearance due to the same origin, followed by a long-time classic civilization period wh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develops independently along their own relatively separate systems.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times, the mutual exclusivity of culture & technology was broken,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fusion and conflict situation at industrial period. At the information era,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 technology present a depth fusion trend promoted by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e &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nova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historical context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战略路径研究”(11&ZD02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市文化经济发展中的‘景象’营造研究”(GD14XYS19);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研究”(2015WCXTD002)
李凤亮: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宗祖盼: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