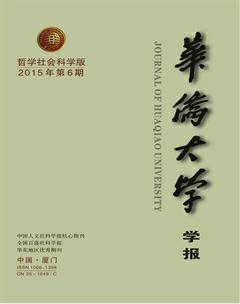个体生存的三重向度及其宗教体验的最终指向
摘要:为黑格尔哲学所宣扬的理性主义滥觞,构成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批判的起点。通过碎片化、复调式的表达,后者在结构与内涵上,揭示出个体存在的真实境遇。与追求抽象统一的思辨诉求大相径庭,克尔凯郭尔试图在审美与伦理的两难抉择中,揭示非此即彼的生存现状。并且,从辩证维度,通过展现二者的内在危机,进而为之后宗教体验的合法性奠定基础。因此,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毋宁是,以美学与伦理学的方式,对其宗教思想的间接表述。而它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辩证法,毋宁构成神学辩证法的先声。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审美;伦理;宗教
中图分类号:B5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6-0068-09
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批判,构成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中有关宗教信仰的神圣体验。作为一种激情抑或情怀,它在《畏惧与战栗》以及《恐惧的概念》等假名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克尔凯郭尔运用心理学手段,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真实再现了人、神之间近似荒谬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受难、焦虑等情绪的伴随下,完成由美学抑或伦理,向宗教层次的飞跃。按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分别构成人生道路诸阶段的美学、伦理以及宗教,彼此之间并非是逐级递进的线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可供个体选择的生存样式,它们彼此平行、互不干涉。至于以何种模式展开生存,均以“非此即彼”的选择为前提。鉴于此,克尔凯郭尔就以个体生存面对“选择”的形式,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体系分道扬镳。
从个体生存维度,对辩证法的理解来看,克尔凯郭尔旨在建构一种非线性的、断裂的辩证法,即个体生存的辩证法。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之所以是可能的,皆因思想者找到了某种‘终结点,借助这个支点,思想者可以依靠反思的力量将思想的‘碎片连缀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1]65但是关于个体“生存的体系(tilvaerelsens system)则是不可能的。”[2]这是因为,个人所处的生活世界,本来就是有限的、碎片化的存在。它与思辨的无限
收稿日期:2015-11-0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比较研究”(2015M580418)
作者简介: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截然不同。至于抽象体系对其进行的“整体性”反思,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不过是绝对理性的一厢情愿罢了。只有宗教的绝对悖论式的体验,才能真正从辩证维度,全面把握个人生存的全部境况。一感官直接性的困境:生存辩证法的审美维度
审美作为个体生存的最初阶段,其特征被克尔凯郭尔定位为感官直接性。并且,它以内在性的方式抽象地展现自身。对此,克尔凯郭尔指出,最抽象的理念即感官的天赋。原因在于,它“内在性的定性自身”[3]61。这表明,审美主体凭借感官天赋,抽象直接地把握外在世界。其最大特点,就是审美主体之于对象的瞬间性关系。对此,克尔凯郭尔明确指出,在其中“我们享受某种彻底偶然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3]366-367值得一提的是,在审美的直接性与瞬间性中,依然隐含着生存辩证法的踪迹。在《非此即彼》的美学部分,克尔凯郭尔通过对诸如唐璜、切鲁比诺等艺术人物的分析,构造出审美层面的生存辩证法。从中不难看出,审美的辩证运动也是由自在(an-sich)到自为(fur-sich)的过程。
克尔凯郭尔对审美辩证法的分析,始于他对音乐与语言的区分。在他看来,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具备前者所缺乏的反思意识。因此,语言无法说出可为音乐所表述的“直接性”。由此可知,审美辩证法的起点,始于非反思的直接性。作为一种暗哑的欲求,它欲求那将要成为欲求对象的事物。但在主观上,它却从未以“欲求这对象”的方式占有该对象。这说明,此时的审美主体还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其说他“在欲求”对象,不如说他被动地拥有对象。未明确主体性的主体,无异于混沌的抽象存在。类似于黑格尔的纯存在,这种感官直接性是毫无规定可言的纯粹抽象。其典型人物形象,克尔凯郭尔认为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以侍从身份出现的切鲁比诺克尔凯郭尔认为,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切鲁比诺被莫扎特塑造成为懵懂的爱欲追求者。他在爱上马尔瑟丽娜的同时,又爱上伯爵夫人。在回应苏珊娜对他的嘲讽时,切鲁比诺的回答是:她们都是女人。由此可见,就审美对象的个体性未被确立而言,切鲁比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抽象的。对此,克尔凯郭尔指出,“他永远也达不到更远,他永远也无法出发,因为他的运动是幻象,这样,也就没有运动。”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卷)[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3.。
但是,审美主体不能沉浸在抽象的对象化中黯然消逝。转而,凭借对审美对象的多样性进行区分,他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主体性。对此,克尔凯郭尔认为,欲求与欲求对象以主体生存的方式,绝对地一下子进入世界。但是“进入存在”(tilblivelse)不是两者的合一,而是两者的分裂。其结果是,欲求被从自己的实体性的“憩于自身”之中拉扯出来,并分化为一种多样性。[3]84-85审美对象以多样性的形式被区分,意味着审美主体通过界定客体的性质,间接地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
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审美主体,却陷于眼花缭乱的对象之中。因此,无法明确给出所欲求对象的性质。如前所述,在第一个阶段中,审美主体的欲求无法占有任何对象。仅是非欲求地拥有后者。因此是一种主体的暗哑状态。在第二个阶段,审美主体虽然通过欲求对象的多样性,显示出自己。但由于后者的性质未得到具体的明确(即未从“这些”对象转变为“这一”对象),故而,主体仍然徘徊在其中,无法被准确定位。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审美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开端,以唐璜为标志。因为“在唐璜中,那欲求则被绝对地定性为欲求。”[3]90这表明,审美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前提,是它具有唯一确定的审美对象。
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辩证法,强调主体的个体性。鉴于此,审美主体自然具有个体性的特征。从最初的抽象地欲求对象,到在对象的多样性中欲求对象,再到绝对地欲求唯一对象。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主体,完成了从直接抽象到直接具体的嬗变。因此,由切鲁比诺经由帕帕吉诺,再到唐璜的演变,旨在表明审美主体的个体性不断完善的辩证历程。他指出,“第一阶段理想地欲求着‘那唯一的;第二阶段在‘那多样的定性之下欲求‘那单个的,第三阶段由此得出统一。欲求在‘那单个的之中有着其绝对的对象、绝对地欲求‘那单个的。”[3]90显而易见,其中蕴含着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对唯一对象进行绝对欲求的个体,仍然不是审美主体的最终形态。这是因为,他的欲求仍是直接意义上的感官刺激,并且仅仅停留在片刻的享受之中。以唐璜为例,克尔凯郭尔认为,他的生命是由支离破碎的“片刻”构成。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聚合性。进而,虽然在此时,个体可看做是片刻的总和。但归根结底,片刻的总和仍然是片刻。因此,感官直接性的审美主体只作为瞬间性的存在,而不具有永恒性。
鉴于此,感官直接性的主体进入反思的环节。以悲哀为研究对象,克尔凯郭尔指出,反思的主体持恒地寻找自己的对象,并且“寻找”构成反思主体的整个生命。[3]220不难看出,感官直接性的主体以反思(寻找)的方式,进入永恒(持恒)。在他的“内在不是一种安静的精神的刚直不阿的本质,而是一种不安的精神没有结果的忙碌”[3]226。主体陷入自身的无限反思当中,在没有结果的不安里挣扎。这意味着,反思的审美主体进入完全的内在性,并于其中找到痛苦的永恒。内在反思主体的典型,克尔凯郭尔选择了玛丽·博马舍。在遭到未婚夫克拉维果的欺骗,并被撕毁婚约后,她开始了漫长的质疑与痛苦的反思。试图证明克拉维果并未对她进行欺骗。然而,结果却是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并在骗局与悲哀中不能自拔。
与玛丽·博马舍不同,修女爱尔薇拉表征另一种形式的反思审美主体。她在被唐璜欺骗并失去一切后,没有被反思的痛苦所束缚。而是以整个生命的转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这样,她就从审美的反思当中挣脱出来。但是,随后她将面临两种选择:进入伦理抑或宗教的定性;或者继续接受审美状态。[3]240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反思的层面出离后的审美主体,将以什么形式保持个体的永恒性?对此,克尔凯郭尔对审美的反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爱尔薇拉之于唐璜是一种单纯的“属于”关系。因此,当骗局被揭穿,爱尔薇拉开始新的生活时,作为“片刻”集合的唐璜又会对之产生欲求(因为,前者的特征已发生可改变。现在的爱尔薇拉已不是先前的她自己。故而作为一个新的“瞬间”,会重新燃起唐璜的欲求)。但他已不可能再拥有她了。
与之相反,克尔凯郭尔认为,在《浮士德》中,浮士德与玛格丽特之间的关系可以超越以上困境。这是因为,浮士德作为一个诱惑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单纯无辜的玛格丽特。他用直接的信仰装饰她,这样玛格丽特的灵魂就与浮士德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有趣的是,以坚信不疑的方式,灌输给玛格丽特的东西,对浮士德而言则是最值得怀疑的。这意味着,浮士德以彻底欺骗的方式,使“玛格丽特完全地消失在了浮士德之中”[3]252。之所以说浮士德的欺骗是彻底的欺骗,原因在于他对玛格丽特的欲求是绝对的。毋庸置疑,对唯一欲求对象的绝对欲求,就在保留永恒性的同时,彻底取消了反思的可能。作为代价,就是将审美对象重新纳入审美主体之中。
由此可见,从直接审美向反思审美的过渡,同样是以辩证的方式进行的。其中,痛苦的内在反思构成审美反思的自在(肯定的)方面。这时,主体被对象(以自身为对象)所限制;而打破反思的束缚,开始新生活的尝试,则是审美反思的自为(否定的)方面。此时,主体脱离对象的桎梏,以否定的方式生存;最后是对反思的消极扬弃。主体通过绝对的占有审美对象,而从消极的层面把审美对象纳入自身当中,进而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
然而克尔凯郭尔马上指出,对唯一对象进行绝对欲求的绝对主体,是“最不幸的人”。这是因为“他的理念、他的生命内容、他的意识财富,他的根本的本质以某种方式是处在他自身之外的”[3]274。对唯一对象的绝对占有,在审美层面意味着绝对的欺骗。看似审美主体完全占有了他所欲求的对象,但由于欺骗营造出的虚假表象,所以作为欲求客体的审美对象,并没有真正被纳入他的视野。而是以虚假的形式,外在于审美主体。后者得到的,仅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虚假片段。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因为反思的介入,变得更加难以弥合了。可见,“审美者滥用了思想的自由,以至于他们从根本上否定行为的意义,最终完全被生存的矛盾和悖论所俘获。”[1]32
鉴于此,通过生存辩证法的演绎,以感官直接性为特征的审美生存方式,其困境就得以显现:以“片刻”的享受为生活方式的审美主体,必将陷入无限的绝望当中。因为外在现实是一个与他完全隔绝的世界。前者被他以欺骗的方式,永远地排除出个体之外。显然,审美维度的生存辩证法,意在揭示个体生存,将承受内在反思与外部现实之间矛盾的巨大张力。“审美者……以切身的感受完成了对生存的‘现实性展示。这个世界是矛盾的、偶然的、悖谬的,个体被抛到这个世界上……面临最为严酷的‘现实性。”[1]32
二普遍有效性的两难:生存辩证法的伦理维度
克尔凯郭尔认为,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由审美到伦理的转向,可看做主体存在的瞬时性向永恒性的嬗变。为此,他对二者的性质专门进行了区分:与审美直接性的转瞬即逝不同,伦理体现出个体对于现实的持恒性。究其根源,克尔凯郭尔指出,这首先体现为二者对“反思”的不同理解。以“爱情”为标的,分别以审美和伦理的视角进行反思,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倘若反思指向爱情的永恒元素,无疑会起到强化的作用;反之,如果反思对象的性质仅具有现世性,这将对爱情本身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该结论的突出例证,可参照莫扎特笔下的经典形象——唐璜。并且,现世性可被理解为当下性。唐璜专注于对现世性的欲求,因此无论从审美主体,还是审美对象来看,其意义只具有瞬间的合法性。一旦与外界建立联系,它的连续性就会丧失。克尔凯郭尔提到,在该层面若要保持爱情的永恒性,只有以绝对的方式,绝对地占有对象。然而,通过对浮士德与玛格丽特之间矛盾关系的分析,克尔凯郭尔认为,其中必然存在绝对的欺骗因素。显然,无论从直接的角度,还是从反思的角度出发,以“现世性”为着眼点的反思,将引发爱情永恒性的瓦解。诚如克尔凯郭尔借威廉大法官之口讲到:“它们(审美者——笔者注)虽然是在反思的领域里被达成信守,但却没有达到那种永恒的意识,这种永恒的意识是道德伦理性所具备的”。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5.
值得一提的是,克尔凯郭尔把以上差别的原因进一步归纳为,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他指出,以感官直接性的形式表现出的爱情,最初具有反思的特质。然而它是“最初的爱”所匮乏的。因此,在爱情的最初状态中,只表现出必然性。但爱情的载体——作为个体的生存主体,恰恰从这一必然性之中,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该论断的提出,是克尔凯郭尔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的结果。他认为,以必然性的方式出现的“最初的爱”,在其自身当中有着双重性。它将自己作为先决条件,以回溯的方式设定进永恒的同时,也以面向未来的方式进入永恒。回溯意味着某种必然性,而面向未来则意味着自由的可能。因此,那个体恰恰是在这一必然性之中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在此之中感觉到自己整个的个体能量,恰恰是在这之中,感觉到他对他所是的一切的拥有。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3.对此,克尔凯郭尔总结道,“那最初的爱”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体。个体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拉向另一个体,但在之中他却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这意味着“那普遍的”与“那特殊的”间的一种统一。[4]45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当中感到“自由”,克尔凯郭尔意在说明,审美主体本身就蕴含着向伦理境界过渡的可能性。
“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伦理法则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一种内在于主体的自然法,它以必然的形态,蛰伏于最初的审美必然性之中。随着个体生存向伦理层次的跃迁,之前以必然为前提的个体自由,通过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最终成为现实的自由。后者以婚姻的方式为爱情贴上了伦理法则的标签。于是,囿于单个人内心的审美无限性,以与其他个体建立联系的方式,在普遍性维度获得了公开性。而“爱情则通过公开而在自身之中有着一种永恒之定性,……在这公开中,那最初的爱的直接性沉底了,但却没有被丢失,而是被吸收进婚姻性的觉悟中”[4]121。
通过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演绎,克尔凯郭尔试图揭示伦理自由的现实意义。与审美内在性相比,个体生存的伦理状态具有普遍性与公开性。后者凭借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打破了审美主体不可告人的秘密(直接性、欺骗)。在将其公诸于众的同时,它就为个体走出孤立的内在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克尔凯郭尔认为,从审美到伦理的转向,关键在于生存主体对自身的选择。他指出,选择在内容上,对个体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选择,个体就与被选择的事物建立联系。而如果他不进行选择,就只能在消耗中“枯萎”(——克尔凯郭尔语)。个体开始选择,意味着他已进入现实的世界。与审美主体的内在性不同,伦理主体代表个体生存的普遍性与现实性。克尔凯郭尔强调,它是审美主体所蕴含的内在可能性,在现实世界的投射。针对该结论,他指出,“伦理生活的人,他把自己当作为自己的任务。他的‘自我是作为直接地偶然地定性的,而那任务则是去把‘那偶然的和‘那普遍的改造为一体”[4]310。伦理对审美的改造,旨在把内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并通过现实的过程,将其实现在现实中。伦理主体作为不断完善的存在,持恒地对偶然性实施普遍有效性的改造。
不可否认的是,在审美主体那里也具有选择。然而审美的选择难逃直接性的窠臼,并且时常迷失在感官对象的多样性中。与之相反,伦理性的选择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的选择”。它是“在我的永恒性中的我自己。……它是一切之中最抽象的,同时就其自身又是一切之中最具体的东西,亦即,它是自由”[4]265~266。绝对的选择等价于个体的自由。这是生存辩证法在伦理维度的重要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它并非是针对善恶的具体伦理抉择,在更高层面,它标识了个体在“选择善恶”,与“排除这一善恶选择”之间的两难境地。
克尔凯郭尔指出,个体的现实生存,依托绝对的选择得以设定。因此,后者是个体进入现实的必要条件。同时,作为自由的开端,又构成伦理层面的绝对命令。针对以上关系,不难看出,“确立了‘选择的‘伦理性就等于确立了‘选择原则的‘必然性——必要性,从而把‘选择变成个体为了‘自由而在人生历程当中必须执行的一项‘命令”[1]46。既然伦理主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不断统一的过程性存在,那么他的现实性,就是一个持恒选择的连续进程。与审美的片段性和瞬时性不同,连续性的介入,使伦理主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了自身的实在性。通过之前的分析不难看出,这是个体的特殊性,融入个体间普遍性的结果。特殊的个体以“去成为”普遍个体的方式,在持续的过程中实现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鉴于此,伦理个体相对于自身,就有着内在(特殊性)与外在(普遍性)的双重性。
值得一提的是,某一个体以普遍性的方式,进行伦理的绝对选择时,并不意味着其特殊性(个体性)被后者所消解。与之相反,该特殊性恰恰在普遍性之中获得了自身的现实性。克尔凯郭尔指出,在伦理维度,个体人格以绝对选择的方式关注自身,并且伦理地选择自身。与此同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该主体不是去成为“另一个存在”,而是成为他自己。这样,仅以内在可能性为表现形式的审美个体,就以现实性的方式得以复归。对此,克尔凯郭尔专门引入了历史与时间的概念,对之进行解读。他指出,“真正的历史与那作为历史中的生命原则的东西都争着,它与时间都争着,但是,在我们与时间斗争的时候,‘那现世的以及每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恰恰因此而都有着自身极大的实在性。”(参见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王齐教授在《生命与信仰》一书中,做了进一步诠释。她将历史具体化为“内在的历史”。并提出:“从‘内在的历史出发,‘发展自我也就是个体要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通过切实的行动不断完善这段‘历史,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灵魂和‘自我,并且从中获得满足和安宁。”(参见王齐:《生命与信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可见,个体之于现实的关系,就是自身的内在历史不断得以填充的过程。这就构成克尔凯郭尔伦理辩证法的核心。他试图借助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和解,在现实性层面,以不断选择的方式,持恒地使个体获得永恒的存在。
但问题在于,“‘那普遍的就其自身是不会存在任何地方的,而我在‘那单个的之中到底是看见‘那普遍的还是仅仅只看见‘那单个的,这则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意识的能量”[4]386。无疑,克尔凯郭尔意在揭示特殊与普遍的绝对差异。虽然在伦理层面,个体通过绝对选择,以一种持续的方式获得了二者的统一。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单个的”不等于“那普遍的”。归根到底,伦理的普遍性仍是相对于个体的外在存在。对此,克尔凯郭尔将其描述成一个“严厉的主人”,它并不断把审判之剑举在个体的头上。因此,以伦理方式对特殊性与普遍性进行统一,并从中获得个体自由的方式,又转化为外在必然性对个体的压制。换言之,伦理的普遍性将以必然法则的角色,行使主人的权利。
毫无疑问,作为普遍法则的伦理必然性,僭越了自身作用的范围。凭借绝对选择对个人生存,与现实自由的先验设定,它俨然具备创造个体的能力。其实不然,克尔凯郭尔明确表示,个人虽然借助自由来发展自己,但他却不能从乌有之中创造出自己。伦理追求普遍有效性,因此决不允许例外的出现。但事实证明,“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外”[4]389。而且,与普遍性保持着巨大的差别。
凭借持恒地面向未来的方式,自由的个体表明,从“永恒性”的视角来看,他比“现世的”(当下的)自身(self),蕴含着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他既是“那普遍人性的”又是一个例外。这样,生存辩证法在伦理维度就陷入了新的两难:如何使现实的生存个体,在普遍性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换言之,二者的关系该以何种方式得以界定?
三绝对个体性的悖论:生存辩证法的宗教维度
生存主体在伦理层面遭遇的两难,实则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相互角力的结果。对二者关系的反思,意味着道德准则的合法性成为值得商榷的议题。质言之,克尔凯郭尔对伦理内部矛盾的揭露,旨在规划普遍性道德的作用范围。并为个体生存的更高层次样态,提供先决条件。他指出,对伦理普遍性的超越,其实质是具有绝对内涵的生存个体,对一般道德法则的突破。鉴于此,克尔凯郭尔将之归纳为,“作为一个单个的人将自身设定在一个与‘那绝对的的绝对关系之中”[5]58。不难看出,绝对个体与绝对本身的绝对关系,直接指涉个体生存的宗教维度。而它的典型形象,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非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克尔凯郭尔取材于《圣经·创世纪》的人物。其中,神欲试探义人亚伯拉罕,便要他以自己的独子以撒献祭。但以撒是上帝给予亚伯拉罕与撒拉信仰的礼物,二人对其视若珍宝。然而亚伯拉罕没有犹疑,他毅然按神的指示告别妻子,并携其幼子来到摩利亚山,准备献祭。在准备好燔祭的柴火与利刃,并准备杀子奉献时,上帝的使者突然降临,并告知已有羔羊代替以撒。神对亚伯拉罕盛赞有加,称其为敬畏上帝的义人,且赐予大福。(参见《圣经·创世纪》(22:1-19)克尔凯郭尔对该人物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并在宗教意义上略加改动。为详细阐述其宗教观点,在《畏惧与颤栗》一书的开头,他对该故事进行了四种版本的演绎。莫属。
作为父亲,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举动完全有悖伦理。但他所蕴含的宗教体验,却构成克尔凯郭尔反思伦理普遍性的切入点。针对亚伯拉罕所表征的的宗教性质,克尔凯郭尔指出:“信仰的运动必须依据于那荒谬的不断地得以进行。”[5]29荒谬意味着与伦理法则不同的思维模式。亚伯拉罕杀害自己的独子,是伦理道德坚决鄙斥的行为。并且,它不能为一般的理性思考所理解。因此,克尔凯郭尔将其归结为荒谬的举动。
然而,在杀子献祭的荒谬性中,恰恰蕴含着个体走向宗教的必要前提,即对有限事物的无限放弃。作为开始信仰之前的最后准备,克尔凯郭尔指出,只有在无限的放弃中,信仰对自身而言才具有无限的有效性。惟如此,方能论及个体以信仰的方式把握生存。在亚伯拉罕那里,关爱幼子的伦理行为与信仰上帝的宗教行为相比,只是有限性的存在。与之相反,对上帝的责任才具有无限性的意义。因此,荒谬的实质是宗教无限性,对伦理有限性的绝对弃绝。作为一个悖论,它表明“单个的人高于‘那普遍的……在他进入了‘那普遍的之后,他现在作为单个的人将自身隔绝为比‘那普遍的更高的”[5]52。
单个的人(或生存个体)对伦理普遍性的超越,可看做信仰的荒谬性对伦理理性的战胜。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的起点就是理性的终点。在后者看来,绝对个体的实现,只能表现为绝对的悖论。质言之,伦理宣称亚伯拉罕要谋杀(murder)以撒;宗教则认为亚伯拉罕要献祭(sacrifice)以撒。二者构成谋杀与献祭、伦理与宗教之间的巨大悖论。[6]49该悖论的出现,致使理性的普遍性没有相应的适用空间。此外,个体以信仰的方式与上帝建立了绝对关系。与之相比,伦理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就只有相对意义。
如果说亚伯拉罕的无限弃绝,意味着伦理有限性的终结。那么上帝使其重获以撒,则表明宗教无限性的开端。它是信仰的力量,并以再现的形式显现于有限世界。一个人可以放弃外在的有限性,但只有上帝才能重建被否弃的有限性。这是上帝在亚伯拉罕顺从地献祭以撒后,将后者还给亚伯拉罕的信仰的力量。[6]46重获以撒表明,亚伯拉罕曾经失去的有限性,又失而复得。这是从直接性到直接性的过程。
但要注意,信仰的直接性不是最初的直接性。从中,克尔凯郭尔无疑构建了一个由伦理向宗教跃迁的生存辩证法。即伦理法则的直接性经由绝对个体的无限弃绝,最终使个体重获直接性的过程。不难看出,个体凭借宗教体验,以绝对的方式从伦理普遍性中超拔出来。并通过荒谬的悖论,在信仰层面与上帝构建了绝对关系。伦理法则中,个体的直接性被普遍性遮蔽,因此是一种自在的状态;通过无限弃绝,个体在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同时,成为了超越普遍性的绝对个体,此时他以自为的形式出现;最终,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在否弃普遍性之后又重获自身的直接性——这就是个体生存的自在自为状态。
克尔凯郭尔认为,绝对的生存个体对普遍性的超越,本质上是荒谬对理性的战胜。它以悖论终结了理性思维的普遍有效性。因此,“关于‘他(亚伯拉罕——笔者注)是怎样进入到这悖论里的是无法解释的,正如关于‘他是怎样留在这悖论里的也是无法解释的。……信仰是一种奇迹,但却没有任何人是被排斥在它之外的”[5]62。一旦个体与上帝建立绝对关系,他就与理性普遍性彻底隔绝了。与此同时,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将成为无法公诸于众的秘密,而被所谓的伦理道德永远雪藏。换言之,当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高于他与其他个人的关系时,伦理道德的义务就被更高的、指向上帝的义务悬置了。[7]克尔凯郭尔将之归结为,单个的人以沉默的方式保守秘密(他与上帝之间的绝对关系),从而在信仰的力量中获得拯救(个体重获直接性)。
对宗教悖论的揭示,意在突显信仰对理性的优越性。克尔凯郭尔不希望任何哲学理解通过将信仰置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做法,超越信仰。[6]41他认为,与形而上的体系相比,信仰具有前者所不能比拟的超验性。它依托人类之外的力量,以奇迹的形式得以展现。显而易见,在单个人与上帝的绝对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可以实现过渡的中介在上帝与人之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只存在鸿沟(gap)而没有中介。并且,它不能为理性与知识所战胜。这就是亚伯拉罕不能被理性完全解释的原因。与此同时,他的信仰也不是得以完全确证的。相反,它充满畏惧(anxiety)与紧张。因此,亚伯拉罕虽有信仰,但却充满恐惧与战栗。(参见Jon Stewart:Kierkegaards Relations to Hegel Reconsider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18~319)此外,通过亚伯拉罕的信仰,又区分出两个重要概念。即希望(hope)与期望(expectation)的差异。路易斯·麦凯指出,伟大的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和希望。但是对于人们来说,更伟大的是以信仰对抗理解,以希望对抗期望。(参见Louis Mackey:Point of View. Florida: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45)。因为“所有中介恰恰是依据于那普遍的而发生的;这是并且在所有的永恒之中继续是一个悖论,对于思想来说是无法进入的”[5]53。从伦理到宗教的跃迁,意味着生存主体自身的一种飞跃。并且,这是对之前有限性的绝对弃绝。
结合前文,从审美到伦理,再到宗教的嬗变,意味着个体不断对自身的生存样态进行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之间绝非不断递进的扬弃关系,而毋宁是彼此断裂的板块性存在。鉴于此,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以什么样方式展开生存,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本身是理性所无法掌控的。此外,虽然审美、伦理、宗教三者之间是漠不关心的平行关系,但选择本身却具有设定个体生存的绝对意义。并且,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它的最终指向,就是宗教状态中,个人与上帝的绝对关系。
选择在构成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核心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与后者不同,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三境界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并且,支撑三者的理论核心,也不是思辨的反思主体,而是以现实生存的个体取而代之。它将封闭在思辨领域中的抽象主体置于现实的存在领域予以考量,目的在于,以真实的生活碎片为武器,对黑格尔哲学抽象封闭的体系予以反戈一击。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生存状态显然不是以整体对环节的扬弃为前提的必然过程。与之相反,由于个体生存的有限性,所以它才以选择的方式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他最大的无限性,毋宁是与上帝的绝对关系。
审美的困境、伦理的两难抑或宗教本身的悖论,均可视为对黑格尔抽象体系的反讽。以理性之名,后者所携带的绝对普遍性与完全有效性,根本无法了解生存本身的悖论。这在个体与上帝的绝对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在形式上,从审美经由伦理再到宗教的发展,可看做个体生存模式的辩证运动。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以辩证的手段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的内部瓦解。因为,辩证运动的主体已由抽象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具体的单个个人。况且,个人的选择行为就是非理性的举动。鉴于此,马兰楚克(Malantschuk)将之归结为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抗,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Kierkegaards Thought”)一书中,他指出:“就一般意义而言,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思辨持否定态度,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他可以运用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8]
克尔凯郭尔以生存代替思辨的方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之后,超越理性必然性的个体选择,就以开放的可能性,以有限的存在昭示无限的意义。进而打破黑格尔封闭的体系,以荒谬、悖论的方式,为个体的绝对自由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1]王齐.生命与信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转引自,王齐.生命与信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5.
[3][丹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卷[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丹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 [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丹麦]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Louis Mackey.Point of View[M].Florida: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7]Jon Stewart.Kierkegaards Relations to Hegel Reconsidered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324.
[8]Malantschuk.Kierkegaard's Thought[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58.
Three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Final Point of
Religion Experience
——On Kierkegaards Dialectic of Human-Haven
WEN Quan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 , Nanjing ,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preaching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ationalism origin constitut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Kerr Kierkegaards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lif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fragmentation and polyphony, the latter, 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reveals the real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Different from the pursuit of a unified abstract speculative demand, Kierkegaar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urvival status of either this or that in the aesthetic and ethical dilemma. And, from the dialectical dimension, 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two internal crisis, this paper sets up the base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Therefore, Kierkegaard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is the indirect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ideas in aesthetics and ethics. But, it embodies the aesthetic and ethics dialectics, constituting a harbinger of dialectics of theology.
Key words:Kierkegaard;life dialectics;aesthetic;ethics;religion
【责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