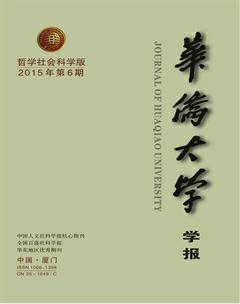夏商周经济制度新探
摘要: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是一种独特的私有制,亦即官有制,完全归官吏和官吏阶级所有:一方面,土地是王有制,归国王一人所有;另一方面,不但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而且工商经济权力也是官有制,因而所有经济部门的经济权力都实行官有制,归官吏和官吏阶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所有。这样一来,一方面,分封制和血缘宗法制以及井田制三大国家制度,是王有制及官有制的三大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井田制是夏商周的土地制度,而井田耕作者既非奴隶,亦非农奴,而是拥有人身自由的佃农。因此,全面说来,夏商周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的非农奴制的血缘宗法制的分封制的封建社会;究竟言之,夏商周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的封建社会:非农奴制和血缘宗法制以及分封制都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的产儿。
关键词:夏商周; 官吏阶级; 庶民阶级;官有制;民有制;王有制;井田制;宗法制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6-0005-46
夏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因此,若不理解阶级,也就不可能理解夏。特别是,夏商周以降,一方面,中国主要讲来只有两大阶级:全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垄断的官吏阶级与全权丧失的庶民阶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最根本的特色就是官有制,亦即生产资料官吏阶级所有制;而西方则是民有制,亦即生产资料庶民阶级所有制。
可是,按照中西主流见解,阶级是个经济概念,因而并不存在什么官吏阶级与庶民阶级——官吏阶级与庶民阶级属于政治阶级范畴——而只有经济阶级: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中间阶级。这样一来,必须首先科学地界说阶级概念。否则,不可能理解官吏阶级与庶民阶级,不可能理解官吏阶级所有制与庶民阶级所有制,不可能理解夏商周,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特色。所以,研究夏商周阶段中国经济特色的起点是:阶级究竟是什么?
一阶级概念:破解夏商周的钥匙
阶级概念,正如斯凯思所言,恐怕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难界说的概念之一:“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关系的所有概念中,社会阶级可能是最模糊、最不确切的。”[1]赖特亦如是叹曰:“正
收稿日期:2015-11-30
作者简介:王海明(1950-),男,吉林白城人,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学和中国学以及伦理学。像埃尔西惊异于为什么一头奶牛是一头‘奶牛一样,是什么使一个阶级成为一个‘阶级这一问题长期令人困扰。”[2]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2章“阶级”也这样写道:“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3]遗憾的是,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的手稿就中断了。那么,究竟何谓阶级(阶级定义)?究竟是什么使一个阶级成其为阶级(阶级划分根据)?
1阶级的词源含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阶级(class)”词条说:“这个词语起源于拉丁文classis,其用法中含有依据财富细分人口的意思。”《韦氏英语大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阶级”词条也这样写道:阶级亦即种类、类别,是具有相同的社会或经济地位的人所结成的群体。从中文来看,“阶级”由“阶”和“级”合成。“阶”和“级”原本同义,都是台阶的意思。《说文解字》:“阶,陛也。”《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礼记·曲礼上》:“拾级聚足,连步以上。”“阶”和“级”合成的“阶级”一词,也是台阶的意思。陆龟蒙《野庙碑》:“升阶级,坐堂宴。”引申为不同等级——特别是官位奉给的等级——的群体。《新书·阶级》云:“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三国志·吴志·顾谭传》云:“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可见,从词源来看,不论中西,阶级都是指人群的划分、种类和类别,亦即人们所分成的一些群体或集团,这些群体或集团的内部成员具有某种相同性,而群体相互间则根本不同。只不过,西文词源含有阶级划分的根据在于财富,说到底,在于经济权力;而中文词源含有阶级划分的根据在于官位,说到底,在于政治权力。那么,从概念的定义来看,阶级究竟是什么?
毫无疑义,就概念定义来看,与其词源含义一致,阶级也是指人群的划分、种类和类别,亦即人们所分成的一些群体或集团。这些群体或集团,就划分的根据来说,一方面,相互间根本不同乃至恰恰相反;但是,另一方面,每一群体内部成员则完全相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阶级划分的根据究竟是什么?
2马克思主义阶级定义
对于阶级的概念分析将令我们惊奇发现,阶级划分的根据,竟然也与其中西词源含义相同,乃在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影响深远的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根据和阶级定义,与阶级的西文词源含义大体相同,认为阶级划分的根据是经济关系,说到底,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关系:阶级是人们因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而形成的不同集团。列宁说:
“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4]“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让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
新马克思主义者罗默也这样写道:“阶级是一种群体,这一群体的所有成员以相似的方式与劳动过程相联系。例如,所有那些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形成一个阶级;所有那些雇佣劳动力的人形成一个阶级;所有那些为自己劳动从而既不出卖劳动力也不雇佣劳动力的人形成第三个阶级。”[6]赖特亦如是说:“将阶级概念限制在财产关系上是合适的。”[7]
然而,细究起来,马列主义的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根据理论是不确切、片面和不科学的。首先,它将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而不是经济权力垄断——作为阶级划分根据,不能科学地说明阶级关系的根本特征。因为所谓阶级,主要讲来,不外乎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地主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因而阶级关系的根本特征,诚如马列主义所言,是“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是剥削与被剥削以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是,仅仅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垄断并不能造成——只有当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垄断转化为经济权力垄断才能造成——剥削与被剥削以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为,前一章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或生产资料垄断之所以是剥削的根源,就是因为生产资料垄断转化为经济权力垄断,亦即生产资料垄断者通过建立雇佣关系,使自己成为支配和领导没有生产资料者的雇主,成为劳动价格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说到底,成为经济权力的垄断者,从而才能够无偿占有没有经济权力的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经济权力垄断是剥削发生的直接原因。
对于生产资料或财产垄断通过雇佣关系而转化为经济权力垄断的道理,斯密曾有深刻论述:“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巨大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继承了任何政治权力——不论民事还是军事方面。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两者的手段,但仅有财产未必就拥有政治权力。财产使他立即和直接拥有的权力,乃是购买力,是某种对于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亦即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8]罗默进而将这番道理归结为一句话:“生产关系就是经济权力关系。”[9]
但是,生产资料或财产并不是经济权力;生产资料或财产只有作为资本雇佣劳动者,才转化为经济权力。这个道理,戴伊早曾有洞见:“把个人财富与经济权力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单单拥有个人财富,哪怕有一亿美元,也还不能保证能有经济实权……经济学家阿道夫·伯利在论述个人财富与机构权力之间的关系时说的好:‘今天的美国和西欧,富人之所以权力很小,就是因为他富有……假使他希望得到一个有权力的职位,他必须到他的银行户头之外去找。”[10]
如果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并不用以雇佣工人而成为雇主,并不使其生产资料和财富垄断转化为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力垄断,那么,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就仅仅是个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就仅仅是个钱口袋和守财奴,而不可能成为压迫者和剥削者:没有被雇佣者,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去压迫和剥削谁呢?这样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群体,显然构不成任何阶级:既不是奴隶主阶级也不是地主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而仅仅是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垄断者群体,仅仅是钱口袋和守财奴群体,仅仅是富人群体。因此,阶级划分的根据,真正讲来,并不是生产资料或财产垄断,而是——正如赖特所指出——经济权力垄断:“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这么一个事实,即阶级关系是权力关系。”[2]36因此,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而不是经济权力垄断——作为阶级划分根据是不确切的,不能科学地揭示阶级关系的根本特征:压迫与剥削。
其次,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作为阶级划分根据,不能科学地界定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众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所周知,都从阶级划分根据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出发,界定无产阶级为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群体:“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1]殊不知,属于经理人员的白领工人,虽然也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却拥有行使一定经济权力的管理权,因而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新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的根本特征就是没有生产资料却有经济权力。因此,阶级划分的根据,与其说是生产资料垄断,毋宁说是经济权力垄断:经济权力垄断是阶级划分的深层根据;生产资料垄断是阶级划分的表层根据。从此出发,才能科学地界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阶级:资产阶级是拥有生产资料并作为资本和经济权力雇佣劳动者的群体;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和经济权力的被雇佣劳动者群体;中间阶级是介于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群体,亦即没有生产资料却有经济权力(经理人员)和有生产资料却无经济权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群体。
最后,正如波朗查斯所指出,马列主义的阶级定义和划分根据理论是片面的,他称之为“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社会阶级概念完全根据生产关系的经济方面确定社会阶级的定义,尤其是把社会阶级作为它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所起的作用来解释。”[12]104确实,这种所谓经济主义的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根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对立阶级——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却失之片面:它不能说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亦即官吏阶级,被统治阶级亦即庶民阶级,二者的形成源于非民主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制,特别是普选制民主,那么,全体公民和国民便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因而不存在政治权力垄断,不存在垄断政治权力群体与没有政治权力群体,说到底,不存在统治阶级(官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庶民阶级);而只存在统治者(官吏)与被统治者(庶民)。相反地,一个国家如果实行非民主制,那么,众多公民和国民必定毫无政治权力,因而便存在政治权力垄断,便存在垄断政治权力群体与没有政治权力群体,亦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亦即官吏阶级,说到底,就是垄断政治权力的群体;被统治阶级亦即庶民阶级,说到底,就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群体。
因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划分的根据并不是生产资料或经济权力的占有、垄断,而是政治权力的垄断或有无。这样,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只要成为官吏,就属于统治阶级,而不属于被统治阶级;相反地,一个人即使是亿万富翁,只要不是官吏,没有政治职务和政治权力,就属于被统治阶级,而不属于统治阶级。所以,波普说:“统治阶级总是某些人。无论他们可能曾经属于哪个阶级,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属于统治阶级。”[13]
因此,阶级划分的根据或标准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与经济权力垄断关系;还应该包括政治职务与政治权力的垄断关系。因此,将阶级定义为人们因生产资料、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力占有或垄断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集团,是片面的;人们因政治权力之有无或垄断而分成的不同集团——亦即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也属于阶级范畴:统治阶级(官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庶民阶级)。
然而,恩格斯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工具。”[14]
这就是说,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被统治的阶级,在政治上也被统治,因而统治阶级也就是垄断生产资料的阶级,亦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就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亦即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阶级划分的根据也就只有经济关系,亦即对生产资料和经济权力的占有或垄断关系。这种观点能否成立?
否。因为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未必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常常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在经济上被统治的阶级,在政治上却处于统治地位。古代雅典民主城邦的统治者,就不是奴隶主阶级,而是比较贫穷的平民。因此,亚里士多德称梭伦“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15]103,并反复强调雅典平民政体是按照穷人的意志进行统治,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的定义为人数甚多的贫民控制着治权。”[15]134
古代如此,当代亦然。实行普选制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为全体国民共同执掌,却势必按照多数国民的意志进行统治,因而往往是按照经济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不是按照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进行统治。否则,就无法解释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瑞典所实行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该法案被称为西方世界从来未目睹过的对资产阶级的最大规模的没收举动[16],结果激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以致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万5千人游行,抗议《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但是,瑞典议会还是于同年12月12日通过了该法案。
可见,认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将阶级划分的根据归结为经济关系或生产资料垄断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了。确实,所谓统治阶级,无疑是所有统治者所组成的群体。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无论他拥有多大经济权力,无论他在经济上“统治”多少人,只要他没有政治职务、官职或政治权力,他都不是统治者,他都不属于统治阶级。我们能说一个大资本家或大地主是统治者吗?我们不但不能说他是统治者,而且——严格讲来——也不能说他“统治”工人或农民;而只能说他管理、支配和领导工人或农民:“统治”和“统治阶级”纯粹是一个政治概念:统治阶级与官吏阶级是同一概念。
因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划分根据乃是政治权力,决不是经济关系或经济权力。有鉴于此,波朗查斯认为阶级划分的根据或标准应该是多元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非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经济标准,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17]17。从此出发,波朗查斯给阶级下定义说:“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决定的。”[17]17
诚然,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根据多元论避免了经济一元论的片面性,可以包括所有阶级。但是,这种多元论的阶级定义显然不但犯了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而且含糊不清,实际上无异于说:阶级由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决定。殊不知,阶级划分不但与意识形态无关,而且与政治职务或政治权力之外的政治——如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等等——无关。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导师,其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无疑都属于无产阶级;但是,恩格斯却是资本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
究竟言之,阶级划分的根据实际上只有两个: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垄断。因为人类社会迄今所有阶级——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中间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显然都是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垄断关系为根据划分的。因此,可以断言:阶级就是人们因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这样一来,阶级显然不仅是个经济范畴,而是经济与政治的综合范畴。我们不妨沿用赛维斯的用语,将经济权力垄断所形成的阶级叫做经济阶级(亦即垄断经济权力的阶级与没有经济权力的阶级);将政治权力垄断所形成的阶级叫做政治阶级(亦即垄断政治权力官吏阶级与没有政治权力的庶民阶级)。[18]这种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既不同于“经济一元论”—— 波朗查斯称之为“经济主义——亦不同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论”,不妨称之为“二元论”,亦即“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二元论”。
但是,这种二元论恐怕还不配享有真理的美名,因其仍然不符合分类的逻辑规则:一次划分只能有一个根据。显然,要避免这种弊端,阶级划分的标准必须是一元的,而不能是二元或多元的。可是,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阶级划分的根据,它既能够包括全部阶级,又可以避免各阶级外延部分重合?有的,那显然就是权力垄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无疑都属于权力范畴。这样一来,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根据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二元论”,就可以转化为 “权力一元论”: 权力垄断是阶级划分的根据;阶级是人们因权力之有无或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这个道理,波朗查斯已有洞见。他再三说:“关于权力和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已经可以得出某些结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12]103“阶级关系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权力关系。”[12]105“阶级关系就是表现在每一个方面的权力关系。”[12]107丹尼尔·贝尔也这样写道:“最终说来,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19]
准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以为阶级仅仅是个经济范畴的片面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政治权力虽然与经济权力不同,却毕竟同样是权力,而且是统帅、指挥、命令和役使经济权力的权力,无疑比经济权力更加严重和可怕,更加具有迫使人服从的强制性、压迫性和剥削性。如果说因生产资料或经济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是阶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不是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岂不明明白白就是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不同群体吗?统治阶级岂不就是垄断政治权力的群体?被统治阶级岂不就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群体?
3阶级的精确定义
精确言之,阶级是人们因权力之有无或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作为阶级定义,还不够全面。因为,权力垄断必然导致压迫与剥削。哪里有权力垄断,哪里分为无权群体与有权群体,哪里就必定存在压迫与剥削。没有权力的群体,必定遭受相应的有权群体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叫做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垄断权力的群体,必定压迫和剥削相应的无权群体,因而叫做压迫和剥削阶级。休谟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人们天生野心很大,他们的权欲永远不能满足。如果一个阶层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能够掠夺其他一切阶层,他们肯定会这么干,并使自己尽可能地专断一切,不受制约。[20]
因此,权力垄断与压迫及剥削如影随形;权力垄断是阶级划分的根据,实则蕴涵压迫与剥削是阶级划分的根据。毋宁说,权力垄断是阶级划分的表层的实在的根据;剥削与压迫是阶级划分的深层的潜在的根据:阶级是人们因权力垄断所导致的压迫与剥削关系而分成的不同群体。所以,赖特认为阶级是一个以剥削为核心和基础的概念:
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这么一个事实,即阶级关系是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特权。……尽管马克思有时利用统治和压迫来描绘阶级关系,阶级对立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仍是剥削。[2]36
考茨基也曾这样写道:“我们所说的阶级,只可以指这样一种集团,它同另一集团或阶级是处在剥削者或被剥削者的关系之中,或者,它如果不是努力抗拒这种关系,便是力图进入这种关系。”[21]
诚然,阶级的这一定义——阶级是人们因权力垄断所导致的压迫与剥削关系而分成的不同群体——能否成立,显然还取决于:以权力垄断及其所导致的压迫和剥削为根据,所划分出来的阶级,可以包罗一切阶级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不言而喻,阶级因权力垄断的种类不同而分为两类:政治阶级与经济阶级。政治阶级是因政治权力垄断而形成的阶级,分为两类:统治阶级(官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庶民阶级)。经济阶级是因经济权力或生产资料垄断而形成阶级,分为七类: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地主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中间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阶级吗?显然没有了。这样一来,阶级的这一定义——阶级是人们因权力垄断所导致的压迫和剥削关系而分成的不同群体——便既包括了所有阶级,又揭示了阶级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根本特征——权力垄断及其所导致的压迫与剥削——因而堪称阶级的精确的科学的定义。
二王有制和官有制: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所有制
1王有制:夏商周土地所有制
阶级的科学的定义是破解夏商周的钥匙,从此出发,就不难理解夏商周的阶级状况,特别是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所有制:生产资料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吏阶级所有制。首先,与五帝时代一样,夏商周的主要生产资料无疑也是土地,也可以等同于土地。那么,夏商周的土地归谁所有?周代的土地制度是王有制,土地、生产资料归国王一人所有:似乎可以称之为史学大家之共识。郭沫若说:
周代的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殷代也应该是这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都是王者所有,王者虽把土地和劳力分赐给诸侯和臣下,但也只让他们有享有权而无私有权。故到春秋年间,尽管周室已经式微,却还往往夺取臣下的田土人民而更易其主。 [22]25
范文澜说:“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土地接受者收回土地……《小雅·北山篇》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77吕振羽说:“(武王)革命军在占领殷朝首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便一面解放奴隶,一面宣布土地为‘王所有,臣民都须从王所表征的革命权力原则(‘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由王的名义册封。”[24]72
翦伯赞说:“周族克商以后,一面把商代的国有土地,转化为王的所有,另一方面,把商代的奴隶及自由民转化为农奴;同时,把残存于其他势力范围之内的诸氏族的土地与人民,也依照封建制的原理而改变其原来的属性。于是在周人的史诗上,便歌颂这一历史的胜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5]257-258
今日史学家亦有如是观者。张传玺说:“西周……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有占有权和使用权。”[26]62其实,并非只有周代实行土地王有制,殷商正如郭沫若等史学家所言,也已经实行王有制:“周代的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殷代也应该是这样)”[22]25。岂止殷代,夏代亦然。因为如前所述:
五帝时代,原始共产主义向私有制阶级社会过渡是必然的,从而私有制的诞生是必然的。但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却不是庶民。因为,当其时也,中国是必须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国家及其政府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因而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国家及其政府所有(亦即国有制和公有制)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必然趋势——私有制与国有制或公有制都是必然趋势——势必造就一种独特的私有制,亦即全国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形式上是国家及其政府,实际上却是能够代表国家及其政府的首脑人物、国王:以国有制为形式的王有制是一种必然趋势。
因此,五帝时代虽然是原始社会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阶段,却不是向庶民私有制过渡,而是向一种极端的官有制——亦即王有制——过渡。夏代公认是完成了这种过渡,因而不仅是私有制,而且是一种独特的私有制:王有制。事实亦然。因为夏商周三代,中国仍然是必须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因而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势必仍然是能够代表国家及其政府的首脑人物:国王。
只不过,一方面,写成于东周的《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充分表明,至迟周代的土地所有制已经不是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形式的王有制,而是蜕掉了国有制和公有制形式,是内容形式一致的王有制,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极端私有制:国王一人所有制。
另一方面,夏代完成了原始公有制或国有制向私有制或王有制的过渡,特别是它所开始的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意味着不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形式的王有制——亦即赤裸裸的王有制——的建立:三代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内容与形式一致的王有制。
2官有制:夏商周土地经济权力所有制
夏商周全国土地归国王一人所有,似乎意味着:全国只有一个地主而不存在地主阶级。所以,郭沫若说:“《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在此以前的奴隶制下,中国是没有所谓‘地主阶级的。”[27]4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因为,如上所述,一方面,阶级是因权力垄断所导致的压迫与剥削关系而分成的不同群体:仅仅生产资料的垄断并不能造成——只有当生产资料的垄断转化为经济权力垄断才能造成——剥削与被剥削以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另一方面,因政治权力垄断而形成的阶级叫做官吏阶级(统治阶级)与庶民阶级(被统治阶级);因经济权力垄断而形成阶级则包括: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地主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中间阶级。
准此观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便是因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的垄断而分成的两大群体:地主阶级是垄断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的群体;农民阶级则是没有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的群体:既没有土地又没有经济权力而受雇于地主的农民叫做佃农;拥有小块土地而没有经济权力雇佣他人也不受他人雇佣的农民叫做自耕农。
因此,地主与土地所有者并非同一概念。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仅仅拥有土地却并不出租,因而没有支配耕作者和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那么,不论他有多少土地,他都不是地主而仅仅是土地所有者。只有当他以土地租给耕作者因而拥有支配耕作者和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时,他才是地主。另一方面,一个人,即使不是土地所有者,却因占有和出租土地,拥有支配耕作者和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那么,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地主是拥有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的人。
因此,夏商周虽然全国土地所有者只有国王一人,但是,地主却并不只有国王一人,而是整整的一个阶级,亦即由诸侯和卿大夫以及士所构成的官吏阶级。因为夏商周实行宗法封受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将土地授予诸侯,诸侯将土地授予大夫,大夫将土地授予士;至于士,则将土地直接出租给庶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28]
这就是说,只有庶民依靠耕种田地生活,而诸侯、卿大夫和士各级官吏则依靠占有所封受的土地而有权直接或间接征收庶民的租税贡赋生活:“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23]77这样一来,诸侯、卿大夫和士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却是土地的占有者和授予者,拥有向土地的接受者和耕作者收取地租或贡赋等经济权力,因而属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就是垄断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的群体。
夏商周三代,一般说来,诸侯、卿大夫和士都是官吏;而所有官吏也都是诸侯、卿大夫和士。因为,正如瞿同祖所言,当其时也,除了奴隶,所有人可以分为天子(国王)、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大群体:“大概地说来,当时的阶级,不外乎上下对立的两种。但细分起来,却可以分成许多级。最普通的是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级。《孝经·开宗明义章》后,便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这种分野,是当时的看法,并不是无意义的。《礼记》上叙说各种礼仪,总是分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大夫、士及庶人的。”[29]112
“诸侯”是治理诸侯国最大的官:“诸侯受封于天子,以治其国。”[29]118“卿”是仅次于诸侯的高官,高于“大夫”:“卿高于大夫,而卿自身中正卿高于副卿,正卿是所有卿大夫中最尊者,是诸侯以下的一人,是军政国政的支配指挥者。大夫受命于卿,以佐治国事,有二级,上大夫高于下大夫。”[29]121“士”是卿大夫之下的小吏:
士是介乎庶人与卿大夫间的一阶级,这是不容否认的。卿大夫是在上的统治者,庶人是在下的被统治者。士处于其间,到底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食于人者,还是食人者?有职业工作否?有赋役义务否?有官禄否?这些是一讲到士便会联想到的问题,若不解决,便不能明白士的地位功能了。我们首先应当明了两种士的分别。第一种是有官禄的小吏,居于卿大夫之下,以佐治政事。称为元士、上士、中士、下士。与另外一种称为“士民”,无官禄,与农工商三民同列称为四民的士,是不同的。 [29]118
然而,既然人有五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之分,既然“士是介乎庶人与卿大夫间的一阶级”,既然“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那么,按照分类的逻辑规则,“士”中就没有“庶人”,“庶人”中也没有“士”,因而没有官职官禄而属于“庶人”“庶民”的所谓“士民”,也就并不是士,而是“士的预备阶级”:
士民以学问为事,不耕不作,又无赋役,如何事上呢?大约诸侯卿大夫阶级都是武夫贵族,并没有很充分的治理知识,而且除了当时所谓大事——祭祀战事外,对于封邑及庶民的直接治理,都非他们所屑为,于是为卿大夫之佐的小吏——士,便有急切的需要了。这些士民便是士的预备阶级,致力于政事学问,以备诸侯卿大夫的擢用,或为家臣,或为邑宰。这便是以治术事上。学未成不为官,便是庶民,被擢用时,便可进而为士,以治庶民了。[29]127
于是,一方面,当其时也,人有五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凡是士都是官吏而皆非庶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构成官吏阶级;庶人——农工商和所谓“士民”——构成庶民阶级。另一方面,官吏阶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是垄断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的群体,因而就是地主阶级:夏商周的地主阶级与官吏阶级是同一个阶级、同一个群体。因此,周谷城说:
夏殷周三代的土地,不是无主的了。(二)主人是谁?统治阶级全体是也。 [30]43
统治阶级的全体固然就是地主;但这里的意思未免太含糊,不容易了解;需有较为具体的解释。具体的解释是怎样呢?约略言之,有下数端: (一)统治阶级的总头子就是一个大地主。《诗》云:“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又古语云:“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这都是我这里所谓统治阶级的总头子就是地主这一句话的正解。所以历来做官的、作家奴的,都称自己为吃皇家的俸禄。因为统治阶级的总头子已经富有天下,已经有了普天之下的土地,能从农民手里夺一部分生产品来养自己、养自己的家族、养自己的亲故,进而养成千成万的官僚。所以做官的叫吃皇家的俸禄,不叫做受小民的供养。 (二)一切特权者如宗室子孙被封而为王的,外戚亲故被封而为侯的也都是地主。统治阶级的总头子是一个地主。他的土地是普天之下的王土。这样大的土地,他怎样管得了呢?为事势所迫,把这大土地分割起来,除自己直辖一部分外,其余的便分给宗室子孙及外戚亲故等去经管。分有土地的宗室子孙,及外戚亲故等或叫做王,或叫做侯,名称复杂极了。所分的土地,或称王国,或称侯国,或称食邑;名称之复杂,更是令人头昏。宗室子孙,外戚亲故等都成了地主,都向农民夺取生产品。夺来之物,大部分养自己,作一切穷奢极欲之用。更分一小部分交给统治阶级的总头子,叫做纳贡。(三)一切大官僚也是地主。官僚所食之俸禄,原是统治阶级从人民手中夺来的。但吃俸禄的办法,有时不方便。于是把统治阶级的总头子,及宗室子孙外戚亲故等所管辖的土地之外,余剩下来的土地一块一块,划给官僚自己经管。这样一来,自然较为方便。土地是这样分给官僚的,名称也有种种不同。 [30]117-118
综上可知,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乃是官有制,完全归官吏阶级所有:一方面,土地是王有制,归国王一人所有;另一方面,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归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所有。对于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官有制,郭沫若论及井田制——亦即夏商周的土地制度——时曾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井田制的用意是怎样呢?这并不是如孟子所说的八家共井,以中央的百亩作为公家的田。周围的八个百亩作为给予八家老百姓的田。那完全是孟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化。那些方田不是给予老百姓,而是给予诸侯和百官的。诸侯和百官得到田地,再分配给农夫耕种以榨取他们的血汗而已。故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27]22
3工商食官:夏商周工商经济权力官有制
夏商周的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亦即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归国王及其官吏阶级所有,意味着:国王及其官吏阶级不仅垄断了全国全部政治权力,而且垄断了全国主要的经济权力,进而势必垄断全国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拥有控制国民的全权。试想,这样一个全权垄断的官吏阶级怎么可能放任与农业并列的另外两大经济部门——手工业和商业——而不垄断工商经济权力呢?更何况,即使国王及其官吏阶级仅仅垄断全国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也足以垄断全国工商权力。
事实确实如此。“工商食官”制度表明,夏商周实行工商经济权力官有制,国王及其官吏阶级不仅垄断了土地和农业经济权力,而且垄断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权力,从而也就垄断了所有经济部门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官有制。张岂之说:“商周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由官府控制。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官府作坊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产品和经营主要是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工商食官语出《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这里虽然讲的是春秋前期晋国的情况,但其制度却由来已久,属于商周旧制。‘工商食官按照三国时韦昭的解释:‘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百工和官贾为官府效力,其衣食住行由官府提供。”[31]
范毓周亦如是说:“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代一样,仍然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享用和战争需求,整个生产完全垄断在奴隶主贵族的官府争中,实行所谓‘工商食官制度。所谓工商食官制度,是指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工正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32]
郭沫若论及殷周工商业时也这样写道:“古代重要的工商业,都和农业一样,是官家经营的。‘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吕氏春秋·上农》)故殷、周的百工就是百官,《考工记》三十六工也都是官,是一些国家官吏管辖着各项生产工艺品的奴隶以从事生产。《周礼》在好些官职之下都有‘贾,地位与胥徒相当。到了春秋,齐桓公还‘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城市,晋文公时也还是‘工贾食官的。”[22]37-38
于是,总而言之,夏商周生产资料和经济权力所有制乃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私有制,亦即官有制,完全归官吏阶级所有:一方面,土地是王有制,归国王一人所有;另一方面,不但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亦即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而且工商经济权力也是官有制,因而全国所有经济部门的经济权力都是官有制,归官吏阶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所有。对于王有制和官有制的私有制性质,何兹全曾有所见:“周代土地所有制不是国有制,王有不是国有。周代的周王、诸侯、贵族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私有制,实质上就是贵族土地所有制。周王是最高的贵族,王有仍是贵族有。这种土地所有制是通过对氏族土地公有制的篡夺而出现的,它是公有制的对立物,是周代土地所有制的第一阶段。周王固然有土地,贵族也都有土地,每个贵族都把土地看作是他自己的。”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3
4关于夏商周所有制的几种理论———“国有制论”与“贵族所有制论”以及“王有制虚化论”
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经济权力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经济权力所有制以及工商经济权力所有制——极为复杂,堪称研究三代理论的首要难题。围绕这一难题,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已。这些争论,要言之,可以归结为四种观点:“王有制论”“国有制论”与“贵族所有制论(或领主所有制)”以及“王有制虚化论”。
王有制的代表有郭沫若、范文澜和吕振羽等。郭沫若说:“周代的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殷代也应该是这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都是王者所有,王者虽把土地和劳力分赐给诸侯和臣下,但也只让他们有享有权而无私有权。”[22]25范文澜说:“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土地接受者收回土地。”[23]77吕振羽说:“(武王)革命军在占领殷朝首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便一面解放奴隶,一面宣布土地为‘王所有。”[24]72
国有制论者大都将王有制与国有制混同起来,认为三代或殷周是土地王有制,亦即国有制。如认为西周是王有制的郭沫若又说:“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周代的诗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明的就是这种土地国有制的实际。”[27]3王有制论者张传玺也这样写道:“夏朝实行土地国有制……商朝亦实行土地国有制。”[26]62侯外庐似乎认为周代是形式国有制而实际贵族所有制:“在周代是土地国有制,即氏族贵族的所有制。王侯是贵者同时是富者,富贵是不分的。”[33]
何兹全、傅筑夫和瞿同祖堪称贵族所有制论、领主所有制或封邑主所有制论的代表。傅筑夫论及西周时说:“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等级不同的大小领主的。”[34]72瞿同祖说:“封邑主对于他的封地有绝对的私有权。”[29]77何兹全说:“周代土地所有制不是国有制,王有不是国有。周代的周王、诸侯、贵族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私有制,实质上就是贵族土地所有制。周王是最高的贵族,王有仍是贵族有。这种土地所有制是通过对氏族土地公有制的篡夺而出现的,它是公有制的对立物,是周代土地所有制的第一阶段。周王固然有土地,贵族也都有土地,每个贵族都把土地看作是他自己的。”[35]
王有制虚化论的代表主要是翦伯赞、冯天瑜、晁福林、张广志和李学功。王有制“虚化”一词即源于冯天瑜:“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于东周的此一著名诗句是对西周封建制的理想化表述,当时周天子对天下田土的掌控其实多是虚化的,孟子曾指出,这一文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36]23冯天瑜此言有歪曲孟子之嫌。且看《孟子》原文:“《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37]万章上显然,冯天瑜曲解了孟子。因为孟子“非是之谓也”指的是“莫非王臣”,而不是“莫非王土”。
王有制虚化论者大都认为殷周土地是名义上形式上是王有制,而实际上则是各级领主所有制抑或贵族所有制和村社所有制。翦伯赞说:“西周的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国王所有。国王以之分封于诸侯,诸侯以之分封于大夫,大夫以之分封于士;至于士,则以之直接分配庶人。这样便完成了土地之封建所有的实践过程。由于土地由上而下地一级一级分封下去,于是形成了各级的土地所有者。”[25]286-287晁福林说:“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之说,但实际上却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地土地所有制。” [38]张广志和李学功甚至认为王有制仅仅是个“形象的、象征性的说法”:
井田制下,由于国家的强力影响已渗入其中,因此,无论“公田” ,还是“私田” ,其所有权名义上都属于周王,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诗·小雅·北山》)是也。不过,这里需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此“王有”云云,实不过是个形象的、象征性的说法,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王有”,因为,没有任何魔力可以使“王” 把全“天下” 的土地划归他一个人账下,并予以自由支配——事实上,只有村社才牢牢地握有土地。 [35]52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或片面的。因为,如上所述,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完全归官吏阶级所有:一方面,土地是王有制,归国王一人所有;另一方面,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归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所有。
准此观之,贵族所有制论、领主所有制或封邑主所有制论的错误,一方面在于将“土地归谁所有”和“土地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亦即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归谁所有”混同起来,因而由“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归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共同所有的事实,误以为土地归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共同所有。
另一方面,贵族所有制论、领主所有制或封邑主所有制论是片面的和肤浅的。它片面,因为一般说来,所谓“贵族”“领主”或“封邑主”只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而不包括“士”;而“士”却拥有支配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因而与诸侯和卿大夫一样,属于地主或土地经济权力所有者范畴。它肤浅,因为它没有看到,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的本质乃是“官吏阶级”而不是“贵族”“领主”或“封邑主”:“贵族”“领主”或“封邑主”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更何况,唯有“官吏阶级所有制”才是——而贵族所有制和领主所有制以及封邑主所有制则不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特色。村社所有制论属于认为井田制是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学说。关于井田制的研究将表明,这种学说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井田制的“平分份地制”“公私田制”等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相同方面,亦即孟子所谓“分田”方面;而没有看到孟子所谓的“制禄”方面,亦即井田制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根本不同的方面:宗法封受制和王有制。
“国有制论”也不正确。因为政治权力控制公有制生产资料等国有资源,因而国有制是个相对的历史的不确定的概念。首先,民主国家每个人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因而完全平等地控制公有制生产资料等国有资源: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民有制或公有制。其次,专制国家意味着,专制者及其官吏阶级垄断了政治权力,因而也就垄断了土地等国有或公有制生产资料,成为垄断土地等国有生产资料阶级,致使国有制沦为官有制:专制国家的国有制就是官有制。最后,家天下的专制国家的国有制则意味着王有制。因为家天下意味着,天下一家,因而天下土地等一切皆归家长(国王)所有,正如家庭的一切财富都归家长所有一样。所以,邢义田说:“在‘家天下的时代,家、国不分,国一样被看成是家的私产。”[40]
可见,国有制是个相对的历史的不确定的概念:它的实质因政体不同而不同,既可以是全民有制(在民主制条件下),也可以是官有制(在专制条件下),还可以是王有制(在家天下专制条件下)。这样一来,说夏商周是国有制,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夏商周乃是家天下的专制国家。因此,精确言之,不能说夏商周是国有制,而只能说夏商周是王有制和官有制:土地王有制和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官有制。
王有制虚化论也是错误的。王有制并不是个形象的象征性的说法,而是具有前因后果的地地道道的事实。王有制产生的原因,如前所述,乃在于,夏虽然完成了原始社会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从而与商周一样实现了私有制;但三代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却不是庶民而是官吏,说到底,是国王。因为三代与五帝时代一样,中国仍然是必须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因而全国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势必仍然是能够代表国家及其政府的首脑人物:国王。这是三代王有制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三代王有制的证明。然而,万事万物有因亦必有果。王有制不但从其原因可以得到证明,更可以从其结果和表现得到证明。那么,三代王有制有哪些结果和表现呢?
三分封制:王有制和官有制的表现之一
1分封制:夏商周国家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土地所有制是王有制和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官有制,不但从其原因——治水社会——得到证明,更可以从其三大结果和表现——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井田制——得到证明。毋庸赘言,证明三代土地王有制的主要根据之一,正如朱本源所言,乃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分封制之实施即表示国王对全国土地之最高所有权已形成。”[41]107然而,细究起来,不但“分封制意味着王有制和官有制”需要证明,而且“三代是否都实行封建制”也需要证明。因为,很多学者,如瞿同祖,认为只有周代才堪称——而夏商则不是——封建制:“殷代末年已经入于封建的酝酿及形成时期;但全部社会组织还不曾封建化。直到周灭殷,以政治的力量实行封建,封建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才入于完成时期。”[29]28
此谬见也!因为,如前所述,分封制始于五帝时代。这里不妨再引证张传玺一段精辟论述:“尧舜时期已有同姓贵族分土封侯制,如帝挚封其异母弟尧(放勋)为唐侯。尧爱帝挚神位之后,又封其兄挚于高辛。舜封异母弟象于有鼻,为诸侯。《史记 五帝本纪 虞舜》载:‘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至夏朝,分封姒姓贵族为诸侯的更多。《史记· 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同书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记载:春秋后期的越王句践,就是禹的后代,他的祖先是夏朝国君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负责守护并祭祀禹的陵寝。”[42]
诚然,夏代与五帝时代的封建制具有古史传说性。但是,一方面,夏代与五帝时代土地王有制的某种历史必然性证明了当时分封制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王有制必然导致分封制。另一方面,商代封建制,正如冯天瑜所言,已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关于商代封建,司马迁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其封国仍以姓、氏为单位。殷商分封现有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为证。殷墟时期的甲骨文显示,殷商已有分封子弟之制,如商王武丁时有许多封国,封为侯爵的称‘候~(如封在雀地的称‘候雀),封为子爵的称‘子~(如封在宋地的称‘子宋)商代封爵有候、伯、子、男、任、田、亚、妇等数种。顾颉刚据此认为殷时已有系统的封建制。胡厚宣据甲骨文材料曾作《殷代封建考论》,论证封建制度至少始于殷高宗武丁之世。晁福林也经考索称:‘卜辞中有称子某的贵族九十余位,其中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周初发布的诰命中,有‘伊、‘旧、‘何、‘夫、‘儿、‘耿、‘肃、‘执诸姓,《逸周书商誓》称其为‘殷之旧官人,此八部族当为商朝分封的异性诸侯,周初继续受封。”[36]15
可见,夏商已行封建制,只不过行至周代更加完备罢了:“封建制成为完备制度,当在西周初年。”[36]16那么,为什么三代实行封建制就意味着:三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王有制和生产资料所转化的经济权力官有制?
2分封制意味着王有制和官有制
“分封制”与“封建制”,如所周知,是同一概念,就是封土建国,亦即帝王以土地分赐亲戚和功臣,使他们在该地建立邦国、诸侯国;诸侯在其封国、邦国再分封其子孙和其他贵族为卿大夫,领有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再分封其后代为士而领有土地;士则最后将土地分配于庶人耕种。翦伯赞论及分封制时曾这样写道:
国王以之分封于诸侯,诸侯以之分封于大夫,大夫以之分封于士;至于士,则以之直接分配庶人。这样便完成了土地之封建所有的实践过程。[25]286-287
但是,除了帝王,不论是庶人,还是士和卿大夫抑或诸侯,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私人独占着地体的一部分,把它当作他们的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一切其他的人去支配它。”[43]由此,诚如李埏所推论:
这样看来,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最一般的规定,就是上面已经引及的马克思所说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这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归谁所有”和“归谁支配”的问题。从这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占有制就由以判分了:假若拥有土地的人们,能够把他们拥有的土地“当作他们的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能够独占地、排他地支配它,那么,他们就是土地所有者,而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就是“土地所有制”;反之,假若他们虽然拥有土地,但不能对土地具备这样的支配权力,那么,他们就只能是土地的占有者;而这样的土地占有形式就是“土地占有制”。[41]25
准此观之,三代土地制度均为王有制无疑。因为不论是周代还是夏商,一方面,除了国王,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拥有的土地 “当作他们的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一切其他的人去支配它”,亦即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因而都没有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不论卿大夫还是诸侯,都不能出售其所拥有的土地:“田里不鬻”[44]。不但此也,诸侯和卿大夫等土地拥有者的土地转让也不准自相授受,而必须上报官府批准,在天子及其官吏参与和监督下完成。李学勤、李修松等学者曾引证有关西周金文,最终得出结论说:“土地的转让常须有三有司参加”[45]“贵族间的土地转让过程一般须在天子或政府官员的参与、监督下完成。”[46]
另一方面,三代土地制度为王有制,是因为唯有国王能将全国土地当作自己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一切其他的人去支配它,亦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分封全国土地给任何人,因而对全国土地拥有所有权。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国王对诸侯、方国和贵族的土地拥有支配权,可以随意将土地授予各级贵族,也可随意从受封者那里收回封地。杨升南引证甲骨文说:“商王对诸侯、方国和贵族所占有的土地拥有支配权。……商王下令从郑的边鄙上取走三个邑……这三个邑所领有的土地原本是郑候的,商王则派人将其取走,以归王室。”[47]66 特别是,杨升南还引证的众多甲骨文说:国王可以到全国各地任意圈占土地,建立田庄。[47]63
可见,分封制意味着,一方面,除了国王,任何人,不论是士还是卿大夫抑或诸侯都不能任意处置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因而都没有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拥有占有权和支配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国王可以像任意处置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任意且合法处置全国土地,因而对全国土地拥有所有权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如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因此,三代实行分封制就意味着:三代的土地是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国王及其官吏阶级所有制。所以,顾颉刚等学者均从“封建制的实质是王有制”出发来界说封建制:“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亲叫做封建,封是分划土地,建是建立国家。”[36]17台湾《中文扥大辞典》亦如是说:
封建时代,土地为国王所有,国王以之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之下有家臣,家臣之下为农民或农奴,如此层层相因,各阶级隶属之社会关系,谓之封建制度。[36]107
确实,封建制就意味着土地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封建制就是王有制和官有制必然的表现、标志和结果。试想,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土地皆归国王一人所有,他一个人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土地?他岂不势必将这些土地及其所蕴含的经济权力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姻亲功臣,亦即诸侯和卿大夫以及士:官吏阶级享有在民主制中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特权是专制统治的诀窍。所以,分封制或封建制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的必然表现。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这种土地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之典型表现,无疑是西周封建制度。因为西周封建虽有封先代之后、封有功异姓和封同性三种类型,但主要是后者:“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48]儒效《左传》干脆称西周封建是封建亲戚:“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49]可是,为什么受封诸侯大都是国王的儿子、兄弟和亲戚——因而形成宗法封建制——而天下不称偏焉?岂不就是因为全国土地原本归国王一人所有?范文澜对这种宗法制的封建所显示的王有制之本质曾有十分精辟的揭示: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候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滕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礼记·坊记篇》载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实际意义就是土地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 [23]75-76
四宗法国家:王有制和官有制的表现之二
1三代:一种宗法国家制度
证明三代土地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的另一个论据是三代的国家属于宗法国家范畴:王有制必定造就宗法国家;宗法国家就意味着王有制。因为王有制意味着国王拥有全国土地,意味着国王拥有支配所有国人的经济权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拥有全国土地的国王同时又是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国家元首。因此,国王不仅拥有支配所有国人的经济权力,同时还拥有支配所有国人的政治权力,进而无疑必定拥有支配所有国人的社会权力(如不准集会结社的权力)和文化权力(如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力):国王拥有支配所有国人的全权。
这样一来,三代的国家便与家庭相似,属于“准家庭”或“类家庭”范畴。因为家庭无疑具有三大特征。首先,所谓家庭,正如费孝通所言,乃是因性结合及其子女所形成的社会,是亲子社会,即父母及其子女所结成的社会:“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生出的孩子。”[50]这是家庭的定义,是家庭根本的非统计性特征:凡是具备这一特征的社会都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其次,家庭是以爱为基础的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社会。这是家庭的统计性特征,是由家庭的亲子关系特征所派生的特征。具备这一特征的非亲子社会,如某些早期基督教小团体,是准家庭或类家庭,因而可以被拟制为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以家庭称之的缘故。最后,家庭是一种领导者(家长)全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垄断的社会。这也是家庭的统计性特征,亦是由家庭的亲子关系特征所派生的特征。具备这一特征的非亲子社会是准家庭或类家庭,因而可以被拟制为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亦以家庭称之。
准此观之,三代的国家既然是国王全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垄断,那么,精确言之,便应该称之为“准家庭”“类家庭”,因而就可以像儒家等传统文化那样,将其拟制为“家”:“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51]这些准家庭的家长和家庭成员——君与臣以及官与民——亦可以像儒家等传统文化那样,拟制为“君父”“父母官”和“子民”等等。
因此,三代国家的国人相互关系——亦即君臣官民关系——便是一种父母与其子女的关系,一种家长与其成员的关系,精确言之,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和宗法关系;而三代的国家制度则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制度,一种父系家长制,精确言之,是一种宗法制度。诚然,“君父”“父母官”与“子民”这种非血缘关系是否属于宗法范畴?规范这种关系的国家制度是否属于宗法制度范畴?说到底,宗法系统是否包括天子和诸侯(亦即君统与宗统是否一致)?这个问题,正如刘家和所言,乃是至迟自汉代以来,学术界“分歧最大而至今犹在争论者”[52]解析这一难题的起点,无疑是界说宗法。
2宗法概念
“宗”的词源含义原本是尊从祖先神灵。《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段玉裁注:“示谓神也,宀谓屋也。”从字音来说,宗尊双声古通用。《国语·晋语五》说:“梁山崩,以传召伯宗。”《谷梁传·成公五年》则说:“梁山崩,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宗作伯尊:宗尊通用。《诗·大雅·公刘》亦云:“宗,尊也。”
“宗法”概念无疑源远流长。但是,“宗法”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北宋张载著作《经学理窟·宗法》开篇名言:“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构成“宗法”一词的“法”与“法则”显然是同一概念,包括规律和规则,亦即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价值规则。因此,朱熹认为“法”与“道”“理”“礼”几乎无异;即使有别,也难以说清楚:“‘道字、‘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此数说不知是同是别?”[53]
这样一来,宗法的词源含义也就是尊从(尊崇和服从)祖先的法则。宗子或父系家长和族长——宗子与父系家长或族长实为同一概念——正如《大传》所言,是祖先的代表:“尊祖故敬宗”。《尔雅·释亲》亦如是说:“父之党曰宗。”因此,宗法的词源含义可以进而引申为尊从父系家长或宗子的法则,因而宗法制度也就是尊从父系家长或宗子的制度:这就是宗法和宗法制度的定义。所以,钱宗范说:“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54]钱杭说:“宗法制度是父系宗族内部关于设立、行使、维护宗子权的一项制度。”[55]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西文宗法制与家长制是同一个词:patriarchy。
可见,宗法和宗法制度的实质乃是家庭——以及家族和宗族——的主从、统帅之法则。所以,瞿同祖说:“宗者主也,宗的本身即一种统率,宗子权即统率之权。”[56]吕思勉亦如是说:“宗与族异。族但举血统有关系之人,统称为族耳。其中无主从之别也。宗则于亲族中奉一人以为主,则男女必择其一。斯时族中之权,既在男而不在女,所奉者知情达理必为男。此即所谓始祖。继其后者,则宗子也。白虎通义曰:‘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是其义也。”[57]
3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主客观条件
宗法制度仅仅是家庭、家族和宗族——而不是国家——制度吗?否!诚然,就宗法制度的定义——宗法制度是尊从父系家长的制度——来看,宗法制度确实属于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范畴。但是,如果一种国家是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国王就是君父、大家长,那么,尊从这种君父、大家长的制度岂不也是一种尊从父系家长的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岂不也是一种宗法制度?这样一来,宗法制度岂不就是一种国家制度?岂不就是一种宗法国家制度?
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宗法制度都是一种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但是,并不是任何国家的宗法制度都能成为国家制度,成为宗法国家制度。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当且仅当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
客观地看,亦即就国家之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来说,该国家必须像三代以来的中国那样,国王及其官吏阶级垄断了全部权力,而庶民阶级毫无权力,因而一方面,该国家类似一个大家庭,属于“准家庭”范畴,亦即所谓“家国同构”;另一方面,国王及其官吏与庶民的关系,类似家长(拥有全权)与子女(毫无权力)的关系,属于“准亲子”范畴。
主观地看,亦即就国家之应该如何的人为制度来说,该国家的统治者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像儒家等传统文化那样,将三代以来这种“准家庭”国家拟制为家庭——“自国以致天下合为一家”[58]——因而将这些准家庭的家长(国王及其垄断各级郡县全权的官吏)和准家庭成员(庶民)的关系拟制为“君父”“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
当且仅当具备这两个条件,宗法制度就不但是一种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国家制度。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国王垄断了全部权力,因而该国家类似一个父家长制家庭,这种准家庭国家又进而被拟制为父家长制家庭,国人关系亦被拟制为“君父”“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那么,这种国家岂不就是一种宗法国家?国人相互关系岂不就是一种尊从父家长制的宗法关系?规范这种君父、父母官与子民的父家长制的国家制度,岂不就是一种尊从父系家长的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这样一来,国家制度岂不就成为一种家庭、家族和宗族的宗法制度?所以,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国王全权垄断和国被拟制为家——宗法制度就演进为国家制度,就成为宗法国家制度。
不难看出,国家成为宗法国家,宗法制成为国家制度,直接说来,虽然是主观人为的结果,是统治者和主流意识形态拟制、制定或约定的;但能否拟制和拟制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国家是否属于准家庭范畴的客观条件。因为所谓拟制,虽如德国法学家Karl Larenz所言,乃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59];但是,拟制或等同视之的前提条件,显然是不同者在某些根本方面相同,因而二者极其相似。举例说,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处罚。“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罪”虽然是两码事,但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极其相似,因而可以被拟制为抢劫罪。
同理,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国王全权垄断因而属于准家庭的客观条件,才可能被统治者和主流文化成功拟制为家庭。否则,一个国家,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国王仅仅垄断政治权力,因而不是一种准家庭国家,那么,这种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成功拟制为家庭。这样一来,这种国家的宗法制度就只能是一种家庭、家族和宗族制度,而不可能成为国家制度。所以,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客观条件(国家属于准家庭范畴)是根本的决定性的;而主观条件(准家庭国家被拟制为家庭)是派生的从属的。
然而,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客观条件——国家属于准家庭范畴——也仅仅是宗法制成为国家制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试想,那些实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埃及,与中国一样,国王全权垄断,因而都属于准家庭国家范畴,却都并不是宗法国家,不存在宗法国家制度。究其原因,岂不就是因为不具备将这种准家庭国家拟制为家庭的像儒家那样的主流文化?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斯大林一人全权垄断,苏联堪称准家庭国家,也具备了宗法制成为国家制度的客观条件,却也并不是宗法国家,不存在宗法国家制度。究其原因,岂不也是因为不具备将这种准家庭国家拟制为家庭的统治者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客观条件(国家属于准家庭范畴)与主观条件(准家庭国家被拟制为家庭)虽有主从之别,分别开来,却同为宗法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必要条件;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充分且必要条件。
4夏商周和秦汉以降:血缘宗法制与拟制宗法制
中国自五帝时代以降,特别是自三代以来,直至请末,虽有封建制与郡县制之根本不同,却始终具备宗法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主客观条件,国人关系始终是一种“君父”“父母官”和“子民”的宗法关系,国家始终是一种宗法国家,国家制度始终是一种宗法制度。对此,刘广明曾有所见:
一般说来,人们都将宗法制理解作父系氏族家长制。在外文中,宗法制和家长制也属同一个词patriarchy,在中文翻译中,既可译为宗法制,亦可译作家长制或父权制。毫无疑问,全世界的学者对宗法制(patriarchy)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patriarchy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宗法国家形态中。因为,宗法国家形态不是一种单纯的由血缘关系构成的父系家长制宗族形态,而是用血缘关系来表达政治关系,用政治关系来再造血缘关系的家、国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内容显然超出了patriarchy的规定,但是,由于patriarchy的原则构成了国家组织原则,所以,这种复合体又未超出patriarchy的外延,因而,将宗法国家形态视作宗法制的特例当是无疑的。[60]
诚然,作为国家制度的宗法制,五帝时代、三代与秦汉以至清末有很大不同。五帝时代和三代是土地王有制,全国土地归国王一人所有,国王能将全国土地当作自己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而排斥一切其他人的意志去支配它,亦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分封全国土地给任何人。因此,国王势必将全国土地主要分给自己的子弟和姻亲。就拿封建制的典型西周来说:
西周封建虽有封先代之后、封有功异姓和封同性三种类型,但主要是后者:“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48]儒效《左传》干脆称西周封建是封建亲戚:“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49]顾颉刚等学者亦均从“封建制的实质是封建亲戚”出发来界说封建制:“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亲叫做封建,封是分划土地,建是建立国家。”[36]17
因此,天子与多数诸侯的关系,便是同姓血缘宗族关系。那些被封的异性诸侯,如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等等,则通过“同姓不婚”等规范,大都与天子成为异性血缘宗族关系。于是,天子对于诸侯,正如《王制》所说:“同姓谓之伯父,异性谓之伯舅。”《诗经》亦如是说:“岂伊异人,兄弟甥舅。”诸侯之下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士或家臣,亦如此层层相因,遂使整个国家制度成为一血缘宗族关系之网,而天子则是血缘而非拟制的天下之大宗。所以,三代的国家制度是一种血缘而非拟制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的宗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秦汉以来,废除了土地王有制,土地也为国王之外的他人所有。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无疑归国王及其官吏阶级所有,因而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61]随着土地官有制取代王有制,全国土地不复为国王一人所有,封建制便失去了根基,遂被郡县制取代。因此,天子与郡县各级官吏关系,主要讲来,便不再是血缘宗族关系。
但是,一方面,全权垄断的国王及其官吏阶级类似父家长,毫无权力的庶民阶级类似家庭成员,国家类似家庭,属于准家庭范畴。另一方面,这种准家庭国家被统治阶级和儒家等主流文化拟制为家,而准家庭的家长(国王及其垄断各级郡县全权的官吏)和准家庭成员(庶民),则被拟制为“君父”“父母官”和“子民”。这样一来,秦汉以降,主要讲来,国人关系便是一种“君父”“父母官”和“子民”的非血缘的拟制的宗法关系,国王便是一种非血缘的拟制的天下之大宗,国家制度便是一种尊从君父和父母官的非血缘的拟制的宗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秦汉以来,“祀”仍然是“国之大事”。
综上可知,五帝时代以降,特别是三代以来,中国始终是一种宗法国家,中国国家制度始终是一种宗法制度。只不过,一方面,五帝时代,特别是三代,实行土地王有制和封建制,遂使国家制度成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天子是天下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之大宗。土地王有制并且只有土地王有制才能导致封建制,进而导致血缘宗法制:封建制和宗法制是土地王有制的结果和证明。另一方面,秦汉以降实行土地官有制和郡县制,遂使国家制度主要是非血缘的拟制的宗法制度,天子是非血缘的拟制的天下之大宗。土地官有制并且只有土地官有制,才能导致郡县制和拟制宗法制:郡县制和拟制宗法制是土地官有制的结果和证明。
准此观之,宗法系统是否包括天子和诸侯——亦即君统与宗统是否一致——的千古争讼,答案是肯定的。古代礼家和经学家认为宗法系统不包括天子和诸侯、君统与宗统为二的观点,显然缘于不晓得宗法有血缘与拟制之分,误以为宗法必以血缘为前提,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不存在宗法关系。那些认为作为国家制度的宗法制度仅仅存在于分封制时代的学者——如瞿同祖和金景芳以及岳庆平等——的错误,亦在于不晓得宗法有血缘与拟制之分,因而不懂得自三代以来,中国始终是一种宗法国家;不懂得三代是血缘的真正的宗法国家;而秦汉以降则是非血缘的拟制的宗法国家。说到底,这些谬误均在于未见宗法国家之根源乃是土地王有制和官有制:土地王有制为血缘宗法国家之根源;土地官有制为拟制宗法国家之根源。
五井田制:王有制和官有制的表现之三
井田制自孟子明确阐述以降,两千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以致胡寄窗“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井田是为国古代空想中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其内涵却又最为混乱的一个概念。”[62]59确实,井田制问题堪称中国史最混乱的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起点无疑是:究竟何为井田和井田制?
1井田制概念
所谓井田,不难理解,就是因划定疆界而由沟渠和道路分割成井字形状的田地;井田制则是将土地分割成井字或相当于井字形状的土地分配耕作制度。郑玄《周礼·地官·小司徒》注曰:“立其五沟、五途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亦如是说:“屋三为井,井之名命于疆别九夫,二纵二横如井字也。”但是,井田制的经典表述,无疑是《孟子·滕文公》:“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这就是说,按照井田制,一个井地共九块,每块一百亩,共九百亩。中间的那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农夫每家分得一块,八家农夫要先耕公田,再耕私田。然而,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因而当通行全国,普遍适用于各地。但是,全国各地土地情况千差万别,有河流灌溉的平原,也有山林沼泽地带,不可能都分割成九块合成、每块百亩的井字形状土地分配耕作。
不难看出,井田制正如杨宽所言:“一般只实行在有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63]123因此,孟子的井田制图式不过是井田制的一种具体的典型的理想的案例,而不是井田制的一般的普遍的制度。那么,井田制的普遍制度是什么?或者说,适用于全国的井田制之普遍形态是什么?说到底,井田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综观两千年来井田制的研究和争论,井田制的普遍或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授还田制度、农民份地平等分配制度、官吏土地宗法封受制、公私田制和贡助彻的税赋制。
2授还田制
井田制的前提和根据无疑是全国土地王有制。因为每人的井田都不是买来的,而是国王及其政府分配、授予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分配——而不是买卖——制度。《通考·田赋考》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鬻卖;故《王制》曰:田里不鬻。”所以,井田制的首要特点是授还田制。一般说来,农夫二十岁受田,六十岁仍还之于政府。《周礼正义·载师》云:
案受田之年,经无明文。贾据郑《内则》注义谓“三十受田”。《后汉书·刘宠传》李注引《春秋井田记》同。而《汉书·食货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则样郑说早十年。陈奂云,“古者二十受余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归田于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归田,乃子受田矣。”案陈足证郑义。
3农民份地平均分配制度
郭沫若认为井田制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用课验勤懒的计算单位。”[27]22郭沫若此言能否成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帮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37]滕文公上何谓分田制禄?林甘泉说:“孟子谈到了施行井田制的用意在于‘分田制禄。所谓‘分田,就是对农民授田;‘制禄则是以井田作为各级贵族的禄田。”[64]诚哉斯言!井田制的实质,亦即作为一种土地分配制度,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分田”,亦即农民、庶民份地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制禄”,亦即“以井田为各级贵族的禄田”,更确切些说,是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官吏阶级封地的分配制度。
考古学表明,夏商周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三个平行的国家:“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个国家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间的势力消长各代不同便是了。”[65]87这样一来,夏商周不但离原始社会不远,甚至都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因而农民份地分配仍然沿袭农村公社传统,实行平均分配原则,杨宽称之为“井田制中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制度”[63]124。平等分配份地的具体方法因地形沟洫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无疑如孟子所云,将土地划分成井字,每块百亩,每个农夫一块。这种“等长直线内包括的地块”,正如拉法格所指出,最能体现平等精神:
在原始人学会以底乘高来测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之前,因而也就是在他们学会比较平行四边形之前,每个家庭分得的土地块只有包括在等长的直线之内,他们才会感到完全满意;他们用同样的木棍在土地上度同样的次数而得出这些直线……等长的直线内包含的地块满足了平等精神和不给纷争留下余地。因此,划直线是测量的重要的部分;一旦直线划定,家长就会满意,他们的平等感情得到完全满足。[66]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论及农村公社平等分配份地原则时指出,这种平等分配的份地所组成的耕地是棋盘状的:“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67]452
可见,将土地划分棋盘状以及与之类似的井字形状的目的,除了沟洫灌溉,更根本的,乃在于平等分配:平等分配份地是井田制的根本制度。所以,《国语·齐语》记述管仲说:“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大戴礼记·夏小正》亦云:“农率均田”。井田制之均田制精神,正如杨宽所言,尤其表现在它的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办法:
井田制度,有着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办法。这种办法,古时叫做“换土易居”,或者叫做“田易居”。《说文解字》解释“”字说:“田易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何休这个说法,得到了近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田法》的证实。《田法》称:“三年壹更赋田”,“赋”是授予之意,“一更赋田”就是说要一律更换授予的田亩。何休所说“三年一换土易居”,就是古代村社中定期分配份地的制度。何休所说“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就是以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为标准,把土地分为三等的品级,上田是年年垦耕的,中田是二年轮流垦耕和休耕的,下田是三年中垦耕一年而轮流休耕二年的。所谓“肥饶不能独乐,硗确不能独居,”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平均垦耕品级不同的的田地,平均大家劳动生产的条件。[63]127
4宗法封受制和公田私田制
井田制中无疑蕴含对于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官吏阶级的土地分配原则:宗法封受制。因为三代是土地王有制,全国土地归国王一人所有,国王能将全国土地当作自己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而排斥一切其他人的意志去支配它,亦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分封全国土地给任何人。因此,国王势必将全国土地主要分给自己的子弟和姻亲。这样一来,天子与多数诸侯的关系,便是同姓血缘宗族关系。那些少数诸侯,亦即被封的异性诸侯,如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等等,则通过“同姓不婚”等规范,大都与天子成为异性血缘宗族关系。诸侯亦如此这般将土地授予大夫,大夫亦如此这般将土地授予士,如此层层相因,遂使整个官吏阶级的土地封受制度成为一血缘宗族关系之网,因而可以称之为宗法封受制。
在这种宗法封受制的土地分配制度下,国王将土地授予诸侯,诸侯将土地授予大夫,大夫将土地授予士;至于士,则将土地直接授予庶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28]这就是说,只有庶民依靠劳力种田生活,而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级官吏则不劳力种田,依靠占有土地而拥有征收农夫贡赋的经济权力而生活:“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23]77
当其时也,最重要的贡赋无疑是劳役地租。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级官吏授予下级土地同时,都留给自己及其所辖政府一定的土地,亦即所谓“王田”“籍田”“禄田”“官田”。这样一来,全国土地便分为两类:一是农夫的份地,叫做“私田”;一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级官吏及其政府的土地,叫做“公田”。张传玺论及井田制的公田与私田之剥削方式便这样写道:
这种剥削方式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农奴)无土地权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剥削的义务。具体剥削方式,是贵族们将田地分为两类,一类为贵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属农奴们集体无偿代耕,就是劳役地租。另一类大致以百亩为单位分给农奴各家耕种,收获物归农奴所有。[26]62瞿同祖通过比较中英公田而定义公田与私田:“所谓公田,便是封邑主自己划出来的一部分田土。公者,便是主人的意思,和英国封建社会所谓公田(Lordsdemesnc)相仿佛。私田便是分给农民耕种的土地了。”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82
农夫、农奴或庶民的份地叫做私田。所以,《毛传》云:“私,民田也。”私田就是民田,就是农夫、庶民的份地,毫无疑义。但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级官吏及其政府的土地为什么叫做公田?一方面,恐怕是因为这些土地都是农夫们共同耕种、集体耕作的耕地;共同耕种的田地,相对于一个人自己耕种的田地来说,可以称之为公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凡是国家和政府及其代表——官吏——都叫做公家和公家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叫做公家的东西或公家人的东西,因而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级官吏的田地都叫做公田。对此,长野郎曾有所见:
自古以至秦代,凡政府所有的东西,都不叫做“官”,而叫做“公”,政府的所有地,也就叫做“公田”,所以中国古代的土地观念是公有的。[68]
5贡、助、彻
“贡”“助”和“彻”是井田制的三种赋税制度。《孟子·滕文公上》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何谓贡?贡的本义是奉献。《说文解字》:“贡,献功也。”段玉裁注引《国语·鲁语》:“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衍则有辟,古之制也。”韦昭注曰:“社,春分祭社也。事,农桑之属也。冬祭曰蒸,蒸而献五谷布帛之属也。”可见,贡就是奉献农业生产物。因此,作为赋税,贡就是农业生产物地租,亦即实物地租,税率为什一,也就是收成的十分之一,说到底,则如龙子所言,乃是若干年收成年平均量的十分之一。
何谓助?孟子答曰:“助者籍也。”朱熹注曰:“籍,借也。”郑玄《考工记·匠人》辨析助贡之异同说:“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谷;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可见,所谓助,也就是劳役地租。助与贡都行什一之税:“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以七亩助公家。”[69]但是,贡是定租制,不论年景如何,税额不变;助是分租制,税额随年景丰歉而变化。所以,孟子援引龙子的话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
何谓彻?彻的含义很多,但作为税法,无疑可以训为“通”。郑玄注《论语·颜渊》曰:“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也。”朱熹亦曰:“彻,通也,均也。”[39]57可是,究竟通什么呢?地租无非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货币地租。贡是实物地租,助是劳役地租。彻不可能是货币地租,因而必定属于贡与助——亦即实物地租与劳役地租——范畴,只不过与夏商的贡助有所不同、有所改进罢了:彻是经过通盘核算而改良的贡与助。因此,彻之为通,正如宋儒杨时所解,亦即通贡助:“彻者,彻也,盖兼贡助而通也。”[39]56那么,彻究竟在哪方面改良了贡助?姚文田答曰:
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此其与贡异处。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无烦更出敛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尽力于公田者,帮周直以公田扫授八夫,至敛时则巡野观稼,合百一十亩通计而取其什一,……民自无公私缓急之异。此其与助异处。……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39]57
可见,彻是经过通盘核算而改良的贡与助:通年之丰凶而改良贡法;通田之公私而改良助法;通地之肥硗而改良贡助。
综上所述,井田制乃是一种土地分配——而不是买卖——制度,包括三方面:(1)官吏阶级土地的宗法封受制度;(2)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度,这种制度的外在形式和典型手段是将土地分割成井字形状;(3)官民的土地关系制度,亦即授还田制和公私田制以及贡助彻的税赋制。将土地分割成井字等形状是井田制的外在形式和典型手段;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和官吏阶级的土地宗法封受制是井田制的核心;授还田制、份地平等分配制、宗法封受制和公私田制以及税赋制是井田制的基本内容。
因此,所谓井田制,简言之,乃是一种将土地分割成井字等形状的平等分配农民份地的土地分配制度;要言之,乃是以官吏阶级的土地宗法封受制和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为核心的土地分配制度;精确言之,乃是以授还田制、宗法封受制和公私田制以及税赋制为基本内容的将土地分割成井字等形状的平等分配农民份地的土地制度。
6井田制:王有制及官有制的结果和表现
不难看出,井田制之全国土地分配——而不是买卖——制度,特别是官吏阶级土地的宗法封受制和庶民阶级份地平等分配制度以及授还田制、公私田制,意味着:井田制是——并且只能是——王有制的必然结果。因为王有制意味着:任何人——除了国王一个人——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土地买卖:土地买卖以卖者拥有土地所有权为前提。国王能够卖这些土地吗?也不可能。如果国王出卖土地,全国土地就不是王有制了。可是,国王一个人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土地?他除了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国人又能怎样呢?所以,土地分配——而不是买卖——制度是王有制的必然结果。那么,国王将怎样分配土地给国民?他势必实行以官吏阶级的土地宗法封受制和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为核心的井田制:
一方面,他势必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姻亲、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等大都通过联姻而与国王结成异性血缘宗族关系)等官吏阶级——官吏阶级享有在民主制中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特权是任何专制统治的决窍——使其拥有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从而成为地主阶级,通过公私田制和贡助彻等税赋制度,共同瓜分农民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他势必沿袭农村公社农民份地平均分配传统,使庶民阶级每个农民都有平等的份地耕种,从而平等地上交税赋,平等地为国王及其官吏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7这种平等分配份地制度的外在形式和典型手段是将土地分割成井字形状。
可见,不但井田制的根源乃是土地王有制:井田制是并且只能是王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且井田制是土地经济权力官有制的表现:井田制意味着只有官吏阶级——天子和诸侯卿大夫以及士——拥有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诚然,土地国有制和公有制——特别是农村公社所有制——也必定实行土地分配而不是买卖制度,特别是必定实行平等分配份地、公田私田等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与井田制形似神异,根本不同。因为在名副其实的国有制、公有制和农村公社所有制条件下,一方面,所有公民对于土地拥有平等权利;而不可能像井田制那样实行土地宗法封受制度,国王及其主要由其子弟姻亲构成的官吏阶级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等一切权利,而农民只有耕种的使用权,存在着官吏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
另一方面,在名副其实的国有制、公有制和农村公社所有制条件下,公有地是同等属于所有人、所有国民的土地,是所有人同样享有的公用地,对于公有地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完全平等;而不可能像井田制那样,公田乃是国王、诸侯、卿大夫等官吏阶级的籍田、禄田,由农民无偿耕种,以劳役地租的形式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
可见,“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等公有制或国有制的土地制度,虽都平均分配份地,但农村公社土地权利人人平等,而井田制官民土地权利却极端不平等:国王及其官吏阶级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等一切权利,而庶民只有耕种的使用权。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于所有制:公有制导致土地权利人人平等;王有制则必定导致土地权利极端不平等,必定导致宗法封受制为其实质的井田制。一言以蔽之曰,当且仅当王有制,才有宗法封受制为其实质的井田制:井田制是王有制的必然结果和证明。这意味着,井田制不但必定是夏商周——三代均为名副其实的王有制——的土地分配制度,而且必定与王有制、分封制同时诞生而开创于五帝时代;因为五帝时代土地所有制是以国有为形式的王有制。唐代杜佑《通典》曰:
昔黄帝始终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设井于中。一则不洩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门讼之心耳。既牧之于邑。帮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70]1
诚哉斯言!因为五帝都是黄河流域的部族领袖,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皆建都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土壤富饶,是拥有只能由政府统一兴建的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辽阔平原。在这种平原平等分配份地的最适宜的方法,无疑是由沟渠和道路将田地分割成井字形状。因此,五帝时代黄河流域所开创的,可能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将田地分割成井字的平均分配份地的土地制度,因而名之为“井田制”。
尔后,这种名为井田制的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势必推行全国,虽然各处田地形态千差万别,特别是山林沼泽崎岖等地带,更是不可能分割成井字,却必定如《汉书 食货志》所云,因地施宜,通过其他方法实现井田制的平均分配份地等原则:“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金鄂《井田考》讲得就更清楚了:
窃谓古者地广人稀,田不尽井,随处皆有间田余地,授莱田取之于此,圭田及余之田亦取之于此。且生齿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给,亦取于此以授之,每夫百亩,不必尽为井田之制也。……是知井田之制,不必尽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广野,可作数井,数十井或百井则为一通一成之制,尽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险阻之地,或止有九百亩,但为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亩,其田不能成方,则但以方田计之,以九百亩为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皆不为一通一成之制,心方如棋局,沟洫亦随地为之,不必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不浍也。[71]340
这种不是将田地分割成井字的平均分配份地的方法,仍然叫做井田制。因为井田制之所以叫做井田制,是因为开创于灌溉平原的这种制度最初将田地分割成井字;但是,井田制之所以为井田制——亦即井田制的本质——则与其名字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以授还田制、宗法封受制和公私田制以及税赋制为基本内容的将土地分割成井字等形状的平等分配农民份地的土地制度,是源于王有制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创始于五帝时代而通行于三代的土地分配制度。
7井田制学说:孟子理想说和封建庄园说以及农村公社土地制度说
学术界围绕井田制所形成的三大流派——孟子理想说和封建庄园说以及农村公社土地制度说——看来都是不能成立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说的代表有杨宽、徐中舒、金景芳和徐喜辰等学者。该派认为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徐喜辰说:“井田制就是古代公社所有制。”[72]金景芳说:“井田制的本质特点正在于把土地分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73]“井田制是农村公社的一种表现形式。”[74]杨宽讲得就更清楚了:“我国春秋时代以前确实存在整齐划分田地而有一定亩积的井田制度,并且确实存在平均分配‘百亩份地的制度。在井田制度中,既有集体耕作的‘公田,又有平均分配给各户的‘私田(份地),‘私田又有按一定年龄的还受制度,这无疑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63]120
农村公社土地制度说是错误的。因为井田制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根本不同。井田制的土地所有制是王有制,而农村公社土地是公有制:“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75]68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农村公社所有社员对于土地拥有平等权利[67]359;而不可能像井田制那样实行土地宗法封受制度,国王及其主要由其子弟姻亲构成的官吏阶级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等一切权利,而农民只有耕种的使用权,存在着官吏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农村公社土地制度说的错误显然在于片面性,只看到井田制的“平分份地制”“公私田制”等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相同方面,亦即孟子所谓“分田”方面;而没有看到孟子所谓的“制禄”方面,亦即井田制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根本不同的方面:宗法封受制和王有制。
孟子理想说的代表有胡适、万国鼎、李亚农、齐思和、瞿同祖和胡寄窗等学者。该派认为井田制不过是孟子的理想制度。胡适说:“不但‘豆腐干块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也是不可能的。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76]万国鼎认为西周实行采地制:“采地制既有公私田之分,及藉而不税之制,私田授之庶人,当亦不无授还法之规定,其形式绝类所谓井田制。然有一根本不同之点在。儒者所以歌颂井田者,为其均贫富也。而采地制则为领主压迫农奴,榨取利益之一种制度。周既以力服商,对于被征服者,谓其将如儒者所传,採用理想的均贫富之井田制,谁实信之。余于上文曾论西周庶人终岁勤劳而穷困,较之领主之安闲快乐而有食,诚有天渊之别。然则此为儒者所钦慕之井田制度下之农民生活哉!即此可见井田论之非事实矣。”[70]55-56
胡寄窗说:“孟轲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最混乱的空想。既是如此不合理的空想,何以在过去二千年中还不时被人们所向往呢?中国的封建经济在战国时代已开始土地自由买卖。因此,土地兼并成为经常伴随出现的土地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广大无地农民均切办好有小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之出现,甚至封建统治集团也未尝不愿意有某种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免农民流亡藉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的基础。井田制正好是先秦出现的唯一小土地平均分配空想,尽管是望梅止渴,却适应了这一期望。”
齐思和则通过列举井田制什一税不符合古代农民实际上的籍、赋、役之繁重负担等问题而得出结论说:“井田制之为孟子之理想,似无问题。不过,孟子此种理想,自亦有所依据。”[71]345依据什么呢?齐思和的回答是:中国古代庄园制度。然而,中国古代庄园制度“典籍缺略,已难详征。西洋庄园制度之废除,不过近百余年前事。其制虽各时各地,并不相同,而其基本原则,固无二致。”[71]345于是他略述西洋庄园制度,之后说道:
吾人试以此与吾国古代之庄园制度相较,则其农田有公田、私田之分,以及其农民与庄主间之关系,与中国古代之所谓“助法”,根本相同。其私田之划分,虽较《孟子》所称者为苛碎而较全实际。其时农民负担之重,工作之繁,亦与《 风》所述者略同。然则助法乃封建制度下田制之通则,孟子不过于此等制度,加以理想化,整齐化,将之由虐民之制,变为“仁政”之基。后儒不知其然,遂以此为三代田赋之通制。[71]347
可见,孟子理想说的主要依据乃在于:井田制的均田(均贫富)制与仕一税不符合籍、赋、役税负繁重的农民穷苦生活之实际,因而不可能是三代之事实,只能是孟子之理想。这一根据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方面,井田制的核心是分田制禄,亦即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分田)和官吏阶级的土地宗法封受制(制禄):国王及其官吏阶级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等一切权利,庶民阶级每个农民则只有平等的份地耕种权利,从而平等地上交税赋,平等地为国王及其官吏阶级创造剩余价值。试问,这怎么是均田制和均贫富?胡适、万国鼎和齐思和等学者断言井田制是一种均田、均贫富的制度——因而只能是孟子的理想——显然是错误的片面的:只看到井田制之庶民阶级份地的平等分配制(分田)而抹煞其官吏阶级的土地宗法封受制(制禄)。
另一方面,井田制是王有制的产物,诞生于五帝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代。当其时也,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国有为形式的王有制,农民所能接受的无疑只能是一种与农村公社相差无几的税负:什一税。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23]77特别是,五帝时代专门的正式的独立的常设的官吏还刚刚产生,人数必定极少,什一税足以使其生活远远高于庶民。三代实行什一税亦不奇怪。因为考古学表明,夏商周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三个平行的国家,[65]87都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因而税负若与农村公社相差不多,何怪之有?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正如王玉哲所指出,当时乃銅石并用或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什一税差不多是农民所能负担的极限:
有人怀疑孟子所说的这种什一而税的制度,以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这样轻微的剥削,并由此怀疑孟子到井田制度的存在。这是没有从历史主义上看问题。十分之一的租税,若在生产力很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确是极低微的剥削,但是,西周是从氏族社会刚过渡到初期封建社会,生产力虽然比以往有所提高,但还是很原始的。一个劳动者的所获,若被剥削十分之一,其所剩下的除了他本人生活之外,也不会再有多大富余。战国初年李悝曾根据当时魏国的农民的收支及生活,做过一次计算。他说五口之家的一个农夫耕田百亩,除了什一之税及其吃饭穿衣祭祀等必要开支,每年要亏空四百五十钱。战国初年生产力已比西周提高了很多,农民负担什一之税,尚且如此吃力,西周的情形,就可从这里逆推了。所以说十分之一的税,具体到西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看,并不能说是极轻微的剥削。从而也就不能怀疑孟子所说的为“幻想”了。[77]
更何况,与春秋战国秦汉以降拟制而非血缘的宗法国家——因而拥有庞大臃肿的官吏阶级——根本不同,三代是血缘的真正的宗法国家,官吏阶级主要由国王子弟姻亲构成,人数极少,不过是国王、诸侯、卿大夫和士而已。因此,什一税亦足以维持官吏阶级远远高于庶民阶级的生活水平。这些恐怕就是为什么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会实行什一税的井田制。万国鼎和齐思和等学者认为什一税不可能是三代之事实而只能是孟子之理想,显然是根据春秋战国秦汉以降的税负推断三代税负的结果。
封建庄园说的代表主要是傅筑夫。该说认为井田制“类似于欧洲庄园制度”[34]67,是一种封建庄园土地制度。傅筑夫说:“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度,而井田制度又是与欧洲的庄园制度基本相同的,因为两者都是适应着农奴制的剥削而产生的。只要剥削关系是农奴制剥削,则与之相应的土地制度必然是井田制度。”[34]83齐思和虽是“孟子理想说”的代表,但如上所述,他断言井田制是孟子理想的依据,却与“庄园说”相同,认为中国古代必定存在与欧洲大同小异的庄园制度:“孟子不过于此等制度,加以理想化。”[71]347
井田制与欧洲庄园制度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公田和私田、劳役地租,特别是农民份地平均分配原则。胡寄窗曾根据“庄园制下的份地基本上是条形,并不正方,更非井形”[62]65否定封建庄园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庄园制的条形份地与井田制的井形份地实质完全相同,都遵循平均分配原则。
原来,英法德所代表的西欧世界开拓者的祖先,主要讲来,乃是古代日耳曼人。英法德等封建制国家没有经过奴隶制而直接由古代日耳曼人的马克公社转化而来,因而其庄园制与中国井田制一样,沿袭公社平均分配份地传统。只不过,这种平均分配的份地的形状是条形而不是井形罢了。对此,马克垚论及庄园制农民份地分配原则时曾有说明:
各户的耕地,甚至领主自营地,都并非完整的一块,而是作为一些狭长的条田,分散分布在各大块之中。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中,各户都有一份,土地肥瘠、高低、便利与否等等,大体相当,体现出一种平等倾向……这样一种土地分配办法,究竟是怎样来的?长期成为研究和争论的话题。自公社说建立后,方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78]267
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像傅筑夫那样得出结论说,井田制是一种封建庄园土地制度?或者是否可以像齐思和那样,断言井田制是庄园制的理想化?否!因为井田制的核心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分田”,亦即农民、庶民份地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制禄”,亦即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官吏阶级封地的分配制度。就农民份地分配制度来说,井田制与庄园制虽然相同;但就封地的分配制度来说,却根本不同:
井田制的土地封受制度是一种王有制的家天下的宗法国家制度,封地的封授者和受地者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是官吏阶级;这些官吏相互间是血缘宗法关系:同姓血缘宗族关系或异性血缘宗族关系。相反地,庄园制的土地封受制度并不是国家制度,更不是宗法国家制度,而只是任何两个人就土地授受所达成的封君与封臣之利益交换关系的契约:土地授予者为封君;土地接受者为封臣。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句名言: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对此,马克垚说得很清楚:
西欧封建君臣关系并非国君与臣民的关系,而是封建主个人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学者说它属于私法范围,而不属公法范围。当西欧的大小封建主,彼此都结成这种关系,形成十分复杂的等级连锁,直接影响到其对土地的权力。这种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两个人,在上的是封君,在下的是封臣。[78]101
因此,冯天瑜分别称西欧和中国的封建制为“契约封建制”与“宗法封建制”:“西欧的feudalism,本为一个契约形态的法律术语,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所以,西欧的feudalism可称之‘契约封建制。与之相比照,中国西周的封建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的控制(当然又以武力征服、军事镇慑为实行控制的基础),故可称之‘宗法封建制”。[36]113
可见,井田制与庄园制,就农民份地分配制度来说,虽然相同,都是平均分配;但就封地制度来说,却根本不同:井田制的封地制度是整个官吏阶级宗法封受制,而庄园制的封地制度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封受制。所以,不论傅筑夫认为井田制与欧洲庄园制度本质相同,还是齐思和断言井田制是庄园制的理想化,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有见农民份地平均分配之同,而无见封地宗法封受制与契约封受制之异。
六夏商周社会形态:生产资料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的封建社会
综合夏商周王有制、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的研究,不难看出,三代的社会形态乃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生产资料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的分封制的和宗法制的非农奴制封建社会。但是,这一结论却关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而该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七十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恐怕是凝结学者心血最多但也争议最大的跨世纪难题。难题的症结何在?张广志曾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感慨言之:
七十多年来那么多学者的心血汗水换来的不是问题的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而是分歧的僵持和进一步扩大。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我看来,是由于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走入误区,至今仍深陷误区而难以自拔。中国本来并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你在那里先设定中国有个奴隶社会,再以此为前提支进行什么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讨论,岂不荒唐,岂不白白耗费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多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心血。[79]
诚哉斯言!中国古史分期争议的核心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而关键则在于中国究竟有无奴隶社会。这些问题的焦点,正如刘家和所言,又可以归结为奴隶制与农奴制以及奴隶与农奴的区分:“古史分期问题,亦即奴隶制与农奴制区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而论,目前争论之点也很多。但就最根本处而言,争论焦点大抵不外以下两类:一种是对同一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是奴隶制或农奴制)看法不同,因而产生论点的不同;另一各是对同一社会的同一阶级的性质(是奴隶或农奴)看法就不相同,这当然就更不可能得出同一结论了。”[80]那么,奴隶制与农奴制以及奴隶与农奴的区分究竟何在?破解这一难题的出发点恐怕在于:奴隶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1奴隶和奴隶制经济形态
奴隶产生的途径虽有很多,但最早最主要的来源无疑是战争俘虏。因此,《查士丁尼法典》在界定奴隶时这样写道:“奴隶(Servi)一词是指将领们命令把俘虏出卖,于是他们的生命得到解救而不被杀掉。奴隶又叫‘Mancipia,因为他们是被我们从敌人那里抓来的。”[81]235原来,当原始国家由游群进化到部落,复由部落达于酋邦时,虽然仍处于农耕和畜牧阶段,但其生产专门化的程度较高,以致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金属劳动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生产较多剩余产品,形成一种财产私有和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
这样一来,一方面,战争的胜利者便不再屠杀俘虏,而使其变成能够为自己生产剩余产品的奴隶,也就是使俘虏的人身不属于俘虏而完全为自己所有,成为自己的一种如同牛马一样的财产。另一方面,对于俘虏来说,与其被杀死不如成为战胜者的财产而活下来。因为变成战胜者的牛马一样的财产或奴隶固然是恶,自己的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完全为战胜者所有固然是恶;但是,被杀死岂不是更大的恶?更何况,奴隶还有被释放而重获自由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奴隶:一种自己本人成为他人财产而可以买卖的人,一种自己的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完全为他人所有的人。因此,马克思赞成瓦罗所记载的古人的观点,奴隶与牛马、牲畜一样,属于主人可以买卖的农具、生产资料或财产范畴:“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82]罗马法亦承认:奴隶“违反自然权利沦为他人的财产。”[81]223
可见,奴隶就是自己本人成为他人财产而可以买卖的人,是自己的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完全为他人所有的人;奴隶主是奴隶的主人、所有者,是完全占有他人的人身而使其如同农具、牛马一样为自己所有的可以买卖的人;奴隶制则是国家制定或认可战俘等应该成为战胜者财产的规范体系,亦即使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财产的制度。所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奴隶制词条的定义是:“一人是另一人的财产的制度[83]。举例说,罗马法规定:“如果我们的东西落到敌人(hostes)或落到与罗马没有结盟(foedus)关系的某个国家手里,则均变成他们所有,如果我们的自由人被他们抓获,则成了他们的奴隶。当他们的人落到我们手里时,情况也是如此。”[81]236这一法律就是一种奴隶制度。
可是,一方面,按照影响深远的斯大林的定义,奴隶之所以为奴隶,不但在于他的人身被完全占有,而且在于他可以被屠杀:“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底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84]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奴隶没有财产权,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经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85]。
诚然,奴隶与牛马一样,属于主人的财产而完全为主人所有。因此,在某些奴隶社会,特别是奴隶社会初期,便有这样的法律,使奴隶的生命和财产,与牛马的生命和“财产”一样,皆为主人所有,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生杀权和财产权:
查士丁尼法律规定:“奴隶处于主人的权力之下,这种权力渊源于万民法,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哪个民族,主人对于奴隶都有生杀之权(vitae necisque potestas),奴隶所取得的东西,都是为主人取得的。”[81]233
布洛赫亦如是说:“奴隶在法律上仍然是主人的有生命的财产,主人对奴隶的人身、劳动及其财产拥有不受限制的处理权。”[86]这种法律无疑是恶法,在这种法律下,可以屠杀和没有财产权确为奴隶之所以为奴隶之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牛马等牲畜虽然为主人所有,主人也不可任意对待;否则将受到诸如动物权利法律——良法——之惩罚。牛马尚且如此,何况奴隶!古代希腊和罗马奴隶制时代都曾出现禁止奴隶主虐待和杀害奴隶的法律:“公元75年,韦斯帕芗立法规定:‘凡被主人强迫为娼的女奴,应得自由。公元90年,图密善立法,禁止伤害奴隶肢体并使之致残。哈德良则禁止售卖奴隶为角斗士,禁止杀害奴隶。他对奴隶主翁布里启娅(Umbricia)因极细小的原因而极其残酷地处置奴隶表示强烈不满,下令将其放逐5年。”[81]246因此,可否杀害并非奴隶的特征:不但不可杀害的人可能是奴隶,而且可杀害的人也并不都是奴隶,如人殉、人祭者无疑不都是奴隶,战俘可以杀害,并非奴隶,希特勒时代犹太人可以杀害,也不是奴隶。
另一方面,在某些奴隶社会,特别是在奴隶社会初期,奴隶确实没有财产权,没有自己的经济,因而如马克思所指出:“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87]590“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人劳动一次而永远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却不是他的商品。”[88]但是,这种没有财产权和自己的经济的奴隶只是奴隶的一种类型,亦即所谓“物化奴隶”“动产奴隶”或“古典奴隶”;此外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奴隶,即所谓“授产奴隶”或“分居奴隶”,这种奴隶拥有财产、财产权和独立经济,这种奴隶制被称之为“特有产奴隶制”。杨共乐论及罗马帝国早期建立的“特有产奴隶制”时曾这样写道:
特有产奴隶制发展迅速。按照《罗马法》对特有产的下的定义,特有产(Peculium)就是指奴隶经主人准许所拥有独立于主人财产之外的、扣除他对主人所负的债务的那部分财产。奴隶主常常将一部分财产授予奴隶,让其独立经营农业耕作或工商业。奴隶主每年都从这些奴隶手中收取一定的“代役租”,留下的盈利部分也就成了奴隶的特有产。特有产制首先对奴隶主有利。通过这种方法,奴隶主直接摆脱了经营上的劳累。同时,特有产制也对奴隶有一定的好处,这使他们的在经济上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奴隶借助于特有产可以直接向主人赎身,成为被释奴隶。在帝国早期,奴隶对特有产的权利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奴隶不能脱离他的特有产被主人单独出卖;主人冒名顶替用奴隶的特有产去还债被严厉禁止。[81]247-248
同时代的日耳曼人奴隶也属于“授产奴隶”或“分居奴隶”范畴。因为,据塔西陀记载,按照他们的奴隶制度,虽然杀死奴隶不受惩罚,并且没有罗马那种家内奴隶,却也属于这种“特有产奴隶制”:“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们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社会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儿女来负担。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他们也往往杀死奴隶,并不是为了整肃严格的纪律,而只是由于一时的暴怒,才将奴隶杀死,就犹如杀死一个仇人似的;不过杀死奴隶不受处罚而已。”[75]67
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也将奴隶分为这样两类,只不过他称“授产奴隶”“分居奴隶”为“租佃奴隶”或“定居奴隶”:“一些奴隶部分地从事较低级形式的家内役务,部分地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生活在主人家中或农场上。他们仍然被视作人畜,被正式列入动产之列。另一方面,租佃奴隶有自己的住处,靠自己的劳动产品维生,如果收获物碰巧有剩余,他可以卖掉这些剩余产品,不会受到阻拦;他已不再直接依附于主人生活,而其主人也很少干预他的生活。毫无疑问,他仍然要承受领地‘法庭(domanial‘court)的所有者强加于他的极为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些负担至少是有限度的;有时在法律上确实一律受到限定。诚然,一些调查报告告诉我们,一个佃户‘如果其主人发出命令,则必须永远为主人效劳;但是,众所共知的利益促使主人为每一位小农留出必要的劳动日去耕种自己的佃领地,否则他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就会化为乌有。这些‘定居奴隶的生活很类似于‘自由租佃人。”[86]406
那么,这些定居奴隶或授产奴隶是否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呢?答案是肯定的。诚然,初为奴隶,毫无所有,奴隶使用的生产资料完全是奴隶主授与的。但是,随着授产奴隶有了自己的财产,或迟或早,他不可能丝毫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试想,他既然有了财产,怎么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哪怕只是极为简陋的一两件生产工具呢?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镰刀锄头呢?古罗马农学家瓦罗告诉我们,当时从事畜牧的牧奴已有少数牲畜等自有财产:
有少数通常作为奴隶自有财产的牲畜,这部分东西是为了使奴隶较为方便地维持生活,并使他们较为勤快地干活。[89]55
马克垚论及西哥特奴隶的经济地位时,也这样写道:“这时的奴隶与罗马帝国极盛期的奴隶的经济地位已很不相同。他们大都已被分与小块土地,自己耕作经营,向主人交纳实物。因之其经济上的独立性不断增长,拥有土地、房屋、牲畜等,有自己的家庭,并且处分其财产物。”[24]41[78]41
但是,毫无疑问,授产奴隶只可能拥有极少量的、简单的、对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毫无影响的无足轻重的生产资料,而不可能有对可以影响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的主要的重要的支配性的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因为,一方面,奴隶的人身完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的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以及奴隶有什么财产和有多少财产,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意志,因而奴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不可能是能够决定其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的重要生产资料,而只能限于“使奴隶较为方便地维持生活,并使他们较为勤快地干活。”[89]55
另一方面,授产奴隶对奴隶主所负有的义务和贡物、劳役、代役租等远多于非奴隶佃户。即使是古希腊授产奴隶黑劳士(Helots),虽然与遭受主人任意剥削的其他授产奴隶有所不同,国家规定主人不可向他们索取出超过半数的收获物,却仍如当时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所言:“他们像驴子一样精疲力竭地处在重负之下,他们必须极紧迫地向主人提供所有粮果产量的半数。”[90]即使那些幸运的授产奴隶由于种种偶然而积累了一些财产,也首先要用于赎身。赎身之后,不管他有多少财产和生产资料,也都因其不再是奴隶而不属于奴隶所有。所以,不论何种类型的奴隶,充其量,都只能拥有对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毫无影响的无足轻重的生产资料;能够影响经济地位和产品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只能为奴隶主所有。
综上可知,“没有生命权、可以被杀害”和“没有财产权、没有自己的经济、毫无生产资料”并不是奴隶之所以为奴隶的普遍特征。奴隶之所以为奴隶的普遍特征只有一个,亦即自己的人身成为他人财产而为他人所有:奴隶就是自己的人身成为他人财产而为他人所有的人,分为没有财产权和自己经济的物化奴隶与有财产权和自己经济的授产奴隶。因此,奴隶制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就是因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财产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就是因人身占有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说到底,就是不但生产资料而且生产劳动者人身都归人身占有者——奴隶主——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的特征是没有生产资料和自己经济的物化奴隶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87]590另一类的特征是有极少量生产资料和自己经济的授产奴隶的劳动,他的劳动及其收获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另一部分是为主人的,如贡物、劳役和代役租。
毋庸赘言,任何国家或社会,往往多种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并存。因此,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存在奴隶制,未必就是奴隶制国家,未必就是奴隶社会;只有当奴隶制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的、核心的、支配的或主导的制度时,该国才堪称奴隶制国家和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就是奴隶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就是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之财产的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就是不但生产资料而且生产劳动者人身都归人身占有者——奴隶主——所有的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说到底,亦即生产劳动者主要为奴隶——人身成为他人财产而为他人所有的人——的社会。
2农奴与农奴制经济形态
谁都知道,农奴与奴隶根本不同。但若细究二者区别,古今中外,恐怕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这是一种“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的问题”。马克垚曾总结西方学者的农奴概念:
从中世纪的法学家直到晚近的西方学者,都强调农奴人身的不自由,强调他们人身属于主人。法国的农奴被称为homo de corpore,即人身属于主人之人。1166年法国一个修道院长谈到某人是他的农奴时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我的。”强调的是该农奴的人身,即身体属于他,这仍是沿用罗马法上奴隶是物的概念。英国12世纪的文件《棋盘署对话集》谈到英国的农奴(称维兰)时说:“按照这个国家的习惯,维兰不仅可以由他的主人从这一份地转移至另一处,而且他的人身也可以出售或用其他办法处置,因为他本身以及他为主人耕种的土地均被认为是领主自营地的一部分。”也是强调人身属于主人。所以布洛赫说:“农奴就是世代相传地人身属于主人的人。”[78]196
可是,人身属于主人的人:这不是奴隶吗?奴隶不就是自己的人身成为主人财产而为主人所有的人吗?所以,界定农奴为人身属于主人的人,混淆了农奴与奴隶,是不正确的。诚然,农奴的西文是serf,原本由称谓奴隶的词service转化而来,因而与中文的“农奴”一样,都有奴隶的含义:农奴就是“土地的奴隶”(Servi terrae)。但是,农奴显然不属于奴隶范畴。从概念上看,农奴是土地的奴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种说法表达的真谛乃在于:农奴是glebaeadscrptaae,亦即束缚于土地上的人。伯尔曼说:“在11和12世纪,农奴制度法律概念第一次得到系统阐述。农奴被称作‘束缚于土地上的人。”[91]因此,农奴就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耕作者。这就是农奴的定义,只不过有形象和比喻之嫌,是一种简单的粗略的定义罢了。
要找到农奴的精确定义,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究竟如何才能使一个耕作者成为“束缚于土地上的人”?方法无非有二。一种诚如马克垚所言,是使耕作者的人身被占有,使耕作者的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主人:“固着于土地是被用强力限制不得离开土地,这样其前提当是耕作者人身被固着于主人。”[92]但是,这种方法使耕作者成为奴隶而不是农奴——因人身被主人占有而束缚于土地上的人是奴隶而不是农奴——因而与农奴的定义无关。
另一种使耕作者成为“束缚于土地上的人”的方法,是主人并不占有耕作者的人身,而仅仅占有耕作者的人身自由,亦即不准耕作者离开和放弃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如果他们逃走,主人有追捕权。这种方法,也就是通过追捕等超经济强制剥夺耕作者的人身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身不自由而被束缚于土地上的人,成为一个人身不自由而必须为主人耕作土地的人,从而成为一个农奴而不是奴隶:农奴就是人身自由——而不是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主人的人,就是人身不自由——而不是人身被占有——的人,就是受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作土地的人。这就是农奴的精确定义。
可见,所谓农奴,形象言之,就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精确言之,就是人身受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作土地的人。所以,汤普逊说:“按法律的假定——就是,在技术上对农奴的看法——农奴在人身上是一个自由人,而在经济上是一个不自由的人。”[93]勃拉克顿则更恰当地将农奴的识别标准归结为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早上要干什么,那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奴。
农奴既然是束缚于主人土地上的人身不自由的人,实际上也就被看作主人土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往往被主人连带土地一起——逐渐也可以不连带土地——拿去遗赠、出卖和交换。这样一来,农奴与奴隶——特别是授产奴隶——的根本区别,说到底,便只有一点,亦即人身不自由与人身被占有:前者是农奴而后者是奴隶。因此,布瓦松纳论及农奴与奴隶的区别时写道:
他们与奴隶不同的唯一特征,就是他们有一个为习惯或法律所承认的法律上的人格。再者,一旦他们在一个份地上定住下来,他们就可以有一个住所,一个家庭,甚至有一份世袭的动产;他们的大多数是处在这种地位的。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人身毫无自由处置的权利。他们象家畜一样是领主自留地的一部分。他们象经济保证金一样,被看做农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丧失一户农奴,对于一个领主来说,犹如丧失一群牛羊一样——也许损失更大些。因此这些人身家畜是不准放弃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否则就要追捕;不论他们逃到那里,由于领主有追踪(suite)或防护(par6e)的权利,他们都要冒被俘获并押回他们原来的家的危险。农奴常连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一起被拿去遗赠、出卖、交换。[94]
可见,农奴与奴隶的根本区别乃在于人身不自由:农奴就是因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种土地的人身不自由的人。因此,农奴制经济形态就是因耕作者人身不自由——不是人身被占有——而形成的经济形态,就是耕作者因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种土地的经济形态。于是,这种经济的主要形态便表现为劳役地租:
农奴最主要的负担是劳役。虽然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实物及货币交纳,但剥削剩余劳动最多、最具体的形态,是劳役。我们也可以说,是劳役租这种形态决定了西欧农奴制的存在。[78]202
农奴的劳役,一般说来,是每周有三天耕种农奴主的自留地,亦即所谓公田;尔后才可以耕种自己从农奴主那里租来的份地。农奴有自己的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是独立的小生产者,有独立的经济。马克思认为这是区别于奴隶制经济的农奴制经济的根本特征:“它(农奴经济——引者)和奴隶经济或种植 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前所述,没有财产权和自己的经济的奴隶只是奴隶的一种类型,亦即所谓“物化奴隶”、“动产奴隶”或“古典奴隶”;此外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奴隶,即所谓“授产奴隶”或“分居奴隶”,这种奴隶拥有财产、财产权和独立经济,这种奴隶制被称之为“特有产奴隶制”。农奴制与这种奴隶制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农奴制劳动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而奴隶制劳动者人身是被占有对。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因耕作者人身不自由——不是人身被占有——而形成的农奴制经济形态就是封建制经济形态?抑或全等于封建制经济形态?
3封建制:两种封建概念和两种封建制
“封建”无疑是人类所创造的争议最大且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它曾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半个世纪后,亦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战的波澜再起;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封建概念及其演变?封建社会概念争议之大,不独中国,西方亦然。马克·布洛赫在其巨著《封建社会》第32章“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中写道:“今天,有关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充满异国色彩的说法,似乎充斥着世界历史……这个词语在世界上一直歧义纷呈,经历了许多曲解。”[86]697-698那么,究竟何谓封建?
“封”字在甲骨文中状如“植树于土堆”,本义是堆土植树、划分田界。唐代考据家颜师古说:“封,谓聚土以为田之分界也。”从此出发,进而引申为帝王将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作领地、食邑。所以,《说文解字》写道:“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组成“封建”的“建”字,起配搭作用,与“封”义近,本义为“立”。唐人孔颖达说:“建是树立之义。”
“封”与“建”合为“封建”一词,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蕃”。《左传》曰:“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这也就是“封建”概念的原初含义:“封建”就是帝王以土地爵位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他们在该地建立邦国或拥有某种最高权力的社会:邦国就是拥有某种最高权力的社会。所以,杨伯俊的《春秋左传词典》说:“封建,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顾颉刚说:“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叫做‘封建,封是分画土地,建是建立国家。”[95]
因此,“封建制”概念的原初含义与其词源含义完全相同,亦即以土地封人而使之建立拥有某种最高权力的社会,因而属于政治制度、政体制度或政府制度范畴,与“郡县制”相对立;二者之优劣,遂成为秦汉以降列朝政论的大问题,历经千百年而不衰:郡县制的特征是地方政府没有主权,主权完全执掌于中央政府,因而属于单一制政府制度;封建制的特征是宗主国与诸侯国分享主权,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分享主权,因而属于联邦制政府制度。因此,就封建概念的原初含义来说,秦汉至明清便不是封建社会,而只有夏商周才堪称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划分的根据是某种政体或政府制度的性质。
以中文“封建”对译的英文feudalism一词,从拉丁文feodum(采邑、封地)演化而来,原本指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因而与中文“封建”概念的含义相同,都是以土地封人使其在该封地建立拥有某种最高权力的社会:诸侯邦国与领主庄园。所以,西欧feudalism概念的原初含义,正如布洛赫所言,也不是指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制度;而是与中国“封建”概念的原初含义一样,指一种与中央集权相反的分权政体:“最初的命名者们在他们称作‘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所意识到的主要是这种制度中与中央集权国家观念相冲突的那些方面。”[86]697马克尧将这些方面归结为三:“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96]4
显然,中西封建概念的原初含义完全相同,都是指一种政体、政府制度或政治制度,因而所谓封建社会便都是以政体的某种性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为根据而对于社会的分类。但是,这只是封建社会的原初含义;封建概念后来是指一种经济形态、经济制度:“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96]4那么,它指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经济形态、经济制度呢?
这种后来大行其道而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为经济制度的封建概念,如所周知,指的就是作为政治制度概念的封建社会——亦即中国夏商周和西欧中世纪社会——之经济制度,也就是中国的井田制和西欧的庄园制之经济制度,亦即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者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也就是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的自然经济制度,说到底,就是地主依靠拥有土地经济权力而占有农民地租和剩余劳动的自然经济制度。1989年出版的《辞海》的“封建制度”词条便这样写道:
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其剥削和压迫。……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封建概念的这种含义,固然与其原初含义大相径庭,却同样源于其词源而有其词源依据。因为“封建”的词源,不论中西,都是“封土”“封地”,因而可以引申为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制,亦即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的经济制度。更何况,耕种是当时土地最主要的用途。因此,如果“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那么,受封者岂不就要将所获得的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岂不就要“以土地租人使之耕种或自耕”?这样一来,土地的经济权力岂不就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地主岂不就能够依靠拥有土地经济权力而占有农民地租和剩余劳动?
事实确实如此!夏商周和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之经济制度,岂不就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岂不就是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的经济制度?岂不就是地主依靠拥有土地经济权力而占有农民地租和剩余劳动的自然经济制度?所以,“以土地租人使之耕种或自耕”和“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亦源于封建之词源,实乃“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应有之义。
因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的“封建制度”词条写道:“英文feudalism一字来自德语fehu-od(英文fief一字又由此而来),原指牲口财产,后来指地产,强调土地享有权及其所属的权利义务。”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封建主义”也这样写道:“封建主义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费正清亦如是说:“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97]
因此,就连极力排斥“封建”作为经济制度概念的冯天瑜,也不得不承认,在古代语境中,“封建”有经济制度含义:“在古代语境中,‘封建主要是一个政制概念,却又牵连着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一位经济史家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农奴制剥削,是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役,为了实现这种无偿劳役就不能不有一个适应这种剥削的土地制度,……正是由于土地是由封建领主根据一定的土地分配办法分配给(即授予) 农奴的,建立起上下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封建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关系之上,1‘溥天之下,莫非王土,2‘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后者又是实现前者的条件。”[36]19
可见,从“封建”的词源含义不仅可以引申出“封建制是以土地封人而使之建立拥有某种最高权力的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封建概念的原初定义,而且可以引伸出“封建制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的封建概念的后来定义:封建制就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就是土地所有者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就是因土地租佃与自耕而形成的自然经济制度——以土地租人耕作者叫做地主;自耕者叫做自耕农,租入土地耕种者叫做佃农,二者合为农民。
这样一来,作为自然经济制度的封建制概念,说到底,也就是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的自然经济制度。因为自耕农虽然拥有土地,却与佃农一样没有土地经济权力,亦即没有依靠土地来雇用和支配他人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但是,一方面,既不能说封建制意味着土地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因为属于农民范畴的自耕农拥有土地;也不能说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因为自耕农每家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但自耕农阶层却因其可能占农民人口多数而拥有全国多数土地。
另一方面,更不能像梁漱溟那样,说封建制意味着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承受其超经济强制:“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98]这种观点虽然堪称主流,却是片面的。因为自耕农显然没有所谓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问题。至于佃农,也不都是农奴,而可能是自由民。农奴人身固然依附于地主,遭受其超经济强制;自由民的人身却并不依附于地主,不受其超经济强制。
封建制就是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者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对于这个封建概念的后来定义,亦即作为经济制度的封建概念,瞿同祖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虽然他坚持封建概念的原初定义,认为秦汉以降并非封建社会。
首先,他引证梅因的观点:“亨利·梅因从所有权来看,特别着重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一点上。以为两重所有权——主人封邑的优越和农夫财产的卑微——为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29]7接着,他引证维纳格鲁道夫:“他也着重于土地的所有权,和梅因差不多。以为有优越和卑微两种。前者有所有权,而后者只有使用权。不但一切人的地位都以土地的有无来决定,土地的所有并且能决定政治上的权利和义务。”[29]7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一)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二)主人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前者实系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为封建社会的中心组织;后者只是当然的现象,有土地者为主人,无土地而耕种他人的土地者为农民。这样便形成了特权与非特权阶级,而确定了两阶级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特权阶级的一切权利义务都以他的封土为出发点,他对于在上的封与者有臣属的义务,特别是兵役的供给。他对在下的臣民有治理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义务的供给。从非特权阶级来看,因为他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不是特权阶级,而必须对于给他耕地的主人忠诚地供给各种役作的义务。根据以上所述,更简要而言之,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29]8
总而言之,作为经济制度概念,封建制就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就是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者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就是因土地租佃与自耕而形成的自然经济制度,也就是土地的经济权力不归农民而归地主所有的自然经济制度,说到底,亦即地主依靠拥有土地经济权力而收取农民地租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自然经济制度。准此观之,农奴制显然并不全等于封建制,而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封建经济制度,可以称之为“农奴制封建经济制度”。因为封建制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而即使是农奴制封建社会典型的西欧,耕作者也不都是农奴,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亦即自由农民和农奴:
随着农奴制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西欧封建农民阶级的认识也有所变化。过去我们总是以为他们大体上是统一的农奴阶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中世纪的乡村。现在看来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农奴不是当时农村中的大多数居民(由于农奴的定义不同,所以对农奴数目的估计也有差别),甚至也许不占多数。法国、德国当然是如此。就是在英国,它的“导入的封建主义”更为典型,庄园制、农奴制更为巩固,农奴的数目也被估计为其户数最多占农户(指佃户,不包括贵族地主)的五分之三……科斯敏斯基统计了百户区卷档中散布在5个郡的10个百户区9,934户农民,其中5,814户是农奴(占58%),4,120户是自由农民(占42%)。也就是说自由农民和农奴的户数之比约为2:3,可见自由农民占有很不小的数目。中世纪西欧的农奴,每户都有着自己经营的一小块土地,称为农奴的份地。这块土地名义上不是农奴的,不过是交给他使用而已。其他身份的农民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也往往是封建主的,也是一份份地,所不同者只是对封建主的负担较轻而已。由于西欧在封建时代通行的是“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个原则,所以真正的自主地,即不受任何负担、完全归某人处分的土地是较少的。对于农民来说,尤其是如此。[78]219-221
不言而喻,根据封建制的定义——封建制就是以土地租人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不但地主租地给这5841户农奴耕种的经济形态是封建经济,而且租地给这4120户自由农民耕种的经济形态也是封建经济。只不过,前者是农奴制封建经济;后者是非农奴制封建经济罢了。因此,精确言之,封建制就是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者以土地租人——农奴与自由农民等非农奴农民——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租地给农奴耕种的经济制度叫做农奴制封建经济;租地给自由农民等非农奴农民耕种的经济制度叫做非农奴封建经济。
这样一来,所谓封建社会也就是封建制(农奴制或非农奴制封建制)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就是土地及其经济权力所有者以土地租人——农奴与自由农民等非农奴农民——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说到底,亦即生产劳动者主要为农奴或自由农民的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是生产劳动者主要为农奴——亦即因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种土地的人身不自由的人——的社会;非农奴制封建社会是生产劳动者主要为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的社会。
4社会形态性质的判别标准
综观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以及奴隶、农奴和自由民之区别,不难确定夏商周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诚然,这是一个难题;该难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一直众说纷纭。但是,这些争论主要讲来,正如张广志和李学功所言,可以分为三大流派:“西周封建说”认为夏商是奴隶社会;“战国封建说”认为夏商西周是奴隶社会;“魏晋封建说”亦即“秦汉奴隶社会论”,认为夏商周秦汉都是奴隶社会。[39]263因此,中国古史分期理论的主要流派虽有分歧,却一致认为夏商是奴隶社会。相反地,张广志、李学功等学者则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究竟谁是谁非?恐怕后者是正确的。
诚然,夏商周都存在大量奴隶和实行奴隶制。何兹全说:“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时期,奴隶制的产生是正常的。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周礼·秋官司寇》有:‘蛮隶百有二十人,闽隶百有二十人,夷隶百有二十人,貉隶百有二十人。郑玄分别注说: ‘征南夷所荻、‘闽,南夷之别、‘征东夷所获和‘征东北夷所获。并说:‘凡隶,众矣,此其选以为役员,其余谓之隶。这些蛮隶、夷隶,都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奴隶……奴隶的另一来源是罪犯。《周礼·秋官司寇》有‘罪隶一条,郑玄说:‘盗贼之家为奴者。贾公彦解释说:‘此中国之隶,言罪隶。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稾。故注云盗贼之家为奴者。郑玄也说过:‘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由此看来,先秦时代,奴隶有两大类,一类是战争中的俘虏,一类是罪犯。”[99]55-58
然而,任何社会,往往多种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并存。因此,一种社会,存在大量奴隶和奴隶制,未必就是奴隶社会;只有当奴隶制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的、核心的、支配的或主导的制度时,该国才堪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就是奴隶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经济制度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究竟取决于什么?是否取决于构成各种经济形态的劳动者数量之比例?奴隶社会是否就是生产劳动者主要为奴隶的社会?马克思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00]
原来,所谓生产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所谓生产关系亦即经济、经济基础,也就是创获——创造和获得——物质财富的活动,说到底,亦即生产和交换以及分配与消费;所谓经济形态也就是生产关系、经济或经济基础的类型,也就是创获物质财富活动的类型。这样一来,所谓基础的、核心的、支配的或主导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无疑是创造社会主要物质财富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一个社会主导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就是创造该社会主要物质财富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这就是主导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经济制度的判断总标准。
因此,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奴隶制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占主导地位,因而是奴隶社会,那就意味着:该社会的主要物质财富是奴隶劳动创造的。所以,马克思说,奴隶社会乃是这样一种社会:只要奴隶劳动“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101]恩格斯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在希腊便大大地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102]当代英国史学家芬利亦如是说:“一个奴隶制社会是一个为统治阶级或贵族提供剩余产品的主要劳动是奴隶劳动的社会。”[103]
那么,一种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是否创造该社会主要物质财富究竟取决于什么?一方面显然取决于该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或生产力水平,此即所谓“劳动生产率标准”或“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则无疑取决于劳动者数量,亦即取决于从事该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的劳动者的数量,也就是与从事其他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劳动者数量的比例,此即“劳动者数量标准”或所谓“数量标准”。这就是主导的生产、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的两个判断分标准。
不过,如果就古代社会的性质——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来说,则几乎完全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标准。因为农业是古代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创造社会主要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亦即所谓主要生产劳动部门;而古代社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论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相差无几。因为,一方面,虽然奴隶的劳动积极性较低,封建制小农——自耕农和佃农以及雇农——的劳动积极性较高,但奴隶制的生产工具好劳动规模却可能较先进。
另一方面,就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一般说来,虽然封建制高于奴隶制;但就某些情况来说,也可能恰恰相反,奴隶制劳动生产率高于封建制劳动生产率。譬如说,古罗马和秦汉时代,正如马克垚所言,都曾有奴隶制劳动生产率高于封建制小农劳动生产率的事例。[104]马克思亦曾指出,同一水平的生产力既可以产生奴隶制,也可以产生封建制:
以部落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其最基本的条件是作部落的成员,这就使得那被本部落所侵占所征服的其它部落丧失财产,而把那个部落本身变成本部落无机的再生产条件,看成是归它所有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不过是那以部落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必然的一贯的产物。[105]
这就是为什么,封建制能够与奴隶制一样,适合同一水平的生产力,甚至低于奴隶制生产力,如日耳曼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岂不就落后于罗马奴隶社会的生产力?这样一来,古代社会的主要物质财富,究竟为奴隶还是农奴或自由民创造,大体说来,便与劳动生产率无关,而完全取决于劳动者数量。因此,古代社会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大体说来,便与生产力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没有必然联系,而完全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标准”,亦即取决于该社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究竟是奴隶还是农奴或自由民,亦即取决于奴隶与农奴以及自由民的数量比例:生产劳动者主要是奴隶的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因此,休谟判断古代雅典和罗马奴隶社会性质时指出,奴隶与自由民的数量比例“是个最重要、也是最难确定的问题”:
关于奴隶同这些公民之间的比数,我们究竟应该确定为多少?这是个最重要、也是最难确定的问题。雅典是否也能建立起一套罗马那样的统治,是颇令人怀疑的。有可能雅典的奴隶较多吧,因为他们雇用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而这却是罗马这样的都城所没有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考虑到罗马人的崇尚奢侈,十分富庶,说不定罗马的奴隶要多些。[106]144
然而,何兹全、日知和王思治等秦汉奴隶社会论者却认为,一种经济形态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该经济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并不取决于各种经济形态劳动者数量的比重。他们的理由主要在于,如果主导与否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古希腊罗马就不是奴隶社会了。日知说:
如果单从量看,很容易从材料证据上取消很多的奴隶社会,而予费产阶级学者以否定奴隶社会存在的可乘之机。例如,据近代西方学者的估升,约当公元前430年,亚狄加的全部人口为315000,其中奴隶为115000;在雅典及比里犹斯港,全部人口为155000,其中奴隶为70000。罗马城市的奴隶人数与自由民主之比,据估计(时代未祥),一说为自由民520000,奴隶280000,另一说为自由民780000,奴隶200000。这些数字都说明自由民多于奴隶。但这对于雅典、罗马应为奴隶社会,又有何害?[107]
何兹全则从此出发,进而论证说:奴隶数量的多少,对于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是奴隶社会当然是有关系的,奴隶数量稀少的社会当然不会成为奴隶社会。但划分奴隶社会的标准,似乎不能是奴隶的数量。雅典的奴隶数量多,在劳动人口中的比数大,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恩格斯当年使用的雅典奴隶数量的材料,也有人认为估计过高了。)罗马奴隶数量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会比自由民多,一般估计,奴隶数量不超过自由民人数的三分之一。
一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决定的因素是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社会诸生产方式中所居的支配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封建社会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比起农民来总是少数。但我们已经称它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一社会中已居于支配的地位,社会的发展路线是由它规定的,农民的命运、小农经济的命运,已处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支配之下。尽管从人数上看,农民比起产业工人来是多得多。
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决定的因素应该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所居的支配地位。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表现在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工商业大农业和城市交换经济在整个社会中所起的支配作用,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衰落整个过程,也是在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工商业、城市经济的支配下进行的。[108]412
这种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古代雅典和罗马是否奴隶社会,取决于农业——古希腊罗马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主要劳动者是否为奴隶。诚然,这一问题颇有争议。恩格斯说:“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九万人,而男女奴隶为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四万五千人。”[109]休谟则怀疑雅典奴隶40万的说法而估算说:“雅典自由民的人数应为八万四千人,异邦人四万名,至于奴隶,按上面的最小数推算,又假定他们也以和自由民相同的比率结婚生育,则应为十六万人。”[106]144郭小凌进而指出:
19世纪末的古史大家彼洛赫和迈尔,他们将休谟的怀疑变为具体的考证,根据对雅典输入粮食的数量、自由人和奴隶人口的零星数据的细心分析,认为雅典尼乌斯提供的数字严重失实,雅典奴隶的总人数应当在10万以下(彼洛赫认为在7万左右)。由此两人均认为奴隶制在生产中仅起辅助作用,公民小生产者和雇工的劳动占有优势。[110]
如果像恩格斯和休谟所说的那样,雅典奴隶远远多于自由民,无疑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那么,雅典显然是奴隶社会。如果像彼洛赫和迈尔等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奴隶劳动仅仅起辅助作用;或者像何兹全所说的那样,奴隶不超过自由民的三分之一——并且假定二者从事农工商的比例相同——因而农业的主要劳动者不是奴隶,那么,雅典以及罗马就不是奴隶社会。因此,由古希腊罗马奴隶少于自由民,或不超过自由民的三分之一,并不能否定判定一个社会是否奴隶社会的奴隶数量标准,充其量,只能否定古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
其次,毫无疑义,资本主义是资本通过雇佣劳动而增值的商品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雇佣劳动者——包括农业雇佣劳动者和工商业雇佣劳动者——是主要劳动者的社会,是社会物质财富主要为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因此,资本主义初期,产业工人即使比农民少,是少数,也并不意味着雇佣劳动者是少数,因为农民包括农业雇佣劳动者;即使全部雇佣劳动者是少数,也并否定雇佣劳动者因资本主义生产力远远高于封建制生产力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也并不否定判定主导经济形态的双重标准:“生产力标准”或“质量标准”和“劳动者数量标准”或所谓“数量标准”。
最后,古代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为农业所创造。战国秦汉时期,如所周知,小农经济繁荣,社会物质财富无疑主要是小农——而不是何兹全所说的“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工商业大农业和城市交换经济”——创造的。因此,“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工商业大农业和城市交换经济”并不居于秦汉社会的主导地位,奴隶制并不居于秦汉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何兹全认为秦汉时代“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工商业大农业和城市交换经济在整个社会中所起的支配作用”,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否定判定奴隶社会的奴隶数量标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5夏商周:王有制分封制血缘宗法制的非农奴制封建社会
社会性质的判定,如上所述,虽然有双重标准——亦即“劳动生产率标准”或“质量标准”与“劳动者数量标准”或所谓“数量标准”——但是,如果就一个社会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来说,则几乎完全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标准。因此,夏商周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以及究竟是农奴制封建社会还是非农奴制封建社会——取决于夏商周生产劳动者主要是奴隶还是农奴抑或自由民?
如果生产劳动者主要是奴隶——亦即人身不属于自己而完全为他人所有的人——就是奴隶社会;如果生产劳动者主要是农奴——亦即因超经济强制而必须为主人耕种土地的人身不自由的人——就是农奴制封建社会;如果生产劳动者主要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就是非农奴制或自由农民制封建社会。这一点,郭沫若——认为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主要代表——也是承认的。所以,他在考证殷代社会性质时这样写道:“殷代无疑是有大量的奴隶存在的。但殷代的主要生产是不是在使用奴隶呢?”[27]14
夏商周不但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土地制度都是井田制。因此,夏商周究竟是什么社会,说到底,正如傅筑夫所言,取决于井田制中的生产劳动者究竟是什么人:“换句话说,在井田中那些实际耕田的人即直接生产者究竟是什么人?”[34]52-53
井田耕作者,正如何兹全所言,既有奴隶,亦有农奴:“奴隶不仅参加家内劳作,也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如克鼎载:‘锡汝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除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外,依附关系,即农民对贵族的依附关系,在西周春秋时期也是存在的。《诗经·幽风·七月》和《魏风·硕鼠》所描述的农民和主人的关系,就是依附农民和氏族贵族的关系。”[108]244但是,奴隶和农奴并非井田的主要耕作者;井田的主要耕作者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
自由民更是大量存在的一个阶级。氏族解体中,绝大部分公社成员成为自由民阶级……西周春秋时期,自由民这一阶级数量是大的,而且是生产劳动的主要负担者。[108]244-248
诚哉斯言!井田主要耕作者既非奴隶,亦非农奴,而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因为,如前所述,井田制是王有制的产物,诞生于五帝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代。当其时也,中国是必须建立唯有国家及其政府才能承担的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因此,中国不可能出现像西方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那样名副其实的土地私有制,而必定在名义和形式上仍然保持土地国有制或公有制。因为,一方面,如果不是土地国有制或公有制,而是像西方那样的土地私有制,田土都一块块归每个人私有,此疆彼界,各私其私,那就不可能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另一方面,国家及其政府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意味着:水的所有者是国家及其政府;进而意味着,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及其政府;归根结底意味着,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代表,亦即国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因此,与西方“古典的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对原始公有制的革命——因而是一种形式与内容完全一致的私有制——恰恰相反,五帝时代生产方式则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改良,因而是一种保留原始社会“公有制”的躯壳的私有制,亦即保留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国有”的躯壳和形式,而改变其灵魂和实质,代之以土地“国王所有制”[111];说到底,便是以“公有制”为形式的“王有制”。夏商周虽然与五帝时代有所不同,抛弃了公有制的形式,而实行形式与内容一致的王有制;但考古学表明,夏商周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三个平行的国家:“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个国家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间的势力消长各代不同便是了。”[65]87这样一来,夏商周不但离原始社会和五帝时代不远,甚至都是直接从原始社会和五帝时代转化而来。
这就是为什么,五帝时代和夏商周每个农民耕种的井田不但仍然沿袭原始社会农村公社传统,是国家、政府及其官吏分配、授予的,而且所有农民份地分配也仍然沿袭农村公社传统,实行平均分配原则;特别是所有农民所担负的税赋——什一税——也比较轻微,恐怕比农村公社时代多不了多少。“《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1994:77只不过,农村公社时代的税赋完全用于公社、国家和每个社员,而夏商周时代的税赋则主要被国王及其官吏阶级——诸侯和卿大夫以及士——所享有和剥削罢了。
这样一来,与西方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主要生产劳动者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税负沉重、两极分化、生活无着、战争频繁、寻求保护等等而沦为奴隶与农奴根本不同,夏商周农民因土地王有、不可买卖、永久耕种平均分配的份地的保障和不太沉重的税负以及社会稳定,晁福林说:“先秦时代不存在后世那样的农民起义,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暴动或震动,过去所指出的先秦时期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云云,都经不起推敲。可以说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经历着平稳的发展而不是急遽的变革。”(晁福林.夏商西周社会史:第二版[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23必定仍然像农村公社时代那样,不但人身完全属于自己所有,而且完全拥有人身自由,而不是奴隶或农奴。他们不是物化奴隶,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他们也不是授产奴隶和农奴,因为授产奴隶和农奴不可能担负如此轻微的税负:仕一税。
诚然,他们不可能自由自愿被国王及其官吏阶级剥削;但是,他们必定自由自愿耕种于井田。因为他们不但离不开唯有国家及其政府才能承担的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而且无论他们去哪里,实际上都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何况,当时无论他们去哪里,显然都不可能有比耕种于井田——仕一税和平均分配份地——更好的生计。因此,国王及其官吏阶级也就毫无必要使用超经济强制,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使其成为人身不自由的农奴:五帝时代和夏商周时代的农民都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
因此,范文澜一再说,夏商周的地租——贡助彻——交纳者都是自由民:“从夏朝起,发展中的私有财产制度逐渐改变了原始公社的性质。公社成员在分化。少数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主要是发展奴隶制度。大多数人成为自由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向统治者纳贡……贡、助、彻是表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地租名称。所谓贡,就是自由民耕种土地,统治者依据耕地上若干年的收获量,定出一个平均数,从平均数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贡物。遇到凶年,耕种者便有饿死或沦为奴隶的危险。夏朝的贡法,可以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最原始形态。所谓助,就是自由民的耕地,所有权被统治者占有了,因此必须替统治者耕种所谓公田(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公田上的收获物全部归统治者所有。商朝的助法,显然已经是力役地租。周国和周朝也行助法,大抵自共和以后,王畿内助法改为彻法,即实物地租代替了力役地租。贡、助、彻的逐步变化,说明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发展,这和自由民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23]50-52
周一良论及商代农业主要耕作者的身份亦如是说:“他们是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112]杨宽在“重新认识周代社会性质”中也这样写道:“这种接受国家分配的‘份地耕作而上交地税的小农,与专制君主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关系,但是性质上不同于欧洲领主封建制下的农奴,而具有自耕农的特点。他们是编入户籍的良民,除了交纳赋税和定期服兵役、劳役以外,生产和生活都是自主的。”[63]226张广志李学功讲得就更清楚了:
井田制下的耕作者虽已沦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但他们借助血缘的联系,借重有着久远历史的村社共同体,仍得以维持着一定的社会地位、身份自由和自己的家庭经济生活。[39]53
夏商周农业主要耕作者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还得到甲骨学和古代文献的印证。胡厚宣通过籀绎卜辞得出结论说:
殷代农业及军事之直接劳动者,既皆为众及众人,则众及众人者,又为何如人乎?曰,此可以《尚书》证之。《盘庚》有众字凡十二见:
率吁众惑,出矢言。
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众!
恐沈于众。
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凡尔众,其惟致告。
诞告用亶其有众。
用奉畜汝众。
绥爰有众。
罔罪尔众。
念敬我众。
此其义皆为民众或众庶之称,乃国家之主要分子,其身分极高,帮殷王命其悉至于庭,而相与讨论迁都之事。卜辞之众人及众,即与此相同。试观卜辞言“王大令众人曰: 田,其受年”,其口吻不与《盘庚》所言“若农服田力啬,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者至相类乎?然则殷代之农业军事劳动者,至少亦为极自由之公民。[113]
西周农业主要耕作者则叫做庶人:“庶,来自周。”[99]41 “庶人是西周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国语·周语上》:‘王耕一坡,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左传·襄公九年》:‘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管子·君臣上》:‘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周礼·司徒·间师》亦谓:‘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39]65西周所谓庶人也既非奴隶亦非农奴而是自由人:
庶的最初意义,似乎就予众多之外有着低下的意思。但是尽管庶子身分地位低,可是总仍是同氏族或同部落联盟的成员,所以才称“庶民子来”。《礼记·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亲未绝而列予庶人,贱无能也。”这也可证庶人是同族人,甚至包括贵族五服以内的子孙。他们虽贱,仍是自由人。[99]42
夏商周农业主要耕作者既非奴隶亦非农奴而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意味着:夏商周既非奴隶社会,也非农奴制封建社会,而是非农奴制(或自由农民制)封建社会。因为如上所述,封建社会就是土地所有者以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农民或耕作者主要为农奴的社会叫做农奴制封建社会;农民或耕作者主要为拥有人身自由的人的社会叫做非农奴制封建社会。
然而,郭沫若认为封建社会必定存在地主阶级,没有地主阶级必定不是封建社会。因此,他根据殷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国王一个地主而没有地主阶级——便断言殷周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诞生于首次出现地主阶级的春秋与战国之交:
《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在此以前的奴隶制下,中国是没有所谓“地主阶级”的。地主阶级既不存在,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立的这个主要矛盾也就还未成立。那么,在春秋中叶以前的中国社会便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27]4
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社会,不论地主有多少,不论地主只是皇帝一个人还是由无数地主所构成的地主阶级,只要土地所有者以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该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是土地所有者以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或自耕的自然经济制度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只不过,全国土地归皇帝一人所有的封建社会叫做王有制封建社会;全国土地归一个地主阶级所有的封建社会叫做官有制或民有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主要由官吏构成者叫做官有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主要由庶民构成者叫做民有制封建社会。
更何况,古史与考古研究,正如张光直所言,充分证明了夏商周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历史发展。《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数十年来的古史与考古研究,都充分证明了从殷到周之间,中国的文明史可心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甚至于从考古学上说,从考古遗物上去辨认晚商与早的分别,常常会有很大的困难。夏商之辨,可能也是如此。从考古学上判断为一脉相传的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一线,在政治史上分为夏商两代,不是不可能的。”[65]121
诚哉斯言!夏商周社会形态确实没有什么不同,不但都是封建社会,而且都是土地王有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的非农奴制——以及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封建社会。王有制是非农奴制和宗法制以及分封制和经济权力官有制的根源。因为,如前所述,一方面,王有制使农民不但离不开唯有国家及其政府才能承担的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而且无论他们去哪里,实际上都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国王及其官吏阶级也就毫无必要使用超经济强制,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使其成为人身不自由的农奴:王有制是非农奴制的根源。
另一方面,拥有全国土地的国王,势必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姻亲、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功臣亲信和先代之后等大都通过联姻而与国王结成异性血缘宗族关系——令其成为诸侯和卿大夫以及士等官吏阶级,拥有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遂使国家制度成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天子是天下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之大宗;王有制是血缘宗法制和分封制以及经济权力官有制的根源。
因此,全面说来,夏商周是王有制和官有制的非农奴制的血缘宗法制的分封制的封建社会;究竟言之,夏商周则是王有制的封建社会。王有制是夏商周的最根本特色。因为我们将看到,一方面,西方始终是民有制社会:民有制的非宗法制的奴隶社会和民有制的非宗法制的农奴制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秦汉以至明清,是土地官有制的封建社会,是郡县制的拟制——而非血缘——的宗法制的封建社会。
参考文献:
[1]斯凯思.阶级[M].雷玉琼,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M].陈心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4]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233.
[5]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82.
[6]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 and Frank Roosevelt.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Command,and Change,Third Edition[M].New Y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5
[7]赖特.阶级[M].刘磊,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6.
[8]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Books I-III[M].England Penguin Inc,1970:134
[9]John E.Roemer,Free to Los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oCambridge,Massachusettso1988:109
[10]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第2版[M].梅士,王殿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5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12]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3]波普.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91.
[14]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6]戴维·加尔森.神话与现实[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76.
[17]康文龙.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多重解释[J].学术论坛, 2006(3).
[18]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7.
[1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99.
[20]转引自刘军宁. 民主二十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41.
[21]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20.
[22]陈苏振, 张帆.中国古代史读本: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25]翦伯赞.先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6]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8]《国语·晋语》
[29]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0]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8.
[31]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2.
[32]邱树森, 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1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02.
[33]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
[3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M]. 北京:三联书店,1956.
[35]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3.
[36]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7]《孟子》
[38]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7.
[39]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0]邢义田.天下一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1:165.
[41]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6.
[42]张传玺.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
[4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03.
[44]戴德.礼记·王制[M].
[45]李学勤.李学勤说先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199.
[46]李修松.先秦史探研[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69.
[47]扬升南,等.商贷经济与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8]《荀子》
[49]《左传·繥公二十四年》
[50]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41-42.
[51]《礼记·礼运》,转引自邢义田.天下一家[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4.
[52]刘家和.宗法辩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2.
[53]朱傑人,等.朱子全书:第2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2.
[54]钱宗范.中国宗法制度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4):78.
[55]钱杭.关于宗法制度形成的条件问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1):145.
[5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
[57]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94.
[5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 陈苏振, 张帆.中国古代史读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59]Karl Larenz .法学方法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160.
[60]刘广明.宗法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19.
[6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8.
[62]胡寄窗.关于井田制若干问题的探讨[J].学术研究,1981(4):59.
[63]杨宽.先秦史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64]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
[65]张光直.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
[66]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王子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88.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2.
[68]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M].强我,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15.
[69][汉]赵岐注《孟子》,转引自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5.
[70]万国鼎.中国田制史[M].南京:南京书店,1933.
[71]齐思和.中国史探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40.
[72]徐喜辰.井田制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24.
[73]金景芳.论井田制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1):37.
[74]金景芳.论井田制度(续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4):7.
[75]塔希陀.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M].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6.
[77]历史研究编辑部.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7:275.
[78]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9]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
[80]刘家和.略论区分奴隶与农奴的理论标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5):17.
[81]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2,注17.
[83]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00.
[8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727,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1.
[86]马克·布洛赫. 封建社会:上卷[M].张绪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06.
[87]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5.
[89]胡庆鈞.奴隶制是否人类社会一个独立发展阶段[J].云南社会科学,1988(1):55.
[90]胡庆鈞.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J].世界历史,1995(6):64.
[9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 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00.
[92]马克垚.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6.
[9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卷[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1.
[94]Р.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五至十五世纪)[M].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8-1419.
[95]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29.
[96]马克尧.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9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
[9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50.
[99]何兹全. 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5-58.
[100]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21.
[101]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39.
[1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
[103]转引自: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J].世界历史, 1999(6):99.
[104]马克垚:“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J]. 历史研究,1981(3):40.
[105]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0.
[106]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M].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7]日知.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J].历史研究,1956(12):13.
[108]何兹全. 何兹全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
[110]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J].世界历史,1999(6):99.
[111]王海明. 论五帝时代:中国特色之起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9.
[112]周一良.新编中国通史:第1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4.
[113]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5.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WANG Hai-ming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anya Univ, Sanya,572022,China)
Abstract: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are of a unique kind of private ownership, which is official ownership wholly own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fficials of all classes. On the one hand, the land belongs to 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 where the King owns all land;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the 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power-mainly the economic power over land and cultivators andrent charging-are of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the power over industry and commerce is also of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Therefore, the economical power of all economic sectors is also of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owned by officials and the class of officials (kings, princes, bureaucrats and scholars). Hence, for one thing, the feudal system,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nine squares” system, are the results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for another, the “nine squares” system is the land system of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and the workers in the fields are neither slaves nor serfs, but tenants with personal freedom. Thus, overall speaking, the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are feudal societ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the non-serfdom system,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enfeoffment system. Therefore, the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are feudal societ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non-serfdom system,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enfeoffment system all derives from 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
Key words:Xia Shang Zhou dynasties;the official class;the subaltern class;the official ownership system;the king ownership system;the “nine squares” system;the patriarchal system
【责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