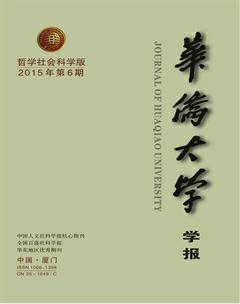“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框定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不断拓展、深化“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的和更复杂的非市场风险。从深层次的实质根源来看,这些风险往往来源于投资相关各方在利益的认知、诉求和分配上的分歧与矛盾。因此,应建立、完善和充分运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协调的风险治理机制。为此,根据国际法和国家间协调合作上的考虑,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基本内容与类型予以识别框定,并进一步明确建立、完善风险治理机制的目标与框架。
关键词:“一带一路”;直接投资;风险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F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6-0095-10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系统性工程,其中,中国企业等国内机构的境外直接投资是具体实施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境外直接投资者往往面临着各种非市场性的投资权益风险,以及来自于各种层面和领域的复杂多样的利益矛盾、冲突等问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平均等级较高,其中,一些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政治体系脆弱、国内矛盾和冲突严重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影响,导致外国投资面临着很高的国别风险。随着中国不断拓展、深化“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的和更复杂的非市场风险和利益冲突,国家和政府层面也将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笔者认为,为防控和化解“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应建立、完善和充分运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协调的风险治理机制。这需要进一步分析明确有关境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法规则与机制,研究如何调整、完善这些国际法原则、规范和机制,使其能够更为公平合理地、协调平衡地应对解决境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各种矛盾、冲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建立和运用风险评估、预警以及应对解决的治理机制。为此,首先需要考虑和分析的是,从国际法和国家间协调合作层面分析框定“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以及建立、完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政府参与全球性治理若干法律问题研究”(10BFX098)
作者简介:赵洲(1969-),男,安徽巢湖市人,法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善风险治理机制的目标与框架。
一国有化或“间接征收”的风险
在国际法上,国有化是指主权国家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制度,将原属于私人(包括外国自然人和法人)所有的某项财产以征收、征用或其他类似方式收归国有的法律措施。其中,征收又称为“没收”,它是指国家以不支付补偿的方式将原属于私人所有的某项财产收归国有的法律措施,它具有无偿性与惩罚性;征用是指国家以支付补偿的方式将原属于私人所有的某项财产收归国有的法律措施;所谓其他类似方式是指实际上将产生所有权变动效果的类似法律措施,包括逐步国有化等措施。此外,晚近以来,在正式的国有化之外,东道国更多的是运用“间接征收”措施,即东道国基于“公共利益”等理由,对外国投资进行规制,从而严重影响或限制投资方的财产权益,达到类似于国有化的效果。对于如何规范和处理国有化措施或“间接征收”问题,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议。发达国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主权国家只有基于公共政策,并依据正当程序方可实施此种措施。而且,东道国应当给予充分、有效、及时的补偿,即所谓的“赫尔公式”。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国有化仅仅为东道国本身的主权行为,不应受主权之外的限制。在国有化补偿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主张“适当合理的补偿”。显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的正常进行和正当权益,东道国可能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或“间接征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风险。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国有化或“间接征收”的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根据有关国有化问题的既有国际法规范及相关实践,进一步分析明确国有化制度存在、发展及适用上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东道国实施国有化措施所应遵循的国际法上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例如,如何专门针对“国有化措施”界定和解释运用“公共利益”这样的前提要件,在实施国有化措施方面如何协调平衡东道国主权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关系等。通过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对国有化措施所造成的风险形成总体认识与预估。在这方面应进一步结合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曾经所遭受的国有化措施展开分析研究,例如,随着非洲一些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民族主义思想膨胀,容易出现国有化的政策和行为。如2012年加蓬政府取消中国机械工程公司对“Bélinga”铁矿山的开采权,2013年中石化的子公司阿达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在“Obangue”油田的开采权被加蓬撤销。这些国有化措施经常发生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而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恰恰就集中在这一领域。因此,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而言,分析研究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国有化风险尤为重要。第二、在传统的国有化措施之外,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间接征收”风险是一个更为复杂困难的问题。东道国往往以保护健康、安全、环保等公共利益为由实施“间接征收”措施,其所造成的风险损害并不亚于传统的国有化措施。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家公司在拉美国家的投资就曾遭遇了“间接征收”问题,如厄瓜多尔政府突然将石油税从先前的50%调整到99%,如果拒绝缴纳,将没收外国石油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份。相对于传统的国有化措施,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国际法规范目前对“间接征收”明显缺乏统一、明确的认识与认定标准,所以经常引发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纠纷。为此,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既有的理论、条约与实践及其变化发展,如判定“间接征收”所依据的“效果标准”“目的标准”“效果与目的兼顾标准”,美国2004年《BIT范本》具体列举的判断东道国行为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考虑的诸多因素。通过这些分析研究,明确“间接征收”的法律内涵、界定标准,以及其与东道国的正常管理措施之间的法律界限,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正当合法的“间接征收”,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相应的风险防控方案以及如何解决补偿问题。第三、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相关国家和地区有关国有化问题的国内法、政策等具体情况,分析识别出那些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引发国有化措施或“间接征收”的各种高危因素,如掠夺性开采资源、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规避纳税并严重损害东道国的税收利益、企业活动严重违反东道国的公序良俗等。如在2013年,科蓝煤矿(Collum Coal Mine) 因受到滥用劳工、工作环境不符合标准的指控,赞比亚政府从中方私营业主手中收回了煤矿控制权。通过对这些高危因素的分析识别,提示境外投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尽量避免触及这些高危因素,以防控可能导致的国有化风险。第四、进一步明确那些能够减少或消除国有化或“间接征收”风险的积极因素,如提升东道国技术水平、推动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分析评估和调整投资方在这些积极因素方面的行为和效果,减少或消除国有化或“间接征收”风险。
综上,以上述有关国有化与“间接征收”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实施国有化与“间接征收”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国有化或“间接征收”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针对国有化措施或“间接征收”所造成的分歧争议,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
二东道国因“危急情况”而减损投资权益的风险
在国家责任法上,根据2001年的《国家不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以及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的判决,一国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是为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种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时,“危急情况”则可以作为解除该行为不法性的合法理由。BIT也存在着有关紧急情况的例外处理规定。如2005年中国与芬兰的BIT第3条第5款规定,本协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一方在战争、武装冲突或其他国际关系紧急状态下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2006年中国与印度的BIT第14条规定,本协定不妨碍东道国缔约方在极端紧急状况下根据其法律,采取正常、合理和非歧视的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因此,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可能以“危急情况”为由直接违反投资条约等相关国际义务,如直接取消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税收优惠待遇,直接违反投资保护义务而取消或终止特许投资经营项目。这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正常进行和正当权益构成了严重风险。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危急情况”而减损投资权益的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分析确定“危急情况”的内涵及其构成要件。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对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意见中指出,不应该将“危急情况”所指向的“基本利益”压缩到仅指所涉国家的“生存”,应根据特定情况来判断整个问题。可以援引危急情况的事例包括:对一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的生态养护构成严重威胁。就最近的国家实践而言,维护生态平衡成为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然而,评注意见对“危急情况”的内涵界定依然只是框架性的,不能充分地消除“危急情况”这一例外事由在界定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风险。对此,需要根据国家责任法在这方面的理论与相关的国际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明确“危急情况”的内涵及其构成、适用要件,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防控此类风险以及利益协调奠定基础。第二、分析确定适用“危急情况”这一例外事由的限制因素。例如,适用“危急情况”事由应符合非歧视、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同时,“危急情况”事由的适用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危急情况是由责任国促成的,或如果有关国际义务排除了此种援引的可能性,则不得以危急情况为由不履行条约义务。在CMS Gas Transmission 公司诉阿根廷案中,阿根廷辩解认为,其违反与美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不应承担责任,理由是该国陷于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因此存在着国际法上的“危急情况”这一免责事由。仲裁委员会在2005 年的裁决中认为,阿根廷所采取的措施并非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这种所谓的“危急情况”主要是由于阿根廷政府政策及其缺点所促成的,而外部因素则加剧了这一困难。因此,阿根廷不能免除违反条约的法律责任。[1]56-58鉴于此,需要根据国际法在这方面的理论与相关的国际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明确适用“危急情况”这一例外事由的限制因素,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防控此类风险以及利益协调奠定基础。
综上,以上述有关“危急情况”所致投资权益减损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出现“危急情况”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危急情况”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针对因适用“危急情况”这一例外事由所造成的分歧争议,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
三东道国因“环境保护”而影响投资权益的风险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东道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企业治理制度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容易诱发冲突的是环境和社会责任问题。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2]对此,一方面需要做到的是,不能把“一带一路” 战略变成输出落后和具有高消耗高排放产能的载体,而应把环保和绿色融入“一带一路”战略。[3]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东道国的国内形势与要求等各种情况与因素的变化发展,东道国将会不断地调整和实施环境保护的国内法规、政策与管制措施。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要求及其变化发展将对正常进行中的境外直接投资造成明显的环境成本风险,甚至严重影响境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效益与可持续性。此类情形并不属于对具有明确、硬性的约束效果的国际义务的违反,它所涉及的是东道国所承担的投资保护义务与东道国维护本国环境利益的主权权利之间的协调平衡问题。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环境保护”而影响投资权益的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具体深入地甄别、确定境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环境条款下所面临的环境规制风险。有研究根据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性质、功能和在投资协定中的地位进行类型化,将其分为 “非排除措施”条款(non-precluded measures clauses)、平衡条款(balancing clauses)、除外条款(carve-out clauses)、冲突条款和程序条款。[4] 这些不同类型的环境条款在实际规制效力、作用方式与实际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对境外直接投资所造成的环境规制风险也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二、需要据相关的理论、条约与国际仲裁实践,进一步分析确定东道国调整和实施环境保护的国内法规、政策与管制措施所应遵循的条件,如符合非歧视、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的要求,以及适当的补偿安排,以公平合理地协调平衡东道国规制外国投资、维护本国以及国际社会环境利益的主权权利、责任与促进、保护外国投资之间的复杂关系。在“Tecmed公司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调查了外国投资者是否知晓(或能够合理地预见)那些最终导致它的投资活动被终止的环境义务。仲裁庭认为,Tecmed公司在墨西哥投资建立一个垃圾填埋场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其投资活动的合法性,在分析、考虑与垃圾填埋场选址有关的法律事项的问题上,也没有疏忽。这说明,在投资时,投资者没有获知国家将来要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信息,或者不可能合理地预见这种义务的产生,则仲裁庭将会倾向于保护投资者在投资时的合法投资期望。
以上述有关“环境保护”所致投资权益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的境外投资主体及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应建立和运用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变化调整“环境保护”规制措施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环境保护”规制措施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通过在事前和事中与东道国进一步沟通磋商,及时地规划、调整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效地防控因东道国不正确地适用甚至滥用“环境保护”事由而导致的环境成本与预期效益风险,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各方利益平衡。
四东道国实施国际法上的反措施所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
反措施是一国针对他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不得不采取某种不符合自己对他国原已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一种非武力对抗行为。根据国际法的规范要求,反措施的目的是促使责任国履行其义务。反措施只能针对责任国而不得指向第三方。同时,反措施具有临时性质。反措施必须具有相称性,即反措施必须和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并应考虑到国际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有关权利。因此,在国际法所允许的条件和范围内,东道国可以采取反措施,暂时不执行与投资建设相关的条约和配套的国内法。显然,这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的正常进行和正当权益构成了潜在的风险,而且,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既有的或未来的各种权益争端以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影响增加了这种风险。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东道国实施反措施而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根据国际法在“反措施”方面的理论与相关国际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明确“反措施”的内涵及其适用上的实质要件和程序条件。如在实质要件上如何判定“反措施”已经满足前提条件和相称性要求,在程序条件上如何确定东道国已用尽协商谈判的方法等。在此基础上形成投资方的正当要求,并通过其自身及母国的交涉防控东道国的“反措施”影响。第二、根据国际法在“反措施”方面的理论与相关国际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明确如何将投资权益界定为那种直接受保护的“条约上的权利”,而非条约上的一般利益。在Corn Products International Inc.诉墨西哥案中,墨西哥辩解认为,对原告的征税虽然违反了其根据《北美贸协》所承担的义务,但这是为应对原告的国籍国美国以前的违反行为而采取的合法的反措施。仲裁法庭在其2008年的裁决中认为,废除或以其他方式影响第三方的“权利”的反措施与废除或影响第三方的“利益”的反措施之间是有区别的。反措施不能废除或以其他方式影响除对以前的不法行为负有责任的国家以外的其他当事方的权利,但该措施可以影响到此类当事方的利益。[1]20-21 因此,需要根据国际法在这方面的理论与相关国际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明确投资方在什么条件下具有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国籍国的实质性权利,在什么条件下投资建设方仅仅只是拥有不同的利益。
综上,以上述有关反措施所致投资权益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的境外投资主体及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应建立和运用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实施反措施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反措施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通过风险评估、预警以及与东道国的协商谈判,在事前或事中将依据既有的条约和配套国内法所形成的投资权益界定为有别于投资母国的独立的实质性权利,而不是条约上的一般利益,从而防控东道国实施反措施而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
五东道国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所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将难免涉及到东道国配合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问题。东道国既可能配合执行或遭受来自于联合国的集体制裁,也可能配合执行或遭受来自于联合国之外的多边或单边制裁。这些国际制裁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正常进行和正当权益造成明显的影响。例如,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受西方的经济制裁,导致投资者对赴俄投资望而却步。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法律安全论坛秘书长、中国安全和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永前认为,对于中国企业赴俄投资,不必过于纠结或拘泥于大环境的风险,而是应该更务实地把握具体项目中的风险,并在此过程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5]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东道国配合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而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分析识别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制裁的合法性问题。国际制裁可以区分为联合国制裁和联合国之外的多边或单边制裁。不同的国际制裁的合法性存在着差异,这直接影响着投资方的风险防控与权益保护问题。为此,需要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制裁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不同的权益调整和风险防控预案,并通过与东道国的沟通协商,达成事前和事中的风险解决协议。第二、对于投资前的已存在的制裁,无论是东道国需要配合执行的还是正在遭受的,根据国际法上有关国际制裁精确定位与豁免的制度和具体实践,对拟进行的境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评估和防范投资风险。3、对投资后东道国可能遭受的或需要配合执行的新制裁,及时地分析明确如何在投资主体和政府层面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以及如何形成应对预案和采取早期预防措施。第四、对于投资进行中的新设制裁,无论是东道国需要配合执行的还是直接遭受的,根据国际法上有关国际制裁精确定位与豁免的制度与具体实践,分析明确如何界定处理各种不同领域和内容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国际制裁的遵从执行问题,以尽量缩小国际制裁的损害影响。第五、对于因为遵从正当合法的国际制裁所造成的投资权益损害,根据有关制裁损害补偿的国际法规范、制度与具体实践,分析明确如何确定和实施救济补偿。
综上,以上述有关国际制裁所致投资权益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的境外投资主体及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应建立和运用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配合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配合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通过在事前和事中与东道国进一步沟通磋商,及时地规划、调整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效地防控东道国因配合执行或遭受国际制裁而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
六东道国国家或政府发生异常变动时“既得权益”的确认风险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新的分化组合,这包括国家分裂为数个国家,国家的一部分分离出来成为新的国家,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转移给另一个国家,国家被吸收并入另一个国家,国家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也可能因为革命或政变发生异常更迭。冷战结束后,国家或政府的上述变动情形较为多见和常发。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所在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6]在东道国国家或政府发生异常变动时,投资方原本得到确认保护的“既得权益”将面临着能否得到新的东道国或新政府的确认保护的风险。例如,利比亚是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之一。中国在利比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领域。随着卡扎菲政府被迅速推翻,利比亚新政府的上台,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形成的“既得权益”就面临着新政府是否给予继续确认、保护的法律风险。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东道国国家或政府的异常变动而造成的投资权益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深入全面地梳理归纳与“既得权益”相关的国际法理论、规范与实践,提炼整合其中的合理内核,形成符合当代国际法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既得权益”理论与诉求,为中国投资者处理东道国国家或政府的异常变动时“既得权益”的确认风险提供坚实的理论与规范依据。第二、“既得权益”问题将直接涉及到国际法上的国家或政府继承问题。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有关国家或政府继承的法律原则和规范,如1978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96年生效),1983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未生效)。这些法律原则和规范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条约、国家财产、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与“既得权益”的继续确认与保护密切相关。总的来看,新国家或新政府对条约、国家债务并不承担着一概予以继承的法律义务,条约或国家债务的继承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满足或符合各种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对此,为适应“既得权益”的风险防控要求,需要进一步分析掌握有关国家或政府继承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着重分析提炼和界定那些“继承可被正当否认”的事由及其构成条件,如“恶债不予继承”这一抗辩事由及其构成条件,从而为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规范指引,规避和防控“既得权益”的延续确认风险。第三、为有效地防控和解决“既得权益”的延续确认风险,需要分析建立和运用政治、外交与法律相融合的综合防控应对机制和策略方法。1、对于东道国国家或政府发生异常变动所造成的“既得权益”的延续确认风险,中国在考虑决定对新国家或新政府是否给予外交承认和建交的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和纳入在该国的中国投资者的法律建议和权益诉求,与新的东道国国家或新政府就中国投资者的“既得权益”展开法律谈判。2、对于东道国国家发生异常变动的情况,投资方不能被动地坐等情况的发生,然后再寻求新的东道国的确认保护。投资方需要根据国家继承等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在东道国因为分化组合而谈签相关协议时,通过母国的外交途径等方法积极参与到相关国际协议的谈判协商中,对投资上的“既得权益”作出预先的妥善安排。3、对于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协商未能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寻求国际仲裁等国际司法途径、措施予以解决,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运用国际法所允许的投资方母国的反制措施来应对解决“既得权益”的确认保护问题。这些措施和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压力机制,防控投资上的“既得权益”确认保护风险。
七东道国境内动乱所导致的履约与损害风险
东道国的境内动乱包括一般性的社会动乱,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严重的国内武装冲突或叛乱等。对于在东道国境内的外国投资,这些社会动乱既可能是不具有针对性的扰乱与破坏,也可能是具有特定针对性的直接侵害。有研究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历史问题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大多是恐怖主义多发区。[7] 总的来看,东道国的境内动乱势必严重影响、损害“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的正常实施与合法权益。这包括因东道国境内动乱所导致的投资活动上的各种合同违约责任损失、投资成本与收益损失,以及各种实际的财产、人员损害等。对于东道国境内动乱所导致的履约与损害风险问题,有的投资条约范本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意大利2003年BIT范本第4条的规定,如果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因战争、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紧急状态、内乱或其他类似事件,遭受损失或损害,则受到影响的投资所在的缔约方应就此类损失或损害提供充分的补偿,且不管损失或损害是否由政府军队或其他主体造成。无论如何,有关投资者应得到另一缔约方国民同样的待遇,且无论如何,不能低于第三国投资者取得的待遇。在这方面,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合理、有效的防控与解决方案与机制。如在利比亚、埃及、苏丹和突尼斯这些国家,中国所签订的BIT仅规定,在发生战争或类似事件的情况下,如果东道国采取补偿等措施,外国投资者享受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因此,对于在这些国家因战争或类似事件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中国投资者并不必然能够得到救济补偿。事实上,东道国境内动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风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牵涉到法律责任的界定分配以及投资法律关系的变更调整的重大问题。第一、东道国基于其国家主权,防范与管控境内动乱,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是一项不可推卸的国际法律责任。在国际投资条约和仲裁实践中,“全面的保护和安全”标准是东道国对投资者所承担的一项安全保护责任。对安全义务的违反既包括国家直接对投资者及其投资实施的损害行为,也包括国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本可以阻止的第三方如暴徒、叛乱分子等对投资者的损害行为。第二、从投资法律关系的的正常实施来看,东道国境内动乱必然将影响或改变投资法律关系所原本依赖的基础环境,这应当构成投资法律关系中的情势变更问题,对此,围绕着直接投资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合同等法律关系需要得到相应的变更调整。总之,不能仅仅因为境内动乱的政治属性就完全排除东道国的法律责任,僵化地坚守原有的投资活动上的各种法律关系,让投资方承担全部的履约风险与投资损失。投资方需要根据东道国所承担的投资保护责任及其具体履行状况,通过各种协议安排和机制防控和解决因东道国境内动乱而造成的履约风险与投资损失。
为进一步分析揭示和应对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因东道国境内动乱而造成的履约与损害风险,需要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对于在具有这类潜在风险或高风险的东道国所实施的境外直接投资,需要在理论上全面深入地分析明确东道国的防范与管控境内动乱的具体法律义务,以及不同的动乱风险类型下的东道国保护行为义务,进一步明确东道国未能履行防范与管控义务的界定标准与相应的责任承担,为界定、处理迟延或无法履约的责任归属、损害的分配,以及各种合同等法律关系的变更调整问题提供法理基础。第二、如何在投资条约中引入和细化有关动乱风险问题的处理条款或基本框架原则,或者对于具有潜在动乱风险或高风险的东道国,在其境内开展投资之前,与该东道国政府商谈签订有关处理动乱风险问题的原则、框架安排的补充协定。这包括东道国应承担的风险防范与管控义务的框架原则与具体要求,以及风险损失的界定与分担等。有研究专门针对恐怖主义风险建议,在双、多边贸易协定或优惠安排谈判上,积极引人详细的反恐投人条款,如约定东道国政府保证反恐和治安投人占其财政预算的比例达到某一水平,设立恐怖活动损失理赔专项基金,对遭受恐怖活动损失的外商进行赔付等。[8]第三、充分地分析运用和发展完善国际法上的领事沟通磋商与保护机制。通过领事沟通磋商与保护机制督促东道国履行其投资保护义务,并形成客观全面的证据材料,为后期处理履约与投资损失问题奠定坚实的事实与法律基础。第四、针对各种具体的境外直接投资,就动乱风险的处置安排问题与东道国达成特定协议或承诺,具体明确地界定各方的义务、免责处理、损失分担,以及各种合同等法律关系的变更调整的条件和程序。例如,对于东道国境内的可能动乱,协议达成情势变更的具体类型与判定标准。明确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解除投资活动上的相关合同,并由东道国返还已缴纳的土地使用、资源开采等费用。明确什么条件下投资活动可以被界定为暂时不能实施、需要迟延履行或终止实施等,以及无法实施时投资权益的撤出安排与补偿。
2010年,商务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明确了风险的类型、预警的发布、风险的通报、工作的要求及保密责任等事项。但尚未形成完善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也未形成系统的早期干预和磋商机制。有研究认为,中国尚未针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和体系。[9] 为此,以上述有关东道国境内动乱所致投资权益风险的具体、深入分析为基础,中国的境外投资主体及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风险评估、预警模型与指标体系。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评估、揭示东道国境内动乱这一风险本身,更主要的是评估、预警在如何规范与解决因动乱所致投资损害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在建立和实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之外,在中国投资主体与政府层面应建立和实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通过在事前和事中与东道国进一步沟通磋商,及时地规划、调整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效地防控东道国境内动乱而造成的投资风险。
结语
随着中国不断拓展、深化“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将“成为投资立国的国家”[10]。 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将面临着更多的和更复杂的非市场风险和利益冲突。从规范、机制的表层来看,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来源于相关的国际法、条约和东道国法律在内容和解释适用上存在着空白、碎片化、模糊、不稳定以及权利义务配置失衡等状态,或各种应对解决的法律措施、机制的缺失、薄弱、不完善等缺陷。从深层次的实质根源来看,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往往来源于投资相关各方在利益认知、诉求和分配上的分歧与矛盾。尤其是东道国往往单方界定和处理利益认知、诉求和分配问题。因此,防控“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就不可能是孤立、分散的方式,同时,单纯地依赖和强化国际仲裁机制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控与争议处理所需要的是,从国际法和国家间协调合作层面分析框定“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在投资方、东道国、投资母国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协调平衡的治理机制,通过治理机制所提供的程序、方法和动态进程,相关各方围绕着利益认知、诉求和分配进行沟通、博弈和协调,公平合理地解决利益分歧与矛盾,从而在实质根源上有效防控“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裁判汇编[R]. A/62/62,1 February 2007.
[2]何茂春.“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6-45.
[3]唐朱昌.“一带一路”的定位、风险与合作[J]. 社会观察, 2015(6):13-16.
[4]赵玉意. BIT和FTA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基于文本的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3(9):93-106.
[5]李亚. 走向“一带一路”应重视法律风险管理[N]. 国际商报,2015-08-20(C01).
[6]张明. 直面“一带一路”的六大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5(4):38-41.
[7]王卫星. 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9):6-18.
[8]张晓磊,孙利娟. 恐怖活动风险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J].国际经贸探索,2015(7):64-74.
[9]张雨,戴翔. 政治风险影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吗[J].国际经贸探索,2013(5):84-93.
[10]许正,乌东峰:“一带一路”塑就新经贸关系与三个新常态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42
A Study on Extraterritorial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Based 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ZHAO Zhou
(School of Law, Nanjing Audit Univ,Nanjing, 211815,China)
Abstract:When China gradually enlarges and deepe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Chinese extraterritorial investment will inevitably confront more and much complicated non-market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ot cause, these risks usually come from divergenc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cognition, pursuit and allocation of interest among investors and stakeholders.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perfect and fully exploit risk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inter-state coope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Consi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state coope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this paper frames basic risk contents and types of extraterritorial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and further makes out the objects and frame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risk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 words:One Belt and One Road; direct investment; risk governance mechanism
【责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