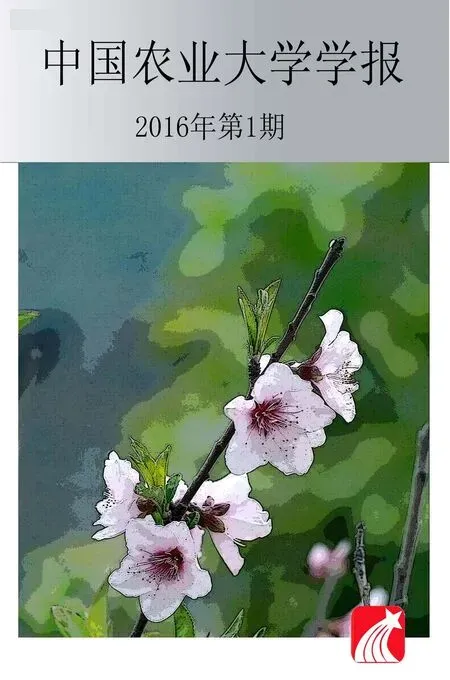从利益输送引导的合作到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K村互助基金会的个案研究
周怀峰
从利益输送引导的合作到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
——K村互助基金会的个案研究
周怀峰
[摘要]文章通过对K村互助基金会18年历程的回顾,探索利益输送怎样引导村民合作以及如何以利益输送为契机组建村民长期合作治理组织的问题,并分析内生于村庄社会的治理组织稳健成长的要件及其实践意义。研究提示,获得组织者的利益输送是村民服从组织并选择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领导者、组织和制度设计是保证村民合作治理的关键;培育合作组织并赋予组织资源是村民合作治理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利益输送; 引导合作; 长期合作; 治理组织
村庄合作治理必须依靠一定的治理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包括以经济资源为主要特征的配置性资源和以政治资源为主要特征的权威性资源在内的组织资源[1]。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村民合作治理所依赖的资源,除了列举经济资源和正式的政治资源外,其他可大致概括为两种:一是领导资源,这些资源由远及近包括传统的中国士绅、近代的乡村经纪人、地方名流和乡村精英、当代的村组干部、退休村干部和村庄能人等等,这些领导资源在村庄合作治理中的角色与行为实践一直是村民合作治理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二是制度资源,这些资源由远及近则包括了“礼俗”、上层正式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与底层的非正式的“听民自便”的自由放任治理实践相结合[2]、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3],以及包括法律在内的正式的制度等等[4]。
上述研究关注各种治理资源及运用这些资源促进合作治理的过程,要么聚焦于村庄合作治理领导权的探讨,要么关注抽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村民合作决策的影响,都明显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治理资源怎样转化为利益输送给村民以引导合作,特别是忽视了村庄治理中经济资源的动员、分配与合作的关系问题;二是村庄合作所依靠的自组织资源问题。虽然有些研究也将村庄集体经济视为乡村合作治理的重要资源,甚至也有人注意到村民治理的自组织资源,但更多的情况则是村庄集体发挥组织农户的基础与能力没有切实的经济和组织资源保障,再者,这些资源怎样转变为利益输送给村民以引导他们合作以及村庄治理资源如何转化成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等系列甚为重要的问题未见深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以K村互助基会的合作治理为例,深入探究治理资源怎样转化成利益输送给村民以引导合作以及如何以利益输送为契机组建村民长期合作治理组织的问题。或许可以为“能否在政府直接治理之外形成一种自发而有效的社会自治并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成功的案例,并推动本土乡村治理组织研究。
一、互助基金会所在的村庄环境
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且无法从中脱嵌[5],因而,研究K村互助基金会不能脱离其微观社会文化环境,因为行动者与其所处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K村位于两广交界的客家人聚居区,目前已被人口约3万人的圩镇包围。2013年底共有905人,包括户籍不在村的村民及其后代,血缘关系都在9代以内,外出人口较多,但都以村为根,多数选择回村养老。常住村民630人,主要从事蔬菜种植、运输、经商和建筑业。除外出精英外,多数村民并不富有。K村中心最显著建筑是民国官员留下来的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林家大院,以前做过学校,1990年代落实政策后其后人捐赠给本村做祠堂和村民公共活动场所。大院散发着浓厚的公共空间气息,不时可见进出往来的村民身影。祠堂大门口左墙分三栏,第一栏零星贴有县、镇政府的有关公告;第二栏是村庄收支明细;第三栏是互助基金借贷信息。右边墙是粉笔板报和村内事务通告栏。大院干净整洁,中间有几排石凳和水泥棋盘桌,常有中老年人或在下棋或在谈天说地,也有不少年轻人在打牌或聊天。祠堂内的三层小楼为主屋,左厢六间房分别为祠堂主司办公室、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棋牌活动室、书报室和网吧;右厢六间房分别为厨房和杂物房。祠堂正门外左边一栋两层小楼为村庄会议室和会客室;右边一栋三层小楼分别是执行委员会办公室、决策委员会办公室和文档资料室。不远处就是学校搬走后留给本村的运动场所。以上机构和场地都有标识,给人正规组织的感觉。
通过对K村的人口、地理位置、空间格局和管理机构的了解,加上作者长期住村的观察、访谈以及在村生活体验可大致判断,K村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村庄,恰恰研究转型村庄更易于发现新的学科知识。
二、互助基金会的发展历程
互助基金源于维修林家大院的余款捐赠,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捐赠形成祠堂基金阶段。维修资金主要由在香港的林家后代捐赠、目前退休回村定居副厅长(时任县长)争取到的文物维修款、建筑包工头林四捐资和其他精英捐资组成,维修完成后余款108 800元。1996年春节,林家后裔建议把余款借给宗族内困难者,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退休副厅长和林四当天就组织外出精英把借贷约定写在祠堂记事本上,包括借贷程序、额度、利率、免息条件、争议解决等等内容,借贷具体工作由祠堂主司“四叔”来做。这样,祠堂基金应运而生。根据保存的书面资料,当年就借出62笔,有59户借款,从1996—1999年,多数家庭借过基金,都按期归还本息。
二是合作形成互助基金会阶段。因村民对基金需求不断增大,2000年大年初一,退休副厅长、副镇长和林四建议把祠堂基金扩为互助基金,此举也得到大家赞同。退休副厅长主持召集村庄精英和各宗支房头的会议,把以前借款约定改为互助基金公约,按照“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增减资不限”原则,新增如下规定:新出资人对出资份额有所有权,按份额得到利息;祠堂基金份额归宗族所有;入会家庭可按银行同期利率得到每次不高于份额6倍的借款,归还本息后可再借;每月初一、十五借还款等等。当时外出精英全部出资入会并出资指定受益至亲30户,另有45户自己凑份。一年后,全部家庭户入会,祠堂基金变成了由宗族产权和私人产权合作形成的互助基金会。
三是互助基金会规范化阶段。1996年的约定和2000年的互助基金公约,虽然都是成文的,但都没有经过全体户主大会表决,理论上还不具备村庄“宪法”的意义,因公约缺陷也导致小部分人颇有微词。针对这种情况,退休副厅长组织外出精英重修公约并提议召开全村户主大会,在全部外出精英和各宗支房头支持下,2003年正月初一召开第一次全村户主大会,表决通过重修的公约。这样,公约就具有了村庄“宪法”的意义,互助基金会运作管理从此有“法”可依。三天后,互助基金会的文书、出纳、会计、总务全部到位,原管理人将工作全部移交给专职人员。至此,互助基金会纳入规范化管理,也变成了一个合作治理的组织。
三、互助基金会的主要工作
(一)制度和文书建设
祠堂基金一开始就有成文制度可循。这些成文制度都是在退休副厅长主持下,组织精英们起草、修改的,靠村庄习俗约束,使用者没有参与治理,但2003年通过新修改的《互助基金会公约》则是K 村治理一个质的飞跃,它为村庄制度建设提供了“宪法”依据,资源使用者依公约形成了合作共治局面。2004年,常务决策委员会建议把户主大会变成全村公共事务大会而不仅仅是互助基金会的会议。当年大会就表决通过这个动议,同时也通过多个村民公约。虽然这些约定文字也不多,但均以书面形式载入互助基金会档案,并且规定每一个公约的废除、修改都须经户主大会表决。至此,K村公共事务治理不仅有组织,而且有据可依,互助基金会变成了全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
文书是把不成文约定成文化,是现代治理的重要标志,对一个组织的历史演变、行为规范和发展定位有不可替代作用。互助基金会领导者有意识地将基金会的公约、会议记录、资产明细、财务报告、各种合同(协议)以及村庄重大活动均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为基金会和村庄管理提供书面依据。
(二)决策组织建设
1996后,K村决策权一直由能给村庄带来实际利益的三个村庄精英担任。2003年后基金会的决策组织得到完善。
一是全村户主大会。户主大会每年正月初一上午在祠堂召开,会上不作具体决策,但对村务和村规有表决权和否决权。大会选举的村民小组长为大会召集人。会议为2小时左右,第一阶段按7个宗支分组讨论,各宗支房头为分组讨论会召集人;第二阶段为大会讨论,每个宗支安排一人把该宗支主要意见在会上发言,相关责任人要对此回应和解答;第三阶段是就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提案做表决;第四阶段是在外出精英中选出决策委员15名。
二是基金会及村务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5名村庄精英组成,其常务委员会由委员会推选。委员会由退休回村的副厅长任召集人,他对村庄贡献最大,最有威望;在任副镇长任第一副主任,因他能争取政府资源;村民小组长林四任第二副主任,因他是本村能人,村民很给他面子。这三人组成常务决策委员会是众望所归。决策委员会每年除夕召开一次大会,主要对基金会和村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常务决策委员会三个人平时就是村庄决策者,其中退休副厅长实际上成为日常决策者。
三是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本村7大宗支的房头组成,七个房头轮流担任召集人,任期一年。这样既照顾到各宗支利益,又保证了代表性。监督委员会负责把各宗支的意见和共识反馈到决策委员会。如果决策委员会不采纳也不解释,监督委员会则可将提案交户主大会表决,表决的结果对决策有最高约束力。此外,还对基金会和村庄财务等进行监督。
四是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文书、会计、出纳和总务四人组成,由常务决策委员会指定,接受户主大会、决策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总务为召集人。出纳主要负责日常现金收付;会计主要是记账与核对;文书负责资料归档、会议记录及档案管理;总务主要负责印章管理和常务决策委员会召集人交办的事务。
上述组织职能明确,各组织及其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及问责机制。各组织之间通过召集人联席会议协调,各召集人在每季度的祠堂拜祖日开碰头会,互通信息而不做决策。
(三)决策管理
K村的决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一是直接建议权,所有成员在每季的拜祖日直接对基金会或村庄事务进行讨论,讨论意见对决策有重要参考,经过三分之一以上户主签名的建议就进入决策讨论。二是间接掌握决策权,由村民把决策权委托给常务决策委员会。三是村民大会虽不具体决策,但对基金会和村务的决策及规章制度有表决权和否决权,当超过80%的户主反对时,决策委员会必须重新做出决策或修改以供下次表决。
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和错用,精英们设计了监督机制和户主大会对精英决策权进行约束。一是约束决策委员会的决策;二是尊重和吸收全体村民表达的异见,发动村民参与决策。户主大会相当于“堵塞交换”的机制[6],形成了对精英决策的限制。村民如果不能达到限制不利于自己的决策,首先可以行使无成本自由退出基金会的权利;如果决策委员会的决策连续两年被户主大会否决,户主大会将行使权力重新选举决策委员会。通过这样限制,达到制止某些物被某些人控制与支配情况的出现,可大大降低不平等和权力滥用现象。虽然从来没出现过否决的情况,但作为一项制度,对决策委员会的权力明显起到制约的作用。
可看出这是一种互动型的公共决策体制,不仅强调参与,更强调成员与决策者互动,不同观点成员可以讨论,也可以直接与决策者协商。这种广泛的、充分的民主和协商使公共决策更体现公共利益。K村这种决策的机制和能力就是自组织治理的标志,强调权力——精英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整合是K村决策过程的核心,K村的决策置权力——精英理性于主导地位,但也将公众——社会系统预设为决策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参与角色,是一种权力——精英理性适度开放、以工具性的公众参与优化的决策,是强调权力——精英与公众共同参与、商谈合作的连续互动社会行动过程。
(四)财务和基金借贷管理
K村在财务和借贷管理方面制定了《互助基金借贷管理细则》和《全村财务管理细则》。财务管理坚持严格的票据手续,坚持月清月结,年终由决策委员会指定人清点核算、公示。通常情况下,财务问题会在季度的联席会议上通报,所有收支及财务细项都要在祠堂公开并备份存档。
另外,还规定决策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均不得从村庄领取任何形式的工资或津贴;执行委员会成员、祠堂主司、村庄保洁员的津贴总额每年不得超过村庄总收入的3%,所有的工作经费每季度公示并接受户主大会受质询。
(五)公共资产经营管理
一定的经济资源是维系一个组织存续和运作的物质基础,更是动员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基金会虽然在初期通过外出精英捐赠和运作取得原始资金,也通过合作扩大了基金来源,但其生存和发展能力一直是精英们考虑的问题。自1996年起,村庄精英利用村庄与圩镇融合的机遇,出租村庄土地、公共房屋和体育娱乐场地,并在圩镇购置商铺用于出租。目前村庄财产出租收入除了公共支出外,年年有结余,结余部分注入互助基金会的祠堂份额,成功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也为K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经济保障。
(六)公共福利和村庄文化活动
自1981至1996年,K村没有集体收入因而没有公共福利。目前村民除能够从基金会借款和分红外,其他福利还有:村内阅览室、棋牌、球类等活动和每月一两次的免费电影;中秋节全村65岁以上老人聚餐;每两年正月初四外嫁女回娘家聚餐;奖励考上大学的村民;大病住院慰问;为逝者举办送终法会等等。此外,还按旧例,每年办元宵灯会、二月二木偶戏表演、清明节开山始祖的祭祀等,这些活动既丰富村庄文化生活,又增加宗族记忆,并起到延续宗族共同体的作用。
四、互助基金会成功的要件
基金会的治理不仅基本解决村民所需借款,而且培养了村民公共精神和合作精神,增强了村民向心力和归属感并形成了良好村治,其成功除了有外出精英捐赠外,还在于具备如下要件。
(一)解决制度供给问题
一种集体资源合作治理的成功取决于制度规则的存在和运行,以便确立稳定的相互行为预期和长期契约合作关系。若正式规则对个体在合作过程中的投入及收益形成明确、成文化契约,则对稳定相互合作预期起到基本作用。若无规则,合作就无从谈起。因此,合作治理首先要解决制度供给问题,包括制度由谁来设计、谁有足够动机和动力设计并能承担相应的组织成本等问题[7]。然而,制度规则作为一种集体产品又决定了其供给存在两个难题:一是组织制定集体规则的本身是一种集体物品生产,市场机制和政府之手都失灵,谁愿意付出额外成本来组织制度生产?这就面临搭便车和机会主义问题;二是其他成员凭啥信服组织者制定的规则并按此规则参与合作?这样,由谁来组织发动、设计规则、承担规则制定成本,又怎样能令其他成员信服并参与合作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因而,找到成员信服的制度设计者来构建秩序并起到组织发动作用是合作治理的关键。
K村客家人的特性决定了村庄精英成为制度设计者,因为他们有能力解决村民个人所不能解决的共同问题并且长期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精英们的资源对村民形成吸附效应,村民对他们都心存感恩,加上精英们不从村庄谋利并且自愿承担制度设计成本,因此,由精英制定规则是众望所归。
(二)内生众人信服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合作治理实际有两个阶段:一是组织和发动;二是实施和维持。组织和发动合作需要活动资金、时间和成员,如何积聚这些必需的资源和成员就需要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开展动员。然而,初始动员的成功与否也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比如人际网络或人际纽带、集体认同感的包容性、集体行动目标的共意性、组织者的动员技术、机遇等等都会对动员成败形成有力制约。初始动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辛的过程,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宣传、动员形成共同意识,如果初始宣传和动员无法形成共意,则合作治理也胎死腹中。合作过程有两类主要角色:领导者和跟随者。由于组织和发动集体合作所需的个体间沟通协调需要成本投入,至少是时间投入。如果没有人充当这种初期组织者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领导者角色,那么搭便车行为将是普遍的,试图通过合作来治理集体资源就难以实现。如果说领导者角色不可或缺,那么谁有能力且愿意带头发动并成为大家都信服的领导者就成为合作治理必须的条件。
K村有明显的、由层次分明的异质性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这就解决了制度供给者和发起者问题。在这个网络结构中,外出精英处于第一层次,常务决策委员会三人是领导者和组织者;七个大宗支房头是第二层次领导者,主要负责本宗支成员事务;每个大宗支又分若干小宗支,大宗支房头指定小宗支房头负责该小宗支事务;小宗支房头处于第三层次;其余村民处于第四层次。这种分层在合作中容易形成领导者—组织者—执行者—参与者—跟随者这样一种原始的初级组织结构,基本上具备正式组织的结构、规则和决策程序。基金会的倡导者和发起者都位于K村社会网络中心和节点位置,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其私人关系接触到所有成员,因此也更容易动员并说服他们参与合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具备了类似正规组织架构,如果不存在一个或若干个具有利他精神的民间领袖或精英并承担起带头人或主持人角色的话,合作也不可能发生。另外,带头人或领导人应该是生存于当地权力文化网络之中的、能令大众信服的人,并能有效地影响到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K村层级结构恰好满足这个条件:第一层次外出精英威望最高,常务决策委员会三人是众人信服的,退休副厅长的话又最顶用,就充当了最高领导者角色。
(三)解决初始成本问题
虽然合作收益决定了合作需求,但行动需要付出成本,合作共同意识即使形成,也并不能自动地或必然地转化成合作行动,尤其是高风险合作。因为集体合作需要时间和资源,还需要有人敢于承担行动失败的风险,这些必要的资源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成员需要人们去组织和动员。没有组织和动员,集体合作就成为泡影。因此,能否实现集体合作还在于是否有人承担合作的初始成本。
首先,外出精英承担合作的初始经济成本。他们承担初始的合作成本包括组织、动员等成本,不少还承担了他们至亲的合作成本,其他合作者仅仅需要支付不限数额大小的份额成本,而且份额所有权属于自己。对跟随者来说,合作成本很小或者不用承担合作成本,所以合作就很顺利。
其次,宗支的大小房头承担了执行成本。虽然外出精英承担了初始经济成本,由于他们大多在外工作,在互助基金会没成立之前,合作治理的宣传、动员等具体工作由谁来执行就是一个问题。虽然参与宣传、动员等活动没有劳务费,但退休副厅长还是能找到各宗支房头来动员合作,而且各宗支房头很乐意配合动员。他们明白合作对自己是有益无害且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而就把动员和说服亲人参与合作是一件造福亲人的事。成立合作组织需要找人,需要做大量说服解释工作,这些房头都乐意这么做,实际上他们就承担了合作的执行成本。
(四)有效的惩罚制度
制度——尤其是附属于它们的惩罚——是能使人们作出的既有承诺得到切实履行的可靠约定[8]。合作制度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没有惩罚的合作制度是无用的。K村互助基金会合作制度的惩罚包括:一是经济惩罚。互助基金会有明确的罚息、本金保障和转借惩罚等制度,惩罚金从违约者的村庄应得利益扣除,这样的惩罚近乎无成本且违约者无法报复。二是声誉惩罚和驱逐。互助基金会规定违约不还借款者将被公示在祠堂并在当年户主大会点名,这样,违约者将成为非议的对象,如果是管理团队成员,还被取消管理资格。在下一年度户主大会召开之前依然未还款者,经户主大会表决认为无正当理由则驱逐出基金会,不得享受基金会福利。
尽管十多年来无人违规,惩罚制度也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但惩罚制度一直保留,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发生作用。这样,人人都预期到违约行为将受到无执行成本的、可置信的多边惩罚,违约者一方面将付出可预见的高违约代价,另一方面又无法对惩罚者施以报复情况下,惩罚机制是有效的,合作容易被维持。
(五)监督制度
互助基金会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团队生产就必然涉及成员监督问题,且监督强度影响产出水平,不同监督强度对应不同产出。基金会的监督至少有三种。首先是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其次村民对管理人的监督。村民与管理者间事实上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隐含合约关系,即管理者受村民委托管理基金和村庄财产。因此,管理人与村民成员的信息对称程度决定了出现委托代理危机的可能性。K村在权力和沟通上不存在等级制度,不强调组织成员间的固定关系模式,它所注重的是以信息和其他资源的共享为目标的网络成员相互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从而形成个体间平等交流、相互支持、合作协调的民主自治运行机制,是一种基于相互合作的横向网络结构。这种结构使成员间信息交流和传播快捷高效,大大降低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委托代理危机。再次是村民的舆论监督。监督本身也是一种集体资源,同样面临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K村就通过村民舆论监督来解决。对于村庄这种社会圈子来说,村民经常闲聊和沟通不失为一种社会控制的理想方式。有关谁诚实可靠、谁好吃懒做或者谁喜欢交际等信息,都会在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中传播开来。这样,监督工作由该群体自身进行,不必由专门的代理人来做。与基金会和村庄有关的所有信息都定期公开张贴在祠堂并存档,村民可以随时查阅。违约信息在村内畅通无阻,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受到其他成员的联合惩罚。畅通的信息和有效的多边舆论监督克服了村民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监督本身面临的二阶困境,也避免了出现“公地悲剧”的集体选择困境。
(六)激励制度
如何有效激励村民参与基金会的合作以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成为基金会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至于如何有效激励个体去为集体多作贡献,根据“选择性激励”理论,每个参与者都应该从集体那里得到回报作为对集体做贡献的奖励[9]。只有当参与者的回报等于或大于集体要求他作出的贡献时,才会继续参与集体行动,否则,参与者就可能产生“偷懒”及“搭便车”等行为。正是K村能以低成本或无成本对不同层面的参与者给予各自所需的激励才使基金会有效运作。
根据激励因素分类,K村的物质性激励指村民通过合作获得各种经济资源;团结性激励指通过合作获得社会资源、社会地位、身份认同等;目的性激励是指通过村庄和宗族的整体发展获得的荣耀感。应该说,加入基金会的成员都受到以上三种因素的激励,但对不同层面参与者来说,三种激励的效用不同。
入会家庭首要目的是获得物质利益,除得到每次不高于6倍份额的借款激励外,还得到份额的利息收入,这等于为村民提供一种积极的“选择性激励”。对外出精英,经济利益的激励肯定不是主要的,他们更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更看重的是他们亲人和熟人的“面子”、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因而团结性和目的性的非经济激励是主要的。宗族提供的荣誉性激励恰恰满足了外出精英回归宗族的团结性和目的性激励需要。此外,他们还获得表达激励,即他们的意见可以在村中充分表达,并且被村民倾听,而表达意见被接受本身就是一种收益和满足。对基金会日常管理者——执行委员会成员,最主要也是物质利益的激励,跟其他村民一样可从基金会借款,还可得到劳务报酬。
(七)有偿使用和最长借款期限制度
互助基金会确定最长借款期限且需还本付息。免费使用必然导致恶性竞争,最终奔向“公地悲剧”。如果没有最长借款期限制,将导致借款被少数人占用而不能周转。正是有偿使用和最长期限不能超过18个月,借款人不仅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借款期限,如果借款收益抵不了成本或借款期满无能力归还就不敢贸然借款。在村民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服务条件下,基金会以同期银行利率,无需担保和抵押,手续极其简单地获得信贷支持,对村民来说是一种应急之需的集体资源,不需要时候就不借,避免了非效率使用,解决了资源使用拥挤问题。
五、经验提示
K村的经验表明,村民事前就能得到组织者的利益输送可能是村民服从组织者并选择合作的前提,领导者、组织和制度设计是保证村民合作治理的关键,培育合作组织并赋予组织资源是村民合作治理的重要保障。领导者在村庄合作治理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既是制度的设计者,也是利益协调者和第三方信任的基石。
K村的经验还表明,村民的合作治理能力可能取决于领导者的公信力和村民共享组织资源的状况。当领导者有公信力且共享组织资源足够多时,领导者动员其关系网络形成“关键群体”和领导机构并承担合作的初始成本就能启动合作治理,村民合作治理能力也因此大大提高;当无领导者或领导者无公信力,村民无组织或无共享组织资源或资源过少时,村民合作治理能力就大大降低甚至无法合作。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合作治理成败的关键,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在村庄社会管理创新中,重建合作组织是村庄治理的关键,能否把村民组织起来并获得充实的组织资源是实现村民合作治理的重要条件。如果事先不存在能为村民输送利益的组织者或组织,村民几乎不会参与合作治理。本身就有资源可输送的组织者或组织是资源动员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因为有资源的组织者或组织对资源具有强大吸附能力,更能为潜在合作者提供参与合作行动的激励,若潜在合作者拒绝对有资源的组织同伴的召唤作出回应,将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组织所能提供的全部收益和保障,这样,最佳策略是选择合作。按此思路,建立一个能够为村民输送利益的组织才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动员村民参与合作治理。
目前很多村庄之所以像一盘散沙,根本原因在于村民缺乏有资源的组织,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如果能培育出为村民输送利益的社会组织并成为村民利益代言人,那么就有可能扭转村民无组织和不合作的局面。虽然目前农村也有作为正式组织的行政村“两委”,但很多“两委”缺乏利益输送能力,很难动员村民合作。可能对于村民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正式组织,而是一些能给他们输送利益的、更为宽泛与综合的、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全方位合作组织。因而,对村庄社会治理的重点不在于上级对村庄的管理,而在于重构村民共同利益基础以重建村民合作组织。没有共同利益为基础,管不成也管不好,如果村民能切身体会到来自组织的利益,就愿意接受并服从组织的规范、秩序和管理。无论领导资源还是制度资源,如果没有形成对农民的利益输送,这些资源都很难起到动员合作的作用。因此,村庄社会治理应以重塑村庄社会组织和共同利益基础为重点,寓治理于村民集体合作和利益之中,化治理于日常村庄生活秩序以达到村庄善治。
那么,转型中的村庄能否依靠村民自身,创造一种以理性和村庄社会为基础的新型组织,由此推动村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也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启示我们:目前的村庄治理既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也不能固守中国的村治传统,它是一种没有理想模式,也没有成型方法情况下根据各自村情所进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摸索。
六、结语
本文为我们展现一个村庄如何利用经济资源动员村民合作并达到自组织治理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资源怎样转变为利益输送给村民以引导他们合作以及治理资源如何转化成长期合作治理组织的问题:(1)当村民共同渴望得到某种资源但无法获得时,此时若有组织或能人输出利益满足村民的需求,这就是发动村民、组织村民的契机,该组织或能人往往成为天然领导者:(2)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理空间和组织资源或许是村庄自组织成长的通则;(3)先就村民需要解决的某一公共问题成立一个组织,然后依托这个组织解决其他公共问题,再把这个组织扩展为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做法。
本文也给村民合作治理研究以启示。我们进一步确认了体验合作和参与观察方法对研究村庄问题的有效性。体验合作让我们以局中人的身份和其他成员互动,真实体验成员的合作决策,为深入了解合作行为提供来自合作者的真实素材;深入村庄的田野调查和体验村庄生活的方法有助于深入研究影响村庄合作治理的主要变量并揭示对合作治理有重大影响但被流行的量化实证研究所轻易遮蔽和排除掉的随机因素。
对个案的初步研究也给我们留下新课题。虽然个案的经验很难推及国内其他乡村,但可管窥出西方治理理论不能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情况,而这正是建构本土乡村合作治理理论的重要线索:(1)我们必须进一步将业已初步整理的文本和记忆的合作与现场的合作进行对话,深入揭示深层的合作机制;(2)虽然接受新思想的外出精英加入有助于建设与传统兼容的治理组织,但怎样吸引和激励他们携带资源回乡参与组织建设需要进一步研究;(3)现代治理组织与乡村传统资源怎样兼容、村庄传统与公共精神或契约精神怎样兼容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4)目前怎样以政府对农村的利益输送为契机,把行政村“两委”改造成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或者引导自然村建立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治理组织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1998
[2]李怀印.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6]Walzer M.SphereofJustice:ADefenseofPluralismand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83
[7]Ostrom E A. Walker J M. Covenants with and without a Sword: Self-governance is Possib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2(2): 404-417
[8]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公共秩序与社会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From the Interests Induced Cooperation to Long-term Cooper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 Case Study of K Village’s Mutual Fund
Zhou Huaifeng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uthentic materials, this paper restores the eighteen-years’ developing process of K village’s mutual-aid foundation, explores the way how does the interests transferred leads to cooperation,and,explores the problem how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giving villagers interests to construct a long-term cooper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analyzes the condition of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actice. The study hints that, firstly, villagers could obtain interests transferred from the organizers in advance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of their obedience and cooperation; secondly, the leaders,organization and the designed system are the key factors to guarantee the villagers’ cooperation; thirdly, cultivating cooper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village and offering them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cooperation governance; lastly, the approach of doing in-depth field research and experiencing the village life helps us reveal the random factors which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ooperation but was easily neglected and ruled out by the popular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Interests transferred; Induced cooperation; Long-term cooper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常英)
[作者简介]周怀峰,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邮编:510006。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广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基于农户融资的定向放贷农村投行模式研究”(编号:2009B070300133)和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以广东省高新区为主导的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创新创业服务网络的构建、评价及决策支撑平台建设”(编号:2014A010108003)的资助。
[收稿日期]201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