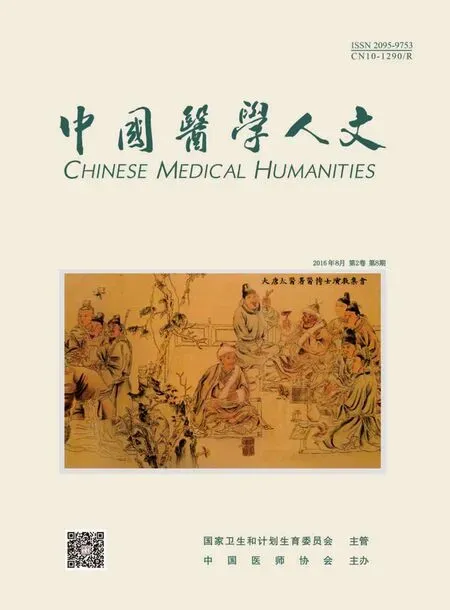告别罗宾逊主教
——在美国做医生的经历
文/乔人立
告别罗宾逊主教
——在美国做医生的经历
那是多年前夏末秋初的一天,是基督教里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不懂基督教,因而记得不是清楚。但是我的病人,罗宾逊主教,选择在那一天告别人世。罗宾逊先生是个教士。他在世时,我随大家称他为神父。但用中文谈起他来却觉得罗主教更来得亲切和令人尊重。样的患者真正病入膏肓,医生早已无力回天。病人由于精神肉体的巨大折磨往往变得难以应付。有人精神崩溃,极度抑郁。有人愤世之极,动辄恶语伤人。也有人变得象个惯坏了的孩子,无论怎样都无法满足他的无休止的要求。管这些病人,每天早上的例检都是一场心理挑战。
可罗主教却是例外,那形同槁木的躯体下包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我每天早上匆匆赶去时,他多半早已醒来,总不忘问侯早安。无论对谁,他浮肿的脸上几乎总挂着微笑,从不为难人。人生活在社会里,生活工作难免有紧张压力,常不自觉地显露在脸上。罗主教风烛残年,但那蔼然的微笑反而给周围人以安慰,有时使健康的人都感到惭愧。
罗主教早已立好遗嘱,他的医疗状态是DNR(DONOT RESUSCITATE),如有心跳呼吸停止,休克等情况,不要抢救,不要用药物或是机器人为他维持生命。医护目标是安慰治疗,只求减轻痛苦。这样,主要医疗手段就是吗啡。吗啡是镇痛镇静的最佳选择,但过量吗啡会造成严重呼吸循环抑制,
罗主教住在九楼南11床。九楼南是VIP病房,都是单间单元带浴室,允许家属陪伴。护士和病人是一对二,照顾得非常周到。罗主教在数月前诊断患有肝癌。教会将他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传教处接回,安排住进芝加哥这所医院。那时我刚开始做住院医,第一个月病房轮转,分管10张床。罗主教是我管的第一拨病人之一。
第一年的住院医叫R1实习医生,负责自己病人的一切具体事项。每天要在八点半早查房之前完成自己例行检查,把每位病人的情况,所有的化验和其他诊断检查结果总结好,订出计划,报告给上级医生,征得同意后再去具体实行。这样每天七点就得去看一遍所有的病人,往往需要将病人唤醒问诊体检。医生紧张,病人也不乐意。
罗主教差不多具有所有晚期肝病的典型体征。肤色黯黄,口唇紫暗,腹涨如鼓。严重的营养不良使肌肉萎缩,皮下水肿。因为失去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无论什么微小的创伤都会造成大片淤血。这致死原因是血压过低和呼吸停止,现在已成为安乐死的标准用药。管理吗啡治疗,医生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调整剂量,达到镇痛的同时防止后者的发生。作为主管医生,我恨不能为罗主教多做些什么。
有一天,住在芝加哥的北美红衣大主教要来看望罗主教。这位大主教德高望重,在教会内外权力影响都很大。他自己也身患癌症,卧病在床,不久人世。他的出动乃是媒体追踪的目标。知道他要来,医院的多位大人物纷纷莅临九楼南。我已被上级医生关照多次,科主任也亲自来查看过病历。就连护士们也都比往日盛装,也许会在电视上露面,或许能得到大主教的恩泽。我的心中甚不以为然,倒不是因为平添了许多跑腿的差事。但事关我的病人,身为主管医生,我当然责无旁贷。
这天直到下午,还没把一天的常规工作做完。九楼南护士台又传呼,说是罗主教要见我。我有些意外,因为罗主教从未主动要求过什么。我匆匆赶去,一路构思着安慰的话。罗主教见面先是道歉打扰,然后提出要做一次腹腔穿刺。原来他的教服因为腹腔积水已不合身。他的口气仿佛是个做错事的孩子,表情使我想起要去见毛主席的红领巾。我稍稍犹豫,因为他的凝血功能不好,最好先输些冷冻血浆。可要等着配置输液,腹穿就差不多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我决定为罗主教冒点险,要抽掉6升腹水,接近生理承受的极限,何况罗主教体质已相当虚弱。针头穿进紧绷的肚皮,暗红色的腹水喷涌出来。一看就是恶性,而且腹腔压力已相当高。我调过身,坐在床上,想挡住罗主教的视线,以免他看见自己身上流出的恶水。
罗主教却看出了我的意图,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是个好医生。”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那第一个月的住院医生生活几乎已让我自信心崩溃。离开医学院已经十年,一直作科研,临床经验为零,不熟悉美国医疗系统,语言半通不通。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每天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晚上还要再看2-3小时的书,这样也只能勉为其难。但是医院要的是能用的医生,不能指望有人会体会你的处境,说实话,当时自己也开始怀疑是否能做下去。罗主教的这句话是我听到的第一声赞誉,何异于久旱禾苗骤逢甘露。
我说了声谢谢,假装埋头在操作上。罗主教跟护士还有一位陪伴的教士聊天,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应着。不知不觉,5升多腹水抽完了。那天晚上,红衣大主教来看望了罗主教,还为九楼南的病人一一做了祝福。而罗主教居然能够走出病房,几乎全程陪同。第二天,人人都仍然兴奋不已。可不是,红衣大主教乃是北美大陆离上帝最近的人,而这位最能代表上帝的人头天晚上就在这层楼上留下足迹信息。看到大家包括罗主教高兴的样子,我的心中也开始重新蓄积起几分自豪。腹腔穿刺虽不复杂,但对晚期肝病的低凝状态,却有相当的危险。要按常规处理罗主教就无法在那天晚上穿上教服,更不可能下床走路。
这之后,我在感情上自然而然地对罗主教多了几分亲近,有空儿常去盘桓一下。原来罗主教很有一番经历。他从神学院毕业便去了巴西亚马逊河下游的热带雨林里向土著传教,一呆就是41年!去时大约还有些行李,回来却只有一身病痛。他没家没业,正仿佛鲁智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听说他有什么非凡动人的事迹,但我相信,能从世界最发达富庶的地方到迄今交通通讯闭塞的地方呆上41年,足以说明罗主教的为人和事业心。他是教士,他的事业当然是传教,他为此献上了毕生的精力而不求回报。我没受过宗教薰陶,看到道貌岸然的人们慷慨激昂或是温柔委婉地称自己是主的仆人常常忍俊不禁。可我对罗主教的为人却是肃然起敬。
罗主教的健康却是每况愈下。肝癌患者平均寿命只有6个月,罗主教已经到了时候。他越来越多地处于昏睡状态,但醒来时仍能得体地对话。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开始向周围每个人反复表示,希望能在那一天告别人世。对于一位行将就木的人,没有人会苛责为什么要选日子。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的末日完全放弃选择权。但罗主教周围的人都有一种默契,希望他的心愿得到满足。他的血压已经很低,已经很少进食。可是能否正好在那一天去世,却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离那天只有三天,罗主教的血压已在休克水平。即使苏醒时,也似乎失去了定向能力。他的唯一亲属,远房侄女玛莎,一位年轻的教授,提出给罗主教输液。充足的体液是维持血压的基本因素。
那天前一天下午,玛莎要求和医生面谈,希望能加大吗啡剂量,帮助罗主教实现心愿,也就是在第二天去世。因为基督教义遣责自杀,玛莎特意邀请了一位神父一同出席,无非表明无论亲属和教会,大家都希望满足罗主教的心愿。可对医生这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那时密执安州刚把一位协助癌症患者安乐死的医生起诉并判有罪,罪名就是协助自杀。罗主教的具体清况实在也就是一两天的事儿,实在不能算自杀。但主治医生不能明说,只答应第二天把输液停掉,然后看清况再说。
第二天早上我5点半就去上班,因为中午全科大查房,讨论我的一位病人。这是我第一次在全科报病例,多少有点紧张,想早些处理完常规工作。那天早上阴云密布,车过湖滨高速,密执安湖上不见日出时的朝霞。湖水沉暗,在不远处便与乌云融成雾茫茫的一片。我的心情也是严肃和说不清,不知道罗主教会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是医生该做的和能做的。和往常相反,我看完别的病人最后才去九楼南。玛莎和一位神父都守在罗主教的屋子里。输液已经在半夜12点停止,但罗主教的清况却相对稳定。他的血压虽低,神志倒还清醒,居然说,早上好。我也用微笑回答他脸上那分明的笑容。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问道,“肝区疼痛厉害吗?”
罗主教回答,“是,一阵阵剧痛。”
我说,“好吧,我把吗啡改为连续点滴。”
我看看玛莎,她和那位神父都严肃地点点头。
我摸摸罗主教的手,说:“GOOD-BYE!”在我心中,实实在在是这话的原意,MAY GOD BE WITH YOU。这是确确实实的告别,因为吗啡剂量再增高,呼吸循环抑制在所难免,这可能是罗主教在人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转身出去,开下医嘱,吗啡静点,每小时5 MG起,可加倍。然后在每日病情记录上写下,因吗啡剂量已不足镇痛而改为连续静脉点滴。这是我第一次未经上级医生写下的重要医嘱。
为此,这一天我都非常紧张,我只是个实习医生,不知上级医生会说什么。再加上大查房报病例的兴奋和兴奋后的松驰,一直到傍晚下班前才又回到九楼南。一看病历,我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两位参与罗主教治疗的主治医生都在我的医嘱上签上了他们的名字,而且一反常态,他们都没写自己的每日病情记录,而只是在我的记录上签名同意。
我去看罗主教。他的血压已经测不出,脉细如丝,气息微微,大约超不过一个钟头了。
玛莎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然后她随我到楼道里,一下子趴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我没出声,只是拍着她的后背以示安慰,任由她的鼻涕眼泪抹在我的白大衣上。我们都是凡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这番交流使我们相信我们各尽所能为将逝者作了些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在生与死两个世界的边缘,无论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活着的人都是站在一起的。
下班的路上,一天的雨已经停止。夜幕降临,芝加哥大都市已是华灯初上。雨水洗过的路面反映着灯光,显得干净而有情调。落日余辉使得天空还很明亮。湖滨高速在市中心急转弯前,笔直地向汉考克大厦而去。大厦顶上有一大片浮云环绕。两根白色的天线杆穿出云上。云上边被晚霞镶出金红的边,正象是西游记里大仙们往返的祥云,在天上人间之间相接。我想,这云一定是到人间迎接什么的。我祝愿罗主教在西归的路上走好。
作者单位/美国南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