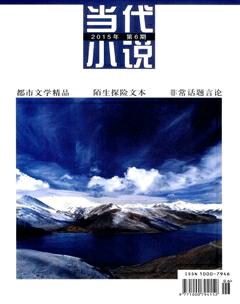恶作剧
陈武
1
电梯是三部,灯都是亮的,说明都在运行中。中间一部停在22,不动了;右边一部正往上蹿,已经到7层了,跟我们无关——如不出意外,它还会往上蹿;左边的一部正往下跑,很快,不停闪动着红色的15、14、13、12……心照不宣的,我和她几乎同时往左边挪一步——我是真挪了一大步。她只是晃一下屁股,或许只做了个挪步的动作罢了。
是的,一层电梯门口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她在我的前方偏左,离我大约有两步的距离,即便是我挪了一大步,也是她更靠近电梯。
我眼睛从显示屏上移开,电光火石般快时间瞄一眼身边的女孩——她其实比电梯更吸引我——脖子细长,肩部裸露的面积太大,白,瘦,骨头一块一块的,汗毛细而密,胸脯不是平,是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裙子不长,在膝盖上边。对了,膝盖很好看,比脸漂亮。表情呢,受气似的,或者是在生气。我知道,漂亮女孩都爱生气玩,拿生气装酷。她不漂亮,凭什么装酷?在她脚边,有两条小狗,不知什么品种,不大,很乖,一黄一黑,分别趴在她脚上。看得出,小狗很享受。
我知道了,她没有像我一样挪步,而是只晃动一下屁股或是扭动一下小蛮腰,是碍于她脚上的两条小狗。要是放在平时,我比较讨厌和狗同乘一部电梯,特别是有的狗还在电梯里撒尿,臊腥烂臭的。但是这会儿,那种讨厌感反而没有了,也许是她脚上的两条小不点太乖的缘由吧。
下行电梯的红灯在3上突然不跑了,定住了一样,已经有一会儿了。右边上行电梯从7开始返回,6、5、4、3、2。经常乘电梯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感觉一部电梯快到了,而先开门的却是另一部电梯,就在右边电梯亮到1时,我移动了方向,准备向电梯走去。几乎同时,我看到左边的电梯也开了门。就是说,两部电梯同时来到一层。我和她,将每人乘一部电梯上楼了。如果一切正常,她乘离她近的左边那部,我乘离我近的右边这部。这也太奢侈了吧,要在平时,说不准拥上一大堆人。像这么奢侈地乘电梯,还是少遇。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女孩走进电梯时,那两条小不点没有随她进去,而是“噌”地蹿进我这部电梯来了——比女孩反应快多了。女孩发出尖叫声,从她的电梯冲出来,迈着小碎步跑进我的电梯,就这几步,加上心急,让她娇喘不停起来。女孩不甘地蹲下,厉声教训抛弃她的两条小狗:“真不乖,啊,真不乖,怎么不跟我走呀?啊?跟谁亲啊?啊?你这骚货、骚逼、臭不要脸,真不知小心,不怕坏人吃掉你?不怕坏人把你拐卖啦?”
我起初看她生气、娇喘地跑进电梯觉得很好玩,待她开口说话时,感觉味道变了。什么跟谁亲啊,什么谁要吃掉她的小狗啊,她是说我吗?我们不认识,更不要说有什么怨仇了,影射我干什么呢?我看着骨瘦如柴的她,恶毒地想,你这小狗有肉吗?好吃吗?我可没那能耐,就算白搭上你,我都下不了手。
我不屑地用鼻子“哼”一声,按一下11。她可能也意识到还没按楼层,仰起脸,生硬地跟我说:“12层。”我点了“12”的按钮,以为她会说声“谢谢”。可她一声没吭,就手抚小狗说:“别怕,乖,别怕啊。”
两条小家伙并没有一点怕意,摇头摆尾地粘在她身上。她还是喋喋不休地收拾道:“小黄,你也不听话啦,别闹!小黑,要死啦,你这小讨厌鬼!”她轻打了小黑一巴掌,因为小黑的两只前爪正好趴在她胸上。
说来真是奇怪,此前一直没有碰过面,自从电梯里的偶然奇遇后,接连几天,都在小区的步行道上或绿化带边碰到她。她每次都牵着小狗,小黄和小黑,有时一手牵着两根狗绳,有时一手一根。对,是牵着的,第一次见到却是散放的。但很快的,小狗就变成一条了。小黑不知是丢了还是送人了。小黄呢,少了伙伴,似乎一点也不乖了,东蹿西跳的,一直不安静,表现出过度兴奋(也或是焦躁不安)的样子。
我会和她在小区的路上或绿化带边相遇,有时是偶尔的,有时是我故意走过去。她还是冷若冰霜,满脸气容,看我一眼或不看我一眼,都像陌路时一样的陌路,如果是无意中瞥到我,眼神中充满了尖酸和怀疑。
女孩不好看,真的。但一白遮百丑,她皮肤是那种玉色的白,很舒服的白。我就叫她小白吧。小白,我默念一句,哑然失笑了,和她的两条小狗倒是匹配啊。不过小白还是小白,小黄还是小黄,那么小黑呢?
做贼心虚,是说做贼的贼。不做贼也心虚,就是说我的吧?自从不见小黑,我怕她真以为是我拐卖了她的小狗,每次碰到她(包括故意走过去),我心里就发虚,怕她找我要狗。她真要是找我要她的小黑,我怎么办呢?可她凭什么找我要小黑?我又没偷!没偷还心虚,说明什么?
那天傍晚,雾霾似乎轻了些,小区散步遛狗的人似乎也多了些,我闲转时,“无意”又看到她。她牵着小黄散步。小黄见到我立即兴奋得一纵一跳的。我假装要躲它,往草坪里退去。她却一松狗绳,追过来了——其实她是在追狗,是小黄牵引她跑来的。
她跟着小黄跑到我跟前时,脸上有了笑容——看来,无论谁,笑还是好看的。她笑笑的样子,似乎要跟我说话。但是我却不敢和她对视,怕她借狗骂人。我脸上做出木木的表情,任小黄在我腿上碰一下,又碰一下。当小黄扑到我身上,两爪扶着我的腿不动时,她还没有开口骂它,这倒是给我一丝“胆量”,我嘴里便向它发出友好的“啧啧”声。
“小黄喜欢你。”她说。
我心里一喜。既然她跟我说话,我就不能不回应了。
“我……也喜欢小动物。”
“真的呀!”她高兴得跳一下,像小黄一样。
太夸张了吧?完全没必要吧?我心里想。看她有些夸张地扭腰,晃屁股,还有满脸的笑,我说:“差不多吧,瞧它,多可爱。”
“不过它不是小动物啊。”她继续笑着说,“它是小黄,不过喜欢动物的人都心善,是不是?我也喜欢。你看小黄对你多好,你们像老朋友了,我都嫉妒了…···那,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晚上要赶飞机,出差…,,,”
2
真是鬼使神差。我要帮一个陌生人看狗了——她叫小白——也许不算陌生了。
答应后我就后悔了。可小白如释重负后的欢笑和快乐。让我没有办法表示后悔,表示后悔就要拒绝。可她笑起来居然有些媚态,眼睛亮亮的,嘴巴里的齿舌鲜嫩而水淋,发声也挺顺耳。总之,她突然变得好看了。她一好看,我真不好拒绝啦。
就是这样,在周五的晚上,包括接连两天双休日,我要和一条叫小黄的狗共同生活了。
真是怪事,小白一离开,小黄马上变脸,对我不亲不近不友好,爱睬不睬的,有时还怒目而视,跟我凶凶地吠几声。我怀疑这才是小黄的天性,是美女故意安排小黄来害我的。你看它,它吠我的时候,好凶啊,看样子,它是真想咬我一口的。我只好哄它吃东西,可它不吃。周六整整一天,我都为它能吃一口东西和它作不懈的斗争。小白临走时给我的狗粮,它闻都不闻,我反复数次拿在它面前,好话说尽了,各种语言上的威胁利诱全用了,它还是不动嘴。我想想,再去买一根火腿肠。它闻了半天,就是不下口。我想起我前任女友骂我的话:“姓陈的,你就像一条狗,跟你再好都没用,闻了半天不下口,别人给你一坨屎,你张口就吃!”
我是这样吗?但前女友的话还是提醒了我——我要对小黄狠一点了。
我把小黄牵到楼下的草坪,让它寻些“野”味吧。只要小黄能吃一口东西,不管吃什么。哪怕是狗屎,只要别饿伤了,只要小白回来不找我算账,我管它吃什么。
小黄见到草坪就不要命了,拖着我到处乱蹿,这里一头,那里一头。小区里路多,亭子多,长廊多,草坪、花坛、水池都很密集,说不定某一处阴暗角落里就会藏着它爱吃的粪便。我干脆就把狗链拿了,让它自由奔跑,自由寻找,总有它感兴趣的吃食。再者说,就是没找到吃的,跑累了,跑饿了,也会吃它专用狗粮的。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事实,小黄跟着我毕竟时间不长,还没到离不开我的时候。我让它自由它就真的自由了,自由得和我失去了联系——小黄失踪了。它一头不知扎到了哪里,毫无踪迹可寻了。
在短暂的惊惶过后,我开始后怕。
接连两天里,找狗成了我惟一的事。
我的经验是,丢东西容易,找回来就太难了,何况是丢了一条带腿的狗呢。小区的夜晚,散步人特多,这里一丛,那里一丛,光是跳舞队伍就有好几拨,算上躲在阴暗处的情侣,小黄应该无处藏身的。但是,任凭我把小区翻了个遍,也不见它的影子。
我站在小区的广场上发呆。发了好长一会儿呆。但是发呆解决不了问题,所谓打盹不能装死,找到小黄才是硬道理。我又抖擞精神,四下张望,没有小黄的影子。但是广场东侧的月牙湖边,突然响起狗叫声。
那是条弧形长廊,有几个女孩在怪腔怪调地唱歌,有一条狗狗在她们周围乱蹿。我远远望着,心里一紧,这不是小黄吗?
我百米冲刺般地跑过去。
长廊下的圆形石桌上,是一个单间的烧烤炉,旁边堆着各种串串、小吃和歪七竖八的啤酒瓶,似乎还有一个蛋糕,不错,是吃了一半的生日蛋糕——他们在举行生日派对。我对一桌的狼藉没有兴趣。我盯着小狗看。我失望了,它不是小黄。它的样子太像小黄了,个头,眼神,还有叫声。但它确实不是小黄,小黄的脖子上有一个拴狗链的金属圈,它没有。小黄的身上是一色的黄,它身上的两侧,掺杂白花色的毛,两眼中间也有一撮黑点,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关键是,它的神态。不是小黄的神态。
“干什么?”一个女孩发现了我,她醉眼迷离地看着我,警惕地问,“干什么干什么?”
她属于丰满型,皮黑,眼大,穿一条短裤,不知是T恤太小还是乳房太大,总之,上身整个变了形。她见我对小狗有兴趣,嘿嘿地傻笑,继续操一口东北口音说:“看好啦?看好也没用,它不跟你去。她们……她们想跟你去哈哈哈,你挑……挑一个?算啦,都带走!”
她说的她们,是指另两个女孩,一个长脸,一个圆脸。长脸的脸色酡红,圆脸的脸色灰白,都和酒精有关。她俩扬着脸,木木地盯着我,眼里充满期待,似乎我一点头,她们就跟我走了。
见我没有反应,长脸女孩指着黑胖女孩说:“求求你大哥,你把胖子带走吧,再贴上一瓶啤酒。”
圆脸女孩听了,抓起两瓶百威,认真道:“两瓶!”
黑胖女孩哈哈大笑着,骂道:“你两个臭流氓、小贱人、大傻逼,看我怎么收拾你!”
但她并没有收拾她俩,而是把趴在桌子上的一个长发的瘦女孩拽起来,推推,拽拽,摇摇,晃晃,对她喊道:“醒醒,醒醒,你老公接你来了,叫你回家吃饭了。”
女孩“哼哼”着,头发散开来,遮住她的脸,她手里还抓着一瓶百威啤酒,作势要喝,却“哇”地吐了一地。
她们轰地狂笑起来。
那条酷似小黄的狗,立即扑上去,舔食地上的秽物,响起诱人的“叭叽叭叽”声。
3
周一早上,我接到电话,是小白打来的。她告诉我,晚上到家,问我小黄的情况。
我告诉她,小黄很乖。
她似乎有些吃惊——我能听出她的惊讶:“很乖?”
我知道我失误了,小黄怎么会乖呢。我赶快改口道:“是啊,比昨天乖多了。”
对方“噢噢”着,表示感谢,问我住11层多少号。她直接来取狗。
我说:“你别来了,我送你家吧。”
她说:“也好,就你楼上,1208,晚上八点就可以敲门了。”
晚上八点,眼一眨,到了。
在八点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着,丢一条小狗算什么呢?她不会计较吧?她会宽容我的吧?我又想着,她会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吧?她会让我赔她的小黄吗?如果赔一条小狗倒是不难,赔一条小黄。我可办不来啊。那么,她会一直哭吗?哭是女孩最好的武器之一,如果她一直哭下去,我还要一直哄下去,把她哄好的难度比找一条小黄还要高啊。我心里不禁打了个寒颤。
后来我发现一个真理,如果设定一个时限,不管是什么事,只要时限到了,人都不会紧张的。掉头不过碗大疤,所以那些被枪毙的死刑犯,临死时都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也就不奇怪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了12楼。
我按响门铃时,整八点。
门开时,我先看到的是一堆顶在头上的湿淋淋的长发,然后才是扬起的脖颈和一张素净的脸,她说:“对不起啊,刚洗了澡。小黄呢?进来进来,换这双。”
她把一双拖鞋踢给我,自己退一步。就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把散乱的长发拢在手里轻放下来了,披散在白色的睡衫上。她脸色清丽,并没有长途飞行后的疲惫,笑吟吟地唤道:“小黄,乖,过来,想死我啦。”
她的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
她没有听到小黄的回应,又问:“小黄呢?”
我说:“你你你……你先坐下。”
“嘻嘻,我光顾找小黄了……你坐呀,随便坐,坐坐,这边吧,我给你泡茶……你要喝茶吗?还是咖啡?喝点什么吧。”
我听出来,她并不是真心要泡茶,只是例行的客套。我想,这样不行,我不能坐下,坐下了,就是想喝人家的茶的,万一她真的泡一杯香茶。万一我真的喝了她的茶,再被轰出去,会更狼狈的。我只好快刀斩乱麻地说:“对不起美女,小黄……失踪了。”
“啥?失踪啦?”
她的表情是夸张、惊讶、疑惑等复合体。再具象一些,她眼睛睁圆、嘴巴张大、鼻孔扩开,身体和两手的造型像直立的四蹄动物,不太稳当。我担心她把持不住,昏厥在地。她果然没有把持住,身体一仰,倒到身后的沙发里。她双手蒙面,趴在膝盖上。我看到她双肩在耸动,但她没有发出抽泣声,而是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似的。我看到她宽大的睡衫滑到了胳膊上,肩和后背大面积的裸露,肩腋处还有一颗黑痣。她的落拓相,完全不顾淑女的芳容了。
我站在她面前,像犯错的小学生,无所适从。
4
我们拿着手电,在小区的各个角落寻找。
小白衣服都没换。她显然急了。刚才,她用一个姿态蒙脸俯身坐在沙发里,半天才抬起头来。我以为她会泪流满面或眼泡红肿,然后跟我勃然大怒。但她什么变化都没有,冷静得让我吃惊。她起身,走进一个房间——我才发现,这是一套四居室的大房子,装潢既考究又简约。考究主要体现在家具和摆件上,简约体现在墙体上。房间很女孩化,适体地摆放各种颜色的鲜花、绿草,还有说不上名目的小盆景,房间里萦绕着一种淡淡的伴随她体香的草香味。她从房间出来,跟我平静地说:“找狗去。”
我明知道这是徒劳,也得陪着。
“房东月底就回来了,房东爱小黄比爱她妈还狠。找不到小黄她非吃了我不可。”小白走在前边,腿脚很灵,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话,“两口子出去旅游了,北欧五国,两个月,还有一周就回了。小黄会躲在哪里呢?不会被人吃了吧?它那么小,那么皮,谁吃呀。”
我听懂了,小黄也不是她的。就连这幢大房子也不是她的。我以为她会抱怨我,责怪我,大声呵斥我,就是大骂我一通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揍我一顿,我也决不还手。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事已至此。她也只能面对现实了。
“房东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特别是女房东,你都没见过那样暴躁的……真的。她委托我看狗,免我半年房租。半年房租是多少钱啊?一万两千块啊……不是钱的问题,我知道她不在乎钱……她想让我帮她看两个月小黄,小黄的祖先是逮黄鼠狼的……那叫什么品种?对啊,小黄会不会去逮黄鼠狼啊?”
她的话不需要我回答。因为她也知道小黄不会去逮黄鼠狼。
“本来我不想委托你……你瞧瞧你……哎,看来我的怀疑是对的,人不可貌相,看来你是个不能托付的人,连一条小狗都看不住……都怪我,怎么会轻易就信了你。”她还是抱怨了,又不切实际地说,“小黄要是你女朋友,你也会撒手让它乱跑吗?你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坏吗?坏人都喜欢勾引漂亮女孩的,而漂亮女孩都盼着被勾引……我真怕小黄凶多吉少啊。”
小白的比喻一点也不恰当,论述也不够准确。但我不准备反驳了。这当儿,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说什么都只能任由她说了。
一连几个晚上,我都被她逼着去找小黄。起初我还乐意,慢慢我就不情愿了。但不情愿也得陪她,她的焦急是真实的。我能看出她的孤独和无助,换位思考一下,我也理解她的难处和处境,还有几天,房东就回来了,她交不出狗,房东会怎么对待她?不会像她对待我这样简单吧?她是拿我没辙,因为我不太可能对小黄的失踪承担什么责任——是她主动让我看狗的。她就不同了。她住在房东家,而且是有契约的——看狗,等于免半年房租。可是这条狗值多少钱呢?我不敢打听,我怕它太贵了,要是值个几十万我心里的负担会更重的。
我知道,等房东一回来,我就解脱了——所有的焦点都对准她——房东不会找我的,她也没理由把我推给房东。
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放松。在第四天晚上,我简直就像散步一样,身边的她就仿佛陪我散步的女友。事实上也有点像,她趿着拖鞋,穿休闲的裙衫,软软绵绵若即若离地傍着我,有时还不着边际地说句夜色多美丽什么的,甚至还哼起了我听不明白的音乐。或许她也知道这样的寻找是徒劳的,无用功的吧。这样的,寻狗,便演变成一种形式了。
到了第五个晚上,我们在小区的各个角落“散步”,已经有好一会儿了,跳舞、打拳、舞剑的人群早散了,就连真情侣们也从暗处走到灯光里,牵手回家了。可我们还到处钻,还到处“小黄小黄”地叫,有时路窄,灯暗,并排走一起时,身体会无意碰撞一下,重一点轻一点都有,这时候她会消除尴尬地说一句:“又白跑了。”我知道她心里是失落的,便安慰她:“明天再找找看。”她也说:“是啊,明天说不定它就主动跑出来了,小黄,小黄……哎,帅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眼面前的东西突然就不见了,发卡、口红或小镜子,找啊找啊,最后发现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我也附和着:“是啊是啊,说不定小黄突然就从哪里冒出来啦。”
说话间,突然响起“汪”的一声,对,是狗叫声。
狗叫声就在我们身侧的小松林里,短促而惊恐。小白紧张地一把抓住我。我也屏息细听,果然又叫了一声。确实是狗叫。我感觉到小白的手痉挛了一下。与此同时,叫声也一声连一声,受压迫、受折磨一样。小白兴奋了,她手腕一带劲,领着我往林中钻,叫道:“小黄小黄小黄……”
我们惊呆了,眼前不是小黄,在路灯的暗影里,是一对躺在草地上的情侣。
我们被骂了句神经病。这是应该的。同时我也想骂他们一句神经病,怎么像狗叫似的,而且还真有点像小黄的声音。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怪我。”她突然说。
这有什么好怪的。我心想。我们已经走到月牙湖边了。一路上她都不吭声。我也有些内疚,同情和怜悯占据了主导,觉得对不住她了。月牙湖的水有一米深,有栏杆围绕着。她靠在栏杆上,满心失落的样子,苍黄的路灯照在身上,像受气离家的小媳妇。我心里一软。情不自禁地拍拍她的肩。她却做出一个让我吃惊的举动,轻轻靠到我的肩上了。
透过薄如蝉翼的小短衫,我感觉她肌肤水一样滑腻和冰凉,而且还有些微微的战栗。
她把脸贴在我的肩窝里哭起来。
我安慰道:“小白,别这样,车到山前必有路j”
她听了我的话,突然不哭了,一动不动靠着我。
我又说:“小白,怪我……没看好小黄。”
我感觉她比先前平静多了。
又过一会儿,她突然推开我,虽然没有太用力,也是坚决的,然后,顾自走了。
她几乎是快速走过文化广场的,明亮的灯光下。她白色的长裙飘逸而浪漫。
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温馨,也有一种好奇,,女孩不论相貌如何,温柔起来都是可爱的。好奇是因为她怎么会突然离去?是觉得我们的亲近过于唐突?可能吧?
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第二天,她不再喊我去陪她找狗了。还有几天,房东、也是狗主人,就要回来了。她怎么去对付他们呢?我不免地担起心来,同时也迁怒于那条小狗了,觉得它真是个祸害。
又是一连几天,我的手机不再接收她约我找狗的短信。我知道,如果按照她给的时间,她的房东,也就是狗主人已经从美丽的北欧旅行结束回来了。她说不定正受到主人的虐待呢,就是被赶出家门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补交了房租也是有可能的。我是不是要去看看她呢?哪怕给几句无关疼痒的安慰,对她也许会很重要的吧。
5
我给她发了短信。
没想到她的短信回复是约我到她家去的。我有些纳闷了,莫非她房东还没回来?或并没有追责她丢了小黄?也许一切都被她摆平了。
我按响门铃。
她依旧穿好看的家居衫来开门。开门的同时,一条黄色的小狗在她身边跳起来,蹿得比她还高,差点吻到我的脸。我大吃一惊,说:“这不是小黄吗?找到啦?”
“是啊,找到了。”
“怎么不对我说一声?”
“嘁,别装了。”她堵在门上,并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似是而非地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姓白?”
“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啊?”我恍然大悟了。她不仅皮肤白,事实上也真姓白。我实话实说,“你皮肤白嘛,你叫它小黄,还有那个小黑,我就叫你小白了——什么时候找到小黄的呀?”
她依旧似笑非笑地看我,说:“真逗,你还知道我做国际货代。你调查过我?”
“我不知道啊?你做什么工作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对我说过。”
“我是没说过,但这些你都知道,你说过的,虽然很含蓄,但你是说过的。”
我想不起来了。这真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告诉你吧,我还知道你三十四岁,未婚,曾有七个男友,你身高一米六四点五,体重四十六点五公斤。这房子也是你的……”
我看到她惊愕地张大了嘴。
“我说对啦?”我也惊愕了——我可是随便胡扯的。
她痛苦(确实是这种表情)地看着我,抬起双手,圈住我的脖子,哽咽着说:“你不是人吧……你是神……神经病,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不识趣的小黄,“哼哼”地围着我们转圈,和小白发出的声音相映成趣。
这一切太突然了。小黄找到了。她果然姓白。我没说过的话她赖到我身上了。我胡扯一句居然说对了。生活怎么会是这样?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她还说我神经病,还让我不要怪她,这一切都让我糊涂了。
生活确实就这样延续下去了。我成了小白家的常客。我也常常带着小黄在小区里遛遛了。小区的草坪上,花园里,常常会有我和小白小黄一起散步的身影。
小白三十五岁生日前两天,要请我去吃饭。我实在是因为要出国,无法去。但是我似乎又不能拒绝她。我怕我的真话被当成谎言。
我只好改了机票。
她没有在家里举行生日派对,也没有在饭店大吃大喝,而是在小区月牙湖边的长廊下吃烧烤。我去的时候,她们吃开了,啤酒大概喝了不少,横七竖八地已经散落了一地。她们是谁,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又似乎全都面熟。我想了想,没想起来,也就懒得想了。但那个黑皮肤的矮胖女孩,还是提醒了我,她们就是那天我找狗时遇到的醉酒的一伙人。
我一坐下,就被她们抹了个大花脸。
也不是我过生日,抹我干什么呀。但我显然是没机会伸冤的。还是那个皮黑、眼大、穿短裤的女孩,抠一把蛋糕上的巧克力,冲我的脸就来了。这下她没有得逞,我跳着躲开了。她跺着脚大叫:“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真不解风情。”
不知趣的小黄蹿到她腿边。她把“怒气”全撒到小黄身上了,左一把右一把,把手上的奶油全抹到小黄身上。小黄立即就变另一副模样了。
那个穿齐臀小短裙的长脸女孩,微红着脸,命令我道:“过来!”
“干吗?”我警惕地看着她。
她见我没动,走过来,迈着小碎步,手背在屁股上。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她绕过桌子,到我面前,说:“别动啊,乖,让我抹一下。”
我果然就没动。
她也没客气,把手上的蛋糕全抹到我脸上了,这里一把,那里一把,挺认真的。她脚边的小黄往她腿上蹿,被她一脚踢开了:“去,别闹啊,让我玩个够。”
可小黄还是不知趣地往她身上蹿,似乎要吃她手里的蛋糕,她又给了它一脚,冲小白喊道:“你这个臭流氓、小贱人、大傻逼,光顾喝了,你管不管你家小黄啦?我白收养它十来天了,它这么不给我面子。”
一边的小白,拿着一瓶百威啤酒,略有醉态地笑得前仰后合了。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