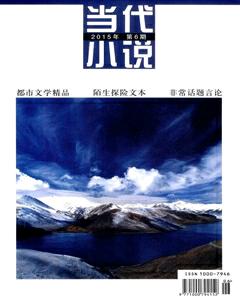我的朋友卡夫卡
徐东
十年前,我和同事杜朴成了朋友。
我们还同居过一段时间。闭上眼睛想起他时,他就鲜活在我的脑海中。从外貌上看,他并无特别之处。不高不矮的个头,不胖不瘦的身材,五官平常,穿灰色调的衣服,普通得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他却是特别的,仿佛那样平淡无奇正是他的特别之处。他让我想到卡夫卡以及他小说中的人物,我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卡夫卡。
卡夫卡是封闭的,缺少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
卡夫卡经常一个人默默从单位走回住处,又从住处走向单位。别的同事,几乎也不太乐意和沉默寡言的他打交道。我们那样走路。走在都市中,人群里,那种存在如同在被谁默读的诗歌。我写诗,总想发现诗性的东西。
有一天,不知受到什么事物的触动,我竟莫名地对卡夫卡说:“如果我们将来分开了,或会邂逅于北京的某个街角。”
卡夫卡惊诧于我能说出那样的话,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也相信,只要我不断地走下去,就会遇见她!”
卡夫卡言词闪烁中的“她”,是他暗恋的梅琴。
那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梅琴,很好奇卡夫卡爱着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卡夫卡说,梅琴在他的心目是位仙子一样的女孩,也在北京工作,只是他不知道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做着什么。他从大学时代便开始暗恋她,大学毕业后,他从同学口中得知梅琴来到了北京,于是也来到北京,希望能在偌大的北京城里与她不期而遇。
“为什么不能通过同学,或别的方式去找她呢?”
卡夫卡说:“那是不一样的。”
卡夫卡一直单身,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一直在期待着梅琴的出现。我想,如果那一天真正来到,他面对她也许会热泪盈眶,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来。
夜色降临时。我也会从房间里走到街上,看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我爱着孤独和寂寞的他们,像爱着所感受中的,他们对于我的陌生,以及潜在的无限可能。我想为陌生的他们写诗。那时的我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价值连城的神奇图画,都有可供传诵千年的诗篇,每个人都有找不到倾听的耳朵的秘密。
卡夫卡便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他在城市中孤单行走,看到一些风景,路过一些人。这是个事实,我发现这个事实,想象着卡夫卡带着神秘心事,走过一段段路,遇到一个个陌生的人,并与他们擦肩而过。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会不会有一种隐隐的,或许并不被感知的痛呢?我想,这会是有的,每个人都那么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向死而生。
从认识卡夫卡始,我便开始想象他。我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我和他面对面坐着,他伏案工作,有时抬起头,我总能看到他脸上有着淡淡的笑,那笑,让我感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奇怪的人。我喜欢那样的他,有时故意没话找话,约他一起去吃饭。
卡夫卡一开始是拒绝,我再三邀请,最终他还是和我一起去吃饭了,于是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成为朋友,在一起时,总是我的话多。我猜测着他的内心,他的存在,向他求证我的猜测是否正确。我猜卡夫卡也在偷偷写诗,他笑着摇摇头。我没话找话,说他心里有个喜欢的女孩子,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猜他在写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他想了想,点点头。
卡夫卡说他在写自己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
“你没有发现吗,孤独是美好的,它使一个人自我,使人能够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想象和感受中的世界里。”
我赞同地点点头,觉得他特像卡夫卡,像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卑微的自我,独自发着光芒,也不在意谁看见。从那时起,我便称他为卡夫卡。
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我把收藏的卡夫卡的书借给了他。他认真看了,算是认同了我为他起的那个外号。
我领到一笔稿费,在外面租了房子,单位不久后也取消了集体宿舍,给我们每个人三百块的住房补贴。卡夫卡一时没能找到理想的住处,我就邀他和我暂时同住。
我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月。我们一起乘地铁上班,一起坐地铁下班,一起寻找吃饭的地方,一起聊天。那时是秋天,风常会在黄昏时吹起。吹动的沙尘弥漫在空中。即使是在那样的天气,卡夫卡仍然会独自走出房间,把手插在裤袋,迈动着猫一样轻巧的步子,在大街上莫名地行走着。从外面走进房间里时,身上似乎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那使我相信,他睁着的那双不大的眼睛,眼睛中有爱的光芒可以穿透城市的每一栋楼房,抚摸到每个女子的秀发与面庞。在那样的过程中,我怀疑他未必就异常地渴望梅琴的出现,或者说梅琴仅仅是他幻想的一个爱情对象。事实上,他爱着所有的女子,所有的人。在那样的他面前,我幻想自己变成上帝,让他暗恋的梅琴出现在路上,被他看见,然后开始真正的恋爱。并最终结成恩爱夫妻,白头到老,过着平凡生活。
卡夫卡后来嫌工资过低,找到了新工作,从朝阳区的定福庄搬到石景山去了。
我们分开后的一年多时间,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每一两个周,通一次电话。有时是我打过去,常常开口便开玩笑似的问他,有没有遇见梅琴。每一次,卡夫卡都认真地回答说,没有。卡夫卡在他的想象中设置了与梅琴见面的重重障碍,想象了正是因为来之不易的邂逅相遇,他们的爱情才因此而变得伟大和感动。
“亲爱的卡夫卡,你真有趣,可以不想她吗?为什么不试着去接触一下别的女孩?”
“梅琴就是梅琴。”
“她应该嫁人了吧?”
卡夫卡坚定且恼火地说:“没有,肯定没有!”
“有时间我过去看你吧?”
“我去看你,也可以。”
“你总是说有时间过来,总是不见你来,你现在没有时间吗?”
“你知道,我是一个活在内心世界里的人。”
我应该去看卡夫卡,自从他搬到新的地方,一直没有去过。
卡夫卡一直在写长篇,那时大约写了一百多万字了,仍然没能给小说起个题目。同住时,我曾看过一些章节,觉得他的长篇将来很难出版。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写得好,好在和别的小说不一样。他写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想象,一段一段的,像散文,像诗,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看到他的小说,我更加相信给他取的“卡夫卡”外号是正确的了。
卡夫卡工作了多年了,有了一些存款,家里也能支持一些,可以在北京通州买房子。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有了房子以后,再遇到梅琴,会好说话一些。她问我,你有房子了吗,我就告诉她,有了。”
卡夫卡想象着与梅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系,他和想象中的梅琴一直在相处着。他与梅琴一直在对话,谈论着四季变化,谈论着都市中具体的事物在内心的映像。他在试图通过想象建构一个世界,有一天梅琴能够走进来。
在一个双休日,我炖了一锅土豆烧牛肉,想让卡夫卡过来和我一起吃。
我打来电话给他,他却说:“我准备去香港发展了,在那儿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我还可以练习英语口语能力,将来还可以到欧州去生活上一段时间。”
“可是,你还没有遇到你的梅琴啊!”
“我不想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了。我想换个地方,一步步到世界上去。”
“嗯,到世界上去?”
“我需要走动,走动可以带动我,可以使我遇见我想象不到的人和事。在陌生的地方,也会遇见更多陌生人,他们或许能成就我,改变我。”
“嗯,我炖了土豆牛肉,你过来吧,我们好好聊聊。”
卡夫卡答应了。我挂了电话,胡乱想着一些人和事儿,等着卡夫卡的到来。
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象着有个陌生的女子出现,来填补我内心里无边无际对爱的渴望空洞,但一直没有。在孤独时,我幻想过在大街上手拿一束玫瑰,真诚地微笑着邀请一个我喜欢的女子,让她爱上我。我愿意退回孩子的天真与单纯,向一个透明的女子说出那样的话。我并不能真正那样去做,因为我在渴望爱的同时,也在渴望着彼此赤裸,合在一起,而那会破坏我的完整性,我的自由。我有些朋友,他们有许多办法让陌生女子成为他们的情人。我认为那个过程不一般,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儿也不一般。
卡夫卡在女人们面前无比羞怯。和我在一起时,卡夫卡几乎每一天都会向我说起梅琴,每一次说起梅琴的时候,脸上便泛起少男少女才有的那种潮红。我觉着梅琴在卡夫卡的心中超过了真实的梅琴的存在,比梅琴真实的存在更加丰富和鲜明。以至于卡夫卡说得越多,我越发的不相信有梅琴这样的一个女子存在。卡夫卡却坚定地认为,梅琴的确存在。他从来没有拉过她的手,不过他们是说过话的,那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卡夫卡似乎怕记忆出错,也曾经一次次地向我复述他们曾说过的话。
十年前,在大学校园里,一个下雨天,卡夫卡发现自习室里的梅琴没有带雨具,冒雨去宿舍取了来给梅琴。
“给你。”
梅琴犹豫着接过来说:“谢谢你!”
卡夫卡转身冲进了雨里。
梅琴微笑着把雨具还给卡夫卡后,又对他说了声“谢谢”。梅琴对卡夫卡所说过的话,大约不到十个字,卡夫卡却暗恋了她十年。
卡夫卡来了,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也许我会在香港谈一个女朋友,在北京,我不想在我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的时候,遇见梅琴。”
我忍不住笑了,说:“你想得可真多,卡夫卡,你真是太有意思了。嗯,不过,如果换个地方可以让你立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会为你高兴的,去吧。想去就去吧。”
“我真是感到累了。”
“是啊,那么想象着一个人,是累。”
“我感到老了,那颗心在变苦。”
“我理解。”
“十年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越来越无法把握我在这个城市中的存在,无法把握我想象中的梅琴与我之间的关系。我的创作也进入了瓶颈,无法再写下去。”
“那就不写,去扑进现实生活的怀抱吧!”
“可是,我还是有些怕!”
“怕什么?”
“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真正醒来后会不会很不适应?”
“没关系,再说你又不是一直在梦中,你以前工作做得不错啊!”
“是啊,我现在是该醒来了,也许,是醒来了。因为,因为我现在竟然在希望自己变得有勇气。我想要做一个花花公子。”
“哈,哈哈,你太有意思了!”
卡夫卡并没有那么快去香港,他需要在香港找接收单位,之后又要回家乡办通行证。他可能也不会变成他所想要成为的花花公子,做不到。他后来向我承认,那天他是在对我开玩笑的。他实在是太苦闷了。那时他辞了职,仍然在租来的小房子里继续写小说,那时他大约写到二百万字了。他在电脑上写,有时会发给我一些章节。看了他的小说,我觉得一部只有两个人的二百万字的小说。太了不起了。卡夫卡所描述的都市,是他的国,那个国像一个个梦境组成的,有时会有一场细雨绵绵,有时又会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卡夫卡决定去香港的前一天要来见我。吃过晚饭后他便从石景山出发了,沿着地铁线路,慢慢地朝我住的方向行走。有许多次他想坐车,没有坐。走到深夜时,没有车了,他也没有想要打个的士。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正在穿过整个北京城来见我,不过,不会那么快能见到我。我劝他打个的士过来,他没有同意。他走得很慢。他要走得慢一些,仔细观察经过的楼房与人。挂掉电话,我想了想,也走出了房子。我当时在想,或许我会在路上遇见他。
大约在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在双桥地铁站附近果然遇见了。灰黑一片中走来一个他,我站住了,在等着他走过来。卡夫卡走过来,我迎上去与他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我的泪却莫名地流了出来。
我们一起打了个的士,回到我的住处。拉亮电灯,看着卡夫卡,我感到他的脸和目光都是冰凉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也是冰凉的。我的心怦怦跳得比平时快了许多。
卡夫卡搓着手说:“啊,北京真大啊,从西到东,那么多楼,我不知道梅琴住在哪个楼上。我边走边想,我会给她最后一次机会,虽然我明明知道,我不会遇见她。”
“还好,我们遇见了,可惜我不是你的梅琴。”
“我的生活像小说,可这并不是在虚构。这是真的,现实世界里难免会有些遗憾。是啊,是啊,我真没想到,我们会相遇了。以前你说过,我们会在北京的某个街角相遇。”
“是啊,想要为此流下两滴热泪吗?”
“谢谢你,真的。”
我有点爱上了卡夫卡。我当然并没有和卡夫卡相爱,不过,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男子产生爱的感觉。
卡夫卡走时,我并没有去火车站送他。我不喜欢送人。卡夫卡到了香港之后,给我来过电子邮件。告诉了我梅琴工作的单位和电话。他说大学时的一位朋友无意间透露了梅琴的工作单位和电话。他打过一个电话,她接听了,一听他就知道是她。可他什么都没有说,挂了。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他怕和梅琴见面,怕对她说,他爱她。
我不知道卡夫卡为什么要告诉我梅琴的单位和电话,不过,我的确想见一见梅琴。
我见了,我向她说起杜朴。而她彻底忘记了一个叫杜朴的人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